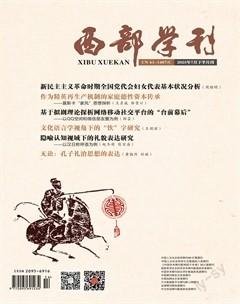清廷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
摘要:首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于1909年开始,起初由外务部全权负责,后因朝局变动,学部不断积极介入选派活动,形成了由外务部与学部两部共管的局势。在商讨细则的过程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导致选派细则难产。由于美国的干预,最终方案参考多方利益制定而成,外务部与学部的矛盾也不得不通过“平分名额”的方式加以制度化的妥协。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是清末新政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斗争的缩影,反映出当时清政府中央部门间权限划分不清及利益团体利用制度漏洞徇私舞弊,为晚清之后的乱局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庚子赔款;外务部;学部
中图分类号:K257;G64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4-0128-04
The Debate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First Group of Indemnity Stud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Liu Jianpeng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03)
Abstract: Under the Boxer Indemnity, the selection of the first group of indemnity students to the USA began in 1909. Initiall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as in charge of the selection, but as the dynasty changed, the Ministry of Academic Affairs actively intervened in the selection activities, creating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se two ministries were in charge of the selection activities together. During the rule-making process, there was a fierce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forc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ettle the selection rules.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al plan was formed with reference to many parties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se two Ministries had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mitigated through the “equal sharing of quotas”. The dispute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demnity students to the USA was a microcosm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h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s New Deal, reflecting the unclear delineation of authority between the centra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system loopholes for favoritism by the interest groups, which posed a hidden danger for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e Boxer Indemnit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Ministry of Academic Affairs
1908年5月,在中国三任外交官及美国非政府人士的筹措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清政府围绕这笔退款的用途展开了争论,最后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及国际形势出发,决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直到1909年10月,首批庚款留美生被派出,历时一年有余。其中时间虽短,但却在晚清政局中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这反映出当时清末新政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展现了当时历史局面的复杂性。
一、美国退还庚款与留美计划的确定
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签署了最为屈辱的《辛丑条约》。根據条约中的赔款规定,美国应得的赔款是三千两百多万两白银,折合美金两千四百多万元。利息共约两千九百万美元,本息总共约五千三百多万美元。当时,如何使用这笔赔款,美国朝野上下颇有一番争议。国务卿海约翰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出发,带头表示“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可以考虑退一部分[1]。
1907年初,驻美公使梁诚通过运作与其深交的内务部与工商部主事者格斐路与斯特劳斯向美国总统发起提议[2]。梁诚紧紧抓住时机,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应诺,美国将多得的庚款退还中国。后又经周自齐、伍廷芳两任驻美公使筹措,终于敲定了美国首次退回庚款议案。1908年5月议案正式被通过,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 655 492.69美元,余下10 785 286.12美元退还中国[3]。
在美国通过退还庚款议案后,美国退款已成定局,那接下来就是退款用途的问题。当时国内对退款用于何处一时争端不断,国内各势力对此虎视眈眈,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人想借庚款修路来实现其扩军计划,清廷老官僚徐世昌主张用其办银行来开发东北三省以应对日本的侵犯。
然而由于退款的自愿性,此事的决定权自然在美国手中,这些计划统统被美方所反对,一是日本听闻中国要借此退款来抵抗日本的消息后,与美国积极接洽,最终双方结成同盟,美国选择了联合日本而舍弃中国,所以断断不会同意损害日本利益的计划;二是美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教育活动从而进行文化沟通,最终达到商业上的成功。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4]。这种想法从美国传教士使华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培养出来的学生一直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美国坚持用退款帮助中国办学,并表示希望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担任公职的愿望,借此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由此,庚款留美计划得以确定。
二、外务部与学部的斗争
当时,此事被正苦于没有经费的学部获悉,借此时机积极介入退款的具体流向事宜。但学部发起的提议被外务部榷算司阻挠,并致函度支部度支部:官署名,成立于1906年,清代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主管官为度支大臣,另有左、右侍郎和左右丞、左右参议。声明称减款之事尚未确实,要求度支部搁置学部派款要求[5]。由此,外务部和学部拉开了争夺退款使用权的帷幕。
外务部成立于1901年,它的前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当时常与西方交涉,位列六部之首,外务部常常有侵犯别部职权之嫌。学部成立于1905年,统一管理全国教育。学部是一新成立的部门,职责划分亦不明确,所以常与其他中央部门相互掣肘。关于学部各项收入的性质,除了学部俸银及原由户部拨发的八旗学堂经费与国子监膏火外,大学堂、学务处与学部的入款不在部库支出之列[6]。学部承受新旧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任,苦于没有教育资金来源,没有保障,故积极争夺退款的使用权,以期作为学部的经费来源。
1908年,庚款留学事项提上了日程。7月,外务部先后与驻美公使伍廷芳、驻京美使柔克义商量了具体派遣方案。10月,公使柔克义在给美国国务卿鲁特的信上附了袁世凯制定的具体留美的章程草案。从此草案中可以看出,外务部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学部则负责一些甄别资格考试等微末事项。甚至也有报刊爆出外务部想直接越过学部,全权负责庚款留美事宜,这些无疑对学部的处境来说是恶劣的。
鉴于这个情况,学部官员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活动,企图扳回一局。从当时报刊中学部出现的次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除了从舆论上占领制高点,学部也率先对各省发出了选派留美生的消息,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安徽就是在得知学部发出的消息后,选送了六名学生来中央[7]。
随后因朝局变动,学部与外务部关于选派权的争夺也有了一些变化。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病逝,中央大权转移,素对袁世凯有嫌隙的载沣摄政,上台伊始,外务部的幕后大佬袁世凯就被罢黜,外务部的特殊背景不复存在,选派权争夺的优劣之势急转直下。
然而,在庚款留美选派权的争夺上,学部很好地利用了朝局的变化,对于外务部进行有力的打击,挽回了一局。随后有外刊爆出,学部将全权负责选派之事。但其中涉及与美外交事宜,因此外务部协同办理[8]。到此,庚款留美生的选派进入了外学两部共管的时期。
庚款留美选派的归属权确定后,摆在外学两部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派,即选派方式,具体包括选派人数、办法、分配学额等方面。外学两部在选派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以梁敦彦为首的外务部主张效法1872年的留美幼童,选取年少学生进行彻底的西化教育。梁敦彦还曾建议送上千年少学生直接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分配各地,之后在地方上直接完成改造。分管学部的张之洞,以其《劝学篇》而得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便是出自其手。因此,以张之洞为核心的学部主张选派有中学根基的学生前往,张之洞的这种态度可以从当时的相关报刊中窥察一二。《大同报》报道称:“张相国与荣尚书会议,凡出洋留学者多半聪颖少年,遽行擢用殊为可惜,务须设立通儒院,以经史为主,凡留学归国者,令其入院肄业,庶几中外学识融会贯通,体用皆备矣。”[9]从中可以看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在这里表现的很明显,他主张设立通儒院,让归国学生在此接受经史的熏陶,肄业之后才能得到任用。
外学两部官员关于如何选派留美生的意见分歧,与他们各自所出身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关系。梁敦彦是1872年晚清所派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后官至外务部尚书,从幼童时期就在美国学习与成长,对西方教育有莫名的好感,主张全盘西化教育,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归为激进派;而分管学部的张之洞,它出身于旧科举,14岁中案首,不满16岁中解元,在27岁时中探花,这种经历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也不多见,因此他对中学、功名看得非常重。他担忧西学教育过于膨胀,会对中学教育产生打击,因此极力反对梁敦彦等人的主张,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归为保守派。他们身处的教育体系不同,导致了他们的教育理念也相差甚远,最终这种理念演变成了对派遣细则上的针锋相对,如年龄、功名、考试资格等,这也是导致派遣细则难产的主要原因。
外務部与学部之争遂演变成激进与保守之争,态势也愈演愈烈。1909年3月,《新闻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文章[10]。从这篇批判文章可以看出,这篇报道将矛头直指以留美幼童梁敦彦为主的外务部。可以总结出两部的主张与争端:就年龄而言,学部倾向派遣大龄的学生,而外务部倾向派遣低龄学生;就资格而言,学部必须要中学校文凭的学生才具备入学考试资格,而外务部倾向不拘一格招人才。
三、制度化妥协与庚款留美生的考选
1909年夏,清政府在北京侯位胡同正式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利用退款向美国选派留学生,同时也是外学两部制度化妥协的外在表现,即协商场所。该机构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外务部与学部之间理念、利益的较量,最终以总办身兼两部身份,并各派一名会办的方式而妥协。
在两部联合上奏折《收还庚子赔款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事》之前,游美学务处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11]。1909年5月,外务部决定任命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总办选派庚款留美生相关事宜。周自齐有留美经历,并且外交工作经验丰富,参与过庚款留美的谈判,由他出任总办一职应该说是十分合适的。创办初期,在人事安排上,外务部主张设一名总办,两名会办,但分管学部的张之洞似乎有不同意见。8月8日,张之洞为游美学务处人事安排事致函外务部:
“敬复者,前奉惠示,敬悉一切。游美学务处派周参议为总办,由两部会同札派各节办法,均极允当,惟事关两部,似以各派总办一人察承两衙门堂官会同办理此事,较为灵捷。前在枢廷已与那中堂商妥,贵部派周参议,敝衙门派杨郎中熊祥,现拟仍照前议,派总办二员,即如尊议,由两部会同札派,仍请贵部主稿,以便早日派定,及时创办。既派总办二员,自无庸再派会办,拟改设为书记官或文案二员,专司办理华洋文牍,即由两衙门各派一员分司其事,总期同心合力,以济要公,即请执事裁定示复。”[12]
从信中可知,张之洞开信函开头表示由周自齐任总办,两部会同札派各节办法,都极为合适。但后来又提出,两部各派出一名总办,并会同办理此事,才较为妥帖,并称已与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统一意见。
张之洞与那桐谈妥两部各派一名总办,这给外务部出了一个难题。外务部另辟蹊径,在8月9日致函张之洞,称“拟改派本部后补主事唐国安为总办,与学部所派杨郎中商同处理一切”。对于外务部这一挑衅举动,张之洞十分恼火,复函外务部拒绝唐国安出任总办,但這也让张之洞有了新的想法。学部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时也为符合两部共管的规定,主张由周自齐身兼两部之职,总办庚款留美的选派事宜。至此,游美学务处人选派定,总办周自齐、两会办为范源濂、唐国安。学务处总办与会办之争到此结束。
在此之前,美国对此做出过预期。驻京美使柔克义认为在明年秋天之前,中国庚款留美生就能进入美国学校就读。1909年5月,根据与清政府的协议,美国大使馆向清外交部发出照会,并派中国事务参赞丁家礼为代表,帮助选拔学生。大多数美国学校都是在九月份开学,但直到1909年6月,中国也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派遣计划。柔克义因此照会外交部,严加申斥,并称如不从速派遣留美学生,请交还所退庚款。
面对着庚款被退回的威胁,外学两部不得不暂时妥协。外务部与学部联合起草的《遣派学生赴美办法大纲》,得到了朝廷的赞同。这个大纲提出,派遣留学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选取年龄在15—20岁之间的青少年,每年选取100名,考选中文、英文和专业技能。由学部和外务部联合在北京招生,地方选送的考生也要在京复试;另一部分是,选取15岁以下的少年,每年选送200名,名额根据各省的大小和所负担的赔款多少分配。这两部分学生录取后,都要进入留美预备学校集中培训数月或一年,然后从两部分学生中各选拔50名进入美国学习。未入选的学生,则继续在留美预备学校学习,等待下一学期进入美国学习。很显然,第一部分是学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志的体现;第二部分是外务部彻底西化意志的体现,而两部分各取50名学生,则是两部以“平分学额”的方式达到了妥协。
经过艰难的选拔,从各省选拔出150多名学生,直隶地区参考学生400余人,考试总人数600余人。外学两部又对这600余名学生进行了统一考试。初试的时候,600余人淘汰了三分之二还多。复试后,录取的学生仅有47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中美双方协议中规定的最初4年每年须派遣100名学生的约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考试录取的47名学生仅仅是学部的学额,外务部的学额被搁置。外、学两部通电各省督抚等,告之是年因时间紧迫,专取第一格学生先行派遣[13]。
另外,在录取的这47名学生中,可以看到不少政要子侄的身影。就在选派细则确定后,多方利益诉求接踵而至。不断有人向上递条子托关系,甚至有官员相互约定确定录取后送子侄进京,故而这次看似公平公正的考试,实则被别有心机之人徇私舞弊。从上榜生的名单不难看出过往政要的影子,如排名第五的唐悦良出身广东香山唐氏家族,唐绍仪是其堂叔;排名二十七的金邦正是安徽人,他的兄长金邦平曾任袁世凯秘书;排名倒数第三的曾昭权出身湖南曾氏家族,祖上正是曾国藩,这种现象不胜枚举。抛开考生个人实力,考生的背景似乎是这场考试胜出的重要因素之一,留洋已经成为当时豪门贵胄子弟入仕的终南捷径。
四、结束语
首批庚款留美生派出之后,从1910至1911年又相继派出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留美生,至辛亥革命前夕,总计派出留美生180人。庚款留美运动培养出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但庚款留美运动的影响不止于此。
庚款留美政策的最终实施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反映出当时历史局面的复杂性。从美国退还赔款来看,正是由于退款的自愿性,美方对退还资金的流向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同时受国际局势以及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最终否决了中方提出的各种方案,坚持选派留美学生。最后,清廷也不得不同意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从庚款留美生的选派活动来看,该活动一直在中央及地方利益博弈下进行着,官员们徇私舞弊,中央部门间明争暗斗,地方利益团体也暗流涌动。因此,庚款留美政策的实施是多方利益博弈下的结果,当时晚清政局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87.
[2]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151.
[3]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M].王绍坊,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619.
[4]LAWRENCE F.ABBOTT.Impessions of THEODORE ROOSEVELT[M].New York:[出版地不详],1920:14.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78.
[6]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J].历史研究,2020(5):108-129,222.
[7]安庆通信[N].安徽白话,1908-05-04(5).
[8]议派留美学生纪事详[N].申报,1909-03-11(3).
[9]张相国与荣尚书会议[N].大同报,1909-10-32(11).
[10]论选派学生赴美游学事[N].新闻报,1909-03-09(1).
[1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79.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游美学务处档案史料[J].历史档案,1997(3):63-78.
[13]李守郡.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的选派[J].历史档案,1989(3):100-107.
作者简介:刘健鹏(1999—),男,汉族,天津人,单位为吉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