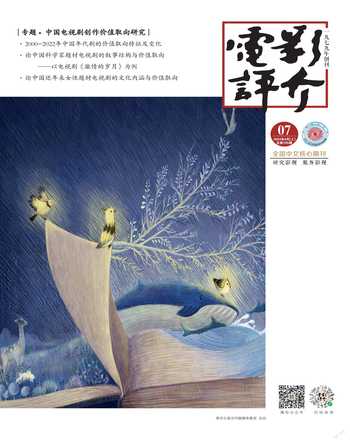《宇宙探索编辑部》:类型策略、悲情形象和失衡立场
张燕 贾茂松


不同于特效过硬、宏大叙事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019),曾在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节亮相展映,并于2023年4月1日正式公映的科幻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不论是科幻这一类型的选取,人物塑造取得共鸣的方式,还是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与情感的发掘,后者几乎走了一条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科幻片创作路线。
《宇宙探索编辑部》讲述了一个颓唐、执拗的《宇宙探索》杂志主编唐志军询问未知与寻找希望的故事。影片在类型元素混杂使用的同时,通过对一组形态各异但又不尽相同的人物群像的塑造,勾勒出一幅现实社会中边缘人群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经验的图像。在现实与虚构的影像之间,记录了一位悲情的探寻者、一位父亲对宏大宇宙中人类自身存在问题的询问和对自己最私密的个人情感经验的探寻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情节推进与情绪积累,影片所展现出的两种对待“科幻”的立场逐渐由游移暧昧转到倾斜失衡,最终导向一种更加普世、民主的“科幻”,其背后所蕴含的是对“科幻”是非曲直问题的反观,以及“科幻”本身之于当下现实的意义。
一、科幻、喜剧与伪纪录
(一)科幻类型的建构与混合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通常采用大量科幻元素作为题材,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来想象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作为类型片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幻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生产体系的发展与成熟。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硬科幻”电影实力之作,其足够震撼的视觉效果背后,折射出科幻电影所必须依靠的“硬性要素”——精良的工业化电影体系和高度成熟的科技实力;但是影片最终的成功并不完全仰仗炫目的视觉特效,而是在于对故事逻辑的编排和科幻世界观的架构,以及其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园故土文化的传达。由此引出问题的关键,即科幻片最重要的元素是具有科幻的意识与思维,即使没有炸裂的视听效果和华丽的特效技术,它也能被科幻这一类型认可。从这一层面来看,《宇宙探索编辑部》内容更加接近于“软科幻”电影。“软科幻”作为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科幻流派,其与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assc Asimov)所阐释的“硬科幻”[1]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区分模式,即“不写任何我们已知的科学,而是去阐述人类情感”[2]的科幻故事。影片在前半段叙事的段落中几乎没有特效的使用,甚至颇有“伪科学”的呈现,这在于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严谨、思辨的科学逻辑,而是叙事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情感表达和幻想实现,强调的是科幻元素与人以及社会现实的内在关系和情感联结。因此,当片尾中最科幻的一幕出现时——镜头远离地球以拉远至身后无尽的太空,星系与星云在眼前消失,关于宇宙与科幻、未知与意义的迷茫与寻找在此有了最后的注脚。
在类型构建上,影片的另一亮点是科幻类型与喜剧元素的混杂,即几乎无处不在的喜剧化情境与科幻叙事之间的弥合。不论在编辑部时秦彩蓉与唐志军角色性格之间形成的明显的戏剧反差,还是动身入蜀之后的方言荤口呈现和肢体喜剧表演,影片所营造的喜剧性瞬间在有着自身商业类型化诉求的同时,也拉近了影片高信息量文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又如用头部按摩仪接收外太空信号、“流浪的球”的客串和外星人驻地球联络站等。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影片的主导情绪急转直下,直至唐志军在山洞里缓缓读出那封短消息时的冰冷与痛苦,影片前半段所着力展示的这些密集笑点在这一刻突然指向了一种“虚无”,即观众在影片角色身上获取的笑点与他们最终希冀的目标之间出现了一种绝望与无力,而这些笑点所带来的幽默感实际上也是指向深层的自嘲。英国哲学家怀利·辛菲尔指出:“我们已置身于20世纪的‘尘埃和冲突之中,并认识到落在人类头上的最可怕的灾难如何证明了人生归根结底的荒谬。人生的喜剧观与悲剧观已不再相互排斥。”[3]荒诞的喜与悲在这一刻无法区分。在山洞中,当唐志军意识到“石球”被孙一通取走之后,站在他面前的孙一通成为解救他脱离自我困局的窗口,可是他问出的问题并没有答案,反而令他更加绝望——“但是,如果他们也不晓得呢?或者说如果他们那么远过来也是为了问我们这个问题呢?”围绕唐志军一路探寻所积累的喜剧元素瞬时转化为对人生与存在问题的不可抗拒的悲剧化符码——“自信姿态”与“徒劳境遇”之间巨大落差的荒诞性。这正是影片的喜剧元素在由表及里地混杂在科幻类型之后,藉由充满张力的西南山区地域景观和远离主流叙事语态的川蜀方言情境,以构建出一层层远离日常情境的俚俗奇观,进而完成一次“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幻类型实践。
(二)公路片的框架与元素
除了在科幻类型之下影片对于荒诞式喜剧元素层层深入的展示,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在以章节为单位的叙事结构内,内嵌了公路片的类型框架。学者郝建在《类型电影教程》中指出,“具体的电影类型是按照叙事模式、主题领域、场景、视觉风格来划分的,电影类型是外部形式与内在观念场域的结合。”[4]诚然,与20世纪60年代新好莱坞黄金时代以来所逐渐发展成熟的好莱坞公路片不同,国内成熟的汽车文化和公路文化环境的缺失使公路这一意象徒有消费上的价值,公路本身也并非承载了“自由”“反叛”等寓意的符号。但即使如此,在国内公路片的类型语境中,汽车、公路和旅伴的意象和“在路上”的状态依然构建了公路片的外部形式框架。在此基础上,或以治愈为目的、或以逃离现实为借口开始一段旅途,最终得到心灵救赎、获得成长,以此形成一种特有的“治愈系旅途片”。
在这一类型编码系统中,也包含着公路片固有的类型模式——相对定型化的人物、公式化的情节、图解式的视觉形象。在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唐志军为了去调研“奇异天象”而卖掉宇航服,由此带领众人开启了一段“蜀道难”旅途,編辑部里尖酸刻薄的秦彩蓉与性格温和却固执的唐志军构成了反差式的主人公与伙伴的角色,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物之间不断的冲突与矛盾。如入蜀之后秦彩蓉的处处讥讽与不屑,与唐志军的沉默和执拗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从而不断制造出紧张的戏剧张力。
在情节设置上,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危机的不断升级结构着整部影片。片中一行人来到四川探究鸟烧窝村的奇异天象,包括等待麻雀落满石狮子、带路的孙一通失踪、秦彩蓉被狗咬伤等情节,主人公一路旅行与探寻的过程也正是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直至最后旅途结束,所有的危机得到解决,即唐志军抵达了宇宙尽头,得到了答案。
汽车与风景,作为公路片不可或缺的视觉形象在影片中有着明显的区分。从北京到四川,从国际化现代都市到西南山区与热带雨林,其中穿插着作为叙事手段、交通工具和类型元素的火车、汽车,在交通工具的活动空间内,角色有机会相互交流与倾诉、生发情感,而异域的自然风光则负担着对主人公心灵的抚慰功能。
(三)从现实层面到虚构层面的过渡
在技术层面,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通过采访式镜头刻意制造了一种伪纪录片式的质感,并且几乎全程使用“跳切”手法将这种纪实感无限放大,这一质感的创造是从影片的形式出发的,但也在其中拓展出与内容层面上的呼应。
角色面对镜头进行回忆般陈述的这一行为经常出现于纪录片或者电视纪实节目中,在此出现极大地调动了观众既有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从而使影片整体的叙事充满了真实感。影片中,唐志军在自己家里面对镜头自说自话,有意无意地瞥向镜头,向观众讲述荧幕上雪花点的含义;秦彩蓉在眼镜店内向摄影机背后不存在的“采访者”吐露自己与唐志军的不和,转而娓娓道来唐志军背后所不为人知的秘密;在火车上,那日苏一边喝酒一边讲述自己的经历,如同和新朋友聊天初识;在鸟烧窝村里,女孩晓晓对摄像机讲述着自己的童年成长故事;孙一通在田埂上对着摄影机读诗,以及在日全食时要求摄影机“闭上眼睛”。这些穿插其中的采访镜头的“真实呈现”,顺从了观众惯常性的审美经验,在假设了摄影机“拍摄在场”的同时,也假设了人物情感和叙事内容的真实性,建构了一种具有纪录片审美倾向的伪纪录片外在样态。
此外,不断地跳切剪辑也是塑造伪纪录片质感与纪实性的一种关键手段,在破坏单一镜头内连贯时空的前提下,以情节或者人物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依据,组接起被摄制主体的必要动作,以突出某种情感或者某个重要动作内容。贯穿《宇宙探索编辑部》全片的跳切镜头省略了动作起伏较小的部分,而只呈现那些最戏剧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瞬间动作,强化了动作被关注的速度与密度,从而使观众的注意力在略显亢奋、在应接不暇的剪辑节奏之中无法分辨影片的现实与虚构情节。而在这不间断的跳切中,影片也大量采用了手持镜头来模糊影片虚构与现实真实的距离,并且保持着统一的美学风格,从而在整体上深入塑造出影片在内容层面的整体气质——真实性与虚幻性的合二为一。直至片尾在山洞里,唐志军目睹孙一通离开这一段,才将这种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梦境的撕裂张力推至顶峰。
二、“追UFO的人”
(一)理想主义背后
在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经典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一台名为“深思”(Deep Thought)的超级电脑经过长达750万年的思考,得出了关于“生命、宇宙和任何事情的终极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42”。小说出版十多年后,依然有众多探究者好奇这一答案究竟意味着什么,亚当斯不堪其扰,声称这个看似无厘头、毫无意义的数字出自他的随意选择,但是亚当斯一开始并没有说明那个“终极问题”究竟是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结果的关注要超过所问出的问题。为了求得一个准确、明白的结果,人们会选择性地遗忘在探寻的路途中所经历的曲折与艰辛,这是否正是《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唐志军理想主义形象的写照?30年前,唐志军是《宇宙探索》杂志的年轻编辑,他坚信地外文明的存在,认为外星人的到来将为地球带来人类文明的再进化;30年后,他困囿于世俗生活之中,但依然秉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固执。随着科学的发展,没有人会再相信他的那一套理论,甚至与他关系最亲近的秦彩蓉也对他想要进入飞碟仓的行为嗤之以鼻,而他珍惜的伪造宇航服也只是用来拉赞助的展示品。
至此,在影片第一章《追UFO的人》中,观众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怀揣着对宇宙、人类宏大问题探究理想的普通人在近乎疯癫的执拗中踽踽独行,即使他身处于一个几乎可以用眼神就可以把他置于死地的现代都市环境中,但他对于探寻结果、答案的执着又足以使他不顾旁人的眼光,不顾“声色犬马,口腹之欲”。起初,支撑他前进的动力,似乎是年轻时的执念,似乎是职业与身份的需要,也似乎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自知的一种方式,他理想化地探寻着人类生存的意义、外星文明的可能性和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而甚少关注自身现实生活的困窘和无奈。在破败不堪的屋子内,他认真地向观众展示电视荧屏的雪花点和观察检测宇宙的“望远镜”,在最简单的食材中煮出仅仅能饱腹的食物,每日骑着一辆破败不堪的电动车穿行在北京的街头,在精神病院里面对着无人听讲的屋子侃侃而谈……就像秦彩蓉所说“他以为他是个大科学家,其实说白了就是个民科。”观众此时的态度就像秦彩蓉一样,对唐志军的所作所为充满了不解,无法理解一个曾经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怎么会沦落成一个别人口中的“怪胎”,30年前充满朝气与希望的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沦落到如今落魄颓唐的地步。
(二)存在的谜题,悲情的答案
当人们从秦彩蓉口中得知唐志军孑然一身的背后还有对女儿抑郁而终无法接受的痛苦后,影片从这时便开始缓缓渗透出一种悲哀的情绪。荒诞的现实遭遇里,伴随着对人物的同情和体谅,直至他在山洞中缓缓读出女儿自杀前发来的短消息时,这种悲情的氛围被推至顶峰,然后在孙一通的离去中释放出一种无可比拟的释然与宽慰情绪——他已然得到了那个答案。从这一刻往回看,观众才终于理解之前唐志军这个角色内在的清醒与智慧。女儿的去世是他“永远想不明白”、躲不开的困境,女儿生前留下的问题是对他无法停止的折磨,而唯一解决这个宇宙终极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让他们来告诉人类。
195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了一个科学论题,被称为“费米悖论”,阐述的是对地外文明存在性的过高預期和缺少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即外星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无法分别证明之间的悖论。①70年过去了,“是否有外星人”如此宏大的问题至今无解,找到外星人不仅是唐志军身为科幻杂志编辑的职业选择,也是他身为父亲为女儿寻求谜底、疗愈自身的途径,更是成为支撑他抛弃物质主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仰。因此,也不难理解他将电视机的雪花点视为“宇宙诞生时的余晖”,将精神病院的病人看作可以读取外星信号的特殊人群,将电视机的停机想象成地外文明发射强烈信号导致的过载。“电视机没有出现问题,而是宇宙出现问题”……任何一点有关外星人的传闻与谣传,他都要第一时间前往,即使代价是卖掉珍藏的宇航服。
“我们人类存在在这个宇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唐志军女儿自杀前留下的最终谜题,他清醒地知道这是他的目标,他坚定地追寻着,如此痛苦又如此热爱,如同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理想主义者日复一日地在庸常的生活里推动“巨石”到山顶,又一次次看着希望坠落,明知一直做着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却仍旧坚持,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巨石终将落下,但是推动巨石前进的过程也更加珍贵,这也是唐志军所悟到的那个终极问题的答案——“我们既是存在的谜题,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
(三)未尽之“诗”
从影片终章《未尽之路》开始,影片中主要角色逐渐退场,唐志军决定一个人继续走下去。这一刻,人物在剥离了现代城市与人际关系所赋予的特殊环境的外表之后,剩下的就是作为人本身对自身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探求。影片英文译名“Journey to the west”直译中文即是“西游记”,从寓言层面来讲,唐志军此刻如同那个一心要到西天求取真经的唐僧,“取经”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接近答案的过程,取经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与磨难。那头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驴,也正是他个人形象的赤裸隐喻,他正像那只迟钝、不开化的犟驴,在自己的河流中奔跑,奔向那只永远在眼前的“诱惑”胡萝卜。他在这一刻也完全获得了理解与认同,身为观众也能体会到他内心保有的对人类存在问题不断探索的心境,于是观众也在这一刻化身成为理想主义者唐志军——不再在乎别人的看法,所想即为所见,所见即为真实。
唐志军在溶洞中目睹亦真亦幻的“奇迹”出现的段落,既意味着他夙愿的实现,又是影片在叙事上所做的有意编排。在溶洞里,孙一通告诉他吃过的蘑菇有毒,此处便揭晓了之前河边突然出现的驴和之后麻雀升空奇观出现的原因,这一切可能都是唐志军吃了毒蘑菇之后的致幻体验。曾经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情在潜意识的作用下被激发出来:丢失又出现的驴、丛林里的小红帽和座舱、从天而降的孙一通、变长的外星人腿骨、溶洞石壁上的画、女儿的短消息、孙一通的反问……所有经历过的痛苦、恐惧与迷茫在自己的梦境中再次集结出现,冲击着他情绪最后的界限;也正是在这样自我情绪狂欢的时刻,他才能在麻雀的升空与离开中以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摆脱这一切的拘囿,了却那一桩心愿。片中引用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库布里克、拉斯·冯·提尔、姜文等众多导演都用过这一曲子。在关于导演的采访中,导演孔大山引用了一个评论——“一种理想主义怀着热烈的情感在巨大的悲剧里狂欢,在痛苦和绝望里产生了美好又盛大的幻觉”,他认为这个评论“其实就是唐志军的判词”。[5]
但不论如何,影片从头至尾,银幕前这个疯癫执拗的“神经病”经历着从不被理解到最终被谅解的过程,也嫁接了影片整体风格从冷峻的现实主义到诗意的浪漫主义过渡的过程。随着人物内在多元性格的释放与表达,人们在他身上逐渐体会到人性的温暖和现实的温情关照。影片基调的从冷到暖,从失落的现实到浪漫想象,又回归希望现实,观众从对他的不解到对他产生同情,整体上呈现了一种原谅与和解的变奏,而这正是他片尾献给未读出的“未尽之诗”的最终表达——与女儿、与好奇心、与这个世界的和解以及与爱的接纳与包容。川蜀之行结束后,在外甥的婚礼上,在众多陌生人的眼光中,在片刻沉默的尴尬后,他讲述了梦中所看到的宇宙的轮廓:“如果宇宙是一首诗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组成这首诗的一个个文字。”唐志军最终明白了,我们即是存在本身,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持续发问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执着探究宇宙“终极问题”的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续写这首关于人类理想与探索的“未尽之诗”。
三、游移与失衡的立场
(一)一个人的“科幻”
在影片中,所谓可以检测超出自然界信号的盖革计数器,所谓可以展示宇宙异常波动的雪花点,所谓可以联系人类与地外文明的“精神病”,所谓红超巨星出现的重力崩溃,所谓可以“用爱发电”的外星人腿骨等“假大空”,都不能被算在科幻的范畴中。影片并没有运用任何严谨科学的设定去呈现一种科幻的外在样貌,也没有将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运用于任何实践操作中,甚至在影片内容层面也是角色在将科幻当作一种表演“噱头”——山洞中所谓的“科幻实现”只是中毒之后的幻梦体验。可以说,影片所展示的这些荒诞“神迹”,仅仅是主人公唐志军一个人的“科幻”或者“科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影片所要传达的并不是让观众讨论是不是科幻、有没有外星文明。导演没有用一种刻薄的态度去俯视、嘲笑他,而是试图去捕捉到在文明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伪科幻”人群的“科幻探索”过程,并观察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少数群体执着且孤独地向着他们理想方向的过程,即使这些“理想方向”处于一种被歧视、被排挤的现实处境。
在影片前半段,观众会轻而易举地和秦彩蓉这一角色产生共鸣,在她这个现实社会中的常人看来,唐志军要宇航服不要命的这一行为令人气愤的程度不亚于花520元只为看硅胶外星人“用爱发电”;鸟烧窝村里她埋怨着唐志军把她带到了泥坑里,转而嘲笑孙一通头上能接受宇宙信号的锅;她也迷信孙一通晕倒是鬼上身,轉头就花钱烧香,称这些人就是“神经病大聚会”,将认真对话的孙一通和唐志军视为“俩傻缺”。总之,秦彩蓉是世俗社会里以为自己看得清楚明白的精明人,她嘲讽揶揄着“民科”唐志军的疯癫行为,也不相信这些“伪科学”和唐志军不切实际的行为。但是在另一语境中,她也像《西游记》里西天取经途中只想着抱怨与放弃的猪八戒,罔顾取经之路的崎岖与坎坷,好吃懒做絮絮叨叨。两种语境的对立,实际就是影片内部所展示的双重立场的价值观冲突——现实问题与理想存在的鸿沟与接壤,大众与边缘少数特殊群体的矛盾与耦合。但是,影片在前半段并未对这两种语境作出取舍,而是保持着一种暧昧多义的含混状态,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思索哪种立场才是“正确”的。
(二)立场的失衡与民主式的科幻
影片中段,身世复杂、性格纯粹的孙一通出现了,他神经质式的行为和古怪的气质,以及如同影片《路边野餐》中缓缓念出的意味深长的诗,在给予这个角色无限神秘与潜在魅力的同时,也考验着观众对于前文所提到的“双重立场”的选择与倾向。一方面,他所说的消失的石球、会突然的晕倒、头顶的“锅”与锅上被检测到的信号给人带来了无限好奇心,吸引着众人想要知道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外星“科幻”;另一方面,或许也是秦彩蓉逐渐认识到的——孙一通充其量是一个比肖全旺(硅胶外星人的主人)会包装自己的骗子而已;麻雀落满石狮子或许也只因那日苏在上面多撒了一把饲料;所谓外星生命体要他去取石球也只是他想去父亲生前工作的石材厂的理由;而村里那些人的话也都是配合着以讹传讹让外地人来烧香跪拜的赚钱把戏。至此,影片对于两种语境的取舍呈现出暧昧的平衡,在麻雀落满石狮子这一刻被彻底打破。面对秦彩蓉无尽的嘲弄和取笑,人们更愿去相信孙一通背后故事的真实,随之而来的是观众选择站在了这群“傻缺”的一方,并相信他“赌对了”。
另一个促进这种平衡被打破的角色,是那个吃抗抑郁药的单亲家庭女孩晓晓。从她加入这支队伍开始,她的存在感就弱于她人,除了车站里激动的介绍和热情的招呼,在鸟烧窝村她几乎没有和片中其他角色产生过任何互动,她保持着一张平静而坦然的面容去看待这场“闹剧”,聆听着每一个人相互矛盾的激烈话语。当镜头对准她时,她对着不存在的“采访者”说出了她的一段经历——对于科幻、宇宙和飞碟的着迷既是她童年培養的兴趣,也是对父亲的缺席无法彻底弥补的代偿。而这一“女儿”角色的设置,也呼应了唐志军女儿的缺席,影片为观众铺设了这一充满笑泪与辛酸的插曲,不仅是对这一执着于所谓“科幻”的少数群体直抒胸臆的关怀和同情,实质上更完成了创作者对于所展示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映射与批判,即对社会现实到社会问题出现之后的缝合。
从整体来看,影片所呈现的立场倾向扭转的过程,正是一个纯粹少数人的理性到变成感性、到多数人开始观察到的理性的过程。这种情感态度上的“失衡”促使观众一步步与角色保持认同,从“以为一切都是装神弄鬼”转变为开始试图理解这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的意义,以及好奇这种行为又会最终把他们带向何地。简而言之,可以说这是一种试图做到“人均平等”的“科幻”电影。它抛去了类型对于故事本身的枷锁,而是落脚于更加清晰可辨的情感与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地照顾每个人的选择与各自所理解的“科幻”,在不断累积的“科幻”与“伪科幻”的争论之中,我们已然忽视了二者的对错区分,而是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所热爱与坚持的,是否就是那个终极的答案?因此,在溶洞里,在观众和唐志军眼前,孙一通念着诗,在翔集的麻雀中如同“神迹”般消失,那种久违的理想实现、幻梦成真的悲壮感足以瞬间触动每个理想主义者——“哪怕是摔倒在地上,也要努力地抬头,仰望星空”。
结语
科幻作家赫伯特·W.弗兰克对科幻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6]从弗兰克这句话的角度审视《宇宙探索编辑部》整部电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幻”本身是虚构的,也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但最终还是属于每个人的。每个人对于世界的观念不同,对待科幻的方式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分别;每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对于知识的接受程度有差距,也才会有“科学”与“伪科学”之分;但是,即使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不同,对万事万物的体验与感受有异同,依然能同样感受到理想降临的喜悦与如愿以偿的幸福。这也许正是影片所展示的科幻的魅力所在——它在庸常的世俗中带来了神秘与未知,也给每个人带来了无限的想象与希望,如同影片片尾处摆在阳台上的那只锅里长出的青青绿叶。
《宇宙探索编辑部》在2021年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了费穆荣誉和青年评审荣誉的大奖,也取得了迷影选择荣誉奖,这分别代表着从专业、青年和影迷角度对影片艺术水准的认可。但是,影片终究要回归电影市场,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一部分,它还需要被放在当下国内电影市场去检验。
参考文献:
[1]Issac Asimov,(ed.).Stories from the Hugo Winners(vol.2)[M].New York:Fawcett Crest Books,1973:299.
[2]Peter Nicholls,(ed.).The Science Fiction Encyclopedia[M].Garden City,New York:Dolphin Books,Doubleday,1979:556.
[3][英]怀利·辛菲尔.喜剧:春天的神话[M].傅正明,程朝翔,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182-183.
[4]郝建,类型电影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2.
[5]梵一.对话《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聊聊郭帆、科幻和伪纪录片创作[EB/OL].(2021-10-19)[2022-02-07].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23886424/60ca8a5802700yilh.
[6][美]克里斯蒂安·黑尔曼.世界科幻电影史[M].陈钰鹏,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2.
【作者简介】 张 燕,女,江苏海门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史论、亚洲电影研究;
贾茂松,男,河南漯河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创建世界一流影视之都——北京迈向世界影视高地的事业产业发展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