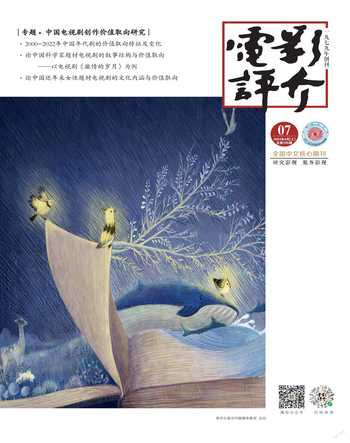中国香港武侠电影的东方形态与美学风格:以嘉禾影业为中心
钟倩
香港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在五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致力于电影类型的创新融合,在喜剧和武侠两种传统类型的基础上,加入复仇、争霸、探案、抵抗外辱等元素,整体上丰富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呈现样式。与武侠电影初期浓重的神怪色彩不同的是,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嘉禾影业制作并发行的武侠电影主要是以功夫技击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人物传记和谐趣喜剧,其中功夫电影李小龙系列、省港旗兵系列、警匪系列、新黄飞鸿系列影片,不但开辟出依靠真功实打取胜的市场新路,为武侠电影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还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动作电影的观影热潮。作为中国电影文化的特有范畴,武侠电影的呈现形式无论如何创新和颠覆,其精神构架始终离不开中国式的文化伦理和价值体系,在美学风格上也凝结着浓郁的东方式审美。文章以新武侠电影催生出的功夫类型片为主,以嘉禾影业制作并发行的“李小龙系列”“醉拳系列”“黄飞鸿系列”等影片为对象,阐述20世纪70年代以來中国香港武侠电影内含的东方形态和美学特征。
一、影视奇观中的东方形态
关于武侠电影本体论的表述,学者陈墨在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武侠电影即‘有武有侠的电影,亦即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及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所构成的类型基础的电影”[1]。基于此,本文采取武侠电影的概念来论述实战技击的动作影片,主要是因为关于“武侠”与“功夫”的内在定义问题历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功夫”一词本身就有着多重的外延和泛化。但是从类型建构上讲,武侠称谓对“武”的外在形式和“侠”的精神价值的概括,与功夫电影弘扬的武德理念一脉同源,故以武侠电影来统称该类影片并不违背其精神主旨。我国武侠电影中的任侠之风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史书有关侠客的人物形象,有布衣之侠、乡曲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的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墨家兴利除害思想为精神源动力的侠客精神,经历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文学演变,于民国时期开始突破固定的创作模式,在对忠君思想的背离中融入了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叙事内容也借助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江湖争斗间接指向动荡不安的生活情状。以武侠文学为蓝本的武侠电影,经历了近百年的光影变幻大致形成了神怪、写实、喜剧三种主要形式,但是不管形式如何多变,作为我国民族类型电影的重要标识,武侠电影独特的东方形态主要体现为,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伦理中凝练出的以“武”的外在形式和“侠”的超凡道德为核心的武侠观。
(一)“武”的文本之魂
武侠电影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框架中起舞,又在刀光剑影、民族情状、复杂现实的交汇中巩固并延续着这一文化形态。尽管在近9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叙事文本和叙事类型,对侠义精神的阐释有除暴安良、忠孝抉择、民族大义,但是武侠电影动作叙事的根基永远是中国正统的、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同时这也是消解武侠电影以暴制暴、以杀止杀等叙事“原罪”的关键。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每个时代对应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武侠电影在刀光剑影中对侠义精神和传统伦理的捍卫一直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前提,英雄人物转暴戾为仁义、转蛮横为忠恕的行为准则,也是推动影片叙事最为关键的动力元素。
例如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1972)、《猛龙过江》(1972)、《龙争虎斗》(1973)等影片在与强势文化对抗的困境中弘扬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和国人的民族自尊。成龙主演的《醉拳Ⅰ》(1978)在惩恶扬善的故事情节中,深藏着忠孝传家和尊师重道的叙事母题。与第一部散漫、浮躁的少年天性相比,《醉拳Ⅱ》(1994)对主人公的自我道德约束明显增强,并将忠义仁孝的伦理文本上升到守护国家物质遗产、维护民族利益的高度。由徐克执导和监制的黄飞鸿系列影片一共五部,每一部都没有流于武林各派或者江湖庙堂的争强斗狠,而是通过纷纷扰扰的江湖纷争,将英雄儿女的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第一部《黄飞鸿》(1991)以十余条线索刻画了清末大厦将倾时的众生百相,对麻木的梨园子弟、落魄的江湖艺人、贩卖国人的掮客、压迫同族的沙河帮等群体的呈现,全方位地描摹出一幅中西观念碰撞下的时代剪影。第二部《男儿当自强》(1992)在尊崇尚武精神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批判和反思民众的思想革新问题。第三部《狮王争霸》(1993)将你死我活的人心争斗从江湖升级到庙堂,主人公以民族大义为先,力平纷争之余选择为民族的命运建言献策。叶茂源于根深,尽管武侠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都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神话色彩,但是传统伦理的道德观和被社会认同的文化取向才是武侠电影提振观众精神力量的根本原因。
(二)“侠”的永恒正义
众所周知,武侠电影的动作场面不仅在作品中承担着叙事功能,在市场层面也是该类电影的关键卖点之一,尤其是作品结尾处的“最后一战”或“最后一分钟营救”场面,历来都是武侠电影动作叙事的中心环节,也是该类电影观众非常青睐的重头戏。这意味着几乎每部武侠电影都绕不开以动作对抗为主的暴力冲突,这种视觉奇观的塑造决定了武侠电影要始终面对以暴制暴、以杀止杀的叙事“原罪”。“实际上,武侠电影最为原初的内涵是武(武术)与侠(侠义)的相互融合,是动作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并且“对武术外部击打功能的认定,往往都是在中国武术整个价值体系的末端”[2]。在传统文化正脉中延伸而出的武侠电影,其技艺对决往往不是单一的能力对抗,其中还裹挟着正义与邪恶、压迫与反抗、人情和宗法的尖锐冲突,而单纯依靠暴力让观众获得感官刺激的动作电影显然不符合武侠电影所秉承的价值理念,那么如何利用故事的精神内涵来消解武侠电影的暴力和残酷,也是该类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首先,武侠电影会借助武德精神的弘扬来支撑暴力的合理性。在我国经典的武侠电影中,轻生死、重名节的精神取向和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价值标准是作为侠者最为明显的标志。影片主人公的精神高光并不取决于武术竞技的胜负,而在于人物在逆境中能够铁肩担道义,凭借不屈的精神意志来阐释一种浪漫的侠义情怀,这一点在黄飞鸿系列影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电影中黄飞鸿面对同行切磋,一直是拳让三分、点到为止,调和拳派纷争始终将“拳脚小功夫,容忍大丈夫”“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等忠恕之道贯穿于行动中。《狮王争霸》里谭家、赵家、蔡李佛、白眉派、大成宗等门派,在未参赛之前彼此争强斗狠,已将实力消耗殆尽,局面不可控之时黄飞鸿能够及时站出平息纷争,并适时点明武术修行应以内外兼修、禅武合一为根本宗旨。同样的醉拳系列,也没有一味地弘扬拳法搏斗的精髓要领,而是看到了酗酒对习武强身法则的违背,通过醉拳与醉鬼的微妙关系讲述武术拳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矛盾对立。
其次,是通过动作的正义消解暴力的残酷。“电影对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化了暴力的恐怖和惊悚,还是消解了暴力的血腥和残酷,便成为我们判断一部影片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影片精神境界的重要标准”[3]。作为一种丰富的历史文本,武侠电影中生死拼杀的暴力行径,必须是在正义的、道德的名义下进行,并且打斗场面的逐层升级,要与人物的行为逻辑、影片的叙事逻辑自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暴力存在的必然性。对此,我国的武侠电影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较为经典的文本样式——在充满动作、暴力的情境中,主人公以无奈但又不得不打的解决方式以暴制暴,快速果断地平定乱局,让剧中人的生活回归正轨。
例如,《精武门》中陈真是经历了灵堂挑衅、租界羞辱、精武馆被砸、得知霍元甲死因等一系列事件后,才决定与虹口道场决一死战。同样以黄飞鸿为原型的醉拳系列,第一部在情节上最明显的叙事弊病在于主人公的每场打斗都缺乏合理的细节支撑,成龙饰演的黄飞鸿与师兄不合打架、调戏女子打架、吃白食打架、师徒相识也要打架,甚至人物内心的独立和成长也仅限于个人的尊严得失。而《醉拳Ⅱ》为这一叙事弊病做出了明显的修正,主人公的每一场对峙都有着不得不打的无奈,同行切磋武打动作也是点到为止,胶着之时又能主动认输。而且其人物的成长引线源于中国最后一个武举人福民琪为保护民族遗产惨死街头、外国势力对劳工的欺压以及欺压背后的真相,最终激起了仁人志士的反抗。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嘉禾影业公司制作并发行的武侠电影极具特色的东方形态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和世俗伦理中的侠义精神,这一精神既丰富了电影的叙事内涵,又在形式的多变中支撑着“武”的外在形态和影片的整体叙事逻辑。
二、兼收并蓄的风格变奏
秉承兼收并蓄、和而有新的创作理念,嘉禾影业对武打动作形态进行创新,整体上丰富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呈现样式,无论是李小龙电影、成龙电影的写实色彩,还是徐克武侠的浪漫风格,都能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纵观20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功夫电影可以发现,在侠文化的叙事文本中,李小龙系列、醉拳系列、黄飞鸿系列影片,全部由具备扎实武术功底的专业人员担任主演,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更加注重武术动作本身的魅力。从真功实打的动作形态来看,南拳的刚劲猛烈、太极的柔韧舒展、长拳的迅疾紧凑都为武侠电影的动作设计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势力,也使该时期的武侠电影发展出不同的风格流派。其一是以李小龙、刘家良等人为代表的、真实呈现格斗功能的作品,影片在动作设计上注重拳法、腿法的正统性和独特性,充分利用电影语言来表现中华武术的魅力和精深。
20世纪70年代以后,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影片的出现,预示着以写实风格为主的动作片拉开了帷幕。由李小龙开创的“截拳道”在南派咏春拳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北派拳法的精髓,并借鉴柔道、空手道的技击方法将武术的实战性与动作观赏性融合在一起。《猛龙过江》中,李小龙曾强调自己的拳法理念是要“无限制地去运用身体”并且要“尽忠地表达自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单纯追求动作形态的展现使电影文本让位于武术动作的做法,也导致影片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同时情节上弱化正邪双方的戏剧冲突,对主人公的刻画过于刚毅、偏执,种种因素致使该类影片在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比如以今日的视角来看《精武门》,牺牲个体生命为民族雪耻,结局却死在殖民者的乱枪之下,这样的胜利总带有挥之不去的无奈和悲凉。对此,导演徐皓峰狠辣地将武侠片的个人英雄主义评价为“在没有明确价值观和生死观的同时以‘民族大义藏拙,以‘对外宣战给观众廉价兴奋”[4]。
第二种美学风格是从写实到杂耍的形态转变。显然,依靠真功实打制造感官刺激的影片在动作形态上难以丰富出更多新意,因此嘉禾影业在创业低谷期与成龙携手推出滑稽杂耍为主的功夫喜剧,在拳脚打斗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同程度的冒险、探案元素,使功夫喜剧成为武侠电影中别树一帜的一种亚类型。继《醉拳Ⅰ》之后,成龙又相继主演了《师弟出马》(1980)《龙少爷》(1982)等影片。其中1994年拍摄的《醉拳Ⅱ》,完美地体现了武打动作在“亦庄亦谐”之间的风格接续。《醉拳Ⅱ》的拍摄时间与第一部相隔十几年之久,此时成龙动作喜剧的风格已经基本成型,但是影片邀請了南派洪家拳的嫡系传人刘家良来饰演满清最后一个武举人福民琪,于是传统功夫打斗的“庄”与杂耍喜剧的“谐”在影片中产生了碰撞。电影开篇仅15分钟便上演了三场精彩的打斗,从火车底部逼仄空间里的铿锵过招到纵横交错的木屋对决,再到草屋里的拳法切磋,兵器也从长棍、长刀过渡到赤手空拳。刘家良与成龙在影片中的打法一个中规中矩、泰然处之,一个随性洒脱、适时求变,画面也在中景与近景中不停地切换,动作设计既有对拳术本身魅力的呈现,也有紧张刺激的氛围营造,传统武打动作的规板刚正和功夫喜剧的轻盈敏捷,被完整地呈现在镜头前。观众通过三次打斗场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传统功夫与杂耍炫技的风格碰撞。
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武侠电影开始借助特效技术制作动作奇观。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系列将特技手段与拍摄技巧紧密结合,形式上注重动作的连贯性和爆发力,在大开大合的动作形态中突出细节元素,同时利用云梯、狮头等夸张道具表现动作的力量感。人物之间不再是一打一停的硬桥硬马式过招,而是依靠技术加持凸显武术动作的形体美感,加之短促的镜头和快速的剪辑,还有戏曲舞蹈化的程式动作、雕塑性的人物亮相和高度提炼的戏剧冲突,使人物的动作形态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整体上呈现出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风格。除了黄飞鸿系列之外,同一风格下的神怪类武侠电影也是佳作频出。对此,有文章总结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写实风格到浪漫主义的变奏,认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将武术看作是武侠电影的一种元素而不是根本诉求,这种立场的改变才是武侠电影动作形态在这一时期出现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5]。
从主题内涵上不难发现,与以往武侠电影的门派对立和个人仇恨相比,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的浩瀚影海中其实深藏着近现代民族觉醒的精神脉络。该时期的武侠电影大都将传统的道德主题上升到民族大义和抵抗外侮的精神层面,其中最能凝聚这一精神特质的也是徐克武侠的出现。在黄飞鸿系列中,主人公直面内忧外患的民族困境与外国掠夺者展开一场场生死之战,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混沌世道中彰显豪侠义士的精神担当,观众在每一部电影的结尾都能感受到创作者对民族命运的深思。第一部经历过生死浩劫的黄飞鸿,深刻意识到“功夫再棒,也抵不过洋枪”的危机,《男儿当自强》是“但愿朝阳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鲜血满地”的临别赠言,《狮王争霸》是与庙堂权衡下“广开民智、智武合一”的慷慨陈词。也可以说,黄飞鸿系列电影的精髓就在于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手法,以自强人物和反自强人物的冲突对抗来呈现一个民族先行者的自省进取和图变求新。
结语
止戈为“武”,仁者为“侠”。武侠电影是极具民族元素和文化精神的电影类型,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枝繁叶茂的侠义文化对英雄人物超凡道德的描摹具有普适意义。嘉禾影业在五十多年的发展中注重武侠文化与文学、伦理、宗教等艺术的内在联系,对美学风格的兼收并蓄使该时期电影在写实风格和浪漫主义两条道路上的发展成绩斐然。而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技术的参与也预示着武侠电影将迎来新的变革,但是无论呈现形式如何创新和颠覆,“武”的文本之魂和“侠”的永恒正义永远是武侠电影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墨.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303.
[2]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命名与类型演变[ J ].电影艺术,2017(05):3-8.
[3]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4]徐皓峰.刀与星辰[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3.
[5]李骥.武侠电影动作形态的变化与发展[D].重庆:西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 钟 倩,女,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口语传播及电影电视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课题“‘密苏里方法的本土化应用——新媒介生态下高校传媒专业实践
教学的创新研究”(编号:2018-ZZJH-28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