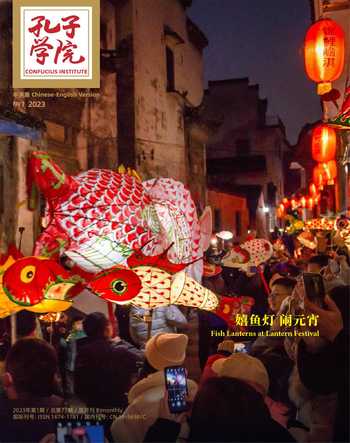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自然村,背依太湖山,面临裕溪河,地理环境优越。从遥感照片看,凌家滩遗址像一尊仰身睡卧的大佛,头枕太湖山,脚抵裕溪河。
1985年,凌家滩村民葬坟时发现了凌家滩遗址墓葬,遗址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5300—6000年。遗址上分布着墓地、祭坛、居住区、作坊、宫殿或神庙遗存,还有中国唯一巨石阵(在20世纪70年代被破坏)。1998年,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出土的玉双联璧是第24届冬奥会奖牌设计的灵感来源。现主要介绍凌家滩出土玉器,以飨读者。
玉人——华夏民族的祖先
凌家滩遗址共出土六件玉人,三件坐姿、三件站姿。玉人都双臂弯曲紧贴胸前,作祈祷状,反映了凌家滩先民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玉人的衣饰说明当时已有纺织技术,人们已穿上衣裤、戴上帽子。玉人双耳的耳孔和手臂上的刻纹表明,当时的人们有佩戴首饰的习惯。玉人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剃须工具,表现出玉人的绅士风度和当时相当高的物质文明。凌家滩玉人面孔都呈长方形,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嘴,身材比例匀称,面部表现出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同现在的中国人一脉相承。这有力证明了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的人种一直未变,文化传承未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三国都出现原有文明的中断和人种的变迁,唯有中华文明历史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石钻——先进的玉器制作工具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石钻,是中国20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其形状表明凌家滩先民对物理、数学、几何、机械力学知识的掌握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国内外知名学者看到这件石钻时瞠目结舌,称他们到凌家滩简直是来“朝圣”的。没想到在那么遥远的年代,中华文明就已如此流光溢彩。
玉龟、玉版和原始八卦图
在07M23出土的两百多件玉器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三件组合的玉龟形器和玉签。87M4也曾出土玉龟、玉版。这些玉件器形基本相似,功能相同,均为占卜工具。其工艺技术非常先进,已达到比较完美的程度。
这几件出土玉器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也印证,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龟、八卦和占卜的记载确有史实依据。这表明,在远古时代,凌家滩先民就已熟练掌握和运用玉龟占卜,以测吉凶,证明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占卜学的记载是可信的史料。
砖的祖型
发现最早和面积最大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其质地坚硬,是中國砖的祖型。遗址中还发现一口井壁用红陶块砌成的水井,井口直径1米,深3.8米。
代表丰富精神世界的玉器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其展开的翅膀上刻有猪的形状。鹰是百鸟之王,飞得最高,能与天上的太阳神接触,代表神的意志和权力。人们用飞鹰把猪供献给太阳神,寓意祈保安康幸福、五谷丰登。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冠饰反映凌家滩文化镂孔技术已向成熟阶段发展。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令世人震憾。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文化源远流长。凌家滩玉龙首尾相接,两角耸起,脑门阴刻皱纹,显得庄重、威严,须、嘴、鳞等龙的要素齐备,其造型和神韵都一如今人之作。五千多年的漫长时空在这件玉龙上如此神奇地叠合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足以说明巢湖流域是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此外,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有的玉璜被切割成两半,在两半的接合处各对钻一孔,有凹槽相连;有的在出土时只有一半,另一半可能在他方。其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具考古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虎首璜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
玉猪——信仰图腾
07M23出土的玉猪,重达88公斤,器形与1987年出土的玉猪十分相似。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最大、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这件器物所用的玉料是自然形成的、标准的玉籽料,如此巨大就已经非常难得,5300多年前的凌家滩先民更是匠心独具,完成了如此巧夺天工的艺术杰作。无论从哪方面论述,凌家滩遗址文化都表明,凌家滩先民已脱离对自然和图腾崇拜的低级阶段,进入到高级阶段的文明社会,这是文明古国文化的特征。凌家滩遗址可追溯到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玉器玉质种类丰富,其工艺技术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突出了精神文明的先进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为我们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具有极大的考古、艺术、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的价值,在中国甚至世界考古界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中国考古界、史学界专家学者认定,凌家滩遗址是中华史前文明源头,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作者简介:徐红霞,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张敬国,著名考古学家,发现和主持发掘凌家滩遗址的领队。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徽省玉石文化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古代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