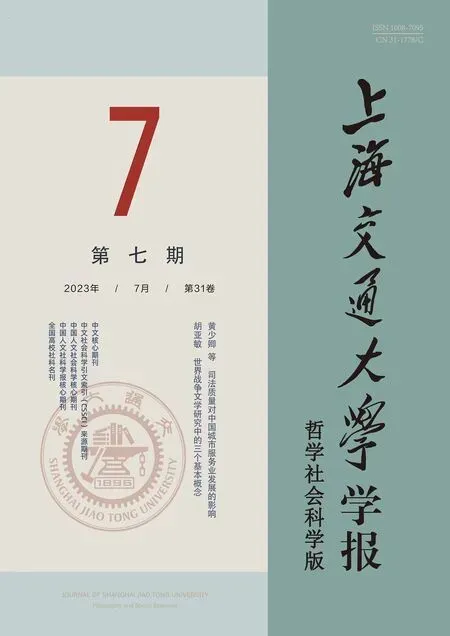《共产党宣言》的百年汉译及其经典化
许文胜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自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翻译史中,与同类著作相比,《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思想和内容在译介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上是无可比拟的。
《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大致以“五四”为分水岭,前后经历“片语式摘译、章节式节译、发展式变译、解读式译述到全文式翻译,译词、译语、译文、译本迭出不穷”。(1)靳书君: 《〈共产党宣言〉百年汉译的历史轨迹》,《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 12期,第4—10页。具体言之,形式上,这一时期是节译和全译的分界;内容上,从片段摘译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相关内容转向《宣言》思想的体系性引进;翻译和传播主体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系统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在翻译目的上,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建党以后,党领导的译者群体进一步正本清源,基于多语译本对《宣言》进行校译,配合党在各时期的实践和推崇的《宣言》阅读模式,建构其经典地位。
一、 “五四”前的《宣言》摘译
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自《宣言》,且“五四”前其译介几乎可代表这一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全部。一般而言,依据信仰和身份划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宣言》的摘译主体包括:“一为传教士,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四为无政府主义者,五为追求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2)陈家新: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第116—133页。“五四”以前,前四类是翻译和阐释《宣言》的主体。他们依据不同目的和立场,零星编选和摘译《宣言》不同部分,且多依据日文社会主义文献。
(一) 传教士的摘译
传教士在协助晚清封建官僚群体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偶然翻译了《宣言》。1878年,隶属官办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的传教士林乐知和蔡锡龄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第2卷中就介绍了“共产党”和《宣言》思想,但表达的是污名化态度。文中提到“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以体恤工人为名……与富贵之人为难”。(3)《西国近事汇编·光绪四年卷二》,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上海: 上海机器制造局,1878年,第19页。其中,“康密尼人”是“Communist”的音译。“康密尼人乱党”即是“Communist Party”,“乱党”则有污名化之嫌,特别“党” 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里具有浓重的负面含义,从而创造了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立的印象,(4)许文胜、刘朋朋、程璐璐: 《正本与清源——建党伟业中的翻译活动研究》,《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年第44卷第4期,第66—75页。反映译者政治立场和对该词的操控。“贫富适均”和“与富贵之人为难”,是译者对《宣言》“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思想采取的一种话语姿态。
1899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后发表于《万国公报》的英国思想家颉德的《社会进化论》(SocialEvolution)中,首次摘译《宣言》第一章“有产者”和“无产者”中的内容:“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现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前一译语同样充满封建意识形态,将原文中的“Länder”/“country”(国家)表述为“君相之范围”。强调“资本主义”对统治阶级的危机,省译原因——“世界市场”开辟。
总体而言,在传教士和封建官僚群体的“勾结”下,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过是“康密尼人”和“纠股办事之人”,对既有政体造成威胁,且他们属于偶然翻译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毕竟,《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旨在了解世界动态,但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观点并非官僚机构本意。
(二)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摘译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封建官僚阶级濒临倒台,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以积极态度正面译介《宣言》思想。
1903年,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了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参议员福田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克思及其主义》摘译了《宣言》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中的最后一段: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5)福田准造: 《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 上海时代书店,1903年,第127页。
值得肯定的是,相较传教士和封建官僚阶级,赵必振转译而来的《宣言》内容是正面的,但译笔上也是保守、谨慎的。日语译本转译自1888年由 Samuel Moore 翻译、恩格斯钦定的权威英译本。拿该译本对照便知,“大改革”的原文是“forcible overthrow”,字面意义为强力颠覆。此外,转译文表达的是与统治阶级的协商乃至妥协态度,传递的正是社会改良愿望。
这种译笔有因可循。译者本身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与维新派梁启超过从甚密,留日期间协助后者编辑《清议报》《新民丛报》,其中的言论是相对温和、中性的。此外,就选译对象而言,福田准造本身就是明治政府官僚,倡导“君主立宪制”,这也是近代维新派学习的政治体制。故而,从原文作者到译者在编译《宣言》内容上,难以避免对源文的审查意识,在日文译语中可能已经钝化措辞。
(三)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摘译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集中摘译《宣言》革命思想。1905年,同盟会领导的《民报》在东京创刊,旨在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6)宋庆龄: 《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487页。在日本期间,他领导下的同盟会利用《民报》这一阵地大量翻译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就包括重点摘译《宣言》最后一章。
1906年,《民报》第2期刊登朱执信化名蛰伸翻译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译述《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和最后一章结尾内容:“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忠而可耻。”(7)蛰伸(朱执信):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1906第2期,第6页。现译“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该文将Communist译为“共产主义学者”;disdain增译为将意图秘而不宣,即为“不忠”“可耻”,《宣言》因之被蒙上一层儒家传统伦理思想。
同年,该报第5期上刊载了宋教仁化名犟斋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同样涉及《宣言》最后一章内容:“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世一切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索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8)犟斋(宋教仁):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1906年第5期,第80页。可以看到,同样一段译文,宋教仁的翻译远比前文所提赵必振的翻译更近《宣言》原意,在革命精神传递上尤为如此。由于是局部节译,原文语境的缺乏,消弭与隐藏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在当时中文语境下,引导读者联想的是与晚清政府的矛盾。此外,在第7期和第9期上,廖仲恺、叶夏声也分别在该刊译介《宣言》“十条纲领”。
以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宣言》都有一个共同来源,即创刊于1906年的日本杂志《社会主义研究》。该刊由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创办,创刊号首次刊登两人的日文《宣言》全译本。此前,1904年,《平民新闻》已刊出《宣言》第三章以外的所有译文。幸德是一位较福田准造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家,早在1903年就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编译马克思的《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一时成为中国人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介”。(9)靳书君: 《〈共产党宣言〉百年汉译的历史轨迹》,《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4—10页。《民报》对《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转译、对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的关注,以及对“十条纲领”和“阶级斗争”等的重点关注,本质是为印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符合世界潮流。
(四) 无政府主义者的摘译
无政府主义者首次较为完整摘译《宣言》章节内容。1907年,刘师培、何震夫妇在东京创立《天义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言》便成为重要征引内容。
1907年,震述在该报第13和14卷上发表了《经济革命和女子革命》,摘译《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该报第15卷和合刊号(16—19卷)上,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宣言》所作的序言和第一章《有产者和无产者》。
无政府主义者章节式摘译《宣言》,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有产者(资产阶级)与无产者(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以作为消弭对立、实现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与理论依据。但他们认为《宣言》思想,“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10)刘师培: 《〈共产党宣言〉序》,李妙根: 《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0—431页。这一群体似乎计划全译《宣言》,但是否最终译出、出版和传播,难有定论。
以上各群体主要采用转译形式摘编了《宣言》思想,就转译自日文的内容而言,《宣言》成书背景、英文版序言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十条纲领及相关内容,成为译述重点。选译内容的差异和翻译策略,反映的是译者的立场和动机。上文也对不同群体翻译动机予以分析。封建官僚在师夷长技中,偶然翻译《宣言》,将“Communist”译释为谋逆群体;资产阶级改良派,注重其改良封建社会的功效,隐蔽其对统治者的威胁;资产阶级革命派,注重译介其中的革命思想,多次翻译“十条纲要”,一开始就视之为建国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11)李淑文、张彬: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特点与时代价值(1899—1919)》,《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44—148页。无政府主义者翻译、借鉴和批评《宣言》思想,视之为开展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总体而言,“五四”以前对《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多属偶然,内容零星、细碎,各翻译群体并不真正接受这一思想,也并未视之为改造中国的工具。
二、 “五四”后的《宣言》全译本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索。以此为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在华的翻译和传播日渐活跃,“表现出空前的系统性和传播的广泛性”。(12)许文胜、韩晓秋、程璐璐: 《初心与使命——建党伟业中的翻译活动研究》,《中国翻译》2021年第42卷第3期,第5—14页。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3)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在此背景之下,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建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也为《宣言》翻译书写新篇章。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从摘译逐渐过渡到全译、重译,建构起《宣言》经典地位。
(一) 先进知识分子的摘译
“五四”期间,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十月革命追根溯源,开始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故而,先进知识分子摘译《宣言》是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4月,陈李在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登了署名为“舍”节译的《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以及十条纲领,并通过按语揭示《宣言》主张阶级斗争思想。5月,在李大钊协助下完成改版的《晨报》增设副刊,刊登了他早稻田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该报记者陈溥贤转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中便涉及《宣言》第一章。
此外,五四期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首次组稿“马克思研究专栏”,转载了陈溥贤在《晨报》上的译文,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同样转译并摘选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有福田得三的《续经济学研究》,(14)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涉及《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内容。较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宣言》立场部分话语的征用,李大钊更加注重通过译介,呈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性、科学性、体系性。
(二) 第一个《宣言》全译本
1920年2月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上海和北京等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标志着建党群体的形成,共产主义小组也迎来了首个《宣言》全译本。译者陈望道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也是共产主义小组骨干,后期负责实际上成为早期党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的编辑。正因陈李二人的帮助,《宣言》全译本才得以成功出版面世。其中,英文底本由陈独秀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陈独秀还专门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保证《宣言》的成功出版,并在此之前和李汉俊一同仔细校阅其中内容。
不同于“五四”前团体的扭曲翻译和阐释,征引《宣言》只言片语,以陈望道为代表的建党群体译行合一,翻译该文的同时,也实践了《宣言》思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时,内部就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其中就有《宣言》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陈望道的译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理论基础。据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该书是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部重要著作之一。(15)毛泽东: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1921年,先进知识分子更是践行《宣言》思想,齐聚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据参会人员回忆,“一大”宣言很大程度上依此为底本,“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16)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 “一大”前后》(二),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建党之后,早期党员积极践行阶级斗争思想,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领导诸如香港海员、安源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
三、 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宣言》的重译与经典建构
经典定义、生成与传播机制早已在文学研究等领域多有涉及。经典在最早的闪语和希腊语中的含义分别是芦苇和尺度,并延伸为标准和规范,在后世代指宗教著作、法律典籍,并拓展到各专业领域的重要文本,同时也突破了狭义纸质作品的范畴,亦包括其他模态文本。经典具有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普及性,一个基本特征即是被人反复传阅、说道,历久弥新。诗学要素被认为是早期衡量文本是否为经典的重要要素,欧洲文学中的经典是指“获批评家、学者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作品”。(17)刘意青: 《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45—53页。然而,作品的经典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美学价值,也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批评的价值取向和读者”。(18)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71—78页。可见,作品经典地位不仅建立在专业领域人员的共识基础之上,同样受制于外在环境。
翻译作品在接受语境经典地位的确立同样遵循相似机理。埃文-佐哈尔指出经典的动态性,并通过多元文化系统理论阐述了外国文学在接受语境成为经典的生成机制,即当接受国文学一尚在萌芽状态,二较之他国文学处于边缘状态,三处于转折点、出现危机或文学真空,(19)Itarmar Eva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u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94.揭示了外国作品独特美学价值为其在接受国成为经典创造了可能性。勒菲弗尔阐述了影响翻译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三要素”——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20)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其实都是着眼于经典建构的外部力量。查明建进一步定义何为翻译经典,认为一般包括三种:“一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二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的外国文学作品。”(21)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第89—105页。他更注重的是第三种,即主流文学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并将其置于“三要素”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忽略了原作本身思想、美学价值影响下的经典生成。对此,宋学智提出译本经典化的两个步骤: 首先在于“译者进行的文本内部的经典化,(尔后)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的经典化”。(22)宋学智: 《何谓翻译文学经典》,《中国翻译》2015年第36卷第1期,第24—28页。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下的诗学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作品的经典地位。因为作品的选择往往由译者或其背后的赞助人主导,读者群体则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建构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专业评论”一步步将作品推向经典地位。当然,普通读者也有自身的主体性、衡量机制与标准。故而,大众接受还是抗拒作品的经典化,也取决于这一群体对作品异质性和外部推动力量的认同与否。
文学或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如此,我们认为其他作品及本研究的对象《宣言》的经典建构背后的机理同样如此,即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共同推动形成了《宣言》的百年经典地位。就前者而言,《宣言》翻译活动的开展是其在中国经典地位生成的前提和基础,包括: 第一,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翻译机构重译、校定译本传递文本的内在价值;第二,通过集体参与、多语参照、建构副文本等相关翻译模式揭示文本的多重意蕴,丰富了《宣言》的阐释空间;最后,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对《宣言》翻译话语的继承与创新推动文本与时俱进。就外部要素而言,首先,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践行《宣言》理念。其次,党的主要领导人复述与赓续《宣言》翻译话语。最后,广大干部群众持续阅读《宣言》,构筑了其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地位。
(一) 翻译层面对《宣言》的经典建构
时空和语境的变化,使得《宣言》文本意义在不同翻译主体下多变并存在差异。陈望道译本对建党所作出的贡献巨大,但并非基于原本,从而对作者参照的源语和原意无从考证,翻译准确性也有所欠缺。他将《宣言》最后一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其中,译语“劳动者”这一表达正是受翻译底本影响。此外,德语初版后,马克思、恩格斯都亲自对之后的德语和其他语种版本内的表述加以修正、丰富。如此便意味着基于日语和英语的《宣言》中文译本,最初便存在缺陷,这也成为重译的现实依据。《宣言》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建党基石,前进路上的重要指南,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因而,准确、稳定的文本意义将直接影响党的实践,反之也将影响对文本的诠释。这也使得经典译本的建构尤为必要。
1. 重译历程
重译是指在某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及其群体,在同一语言目标内、同一作品已有译文基础上,对其再次翻译。它能够推动作品经典地位的形成,且推动新的重译。(23)刘泽权: 《数字人文视域下名著重译多维评价模型构建》,《中国翻译》2021年第42卷第5期,第25—33页。重译假说就认为(初次)翻译是不完整的,而重译才能增强异质性,使译作不断贴近原作。(24)Mona Baker, Gabriela Saldanha,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485.这也符合作品经典化的程序——内在独特的美学价值得到充分展现是夯实作品经典地位的基础。
一般认为,建党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按初译和初版计算,已出版且有据可考的《宣言》全译本有6个。如表1所示,就译者身份而言,除1945年国统区资源委员会陈瘦石译本外,所有重译本均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译者完成。时间上,这些译本出现在党各时期重要节点并发挥了不同功能。陈望道译本完成于共产党成立前夕,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及党的成立、党内《宣言》制定打下重要理论基础。华岗译本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为“工农武装夺取政权”提供理论基础,对译语表述首先呈现出尖锐化倾向。该译本在同基于1888年权威英译本的翻译中,首次将“打破”(forcible overthrow)重译为“强力打破”,继承陈望道“打破”一表述的基础并传递出译本色彩。成仿吾、徐冰译本出现在抗战初期,是首个基于《宣言》德语原语的中译本,并首次翻译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德文修订版写的序言,特别纠正了一些因转译“曲解”的重要概念,进一步贴近初版《宣言》原貌,将英译本“劳动者”(working men)重新表述为“无产者”,重构《宣言》诞生之时的劳工状况。该译本成为新译本、修订本的重要参照。新中国成立后,在官修本主导统一《宣言》话语表述背景下,该译本依旧得到译者本人多次修订。博古和乔冠华译本分别出现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实都是参照其他语言译本对成、徐译本的修订,沿袭了一些重要表述。同期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中国译者的版本,由于具体译者难以考证,一般被称为莫斯科译本或谢唯真译本。新中国成立后的《宣言》校定和出版基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译本基础上,参照各种语言版本,由中央编译局集体进一步修订再版,并以文内注等副文本在相应地方全面标注各版本的变化,构筑了一个意蕴丰富、历时悠久、影响深远的立体经典读本。

表1 新中国成立前《宣言》代表性全译本信息
2. 翻译模式
集体译校配以丰富副文本的翻译是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译介《宣言》的主要模式与一贯传统。自陈望道首译《宣言》全译本之时,这种模式就存在,后得以继承发扬。陈望道译本出版前夕,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一同校译,译文内部提供了一些专有名词和最后一句口号的英文原文。其后党内译本也都与前人译本构成互文,即便译者与所据底本不同,也是对前译本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宏观上构成一种由共产党人协作的翻译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翻译机构正式成立,在持续修订《宣言》中巩固这一模式,保证了译本的权威性,充分揭示了《宣言》的异质性,丰富了译本的阐释空间。
(1) 机构化集体翻译
党领导的《宣言》翻译一开始就有机构化翻译的性质,反映的是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层面对《宣言》的经典建构。陈望道译本由陈独秀专门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支持出版,时值维经斯基来华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宣言》出版便得益于此。故而,全译本一开始便装饰了一抹“红色”。华岗之后的译本均是在共产党成立后,译者均在党的宣传(或具该性质)部门任职,包括党领导的组织宣传部门、报社与出版社,党作为赞助人的机构化翻译特色则更加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宣言》校译由个人正式过渡到集体,并具有鲜明官修色彩。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专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编译。1958年,该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集体重译,将修订后的“百年纪念版”(1948年的莫斯科或谢唯真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1955年苏联出版的俄文版马列全集第二版)。此后,在1964年、1995年、1997年和2009年,编译局多次参考德文、英文和法文等语种版本的《宣言》进行校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2009年,编译局首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德文版和英文版中收录的《宣言》对中文译本再次重译,该译本被视为“目前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版本,具有政治上、学术上的权威性”。(25)方红: 《〈共产党宣言〉重要概念百年汉译及变迁》,《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年第43卷第6期,第84—93页。在此期间,偶有个人译本的出版或再版,主要都是为纪念“官定本”前面译者或由其本人重校。就传播的广泛度和认可度而言,个人的声音逐渐融入了集体的声音之中,并在《宣言》的副文本中得到体现。
(2) 副文本丰厚翻译
副文本既建构起《宣言》的译介面貌,又体现其内部丰富的阐释空间。副文本具有文化调节作用,包括“(正文以外)一定数量诸如作者名、题目、序言和插图等语言和非语言的材料……服务于更好的文本接受效果和更贴切的解读”。(26)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从首个全译本起,副文本参与到对《宣言》中文本作为经典的构建。从注重原语文本的利用到翻译、收录马恩为各语种和各版本写的序言,党领导下的译者和翻译机构始终追求还原《宣言》之真。1930年,华岗的《宣言》全译本首次收录3个德文版序言,在此基础上,博古的校译本又增加俄文序言。自“百年纪念版”开始,编译局历次重译和校定《宣言》,将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和意大利文在内的7个序言都收录在内,建构与体现《宣言》悠久的译介历程和广阔的传播范围,折射出文本的影响力和经典性。
副文本对《宣言》的经典建构着重体现在译本注释的继承与丰富。从译注方式而言,页内注是所有版本的通用方式。不同之处在于,陈望道译本的注释紧跟译语。自成徐译本起,译注与译语分离,在页内底部或侧端。就译注内容而言,首个译本加注方式为译语对应源语表达,一定程度反映首译的挑战以及译者对译语的把握尚不确定。成徐译本由于参照底本为德语原本,译注有几个特点: 第一,相应部分增译马克思以及恩格斯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宣言》的注释;第二,专门标记指出不同版本特别是1888年权威英译本在一些表述上的变化;第三,标注马恩在首版《宣言》以后的新思想和新话语;第四,译者本人对相关概念的阐释,以“按”提醒;第五,在前一译文基础上的新注释,专门以“译者补注”交代。其后的译本,在做法上基本延续成徐译本。总体而言,趋于“官定本”的《宣言》在翻译上以1848年的初版德语《宣言》为底本,参照各语种版本,注重囊括原作者和各语种版本译者在出版之后所做的任何修正并以副文本形式体现。以2018年“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多语种纪念版为例: 副文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头像,《宣言》手稿影印图,各版本序言,以及德语、俄语和英语的影印文本和主要中文版本的封面。中文译本采用的是2009年的考证版,包括49个文内注和25个文末注(多涉及历史背景说明),文内译注方式与前人基本相同,在充分翻译首版德语《宣言》基础上,指出德语版本表述的细微变化,着重凸显1888年英译本对德语原本的增译和改译现象。中文译本从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发展到几近300页的单行本,内容愈加充实,关键在于不断丰富的副文本信息充分体现了《宣言》的流播史与影响力、思想的深邃与经典性。
3. 翻译语言
中文《宣言》全译本自诞生之日起,就采用多语互参的翻译方式,主要源自英文、日文、德文、俄文、法语等语言。陈望道的首个译本同时参照了英文和日文,在译法和表述上多借鉴幸德秋水译语。(27)陈力卫: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词的尖锐化》,《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93期,第100—112页。其后的华岗译本以英文为底本,更贴近底本相同的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首次参照德文原版,也成为博古和乔冠华重译《宣言》的重要参照。确切地说,博、乔译本均以之为底本,各自参照俄文和英文校译。不过,由于两人改动幅度比较大,一般被视为独立译本。(28)陈家新: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第116—133页。通过对比几个独立译本,可发现在《宣言》百年译介历程中,译本翻译语言的继承与创新,体现每个译本的独特价值,译语的变化是对时代的观照,构筑《宣言》丰富阐释空间,推动翻译文本经典化。
(1) 同一底本译语沿袭
“五四”前的不同译者出于不同目的、立场,通过不同的话语表达,重构了《宣言》的文本意义。“五四”后,党领导下的译者开始正本清源,不断还原和建构《宣言》的全新面貌,各种译本在一些重要话语的选择上,一以贯之,体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立场。
共产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在《宣言》话语的选择上大抵具有较高的沿袭性和连贯性。表2所示为基于两种底本的不同译语。华岗以前的《宣言》话语生成的底本为1888年的权威英译本。陈望道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相关话语的表述并不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但通过对比华译本和陈译本,可以发现基于同一底本的华岗译文在形式和表述上十分贴近后者,基本可以看作后者的校订版。首先,从措辞上看,1930年的华岗译本在多数语句上与陈译本一致,除去关键话语的修正调整,如美国纠正为美洲,Communist根据语境表述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无句子上的重大调整。排版上看,除去首版将1888年英译文作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为中译文,同年的翻印单行本,译者化名彭汉文,变为从右到左竖排排版,和陈译本高度一致。

表2 《宣言》代表性话语翻译
以英文为底本的《宣言》最终在1938年由成仿吾和徐冰参照德语版翻译的《宣言》版本所替代。同样从表2可以看到,后出博古、谢唯真等人的译本在措辞上高度继承成徐译本,在关键概念表述上与后出译本基本相同,体现该译本的重要参考价值。需指出的是,如表1所示,成徐之后,博古、乔冠华等的译本本质上都是以两人的译本为底本,不过是参照各语种《宣言》进行的校译。因此,其后译本有德语原本的底色。以Communist一词为例,以前的译者依据自身的立场将之同化为同一阵营,有“同盟者”和“吾人”等表达。陈望道将之译为“共产党”,表明译者已具备政党意识,但不一定具有对此团体的自我认同意识。毕竟,当时尚未建党,各地对于什么是共产党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成仿吾等译为“共产党人”进一步展现建党后的译者身份认同,同时也属对译语的精确把握。
尽管有底本差异,一些词汇的色彩、意蕴在陈望道和华岗译本中就奠定了基调,成徐译本则联系实际,进一步精确翻译,相关译法也得以延续。如将“forcible overthrow”译为“暴力推翻”这一译法。1938年,立足延安以后的共产党,在历经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挫折和长征艰辛后,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和最终难以调和的矛盾,必须坚决开展阶级和革命斗争。尖锐化的译语正是这种决心的体现。“Communistic revolution” 在成译本前被视为“共产的革命”,其后则是“共产主义革命”,表达相似,但内涵上相差甚远。与“的”相比,“主义”体现的是译者政党意识,是特定而非泛化群体的目标与信念。“Working men” 在德语原文其实就是“proletarier”,是莫尔(Moore)在1888年的英文译本中在征得恩格斯同意后改为“劳动者”。(29)王保贤: 《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问题: 兼评郑高之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第132—138页。陈译本及之前的译介受到日语和英语底本的影响,华岗译本予以纠正,虽首次译为“无产阶级”,但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广大劳农、劳工还未掌握先进生产力,译语未必反映现实。成仿吾等译本据现实情况将之纠正,“无产者”这一表述由此得以沿用。
(2) 译语通俗化
党领导下的《宣言》译校注重译语的通俗化表达,是其成为经典的重要条件。作品的美学价值再高、思想再深邃,如果不能得到广泛阅读、理解和传播,终将被湮没。而通俗的语言却能增强受众的理解度和文本的传播度,是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前文的译介史梳理中可看到,无论是受现代思想启蒙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译介《宣言》的语言依旧是古文,以致其译文终究难以被最广泛的劳动群众接受,也难以获得群众基础。
陈望道译本奠定白话文译介《宣言》的基础,其后译本愈加通俗。以《宣言》第四章“共产党对各反对派的态度”中的关键话语为例,相应底本表述为:
Die Kommunisten verschmähen es, ihre Ansichten und Absichten zu verheimlichen//The Communists distain to conceal their aims and views.
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到共产党领导的译员群体历时生产的译语为:
赵必振: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
朱执信: 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忠而可耻。
陈望道: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华岗: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政见和目标。
成仿吾、徐冰: 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
博古: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
谢唯真: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
编译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由上可看到《宣言》翻译话语形态经历了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与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白话文形态的《宣言》是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前提。党领导的译者群体则在白话文形态基础上,致力于用朴素简洁、与时俱进的译语传递出《宣言》思想。如用词上,verschmähe/distain的表述从“鄙薄”“认为……可耻”到“不屑于”,逐渐摒弃文言带来的思维桎梏。语言进一步凝练,句子结构也更为短小。实际上,对照同一底本的陈望道和华岗译本,就会发现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有意识地通过增加标点截分译句,以增强可读性。字体上,1956年简体字审订推广后,后续修订的《宣言》译本语言也与时俱进,将以往译本的繁体字逐渐转为简体字。
《宣言》重译体现的是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对原语文本的回归。这一群体通过继承、更新、简化前辈译语,促进普通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和接受并得以洞悉历史语境,充分体现了文本价值。此外,通过副文本建构起来的中文译本充分展现《宣言》的接受史、发展史和丰富意涵,也为《宣言》话语与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二) 实践层面对《宣言》的经典建构
中文《宣言》成为经典离不开党及其领导下的译者群体始终践行译行合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党领导下的《宣言》翻译和重译活动实现了对文本异质性的充分展现,而建党、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均融入了《宣言》理念且取得系列成绩,体现了中文《宣言》的价值。此外,一些经典的翻译话语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被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领导人反复言说,成为中国核心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最后,《宣言》在广大党员中以“经典”“必读”形式推广,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重要记忆。
1. 《宣言》理念的实践
先进知识分子自建党起,就从《宣言》话语中汲取力量并付诸行动。《宣言》第二章开头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和无产者同盟互助关系。据此,建党过程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注重团结劳工阶级,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比如上海李启汉前往普陀区小沙渡成立工人半日学校,教学员读书识字;北京邓中夏等人前往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广州谭平山和武汉董必武等创办“机器工人夜校”和“工人识字班”等。这些工人群体后来成为建党之初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基础。这些活动作为早期党员组织力和领导力的体现,均以《宣言》为指导。此外,《宣言》倡导的消灭私有制及“十条纲领”影响新中国成立之时的国体确定和改革措施: 首先定国体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继而实施“三大改造”基本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思想寓于行为之中才是文本经典性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括《共产党宣言》精神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30)赵伟: 《继承〈共产党宣言〉精神,谱写时代新篇章》,光明网,2018年5月7日,https: //theory.gmw.cn/2018-05/07/content_28667743.htm,2022年4月28日。自改革开放起,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便是对消灭私有制的科学回应和战略调整,其中,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本身是《宣言》之道的一以贯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共产党人不断回归初心和使命,对内强化反腐倡廉工作,坚守原则——“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对外推动“一带一路”落地,促成“文明国家联合行动”,在“共商、共享、共建”理念下,逐步迈向《宣言》理想——“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31)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译: 《共产党宣言: 多语种纪念版》,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2. 《宣言》话语的赓续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宣言》作为经典地位的建构还表现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话语成为党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这一点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日常话语和党的纲领文件中均得到体现。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2)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367页。这是先进知识分子最早援引《宣言》话语,呼应“they have a world to win”(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陈望道的首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后,陈独秀为纪念工农运动中的牺牲者又号召“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呵!”(33)陈独秀: 《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任建树、李银德编: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427页。
两位建党先驱之后的领导人在各时期不同场合的讲话体现了《宣言》的影响,推动其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形成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就将陈望道所译《宣言》视作奠定其共产主义信仰的关键。新时期,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着重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话语和议题,均是《宣言》思想和话语的当代应用。因为早在一百年前诞生之刻,《宣言》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34)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 《共产党宣言:多语种纪念版》,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宣言》的中译话语也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沿用。早在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就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到阶级斗争、生产工具、消灭私有制等话语,表明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前夕就以《宣言》为行动圭臬。此后,入党誓词和党的章程中都镌刻了《宣言》因子,成为每一位党员的基本行为规范。纵观从“土地革命”到“十二大”以来的入党誓词,每一位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都须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头便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话都能在《宣言》中找到影子:“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回应的是《宣言》的“消灭私有制”。“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回应了《宣言》中的“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章虽非原原本本援引征用,却是共产党人将《宣言》思想与中国现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体现,激发了《宣言》的悠长生命力,源文本的话语和意义得以延续、拓展。
3. 作为必读文献的经典著作
《宣言》成为党内必读文献体现的是读者要素对其作为经典的建构。《宣言》一经翻译出版,便成为在话语上构筑政党形态和党员身份的重要依据。延安时期以来,《宣言》被明确规定为党内必读文献。以后党在各时期工作重心虽有所变化,但党内始终坚持对《宣言》作为经典的阅读,《宣言》对不同时期群体产生不同影响,铸就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宣言》记忆与情怀。
建党期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国语学社,培养革命干部,为建党和革命事业打下重要干部基础。该时期,陈望道翻译的《宣言》自出版起又陆续传播了十多版,成为包括刘少奇和任弼时等学员在内的最早一批留苏学生的必读和学习书籍。事实证明,该译本对于为党的成立和日后革命事业准备一批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革命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言,陈译本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继之而起的华岗译本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成为苏区军民必读书籍。该译本大致到抗战初期仍广泛流传,前后总共7个版次,以不同署名和书名出版。译者首次在译本上留下译者序,动员鼓舞广大知识群体、有为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且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提升了当时党员群体的使命意识和组织意识。
延安整风时期,为提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党内确立了“干部必读”书籍。博古受命在成仿吾、徐冰译本基础上重译校定《宣言》。该译本首次成为党内干部必读丛书之一,出版次数保守估计约70次。从1946年到1949年的再版过程中,《宣言》先后被列入或定为“干部学习丛书” “干部高级读物”“中级党校教材”“干部必读文件”和“干部必读”。(35)张远航: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第1期,第69—76页。这一传播方式提高了党员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了这一群体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心,既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又推动广大党员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成立,“百年纪念本”替代博古译本成为权威译本和干部必读著作,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数次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其中,党通过课程化与体系化诠释、集体化和组织化解读,引导《宣言》在群体中的记忆从革命和斗争转向建设和发展,并在各地掀起学习《宣言》热潮。新中国成立前夕恰逢《宣言》诞生100周年,此时中央也通过了《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工作。这一背景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宣言》的文本,包括柯柏年的《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范若愚的《共产党宣言名词解释》,解释《宣言》诞生的背景,特别对文内的人名、活动、概念和历史事件等做了充分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定后,《宣言》话语开始被用于诠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36)陈红娟、姚新宇: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文本诠释与意义生产》,《探索与争鸣》2021第6期,第34—45页。新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宣言》的群众记忆建构趋向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一话语如今深入人心,走向国际。而“共同体”的英译“community”和“communism”同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继承,是流播一个多世纪的《宣言》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新展示。
结 语
自19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1920年首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发展至今,《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已逾百年。在这一历程中,前后出现封建官僚群体、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觉醒一代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对之加以译介及进行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宣言》的内容、思想曾因从英文、日文、俄文版本转译以及不同译者群体的立场,被不同程度地“操控”。直到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建党群体的涌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领导的译者群体正本清源,在翻译注重回归原文的同时,更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考证、借鉴和参照多语种《宣言》,建构起《宣言》中译本的权威。
《宣言》在中文语境经典地位的建构,与其翻译和阅读方式密切相关,后者使这一文本的思想和意义得以长久播撒与延续。首先,党领导下的译者群体以集体参校且不断增加副文本比重的方式推动了中文《宣言》的异质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与之配合的是《宣言》话语融入历代国家领导人的日常用语以及党内文件,中译本成为各时期广大党员与先进群体的必读文献。如此便保证了《宣言》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有效接受。在此基础上,《宣言》中的话语在不同时期也被征引用作党领导的主题事业的重要依据并被深入阐释,进而丰富了其中的内涵、意蕴。这一文本和现实的双向阐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和动力,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论著在中国成为经典的建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