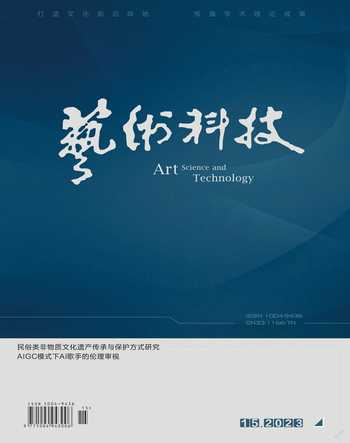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尊碑”思想的提出与清代社会转向研究
摘要:清代碑学被认为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其呈现出对唐宋以来以“二王”为中心的帖学典范书法体系的审美纠正,以及对自上而下书学体系的解构。宋代以来帝王推崇下的上行下效以及书家的推崇,成为书学思想传播的主要体制,而清代由于对科举规范的严苛要求以及“崇古”与“汉学”的盛行,对唐代及以前的金石碑刻的探访临习,使诸多游幕学人完成了书学审美思想由帖到碑、由“二王”到篆隶的转换,帖学文本经典性的流失、多次翻刻后笔墨的失真导致帖学开始为书家所诟病,古拙、质朴、雄强成为这一时期以篆隶为取法对象的艺术群体的审美精神写照。
文章首先总结“碑”“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面貌及成因,然后就金石学的复兴、崇古思潮与当时幕府的兴盛两个角度,对清代“尊碑”思想的提出及其时代必然性进行陈述。当前关于清代碑学的研究,多以书法家为纲,以书法风格为线索,对其进行梳理,但其变革的意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变化也值得讨论。文章尝试思考和借鉴戴小京、金丹等学者对清代碑学的研究成果,将碑学的兴起嵌入清代的社会、政治、文化中进行研究,以阐释“尊碑贬帖”观念的形成以及其中包含的学人立场。
关键词:“尊碑”;清代;社会转向;游幕学人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5-0-03
1 “尊碑”思潮与清代社会转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尊碑”的提出一方面涉及书学的“师法”问题,宋代姜白石批评了唐代因以书取士而昌盛的“昧于学古”对书法艺术传承的不利影响,认为其磨灭了书写性灵的本质。而康有为在书中讨论由唐宋至清代,书法在仕途的引诱下渐呈衰微之势。另一方面,康有为认为所谓的“帖学”,亦是自唐宋之后书法日渐式微的原因。因其以为晋人之书帖直至明代或还存有真迹,所以宋元明崇尚帖学,但纸寿不过千年,大部分书帖已是辗转翻刻失真了的复制品,字的形态已然不复从前,其风格意趣也已无处可寻,学者所精研的更多在于其作为名人之书的观念,而不能真正传承感悟其韵味。而碑刻因其载体的稳定性,对书迹之原貌多有保留,同时易于临摹,可以在对其的临习中考书体之变、笔法之妙,此为后世书学临帖鲜有[1]。
但康有为在著论中对碑学的推崇亦受限于其精于变革的立场。戴小京在《康有为与清代碑学运动》一文中,便指出了其书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一脉相承,而将其对社会变革的观念影射到其对书学判断中的矛盾,时而强调“变”和“崇古”的重要性,认为由于帖学的流行,书法自唐式微,但对欧阳询、虞世南的评价甚高,在“尊碑”和“抑帖”的同时,强调了帖学对草书传承的重要性。因此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的论证可参照以阮元、包世臣为代表的清代中期碑学潮流,结合《南北书派论》《艺舟双楫》《字学札记》等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理解清代语境中“尊碑”的真实动机与含义。
学者马新宇在《清代碑学研究与批评》中,结合清代学者梁章钜对清代“今人学书,需从唐人入手”的研究论述,认为清代碑学的兴起涉及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乾嘉时期推崇欧体,并以《化度寺碑》和《九成宫醴泉铭》作为唐楷研习的典范;二是面临佳帖难求的困境,虽然当时唐碑的留存情况与佳帖相比无甚乐观,但可以“书于壁间,观之入神,会悟其意”。尽管传拓会导致字形的失真,但仍有真迹可考,这些使清代前中期对书法古意探究的重心逐渐向以欧阳询为代表的唐碑转移[2]47-50。对六朝碑版推崇的盛行可以追溯到乾隆、嘉庆之后,相关的学术著论呈现出由唐碑向六朝过渡的趋势,由阮元建立了碑学理论框架的雏形,并提出了北朝碑刻为“书丹原石”,将其奉为唐楷追溯的本源。金丹在《包世臣书学重新审视》一文中也提到了郑簠、金农等前碑派对书法“宁丑毋媚”的审美取向(与清代书学家对将书法取向与取仕紧密关联思想的反叛有关系),同时受到了以隶书为“古法”观念的影响,阮元、包世臣等人开始推崇北碑,并成为乾嘉金石学风的重要推动者[3]。
另外,在这一崇碑观念中,涉及南北分界的问题,陈介祺对北碑的推崇和南北分界一说的论述为“钟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法真力足”。这一分类不仅是从书风上进行区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与以崔悦、卢谌为代表的北派),而且将南北之分与碑、帖的对立呼应。从康有为对这一划分的批判来看,如此分类的目的并不单纯是要对书体进行严谨的学术区分,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看似中立的划分方式来为对传统帖学的变革找到合适的出口。在当代学者马新宇看来,除了前人对这一区分的批判外,以碑、帖的区分来衡量书法艺术“古法”的得失并不严谨。第一,碑与帖从“文”的题材、用途、载体以及制作技巧来看,都有较大的不同,很难单单通过视觉风格来衡量和比较;第二,讨论南北书法风格之异同却忽视了同类之间(南碑与北碑、南帖与北帖)的对比,并不严谨[2]20-25。尽管如此,这一概念划分方法论的缺陷正是隐匿于书体单纯美学风格讨论之后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这一方法才得以宣传“尊碑”的思想,而对“帖”的态度之成因又是什么。
2 帖学——作为典范的衰落
在《清代碑学的兴起与发展:一个“范式”转换的研究》中,帖学范式源于对书法典范王羲之及其相关作品的推崇,与其兴起直接相关的因素主要为帝王对书家的推崇,如宋太宗刊刻了收录历代经典法帖的《淳化阁帖》,从统治的角度对书法范式进行规范。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注重卷面书写,致使诸多文人以帝王尊崇的帖法为参照,力求通过书写入仕或进入书家之流[4]172-174。既有帝王的推崇,则上行下效,文人便将之作为典范,尤其是以“二王”手札为代表,其楷则“中和”之美成为书法的审美标准与评鉴参照,孙过庭曾在《书谱》中赞其“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这一现象致使帖学的兴起以宣传时代推崇之典范为动机,并形成带有通过书学实现功利之志之嫌的帖学范式体系。阮元曾评价其为“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褉帖》之外,更無书法”,肯定了以王羲之为主的晋唐书法体系,以书帖为载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5]81-83。
而帖学的衰微,与至晚明尤盛的以帖学临写为主的书法承续体系逐渐僵化息息相关。清朝统治加强了对学子思想文化的钳制,导致许多针砭时弊的主题受到“文字狱”的打压,学子们转向对金石学的深入探究,致使书法审美风尚发生转向。帖学书法典范的权威性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对金石古迹的临摹,不仅停留在遗貌取神上,还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注入古迹中,由帖到碑的转换在文人美学意趣的转圜中表现出了由范本规化到精神关注,由得其神貌到变通其法,对传统的批判和变革的尝试。
3 碑学与士人身份转化
清代士人身份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的“尊碑”风气,一方面缘于清朝科考录取名额的缩减,加之对明朝以来程朱理学的质疑,许多学子在亡国之恨、加官无望之后致力于对精神学术的复兴,并积极通过自身学识抱负谋得生存和声名。
学者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指出,除科考体制和复兴思潮的影响外,清代幕府兴盛亦得益于清统治的支持,游幕学士大多为家境贫寒或科举失利的“无组织社会自由流动资源”,不利于统治权威的巩固,而幕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情况起到了调节和引导的作用[4]29-30。这一引导主要表现为清中期皇帝对以考据学为主的学术文化的高度重视,“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其事皆有待于学者”,而对游幕学者而言,受到传统“士农工商”价值体系的影响,为传食之客或为人幕之宾亦是时下的良选[6]。以汉学为主的阮元幕府有学人120余,成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学人幕府,主要从事与汉学、金石学相关的编书与校对工作。其中有影响力的金石碑刻著录如阮元署名,朱文藻、武亿等人撰著的《山左金石志》(一说为阮元、毕沅同著),对山东地区的金石碑刻进行了系统的搜寻和研究,主要涵盖商周到元代的碑刻内容,因其认为明清碑刻在形制、字体上与隋唐相近,同时反映出明朝至清初碑学的发展较为缓慢。还有阮元署名,何元锡、赵魏等人主撰的《两浙金石志》,对浙西、浙东地区自秦到元的金石碑刻进行发掘和编著。
此外,以阮元为例,因其在嘉道年间时任封疆大吏,其幕府在组织学术活动之外还会协助处理各种政务,即清代幕府多为学术与政治活动并行,为其将时政、士人抱负与本篇所探讨的书学相互通融陈述提供了条件。包世臣也曾入陶澍、裕谦、杨芳幕府,并为其出謀划策、代写文书,在入陶澍幕府前就曾为两江总督慷慨献言,后佐陶澍处理盐政,因陶澍幕府沿经世之风主张改革活动,在包世臣的“尊碑”论著中亦可以见得其改革的意图[7]。
除去幕府制度对学风思潮的影响外,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进步思潮的发展,也演化为探究清代文艺风气的重要前提。张研等人在《清史十五讲》中将这一时期文艺发展的学术语境归纳为两种学风的流行,即“经世致用”与“考据之风”。经世致用以颜元、李塨为代表,针对清朝正统对理学思想的延续(崇儒正道,强调三纲五常),认为学术应致力于培养济世人才,重视知识的实用性[8]。考据之风则崇尚通过科学的考据方法对文献古籍进行重新挖掘整理,推崇汉学,并对今文经学学说进行批判(乾嘉学派为清代的古文经学派,倾向于考古、文字学,至嘉道时期,今文经学被主张变法的康有为等人推崇)。这两种思潮皆可以被看作对经学的延伸和对理学的批判。早清时期相较于“经世”,诸多偏向考据的学者转向了较为“避世”的纯学术考证,直至18世纪初期,考据学逐渐发展为主流,阮元便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经学成就,由探求义理转向金石文字音韵之学,其碑学著论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侧重于历史还原与考据[5]29-37。
而在康乾之后,随着仕人学者对社会矛盾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许多学者倾向于就今文经学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发展来推动新的经世思潮,包世臣便是这一时期新兴经世文派的主张者和推动者,其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认为文章当与经世相结合,需有关国计民生,不是空疏无用之学。在其《艺舟双楫》中,虽然继承了阮元关于北碑南书的思想理论,但不止于考古,不仅通过笔法、意趣和审美对北碑进行鉴赏与肯定,还借由“尊碑”这一追古的审美观念来匡正时弊,并总结出了更为具体的碑学风格与笔意技法作为依据[2]45-47。
4 结语
由“尊碑”之书学风气产生的时代动机得以见出,清代由帖学到碑学的转变不仅在于书学审美的嬗变,还是对书学谱系的重新审视。首先是关于书学典范审美方式的转换。清代文人书家开始将其视野由“二王”“四家”转向碑版石刻,书法所承载的文化也不仅限于文人雅士之流,不只是对金石学的深入,而且“乡野碑版”“穷乡儿女造像”乃至“酒肆招牌”都可成为其书法取法的对象。从书学沿革来看,这一趋势为清代书法“形”的塑造、“艺”的表达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经世思想的复兴亦推动书学由固化体制转向注重文人气质风貌、个性意趣。
此外,这一时期,科考制式内容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对幕府形制的支持,一方面,为时下通过幕府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如阮元幕府关于金石考据的成就,为其“二论”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参照;另一方面,幕府的协政之职能,为不少文学家、书学家将其政治理念、变革思想借由学术理论彰显出来创造了条件。
以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尊碑”思想与历代碑学沿革为例,在关于“尊碑”思潮与社会转向的讨论中,本文通过“碑学”“帖学”风气的成因及其社会背景,从书学典范的移位及文人身份的转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尊碑”思潮的时代动机,并就碑帖的南北划分理论讨论了该分类的流行在书学风格以外的社会动机与其中蕴含的政治性和变革趋势。结合包氏“尊碑”的时代语境与历史上碑学的理论沿革与发展趋势,以及上文提及的社会成因,从横(时代背景)、纵(碑学沿革)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书法美学风格中的语境要素与时代必然性。
参考文献:
[1] 戴小京.康有为与清代碑学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56-57.
[2] 马新宇.清代碑学研究与批评[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7-50,20-25,45-47.
[3] 金丹.包世臣书学的重新审视[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5:23-25.
[4] 胡泊,弘陶.清代碑学的兴起与发展:一个“范式”转换的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9:172-174,29-30.
[5] 王友贵.清代北碑书学观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5:81-83,29-37.
[6]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26-128.
[7] 欧阳世明.阮元《两浙金石志》考述[J].艺术家,2019(1):172-173.
[8] 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4-176.
作者简介:朱子晗(1999—),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书法与篆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