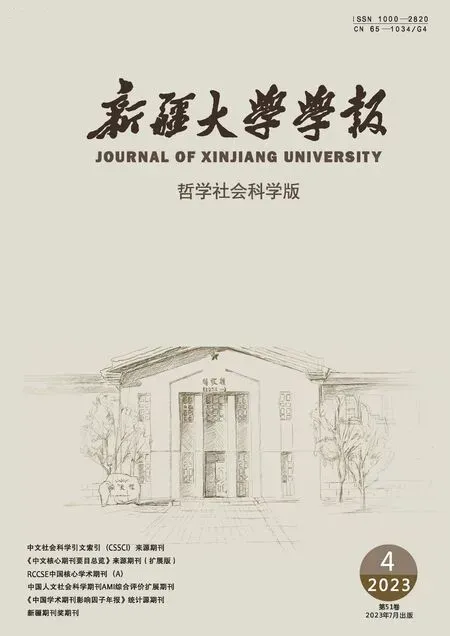古汉语指示代词“是”的功能、特性与形成*
薛宏武,闫梦月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一、引 言
先秦汉语的指示代词系统及其类型构成状况如表1。“是”为指示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的中指代词①参见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2-102页。。先秦指示代词在句首作主语倾向选择“是”,“此”次之。②参见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48-149页。换言之,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也能用“此”回指,例如(1)的“此”回指的是因果事理句。观察:

表1 先秦指示代词类型及构成
(1)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j,此j变之正也。(谷梁赤《春秋·榖梁传》)
看来用“是”回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是条软规则。这自然会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明确回答:一是回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为何倾向“是”,是巧合?二是回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上“是”与“此”等有何区别,或者说“是”的回指特性为何?三是该特性从何而来?
二、指示代词“是”的语篇、人际功能及其特征
(一)指示代词“是”的语篇功能与特征
“是”通过回指先行成分去组织句子(sentence),就是其语篇功能。例如:
(2)S1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S2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S3今男女同贽j,是j无别也。(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例(2)的小句“是无别也”通过“是”回指先行小句“今男女同贽”而形成一个句子。郭锡良把“是”的这个功能称为忆指,认为这是“此”等所没有的功能,因为先秦指示有形可迹、近而可指的事物用“此”。③参见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0-103页。下面引述其两例,比较:
(3)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j,守者曰:“此j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孟子《孟子·尽心上》)
(4)杨氏为我j,是j无君也。墨子兼爱j,是j无父也。无父无君j,是j禽兽也。(孟子《孟子·滕文公下》)
例(3)的“鲁君呼于垤泽之门”有形可迹、近而可指,即“此”的回指特征是[近指][实体]。例(4)的“是”回指对象如“杨氏为我”等,是抽象事理。抽象事理与说话人没有物理距离,不存在远近分别。即“是”的回指特征是[-远近][-实体]。
“是”的回指特征[-实体][-远近],可以一定程度说明它是由谓词“是”发展而来的,而绝非是基于语音巧合的假借,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与“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相宜。
(二)谓词“是”的基元及基本特征
《说文解字》把谓词“是”释为“直也,从日正”[1]。段注曰“直,正见也。从日正,会意。十目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谓以十目视乚,乚者无所逃也”[2]。这有三层意思:一是“乚”指“曲折隐晦的事物没有逃处”,“直”是“十目视乚”,因此“是”的意义是烛照洞悉一切,表示认识了事物的全貌。“认识事物全貌”就是“完尽”,概括说是[周遍]。二是“直”为“正见”,“正”是不曲不弯不斜。即“正见”指认识事物不仅没有歪曲并已达到充分。换言之,“是”指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真实相吻合,通俗说就是“正确”“对”等正恰义。三是“天下之物,莫正于日”说明以“日”为“正”是主观看法,抽象性显著。综合看,谓词“是”语义基元是“正见”或“正恰”,特征是[主观认定][周遍][抽象]。为行文简要,下面把谓词“是”及其基元分别称为“是0”与[正恰]。相应地把指示代词“是”称为“是1”,小标题及用例里的“是”除外。
肖娅曼构拟了“是0”发展为“是1”过程①参见肖娅曼《中华民族“是”观念来源于“时”》,《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8-43页。,本文将之概括为如下一条Gs链:
日正→时间名词→指示时间→指示其他对象
Gs是一个语法化过程,因为“是0”语义在缩减或虚化,指示功能却扩展。按照语法化的滞留原则(persisting),“是0”的基元[正恰]或其[主观认定][周遍][抽象]的某一或某几方面会在“是1”有所滞留的。从例(2)(4)看,首先是滞留了[主观认定],如“无别也”是说话人认为“男女同贽”与“没有分别”等同。这种看法与先秦历史文化的客观实际达到了统一。当然也有纯主观看法的,如“韩是魏之县也”(刘向《战国策·赵策》)。因为韩国客观上不是魏国的县,但叙事者认为魏国用“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反魏”的手段,可让它成为魏国的县。其次滞留了[抽象],因为它回指对象是事理或抽象物,如例(2)(4)的“男女同贽”“杨氏为我”“墨子兼爱”。即使“韩是魏之县”的“韩”也难说就是实体,而是个抽象的“国家”概念。最后是滞留了[周遍],只不过是隐性的,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断言。如断言例(4)的“是禽兽也”前提是“无父”“无君”,缺少任一方面都不能成立。当然[周遍]是代词共性,因为它们的语义都打包(wholly packaging)自先行成分,但“是1”本身就有此语义特征。这在它语法化为系词、特别在系词的词汇化中有充分体现,这方面拟另文考察。
当然“是1”也滞留了基元[正恰],如“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孟子·梁惠王》)的“是”就有“这正是/恰恰是”的意味。只不过[正恰]有时受语境影响表现不明显,例如(2)与(4)的“是1”就是这样。基于此,下文不再专门对此说明。
总之,“是1”不仅滞留了“是0”[主观认定][抽象][周遍],同时也滞留了它的基元[正恰]。
(三)指示代词“是”的回指本质、人际功能与成因
把“是1”称为回指代词是静态的表象刻画,其本质或动因则是认定追踪事物、事件或其参与者(下称X),具体表现为X 在语篇的某处再次被提及。追认不仅是语篇组织方式,也关系到怎样便于受话人解读。典型的追认是用指示代词,这在抽象语篇很普遍,如例(4)。此外,指示代词作为追认的手段,还可能获得“评估”意义。Martin 和Rose曾刻画过英语的追认系统,分别为图1与图2。为凸显指示代词的追认类属,本文用加重的斜体及下划线体现。②参见J·R·Martin&D·Rose《语篇研究——跨越小句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72页。

图1 英语的“认定”系统

图2 英语的“追踪”系统
图2 的“桥接/推理”是指用指示代词打包先行成分X,并把它延伸为后续句的话题。例如:
(5)The effect of amnesty is as if the offence had never happened, since the perpetrator's court re‐cord relating to that offence becomes a tabula rasa,a blank page.This means…that the victim loses the right to sue for civil damages in compensation from the perpetrator.That isindeed a high price to ask the victims to pay,butit isthe price those who negotiat‐ed our relatively peaceful transition from repression to democracy believed the nation had to ask of vic‐tims.
例(5)的this 打包the effect of amnesty(X)目的是追认并延伸“民事损害赔偿的后果”(This mean……)。之后它又用that 打包追认且获得评价(That is……),最后是得到认定(it is……)。this与that 追认X 的效应是,使X 的意义变小或具体化,这显然是二者在句内作话题被陈述的结果,因为被陈述,它就可以得到更具体的解释。此外,this与that 还可以用自身明确的语段跟X 的所在句在语篇内形成一个间停(pause),从而起到标示句界的作用。
要之this与that的功能是:ⅰ)追认X;ⅱ)打包X,功能是回指;ⅲ)给语篇添加语段停顿,并桥接X;ⅳ)作话题,在后续句获得新的句法语义角色与评价。其中ⅰ是动因,ⅱ、ⅲ、ⅳ是结果。可见回指就是追认,其语法作用是组织语篇、人际评价以及给句子确立语段性的界限等。
“是1”与this、that的功能基本平行①严格说this、that跟“此、彼”类同。“是”跟二者除了是近、远指与中指的不同外,还在于前者无[主观认定]而后者有。,如它在例(2)回指“今男女同贽”(X)就是追认,语法效应一是在X 与“无别也”(Y)之间形成明确的句界,便于解读;同时也把X 与Y 桥接起来形成解释关系。二是它打包X 后,作Y 的话题。由于被Y 陈述,意义不仅延伸了,而且还产生了新的评价义“男女同贽等同于没有分别”。
“是1”获得人际评价义,表现在它的谓语“无别”是性属成分,性属成分有评价性。《今文尚书》《左传》《孟子》等有限语料显示“是1”的谓语就是性属成分,行为或动作的鲜见。
(6)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左丘明《今文尚书·秦誓》)
(7)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年》)
(8)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众也。(孟子《孟子·离娄上》)
“能容之”与“寡人之过”是性属成分,“播其恶於众”表示“不仁而在高位”之人的属性而非动作行为。例(6)(7)(8)还显示“是1”身兼二职,回指先行成分X,功能是外连;在句内又给Y 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称或陈述对象,功能是内指。这两方面形象地说就是桥接。它集语篇组织及句法语义于一身,是二者之间的界面。它回指X,在强调X的同时,也把“是Y”标示为一个清晰的句子。
再看“是1”的忆指。这是指信息(语篇)加工中的心理活动——忆起先行信息并追认。“是1”的追认功能就是主观再肯定,究竟地说是来自其基元的[主观认定]。“‘是’近指性不及‘此’强,但承指却比‘此’更合适。”[3]“承”就是在语篇里承接上文,至于为何“更合适”吕叔湘先生未说明。我们认为是“是1”有[主观认定],它的追认度比较强且没有区别性,能单一地凸显对象。
观察表1 可看到,Ⅰ、Ⅱ、Ⅵ、Ⅶ的指称特征决定了它们作语篇回指成分都不够理想。Ⅲ与Ⅴ特征是[可点指][远近][区别],[可点指]是说被指对象是可点指的“形而可迹”的实体,[区别]是说点指近的实体一定与远的区别。显然,二者与回指的抽象事理不相宜。“是1”则不同,[主观认定]是不可点指的心理意识,没有远近之分,自然与回指的动因、目标及对象最相宜。至于它的近指性弱,跟它在元语里没有对立词有关。“此”则不同,元语里有“彼”跟它对立,近指示性强。①“斯”与“此”是地域差别。基于此,本文以“此”为例讨论。参见朱淑华《上古汉语指示代词“此(斯)、是”名词性回指比较》,《社科纵横》,2008年第4期,第111页。总之“是1”的忆指与更适合承指特性,是基于[主观认定][抽象]。可见“是0”语法化为“是1”之后,语义基元及其特征仍起着应有作用,这显然是语法化的后拉或回头看效应的体现。正因为这样“是1”才会回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因为语法实体组配中,语义或功能相宜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上文指出“是1”在衔接语篇中还可被解释,如例(4)的“无君”就是解释它的。解释关系容易发展为因果关系,如例(2)的S1、S2是大前提,S3是小前提,“是无别”是从大小前提推理来的。“是1”是处在推理关系句中的虚成分,吸收语境义获得因果义也在情理。这在先秦就已普遍。例如:
(9)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下》)
“是1”表因果关系,还表现在与“故”词汇化为因果关系词“是故”。例如:
(10)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於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1)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孟子《孟子·离娄上》)
“是故”位置灵活,在例(10)是在主谓之间,在(11)处于句首。比较例(9)(10)(11)与(12),还可发现它们之间是变换关系,说明“是1”或“故”择一即可表因果。
(12)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孟子·梁惠王》)
“是1”表因果,至今还保留在推荐、序跋等语体里,如“是为荐/序”等。顺及指出现代汉语的指示代词表因果也是常见的。例如:
(13)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那就证明我…动了情?(王朔《过把瘾就死》)
指示代词发展为表达因果关系,是普遍现象,如Hixkaryana(希卡利亚纳语)、Khasi(卡西语)及德语等。②参见B·Heine&T·Kuteva《语法化世界词库》,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107-108页。观察:
(14)The shops were closedsoI didn’t get any milk.
尽管例(14)的so 是表结果的,但语感里它仍然有回指先行句的迹象。
前文指出“是1”在回指先行成分X 的同时,还可以给句子立界,表示为构式[…Xj,[S是jY…]],记做Ct。但它仅是Ct的一个便于书面解读的羡余成分,比较例(15)的第一二与三句:
(15)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j,øj礼与?”孟子曰:“øj礼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孟子·离娄上》)
第一二句没用“是1”,因为对话里可用停顿识别出“礼也”是一个独立句。第三句用了,说明说话人用它追认强调“嫂溺不援”之外,还要明确表达“豺狼也”是独立句,因为它可使句子有清晰的句界,避免解读费力,这对无标点的古代书面语很必要。看来“是1”还体现了表达清晰的方式准则与礼貌原则③参见何自然《语用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1-100页。。观察例(15)还可看到“是1”回指的是叙述性成分,“豺狼”是它的评说成分。概括说,例(15)信息分布与构成是由叙述到评论,“是豺狼”是语篇信息峰。
(四)“是”的特性
“是1”的回指本质是追认。它是忆指的且更适合承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是基于[-可点指][-远近][-区别][主观认定][抽象]。它桥接语篇,不仅可标示句界、表达解释关系,还是语篇的信息峰。它继承了“是0”的[主观认定][抽象],是一个重指示代词。这就是有学者认为它有“论断”等意义的所在①参见敖镜浩《〈左传〉“是”字用法调查》,《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此”以“人的双脚比并、停止不走”表示“就在此”之意,是个罕见的不用假借而专为指示代词造的字。②参见陈年福《甲骨文“何”“此”用为代词考论》,《中国语文》,2006年第5期,第402页。论断基本可信,但我们认为“此”不是专为指示代词造的,它最初是动词,指示代词是语法化的结果,过程如下:
Gc:ⅰ)人双脚比并、停止不走→ⅱ)实体在此→ⅲ)指示实体→ⅳ)指示抽象事物
其中的ⅰ说明“此”是空间动词,近指用法是由ⅱ(就在此)发展而来的。ⅰ到ⅱ以及ⅱ到ⅲ是转喻,而ⅲ到ⅳ是隐喻,这就是它的语法化机制。这样,“此”自然就可带有[实体][空间][可点指]特征。这就是它多指示形而可迹、近而可指的对象之因。当然它也可指示抽象事物,如例(1),但这是指示功能的泛化。至于它的指示性强,一方面是滞留有[实体][空间][可点指],同时也跟元语里有对立的“彼”相关。
三、指示代词“是”的话题标记功能与特征
“是1”标记的话题有[(惟)NP 是VP]、[是NP 也(,)VP]两种形式。
(一)[(惟)NP是VP]与“是1”的特征
(16)a.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左丘明《今文尚书·蔡仲之命》)
b.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柏舟》)
c.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左丘明《左传·僖公四年》)
例(16)的“是”通常称作复指代词。复指基本就是回指,差异仅在两方面:一是复指的对象是NP,如“德、下土、不谷”等;而回指对象是NP、VP或S,如例(2)。另一方面“是”与复指的NP 紧邻,如例(16);而“是1”与回指对象X 之间却有停顿,如例(2)。当然复指的“是”与X 之间也会有停顿,但是有条件的。观察:
(17)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左丘明《今文尚书·牧誓》)
例(17)为了表达经济才出现了“崇、长、信、使”共用宾语“四方之多罪逋逃”现象,“是”仍是紧邻回指代词,这样才在“四方之多罪逋逃”与“崇、长、信、使”之间出现了停顿(书面表现为逗号)。下面为比较之便,把例(16)等的复指“是”称为紧邻回指,表述为“是1a”,以区别于它的语篇回指。
例(16)用“是1a”回指NP 并且还加了一个肯定语气词“惟”,目的是使NP 成为强式焦点结构而置于句首强调,因为先秦尚未发展出用词汇强调NP宾语的强式焦点结构。③参见石毓智、徐杰《汉语史上疑问形式的类型学转变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及其影响》,《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第454-458页。那么,句首强调NP 有何独特性?句首强调NP 宾语的句子是受事主语句吗?若不是,成因是什么?
1.句首与句尾的语法特征
重要信息的词语在句子里有选择靠前或靠后分布的特征,前者尤为突出,因为信息存储与提取时先出现的会影响后出现的,此即前摄干扰。④参见桂诗春《实验心理学纲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9-133页。句首地位显著⑤句首包括次话题/次主语位置,如例(17)的“妇言”前面其实还有主话题/大主语“商王受”。为讨论方便对此不做分析,这不会动摇前摄干扰原则及相关结论。,信息可先入为主地被存储与提取,是心理焦点域。另一方面信息分布还遵循尾重原则,因为句调核心常在句尾,只有二者一致,句子才能平衡。⑥这指一般句子,强调句并非如此。这样句尾NP 自然带有句调核心的重音,是个重成分。尽管如此,它的信息地位却是一个常规的自然焦点。
2.[(惟)NP是VP]句子特征
例(16)的句首NP 在句尾时是自然焦点,也是被强调的,但仅是靠自然重音提示的弱强调。前置到句首不同,如“德”既是心理焦点又是重成分,特别被“是1a”回指后是重上加重的同位结构“德是”。“德是”句法语义与“德这方面”等相当,再加上排他性“惟”的强调,语义更重了。总之句首“德”的强调性比在句尾显著,是话题焦点句。
例(16)的句首NP 表面是受事主语,如“德”是“辅”的受事主语,但语感上却与(18)的受事主语句有异,比较:
(18)a.蔓草j犹不可除tj,况君之宠弟乎?(左丘明《左传·隐公元年》)
b.锲而不舍,金石j可镂tj。(荀子《荀子·劝学》)
c.兵j挫tj地j削tj,亡其六郡。(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可发现例(16)与(18)有五方面不同:
第一形式不同。例(16)的句首NP 有连带成分,且它们已组块为同位结构[(惟)NP 是]。[(惟)NP 是]音节数是[1,7],单音节的如“德”;7 音节的少见,如例(17)的“四方之多罪逋逃”。例(18)的NP 无连带成分,通常是单或双音节的。再看VP,例(16)的VP 是单音节,如“辅、冒、为、继”等;而例(18)的VP 是复杂结构,如“犹不可除”“可镂”等,单音节的罕见。总之,例(16)与(18)形式对立,前者NP 复杂而VP 简单,后者NP 简单而VP 复杂。本文通过CCL 语料库的《诗经》《左传》《战国策》《史记》检验,发现例(16)与(18)的NP 与VP 的确有这两方面的对立,说明例(16)的NP 长度总体比(18)的长,是个重成分;而它的VP 相对于(18),则是短的轻成分。
第二语义语法不同。例(16)的[(惟)NP 是]语义重且有对比性,是话题焦点。例(18)的NP 语义轻没对比性,是受事主语,如“金石、兵、地”等。至于“蔓草”带重音有对比性,是语境里跟“君之宠弟”对比形成的。VP 方面,例(16)的行为或动作性模糊而状态性明显,如“惟德是辅”的“辅”。这反映在形式上就是“辅”之类VP 不带动作或行为标记,即(16)的VP 没有动态性或被动义,是事态性的(affair-state)。现代汉语“类似”句子亦此。观察:
(19)a.你这个家伙,不敢来硬的。(老舍《老舍戏剧》)
b.纪晓岚这个人一向以机巧欺人,沽名钓誉。(电视剧《铁嘴铜牙纪晓岚》二部38集)
所谓类似,一是说例(19)a 里回指“你”的“这个家伙”是指量名结构,二是指“来、欺、沽名钓誉”还有连带成分,如“不敢、一向”等。但不管如何,VP 都呈状态性。例(18)的VP 是动态的,被动义明显,是动作行为句,如“蔓草不可除”“兵挫地削”。并且若语境需要,可用介词引进施事而变为被动句。
第三信息分布模式不同。第一二方面显示例(16)的信息分布是头重尾轻,NP 置于句首是语序标记,“惟”与“是1a”则是使之成为话题焦点的词汇标记。它综合使用了词汇与语序标记,显然NP 是强式话题焦点,比在句尾作弱式自然焦点重。(18)的信息分布相反,是由轻到重,NP轻而VP重。
第四形成动因不同。例(18)的NP 是域内论元,移到句首是为获得主格位,并且是在拼读(spell out)之前就已完成的内部句法运算,如“蔓草犹不可除”形成可简要表示为:
[CP蔓草j[犹不可除tj]]
例(16)的NP 是语用移位,是外移位,如“惟德是辅”之“德”,“惟”与“是1a”是语用标记。移位动因不同,句子功能有异:例(16)是情感评价句,(18)是叙事句。前者所以有显著的人际评价功能,是基于“是1a”的[主观认定]。看来,例(16)与(2)是平行句,平行性的基础是“是1”的回指功能。
第五句首NP 语法身份不同。例(18)的NP,如“蔓草”立足语篇看也是话题,但从句法语义看却不是。(16)的NP,如“德”,句法语义与语用都是典型的话题。顺及指出例(16)的NP 宾语前置除了与强调有关外,也跟语篇组织有关,如前置“德”可跟后续“惠”平行对比映衬。再如例(17),前置“四方之多罪逋逃”可跟“妇言”平行衔接。至于前面又用了个“乃”,目的是使它形成强于“惟妇言”的递升语势。
3.“是”话题化NP宾语的基础与特征
例(16)是话题句,“是1a”是NP 话题化标记,“惟”是强化NP 话题身份的选择成分。有之,“德”的话题焦点身份更显著;无之,它仍是话题焦点。现代汉语的指示代词也有此功能,观察:
(20)马承林这人以前你曾给俺讲过。(李文澄《努尔哈赤》)⇌a.马承林以前你曾给俺讲过。
例(20)跟其变换式a分别是情感句与叙事句,差异是由“这人”的复指形成的。
4.“是”的特征
例(16)用“是1a”与语序把句尾自然焦点NP 前置为强式话题焦点句,结果是NP 话题化。在此过程“是1a”的[主观认定]是关键成分。无之,句子或者是受事主语句,或者不合法,或者可受性有问题,如删去(16)的“是”即可看到。问题是如例(16)a 所示,句尾NP 宾语既可用“是1a”复指,如“德”;也可用泛指“之”复指,如“惠”,那么二者复指功能有何区别?
回指是追认,“是1a”紧邻NP,它的追踪功能虽有抑制,但认定功能还在,因此对NP 的强调力一定比“之”强,如“惟德是辅”就比“惟惠之怀”的强调性显著。事实支持有二:一是句尾NP 宾语前置多用“是1a”;二是含有疑问代词的NP宾语前置时,用“之”而不用“是1a”。观察:
(21)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左丘明《国语·勾践灭吴》)
疑问与否定的对象是强式焦点①参见徐杰《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自然“何後”就是强焦点结构,它的语义比一般NP 重,无需再用[主观认定]的“是1a”就可前置到句首,因此“之”就是标记它是话题化的身份。由此可发现两点:一是先秦NP 宾语话题化有强弱两式,分别用“是1a”与“之”标记。二者与标记对象的匹配原则是语义重者用“之”,轻者用“是1a”。二是进一步说明“是1”确实是重指示代词,“之”是空代词。顺及指出表1 的Ⅲ与Ⅴ,系统看也是“重”代词,但它们主要是以元语对立体现的,如“彼”与“此”;或完全由元语对立体现,如“斯、夫”。至于Ⅵ的“莫”、Ⅶ的“然”,与“是1”一样,本身就是重代词。
(二)[是NP也VP]句与“是”的特征
“是1”还跟语气词“也”同现标记话题。为了与“是1a”区别,下面把它称为“是1b”。
句法上“是1b”主要功能是作NP 的限定语。例如:
(22)季武子将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3)(威后)乃进而问之曰:“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刘向《战国策·齐策》)
例(22)与(23)的“也”显性功能是提顿,本质是句子主次信息的分界。它提示“人”“其为人”是话题的同时,还标记后面的部分是主要信息。再看“是1b”作用,一是把(22)的类指的“人”限定为定指话题“是人”,“是人也”与“这个人啊”等相当。二是(23)的“为人”被特指代词“其”限定为特指话题后,“是1b”的指示功能羡余,作用是标记并凸显话题“其为人”的。看来,例(22)(23)的“是1b”功能与[(惟)NP 是VP]的“惟”平行,平行的基础是[主观认定]。语料考察显示在“其为人”这类话题前面加其他的指示代词的用例是没有的,说明“是1”确实是个携带了[主观认定]、[抽象]等的重代词。
总之“是1b”是凸显NP话题的标记。这还有一个证据,现代汉语的“‘这’能加大话题的可识别度”[4]。加大话题可识别度即凸显话题身份,如例(24)(25)的“这”显然是跟“是1b”的功能平行。观察:
(24)董将士一见高俅……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施耐庵《水浒传》)
(25)这人呀,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净想着往高里攀,回头摔个大马趴,脸往哪儿搁?(陈建功《皇城根》)
再看例(22)(23)的VP 及句义特征。VP 也表状态,是话题评价成分。这跟例(16)的VP 平行,只是句子感情比(16)的强。原因在于“是1b”是NP的限定语,而“是1a”是NP 的话题化标记。当然若“是1b”羡余,它就是NP 作话题的标记及指示说话人情感的成分,如例(23)。可见“是1b”的限定性跟情感表达是反向关系,限定性越弱,情感表达越强。反之,限定性越强,情感表达就越弱,
当然“是1b”也有语篇功能,如例(22)的“是人”通过替代“公子裯”与先行句衔接。另一方面通过语义打包“公子裯”,与“季武子将立公子裯”连贯。可见“是1b”与“是1a”的功能也基本平行。看来“是1”确实是滞留了“是0”的基元与特征,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巧合,因为例(16)(17)与(22)(23)的“是”,紧邻回指的对象与限定的对象仍然是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物,如“德”“夫言”与“人”“为人”等。
四、结语与余论
“是1”由“是0”语法化而来,继承了后者的基元[正恰]及[主观认定][抽象]等语义特征,是一个重指示代词。这样才更适合回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作话题标记及表达评价,才与“此”的篇章回指、“之”的话题标记功能形成差异。“是1”作话题跟作话题标记的功能平行,都有语篇功能且其谓语都呈状态性。此外,还发现“是1”标记的话题句与受事主语句对立,包括谓语的状态与行为、人际评价与客观叙事两大方面的对立。当然“是1”的“是1a”与“是1b”标记的话题也有平行性:一是前者紧邻回指前置NP 宾语并将其话题化,后者限定句首NP 并将其话题化;二是它们的谓语都呈状态性,评价或情感特征明显。
学界共识是系词“是”(下称“是2”)由“是1”发展而来,这有两个根本问题需回答:“是2”的形成是不是语法化,跟印欧语be 之类系词的根本不同究竟如何产生或体现在哪?其实二者得到根本解决都离不开“是1”的特性。我们初步考察发现“是2”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是1”演变为前系词(pre-copula),下称作“是21”。它不是成熟的系词,有点类似附缀(clitic),功能是作“前谓语”[5]。二是“是21”演变为成熟系词或判断动词。显然,不执着于原子主义的语法化观,从语法化是构式的语法化看,①See C·E·Traugott&G·Trousdale.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2,pp.100-105.前者完全符合语法化一般规律:不仅语义、构式义及其功能在缩减,并且产生了一个新范畴“是21”。后一阶段是“是21”去语法化而词汇化。有人认为主要是由判断句的NP 次类、变换、语序变化、句式变化及语气变化引起的②参见马贝加、蔡嵘《系词“是”的语法化》,《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3期,第57-60页。。观察客观但未触及根本,因为这些是外部机制。本文认为“是21”能词汇化,是滞留了“是1”的[主观认定]。无此,不仅无法说明“是1”可语法化为前系词而“此”等不可之因,更无法充分解释“是21”的前谓语特性,当然也不能充分说明“是21”的词汇化之因。“是1”若是个空代词,是不可能词汇化的。一句话在“是1”发展演变为“是2”中,传承的[主观认定]是内因,这已有学者意识到了。可见“是2”是一个有[主观认定]的主观动词,相当于英语“X to be considered/affirmed as Y”等结构意义或功能。本研究就是为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而作先行探索的。至于问题的具体解决与解释,另拟撰文详论。
——以《红楼梦》译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