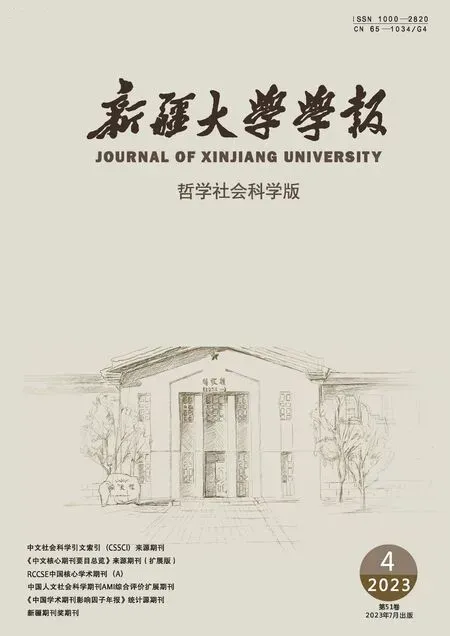《汉回合璧》编者及版本研究*
阎婷婷,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汉回合璧》①《汉回合璧》之书名见于该书序、跋文,其“回”指清代的维吾尔人。成书于清光绪六年(1880),系编者受命于钦差大臣左宗棠而撰。除序跋,全书正文共收汉字1 056 个字,②陈氏《〈汉回合璧〉研究》摘要所述“汉字1 065个”实为笔误,国内引文多直接引用该笔误,实际收录汉字为1 056个。其文体沿用“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千字文韵文体,编纂时先列出汉字义项,再列出汉字标注的维吾尔语注音(简称“汉字注音”),最后列出对应的维吾尔语译文,更易于维吾尔族儿童诵读与理解。相较于传统蒙学识字教材“基本词汇为主,儒家传统词汇为核心”的特点,该书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吸收了部分边疆地区的特有专著词汇③正文所收词汇包括:“初一、十五、元旦、元宵、端阳、重阳、中秋、冬至、新年”等中国传统节日、节气词汇;“经、书、字、画、砚、纸、笔、墨”等中国传统日用器物词汇;“顶戴”“蓝翎”“花翎”等清代官员帽饰词汇。“卡伦”“戈壁”“沙果”“虫八蜡”等边疆地区特有专名词汇。(还包括部分满、蒙语词汇),是清代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儿童学汉语、识汉字,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基础蒙学教材。该书曾历经多次修订及再版,在新疆建省前后大量刊印,广泛应用于南北疆各地的官办义学、蒙养学堂中,对边疆地区的汉语推广工作起到了积极地引导作用。《汉回合璧》一书的编撰及推广不仅是清代新疆地区与中原进行良好文化互动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国内外学者对清末蒙学教材《汉回合璧》的认识不足,对其展开的文献学及语言学研究也十分有限,仅有两位学者对其进行过初步研究。我国学者陈宗振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简称“民研所本”)首次刊布了《汉回合璧》一书,于1989年在《民族语文》发表《〈汉回合璧〉研究》,④参见陈宗振《〈汉回合璧〉研究》,《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第49-72页。向世人介绍了该书编者、版式、体例等大致情况,同时对正文词汇部分进行了初步整理及校勘,并对维吾尔文部分进行了国际音标转写,探讨了清末汉维两种语言的书面语及口语之间的差异。陈先生细心整理所得的“国际音标转写表”为我们后期开展维吾尔语语言研究、汉语语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学者西村多慧基于陈氏构拟的近代维吾尔语口语语音,依据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天理本”)参照《畏兀尔馆译语》与《五体清文鉴》所记的“汉字译音”与“维吾尔文”进行了语言学研究,于2005年发表了《〈漢回合璧〉新ウイグル語の表記に用ぃられた漢語音にっぃて》(《〈汉回合璧〉维吾尔语标记所用的汉字音》),⑤参见西村多慧《〈漢回合璧〉新ウイグル語の表記に用ぃられた漢語音にっぃて》,《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2005 年第24期,第117-130页。重构了“汉语A 音”,认为该书所记录的语言为山阴方言,①西村氏关于《汉回合璧》编者为“山西省山阴人”观点有误,该书所记录语言为“山西省山阴方言”的观点亦有误。具有典型的西北方音特征。
上述学者研究所依据的两种《汉回合璧》广义上可以归为同一版本,但该版本正文存在多处误写、误译及字迹不清等现象,故版本质量不高,正如陈氏所指“本书中还有一些翻译不当,维文字迹混乱不清之处,使读者很难推断维文是什么词”[1]54。笔者在搜集资料时,有幸得见了不同版本的《汉回合璧》,在陈氏“民研所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参校其余诸本对该书的编撰背景、编者及成书时间进行重新考察。
一、《汉回合璧》编撰背景
光绪六年(1880)四月,清政府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向光绪帝上奏《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提出“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2]466,他对新疆善后的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着重推广启蒙教育,主张重修和新办书院,沿袭乾嘉时期的“双语双轨制”,即官办的义塾和蒙养学堂并行,督令各地善后局、房营广设义塾,招收回(维吾尔)民子弟,为其提供更多的教化场所。随后兴办书局刻印、刊发各类书籍,“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3]466。
同年八月《汉回合璧》应运而生。其编撰目的正如序跋中所言:“此议改行省,惟善后之策首重义塾……就汉文中至浅近之字,有事可指、有物可名者依类成句,注以回语,译以回字,俾各塾习是者由回语以明汉语,即由回文以明汉文。语言文字既明,再以六经四书进之,而为之讲解。”这正是对左宗棠在“新疆善后事宜”中提出的教育主张的落实,是一部符合清政府边疆治理需求而编撰的童蒙教材。该书的编撰、大量刻印与广泛刊发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是清政府普及基础蒙学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新疆的官办义学及蒙养学堂的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用教材,更为“新政”刊布后的“学校教育”教材编撰提供了参考,推动了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汉回合璧》编者及成书时间
关于《汉回合璧》的编者及成书时间,此前学界仅有“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1880)”一种观点,该观点源于“民研所本”与“天理本”的编者自序,依此自序不仅可以直接判定该书编者及成书时间,还可以得知编者为山阴县人,曾驻军于温宿(今阿克苏地区)。遂陈氏在其文中指出“孙寿昶为山西省山阴县人,其他方面不详,估计可能是久居新疆阿克苏一带并懂维吾尔语的汉族知识分子”[1]49,认定编者为山西省山阴县人,笔者不知此判定的依据,或许与清光绪年间新疆多陕甘地区官兵有关。此外西氏从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所记录汉语语音进行了研究,考虑语音上具有典型的西北方言特征,也赞同了陈氏的观点。
但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及山西地方志,并未找到有关孙寿昶的记载,故对早期两位学者提出的“编者为山西省山阴县人”观点感到质疑,认为有重新核定的必要。且随着新版本的发现,《汉回合璧》又见新编者史文光、张成基,因此关于此书的编者、成书时间需综合序跋及相关史料重新梳理。
(一)编者
1.孙寿昶
据《清德宗实录》卷之一百十六载“陕甘总督左宗棠又奏丁忧提督孙寿昶请暂留营”、《左宗棠奏稿》载“请将孙寿昶暂留办理营务片”可知,光绪六年七月,孙寿昶正效力于张曜麾下马步十四营(河南嵩武军),随其驻军于温宿地区,任河南候补知县一职。因其父病故,此时本应回籍讣丁父忧,但因营务处理得当,属军中得力一员,且短期内无人能胜任其职,故由张曜上奏饬回籍终制,准其暂留办理营务兼带队伍②“办理营务奏保道员用尽先知府、河南候补知县孙寿昶”。参见《上海官银号浙绍协赈公所启》,《申报》,1884 年7 月4日,第4版;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05页,第2700片——请将孙寿昶暂留办理营务片。。至光绪甲申年(1884),孙寿昶时任提督一职,仍暂留营,未回籍讣丁父忧。这与“民研所本”序言所述史实相符。
但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清代职官年表》等中均查无此人,遂参考了多部地方志文献,对孙寿昶的生平进行了重新考察,并着重分析了其籍贯归属。依据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二日(1884 年7 月4日)刊登于《申报》的一则赈灾款公示,止同年四月,上海官银号浙绍协赈公所又收到捐银两千四百两,其中“山阴孙寿昶捐银八十两,乌程施补华、钱唐蒋其章、山阴李福云三户各捐银四十两”[3]。笔者以此为切入点,率先确定了李福云生平,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记“李福云年五十六岁,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由行伍于同治六年投效嵩武军剿办捻逆,擒斩多名,奖给六品军功”[4]259,因孙寿昶似与李福云同为山阴人,随后查证了《绍兴县志》,在“人物列传”的“陈鈵列传”中找到了有关孙寿昶的部分信息,综上判定编者实为浙江绍兴府山阴人,字吉生,名寿昶,初任观察使,与同县陈鈵曾一同习于汴(今河南开封),之京师司缮写之役,似同任“汉笔帖式”官职,后同赴新疆。①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1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3107页。此也与奏稿中指出的“光绪六年同嵩武军驻军温宿、任河南候补知县”的史实相符,由此可以断定该书是孙寿昶在新疆南疆地区任职期间的成果。
2.史文光、张成基
笔者在搜集整理《汉回合璧》时,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及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有同名之作,但三馆著录编者均为史文光、张成基,经查阅此版本著录信息源于跋文中的“温宿戎幕长沙史君文光、郧阳张君成基编辑《汉回合璧》一书”,此外无其他信息。经考证,编者相关信息如下:
史文光,字觐农,②参见清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清水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长沙人,监生,③参见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31 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84页。曾任候补知县,④参见陶模撰《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七,吴丰培整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7 年,第39页;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稀见方志文献》55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632、639页。后官至知县。早期随湘军前往新疆,属刘锦棠马步二十四营(湘军)一员,光绪五年(1879)初次前往新疆就任,次年任温宿地区戎幕,受命编撰《汉回合璧》一书,后就任于青海、甘肃等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大通县知县,“在任期间发动地方官员、义士和乡绅筹款,再辅以统带祥字营的何德彪捐资,重建了崇山书院”[5],据《大通县志》载“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长河人(此处为笔误,应为长沙人)史文光仍任大通知县”[6]。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时任崇信县知县的史文光又奉文设立了崇信县高级小学堂于锦屏山麓文昌宫”[7],同年“奉文垦荒复额,粮本足额,为书差侵渔,短额四百余两,并非农民实欠,乡民奔走呼吁,请地亩,查串票,公推李建善陈书宪委,史文光禀词矛盾,被免职”[8],此外无其他记载。观其一生,史文光除早期就职于新疆外,其从政生涯的大部分都在青海、甘肃度过,主要政绩也多与修建书院、刊发教材相关,是一位极重视基础教育的文吏,颇有政声。⑤参见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31 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张成基,字养田,原湖南郧县人(今湖北郧县人),寄籍陕西省靖远县,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逝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享年54 岁,其生平及政绩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初期以贡生赋直隶州州判,光绪五年(1879)随刘锦棠马步二十四营前往新疆,同年七月前往吐鲁番城。次年正月,因新疆南北两路剿匪出力奏保,奉旨赏换花翎。七年(1881)五月,因新疆剿平五次边寇出力,经前任通政使刘锦棠奏保,以知州不论单双月尽先选用,调离新疆。十七年(1891)九月因山东河工连年抢险出力,经前任山东巡抚张曜奏保,以知府用。次年十月,再次返新疆,经前新疆巡抚魏光焘奏保,赏加四品衔。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因河州解围出力,经甘肃提督董福祥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次年十月,“因西宁大通解围出力奏保,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5]222,后任甘军营务处道员、湖南记名简放道员,以军机处存记候补道员统带湖南劲字五营。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率部随同湖南藩司锡良入卫,八月驻扎固关,九月积劳成疾,赍志以没”[9],由藩司锡良将其履历功绩咨文报部,同时具折奏请按照军营立功积劳病故之例,从优议恤。⑥参见张瑞萍《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同年十月,朝廷予“山西军营病故湘晋两军统领湖南候补道张成基优恤”[10]。依据上述官方记档,史文光、张成基二人初次进疆处理南北两路事宜时,任文襄公之军幕,该书成书时二人正随军驻扎于温宿地区。但考虑到两人均无除汉语外的语言学习经历,故该书由此二人亲自完成撰写的可能性极小,可能是在其主持下编撰的。
孙寿昶与史文光、张成基为同期官员,进入新疆就任时间基本一致,至于因何故两版本书名完全相同、内容大致相同,但编者署名不同,由此进行了大胆假设:
孙寿昶之所以被委任编撰这样一部汉维双语并行的蒙学教材,与其早年任“汉笔帖式”官职密切相关。其“缮写笔帖式”之名反映出编者孙寿昶的主要工作为缮写满汉奏章及文书,由此可以得知他至少是一名懂得满汉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但他本人是否通晓维吾尔语,笔者尚未找得史料予以佐证,故此书的维吾尔文部分为孙寿昶亲自编写,或是由其主持编写均有可能。相较于史文光、张成基为编者的说法,孙寿昶更符实际编撰者的条件,其语言优势是完成该书所具备的首要条件。但依据版本比对得出的结论,史文光、张成基著本的成书时间稍早于孙寿昶著本,且文中多次出现互相参考、借鉴的情况,①关于《汉回合璧》的版本情况参见本文第四部分——《汉回合璧》版本系统。笔者不得不认为此二人也参与了该书的编撰,已不单单是为提升政绩,“挂名”此书编者。此外,考虑到孙寿昶著本序言为典型的“编者自序”,而史文光、张成基著本跋文为他人所作。故最后得出结论:该书应是先由史文光、张成基二人进行了汉字义项部分的编写,随后由孙寿昶完成了维吾尔文部分的编写,三人共同参与了《汉回合璧》的编辑。
(二)成书时间
现可见的十二部《汉回合璧》中,九部为“孙寿昶著本”,三部为“史文光、张成基著本”。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藏本著录未依序言,记为“光绪年间”和“清代”,其余七本均依古籍序言著录为“清光绪六年”。因史文光、张成基著本的牌记、序跋及正文均不含时间标志,故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与湖南图书馆将其藏本著录为“清光绪年间”“清末”“清同治年间”。上述三种说法中湖南图书馆著录信息最不合情理,该馆似是参考了跋文“同治间土回内讧,安集延人乘隙外至,本地缠头回子即靡然从矣”,将其定为“同治刻本”,这与跋文后句的“相国恪靖侯奉命督师廓清疆宇”②湖南图书馆藏《汉回合璧》,跋文“相国恪靖侯奉命督师廓清疆宇”一句提及的相国恪靖侯,即左宗棠,同治二年(1864)年受封“一等恪靖伯”,直至光绪三年(1877)才由“一等恪靖伯”晋升为“二等恪靖侯”。所示时间不符,该本成书时间绝不会早于“光绪三年”,故此馆著录时间需作更正。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史文光、张成基著本今所示编者、编撰时间、刻印地信息与1952年北京图书馆刊《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中记录的“史文光、张成基编《维汉文汉回合璧杂字本》一书,撰于清光绪六年(1880)(北京)”③此种《汉回合璧》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今国家图书馆藏三种《汉回合璧》之一。参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1952年,第91页。信息不符,需做核实及修正。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本著录信息可进一步完善。
综合上述编者信息及相关史料,可知史文光、张成基与孙寿昶进疆就职时间为同年,都在光绪五年左右,二人在疆处理军务时间也几乎一致,为光绪六年至次年五月,故该《汉回合璧》应成书于此期间,另据孙寿昶著本序言所述,文章认为史文光、张成基著本与孙寿昶著本成书时间应同为清光绪六年(1880)。
三、《汉回合璧》馆藏情况
现国内外各大图书馆藏清代《汉回合璧》共计十二部,分藏十地,其中十一部为未刊布的新版本(六部藏于我国,五部藏于日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藏一部;湖南图书馆藏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部;辽宁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日本东洋文库藏一部;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一部;日本静嘉堂藏一部。具体馆藏情况如下:
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部。均缺失书衣及封皮,但正文内容完整,修缮时经加工重订,附“汉回合璧”为书名的全新书皮、函套,函套侧面附薄纸书写“汉回合璧”四字。此馆现收藏的三部均为未刊布的新版本,其中两部编者一致,为孙寿昶。
其一,编者史文光、张成基,撰于清光绪年间,简称国图“史文光本”。石印本,线装,书高27.6 厘米,宽25.8厘米,板框高22.3厘米,宽21厘米,双面印刷,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向外,页码印于书口,无序言,附一页半跋文,共计35页,第十一页与第十二页页码颠倒。
其二,编者孙寿昶,著录为清光绪年间,实际撰于清光绪六年,简称国图“光绪本”(以其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著录时间命名)。木刻本,线装,书高30 厘米,宽24 厘米,板框高21.8 厘米,宽22.3 厘米,双面印刷,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向外,页码印于书口,前两页为编者自序,无跋文,共计35 页,第七页与第八页内容颠倒。该本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收藏,后于1971年赠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钤“陈垣同志遗书”章,是我国各馆现藏诸多部《汉回合璧》古籍中唯一一部经名人收藏、记录详细藏书来源信息的刻本。
其三,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简称国图“光绪六年本”(以其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著录时间命名)。木刻本,线装,版式及正文内容与国图“光绪本”一致,仅序言存在差异。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藏一部,简称“民研所本”,是国内目前唯一刊布及研究使用的版本。该书为民研所从北京中国书店购买所得,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除封面缺失,纸质较脆外,基本上是完整的。“为便于保存,曾经加工重订。但现有封面是后加的。《汉回合璧》为木板印刷本,篇幅不大,仅35 页,单面印刷,中间有折缝,页码写在折缝中,前两页为400 字左右的编者自序,正文共33 页,书宽24.3 公分,高27.3 公分。”[1]49此种序言与“光绪本”一致,正文内容与国图“光绪本”、国图“光绪六年本”存在差异。
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部,简称“北大本”。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木刻本,线装。油渍外溢现象较为明显,经比对,版式及原文内容与国图“光绪六年本”一致,可确定为同一版本形式。
4.湖南图书馆藏一部,简称“湘图本”。编者史文光、张成基,著录时间为清同治年间,木刻本,线装。封面未经修复,有破损,但书名“汉回合璧”四字刊刻清晰,是国内藏此种《汉回合璧》中唯一一部留存有封面信息的刻本,且正文内容的第25页及第31 页天头处留有“此鷺字當照哈密校本全改”“لارن”字样的朱红色批注印记,各别处留有修改印记,无私章印记。经比对,正文内容与版式与国图“史文光本”完全一致,可确定为同一版本形式。
5.辽宁大学图书馆藏一部,简称“辽大本”。编者史文光、张成基,著录时间为清末,木刻本,线装。版式及原文内容与国图“史文光本”“湘图本”一致,考虑到正文字迹上的细微差异,可推断该刻本与国图“史文光本”“湘图本”应为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形式。
6.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藏《回汉对音千字文》一部,简称“神户外大本”。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木刻本,线装。书高27.3 厘米,宽24.3 厘米,首册封面完整,书有“回漢對音千字文”七个字。板框高21.1 厘米,宽20.3 厘米,双面印刷,无直格,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版心向外,页码印于书口,无私章标记,共计35 页。经比对,与国图“光绪六年本”“北大本”同书异名,仅书名不同,序言及正文内容完全一致,二者可能由同一刻板刊刻而成,因何导致同书同一版本而书名不同,尚未知,但此版本的出现为我们判定该书的书名及文体类型提供了参考。
7.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一部,简称“天理本”。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木刻本,线装。笔者虽无缘得见此版本,但据西村多慧(2005)指出:“异本至少有天理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与神户外大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收藏)两种,除序跋外正文内容相同,但天理本序跋记录了孙寿昶曾居住于温宿地区。”[1]49由此可知“天理本”与“神户外大本”仅序跋有差异,但正文内容一致。
8.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一部,简称“内藤文库本”。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坊刻本,北京二酉斋书坊发兑。①二酉斋书坊,清代北京琉璃厂著名书坊之一,不仅经销各种古版书籍,而且使用模板印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六言杂字》等八旗官员和私塾学生的用书及书法字帖。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汉回合璧》即由该书坊刊刻。经比对,与国图“光绪六年本”“北大本”“神户外大本”版式及原文内容完全一致,应为同一版本。该本另附“湖南亲笔”四字的手书题字及“湖南袐极”私印一枚,此本为内藤湖南②内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湖南”为其号,日本著名史学家及汉学家。“湖南袐极”为其私印,“湖南亲笔”为其题字。收藏,是目前可见诸多《汉回合璧》中唯一一部标明确切刻印地点的刻本。
9.日本东洋文库藏一部,简称“东洋文库本”。编者孙寿昶,撰于清光绪六年,木刻本。经比对,版式及原文内容与国图“光绪本”“天理本”完全一致,应为同一版本。
10.日本静嘉堂藏一部,简称“静嘉堂本”。编者不详,撰于清代,木刻本。收录于静嘉堂文库“经部小学类语学”,因笔者未寓目该刻本,尚无法判定其版本归属。
四、《汉回合璧》版本系统
笔者整理时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及湖南图书馆藏“史文光、张成基著本”与陈氏刊布的“民研所本”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翻译风格迥然。除无缘寓目的“静嘉堂本”外,其余七部与“民研所本”的著者、版式基本一致,序言及正文内容的汉字、汉字注音部分存在细微差异,维吾尔文部分转写大致相同,似是由同一版本经多次刊刻形成的不同刻本形式。为便于后续版本校勘,判定各版本优劣及价值,考订古籍版本源流,本文对目前存世的十二部《汉回合璧》进行梳理,划分了版本系统。
此《汉回合璧》可分甲、乙两个版本系统,其中“史文光、张成基著本”定为甲本,共计3 部;“孙寿昶著本”定为乙本,下分A、B、C三个版本形式。其中A 本现可见1 部,B 本现可见3 部,C 本现可见4部,此A、B、C三本之间存在修版后印的情况,属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另有无法判定版本形式的“静嘉堂本”1部,故十一种《汉回合璧》版本关系如下,参看图1。

图1 《汉回合璧》各版本关系
甲本中的“辽大本”印刷质量略粗糙,字迹不够清晰,存在笔画残损的情况,国图“史文光本”及“湘图本”字迹清晰,印刷质量较好,但后者油渍外溢现象明显,保存略有缺陷,有近人修改的痕迹。故国图“史文光本”质量及价值较优,“湘图本”次之,“辽大本”最末。乙本中,A、B、C 本错讹大多一致,但B、C 本“汉字”“维吾尔文”字迹相对清晰,内容更完整,错讹少于A 本,此两种版本质量略高,版本价值略大于A 本。整体而言,乙本存在较多错误,刻印质量远不如甲本,其版本价值也略逊于甲本。
本文囿于篇幅,关于甲、乙版本系统的划分依据仅就两版本系统之间较大差异及乙版本系统内部明显差异进行举例说明,对其相似处不予赘述。
(一)甲、乙版本系统间差异
甲本系统与乙本系统在版本形式及内容上均有差异,其中版本形式上的差异较小,仅表现为:书高、宽及板框高、宽不同;栏线不同,甲本为“四周单边”,乙本为“四周双边”;页码不同,甲本的第十一页与第十二页页码颠倒,但正文内容无误,乙本的第七页与第八页页码无误,所记内容颠倒。内容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序跋与正文中。
1.序跋
首先,甲、乙本序跋表现形式不同,甲本无序言,正文后附跋文一页半,乙本无跋文,正文前附编者自序两页。其次甲本序跋所记内容与乙本不同,具体差异如下:
甲本跋文:“国朝平定回疆百余年……同治间客回内讧,安集延人乘隙外至……今相国恪靖侯奉命督师廓清疆宇,善后之策首重义塾,择其秀良习汉字、读汉书,两年于兹,而回民犹以入塾为具文……温宿戎幕长沙史君文光、郧阳张君成基编辑《汉回合璧》一书……故是书之作,不敢谓有裨风化,聊为启发回童之嚆矢云尔。”①此本跋文具体参见〔清〕史文光、张成基著《汉回合璧》,国图普通古籍部收藏,索书号:/字230/893.1。
乙本系统的A、B 本序言:“国朝平定回疆百余年……同治间土回内讧,安集延人乘隙外至……今官军廓清回疆,钦差大臣湘阴左公、督办军务湘乡刘公筹办善后,议改行省,惟善后之策首重义塾,遂择其秀良习汉语、汉书,而两年于兹回民,犹以入塾为具文……帮办军务钱塘张公驻军温宿属寿昶编辑《汉回合璧》一书……故是书之作,不敢谓有裨风化,聊为启发回童之嚆矢云尔。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秋之月山阴。孙寿昶叙”②此本序言具体参见〔清光绪间〕孙寿昶著《汉回合璧》,国图普通古籍部收藏,索书号:/42991。
乙本系统的C 本序言:“国朝平定回疆百余年……同治间土回内讧,安集延人乘隙外至……今官军廓清回疆,钦差大臣湘阴左公,督办军务湘乡刘公,帮办军务钱塘张公筹办善后,议改行省,惟善后之策首重义塾,遂择其秀良习汉语、汉书,而两年于兹回民,犹以入塾为具文……爰命寿昶编辑《汉回合璧》一书……故是书之作,不敢谓有裨风化,聊为启发回童之嚆矢云尔。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仲秋之月山阴。孙寿昶叙”③此本序言具体参见〔清光绪六年〕孙寿昶著《汉回合璧》,国图普通古籍部收藏,索书号:/字/230/893。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甲、乙本序跋最大差异在于编者不同,对左宗棠的称谓不同。前者由“史文光、张成基”编撰,称左宗棠为“相国恪靖侯”,后者由“孙寿昶”编撰,称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湘阴左公”,序中还提到“督办军务湘乡刘公、帮办军务钱塘张公”,即刘锦棠和张曜。
2.正文
甲、乙本正文内容的1 056 个汉字义项基本一致,仅存在“正俗字”差异,但与之对应的维吾尔文译文差异较大,甲本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乙本则多采用音译法,此翻译风格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汉字注音也存在较大差异,使得乙本的汉字注音中“同汉语”数量明显多于甲本。见下文:
(1)“正俗字”差异
正文内容的汉字义项及汉字注音部分因字正俗不同导致刻本间的不统一,其中部分俗字今已归为异体字,部分俗字已不再使用。如:
184 肠,甲本汉字词条使用“腸”,乙本汉字词条使用“膓”。今“腸”与“膓”为异体字。
535椅,汉字注音为“屋凳子”,甲本记作“撜”,乙本记作“橙”。今“橙”与“凳”互为异体字,此处“撜”古同“拯”,拯救,应为误写。
839—840 骆驼,汉字注音为“铁格”。甲本记作“銕”,乙本记作“鉄”。今“銕”与“鉄”为“铁”的异体字。
(2)译风差异
甲本在翻译时讲求“直译为主,音译为辅”,整体译风较灵活;乙本则相反,以“音译”为主要方法,直译时较死板,存在按照原文逐字翻译的情况,如对数字的翻译就完全拘泥于字面,并未考虑其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习惯,过于牵强。如:
87—88 六十,甲本维吾尔文记作“altɛ miʃ(六十)”,汉字注音记作“阿勒提密什”;而乙本维吾尔文记作“a(l)tɛ on(六个十)”,汉字注音记作“阿勒提翁”。此处译者使用“六个十”来表达“六十”的数字概念,此外乙本还存在“y(ʧ) on(三个十)”等表达方式,上述说法均不符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
翻译方法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汉字注音”用字,使得甲、乙本中“同汉语”情况差异较大,据统计甲本的“同汉语”为57处,乙本为93处。如:
121何,甲本维吾尔文记作“qajdaq(如何)”,此处为直译,汉字注音记作“凯达克”;乙本维吾尔文记作“χu”,此为汉字“何”的音译,汉字注音记作“同汉语”。
124 季,甲本维吾尔文记作“pɛsili(季节)”,此处为直译,汉字注音记作“排斯里”;乙本维吾尔文记作“ʤij”,此为汉字“季”的音译,汉字注音记作“同汉语”。
(二)乙本内部差异
乙版本系统包含A、B、C 三种版本形式,正文内容1 056个汉字基本一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B本与C 本正文内容完全一致,仅序言存在差异,可能只是更换或修补了牌记,所以B、C 本实为同一版本。而A 本内容及行款明显不同于B、C 本,但序言与B 本一致,故可以看作是同一版本系统内的不同版本形式。如表1所示。

表1 《汉回合璧》部分词条
29 庄,三版本维吾尔文一致,记作“k(ɛ)nt”,B、C 本汉字注音一致,记作“坎堤”,A 本汉字注音记作“坎提”。
252 邻,三版本维吾尔文一致,记作“χoʃni”,B、C 本汉字注音一致,记作“科什呢”,A 本汉字注音记作“科什尼”。
61 土,三版本汉字注音一致,记作“托怕”,B、C本维吾尔文一致,记作“topa”,A本维吾尔文记作“nopa”,有误,可能是字母“ت”字迹模糊,误印作“ن”。
947闻,三版本汉字注音一致,记作“昂拉”,B、C本维吾尔文一致,记作“aŋla”,A本则缺少维吾尔文形式。
A本与B、C本相比,受刻板及工匠印刷水平的影响更大,维吾尔文部分字迹多模糊不清、笔画残损、油渍外溢,可能是由所用刻板印刷次数过多或印刷工匠大批量刊刻造成的,而各本“汉字注音”用字不同可能与编者的语言背景及语言习惯有关。
五、结 语
《汉回合璧》一书采用了独特的编撰方式和成书体例,融汇了以《五体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为代表的清代官修多语合璧类辞典及明、清翻译教材——《华夷译语》系列的各“杂字”“译语”的特点,是保留至今较为稀见的汉语、维吾尔语、汉字注音同行的童蒙教材,是清代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儿童学汉语、识汉字,进而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儒学文化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基础蒙学读物,在清代边疆治理的教育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汉回合璧》对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的语言文化、地方教育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便利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鉴证,为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提供了历史借鉴。
经整理,现国内外可见《汉回合璧》共计十二部,除陈氏刊布、研究的“民研所本”外,其余十一部均未见于我国任何著录,因而也未有学者进行过版本学研究。随着新版本的发现,陈氏研究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也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本文对上述各本馆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察了编撰背景及成书时间,对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该书是史文光、张成基与孙寿昶三人通力合作的成果。此外依据各本版式、内容以及翻译风格的差异,将上述十二部《汉回合璧》划分为甲、乙两个版本系统,A、B、C 三种版本形式,这对评价各本的优劣及价值、考订版本源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