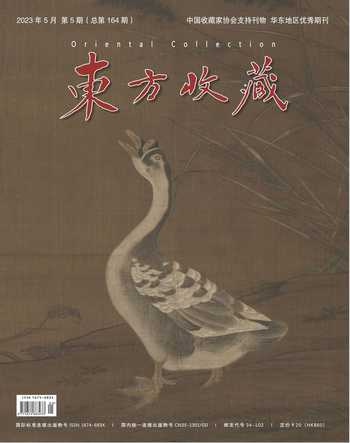《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萩头”考


本文由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交流融合视角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复音词研究,项目编号:XSY202201035
摘要:《吐鲁番出土文书》包含大量名物,其中既包括西域地区独有的风物,更有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的珍贵物产。这些名物生动地反映了异域文化,并为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依据。吐鲁番出土文献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等方面,这些内容涵盖大量的名物词,尤以随葬衣物疏为盛。在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中出现“萩头”一词,文章依据古墓情况断定其为女性头部装饰之物,并对照中原与西域的冠服文化,以及魏晋时期女子(包括西域)很少出现用巾束发的现象,推测“萩头”为女子的假髻。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萩头;幧头;考释
前人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随葬衣物疏进行过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随葬衣物疏的数量、性质、分期及内容等方面。“萩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的时间为高昌郡至高昌王国前期,该时期为随葬衣物疏的第一阶段①,这一阶段是随葬衣物清单里最具写实的时期,基本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所以“萩头”可推断为墓主生前用过的穿戴品。另外,随葬衣物疏中的墓主身份可根据随葬物品以及衣物疏的出土地点等信息获取。“萩头”出现在韩渠妻的衣物疏里,从标题推断为“韩渠之妻”,且结合衣物疏中的其他随葬品实物,如结发(或为女性束发的幅巾,或为假髻),因此认为该墓主为女性,推断“萩头”可能为女性头部的装饰品。
“萩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只出现1次,尽管是个例,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萩头”出自《韩渠妻随葬衣物疏》(63TAM1:11),其原文为“故紫结发故縺(练)萩头”,从内容来看,“萩头”前有一“练”字作修饰,可知其为“萩头”的材质,“练”指布绢,所以“萩头”初步可推断为布帛类的头部饰品。
一、前人所考的“萩头”
关于“萩头”的考释,研究学者甚少,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只有王启涛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和蒋礼鸿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词释》这两本著作有些许论述。蒋礼鸿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萩头”作了解释,认为“萩头”为“幧头”,“萩”为“幧”的音近通假字;他在文后再解释道,“幧头”又可写为“绡头”“帩头”与“陌头”。《广韵》下平声六豪韵:“幧:所以裹髻,七刀切,又七摇切”,而十八尤韵:“萩,萧似蒿也,七由切”。 “萩”(qiū),今检广韵为清母尤韵字;“幧”(qiāo),今检广韵为清母豪韵字。这二者声母同属“清母”,即声母一样,现代汉语的ou来自流摄(即侯尤幽),而ao来自效摄(即萧宵肴豪)。“萩”与“幧”韵母的发音开口度与发音部位相近,主要元音a和o会出现音转现象,所以它们的韵母读音相似,因而蒋礼鸿认为“萩”与“幧”为音近通假字。纵览以上观点,蒋礼鸿释义时仅从音韵角度对“萩头”作了解释,但未针对衣物疏的实际情况作出详细说明,理据不够充分。王启涛沿用蒋礼鸿的观点,认为“萩头”为古代男子束发之物,且训释方法也是沿用蒋礼鸿的路子,并未做出实质性的突破。蒋礼鸿在解释“萩头”时,把它与“幧头”等同起来,认为同指“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这个解释未免有些牵强。原因如下:蒋礼鸿对“萩头”的解释是以另一种名物来释义,并未从其本身词的特点(形音义)入手,这是其一;另外,蒋礼鸿亦没有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衣物疏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上文已提及的“萩頭”出自一位女性墓主,所以牵扯到“萩头”使用对象的性别,是专为男性(女性)所用,还是男女皆可佩戴,这是其二;最后是关于“萩头”的形制问题,若“萩头“为束发之巾,那么对于它的形制,蒋礼鸿亦没有提及。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谈谈个人见解。
1.“萩头”之“萩”为形声字。《说文解字》(艸部)解释“萩”:“萧也,从草秋声”,根据其形旁可知“萩”为一种植物。郭璞注:“萩,即蒿”,认为“萩”是一种蒿类植物,可入药。但从文书中“萩头”的分布来看,它处于随葬衣物疏里,且前面有材质(练)修饰,所以与植物并无多大关联,但我们可推断其应为头部装饰品。
2.关于“萩头”的使用对象。依据疏主的墓葬性质来看,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中的疏主为单人墓葬,并无夫妻合葬的迹象,所以“萩头”应为女性所用。另外吐鲁番随葬衣物疏虽有缺名,但很多疏主仍可根据纪年,以及随葬品清单或是出土地点推断其身份。吐鲁番随葬衣物疏记载的大多是吐鲁番当地居民的墓葬品情况,但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思想也影响着西域地区,所以随葬衣物疏中的名物可能也有阶层之说,这也牵扯到“萩头”是为贵族女性使用,还是底层女性所用。
3.关于“萩头”的形制。蒋礼鸿认为是“束发”之物,但结合疏主墓葬性质和身份,“萩头”可能为女性用来装饰发髻的物品,不会是束发之巾。所以“萩头”究竟为何物,前人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笔者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对“萩头”作出正确的训释。
二、何为“萩头”
虽然蒋礼鸿对“萩头”的解释并不详尽,但他明确指出“萩头”肯定为人头部装饰所用之物,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他的训释方法为本篇文章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蒋礼鸿认为“萩头”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他从音韵角度出发,断定“萩头”是束发之物,这可能源于我国古代社会的“束发”传统。中国的冠服制度,夏商时期初见雏形,到了周代趋于完善。“扎巾”习俗最晚不超过商周时期,《周礼》载:“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这里明确指出,男子二十而冠,则可娶妻。进入阶级社会,冠服制度直接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了,冠服形制的差异能够反映社会阶层的不同。例如古代冠饰就有清晰的等级界限,贵族或统治阶级一般戴冠、冕、弁,而平民阶层则是扎巾(“巾”有幧头、幅巾、角巾、幞头等形制)。按照蒋礼鸿的理解,“萩头”则是束发的巾,这就需要我们对出土文献的时期以及实物作对比参照。
“萩头”为西凉建初十四年(418)②,处于高昌郡及高昌王国前期,为随葬衣物疏的第一阶段。从这一时期男女冠发形制入手来推断“萩头”为何物,我们对“萩头”作了初步推断,可能为头部的装饰品。但蒋礼鸿提出“萩头”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所以我们可以对照这一时期(基本为东晋至唐初)的形制特点来推测“萩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基本沿袭了秦汉旧制,但是由于民族融合与战乱等政治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服饰也呈现出了独有的特点。首先,这一时期的首服是用帛巾包头,先秦时期的“巾”仅限于平民阶层,到东汉晚期,扎巾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士人,甚至是达官显贵也开始用“巾”束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巾”的材质多样,有葛、纱、纶等,且出现了不同形制的“巾”,如“幅巾”“角巾”“帻巾”等。图1为“角巾”的原始形态,此人头巾散开,一个角往下陷,然后搭在前额。图2为“角巾”的变形,角巾中间为有一道棱,两端凸起,好似菱角。根据不同的等级,前述两种形制特征也会有所差异,这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束发的式样。至于蒋礼鸿提到的“幧头”,它其实是盛行于普通老百姓之间用布帛包头的一类巾。古人将巾帕卷成条状,从后绕至额前,并在额前打上结,有点类似于今陕北地区的头巾,见图3。“幧头”最早出自古乐府选文“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帩头”与“幧头”为一物,乃男子所用,并非女子装束,所以蒋礼鸿对“萩头”的释义有误。这一时期汉族妇女的发式亦是独具特色,尤其在贵族妇女中曾流行“蔽髻”,此为在原有发髻上镶嵌的“假髻”。“假髻”源于中国古代女性以长发为美的传统,如《东观记》中所記载的“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反映出东汉时期女子以发长为美的特点,这一现象甚至延续至今。因此后世女子会用到假发髻,最常见的假发髻是在本身头发上掺入假发,叫“髲髢”。魏晋时期女子的假髻有“双鬟髻”“飞天髻”等,如图4所示。这一时期特别是汉族女性的发髻样式十分多样。除“假髻”外,当时的女子还会将自己的头发绾成各类样式,并能够吸纳西域少数民族的发髻式样,如高耸在头顶的单鬟和双鬟发髻,这为该时期女子的发饰样式增添了绝妙的一笔。纵观整个魏晋时期的女子发饰,很少见到用布帛将头发缠绕的工具,即使是普通平民的女性也会将自己的头发打理成各式发髻,这是当时女子共有的发式特征。所以蒋礼鸿理解的“萩头”是用布帛将头发包裹起来的工具,显然不符合时代特征。以上关于魏晋时期男女服饰形制均为中原地区特有,因为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就对西域地区进行行政管理,因此中原地区的服饰文化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西域。基于此,我们以西域的冠服特征为出发点,深入探讨“萩头”。
西域民族的冠服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史前社会,位于西域地区的古代先民在辽阔的西域大地上留下了瑰丽无比的文化宝藏,包括当时的冠服制度。出土于古楼兰遗址的女性古尸,见图5,其头发披散双肩;另外在距今3000余年前的哈密古墓中也发现一名长发齐腰的女子。可见西域地区的原始先民主要以披发为主,这与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关,由于当时物质条件贫乏,没有用来束发或剪发的工具。《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这一记载更佐证了西域先民以披发为主。但是披发不方便,影响先民参与劳作和狩猎活动。因而后来出现了“束辫”之说,束辫既美观又方便,所以受到先民的青睐,见图6。辫发习俗一直延续至今,甚至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的很多人还会辫发,或是用辫发手艺制作帽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先民还会近取诸身,用野兽的皮毛或羽毛制成各类帽冠,形制多样,充分展现出原始先民的智慧以及征服自然的勇气。到了封建社会,尤其是汉代至魏晋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互相往来,思想文化在丝路要道上交汇,因而古人的发饰和冠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现存的文物式样,魏晋时期西域的发式为高耸的发髻,并配有一些装饰品,这与中原地区的发髻形式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外,佛教在魏晋时期盛行,很多佛教造型艺术也随之而来,画师在制作佛像时融入西域民族特色,所以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服饰特点。例如从一些木雕佛像或是各类菩萨人头像上,都能看到异彩纷呈的发髻(波状形发髻、怒发卫冠式发髻、莲瓣式发髻等)。
我们再将目光聚焦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各类人物塑像。从图7北凉泥俑的装束打扮来看,男子用幅巾往额后包发,多余的幅巾使其自然下垂,这也符合前述魏晋时期男子的冠服打扮。该泥俑中还包括女性形象,女子发式为中分并梳到脑后,并没有使用头巾裹发。虽然该泥俑为北凉时期产物,而“萩头”是在西凉时期出现的,但这两个时期相距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其发髻式样并不会相差太多。综上,笔者参照对比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冠服制度和样式,发现魏晋时期男子的确可以用幅巾类的头巾包裹头发,但不论身份地位高低,女子都会编制各式发髻或佩戴假发髻,因此“萩头”应为女子装饰的假发髻。关于“假髻”之说,这可能源于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孝道思想,需要将头发扎起来绕成髻,“假髻”便是古代女子追求美的产物。
三、结论
笔者认为“萩头”为女子装饰的假发髻,这与女子的发式特点和审美相吻合,且佩戴“假髻”在我国已绵延千年之久。至于蒋礼鸿先生提到的“萩头”为“古代男子束发头巾”这一观点,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1.女性墓葬为何会出现男性所用之物;2.魏晋时期女子并没有“裹巾之习”,与时代不符;3.仅从音韵角度推断名物,以物释物的方法太过笼统。因而,本文将所释对象定于某个时间区间(魏晋时期),并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中原与西域的冠服式样,得出“萩头”应为假发髻的结论。
注释:
①侯灿对吐鲁番公元4—7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作过分期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详见其《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②准确来说为“建初十三年”,因为建初十三年李歆已改元嘉兴,所以建初十四年为嘉兴二年(418).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研究所.吐鲁番出土文书(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蒋礼鸿著,吴熊和主编.蒋礼鸿集(第3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高春明著.中国服饰名物考[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4]戴钦祥,陆钦等.中国古代服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M].中国台北:美工图书社,1995.
[6]熊如英.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7]吴娅娅. 吐鲁番出土衣物疏辑录及所记名物词汇释[D].西北师范大学,2012.
作者简介:
陈怡丹(1998—),女,汉族,陕西宝鸡人。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