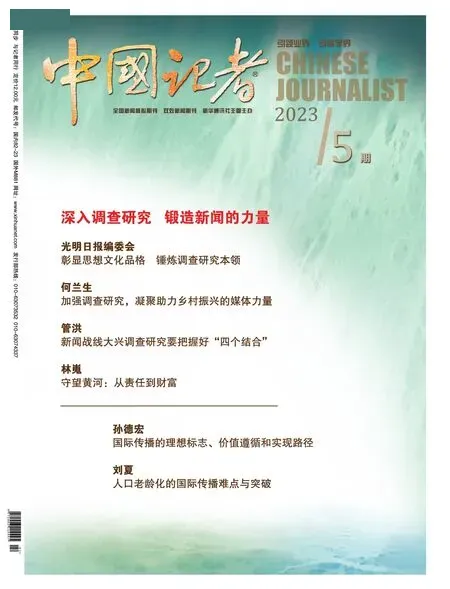网络舆论空间的同情涵化路径
——基于地方融媒体新闻实践的思考
□ 陈俊妮 丁可
一、问题的提出:同情的作用
从18世纪就开始的关于理性与感性的哲学辩论中,同情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一直因其非理性的一面而受到质疑。今天,因为同情往往与涉及民生问题的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网络舆论中这种质疑也一直存在,“在中国网络上看到的多是情绪化的表达及一边倒的声音。网络舆论不是基于理性,甚至不是从基本事实出发,网络对话极其困难。……更加困难的是,中国的舆论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社会的种种情绪来到这里尽情碰撞,由于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中国社会已很难分辨出舆论场的声音哪些是少数人的,哪些有更广泛的代表性。”[1]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对他人遭遇苦难时表达或表现出来的同情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的,是“人类精神中一个根本的道德品质”。它是一种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表现,因为同情可以推动那些让他人或者社会获得一定利益的具体行为或行为倾向,这些行为可以阻止或减轻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侵犯或伤害。因此,从这个角度,同情不仅是一种个体行动的动力,构成了一种情感氛围,还是社会团结中一种重要的情感表现,与其他情感一样,是社会黏合剂的存在。
所以,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面对各种负面情绪,我们尤其需要培养公众基于真相的同情,即需要去涵化,以充分利用它来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实现社会团结。格伯纳(Gerbner)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电视暴力对观众理念、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时提出涵化理论(又被称为培养理论)。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涵化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大众媒介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因此在社会认知塑造上有着重要作用。虽然今天网络舆论场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变化的媒介环境,通过媒介传播的力量,通过对事件与选题角度等的把握去影响公众对事件的感知,激发并培养他们的同情,进而掌握舆论引导力。
在这个涵化的过程中,地方融媒体中心是重要而潜在的“意见领袖”。一方面,从媒体性质来说,地方融媒体中心往往由地方广播电视整合报纸和官方新媒体构成,这些机构掌握着核心资源和一手资料,在地方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从接近性来说,地方融媒体中心作为最基层的机构媒体,在地理与心理两个层面具有与地方民众接近的天然优势。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曾经将距离视为同情产生的重要前提,而这个距离恰好是地方融媒体中心与地方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关注地方事件是地方融媒体中心应有的工作重点,而地方民众更关注身边的事情,他们会判断这些事件在本地媒体上是否被看见、如何被言说、是否得到解决,这些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网上情绪表达。因此地方融媒体对地方民众同情意识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因此,本文以在山东省县级媒体影响力综合排名第二的胶州融媒体中心为对象,基于该中心的新闻实践案例与对该中心记者的访谈,分析如何发挥地方融媒体中心的地理与心理优势来引导舆论,涵化地方民众的同情情感,从而促进社会团结。
二、让地方事件被再次“看见”:涵化民众同情的前提
让事件被看见,这实际考察的是记者是否具有“为无声者发声”的同情意识和责任担当。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下,“全民皆可发声”的论断有其现实依据,但也漠视了还有很多人并没有“话筒”进行自我发声的事实。因此它构成了问题的两面:一方面,依然还有很多无声者及其遭遇需要记者的关注来被大众感知;另一面,当媒体和记者持漠视态度时,也许这些事件会以超出可控的方式、通过很多渠道“明天见”。因此,媒体要把握舆论引导的机会,就更需要有责任和勇气让事件被看见。
地方融媒体更要有这种责任意识,因为地方民众常常会直接通过热线方式来提供线索。民众的报料表明他们实际上正在“观看”事件。“观看”正是同情产生的第二个条件[2]。因此提供线索既包含了对地方媒体的信任,也包含了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即他们希望能通过媒体报道再次“观看”事件。因此认真对待每一个热线线索,从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角度进行价值判断,从而筛选出应该被看见的事件,这既是记者业务能力的展现,也是社会责任的展现。
2019年10月,胶东村民报料一位年过七旬的当地村民本可以有上百万元拆迁款安度晚年,但他的侄子侄女以承诺为他负担养老院费用为条件,替他领取了拆迁款,钱到手后却拒绝支付养老院费用,导致他流落街头。胶州融媒体中心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情况属实,但老人不忍与侄辈起纷争,同时因为没文化,不知道诉诸法律保护权益。这个事件涉及家务事,并且其侄辈是村里有名的“无赖”,还存在新闻曝光后老人因为亲情“绑架”随时“倒戈”的风险。记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判:从这位老人的个体遭遇来说,他孤立无援,属于典型的社会困难群体;从社会影响来说,这是一个地方热点事件,拨打热线只是一位村民基于同情和义愤的匿名行为,但它代表了熟悉事件当事人、观望事态发展的数百名当地村民;从事件性质来说,它既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家务事”,也是一个涉嫌欺诈的“违法事件”。基于这些判断,尽管对老人是否会“倒戈”没有足够的把握,记者犹豫再三但最终还是使用化名进行了报道《愤怒!青岛七旬老人房屋拆迁补偿款100多万,却流浪街头……》,同时将报道重点放在了呼吁法律救援的点上:“一位老人不识字又身无分文,这样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唏嘘。希望能有法律界爱心人士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一把。”这个报道在胶州广电播出后,青岛早报官微进行了转发,并迅速引发地方网络舆情,青岛地区为老人免费打官司的律师把栏目热线都打爆了。

这个新闻作品凝聚了地方民众的同情情感,并促成了事件的圆满解决。参与报道的记者在报道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中获得了同情满足。这种同情满足以一种“反哺”的方式,使记者在面对处于相似困境中的特殊群体时依然会有关注、采访和报道的原始冲动感。
三、在关注地方焦点的距离优势中涵化同情
涵化理论提出了涵化的两层信念,这两层信念之间相互关联。第一层信念认为,大众通过接收媒体报道来形成有关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从而估计真实世界里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概率。当大众基于第一层信念推论出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时,就构成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一般信念,这是涵化的第二层信念。
在第一层信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即尽管大众会深受媒体影响,但他们还是会将媒体报道与现实感受进行比照。所以,媒介建构的象征性现实并不会完全、也不会对所有人有效,它既受信息如何被选择、生产和传播的影响,也受到大众对现实生活的感知程度的影响。反过来,当我们想利用涵化引导大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个的影响。所以正是在格伯纳的两层信念理解中,我们看到了地方融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距离优势。如前所述,地方融媒体位于地方,关注地方,对大众对现实生活的感知有足够的把握,因此只有充分回应这种大众的感知,并通过信息选择、生产和传播的认真考量,才可以在两个层面的信念上产生效果,引导大众的经验认知与媒体认知逐渐达成一致。
这种回应一方面体现在地方融媒体的功能定位和组织架构设置。胶州融媒体中心的全媒体矩阵有8档自办栏目,其中最重要的栏目都聚焦地方民生热点。比如,“胶州新闻”致力于传递政声民意,引导社会舆论,突出凡人善举,以群众视角、百姓语言、聚焦民生热点,讲好市民身边的故事,弘扬社会正能量。另一档节目“民生关注”更是立足胶州本土,将镜头聚焦市民生活,围绕市民群众急难愁盼,深度解读新闻事件真相,监督推动问题解决。这些栏目与《金胶州》报、87.5广播、融媒体传播平台“云上胶州”客户端以及多个网络媒体宣传平台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全媒体矩阵。有了全媒体矩阵,任何一则新闻都可以在技术层面产生联动效果。
回应另一方面体现在具体报道的关注焦点。地方民众不仅关注个人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也关注社区身边人的“小事”,关注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人员的作为,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打交道最多的对象,因此也最容易构成他们关于现实社会的认知。
2015年6月,胶州网论坛出现一则匿名网帖,称胶州市某村村干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老人,并附有多张事发时村干部手拿砖头、老人倒地不起的抓拍照片。这则帖子立即引发论坛热议,对村民的同情和对“村霸”的声讨之声使它迅速成为地方关注的热点。然而记者在这些照片里发现了诸多疑点,经过调取事发时段监控和多方调查发现,涉事老人与儿子不仅因欠集体承包费被当地村民不耻,在这起冲突中还破坏了村委办公室设施、撕扯村干部衣服并用砖头袭击村干部。录像显示,村干部只是出于自卫抢夺了砖头,但老人气急败坏冲向村干部却因此倒地,老人儿子用手机拍下来,制造了老人被殴打倒地的假象。
在网络空间中,看起来是弱势的一方很容易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因为它可能符合民众朴素的爱憎情感和刻板印象,即基于年龄、性别、职业身份等因素来确定强势一方与弱势一方。就像这个新闻中的老人与村干部在年龄与职业身份上形成了强烈反差,会很容易被认定为弱势对象。老人儿子拍摄的视频进行了有目的的取舍,保留了村干部手持砖头、老人倒地一旁的画面。这些与民众在网络中惯常看到的强势方欺凌弱势方的事件具有高度“一致性”,于是民众的同情会很快被激发。对于媒体来说,如果不经过仔细调查就呼应民众的同情,很容易造成新闻失实,并进一步强化民众错误的现实认知和信念,将激发同情变成了煽动同情。
对于地方民众来说,这一类“零距离”事件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情绪,因为地理上的接近性会让他们有更多的角色代入。他们会更笃信事件的经过,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村的村民,如果不是在现场亲眼目睹,根本无法判断事件原委。在这起事件中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事发时只有村干部与这对父子在场,没有其他目击人。所以当地民众大多倾向于同情这对父子。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已有的观念。
所以对于地方媒体来说面对这样已经成为地方焦点的事件,要发挥距离优势来涵化同情,第一步需要深入现场,辨析事件真伪。记者发现照片中村干部手持砖头的方向与老人倒地的方向并不一致,而且村委会办公室的窗户玻璃还有被击碎的痕迹。顺着这些疑点,记者在现场发现村委会墙角隐蔽处安装有监控探头,于是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拷贝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弄清了事情原委,也印证了之前的疑点。最后,新闻以《欠缴承包费起风波 “老人遭村干部殴打”真相》为题播出,不仅还了村干部清白,也打消了不明就里的民众对基层干部的误解,并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村民对峙和网络喧嚣烟消云散。这则新闻回应了地方民众的感知,并且修正了他们的两层信念,在第一层信念上修正了关于强势方与弱势方的关系理解,在第二层信念上修正了对社会正义的理解,这一报道因为积极的社会效果获得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长消息类二等奖。
四、在共振的优势中涵化同情
“人们的同情心并不完全取决于苦难本身,还取决于人们如何观看‘观看’苦难本身,取决于观看者与受难者的‘距离’,而这些距离的远近与灾难新闻报道息息相关。[3]”格伯纳在涵化理论的发展中也提出了与这个距离相关的理解,即“共振”。当受众在媒体中看到的情况与亲身感受的社会环境相吻合时,就产生了共振。这时媒体对他们的涵化效果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2018年,胶州本地的微信朋友圈传闻某个小区一家便利店失火,店内商品被烧损失惨重,所在小区居民闻讯后自发排队原价购买被烧商品。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了购买被烧商品的居民和面对小区居民善意好几次都控制不住自己激动情绪的小店店主,在“云上胶州”微信公号报道了这个爱心故事《温暖!水火无情,人有情!小店失火,爱心居民排队原价争购被烧商品!》。这条新闻获得了当年山东县市级媒体专项奖一等奖。比得奖更重要的是,它将一个小区里发生的“身边的感人故事”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形成了关于同情的价值共鸣。
大部分时候,遥远的苦难是通过传统的媒体报道与即时的社交互动实现其媒介化存在,因此人们在物理空间上缺席,媒介化在场。[4]相比遥远的灾难,地方融媒体报道的事件都发生在身边,对于当地民众来说,事件的真实性很容易被核证,甚至可以亲眼去见证事件,并能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中看到自己和身边人的付出带来的改变。这种见证改变的力量使得对他人苦难的感知具有了具身性与媒介化的双重特征,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与媒体报道的内容形成共振效应。
这种共振效应还可能在媒体与民众行为之间交互出现,尤其是在追踪报道中。2019年,“云上胶州”以《男子车祸成植物人,桃挂枝头只等救命钱!》报道了当地一名村民因为丈夫车祸变成植物人后独自撑起家庭,却着急桃园果子成熟无人帮忙采摘、急等桃子变现给丈夫交医药费的事件。报道播出后,由货车司机、的哥的姐、月嫂等各行各业市民组成的山东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青岛服务队来到这名村民家帮忙摘桃抬筐搬运,只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将2000斤被订购的桃子运出了桃园。因为村民照顾丈夫没足够时间打理桃园,桃子明显不如市面桃子品质好,但前来买桃的爱心人士多达几百人,即使是又小又被虫咬过的桃子也被抢购一空。融媒体中心在一周内又发出新闻追踪稿《男子遭遇车祸成植物人,家中成“爱心汇聚地”!》,以这样的方式回应所有关心这名村民遭遇的民众,肯定所有参与其中的爱心人士,也召唤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爱心活动中。
“情绪感染与情感共鸣是连结网民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桥梁和纽带。情感动员的治理逻辑正是借助情绪感染与共鸣机制,从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使网络事件进一步推进与深化。[5]”所有基于同情的关心有了结果、所有基于同情的参与被主流媒体肯定、参与进来的先行者从媒体看到更多的人被感召、这些被媒体报道感召的人加入后进一步证实媒体报道,这个爱心过程就是媒体与民众之间的多次共振,同时也是媒体涵化民众同情的具体路径。
五、结语
同情作为人的良心形成来源,是亲社会行为的基础,对于整个舆论生态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涵化理论,从地方融媒体扎根地方的优势,分析了如何从关注地方焦点、运用共振效应来引导地方舆论,从而涵化同情资源。相比较中央级媒体,地方融媒体有着与地方民众接近的先天优势,有条件紧跟群众喜怒哀乐生活实际。市县区域人口从数十万到数百万,虽然不会天天有大事件,但守望相助的同情关爱故事资源肯定相当丰富。因此对于地方融媒体来说,如果关爱群众的新闻报道内容减少、分量不重,并非新闻线索缺乏,而是缺乏发现暖新闻的动力。相反,保持人民情怀,积极反映当地民众的呼声,弘扬民众中的同情之爱,就有能力迅速发现新近发生的身边新闻,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和期待,也就有了保有民众同情之心的“活水”。
当然,同情作为舆论引导实践中的一种情感资源,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也有使用的边界。对于记者来说,同情的泛滥不仅会使报道有失客观冷静,也有可能加速同情疲劳的产生,所以在保有同情能力与冷静客观呈现之间如何寻找平衡,也是新闻实践中需要不断去摸索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