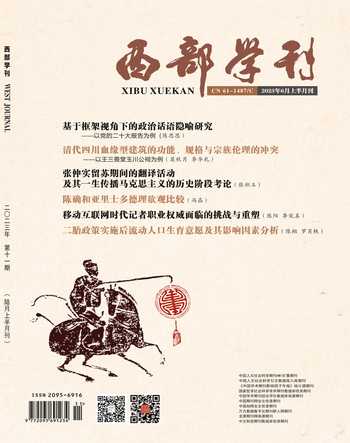先秦诸子论“安危”
摘要:先秦诸子论“安危”的历史背景包括中华民族积极应对安全威胁历史传统、以史为鉴优良传统、传统安全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激荡的社会局势。对“安危”一词的论析几乎涉及诸子百家,杂家、法家、儒家等先秦诸子对安危问题较为重视。先秦诸子重视安危形势及其研判,高度关注国家安危特别是政治安危,重视军事及其将领、国君、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重视道义在国家安危中的特殊作用。虽时隔千年,其依然彰显出持久的魅力,对当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安危;诸子;先秦
中图分类号:K225;K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085-04
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是,“安全”一词在古籍记载虽然有之,但却数量不多,古人通常单以一个“安”字表示“安全”之义。“安危”与“安”息息相关,早在先秦时期便被人广泛使用。与单个“安”字相比,“安危”一词的内涵更为丰富,体现出古人对“安全”整体而辩证的认知与理解。先秦时期对于“安危”一词的全面而深刻的论析,莫有超过诸子百家的。本文全面梳理诸子百家“安危”一词的使用情况,论析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
一、为何论——先秦诸子论“安危”的历史背景
人是历史的主体,其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反映。先秦诸子广泛论述“安危”,深受其历史与社会背景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到中华民族积极应对安全威胁历史传统的影响
“安全”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重要话题,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破坏,甚至毁灭性打击,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进步。上古时代,中华民族便与各类安全威胁作斗争,形成了积极应对的传统。以水患防治为例,《尚书·堯典》记载“(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可见,尧、舜、禹被人称颂并列三皇五帝均与治理水患有密切联系。此外,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也反映出当时水患严重,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灾害,带来了深远影响。甚至到了战国时期,水患依然被认为是最大威胁,《管子》提出了影响国家安全的“五害论”:“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管子·度地》)除了所举水患的威胁外,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还面临着其他诸多安全威胁,有着与之斗争的现实需要和丰富经验。
(二)受到中华民族以史为鉴优良传统的影响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荡》),“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中华民族善于总结汲取历史经验,这种“以史为鉴”的观念形成于殷周之际[1]。商周时期的《尚书》中就有《酒诰》《召诰》《多士》《康诰》《君奭》《立政》《多方》等多篇文献讨论了夏商两代的盛衰兴亡,其目的就是告诫统治者要以此为鉴,以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2]。“以史为鉴”的观念与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不论是儒、墨的称道标榜,还是道、法的贬抑憎恶,先秦诸子几乎都谈及“三代”[3]。如在论述“安危”时,《墨子》就总结了影响国家安全的“七患”,以“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墨子·七患》)为鉴加以论证;《吕氏春秋·长攻》同样以桀、纣、汤、武之史,印证“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的观点。
(三)受到传统安全思想的影响
“安危”一词首次出现于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之中,有“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尚书·毕命》)的记载。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尚书》广泛记叙了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4],对安危存亡有数量众多的经典论述,如“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周官》)、“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伊训》)、“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尚书·太甲下》)。先秦诸子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4],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蕴含其中的安全思想。“安危”由“安”“危”两个词义相反的字构成,本身充满着辩证意味,《易经》之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深刻思考(《周易·系辞下》)。此外,《周易》中还最早出现了“忧患”这一表示安危意识的词汇[5],指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为先秦诸子论“安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荡局势的影响
伴随着周王室的日渐衰微与幽王时期“三川竭,岐山崩”(《国语·周语》)的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平王东迁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6],诸侯争霸、列国兼并,造成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混战,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追求与希望。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原诸国认为“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态势让中华民族忧患意识、文化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私学的兴旺,学术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7],是我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诸子百家流派众多、思想博大,但如果不是看名称而看实质,可以说先秦诸子各个学派大多是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8]。
二、何人论——先秦诸子论“安危”的学派情况
陈垣指出“读史当观其语之自出”[9],因此有必要将先秦诸子著作中“安危”一词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此处仅将论及“安危”一词学派、著作及卷(篇)名进行梳理:
(一)儒家
(1)《荀子·荣辱篇第四》《荀子·王制篇第九》《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君道篇第十二》《荀子·议兵篇第十五》5卷;(2)《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1卷;(3)《越绝书·卷第六》1卷;合计3种著作,共7卷。
(二)墨家
《墨子·卷三》《墨子·卷九》《墨子·卷十二》;合计1种著作,共3卷。
(三)道家
(1)《庄子·秋水》《庄子·则阳》2卷;(2)《列子·力命篇》《列子·杨朱篇》2卷;(3)《鹖冠子·王鈇》1卷;(4)《六韬·龙韬》1卷;合计4种著作,共6卷。
(四)法家
(1)《管子·形势》《管子·立政》《管子·幼官》《管子·参患》《管子·形势解》5卷;(2)《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安危》2卷;(3)《商君书·农战》1卷;(4)《慎子·知忠》1卷;合计4种著作,共9卷。
(五)兵家
(1)《孙膑兵法·客主人分》1卷;(2)《孙子·作战篇第二》1卷;合计2种著作,共2卷。
(六)纵横家
(1)《鬼谷子·飛箝篇》1卷;(2)《战国策·卷七》《战国策·卷二十六》2卷;合计2种著作,共3卷。
(七)杂家
(1)《吕氏春秋·重己》《吕氏春秋·圜道》《吕氏春秋·论威》《吕氏春秋·务本》《吕氏春秋·长攻》《吕氏春秋·离谓》《吕氏春秋·自知》《吕氏春秋·当赏》8卷;(2)《尉缭子·武议第八》《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2卷;合计2种文献,共10卷。
从以上相关情况的梳理、统计,可以得出结论:(1)先秦诸子对“安危”一词的论析几乎涵盖了各个学派。由此可见,“安危”是诸子关心的共同话题,进而反映出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安危问题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的向往追求。(2)若按学派提及“安危”的卷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杂家(10卷),法家(9卷),儒家(7卷),道家(6卷),纵横家、墨家(均为3卷),兵家(2卷)。这虽不能反映各家学派对“安危”的认知深度,但从各学派活动时间顺序来看,至少可以反映出随着兼并战争的逐步升级,社会各界对于“安危”的关注热度越来越高。
三、论什么——先秦诸子论“安危”的主要内容
从论及内容来看,诸子百家对“安危”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一)重视安危形势及其研判
《越绝书·卷第六》记载“安危之兆,各有明纪”,《鹖冠子·王鈇》指出“故能为天下计,明于蚤识逢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六韬·龙韬》指出“主图安危,虑未萌”,《吕氏春秋·长攻》指出“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虽然各家用词不同,但所谓的“兆”“纪”“祥”“稽”“萌”“遇”都是指的一种征兆、形势。如何才能“虑未萌”而对“安危”形势进行研判?《鬼谷子·飞箝篇》提出了“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的要求,指出对安危之计的决定,要以“察”“别”“见”“治”等一系列的甄别判断为前提,体现出审慎严谨的态度。
(二)高度关注国家安危,特别是政治安危
春秋战国时期“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商君书·开塞》),如何在激烈非常的政治竞争、军事斗争中确保国家安全稳定,成为摆在各诸侯国面前最直接的现实命题。诸子百家因势而兴、著书立说、驰辞骋辩,其基本宗旨主要是为国君提供不同的政治方略[10],为未来的世界探寻治理国家的方案[11]。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可以发现先秦诸子对于“安危”的论析,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安危存亡而展开。如《慎子·知忠》指出“国之安危在于政”,《吕氏春秋·圜道》提出“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贤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墨子·卷九》提出“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这些都体现出我国古代“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8]的特点。
(三)重视军事及其将领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几为常态,因此各诸侯国及诸子对军事都给予高度重视。《管子·参患》指出“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六韬·龙韬》指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孙子·作战篇第二》指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阐述了军事特别是将领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先秦诸子并未将国家安危完全寄于军事一端,《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明确提出了“军事是现象、是手段,而政治才是本质、是目的”的深刻认识。此外,《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之语,《孙子兵法·谋攻》所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语,都体现出先秦诸子对于军事是重要手段、而非唯一手段,有重要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的普遍认识。
(四)重视国君在国家安危中的关键作用
《吕氏春秋·自知》指出“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荀子·王制篇第九》指出“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都提出了自身因素在国家安危中的主要作用。具体到一国之中,诸子极为关注国君的关键作用。《荀子·议兵篇第十五》指出“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把强弱、存亡、安危与国君贤能与否等相联系。对于国君应该如何做,先秦诸子提出了诸多明确要求,如《管子·立政》要求国君要慎大德不至仁、见贤不能让、罚避亲贵、不好本事等,并指出“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吕氏春秋·当赏》提出要赏罚分明,指出“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五)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危中的根本作用
虽然重视国君在国家安危中的关键作用,但先秦诸子同时认识到“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子·知忠》)、“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吕氏春秋·务本》),强调人民群众的根本作用。这一认识受到“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深刻影响,从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到春秋时期的“民为神本”,再到战国时期的“民为军本”[12],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重民”意识逐步强化。同一时期的孟子之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荀子之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都反映出先秦诸子对人民群众及其根本作用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六)重视道义在国家安危中的特殊作用
由于“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论语·阳货》)、“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因此,先秦诸子在论析影响国家安危因素时,尤其强调道义的特殊作用。《吕氏春秋·论威》指出“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荀子·荣辱篇第四》指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指出“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其中对于“道义”“荣辱”“是非”等内容的强调,都体现出对道义极为关注的鲜明时代特征。
四、结语
以上是对先秦诸子论“安危”共性内容与特点的梳理,但也要看到因思想主张的不同,各个学派对于“安危”的认识存在明显区别。如“安危”是“天命”还是“人事”,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解。法家重视“天”与“神”的作用,认为“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事天,以天事神”(《管子·侈靡》)。道家、墨家则反对所谓的“天”“神”“鬼”,指出“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责于天道,鬼神奚与”(《鹖冠子·王鈇》)。墨家批驳了儒家“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墨子·卷九》)的观点,鲜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虽然“安危”一词并不能尽然反映出诸子博大精深的安全思想,但从一个词汇入手,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安全思想内容之丰富、要义之深邃,其时隔千年,依然彰显出了持久的魅力,对当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0-197.
[2]董立河.中國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J].史学史研究,2006(4):14-24.
[3]刘家和.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J].史学史研究,2007(1):1-6.
[4]晁福林.上古历史文献的宝库:《尚书》[N].光明日报,2001-02-13(B3).
[5]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81-87.
[6]白至德.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24.
[7]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5.
[8]刘跃进.当代国家安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1-125.
[9]陈垣.陈垣全集:第21册[M].陈智超,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102.
[10]张兆瑞.多元一体的先秦诸子治理思想体系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78-90,221.
[11]朱汉民,胡长海.儒、法互补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2):69-75.
[12]王鑫义.先秦两汉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轨迹[J].安徽大学学报,1993(3):22-27.
作者简介:张红亮(1989—),男,汉族,山西垣曲人,铁道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史、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