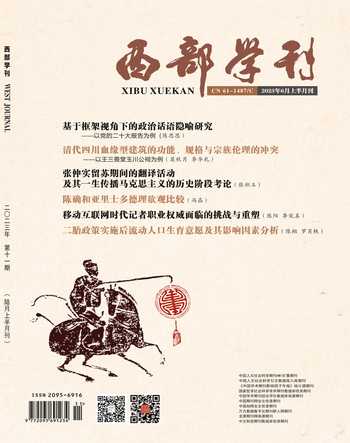蒙古西征对欧洲集体心理的建构
彭钰馨 赵银亮
摘要:蒙古帝国自十三世纪开始的西征,促生了欧洲对东方的集体心理认知,这种心理以蒙古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为基础,经双方交往中政治对话失效、蒙古西征过程中的劫掠杀伐、宗教演绎在欧洲造成的恐慌等互动方式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而产生,主要表现为欧洲对东方的恐惧、怀疑以及将东方看作欧洲世界的威胁。
关键词:蒙古西征;文明互动;欧洲集体心理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095-04
蒙古帝国自十三世纪开始的西征,在物质与文化层面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欧洲对东方认知的基调。蒙古帝国与基督教欧洲在十三世纪前后的交往,学界主要关涉蒙古帝国对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科学技术的影响,及考察双方的外交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侧重物质层面的考察,对欧洲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考察略有不足。事实上,蒙古帝国的崛起,对欧洲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更加深远:西征使欧洲各国产生了对东方的恐惧与怀疑,更将东方世界看作潜在的威胁。
一、文明间互动的基础
互动,指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推至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层面,则指政治实体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行为体互动的基础,即双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异同——二者在上述方面趋同,建构起共同的政治话语、良好的对话机制、互利的商贸关系、共通的社会文化,则能够建设良好的关系;反之,双方则会趋向对立甚至战争。由互动角度切入对欧洲集体心理的考察,首先需要比较当时的欧洲世界与蒙古帝国在上述诸方面的异同,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二者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互动。
(一)政治体制
十三世纪的欧洲世界,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制。这一政治制度以领主与封臣间的附庸关系为特征,以二者间的契约为纽带。封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政治体制,封臣只对与自己有直接附庸关系的领主履行义务,因而国王只对其直接管理的封建主拥有支配权,而无权调动封建主的附庸,因而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体系是碎片化的,不存在中央权威。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导致基督教欧洲军事上的无力;君主实际权力的衰弱,使其难以动员境内的物质资源来组建常备军;众多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使各国利益复杂交织,在军事战略方面自然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
这一时期的蒙元帝国则建立起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已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起帝国。这一时期的蒙古帝国,在政治体制上初现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各汗国虽然具备相互独立性,但均承认大汗的中央权威,不同程度上听从其指挥。大汗因而可将其权力影响施加至帝国内的各大小部落,帝国各部的内外政策因而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中央权威建立后,大汗得以调配帝国内部的所有力量来达成政治目标,具备足够的物质资源以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
由此可见,就在欧洲政治处于缺乏中央领导的破碎局面,军事上缺乏团结、软弱无力之时,蒙古帝国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发达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调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征伐。双方在政治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巨大的实力差距,欧洲各国无力抵挡蒙古帝国的军队,蒙古与基督教欧洲的互动展现为基督教世界对蒙古扩张的被动反应。
(二)经济发展模式
庄园制是中世纪欧洲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制度建立在当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上。大领主将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后,各封臣就对自己的封地拥有独立管辖权,在经济上可以支配封地内的耕地及农民。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这意味着领主的最主要经济来源是其封地内的农业生产,只与其他领地发生极其有限的商业关系。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庄园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封闭性。
在经历统一成为帝国前,蒙古前身为栖居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蒙古崛起成为帝国后,以草原游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草原的旱雨两季气候,使蒙古难以发展农业;蒙古高原的自然资源使部落难以发展出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多以通商换取货物。蒙古统一后,草原无法满足民众生活与帝国发展的需要,因而进行战争、扩展疆域势在必行。因此,蒙古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开放性和扩张性为特征。
十三世纪,欧洲世界与蒙古发展出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发展条件上,欧洲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农耕经济,蒙古需要扩张与战争满足物质需要。两种经济模式间的潜在冲突,使双方在交往中的经济关系表现为游牧部落对庄园农耕经济的侵夺。
(三)社会文化
十三世纪的欧洲各国处于基督教影响之下。受奥古斯丁战争理论的影响,基督教欧洲各国强调战争的正当性:“在基督教语境下,……正义的战争应该被看作惩罚罪恶的手段。”基督教义虽然并不完全禁止战争,但只支持受到上帝授权的正义战争,而禁止追求扩张、杀伐无度的不义战争。
在蒙古帝国的社会文化中,权力和军事征服是部族稳定的核心。在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最初是极其弱小的,在早期缺乏稳定的部族支持。同时,草原部落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充满变数,“成吉思汗在战斗中与其他草原领袖相比要冒更多风险,因为他需要不断用胜仗巩固自己。”由此可见,权力斗争与军事手段在成吉思汗崛起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要素是大汗保持对各部落控制、对外交往的核心手段。
草原部落的擴张性与政治不稳定性,使蒙古帝国将权力与征服看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必要手段;基督教欧洲则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两种社会文化的冲突,意味着二者对战争的不同理解与解释,而对战争的理解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发展及相互认知。
二、文明互动的过程性要素考察
如前所述,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是文明间互动的基础,交往中的过程性因素则决定了文明间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双方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进行有效的政治对话、采用和平的手段、相互了解彼此的社会文化,则会发展出积极的关系;反之,可能导致双方在政治上的怀疑、对立甚至是战争。
对于基督教欧洲—蒙古帝国这对文明而言,影响双方关系的过程性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政治对话的失效、战争中的掠夺杀伐以及宗教演绎造成的恐慌。
(一)政治对话的失效
欧洲各国君主派出使团,以较为和平的姿态与蒙古进行政治对话,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有关。如前所述,基督教欧洲封建的政治体制,使各封建主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各国君主因而无法对所有封臣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同时,此时的欧洲还处于教权与君权分立的状态,教皇才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世俗君主的行动多受教会制约。由此可见,封建主、君主、教皇三方力量各自独立且相互掣肘,难以有效统合军事力量抗击蒙古帝国。征伐花剌子模国后,蒙古统治者将自己看作世界的征服者,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处理对外关系,欧洲使团提出平等对话的要求很难博得蒙古大汗的认可。
1241年,蒙古帝国击溃匈牙利,部分军队进入奥地利境内,中欧与西欧对蒙古军队而言如囊中取物。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正与教皇进行政治斗争,基督教欧洲处于分裂状态。蒙古入侵的消息传至西欧,腓特烈二世致函英、法两国王,建议联合抗击蒙古人,但并未受到双方信任:西欧各国与罗马教廷都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建议是为反对教皇,壮大自己的势力。
政治上破碎的欧洲难以组织起有规模的联军,只能先以对话作为手段。教皇英诺森四世即位后,曾派出分别由普兰诺·卡尔平尼、劳伦斯与阿瑟林率领的三个使团阻止蒙古入侵。欧洲各国阻止蒙古入侵,主要以劝阻和宗教上的同化为主:首先,谴责和劝阻蒙古的入侵行径;其次,表明基督教欧洲无意与蒙古为敌,争取和平谈判;再次,规劝蒙古人信仰基督教;最后,了解蒙古侵略的原因和未来的打算。
然而,此时的欧洲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与蒙古进行平等对话。各部落的统一使蒙古大汗能够聚集资源,形成强大的军队,对花剌子模国的征伐使蒙古显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蒙古帝国看来,教皇做出的和平姿态与其说是平等的政治对话,不如说是对蒙古的臣服。因此,贵由汗在回信中对英诺森四世表示:“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由此可见,基督教欧洲与蒙古进行政治对话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政治上破碎的欧洲与统一的蒙古帝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欧洲各国缺乏与蒙古进行平等对话的政治资本,寻求和平的尝试被蒙古看作对帝国的臣服。
(二)蒙古西征过程中的劫掠杀伐
在有关蒙古西征的史料中,蒙古对被征服国的杀伐行为尤为引人注目。1220年,蒙古攻破花剌子模国的忒耳迷城,居民被赶至城外,全部被杀。同年,蒙古破花剌子模国你沙不儿城,成吉思汗为报亲仇、惩治叛乱,屠尽全城。1383年,蒙古在呼罗珊等地区作战,一旦破城即将居民屠戮殆尽。
蒙古帝国的掠杀,首先出于经济需要,其次由于社会文化。在蒙古帝国征伐中亚及东欧地区时,对当地进行的掠夺、破坏及屠杀行为引起了西欧各国的极大恐慌。
首先,为满足经济需要是蒙古掠杀的重要动因之一。如前所述,蒙古帝国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模式,当部落规模扩大,草原便难以支撑部落发展,促使蒙古对外扩张。由于此时蒙古尚未意识到利用被占城市的重要性,倾向扩大领土和草场。当破城时,蒙古军队往往通过直接掠夺城市财产扩充军需,掠走手工业者满足生产需要。
其次,蒙古帝国对被征服地区的杀戮,还源于其社会文化与习惯法。如前所述,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过程中,蒙古帝国内部产生了崇尚权力的文化传统。在西征过程中,这种文化传统便表现为屠城。屠城行为能够震慑周边城市和国家,降低这些地区反叛的可能性,降低占領成本。
综上所述,西征过程中的劫掠、屠城行为,既出于游牧部落经济发展需要,又来自于蒙古的社会文化与习惯法,同时利于稳定被占地区秩序。然而,西征过程中的杀戮,在欧洲人眼中却是违反道德的不义行为,造成了欧洲世界的极大恐慌与反感,对欧洲各国集体心理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三)宗教演绎在欧洲造成的恐慌
基督教义是中世纪欧洲世界观的支柱。自教皇至普通民众,均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理论为基础,对自然及历史做出解释。对蒙古的扩张,基督教会将其解释为上帝的刑罚,由此将蒙古演绎为“基督的死敌”等宗教意象,二者的对立深化至意识形态层面。
蒙古帝国在十三世纪的崛起,使欧洲世界倍感惊诧。此时,欧洲对蒙古缺乏了解,对其概况、战略、目的等只能在神学框架下进行推测和解释。当时的欧洲人将天灾、外族入侵等事件解释为上帝对人罪恶的惩罚,《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曾记述:“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基于神学框架对西征历史的记述,很大程度上将蒙古帝国及其军队妖魔化了,使其成为“反基督”的化身。事实上,蒙古对西欧的入侵至远只到奥地利的维也纳边境,西欧人对蒙古军队的目睹见闻甚少,此时西欧对蒙古的见闻以宗教的想象为主。在西欧的马太·巴黎最早对蒙古的入侵进行记述时,就将蒙古帝国比喻为“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
当时的欧洲世界,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基于基督教义的框架,政治事务也不例外。面对陌生部族的崛起与入侵,教廷只能以基督教义对其进行解释,因而将其视作上帝对欧洲世界的惩罚,将蒙古的掠杀看作魔鬼的差遣。将蒙古入侵演绎为天罚的宗教预言,在当时造成了极大恐慌,也塑造了欧洲对东方世界的集体心理认知。
三、欧洲世界集体心理的形成
在蒙古帝国西征的过程中,政治对话的失效、蒙军的掠杀与基督宗教的演绎,给欧洲世界造成了极大恐慌,造成了基督教欧洲与蒙古帝国的对立,并使欧洲世界形成了如此一种集体心理:对东方世界的恐惧、对东方世界的怀疑、将东方看作对欧洲世界的威胁。
(一)对东方世界的恐惧
蒙古西征造成了欧洲世界对东方的恐惧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蒙古帝国对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有关。在此语境下,恐惧意味着欧洲各国对再次遭受东方入侵的担忧。
蒙古对中欧的征伐与统治,给当地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动荡,直接后果是欧洲世界对蒙古军队再度来袭的恐惧。事实上,当蒙古帝国停下继续西征的脚步后,蒙古将再次入侵欧洲的传闻却甚嚣尘上。此后一段时间,基督教欧洲仍忌惮蒙古的再次入侵,也内含对东方其他势力崛起的隐忧。
中世纪基督教各国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面对蒙古的崛起,各国对其政治结构、经济模式与宗教文化一无所知,只知道蒙古是从东方而来的入侵者,因而西欧各国长期将东方看作外部入侵的主要源头。对蒙古帝国再度入侵的担忧,随着时间推移演化为对东方世界入侵的恐惧。
(二)对东方世界的怀疑
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对话的基础,如果两个行为体互不了解对方的政治结构乃至政治文化,就难以理解对方的政治语言并建立有效的对话体系以理解对方意图,对他者更加容易产生怀疑与忌惮。对欧洲而言,怀疑指的是难以理解东方世界的意图与敌友身份。
蒙古帝国对当时的欧洲而言是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欧洲统治阶层对蒙古的政治与文化一无所知。在教皇致大汗的书信中,至少体现出三层疑虑:首先,欧洲各国对蒙古帝国征伐的缘由并不清楚;其次,欧洲各国不了解蒙古帝国的政治文化与行为模式;最后,基督教世界不明确蒙古帝国是否对西欧各国抱有敌意。
面对新的力量,教皇以规劝蒙古人归信基督教的手段尝试建立“基督教下的和平”。然而,教皇的尝试是失败的,对话的意图被大汗理解为弱者的臣服,双方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机制,蒙古帝国在欧洲看来仍是难以理解的。欧洲世界的疑虑未获解答,统治者面对蒙古帝国的强大军队,只能将其视作潜在的威胁。
四、结语
作为世界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一次直接接触,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对东方文明的集体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受蒙古帝国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欧洲对东方心理认知的形成,以基督教世界与蒙古帝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差异为基础,由双方交往中的过程性因素驱动,最终使欧洲世界形成了对东方文明的集体心理,究其根本,皆源于西方世界对其他文明缺乏了解,缺乏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对话,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偏见,这种无知和偏见却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国际政治的话语高地。以蒙古西征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明晰歐洲各国对华政策的深层动因,对我国了解当今国际话语环境,取得话语优势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海明.中世纪欧洲政治与经济制度新探[J].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2):3-21.
[2]刘阳阳.从基督教传统看奥古斯丁战争法理论的功与过[J].世界宗教文化,2015(3):27-32.
[3]宋鑫秀.蒙古西征对当时世界的统治及影响分析[J].黑龙江史志,2014(9):54-56.
[4]付欣欣.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国际法:蒙古人的西征与战争法[D].北京:外交学院,2012.
[5]陈启云.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J].史学集刊,2009(4):3-22.
[6]盖吉米.13世纪蒙古人的萨满教及其宗教观[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7.
[7]付来侠.蒙古西征对西方殖民扩张的影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3):118-120.
作者简介:彭钰馨(1999—),女,汉族,河北抚宁人,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制度。
赵银亮(1970—),男,汉族,河南新郑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一体化等。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