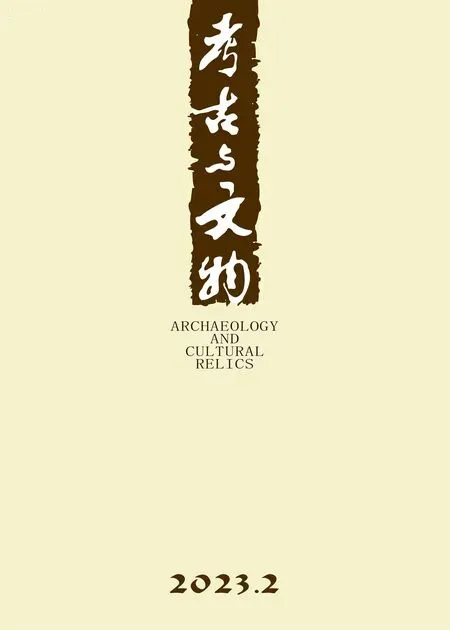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与纸画研究*
王 煜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吐鲁番地区晋唐时期的墓葬集中而丰富,且有机物保存较好,为了解该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众所周知,除文书外,墓葬图像中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是比较丰富而直观的。吐鲁番晋唐墓葬中也有不少比较完整且内容丰富的图像材料,学界以往关注和讨论较多的如唐代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绢画,此不多论。其实,十六国时期和唐代墓葬中的壁画以及与壁画有着同样内容和功用的大幅纸画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由于十六国时期和唐代的墓葬壁画与纸画内容具有较大不同,自成特色,因此本文拟先讨论前者。曾经有学者根据早年可见的材料做过初步探讨,取得了不少基础性认识[1]。由于新材料尤其是更为完整、重要材料的出土,这些认识也还需要适时修正和发展。而后来的研究中多是在叙述该时代的墓葬壁画或讨论其他问题时使用到这些材料[2],或是单个材料的介绍和讨论[3],尚未见专门的梳理及在此基础上的较为全面的文化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化涵义等研究。于是,笔者不揣浅薄,欲就这些问题求教于学界。
一、出土壁画与纸画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墓葬多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有些壁面装饰有壁画,可能还有纸画。这里的纸画专指与壁画具有相同内容和功能的大幅纸张上的图画(后详),不包括文书等纸张上的一些附属性图像或符号。虽然其内容、风格均相同,但毕竟质地和制作有别,这里还是分别介绍。
(一)壁画
目前集中见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其中哈拉和卓墓地已有系统的考古报告出版,可以较为充分地获取材料信息。阿斯塔那墓地的情况目前虽不能全面掌握,但其考古简报比较丰富,其中重要的材料在各种出版物和论著中也有较多披布,做初步的探讨已有一定基础。
1.阿斯塔那墓地西区06TAM605
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出土有东晋咸安五年(375年,“咸安”实际只使用二年)隗田英随葬衣物疏,此时属前凉末期,出土文书中前凉往往奉行东晋年号[4]。
壁画绘制于墓室后壁,长2.16、宽0.7米,画面大致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方位以观者为准,后同)。中部主体部分覆盖于帷帐之下,三名人物(一男二女,或为墓主及其女眷)跪坐于长案之后,面向左侧。其前方为北斗七星和三组两两相对的星象,分别有题记为“北斗”“三台”。人物后侧为马和牛车各一,一人牵牛前行。帷帐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个人脸,分别题记为“月像”和“日像”。左部主要为庖厨和生产场景,有汲水、捣舂、炊煮、仓储等图像,还有骆驼、羊、鸟类(应该是鸡)等家畜家禽。右部与中部相接处有一条类似于分隔带的格子,纵向上八个方格,中间一条竖线分割成四个连接的田字格,下部还有一株树木,根据后述材料应该表现的是田地。其右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阔叶植物,下部为藤蔓带果实植物,根据后述材料,分别为树木和葡萄。左中两部分上端绘垂帐纹。壁画四角各绘出一个黑色的梯形条块,表示固定画幅的贴片(图一)。

图一 阿斯塔那墓地06TAM605壁画
2.阿斯塔那墓地西区M408
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根据其形制、器物及出土文书,发掘者将其时代判定为十六国时期,墓主为吝尊锺及其妻令狐阿婢[5]。
壁画绘于墓室后壁,长2.09、宽0.68米。内容、风格与上述壁画几乎完全一致,只是细节有个别差异。如左部的骆驼后有骑马的放牧人,中部“北斗”和“三台”星象正下方有一案,上有一釜,人物面向釜跪坐。题记也更丰富,可以据此确定上述壁画中不易辨识的部分。如中部和右部相接的田字格条带中题记为“田”,右侧画面上部植物题记为“树”,下部题记为“蒲陶(葡萄)”。此外还有“日像”“月像”(帷帐上部两侧人脸形日月)“马”“车牛”的题记。壁画四角也有表示固定画幅的黑色贴片(图二)。

图二 阿斯塔那墓地西区M408壁画
上述两墓位置接近,出土器物的种类、造型都十分相似,尤其是壁画的内容和风格几乎相同,年代应该相距不远,M408也应为前凉末期或略晚的墓葬。
3.哈拉和卓墓地75TKM98
单室土洞墓,根据其形制、器物及出土文书,发掘者将其时代判定为十六国时期[6]。
墓室后壁绘有一幅壁画,长2.25、宽0.63米,大致也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左部主体为四名跪坐人物(一男子后随三名女子,或为墓主及其女眷),面向左侧。其左分为两个竖栏,左栏似为悬挂的弓箭,右栏为长案、侍女及容器,或为备食场景。中部又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炊煮,中部的格子对比前述材料应为田地,下部藤蔓上垂有成串果实,应为葡萄。右部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树木,下部为牛车和鞍马,一人牵牛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左部人物的上部有垂帐纹,其上虽比较漫漶,仍能大体辨识左右各有一圆形和新月形图案,根据其位置和形象,应当表现的是日月,其形象与上述两例不同(图三)。

图三 哈拉和卓墓地75TKM98壁画
4.哈拉和卓墓地75TKM97
墓室后壁有一幅壁画,长2.2、宽0.55米,左右两部分间略有错位。左部主体为一男一女两个人物跪坐于帷帐之下的榻上,面向左侧,其面前似为一灶,上面和左侧悬挂两套弓箭,最左侧为一仆从于三足炉前炊煮。右部左侧为一仆从牵鞍马,其旁还有一头骆驼;中间上面为树木,下面为牛车;右侧为横格,应为田地。左侧壁画的上端还有隐约可见圆形的日和新月形的月(图四)。墓葬年代推定为北凉时期[7]。

图四 哈拉和卓墓地75TKM97壁画
5.哈拉和卓墓地75TKM96
单室土洞墓,出土有真兴七年(425年)随葬衣物疏,“真兴”为大夏赫连勃勃年号,北凉向大夏称臣后奉其正朔[8]。根据衣物疏的记载,墓主应为宋泮及其两个妻子隗仪容和翟氏。
墓室后壁绘有壁画,长1.68、宽0.45米,大致亦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部最左侧不甚清晰,似为生产器具,主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棋格状的田地,下部为藤蔓植物,应为葡萄。中部为一男一女两人物跪坐,应为墓主。右部有一仆从、俎案、磨、炉(?)等,似为炊煮奉食场景,最右侧残损难辨(图五)。

图五 哈拉和卓墓地75TKM96壁画摹本
另外,据报告称哈拉和卓75TKM94、M95墓室后壁亦有壁画,但图像资料已不存,墓葬时代仍推定在十六国时期[9]。斯坦因在该地调查时也发现有一些墓葬壁画,根据其描述的内容,与上述类似,应该大致也属于十六国时期[10]。
(二)纸画
十六国时期的大幅纸画目前主要见于阿斯塔那墓地,较多提及的如M13出土者。整幅纸画由6幅纸片拼接而成,通长1.05、宽0.46米,内容与上述壁画基本一致,大体上亦可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中部的主体仍为帷帐和墓主,一男性人物跪坐于长案后,身后有一女性人物,站立且比例较小,似为仆从。帷帐前有一株大树,上栖凤鸟。左部主要为鞍马及仆从。右部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田地和农具,下部为炊煮、炉灶、捣舂、碾磨、储藏等生产生活场面,有一女仆。此外,整个画面上方左右两侧为日月,右侧日中有金乌,左侧月中绘画较为随意,看似人脸,但对应来看,更应为蟾蜍,中间有两个呈斗状的七星[11](图六)。

图六 阿斯塔那墓地M13出土纸画
在斯坦因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类似材料,并对两幅进行了公布。
其中2 区1 号墓出土的一幅纸画,约长0.41、宽0.37米,整体略呈竖长方形。画面上部主体为帷帐之下,墓主人跪坐于榻上,左右各有一女仆侍立和奉食,其左尚有一男一女跪坐面向榻上之人,或为家眷。下部主体为乐舞,两人跪坐奏乐,一女子扬手起舞。其下和旁边主要为各种炊煮和生产生活器具,也有一乘牛车。中部左侧还专门画出一个方框,并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为田地,右为树木[12](图七)。
该纸画的内容和风格与上述墓葬壁画十分相似,都是将墓主坐像及生产生活的各种场景、器具,乃至田园、树木等财产集中绘在一起,其时代和功用应该基本相同。人物的冠帽、服饰和器物的形态、特征也与上述材料一致,说明它们确实属于同一时期。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其一,该纸画中增加了乐舞题材,不见于上述材料。但此种乐舞图像为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中的常见题材,如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13],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和纸画受到河西地区较大的影响(后详),出现乐舞题材也属正常。其二,该纸画为略呈竖长方形,前述壁画和纸画皆为横长方形。然而,上述纸画是由多幅纸张拼接而成,该纸画目前所见部分为自成一幅的完整画面,其画幅有所不同也能理解。而且非科学发掘出土,是否还有其他部分与其拼接成一个整幅,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对比前述材料,其内容较为完整,这种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从总体上看,其时代、风格、内容和功用应当与上述纸画一致。
6区3号墓出土纸画,现能看到的部分为一横长方形画面,约长0.73、宽0.22米,主体为四名女子,一人跪坐于席上,似为主人,其他三名侍立或奉食,人物中间尚有案、罐、杯、衣架等器物[14](图八)。

图八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纸画(斯坦因公布二)
该纸画与上述材料有一定相似之处,如内容皆为以墓主生活场景为中心的图像。但也有较大不同:一是就目前所见部分而言,其内容比上述材料单纯得多,不见生产、田园、车马等题材,不过也可能是由于图上主要为女性人物场景的原因;二是人物发式也有较大不同,女性皆梳较大的双环髻,不过此种发髻广泛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直至初唐,尚不能作具体判断。由于信息缺失,目前只能判断该纸画属于魏晋北朝时期,与壁画有类似之处,应该也是作为墓葬装饰使用。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壁画和纸画材料(一例时代可能略有差别),总体来说该地区墓葬装饰并不多见,但亦有一定数量。壁画皆绘制于土洞墓的后壁,呈横长方形,长度在两米左右。该地区墓葬中的尸身往往紧贴后壁横放,与壁画贴近并大致等长,说明壁画直接服务于死者的功能。壁画内容包括天象,墓主及家眷、仆从,家畜家禽,生产生活场景和田园财富等,总体来说是汉代以来内地壁画墓中的常见题材类别,但将这些内容集中于墓室后壁的一幅壁画之上,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画面中往往以帷帐之下的墓主坐像为中心,周围分布其他题材。由于画幅限制,帷帐顶上两端绘制日月,北斗等星象甚至绘于帷帐下的空白位置(仔细观察阿斯塔那的两幅壁画,帷帐顶上确实已经没有空间绘制日月之外的其他天象,而纸画中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就将北斗等绘于顶端,看来确实是画幅限制,而不是有意为之)。
从最完整的材料来看,纸画的总体内容与壁画完全一致,只是由于纸张的限制,其大小、形制略有差别而已,二者应有共同的功用。关于其功用,有学者认为是壁画的画稿[15]。不过上述壁画皆十分简略而制作随意,是否需要临摹画稿,尚存在疑问。而且吐鲁番晋唐墓地中广泛存在以纸质葬具、明器替代实际器物的情况,根据这一传统,这些纸画更可能还是一种替代品。甘肃玉门魏晋墓中曾出土过贴于棺板上的伏羲女娲纸画[16],有学者据此推测吐鲁番出土的也是贴棺的纸画[17]。河西魏晋墓葬的棺板上往往绘制伏羲、女娲,玉门出土伏羲女娲纸画的内容符合这一饰棺传统,而吐鲁番十六国墓中并无与其纸画内容类似的棺画,甚至不用木棺等葬具,其为棺画替代品的可能性也不大。
笔者推测,纸画也是张贴于墓室壁上(最可能仍是后壁),充当壁画来使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壁画的四角还绘出了固定张贴的贴片,认为是仿照画布的悬挂方式[18]。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就壁画的内容来看,它不可能是仿生前使用的居室装饰,因为居室装饰中一般不会将天象、主人、奴婢、财产等绘于一幅,只有墓葬中有此传统。也就是说墓葬中也应该有此类用作张贴的画幅,那么,上述纸画最为符合这种功能和使用方式。另外,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多挖凿于戈壁之中,壁面多砂砾,绘制壁画往往需要修整壁面并涂抹地仗,较为费功,而当地的社会经济总体贫乏,这也是壁画墓少见和将各类题材集中于一幅的一个客观原因,张贴纸画以代替壁画应该也是在干旱环境和地域传统下采取的一种节省行为。当然,由于科学发掘和具有详细信息的材料缺乏,是否如此,还需今后的发现进一步检验。
另外,吐鲁番地区唐代墓葬中也发现有壁画,多是在后壁绘屏风画,同样发现有仿屏风画的纸画,看来壁画和纸画代替使用确实是该地区的一种传统。
二、文化传统、因素与丧葬内涵
新疆地区缺乏早期墓葬壁画的传统,楼兰地区发现过3~4世纪的大型壁画墓,但其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风格都与吐鲁番地区相去甚远,一般认为是来自中亚的粟特或贵霜人的墓葬[19]。对于吐鲁番墓葬壁画和纸画的渊源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乃是内地同期壁画墓题材的缩影。而其壁画构图布局,则又是在内地影响下根据自身的特点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构图形式”[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具有独特的起源,不能强用河西或其他地区的情况加以比附”[21]。笔者认为要厘清这一问题需要仔细分辨其主体文化传统和地方及其他文化因素。
首先,壁画和纸画的整体内容、具体题材和风格,均属于汉代以来的汉文化墓葬装饰传统,尤其受到河西地区,特别是其西部的酒泉、敦煌、嘉峪关一带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的强烈影响。
众所周知,西汉中期开辟河西以来,汉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传播和推进,尤其是汉末中原动乱,大量人民西迁,汉文化传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壁画墓特别流行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河西地区的壁画墓基本为砖室,有单室和多室,以前后双室最为多见,大多一砖一画,也有大幅画面。壁画内容和题材丰富,广泛分布于照墙、墓室顶部和墓室四壁,且配置具有一定规律。一般情况下,神仙、神兽等题材集中排列于照墙之上,有的墓室顶部也绘有日月和神仙、神兽;多室墓的前、中室往往绘墓主人、宴饮、庖厨、仆从、各类生产、田园财富及牛车等,后室绘绢帛、丝束及生活用具等;单室墓则往往在后壁绘墓主帷帐或宴饮,其他壁面绘生产、生活题材;另外,棺盖内部往往绘伏羲女娲和日月,也有个别星象。总体配置是以墓主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生产生活画面[22]。
可见,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和纸画总体上延续了河西墓葬壁画的题材内容和配置原则,只是将其简省并集中于墓室后壁的一幅画面之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河西壁画墓中的单室墓多发现于最西端的敦煌地区,而且除照墙之外,墓室中的题材内容已经大为简化。敦煌佛爷庙湾M37的墓室后壁上主要绘出墓主帷帐,其他墓壁上的生产生活画面则比较简略[23],敦煌祁家湾M310中也仅在墓室后壁绘墓主宴饮、庖厨的题材[24]。也就是说,在单室墓中将壁画简省并集中于后壁的做法在河西地区的西端已见端倪,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纸画应该直接延续了这种趋势。并且,河西地区尤其是西段的墓室壁画和棺画中有很大部分绘制比较随意,其风格及人物冠帽、服饰与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纸画(尤其是壁画)十分相同,也可看出二者之间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另外,在墓葬或葬具上张贴纸画以代替壁画的方式在河西地区魏晋墓中已可略见端倪,如上述甘肃玉门出土的伏羲女娲纸画。嘉峪关新城南墓区晋墓墓室无壁画,前室四角各放置一块长、宽均为0.52米的方形木框,框上残留木钉,有钉过画布的痕迹[25],也可以看作张贴纸画的雏形。
吐鲁番壁画墓中不少出土了随葬衣物疏,根据其上的墓主姓名及其他信息,皆为汉人,有隗、令狐、宋、吝、翟诸姓。史学界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高昌的隗、令狐、宋三姓就直接来源于河西地区[26]。《魏书·高昌传》记载北魏孝明帝对高昌的诏书:“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27]可见,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看来,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居民多是汉魏以来迁徙至此的百姓,而河西地区则是其必经之地和最重要来源。
结合来看,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纸画应该不仅仅是受到河西影响,而且是直接延续和发展了河西地区墓葬壁画往西的变化趋势和以纸画代替壁画和棺画的个别做法,进一步结合本地条件而形成。并且,这种趋势很可能是直接伴随居民迁徙而产生的。我们注意到,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典型的带照墙的砖室壁画墓已有发现于新疆库车地区[28],这显然不仅仅是文化传播,而是移民的直接带入。
以上是就其主体文化传统和直接来源而论,墓葬壁画在进入吐鲁番之后确实也有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改造,如纸画的出现和画幅的缩小、集中。学者们也都注意到葡萄园题材的出现,是不见于内地的本土特色。葡萄的种植在吐鲁番地区历史悠久,并与水利灌溉结合在一起,阿斯塔那382号墓中出土的十六国时期文书中就有“引水溉两部葡萄”“五人知行中部葡萄水”的内容[29]。上述壁画和纸画中葡萄园为最主要的题材之一,不仅是吐鲁番葡萄种植的最早图像材料,也说明其已经成为当地农业和经济生产的主要代表。
壁画和纸画上的日月图像也值得特别注意,其形象并不固定,既有内地传统的金乌、蟾蜍的表现形式,也有用圆形和新月形来表现,比较有特色的是以人脸来表现,并在旁边题记“日像”“月像”。
以新月形表现月亮在汉地见于西汉前期的帛画中[30],之后基本不见。而新疆地区3~5世纪的石窟壁画中正好流行此种新月形的月亮,如克孜尔第38、118窟中的天象图[31],当然应该考虑可能来自本地区同时期或略早的石窟壁画的影响。直接以人脸表示日月目前未见于其他地区,应该是该地区的独特表现。将日月与神话人物联系并加以描绘倒是常见于古代中、西方艺术中。与该地区密切相关的一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和棺板画中常以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怀抱日月,这一形式也被吐鲁番地区后来的墓葬继承和发展,但已不作怀抱状[32];二是如克孜尔石窟中4~5世纪开始出现的驾车出行的日神和月神,这种形象应该来自中亚和印度的太阳神,如密特拉等。虽然这两种图像都是将日月与人物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河西棺板画中的有些伏羲女娲的形象描绘得十分简略,还有“左日”“右月”的题记[33],不排除其进一步简化为人面的可能。但其形象毕竟与吐鲁番墓葬壁画中的人面形日月有很大差距,无法直接指认为后者的来源。总之,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和纸画中的日月形象较为多样,反映了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特色。
至于壁画和纸画的丧葬内涵,就其整体题材、内容而言,显然与河西和内地的墓葬装饰一致,将庖厨宴饮、仆从车马、家禽家畜、田园作物、家居器用等集中描绘于墓主旁边,无非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拥有这些财富并快乐地生活。其与河西最大的不同在于,吐鲁番壁画和纸画中基本是宴饮享乐和生产生活内容,缺乏前者集中于照墙和墓室顶部的大量神仙、神兽题材。即便是出现日月星象,日月也被绘制于画面边缘的帷帐两侧的空白处,星象甚至被置于帷帐之内的空白处,更多画面中则直接省略这些内容,可见其在人们观念中的重要性相对较低。总体上显得比较现实和朴素,这也许是由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决定的。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反映丧葬信仰的题材出现。上述三幅壁画和纸画中出现了北斗、三台星象,也显示出较为鲜明和具体的内涵。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并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北斗信仰[34],其论证总体可信并较为详尽。不过,该文认为上述纸画上的两个斗状的七星为《淮南子·天文训》中“北斗之神有雌雄”说法的体现,或可商榷。星象中本来就有两个“斗”,一个是中宫的北斗,一个是北宫的南斗,形象一致,不过北斗为七星,南斗为六星。但因为南斗的影响不及北斗,受到后者的影响,墓葬星象图中也见有将南斗错绘为七星的情况。如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35]中斗状七星被绘在牛宿、女宿旁(北宫前三宿为斗、牛、女),显然是南斗而非北斗。而且纸画中两个星斗与日月形成对应关系,这样的图像在南阳麒麟岗东汉画像石墓的天象图中也能见到,后者明确将四象、日月、南北斗对置[36]。东晋干宝《搜神记》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祈福皆向北斗。”[37]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赤松子章历》中也说:“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寿无穷。”[38]壁画中北斗又与三台星象一同表现。六朝道书《赤松子中戒经》中说:“天上三台、北辰,司命司禄,差太一直符,常在人头上,察其有罪,夺其算寿。”[39]根据学者研究这里的“北辰”即指“北斗”[40]。可见,将北斗、南斗对置和北斗与三台组合,确实主要与司命信仰有关[41]。笔者曾经讨论过,司命信仰在汉六朝的墓葬中特别流行,其核心不仅是延年益寿,还包括死而复生和升天成仙[42]。
需要指出的是,以南、北斗为司命是汉代以来的传统观念,此点已为共识,无需多论,以三台为司命同样是一种传统观念。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传》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为司命,为太尉”[43]。《黄帝占》云:“三能(即三台)近文昌宫者曰太尉,司命。”[44]《春秋元命苞》云:“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45]《晋书·天文志》亦云:“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46]上述道经只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观念,而不是相反,因此上述壁画和纸画中的相关内容,尚不能直接认为与道教相关。
三、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总体上比较朴素,较少装饰,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壁画存在,该地区还根据干旱的气候环境发展出纸画这一墓葬装饰手法,其内容、功能甚至张贴方式应该都与壁画同类。
该地区的壁画整体上继承了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的内容、布局、风格,甚至直接承接河西墓葬壁画往西变化的趋势,将各种题材集中绘制于单室墓的后壁并贴近墓主,而以纸画替代壁画的做法同样也直接延续和发展自河西地区。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的迁移和文化的移植,与这些墓葬出土衣物疏中的信息一致。除此之外,壁画和纸画上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和本土特色,如主要题材中的葡萄园,日月的多种形象则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说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底色,各种文化向该地区的影响和汇集。
与河西和内地墓葬装饰最大的不同在于,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和纸画内容多现实、朴素,不见前者常见的神仙、神兽内容,与丧葬信仰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南北斗、三台(尤其是北斗)为代表的司命信仰上,这种信仰也是汉代以来传统信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后世道教对之吸纳、整理,因此壁画和纸画上的相关内容是否能反映道教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尚不足论。
此外,从墓葬位置来看,敦煌佛爷庙湾墓地中,使用壁画的不少为家族墓地中的祖墓。吐鲁番十六国时期壁画墓的墓主身份和地位也值得关注。目前,哈拉和卓墓地已有较为系统的材料公布,其中11座十六国时期墓葬中的5座使用了壁画,且位置比较接近。M94、M95和M96、M97、M98分别为两组紧邻并斜向一字排列的墓葬,较大可能为两组家族甚至是家庭墓葬。可见其具体使用者或许与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有所不同,为较为紧密的家族甚至家庭成员所共用。此点需待阿斯塔那墓地材料系统公布和新的考古发现来进一步验证和讨论。
附记:敦煌祁家湾墓地出土有3块人物砖画,除墓主夫妇坐于帷帐宴饮外,尚有牛车、马、庖厨等,也具有将许多内容集中于一砖之上的现象。
[1]a.王素.吐鲁番晋十六国墓葬所出纸画和壁画[J].文物天地,1992(4).b.孟凡人.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和纸画略说[C]//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9-16.c.町田隆吉.4 ~5 世紀吐魯番古墓の壁画·紙画に関XIIItf基礎的検討[J].西北出土文献研究,2007(5).
[2]如a.Sarah E.Fraser.Performing the Visual: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13.b.韦正.试谈吐鲁番几座魏晋、十六国早期墓葬的年代和相关问题[J].考古,2012(9).c.朱磊.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北斗信仰[J].西域研究,2013(2).
[3]a.王素.吐鲁番出土《地主生活图》新探[J].文物,1994(8).b.李肖.吐鲁番新出壁画“庄园生活图”简介[J].吐鲁番学研究,2014(1).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告[J].考古与文物,2016(5).
[5]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 号墓[J].考古,2006(12).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91.
[7]同[6]:183.
[8]同[6]:181.
[9]同[6]:162.
[10]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6-931.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历史文明集粹[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149.
[12]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三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7.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4]同[12].
[15]a.岡崎敬.アス(IX)ァナ古墳群の研究—ス(IX)イas探険隊の調査PH中心として[J].佛教兿術,1953(19).b.同[1]a.c.同[2]a.
[16]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墓发掘报告[J].陇右文博,2003(1).
[17]孙彦.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87.
[18]同[4].
[19]a.孟凡人.论楼兰考古学[C]//新疆考古论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441.b.李青.古楼兰鄯善艺术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400-410.c.陈晓露.楼兰壁画墓所见贵霜文化因素[J].考古与文物,2012(2).
[20]同[1]b:15.
[21]同[2]b.
[22]同[17]:101-115.
[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1-12.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44-46.
[25]同[16].
[26]a.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J].中国史研究,1979(1).b.王素.高昌令狐氏的由来[C]//学林漫录(第9 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184-188.c.高丹丹.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以宋氏家族为例[J].西域研究,2007(4).
[2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44.
[2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2007 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3(12).
[29]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82 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3(1).
[3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40.
[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14.
[32]孟凡人.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C]//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7-30.
[33]编委会.高台文物精品鉴赏[M].高台:政协高台县委员会,2018:51.
[34]朱磊.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北斗信仰[J].西域研究,2013(2).
[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定边县郝滩发现东汉壁画墓[J].考古与文物,2004(5).
[36]王煜.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天象图及相关问题[J].考古,2014(10).
[37]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66-67.
[38]道藏(第11 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204.成书时代依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后同。
[39]道藏(第3 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445.
[40]张勋燎.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北朝墓葬的解注文研究[C]//中国道教考古(第2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504.
[41]同[21].
[42]a.同[36].b.王煜.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天乙”滑石猪与司命信仰[J].东南文化,2017(6).
[43]郑玄注.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57.
[44]瞿昙悉达.开元占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649.
[45]同[44].
[46]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