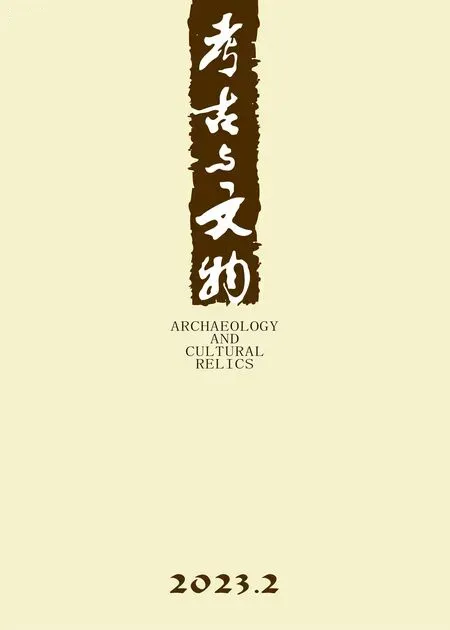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遗存述略
韦 正 宁 琰 辛 龙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本文涉及的是考古所见房屋类建筑遗存,不包括城墙、城门、涵洞、窖穴、墓葬等泛化概念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唐之前中国北方地区建筑基本为土木混筑形式[1],比唐之后以全木构构架为主的时代还长,研究的意义大,困难也大。由于石窟、房形石椁、壁画等材料的存在,北朝时期建筑情况较为清楚[2]。北朝建筑与之前建筑的关系如何?近年来十六国考古新发现不断,结合早年公布的材料,已能部分回答这个问题,并对理解汉晋建筑也有所帮助。
十六国考古材料并不丰富,但在不丰富的材料中,却有相对较多的建筑资料。相关建筑资料的地域特点很明显,关中地区发现的主要是土雕房屋,河北和辽西发现的主要是建筑构件,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主要是墓葬壁画。这几类材料的性质并不等同,加之笔者学力有限,只拟就这些材料进行介绍和基础性讨论,从建筑学角度的讨论留待他日。关于高句丽壁画资料,需说明的是,相当于十六国时期的高句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今朝鲜半岛北部,那里从西汉设乐浪郡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文化面貌日益接近乃至雷同,直到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当地才逐渐开始对高句丽民族文化也有所表现,但中原文化始终突出。因此,可以将高句丽壁画中的建筑资料纳入本文的分析范畴。
一、关中地区的主要发现
关中地区最受关注,尤其是2020年发掘的西安少陵原中兆村M100[3]主要因为土雕建筑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而更受重视。其实,类似的土雕建筑之前就有发现,但保存之好,清理之精细,资料之完整,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代方经发掘的中兆村M100后来居上。下面将关中地区主要考古发现简介如下[4]。
中兆村M100为二过洞二天井双室墓,在二过洞和甬道上方各有一土雕建筑。第一过洞上方的建筑由从上至下依次向前突出的三层建筑组成。最下一层和中间一层建筑保存不好。最上部建筑为悬山顶式,正脊两端有鸱尾,垂脊与正脊做法和宽度基本相同;宽厚的垂脊表明两侧山墙为很厚的夯土墙;正面面阔三间,有一门二窗,并有红色彩绘柱间隔,这个彩绘柱同时也是廊柱;明间设门,是在很厚夯土墙中安装了木门的形象[5];直棂窗四角有放射状线,也表明这是一座厚夯土墙壁的建筑;山面屋檐为排山勾滴的形式,脊槫和下平槫用红色彩绘表示,显示此建筑进深二间,还显示此下平槫架设于前后壁夯土墙顶部[6]。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平台,平台前沿壁面上有红色彩绘的栏杆,或许建筑与栏杆共同表示一个院落。第二过洞上部土雕建筑与前述建筑雷同,但正面屋檐以下部分保存较好,可补前述建筑之缺:瓦作层之下为望板,望板之下为椽子,椽子之下为红色彩绘的橑檐枋,橑檐枋以四根红色彩绘的立柱承托;在椽子下有一小散斗,从图像上看似乎是架于橑檐枋之上,以承托椽子,但实际情况要复杂点,待下文叙述到彭阳新集墓时一并讨论(图一,1)。第二过洞上方建筑的门窗的立体感更强,将厚夯土墙表现得更加明显。甬道上方土雕建筑的屋顶以上部分不存,门也保存得不好,但为一门二窗三开间的格局是清楚的。门窗都是浅雕,表明这是一木构建筑。

图一 关中地区的十六国房屋类建筑遗存
与中兆村M100同在西安少陵原的焦村M25为二天井二过洞的三室墓,在墓道上方、第一、二过洞上方各有一土雕建筑。墓道上方的土雕建筑保存不佳。第一、二过洞上方建筑顶部也已经完全不存,但下部保存完好。建筑正面尚有彩绘,似表现立柱和地栿,已不甚清晰,但二者均为面阔三间的简单建筑。正面均一门二窗,第二过洞上方房屋背面还有一窗。前后窗尺寸接近,似无通过大小以区别功能的目的。门、窗均浅雕而成。二建筑下方均有一平台,表面以红彩描绘类似后代勾片栏杆式的花纹。从这种花纹和浅雕门窗可知,二建筑模拟的也是木构建筑,且有可能建于下面的夯土建筑之上(图一,2)。
早年发掘的长安县韦曲塬上M1[7]被笼统地定为北朝墓,为一过洞一天井的双室墓。过洞顶上土雕一庑殿顶建筑,在过洞前立面由上往下还雕有依次突出的三层建筑。过洞顶上的庑殿顶建筑最复杂。面阔为三间,雕一门二窗,红色彩绘立柱四根。建筑所在生土台长2.8、宽2.3米,所以建筑进深可能是二间。四面屋顶均由筒瓦和板瓦交替铺成,板瓦宽度大约为筒瓦宽度的2倍。发掘简报说屋面四角略起翘,在所附图纸上也如此表示(图一,3)。建筑正面檐下部分颇难以辨别和理解,这与简报的报道状况有一定关系。简报所用建筑术语与常用术语不太一样,根据所附图纸,在瓦作层下有望板(灰背层没有表示。简报称此为“枋”),望板下为椽子(简报称为“檩”),椽下还有一小物体,简报明确称之为“斗”。简报关于立柱的描述最令人迷惑,四根彩绘立柱简报称为“枋”,立柱头上的栱形物,简报又称之为“栿”。应该说简报文字描述不尽完美,让人对所附图纸是否准确摹绘了建筑正面的雕刻和彩绘图案隐有担忧[8]。简报又没有发表照片,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座前面带廊的建筑。这一建筑的门窗似乎与焦村M25的一样为浅雕而成,暗示这也是一座木构建筑。这一建筑之下的三层建筑大同小异,其不同之处是由上往下第二层建筑“在窗下之两根柱间有以线条勾画的镂空装饰”,这大概表示前廊两侧带有护栏,将这种木构建筑表现得更为轻巧。
彭阳新集墓为二过洞二天井的单室墓,第二天井位于封土之下。在第二天井前部有非常简单的长方形土雕建筑,剔雕出略有倾斜的瓦垄。天井后部土雕建筑完整,基本形态同中兆村M100,主要区别有三点:一是山面屋檐不是排山勾滴,而是简单的平板式屋檐;二是屋面远比中兆村M100的厚,不知是否因为承托屋檐的方式与中兆村M100不同,抑或彭阳新集所在地区更为寒冷;三是屋檐下的承托方式,简报描述为:“房檐下出14根挑檐枋,上承替木托屋顶”,从实物来看,是14个斗形物承托连檐(图一,4)。
关于上面的第三小点,需要结合中兆村M100进行适当讨论。中兆村M100和彭阳新集墓土雕建筑的表现方式都与真实建筑有差距。从图像上来看,中兆村M100有前廊,前廊柱头之上为橑檐枋,上托椽子,紧贴椽子之下有小斗。真实建筑的前廊椽子之下不可能有小斗,因为这个小斗不可能是贴附于椽子之下的垫木之类构件(椽子只需与橑檐枋直接接触即可),而只能是悬挑构件,但房屋前廊没有小斗栱臂生根之处。因此,这个图像是半真实半写意的。彭阳新集同样如此,承托连檐的只能是椽子,而不可能是斗栱。因此这个土雕建筑的屋檐部分没有表现椽子,也没有表现橑檐枋。那么是否可能为密梁形式?这个可能性也基本不存在。密梁需与平顶相配,这个土雕建筑是两面坡的悬山顶。如果充分表现的话,彭阳新集土雕建筑的屋檐部分应该是这样:最上为瓦顶,下为连檐,其下为椽子,再下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椽子下为橑檐枋,其下为从墙壁悬挑出的斗栱,一种可能是椽子下直接为从墙壁悬挑而出的斗栱[9]。再有一种可能性是屋檐是从墙壁伸出的丁头栱。以上情况都可能是没有前廊的夯土建筑前檐下的形态,这虽属推测,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支撑,但中兆村M100和彭阳新集墓土雕建筑在发现之前,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可能存在的建筑类型。中兆村M100与彭阳新集墓土雕建筑可以合而观之,中兆村M100将无前廊夯土建筑前部的挑檐情况不恰当地挪到了前廊檐下[10],彭阳新集墓省略了不宜省略的椽子,二者可能也都省略了撩檐槫。长安县北朝M1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导致简报难以清晰准确地进行描述,但建筑的基本情况应与中兆村M100和彭阳新集墓的接近。三座墓葬都强调椽子下的斗栱,可见这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建筑构件。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小斗栱?这当与椽子相当粗大有关。椽子下部能托以斗栱,或者说省略了撩檐槫而以斗栱直接承托椽子,本身就说明椽子直径非常可观。目前还没有这个时期椽径的直接资料,或许瓦当能说明点问题。虽然瓦当与椽子直径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大小相应则是肯定的。假定椽径与瓦当直径相近,以十六国时期常见瓦当直径17~20厘米计[11],与此尺寸相应的椽子是非常粗大的。可能为了使其与橑檐枋牢固相接,并且由于出檐也比较深远,所以从墙壁悬挑出单臂栱,正立面在壁画或雕刻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小散斗。虽然是土雕建筑模型,但几座十六国土雕建筑屋面瓦垄的间距都甚宽大,这应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带有规律性的特征。瓦垄间距大主要是由于板瓦宽大引起的,板瓦宽大,引起筒瓦也有所变大,连带瓦当也相应变大。大同出土一件北魏晚期的石雕屋形龛,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早晚的差异(图一,5)。
墓道中的土雕建筑是关中地区最有特色的发现,迄今只在关中地区发现[12],这一做法目前只能认为是十六国时期在关中地区兴起的。土雕建筑对木构建筑和夯土墙建筑都有所表现。夯土墙建筑中,有前廊和无前廊的都有所表现,但具体的表现方式并不容易完全理解。中兆村M100土雕建筑山面对屋顶、椽、槫、夯土墙关系的表现十分清晰,赋予今人对以夯土墙为主要承重体的土木混筑建筑明确的立体感知。这对于理解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土木混筑式建筑也有帮助。
二、河北和辽西地区的主要发现
主要是邺城遗址出土的一批建筑构件,多展出于河北临漳县邺城博物馆。最大的一件为有“大赵万岁”铭脊头饰,高62.2、宽58、厚8.8~10厘米,背面有一半圆形筒瓦状残痕,有助于推测使用方法。“大□(赵)万岁”铭檐头筒瓦、瓦当多件,其中一件筒瓦直径15.3厘米。半圆形人面瓦饰多件,其中一件宽29.8、高13.8、厚3厘米,上部平齐、背面光素,无明显使用痕迹。“富贵万岁”铭瓦当多件,其中一件直径14.8厘米。莲花纹瓦当[13]规格不一,直径17.8、18.5厘米者皆有。莲花纹檐头筒瓦直径17.2厘米(图二,1~4)。此外尚有多件十六国时期的板瓦、筒瓦,还有植物纹瓦当、名称不详的瓦件、凹棱石柱等。这些建筑构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赵”铭,可据此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建筑遗存无误。但不能忽视的是,前燕也曾在邺城定都,没有“大赵”铭建筑构件也不排除属于前燕时期的可能性。瓦当直径相差也较大,可达3.7厘米。
辽西地区的发现主要有两个地点,一是朝阳北塔和龙城宫城门址[14],一是北票的金岭寺遗址[15]。
朝阳北塔的前身是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楼阁式佛塔,佛塔直接建在三燕时期的宫殿建筑基础上,即以三燕宫殿夯土台基作为佛塔基础。三燕宫殿夯土台基90米见方,作三层的高台式。由于后期频繁利用改造和破坏,三燕时期的遗迹大概只有两个柱础坑、断续的回廊、若干柱洞和局部的地面。出土遗物有瓦、瓦当、半圆形瓦饰、柱础石等物。瓦皆有布纹,筒瓦完整者直径19厘米,板瓦完整者长38~41.5厘米。瓦当多为四叶纹,直径有18、20厘米不同规格。半圆形人面瓦饰出土70余件,规格相近,直径约33、高14.5~16、厚2厘米多(图二,5~7)。柱础石有覆斗形、覆盆形和素平方础。覆斗形柱础较大,下部的平底方座123厘米见方,上部覆斗形部分118厘米见方,两部分通高53厘米。覆斗形四面浮雕龙纹,顶面中间有一圆形大柱窝,直径56、深7.5厘米。覆盆形柱础石下部和大柱窝的规格接近覆斗形础石,可见当时建筑规模之大。
上述数据中,筒瓦、板瓦、瓦当尺寸俱有,筒瓦与瓦当大小正好相配,筒瓦与板瓦结合构成瓦垄时,瓦垄和垄沟宽度相近,即屋面呈现平行等距的瓦垄行列,与关中地区土雕模型上垄沟特别宽的情况不同。发掘报告称半圆形人面瓦饰为人面形陶构件:“人面形陶构件在其他地方的十六国时期遗址中也曾有发现过。这种构件发现数量较多,与筒瓦、板瓦共存,显然是常用的建筑构件。根据人面形构件的宽、高尺寸及与同出的瓦件瓦成(引者注:原文如此)的瓦垅沟相近情况看,它应为正当勾,平面在上,背面贴在正脊侧面。”[16]这是目前最有说服力的推测。
龙城宫城的南、东、北、西四门都经过发掘。南门遗址入选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时代因出土北燕太平十三年(421年)年号陶片而得到确认,与房屋类遗存相关的重要遗物是半圆形人面瓦饰、四叶纹瓦当[17](图二,8)。
北票金岭寺遗址主要发现三组建筑遗址,呈曲尺形分布,东侧一组,北侧两组。北侧靠东的为第一组,由5座体量相近的单元院落组成一个整体。外围墙长度按照北东南西顺序分别为53.75、26.5、52.75、26.4米,宽1~1.1米。隔墙宽0.6~0.7、围墙和隔墙残高0.3~0.4米。每一院落南壁开门,门内外四角尚留有磉墩(引者注:应为柱础。下同),磉墩中间柱洞直径约0.3米。院落中部为近方形的夯土台,边长6.3~6.8米,南部有斜坡状单踏道[18]。夯土台四角有磉墩,中有0.3米的柱洞。夯土台周围散落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在院落西北角有小方形夯土台,边长1.5米,周围也散落建筑构件。北侧靠西一组建筑为第二组,其西部被河流冲毁,现存两个大小不等的院落。东侧一组建筑为第三组,由三个单元院落组成,每个院落中间是体量接近的长方形台基,台基上分前后两排各置3个磉墩,前有两斜坡踏道。每个院落的后部设两个小夯土台。大小夯土台周围散落大量建筑构件的情况同第一组建筑。瓦当直径16.2~17.9厘米,筒瓦宽端直径17~19.7、窄端直径11~17.1厘米,板瓦宽端宽39.2~40、窄端宽35~35.1厘米。瓦当有四叶纹、六叶纹两种,有网格状底纹[19](图二,9)。
发掘报告将金岭寺遗址年代推定为魏晋之际,是“曹魏初年慕容部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这一说法遭到了其他学者的一致否定。田立坤认为遗址年代上限不早于龙城始建的341年,下限可到北燕。其性质可能为“廆庙”—慕容廆之庙,前燕慕容儁于357年始建,后燕初可能曾予修缮,沿用至后燕末年,废于北燕[20]。王飞峰认为与《晋书·慕容垂载记》所载慕容垂“缮宗庙社稷”有关[21]。两种观点均将金岭寺遗址的年代指向三燕时期。瓦件散落在夯土台周围,暗示原来的建筑可能为庑殿顶式。单元院落门附近也有瓦件,表明门上原来用瓦修葺,规格较高。
辽西关于三燕时期建筑遗存的重要发现还有文字类瓦当,在朝阳营州路和朝阳北塔都出土了“富贵万岁”铭瓦当[22](图二,10~12)。
由上可知,河北和辽西地区主要发现的是建筑瓦件,重要建筑为庑殿顶,夯土墙是主要承重墙。
337年慕容皝在辽西棘城称燕王,341年建龙城,353年迁都蓟城,357年迁都邺城。后燕时将都城从中山迁回龙城。北燕继续以龙城为首都。朝阳和邺城是三燕政权在辽西和河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其关系密切,彼此影响,如前燕慕容暐建熙五年(364年)“燕侍中慕舆龙诣龙城,徙宗庙及所留百官皆诣邺”[23],后燕慕容熙时“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24]。因此,在邺城和朝阳、北票等地都出现半圆形人面瓦饰、多叶纹瓦当、“富贵万岁”铭文字瓦当,可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
三、高句丽地区的主要发现
下面涉及的墓葬有5座:冬寿墓(357年)、德兴里墓(408年)、水山里墓、双楹冢、天王地神冢。前两座墓葬都有纪年,明确相当于十六国时期。水山里墓、双楹冢壁画中人物服饰汉式和高句丽民族服装皆有,年代应在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不久,或许为十六国末期前后。天王地神冢的年代可能要再晚一点,但这个墓葬的建筑形象极其丰富,从形象看与前几座墓葬没有多少差异,所以也纳入到考察范畴[25]。
冬寿墓是前室带两个耳室的前后室墓,各个墓室及甬道顶部都作出藻井,体现出模仿地面建筑的强烈意愿。墓葬壁画中最形象的建筑是厨房,虽然厨房的建筑等级低,但山面交代得比较充分,对于理解当时的悬山顶建筑很有帮助。壁画的山面部分很像是房屋的横截面与实际山面上部的结合。壁画中山面前后檐柱上托木梁,梁上为三角形叉手,叉手上立斗以承托脊槫,这些都相当于房屋的横截面。山面檐口以博风板遮挡,这相当于实际的山面。博风板以不同的颜色表示,并遮挡了叉手顶上斗的上半部,但通过斗连接大叉手和脊槫,并提高屋顶高度的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图三)。

图三 安岳冬寿墓壁画厨房
德兴里墓为前后室墓,墓顶下部略近圆形而上收,上部再改为藻井。前后墓室四角皆有彩绘梭形柱,柱头有斗以承梁枋。后室梁枋有两层,两层之间连接方式比较特别,以两个一线排列的人字栱上托很长的一斗三升,转角部位有横跨于两壁梁枋之上的人字栱。由于两道梁枋位于墓顶的下部,这个位置的墓顶弧度并不大,所以,这部分的整个结构看上去有点像抬梁式,只是以人字栱、一斗三升代替后来使用的蜀柱、驼峰而已(图四)。

图四 平安南道德兴里墓透视图
水山里墓是凸字形单室墓,墓顶形式同德兴里墓。墓室内部彩绘木作的形式与德兴里接近,只是具体形式有别。四角为柱头有收杀的立柱,柱头有莲瓣形饰,之上为斗栱,上托梁枋。此梁枋之上还有一层梁枋,两层梁枋之间中部以人字形叉手相连,在角部仍为斗栱,即角部第一层梁枋上下都是斗栱。这与德兴里墓一样都可能表现的是抬梁式构架。由于位于墓室角部,角柱上每面的斗栱都只有半个,实际建筑中角部斗栱是十字相交且外跳,还是外侧垂直割斫不出跳,无法得知(图五)。

图五 水山里墓墓室西壁局部
双楹冢是前后室墓,藻井式顶。前后室之间的过道中并列两根大柱,因此而得名。前后室四角皆有柱,柱头上有两跳斗栱,向上托起梁枋。与德兴里墓和水山里墓一样,梁枋之上有叉手,叉手之上应该再托梁枋,但由于双楹冢在叉手之上已是叠涩,所以梁枋表现得不是太清楚。墙壁转角部位仍然有跨两壁的人字形叉手。前后室过道较长,其中的双柱非常硕大,几乎占据了过道一半的宽度,这看上去虽然有点突兀,但与冬寿墓前后室之间的三大一小4根立柱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不仅说明高句丽地区墓葬建筑传统在延续,而且提供了大型建筑前后进之间如何分隔和连通的状况[26]。双楹冢墓门也是套叠形,说明墙壁非常厚,这为理解前后室过道墙壁很厚提供了方便(图六、七)。

图六 双楹冢墓室北壁局部
天王地神冢为前后室墓,是高句丽壁画墓中表现建筑结构最充分的,特别是将叉手的使用方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且极富立体感。其前室表现的是进深较小建筑的样式。前壁的壁柱表明墙壁是很厚的夯土墙,但壁柱的承重作用并不大,这从平梁直接担在墙壁上可以看出。叉手顶部的座斗很大,座斗与叉手顶部之间有皿板,座斗上部有替木承托脊槫。前壁上方用不同颜色表现了下平槫,下平槫应该位于前壁上部的中间位置。椽子就担在下平槫和脊槫上。几者关系在壁画中交代的很清楚,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后室的图像看上去十分复杂,主要是由于墓顶下半部为叠涩、上半部又改为多边形引起的。室内下部四角的四个叉手位于抹角石之下,可能只是为了表示与抹角石呼应的装饰,实际上并不存在。忽略这四个叉手后,按照后室图像的现状理解的话,可以将后室想象成一座下部为方形、上部为多边形的亭子,亭子内部无柱,在亭子内部上方用叉手支撑起一圈梁枋,以此实现亭子上方的主要结构。也可以将后室直接想象为一个四边形的房屋,只是在四角的上部有四个大叉手。由四个大叉手都横跨两壁,可知叉手上托的是中平槫(下金檩),且这个房屋是庑殿顶式。叉手之上为曲栱,但曲栱为单臂,甚至还是两跳的单臂栱,所托当为上平槫(上金檩)。上述结构方式并不牢固,只能在庑殿顶侧面采用,真正承受屋顶主要重量的还是建筑中间的大叉手或抬梁。也可能是绘画形式的限制,没有将曲栱画全;如果画全的话,曲栱呈一高一低的形式以上托角梁,而不承担托举槫子的作用(图八)。

图八 天王地神冢透视图
高句丽城址、墓葬、寺院的发掘很多,瓦当也发现很多,基本都是立体感很强的莲花纹瓦当。砖也有发现,主要在墓葬附近,此不详述。
上述墓葬壁画体现了高句丽建筑的如下特点:1.夯土墙是大型建筑的主要承重墙;2.庑殿顶是大型建筑的基本样式;3.可能产生了以叉手相连接的简单的抬梁式屋架;4.叉手在建筑内角部的处理方式上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直接或通过斗栱承托角梁,也是负担和联结中、上平槫(金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简单的讨论
以上简述了三个地区考古所见主要建筑资料,面貌差异明显,关中地区以土雕建筑、河北和辽西地区以瓦类建筑材料、高句丽地区以壁画图像各具特色。这种资料状况上的差异,究竟反映了三个地区建筑什么样的关系?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全面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不足以回答三地建筑是否有显著差异的问题。现在只能就瓦当来说,三个地区建筑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中地区可能是继承汉代特色的云纹瓦当[27],河北和辽西地区是多叶纹瓦当,高句丽几乎都是莲花纹瓦当。河北和辽西地区都发现了很多半圆形人面纹瓦饰,关中没有发现,高句丽只发现一件[28],更体现了三个地区的差异。高句丽地区可能存在的简单的抬梁式屋架或许不存在于其他两个地区,就是说高句丽建筑可能发展得要快一点,这当与朝鲜半岛北部与东晋政权保持联系有关,东晋建筑的木构成分要更发达一些是公认的。
但是,三个地区的差异是表面的,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其共性。夯土承重墙是三个地区都能观察到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庑殿顶和悬山顶虽然不能在三个地区都直接观察到,但通过简单的分析是确定无疑的。与这种墙、顶相伴随的是壁柱、大叉手等特点,也必然是共同的。椽架很粗大,屋面很厚重,这虽只在中兆村M100基本可以肯定,但其他建筑也不能否认。总之,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三个地区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分裂而出现本质上的差异。
三个地区相似的技术直接继承了汉晋时期,这可以魏晋时期的高台地埂坡M1来说明,该墓是迄今发现唐之前结构最清楚的建筑资料。河西走廊从汉武帝拓边以来归属中央政权已经四、五百年,河西走廊魏晋汉式建筑已与内地无别。如果地埂坡墓地主人系汉末从中原迁居于此,那么同样也反映的是当时中原建筑的基本情况。地埂坡M1是其所在墓地中建筑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为前室带双耳室的前后室墓,在前室内部雕出了比较完整的建筑内部形象。两榀大叉手梁架前部搭在梭柱上,后部搭在有壁柱的后墙上。壁柱的存在,表示了夯土墙的存在。大叉手下部平梁的后端架于壁柱头部的斗栱之上,之上又有蜀柱上达后墙沿口,这说明大叉手的平梁直接插入了后墙之中。后墙沿口凸出,说明夯土墙的沿口也以木壁板围护,与壁柱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围护系统。大叉手中部对称施顺脊方向斗栱,上承中平枋(槫),上面再承椽[29](图九)。可能是受制于地下土雕的形式,叉手上部与屋脊的关系没有充分表达,但屋脊下部平直,表明更可能是脊枋。只在墓室前部的叉手之下有立柱而后部没有,可能采用了减柱的形式。还有一种可能性,室内大叉手下本不需立柱,之所以立柱是因为前檐墙不是像后墙一样的夯土墙。大叉手下的这根立柱可能在前檐墙里面,也可能表示前檐墙之所在。可以看出,平梁靠立柱这边的端口下部是平齐的,这说明平梁只延伸到这个位置,因此可以将此理解为平梁伸出前檐墙的部分。平梁端口上部有一栱,这一顺脊方向的斗栱也不是无意的,不仅位置上与后檐墙对称,而且承托起下平枋(槫)。下平枋(槫)内外椽子的角度略有不同,外侧椽子的倾斜角要略小,这大概不仅是为了区别前廊与室内,而且是表示廊檐比屋面的坡度平缓,可以纳入更多光线[30]。房屋前后两坡不对称的情况在汉代祠堂和建筑模型中为数不少,祠堂如孝堂山石祠、建筑模型如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墓出土灰陶房[31]。中兆村M100第二过洞上方绘塑一体的建筑也属于这个类型。平梁端头伸入到夯土墙内及壁柱的做法,天王地神冢与地埂坡M1的十分相似。更有甚者,天王地神冢前室大叉手顶部与屋脊的交接方式非常清晰,甚至可以反过来用来想象地埂坡M1的情况,也说明朱鲔石室、冬寿墓厨房山墙叉手上部可能也都是这种处理方式。

图九 地埂坡M1前室北壁上部结构
北魏平城时代的建筑可以明确看出与十六国时期的联系。东汉末年以后,游牧文明在大同地区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直至北魏定都大同。北魏定都平城,人口主要从外地迁移而来,河北和辽西、关中都是主要来源地。因此,在大同发现的与河北和辽西、关中相似的建筑因素,就可以考虑可能与这些地区有关,恰好大同平城时代建筑中都有与上述两个地区相似乃至相同的因素。云冈石窟中的建筑因素极为丰富,其中著名的第9、10窟前后室过道前部,即前室后门的形式几乎与中兆村M100、彭阳新集墓的完全一致(图一〇)。大同地区气候比关中寒冷,对夯土墙建筑的需要更迫切,435年的大同沙岭7号墓壁画建筑从窗户的表现形式看应该是夯土建筑[32],文献记载相当于南齐时期的北魏太子妃还居住在估计就是夯土建筑的“土屋”中[33]。因此,大同地区北魏时期既有可能从别处吸收,也有可能独立发展夯土建筑技术。但是,第9、10窟前室后门与中兆村M100、彭阳新集墓土雕建筑的门太相似了,彭阳在北魏重镇高平附近,关中是北魏掠取人口和资源的重点地区,所以,关中地区建筑影响到平城的可能性还是值得考虑的。相比而言,河北和辽西地区与平城在建筑上的联系要更为明确。半圆形人面纹瓦饰和“富贵万岁”铭瓦当在十六国时期几乎仅见于河北和辽西,可谓具有地域标志性的建筑构件,但在北魏平城有较多发现。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出土有6件半圆形人面纹瓦饰;13件文字瓦当中,“富贵万岁”铭瓦当有7件[34]。半圆形人面纹瓦饰、“富贵万岁”铭瓦当在大同西册田北魏制陶遗址都有发现。文字铭瓦当中,“富贵万岁”铭瓦当居多。西册田北魏制陶遗址还发现了图案有所变化的半圆形兽面纹瓦饰,体现了进一步的发展[35]。“富贵万岁”铭瓦当还见于大同操场城第二号建筑遗址、云冈第3窟遗址、大同方山北魏思远寺院遗址、大同方山永固陵南部的“白佛台”[36](图一一)。北魏与后燕、北燕关系非同寻常,北魏从河北辽西掠取的人口和资源可能要超过关中,这些建筑构件可视为见证之物。

图一〇 云冈第9窟前后室过道门口

图一一 大同操场城遗址出土瓦件
至于高句丽建筑因素,平城并没有可以肯定的发现,但如上文所示,北魏平城时代房屋类建筑的总体面貌与十六国时期相似,那么自然也与高句丽有很多相似之处。云冈第9、10窟前后室过道中虽然没有大立柱,但不表示现实建筑中不存在,高句丽双楹冢的意义不可忽视。
综上所言,对十六国时期房屋类建筑遗存的检验表明,可能由于气候寒冷和十六国北魏政权建立者多为北方民族,夯土承重墙似乎更得到强调,建筑外形整体上变得更加拙重。由于分裂,十六国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地域特征;北魏统一北中国,又将不同地域特征汇聚到了首都平城。从魏晋经十六国到北魏平城时代,建筑方式和建筑技术总体上是相似的,可以说处于同一个阶段。土木混筑的房屋类建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要到北魏洛阳时代,需另文讨论。
附记:就彭阳新集和西安中兆村M100建筑屋檐承重方式问题,清华大学建筑学方向任羽楠博士多次拨冗与笔者讨论,特此致谢!
[1]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30.
[2]同[1]:232-242.
[3]a.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内部材料,2020.b.王艳朋.陕西西安中兆村十六国墓[J].艺术品鉴,2021(3):81-83.
[4]还有一些零星的相关发现。如在汉长安城东北部的十六国至北朝长安城宫城遗址中出土有十六国时期的砖、瓦、瓦当,其中有在云纹与边轮之间装饰菱形网格纹瓦当,被认为属于十六国时期特点,这个瓦当的直径14.8 厘米,倒是与汉代正常瓦当相近;1964 年西安雁塔区纪阳村出土始光元年一佛二菩萨造像碑,上有庑殿顶佛殿。参见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J].考古,2008(9):25-35.b.刘振东.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 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M]//2009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32-135.c.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3.
[5]同[1]:234.傅熹年先生将云冈第九、十窟前后室过门形制描述为:“门额两端伸出立颊外,如古代衡门的形式。但门框自壁面凹入,后壁沿门框四周抹成斜面,所表现的是在厚墙中装木门的形象。”中兆村墓土雕建筑门的形制与云冈第九、十窟的基本相同,所以将傅先生的文字直接移引于此。
[6]这是笔者所见唯一的表现山面结构的十六国资料,非常珍贵。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安县北朝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5):57-62.
[8]四根立柱特别细,不太合理。
[9]这种简单的支撑方法可能是当时最常见的,但限于壁画或建筑模型体量的限制,没有得到充分表现。汉代建筑模型明器发现较多,有些有助于理解,如《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图版七的仓楼二层檐下有二栱从墙壁伸出、直接承托屋檐,图版一九仓楼一层两边各有一柱,柱头也有从墙壁悬挑而出托举屋檐的斗栱。
[10]可参考年代较晚的大同北魏宋绍祖墓房形石椁正面。
[11]汉代瓦当直径通常为14 ~16 厘米。杨焕成.中国古建筑时代特征举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23.
[12]大同考古所侯晓刚先生告知大同一座北魏墓也发现土雕建筑,资料未发表,详情不得而知。
[13]这种莲花纹瓦当与南北朝常见的莲花纹瓦当不太一样,与辽西地区的多叶纹瓦当也不太一样。从半圆形人面瓦饰、“富贵万岁”铭瓦当与辽西地区关系密切来看,可能多叶形瓦当有所变化而成邺城的莲花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之名不是太合适,容易让人联想到南北朝时期,但《邺城文物菁华》等著作中都使用此名称,故本文相从而不改。
[14]龙腾苑遗址也很重要,但未见到详细材料。
[15]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C]//辽宁考古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98-224.
[1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2.
[17]a.田立坤,万雄飞,白宝玉.朝阳故城考古记略[C]//边疆考古研究(第6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01-311.b.万雄飞.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及其建筑特点[C]//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64-82.
[18]为不引起混乱,此处均因袭发掘报告的描述,但此描述有问题,田立坤做了说明和修正,详见田立坤.金岭寺建筑遗址为“廆庙”说[C]//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461-477.
[19]发掘报告没有提供瓦件的尺寸,此尺寸据清野孝之等.金岭寺遗址出土瓦件的研究[C]//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154-203.
[20]同[18].
[21]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12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95-313.
[22]李新全.三燕瓦当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6(1):12-15.
[23]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第101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6:3196.
[24]房玄龄,等.晋书:慕容熙载记(第124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05,3106.
[25]韩国日本学者对高句丽建筑研究持续深入,中国学者钟晓青、张明皓也有涉及。如a.钟晓青.集安高句丽早期壁画墓建筑因素探讨[J].美术大观,2016(2).b.张明皓.浅析高句丽壁画古坟中的建筑形象[J].北方文物,2010(3).
[26]或许也可能类似后代勾连搭顶的房屋;也可能是分前后进的大建筑,如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第四号建筑遗址,其前后进之间有3 米厚的承重隔墙,在前后进隔墙位置至今仍保留有几个大柱础。
[27]同[4].
[28]汉长安城有一件半圆形人面纹瓦饰,但背景资料不明,不能肯定是否属于西汉或十六国。许昌出土一件,被认为属于曹魏时期。朝鲜定林寺出土一件。这些零星的著录,无法与河北辽西的发现相比。关于半圆形人面纹瓦饰的讨论,可参见王飞峰.汉唐时期东亚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纹瓦为中心[C]//边疆考古研究(第7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14-234.
[29]地埂坡墓葬资料承原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王辉先生惠示,谨致谢忱!
[30]王子奇有不同的复原方案,见王子奇.甘肃高台地埂坡一号晋墓仿木结构初探[J].四川文物,2017(6):40-45.
[31]刘冠对屋顶前后两坡不对称情况有集中讨论,见刘冠.汉代建筑图像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502-514.
[3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4-24.
[33]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第57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2:984.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考古系.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5(4).
[35]王银田.山西大同北魏西册田制陶遗址调查简报[J].文物,2010(5):27-37.
[36]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操场城北魏二号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6(4):4-25.b.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第3 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4(6):65-88.c.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J].文物,2007(4).d.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大同近傍调查记(第16 卷)[M].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12.据云还见于大同北魏明堂遗址,但发掘简报中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