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性灵世界
郝鹏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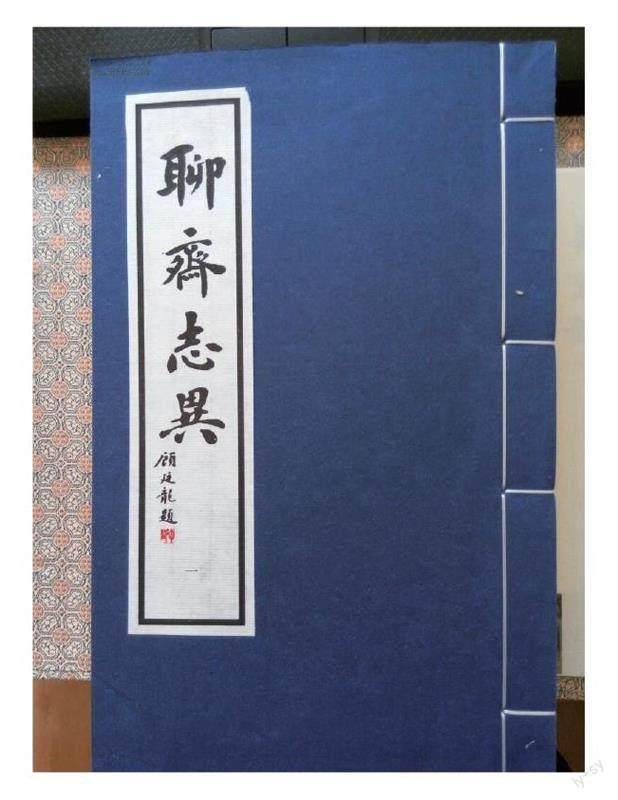


万物皆有性与灵,乃自然之禀性。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选择狐鬼花妖的叙述方式,把自己那些因现实世界的冷酷和黑暗而遭到落空的热情和理想寄予到幻境中去,融自我性、灵于万物。在成人欲望下关照儿童生命,在现实束缚下追求异世的不羁。在性与灵的多重交叠下,尽情抒发其抑郁孤愤,以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与升华。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将自我之性灵融万物之性灵。家境的贫寒窘迫与科场的半生蹉跎,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种种无处可发的情性便在现实的冲击之间迸发出来,缠绕于现实与幻境这两重世界中,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灵寄托与向往。贯穿于始终的实则是蒲松龄的性与灵,他在性与灵的统摄之下剖析生命。
“性灵”范畴之界定
《聊斋志异》里处处闪现着性与灵的跳动,他用性灵织造了整个聊斋世界。何为“性灵”呢?首先对其加以简单界定,明确蒲松龄的性灵世界。
在《辞源》里“性灵”释为“性情。泛指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我们心灵的活动,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真情感触。作为“性灵”的重要诗评家,袁枚强调“性灵”的核心就是要求在创作中直接抒发心灵感受,表达真情实感。如其所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是发自内心的最自然深切的感受,它的自然流露是主体深受触动而抒发出来的,是作品具有感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正如蒲松龄笔下的狐鬼花妖、风云水石等万物众生,都带有独属于自身的一种“性”,同时万物众生存在于聊斋世界中又均仰赖于蒲松龄心中之灵气。司马光集注《太玄·中》“巅灵”为“灵者,心之主,所以营为万务,物之所赖以生者也”,蒲松龄便是一切“灵”之源头—由现实的无可奈何、生活的不尽如人意所激发的一切幻想与想象,投射到万事万物上,于是乎有了聊斋里的性灵世界。
欲望裹挟下的性灵生命
《聊斋》中的狐鬼花妖与书生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儿童形象常被忽视。但儿童作为烂漫的代表,他们身上有着未经世俗浸染的天然性灵,这是他物无可比拟的。不过,儿童特有的这种天然性灵通常被成年人周旋的各种生存、名利、交际场中的欲望所裹挟、吞噬。这种欲望在蒲松龄的笔下集中体现为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矛盾。
儿童与成年人欲望的矛盾
《聊斋》中,有不少关于儿童与成年人“欲望”的冲突。其中,儿童是被忽视的一方,既无独立地位,也没有自尊体验。封建家长或冷酷无情、或贪淫暴戾、或以儿童为牟利工具。在这种欲望支使下的兒童是顺从还是奋起反抗,决定了儿童与成年人的矛盾是和解还是爆发,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
《促织》是儿童与成年人“欲望”的和解。这是一则因父与子、家庭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一出悲剧。矛盾开始是成名之子因贪玩,于无意间将成名辛苦捉来的救命蟋蟀弄死了。成名之子惊惧不已,而父母非但没有抚慰其儿,反倒“怒索儿”。小儿绝望之下跳井自杀,父母虽伤心悲痛,但见“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这是矛盾最高潮。
这出悲剧的根源实是荒淫无道的上层统治者。即便之后成名之子化作颇有灵性的促织,试遍天下蟋蟀“无出其右者”,让成名一家“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但这仍旧是一个悲剧事件。这一悲剧,从其父之名“成名”就能预见了。成名之成名,是其小儿魂化促织为代价的,实乃成年人欲望下的牺牲品,皇帝一个区区的爱好竟要以牺牲像成名之子这样无数个活泼鲜润的生命来取悦,讽刺至极。
《鸦头》则体现了儿童与成年人“欲望”的激烈矛盾。鸦头和鸨母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鸨母贪财重利,当“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女执不愿”时,便鞭打鸦头。但性格刚烈的鸦头并未屈从,她稳定从容策划出逃。虽然后来被鸨母寻得,遭到“横施楚掠”,甚至在“幽室之中,暗无天日,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但鸦头仍“矢死不二”,没有屈服于鸨母的淫威之下,其坚贞不屈的精神或许是其天然性灵之驱使。她的不断反抗,最终使她获得圆满的结局。
儿童与成年人“欲望”之间难以消解的矛盾,往往加倍反击到儿童身上。这种欲望吞噬了儿童的天然性灵,甚至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才求得所谓“圆满”。究其原因,是成年人的复杂心性与儿童纯真无邪之间的差异。但蒲松龄终究还是给了这些小儿一个好的结局,他心里希望小儿保持纯洁心性。
儿童与重组家庭的矛盾
继母与继子的关系向来复杂。有童话情节中的毒苹果,也有继母家庭迫害舜的历史事实,这都关涉到继母与继子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是继母的排挤私欲和继子非己出之间的矛盾形成的。然而蒲松龄笔下此类继母形象不是很多,缘故大概是蒲松龄更愿意用浪漫的方式表达心之性灵。
在《吕无病》中,阿坚与继母王氏的矛盾最为激烈。继母王氏恶毒狠戾,对啼哭的阿坚弃之不顾,甚至施以毒手,阿坚惊悸过度,听到其声音便受惊倒地气绝身亡。妾室吕无病大哭,她还怒道:“贱婢丑态!岂以儿死胁我耶!无论孙家襁褓物;即杀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王氏还下令将阿坚抛尸野外,心肠歹毒至极。阿坚非其亲生,故能心狠如此。究其根本,是受封建社会血缘至上、嫡长子继承制观念的影响,为了个人地位与欲望,会有更多的阿坚遭受迫害与虐待。不过文中的阿坚还是幸运的,最终在吕无病的救助下得以存活。
《聊斋》世界里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矛盾或缓和或激烈,但最后儿童都获得了相对圆满的结局。原因在于蒲松龄向来是偏向儿童,爱怜儿童的,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充满着同情。因此,儿童在与成年人的博弈中,在成年人欲望世界的裹挟下,总有能力自救,抑或得到他人的帮助,并最终获得美满结局。这不仅是蒲松龄反抗恶势力、保护性灵生命的愿望,亦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挣脱束缚下的性灵生命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生活的困顿、科场的挣扎竞争、社会现实的冲击,都使有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性格的蒲松龄展开想象的翅膀,挣脱现实束缚。
困境下看众生相
蒲松龄眼中的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世界是他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但同样是下层百姓的生存困境。这种双重困境是他创作灵感的根本源泉,即“情从心出”。
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但从其祖父那一代开始家道中落。家境的贫寒给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走科举之路成了他的信仰和执念,影响着他的性格并伴随了其一生,成为蒲松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聊斋世界中便是贫寒书生与科举之间的纠葛缠绵,一方面要依靠科举之路飞黄腾达,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却又久困科场,无可作为。这是其“情从心出”之一。
因而《聊斋》里故事主人公大多是家境贫寒的穷书生,这一身份也使他们在婚姻选择上处于被轻视的位置,求而不得的无奈与辛酸或许只有蒲松龄才能真切体会。如,《青梅》里“家窭贫,无恒产,税居王第”的张书生;《姊妹易嫁》中张家大女儿因嫌毛公“家素微”而甚薄毛家;还有《连城》中的乔生。其实相比生计窘迫给蒲松龄带来的困扰,科场上的怀才不遇更让他耿耿于怀,这使得他内心十分渴望有一二知己陪伴。在《连城》里,乔生和连城之间有着浓厚情谊,连城对乔生有知遇之情。“逢人辄称道,又遣媪矫父命,赠金以助灯火”,又告诉乔生“以彼才华,当不久落”。此外,《连城》篇也是蒲松龄对其岳父和妻子当初排除阻碍答应婚事这一份恩情的感激写照。
科举之路上的潦倒窘迫,使蒲松龄从信心满满逐渐地对科考产生不满情绪。但另一方面他仍旧热衷于功名,孜孜矻矻的钻研八股,拜倒在科举面前。如《叶生》里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落榜后“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叶生已经被封建科举制度所吞噬,这是对科举制度下士人灵魂扭曲的极尽展示。这是“情从心出”之二。
除了身世之感的寄托外,蒲松龄对社会的观察也极为细致,这是其“情从心出”之三。蒲松龄在外出谋生做幕宾期间,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也对百姓生活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状况有了切身的体会。于是有了无情地揭示、批判。如《野狗》篇里乡民李化龙所见的“伏啮人首,遍吸其脑”的野狗其实是在反映于七之乱时统治阶级乱杀无辜的残暴血腥;《红玉》里冯相如“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官府成了权势者的庇护伞,作者借异史氏之口激愤地说到“官宰悠悠,竖人毛发”,表达了对当权者黑暗统治的控诉;《狐联》里所谓名士却对不上狐狸的对子,讽刺所谓名士的迂腐和不学;《道士》则是一篇讽刺市侩的语言性质的作品,在此嘲讽的是那些贪婪好色之徒,等等。
现实与幻想之间强大的落差感促使蒲松龄将其“赤子之心”附在茫茫的生命体上,在自我生命和他人生命的历程里展示性灵,在无尽的困境里审视世界,也审视着自己。可以说聊斋世界中的生命群体,既有他失意人生的反映,也有他寻求慰藉的美好希冀。
幻境中寻求慰藉
蒲松龄现实中的生活不尽如人意,这使其不得不在幻想中寻求慰藉。如上文阐释“灵者,心之主,所以营为万务,物之所赖以生者也。”在幻化的圆满世界中,有蒸蒸日上的生活,有谈笑风生的知己,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种种都是蒲松龄潜在的“性”的体现,是在现实困境下对于美善本性的向往与追求。
如《鲁公女》中鲁公女被张于旦的痴情打动,就以鬼的身份与张于旦相恋,他们二人历经坎坷再世重为情侣。何守奇说:“岂情之所钟,固不以生死隔耶?”他们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是蒲松龄对纯美爱情的赞美;《青梅》里婢女青梅和小姐阿喜自主择婿,嫁给了穷书生,最终也获得了美满的生活,这实际上是蒲松龄为穷书生在婚姻上打抱不平;《刘秀才》里沂令担忧县区的蝗灾,听从柳神的指点“即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驴不令去”祈求蝗神手下留情,忧民爱民的沂令实则是蒲松龄对统治阶层的一种期望;《庙鬼》里的王启后面对恶鬼幻化的妇人却不为所动,始终坚守内心,也正是他诚实淳朴的人格救了他;《丁前溪》里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然一饭之德不忘,丁其有焉。”丁前溪与杨姓主人家相互帮扶,他们把施恩与报恩展示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丁前溪和杨姓主人这类游侠义士的赞美……不管故事的主题是什么,蒲松龄其实想向世人传达一些准则,以仁慈宽广的胸怀对待万物。
不论是生而死、死又生的鲁公女,还是心系百姓的沂令,抑或是有着淳朴人格的王启后等,都表现了对人灵魂深处的美的发掘,代表着“灵”本身具有的善和美的品质,体现着蒲松龄对生命的热情与渴望,是对蒲松龄个体性灵世界的映射。可见,聊斋世界里美好与圆满的表达实际仰赖于蒲松龄心中的性灵,将他心中积攒的抑郁孤愤、想倾诉却又无法言说的孤独苦闷抒发出来,在幻境中寻求着慰藉。
超越与升华
人生将近过了大半,蒲松龄深知现实里的这些困境他始终无法破解。正如其在结束四十多年的教书生涯后写的一首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对自己追求科举的一生作了沉痛的总结。或许他会给自己自我安慰,然而蒲松龄浪漫的性格使其更易于用浪漫的笔调将情感倾注在书页上。这情感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写人鬼交往,写人狐恋爱,写自然生物幻化后的真挚淳朴。这些浪漫情感的表达实则暗示了他自己心态上的一些变化。聊斋里有多篇写到书生的人格性情,其实这也是蒲松龄在现实和幻境交叠下的自我净化、自我升华,更是其性灵世界的深切呈现。
《王成》篇开始就点明了王成“性最懒”的性格,但随着故事发展,又展示出了其“王虽故贫,然性介,遽出授之”的品格。他有但明伦所说的“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的人格性情,是狷介之士。这是蒲松龄最为欣赏的,因此蒲松龄又借异史氏之口说:“不知一贫彻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弃之而终怜之也。”《陆判》中朱尔旦死后“三数日辄一来,时而留宿缱绻,家中事就便经纪”,以致其子“竟不知无父也”。这种与家人团圆、子业有成的美满结局是蒲松龄的有意安排,不难说其中包含着蒲松龄对美好安逸的世俗生活的向往。蒲松齡释放了心中的抑郁孤愤,这些书生的人格性情也是蒲松龄自己内心的一定反照。他以真性情、真性灵实现困境和幻境的相互转换,达成现实世界与幽冥异域的交叠。可以说在这里他的一切情绪都得以宣泄和平衡,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解脱,对生命的完满升华。
万物所生仰赖性灵,那么何为性灵?最好的回答或许就是蒲松龄本人。他完美地将真情与个性融于自我的性灵之中。只是随心所欲,浮白载笔,便以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郁的故事性抒写了一个异类有情、幻境浪漫的聊斋世界,这里浸满了蒲松龄的真情和性灵。在这里,蒲松龄用异世的不羁抗争着现世的束缚,也用尖锐的言语鞭挞欲望之下人心的可怕。他在自身的困境中审视着芸芸众生,在自我营造的幻境中寻求慰藉。这是性与灵的交织、碰撞,也是对自我生命的超越与升华。他将本我之性灵灌注在聊斋世界里,释放真性情,诠释着不羁的人生。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