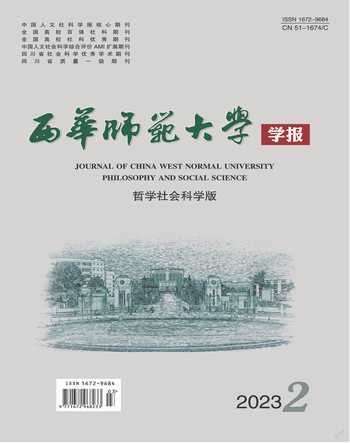“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徐杰
摘 要: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驗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
关键词:语境诗学;反思性;默会性;具体性;后理论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3)02-0093-07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存在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挑选一个要素或范畴作为理论的本体,于是便出现“作品中心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等。有中心必然有边缘,新的范畴成为中心的前提便是对“前中心范畴”的批判,也有了“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等“死亡现象”。西方文论从根源上受到古希腊哲学实体论倾向的影响,比如将世界本源归于“水”“火”“原子”等可见、可说或可触的对象,所以文论中不自觉携带了实体论中的静态性和要素性思维。中国哲学则用不可见、不可说和不可触的“道”“无”“一”等范畴作为世界本原,中国诗学也对动态性、关系性和不可言说性更为注重,比如“味”“气”“象”(区别于实物的“像”)“意境”等。面对西方文论的问题,笔者先后在系列论文①之中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主张整体性、动态性、关系性的诗学理论,即“语境诗学”。语境诗学反对将文学经验与日常话语、人和世界、身体与环境等进行区分和割裂,主张有机的、动态的、连续性的和具象化的诗学观念,强调审美对象的生命性、整体性、生成性和非语言性;它认为文学的存在本质上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综合、语言世界与非语言世界的交织、显性与隐性的意识和情感的融合;它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它重构着当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论题,如情境性、表演性、非语言性、不在场性、气氛、活态、多媒介性、事性、关系等,消解文学审美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文学文本论与世界论之间的争论。当我们完成语境诗学的内部理论体系构建之后,不禁会思考一个宏观性问题:语境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理论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品性?我们试图探讨语境诗学与康德批判哲学、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以及后理论诗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思考其在当下话语体系中的知识谱系和理论品格。理论定位为语境诗学的出场提供了有力的哲学话语支撑。
一、语境诗学之于批判哲学的“反思性”
文学理论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文学知识和文学命题之间的逻辑推演而形成的文学理论体系,以此为基点规范文学批评和实践,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此种文学理论研究路数背后是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重“理性”和永恒不变的真理,轻感性经验。这一种源自古希腊时代的思辨形而上学,世界被古希腊哲学家门分为现象与本质:现象是感官感知的、变动不居的,当然也是非真实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因为它才是永恒的[1]。思辨型形而上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走向其反面。经验主义强调具体个人经验和感官体验,认为理论必须是通过具体个人感官体验和经验归纳产生。这便滋生出第二种文学理论形态。在稳定的经验材料基础上,以实证方式抽象和概括出的经验性文学理论,如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其哲学基础根源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以及后来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知识只来自感觉经验的归纳,而不必依赖“永恒真理”。这种哲学思维特别贴近文艺理论,因为文艺理论的对象必须是感性和体验的。但是问题出现了,文学经验太过繁复和混杂,并非对文学的感觉经验都是具有个人性和偶然性的。以这样的文学经验作为起点并不能建立作为普遍性的文学知识。那么怎样可以规避以上两种文学理论的弊端,结合它们的长处呢?这种思考产生了第三种文学理论形态。以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出发点的“反思型”文学理论,即对理论的理论。一方面,反思型文学理论具有第一种文学理论本体论方式的特点,即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另一方面又不是将文学理论作为“僵硬的规则”而盲从,而是具有阐释学品格的“前见”性质,同时它有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2]。这种文学理论根源于王元骧先生对康德哲学的审视。他认为康德批判哲学对经验派和理性派的统一,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可以作为我们思考文学理论品性的基础。康德提出先验论解决了唯经验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各自的理论盲区:经验必须经由先验的知性形式的“规约”和整合,也就是不存在离开知性的感性,也不存在离开感性的知性。康德的批判哲学对思考文学理论的理论属性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语境诗学属于“反思型”文学理论。语境诗学的提出,宗旨并非仅仅是对文学批评实践进行指导,其理论品性不局限于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进行解释的“工具性”;而在于对文学理论本身的认识和反思(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它思考文学理论体系之中并未被前人所关注的“语境”的维度。透过“语境”范畴,我们到底能在文学理论之中发现什么新的现象,这又对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哪些新的思考?当语境诗学提出后,它反对了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改变了文学理论的什么?语境诗学自我的定位,是试图创造一种可以包打天下的理论,还是在原有文艺理论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完善?
语境诗学作为一种理论归纳和抽象,必不可少带有一种宏大性、体系性、抽象性和逻辑性。在文学理论研究之中,终结文学理论的呼声近年较高,其重要的依据是文学理论是以取消文学为前提的理论,文学理论无法指导文学批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学批评主要强调的是文学理论的工具性,而“文学理论”主张的是文学理论的反思性。文学批评指的是具有较高文学审美素养的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解读[3]13。对文学的反思,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具体的文学经验和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实践作出预设、批评和反思,即“批评的批评”抑或“元批评”[3]12-13。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理论从词源学上本身就与文学实践有着距离。威廉斯研究了“理论”这个英文词汇的历史意义演变,发现它主要是指“俯察直观到的流动外表背后稳定不变之真相的方式。因而,理论与‘存在、同一性和可认知性优越于‘生成的特权相联系”与“实践”经历了从明显不同到形成对立的过程[4]486。同样地,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理论世界是超越于日常生活实践和自然世界观察的,也即属于超验世界[5]31-33。
语境诗学是作为批判哲学的反思性而存在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认为本质并非从感觉经验中得来的,因为他坚信一切事物从一个本原生成,但是“本原”本身不是生成的[6]。正如神学中的思辨逻辑一样,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神造的,神不可能是由他者创造,它是自为地存在的。柏拉图眼中的“本原”或者理式也是自为地存在的,永恒存在的。面对这样的将本质抽象化和静态性的思辨倾向,康德提出先验哲学予以反驳。他认为主体先验地具有一系列“先天的知性概念”,经验必须经过先验范畴这些“有色眼镜”过滤、分解和组合,从而才能得到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可见康德的“先天的知性概念”,不是“僵化、凝固、绝对不变的供推论的现成的结论,而只不过是供反思的原则:目的只在于为了引导人们去探寻真理,发现真理,如同黑格尔说的:‘理性只是真理的规则,而不是真理的工具,理性只能提供知识批判而不能提供关于无限者的理论。”[6]。因而,文学理论除了工具性的维度,还有“批判哲学”式的反思前提或者“反思的判断”。
因而,语境诗学并非首要地去印证理论自身具有多大的阐释力,能够对文学作品有多大的解剖力。相反,它为文学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是一种让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文学语境也不是文学理论建构的目的,它只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认识,它只是使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一个理论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方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7],所以说,语境诗学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文学理论反思的理论支点和理论前提,让我们意识到“语境”在所有文学活动之中存在却被忽视的状态。同时,“语境”在无意识之中参与着文学意义的生成,甚至整个文学理论的建构。因而,文学语境论是作为一种“反思型”的理论而存在的。反思性的理论是怎样的理论呢?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知识进行语境化和问题化,追问其生成的场域、目的和知识逻辑等等[8]。语境诗学建构的重要价值维度就在于,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眼光,带来新的评判尺度的标准,让我们有了看待文学理论体系的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文学语境论作为反思性的理论,也就是具有了伊瑟尔所说的“建构性”的理论框架;它是“加诸于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体系以对其进行认知”,而非操作性的,不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的一套网络结构”[9]。
二、语境诗学之于后批判哲学的“默会性”
我们并非生活在自然状态的世界之中,而是处在一种被文化浸润和洗礼之后的“伪自然”世界之中。人类通过语言将物理世界转换为符号意义,再将意义世界建构成自然状态[10]。我以为,我们已经通过符号或者语言将物理的世界轉化为“意义”环绕的文化世界,这种“意义世界”反过来把物理世界的非自然化现象逐渐变成自然现象,即巴尔特的“伪自然”现象。纯粹的物理世界是无所谓“语境”现象的。语境只针对将对象语言化之后的意义生成或生产过程而言。“伪自然”是意义被语言生产出来之后,反过来赋予对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之中,意义是不断增值和裂变的,而变化的依托就是参与“伪自然”形成的所有因素的动态活动带来的。这一过程不知不觉就形成了,或者说与意义相伴而生,互相构成了。巴尔特提及的“伪自然”现象其实就是对象“意义化”之后所形成的语境,它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着。
何谓默会知识?经过长期训练掌握复杂游泳技巧的人却说不清自己如何飘浮起来的。这种现象存在于普通人骑自行车、医生做手术和品酒师品酒等无数“技能”现象之中。“技能性行为的目标是通过遵循一套规则而实现的,但遵循这套规则的人却并不理解这套规则”[11]58-60。现实生活之中,大量需要通过技能才能完成的事情,包含着能被言述和传授的内容,更多地还有大量未能被言述的知识。这些知识即默会知识,它只能通过师徒制的亲授才能完成,也即是波兰尼所说的“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言说的多”。他从“附属意识”和“焦点意识”的角度来来论证。当我们用锤子钉钉子时,意识可以关注钉子,也可以关注锤子。但是锤击的一瞬间,我们觉知到的不是锤柄震动手掌,更多的是锤头击中钉子。前者就是“附属意识”,后者是“焦点意识”。人的“感觉”本身就像“锤子”,常常是作为注意力的工具,我们极少意识到“意识”本身。同样地,我们使用语言,语言通常具有透明性。人们少有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存在,因为我们是以附带方式觉知语言的。文学阅读中,在获取精彩的故事、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思想之后,我们似乎同样会因为“得鱼忘筌”而忽视文学语言本身。但是,文学自身具有凸显语言的冲动,即什克洛夫斯基主张的“让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的陌生化天性。故而,文学独特性就较为明显了:文学语言表达的对象和语言本身都作为“焦点”被交替地觉知着,而文学语境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属知觉”存在着。“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细节之上,我们的行为就会崩溃。我能可以把这样的行为描述为在逻辑上不可言传,因为我们可以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细节所作的详细说明会在逻辑上和该行为或语境所暗含的东西相冲突”[11]66,按照波兰尼的说法,“默会知识”相对于“焦点知识”就是一种“语境”和“对象”的关系。
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之中言说和未言说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是以“焦点觉知”的方式存在于文学活动之中,而文学语境则是以“附属知觉”的方式存在的。在以文字作为承载物的印刷文学中,文学语境表征为字里行间的文本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以语音作为承载主体的口头文学,文学语境更多地呈现为极具现场感的情景语境之中。“一组落入我们的附属知觉中的细节如果全部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我们可能会最终把它们全部忘记,并无法回忆。”[11]73所以,文学语境作为附属知觉中的细节具有不可言传性,文学对象和文学语言作为焦点知觉可以被言述和传授的。无论是哪种语境,在文学被感知和阅读过程之中都是以隐在的、默会的和非可言说的方式存在着的。波兰尼认为,“语言层面和理性层面的知识需要以非语言、非理性的默会知识或者意会知识作为基础”[11]6。文学知识的重心和基石不是可以言述的东西,而是不可以言述的语境维度的东西。最为突出的是文学作为一种技能,即“写作”的默会性。如果我们视文学为动词(“写作”和“技能”)而非名词“文本和作品”,文学非可言述的默会性立马表现出来。文学的“写作”不可教、“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等就变为可理解的了。文学写作作为一种“技能”并非可以通过言语和理性传授出来的。如果可以的话,作家的孩子必然很容易成为作家,但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作家将所谓的“秘笈”像传授知识那样传授给自己孩子,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秘笈”是一种默会知识,不可言传。
文学语境的默会性使得我们逐渐将语境思维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通过感觉去感知对象而不会意识到“感觉”自身一样,我们无时不在以“语境”思维理解着文学却忽视它的存在。就像波兰尼所说,当我们用“工具”行事时,以附属知觉方式隐藏的工具“必然存在于我们这一边,成了我们自己即操作主体的一部分。我们把自己倾注于它们之中,把它们吸收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寄居于它们之中从而在存在上接纳了它们”[11]67-70。文学语境思维“内居”主体之中,从而将文学的所有“环境”语境化。文学语境并不是文学世界,而是一种“生活世界”,因而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两种:一种将世界作为主体的对象,这种思维方式的前提就是将认识世界的主体与整体世界切割开来,然后才有所谓的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认识行为,即在世界之外超然地思考世界。但是,问题来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无外性”,即万事万物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包括人都不可以在世界之外来面对世界,更不用说言说和思考世界。“世界之为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顽固地拒绝进入人们的意识框定,拒绝被意识对象化,拒绝成为意识的中心。世界总是化各种事物入其内,纳各种事物进其中,但是世界本身恰恰不被任何事物所划入、所纳入”[12]46,于是引出第二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在之中”(海德格尔),它并非意味着空间上的逻辑先后寓居关系,即先存在一个对象,再包含一个对象;相反是一种“融身在世界之中”的关系[13]。这种思考方式认为主体不是面对的一个客观、静止和超然的“世界”存在。相反,主体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主体对世界的一举一动甚至思考,都改变着世界本身,因为主体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不存在一个离开主体而存在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是逻辑意义上的世界,而是内在了主体的“生活世界”。我们常常是以“直觉”和“常识”的方式融身于“生活世界”,以至于它的存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前理论”状态[5]37。
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应到文学理论之中来,我们发现,文学“世界”说是秉承传统的“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世界的模仿,世界是文学的意义之源。这种思维将“世界”理解为一种外在于文学的抽象的自在之物或者客观意义上的“永恒实体”。但是,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的,因而文学的任务“并不是展示一个外部对象世界”,而是“呈现使人类现实生活在其中得以展开的‘语境本身”[14]90。文学语境是一种“生活世界”状态,就像迪莱所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與语境比较接近,都显得“理所当然”[15]20。或者说“生活世界”以一种“底层性”托显着语境,“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具有不同的表现条件,不能通过意向而表现出来;它是一种深层的非主题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5]77。作为一种“生活世界”,摆脱了主体外在于世界,并对世界进行概念和思考的方式,因为文学永远是“在语境之中”,就像“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中的存在”一样。脱离开生活所理解的“存在”并不存在,生活世界才是人类的根基。这让文学语境成为前科学的、前概念的和前理论的“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16]。这种直观性、直觉性、前逻辑性,与后批判哲学所强调的“默会性”有着同样的理论思考点。其一,波兰尼强调一种与海德格尔相似的“内居”(即前面所说的“在之中”),只不过,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界之中”,而波兰尼强调“在身体之中”。“默会认知理论坚持内居与身体使我们能从内部出发,注意到外部事物”[17]156。正如波兰尼所说,“内居就是在世。每一个默会认识的行动,都会改变我们的存在,限定我们对世界的介入,给我们对世界的参与以新的方向。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其他名目下已经探讨了这些过程,现在,我们必须用更为具体的默会认识结构,来重新诠释这些观察”[18]。其二,默会性强调人类认知之中“未被表达的”默会知识,这种知识不能被“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因而默会知识具有非语言性和逻辑性,这使得知识默会性理论的哲学思考与“生活世界”建立的思维是一致的。因而,文学以“在之中”的方式与文学语境同时存在,这让文学语境成为“生活世界”;又因为“生活世界”理论和后批判哲学都强调“去逻辑化”和非分析性,故而语境诗学进而具有与后批判哲学相近的理论品格。
哲学上对“在之中”的思维模式带来我们对文学和文学语境关系的全新思考。非语境的文学思考,是文学的非真实的存在,是文学的单维度。文学天生就与文学语境是共生、共在的关系。我们从纯文学或者“自主性”文学之中脱身出来,反观真实状态下的文学,即语境中的文学,发现了文学的多维性和关系性。表面是文学的语境思考恢复了文学的丰富性,其实不能叫“恢复”,只能称为“还原”。因为文学本然如此,只不过长期主客二元的哲学观念使得我们“反认他乡为故乡”。独立的文学与语境中的文学的差别,就像我们具身化看这个世界与通过图片看这个世界一样,似乎都差不多,但是这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一个是以全息的“在世之中”的状态存在于世界之中,感知世界;一个是以“非在之中”的客观角度认知世界。
三、语境诗学之于“后理论”的“具体性”
“后理论”是文艺理论界新近提出并持续阐释和建构的诗学进路。按照赖大仁先生的考证,虽然有着“理论之后”“反理论”和“新理论”等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是“后理论”转向主要针对具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逻各斯主义的“大理论”,寻求差异性、具体性和语境化的“反理论”路径[19]。反观语境诗学,它反对“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同时又带有“具体化”和“小理论”性。因而,语境诗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后理论”的倾向。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其话语权很多从哲学那里“申请”而获得的,比如文学理论之中的概念: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人物形象的个性与共性;文学现象和文学本质等等。这些术语其实就是从哲学借用到文学理论的。因而,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建构,得到哲学的“恩典”才可能具有知识学或者学科话语的权力。然而,作为独特对象的“文学”,其具体性和感性维度恰好与哲学抽象和思辨是悖逆的。后现代理论之中的“小叙事”成为这种对哲学反叛的标志性口号[20]。
语境诗学正好是顺应着这种思潮,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更“文学化”的理论思考。这主要体现在语境诗学对传统“宏大叙事”的拒斥:面对问题时,这种理论进路的思考方式永远是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按照李春青先生的话来说,文学理论是在“具体问题”的追问和探究之中产生的,我们要区别文学理论之中的“伪问题”和真问题。“伪问题”往往追问的是一般规律、原则和本质问题,“真问题”则是落实在具体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21]。从语境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不是一种抽象的、漂浮于空中楼阁的理论,而应该诞生于具体的文学语境,比如宋代文学观念在哪些方面和怎样受到儒学、道学的影响,而不应该去追问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因为脱离具体文学现象和个体情境的文学探讨是一种无意义的思辨。
文学研究的对象,较之于其他所有学科不同,它强调具体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个人生活经验与细节)。当对象非抽象地呈现时,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对象的“平均数”状态,文学则最需要情景语境的解释。文学关注的是个体命运和日常生活,而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个人被规约为原子化的“同质”人。南帆先生认为即便是与文学最为接近的历史,其最小的分析单位也是社会,而文学的最小分析单位是个人[20]。
在这种“具体化”和“语境性”的理论研究过程之中,文学理论自然需要摆脱科学化倾向。理性化和科学化的文学理论对描述而非阐释文学事实,甚至将其作为“定理、公式、模型”来把握,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个性的、差异的和独创的文学被同质化[19]。文学语境论特别关注的就是对文学事實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对待和研究,更强调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这正是伊格尔顿眼中“后理论”所追求的:“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24]文学的审美性、价值性并非一种从内到外的文学性表征,更不是一种永恒静止的超然属性,它是文学语境包蕴之中的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同时,反观文学理论本身,其理论的建构不是一种概念和范畴的堆砌,而是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情境之中丰富和建构起来的。语境诗学认为文学理论当然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理论体系并非永恒静止不变的,而是在面对不同的文学情境之时,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关系和范畴,并且它持续地、自反地抵抗着自身的抽象性,以期返回到现象和作品的情境中,从而实现所谓的“文学”的研究,而非“文学研究”,正如周宪先生所说,后理论告别和拒斥着“大叙事”,走向一种“小理论”研究[23]。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的复杂化、多变性,这种现象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理论本身走向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倾向,比如网络文学理论、大众文学理论等。文论既需要正视当下语境中的新文学现象,也需要回溯“历代经典化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24]。所以说,语境诗学必然属于“大理论”反面的“小理论”话语范畴。按照李西建、贺卫东的说法,“小理论”提供的不是文学批评的方案或立场,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动和实践[22]。语境性的“小理论”也许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性”,让文学理论回归到与政治和公共文化的共生共存的状态。文学并不能将自身紧锁于文本的内部,而是与当下的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关联[25]。
与此同时,“大理论”的宏大叙事言及的是文学“背景”,“小理论”的情境叙事言说的是文学“语境”。文学“语境”不同于文学“背景”:“语境”遵循特殊性规律,“背景”遵循一般性原则;“语境”遵循差异性原则,“背景”遵循同一性前提。换句话说,“语境”一定是与“具体某个文本”发生直接关联的;“背景”则是可以与“无数文本”发生间接关联或强行被关联。春秋战国的文学思想必然会涉及一般性的时代背景:礼崩乐坏或百家争鸣等,但是这种普遍性陈述无法解释为何同时代儒家和道家差异那么大。因此,李春青、史钰认为我们需要区别文学的“背景”与“语境”的差异:“背景”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大理论”;“语境”则是微观的“小理论”[26]。
在“理论”的地方化追求上,语境诗学和所谓的“后理论”确实具有同样的品格。但是,当我们把语境诗学和“后理论”并举的时候,其实是把“后理论”视为与“语境诗学”同样的具有确定内涵所指和价值取向的理论观念。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后理论”并非具有具体思想指涉的观念,它只是预示着文学理论的一种趋向和转折[27]。所以,“后理论”并非独立的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理论倾向,就像具有形状的陶罐,它可以包容很多具有思想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必定在品格上是符合陶罐的“形状”的。语境诗学则是以语境作为自己的本体概念,重新思考文学理论,试图将作为宏大叙事的文学理论,以语境化的思维方式重新建构。语境诗学拥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体系,具有明确的观念所指、思维路径和理论认知。因此,语境诗学不能等同于文学“后理论”,而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意义上的文学“后理论”。
四、结语
语境诗学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内在地存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反思性让语境诗学摆脱理论工具论的束缚,为文学理论自身提供一种反身的基点,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种种理论范畴、观念和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其遮蔽或忽视的部分。默会性赋予语境诗学以新的话语范式,它将文学理论从可言说推向不可言说的境地。“不可言说”并非让理论消失,而是以“源初自明性”的实践知识替代逻辑知识。语境诗学便生成迥异于传统的理论论域和言说方式,比如从印刷文本走向多模态文本,从静态文本走向活态文本,从语言信息接受走向审美氛围感知等等。“具体性”与“语境性”某种意义上可以同义互换。语境诗学让试图建立普遍或普世的诗学体系落空,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此时此地”的情境性、当下性和特殊性。
[责任编辑:蒋玉斌]
注释:
① 笔者关于语境诗学的系列论文包括:《现状、困境与出路:文学语境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载《当代文坛》2014年第1期;《“文学语境”的本质与本体言说》,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文学语境的实践表征》,载《阅江学刊》2014年第3期;《文学语境的三层境遇及其阶段性特征》,载《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语境与文学理论之关系》,载《武陵学刊》2014年第6期;《空间的逻辑:文学语境空间层域的内部关系》,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何谓语境:对语境本质的批评性考察》,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艺术语境的本体意义与理论表征》,载《学术论坛》2018年第6期;《语境诗学的哲学基础与学理合法性》,载《学术论坛》2019年第4期;《语境诗学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知识谱系》,载《武陵学刊》202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王元骧.读张江《理论中心论》所想到的[J].文学评论,2017(6):80-87.
[2] 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J].文学评论,2012(3):191-199.
[3]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 王元骧.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J].社会科学战线,2008(4):137-145.
[7] 郄智毅.“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建构方式的思考[J].求索,2017(12):153-160.
[8] 肖明华.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11):149-152.
[9]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M].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J].文艺理论研究,2010(3):2-11.
[11]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徐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2]田义勇.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3]徐为民.“非之中”与“在之中”——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主体思想比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93-99.
[14]王德峰.藝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5]DILLEY R M.The problem of context[M].New York.Berghahn Books.1999.
[16]夏宏.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10-117.
[17]邓线平.波兰尼与胡塞尔认识论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18]郁振华.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39-45.
[19]赖大仁.“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J].学术月刊,2015(2):100-106.
[20]南帆.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J].文艺争鸣,2017(8):96-99.
[21]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J].文艺争鸣,2001(3):42-44.
[22]李西建,贺卫东.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与知识生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11-18.
[23]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J].文学评论,2008(5):82-87.
[24]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与建构的理论基点[J].学术月刊,2017(9):102-108.
[25]张羽华.新时期文化语境与乡村文学心理叙事[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47-53.
[26]李春青,史钰.徘徊于理论与历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讨论之一[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41-53.
[27]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J].文学评论,2011(5):166-174.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Contextual Poetics”
XU 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The contextual poetics takes “context” as the ontological category,metadiscourse and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of literary theory,and rethink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the literary theory system.As a kind of poetic discourse,it has the theoretical qualities of critical philosophy,post-critical philosophy and “post-theory”:The contextual poetics is a “reflexive” literary theory,which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empirical facts by subjective concepts and theories,but also opens to the empirical facts of literature dynamically.The contextual poetics is also a kind of “tacit” theoretical discourse,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meaning between literary utterance and non-utterance,“focus awareness” and “accessory awareness”.The literary context has the tacit nature of “original self-evidence”,that is,it “lives within” the world,rather than thinks about the world outside of the detached world.In the “post-theoretical” trend of thought,literary theory began to reject “big theories” or “grand narratives”,and emphasized the use of small theorizing or “contextualized” theories to approach literary phenomena.The contextual poetics pays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facts or the “concreteness” of literary works,as well as the “uniqueness” and “uniqueness” value of literature itself.
Key words:contextual poetics;reflectiveness;tacitness;concreteness;post-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