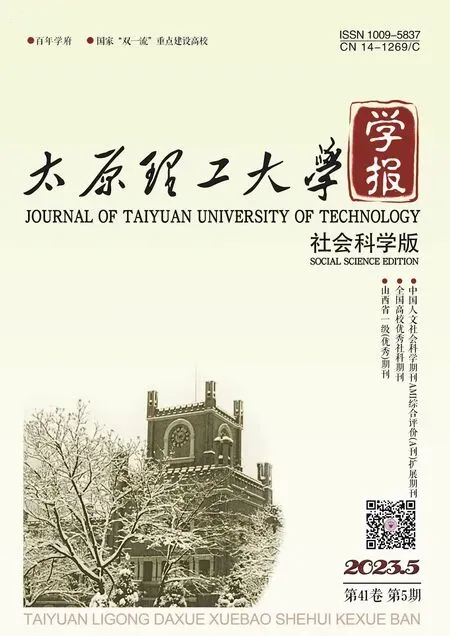老子喻“道”新探
——对宗教世界的超越与现实世界的隐喻
聂 磊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因子,然而道并非直观的、具象的现实之物。老子道论有着十分宏大的体系,老子对道的论述也是多维度、多方位的。老子自身亦知道的难以把握,故而老子以人们最为常知的近身之物喻道。我们可以从老子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两个维度,进一步把握老子的道论。以往对老子道论的研究,仅停留于老子对具体之物的隐喻,并没有从老子喻道的内在理路探析。老子喻道的内在理路从宗教世界而言,则是以神喻道,包含帝、神、谷神、玄牝等;从现实世界而言,是以物喻道,包含根、母、门、水等。这为我们认识老子喻道开启了新的篇章,有助于我们厘清老子喻道的内在意涵。
一、以神喻道:老子对宗教世界的超越
在老子的宗教世界中,老子将夏、商、先周时期的上帝崇拜纳入道的含摄之内,并将宗教成分中神、帝、天的至上性、主宰性,以及神、帝、天在夏、商、先周时期所具的本原性,也归摄于道,进而建构道论体系。老子论道不仅是将道见诸于具体之物上,也将道建基于夏、商、先周时期三代宗教之上。
夏、商、先周时期,人们的信仰呈现为原始宗教信仰,多是对神、上帝、天的崇拜,正如《诗经》所载“敬恭明神,宜无悔怒”[1]424,“昊天上帝”[1]424;《尚书》所载:“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2]1554,“予畏上帝,不敢不正”[2]881,“致天之罚”[2]884,“惟天降命”[2]1381。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上帝的主宰性、至上性,但是发展至西周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已逐渐“由‘自然宗教’发展到‘伦理宗教’的意义水平。它赏善罚恶,可以根据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具有道德和伦理的内涵”[3]12。然而,在老子构建的道论体系中,老子并没有将道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宗教本原。老子所构建的道论是超越于“自然宗教”和“伦理宗教”之上的道论。
老子通过对宗教世界中神、上帝、天的隐喻构建其理性的哲学信仰世界,依托于宗教信仰的具体对象进而转入道论构建。有学者认为道是老子宗教世界的核心,“诸神为道所主宰、为道所生,道是宗教世界以及宗教世界中诸神的本原,诸神对于道具有依附性,从而构成了以‘道’为核心的内在宗教体系”[4]。在老子的论述中,老子以神喻道,又超越于宗教之神;道不是属于宗教体系的道,而是宗教之神的依据,是超越于宗教世界的存在。老子以神喻道主要表现为以宗教世界里的帝、神、鬼、谷神等为具体对象。他认为,宗教信仰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很好地指引人们的生存,因而建构一个理性的哲学信仰是立足现实世界的最佳途径。故而,老子以帝、神、鬼、谷神等宗教对象隐喻道,让这些宗教对象为道服务。我们将从道体之本根性、道与宗教对象存在的先后性、道用之无限性三个方面分而述之。
其一,道体之本根性,乃是道对宗教之神至上性、主宰性的超越。道是无限的真实存在的实体,帝在原始宗教信仰中是至上性的存在,“帝”代指天帝,是原始宗教中最高的、唯一的天神,是主宰万物的神灵。这样的神性存在无疑契合了老子构建道论的需求,老子将帝作为道的儿子,构建道体之本根性,老子并没有试图取代帝,而是将帝下落为道的下一层级的存在。道是万物之宗的宗,位于帝之上。道代替神,而为万物之宗,其存在乃在上帝之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5]12老子以道对帝的超越,呈现出道作为理性信仰的意涵。“老子是利用人们对‘帝’的信仰、崇拜来设计的……帝不仅是神,而且还是至上神;帝不仅主宰世俗世界,而且还主宰信仰世界。同时,帝还扮演万物始祖的角色。由于上下、先后象征尊卑主从,老子以道‘象帝之先’,直接置‘道’于‘帝’之前、之上,从而将帝之于万物的至上性、主宰性以及帝的始祖特征赋予‘道’,使‘道’获得帝的所有权威。”[6]6
其二,道先于宗教对象而存在,乃是道对宗教之神本原性的超越。从神与道的时间维度而言,老子认为道是产生于神之前的;神是宗教世界中的至高主宰,道既然是先于神而存在,那么,道亦即宇宙万物的主宰,同时还含摄了对神的主宰意涵。既然道在神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从神与道的所属关系而言,老子构建的道论体系超越了当时的原始宗教——不仅对原始宗教世界进行了重构,而且还重构了一种新的哲学式的理性信仰。从老子的视域理解神的存在,其实神只是万物之一,神的神秘主义色彩在道面前早已消解。换言之,老子所言之道可以说是神的灵魂,抑或是道发展了神,神在宗教中是至高主宰性的存在,无法再向前迈进了。道作为理性的信仰,将神从宗教世界下落到现实世界,从而使人敢于直面宗教世界,进而引导人直面理性信仰。正如老子所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5]109“一”即道的化身,亦可称之为道的核心因子。在老子看来,无论是宗教世界中天、地、神、谷这些具有神性的神,还是自然世界中的万物,只要具备了道的核心因子,拥有了灵魂,注入了本性,神才能称之为神;万物也能得以生成长养。可见,道之于宗教世界中的神而言,道并非是取代神成为宗教意义的道,而是将人由宗教信仰引向理性信仰,老子之道的进步意义正在于此。
其三,道用之无限性,乃是对宗教之神有限恩泽性的超越。就道用而言,道之用与宗教世界中的神性相比较,可以说是对神性的一个含摄。我们知道神在宗教世界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同时掌管着现实世界中万物的生存,对万物具有生杀赏罚的权力,人们面对神时,往往是卑微求全,对于侍奉神灵亦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殚精竭虑。老子认为神对万物包括对人的主宰权力,在道那里是不成立的,至少是削弱了其生杀赏罚的权力,故而老子将无形无象的宗教神性之用转化为道之用,破除人们心中对外在至上神的依赖性,进而推天道以明人事。正如方东美指出:“其显发方式有二:其一,‘退藏于密,放之则弥于六合’——盖道,收敛之,隐然潜存于‘无’之超越界,退藏于本体界、玄之又玄、不可致诘之玄境;而发散之,则弥贯宇宙万有。故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万物’。其二,‘反者,道之动’——盖实有界之能,由于挥发或浪费,有‘用竭’之虞,固当下有界,基于迫切需要,势必向上求援于‘道’或‘无’之超越界,以取得充养。”[7]156-157道的显发主要呈现在超越界与实有界,然而宗教中神对人们的统治,亦是通过宣扬神在超越界的无限性与实有界的主宰性,进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控制。老子所言道之用,恰是破除了宗教世界里的无限神性。道运化神,将宗教世界拉回到现实信仰层面,由外在的主宰神的信仰,转化为内在的道性信仰。如老子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5]162宗教之神在道之下,无法彰显其神的作用;并不是因为宗教之神没有作用了,而是在道的涵摄之下,宗教之神对人的主宰、赏善罚恶等作用被道消解了。因为道用具有无限性,道用的无限性不仅表现在超越宗教之神方面,在具体发用之中还是理性信仰的呈现。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神虽是不可把握和不可揣度的,在现实世界中人无法直接和神对话,但是,老子构建起道论发展了宗教神性,将宗教神性的信仰指向哲学理性信仰的层面。同时,老子将道作为一切活动的范式,但并非将道神秘化,道也并非直接等同于宗教之神。老子将道作为命运的最后归属,这是老子拔高道的信仰维度,提升道的理性存在,为现实世界人的生命寻找的归属。
二、以物喻道:老子对现实世界的隐喻
如前所论,老子以神喻道,在于假借宗教世界中的神所具有的至上性、主宰性、本原性,进而将宗教世界中的神性统摄于道之内。老子构建道论体系是为了建构道在哲学层面上的理性信仰,上文从道体之本根性、道与宗教对象存在的先后性、道用之无限性三个方面表现出道对宗教之神的超越,展现了老子精妙的逻辑体系和清晰的内在理路。老子不仅在宗教世界中为道之体的构建寻找隐喻,还在现实世界中为道之性的阐发寻求隐喻。老子对现实世界的隐喻主要从以根喻道为万物本根、以母喻道之长养万物、以门喻道为众妙之处、以水喻道之运化状态等四个方面隐喻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化现。
(一)以根喻道为万物本根
老子以根喻道在于阐述道为万物之根。道是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万物源源不断地从道中汲取养分,才得以生成、得以养护。老子以根喻道,区别于以水喻道,以水喻道更多是对道用的运化而言,侧重道在现实世界的具体运化。而以根喻道则是隐喻道对万物的生养关系,万物依附于道而生成,同时还隐喻道之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归属性,不仅个体生命的最终归属要复归于道,自然界中万物的最终归属也要复归于道。从万物的最终归属这个维度而言,道也可以称之为个体生命和自然万物的精神家园与最终归属。
关于“根”,老子有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5]18。老子将玄牝之门解释为天地根,然而对“玄牝”的解释,诸家历来不同。朱熹说:“‘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苏辙说:“谓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谓之玄焉,言见其生而不见其所以生也。”张松如说:“玄牝指微妙的母性,指天地万物总生产的地方。”车载说:“牝,指能够生物的东西说;玄,就总的方面说,共同的方面说,统一的方面说。玄牝,是指一切事物总的产生的地方。”陈鼓应认为,玄牝用以形容“道”的不可思议的生殖力[8]。简而言之,“玄牝”即天地万物得以产生的地方,而且具有内在生生之意。通过对比分析历代诸家对“玄牝”的解释,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老子之“根”。那么,老子以根喻道亦即隐喻道为天地万物之根,说明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道作为形上的本体存在,其内在具有难以把握、难以认识的属性,老子通过以根为隐喻使得形上的本体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也能够为人们所把握,不仅能够把握形上之道,而且也能认识到道之于万物之本根性的存在。
从自然界的视域而言,“根”在现实世界中则指自然界植物的根。既然“根”作为植物深深生长于地下,而且植物的生长都要依靠根才能得以维系,那么,根的存在便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植物来说是本根性的存在。如果说一个植物的根消失了,那这个植物是无法存活的,更无法长出果实;同时,如果这个植物的根不具有内在创生能力,则无法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养分,那这个植物也是无法生长的,最终亦将走向消亡。由此可知,“根”不仅是植物存在的依据,还是植物汲取养分的源泉,同时,“根”内在还必须具有创生力,才能为植物的生存长养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和本根的依据。换言之,老子以此隐喻道,即是将道作为万物之本根,由于道又内在具有“用之不勤”的创生力,正与“根”作为自然界植物的本根这一隐喻相契合。
从个体生命的维度而言,老子以根喻道,“根”虽然是自然界植物之根,但若推广至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如果个体生命背离了道,离开了道的属性,则其个体生命在老子看来也是无法长久存活的。正如老子所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5]39-40老子认为万物最终的归属都要复归于道,道是永恒的存在,复归于道才能“没身不殆”,若将道永葆于个体生命中,自然个体生命亦得以完满。鉴于此,老子还提出个体生命应当将道“修之于身”,道在身可称之为“修身”,亦即“道”的彰显明用;道不在身则可称之为“身不修”。故而,老子强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就是要求个体生命应当不离其“道”,做到以“道”修身。正如老子所言:“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160
究其实可知,老子以根喻道在于根乃是植物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隐喻道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道不仅为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提供依据,还为其提供养分,以保证万物的生长;道不仅为个体生命提供归属,还为个体生命提供指引,以保证个体生命的圆满完成。
(二)以母喻道之长养万物
“母”作为雌性的代表,老子喻道亦常喜用母作为道的隐喻。“母”一般为人所知的含义有三种:一是代指母亲,二是代指本原、根本,三是代指雌性。“母”在老子那里既包涵母亲、本原、雌性三种含义,又蕴含着道的含义。老子之所以提出以母喻道,正在于母本身所指的含义,皆为道所含摄。道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存在,是一种原初性的存在,正如万物皆有“母”一般,母即是指万物之源。
如果说老子以神喻道是在本体论的层面隐喻老子之道,那么老子以母喻道则更多是在生成论的层面隐喻老子之道。老子以母喻道主要表现为:以“母”之生育功能隐喻道之创生万物的功能,以“母”之初始地位隐喻道之作为本原的原初性质,以“母”之柔弱、慈爱精神隐喻道之长养万物的润化精神。
其一,以“母”之生育功能隐喻道之创生万物的功能。以母喻道最为直接的论述,即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5]2。老子认为“母”是万物之母,而非一物一人之母。当“母”作为道的隐喻时,在道创生万物后,即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由于道是无法言说的,道也无法直接作为万物之母,故而以“母”作为一切“有”的根源。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5]2在接续“无”之后,便是“有”的产生;母即是“有”在现实世界中最为直接的呈现。天地之间的万物从母而来,母之于万物是道创生作用的呈现。万物之始是从无而来,当万物产生之时便是有,母对万物则含有“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的作用,因此以母隐喻道之有,并隐喻道创生万物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河上公对此章注曰:“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子也。”[9]2道与万物的关系如同母与子的关系,万物在天地之间长养成熟,离不开道这一“母”角色的运化。万物之母便是道之创生万物在现实世界中的最佳隐喻。老子以母喻道则更多是在生成论的层面隐喻老子之道,就“母”本身给人的直观感受而言,“母”具有生育功能,如母亲生育孩子。老子所言之“母”并不仅仅局限于母的生育功能,更多是在于母的抚育功能。老子有言:“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5]51“食母”即依靠母本而得以长养,“母”既是万物得以生养的依据,亦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
其二,以“母”之初始地位隐喻道之作为本原的原初性质。老子以母喻道最为直接的隐喻便是“天下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5]65道先天地而生,其内在就已经蕴涵着独立性和永恒性,面对这样的道,是无法用具体的、有限的名字来对其进行规范的,故而也只能说“不知其名”,但是道的存在却可以说是天下之母。母是人们最为熟悉的隐喻,就生成论的层面而言,母虽然创生万物,但万物还需要进一步依靠道才能得以生存长养。母作为道的隐喻自然也就承担了道创生万物、长养万物的功能。老子以母喻道,不仅将“母”视为生养万物的母体,还将“母”作为万物复归的本体。如老子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5]143老子以母喻道还从母与子的关系入手,将子作为万物,母即是产生万物之母。从对万物的认识,进而复归于道,万物之所以能够得到道的养护,在于万物时刻不离道。换言之,万物之于道即是子之于母。万物持守道,并将道内化于心,自然就能够做到终身无殆。詹剑锋也指出:“至于‘母’,喻也,取义于母能怀孕、化育、生出。如果‘始’是‘胚胎’,那么‘母’就是能孕育、成形而生出胎儿。然而这是比喻的说法,真正的意义,‘母’是所由以成、所从以出、所得以然者也,故万物所以有之理为母。”[10]169在谈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5]2时,老子所言“万物之母”是就万物得以生成而言,母以此隐喻道在生成论层面的意义。
其三,以“母”之柔弱、慈爱精神隐喻道之长养万物的润化精神。就“母”而言,老子还以母之慈爱精神隐喻道之慈爱精神,道的慈爱精神展现在长养万物的润化作用。老子有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4]176“天将救之,以慈卫之。”[5]176“母”从其母性的视域出发,天然就蕴含着慈爱的精神,老子“三宝”之首即慈,慈当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慈爱,而不是具体关怀之爱,以“母”之内在蕴含的慈爱精神隐喻道之于万物的慈爱是隐性的,是潜行的。有学者从母与子的关系出发,阐释“慈”内在具有的三种特性:一是母子之爱的普遍性,二是母子之爱的恒久性,三是母子之爱的无私性。“从外在理路来看,‘慈’经过华丽转身,由父母子女深切之爱涵蕴、扩充至对整个生命世界的价值关切。从内在理路来说,老子设定了一条‘复守其母’之‘通道’,这条通道保障了天性挚爱之‘慈’的恒久不变和源源不竭,亦即向生命根源的‘德’的回归,亦即通过‘德’而向‘道’的回归。”[11]从老子所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也可以看出老子母之“慈”精神的内在意涵,换言之,“慈”是保证万物得以全生、复归本性的内在精神,亦即道之于万物的生生不息的润化精神。
(三)以门喻道为众妙之处
以门喻道是老子在现实世界中以人为之物作为隐喻。以门喻道区别于老子以水喻道、以根喻道,门不仅是无生命的存在,而且是人为之物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门作为人为之物,是指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的出入口,是进出的必由之道;人不可能穿墙而过,亦不能跳窗而走,门亦可引申为做事的方法、途径、关键。《说文》中解释:“门,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汤可敬撰曰:“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12]1664-1665可见门是内外互通的关键之处,门不仅是进出往来的通道,也是连接内外的关捩之处。老子正是以门连接内外,沟通门之内与门之外,以此隐喻门既可作为连接道的必由之路,亦可作为道向下流注的门户。换言之,老子以门喻道所展现的正是道在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自由转化。“门”此时便是作为沟通的媒介存在,“若从哲学思辨的意义上去厘析其义,则媒介本身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它既使两者分隔又使两者联通”[13]5,可见门在现实世界中之于道的妙用之处。
“门”不仅可以作为沟通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媒介,还可以作为道之出入玄妙之关键处。老子有言:“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5]2门是“有”和“无”所产生的地方,“无”“有”都来自于“门”,这样的门是“众妙之门”,是所有高妙深远的根源的象征,亦即道的象征。道通过“门”而产生“无”“有”,进而化生万物。那么,“门”与道存在着何种关联呢?
首先,“门”与道不是割裂的、对立的存在,而是同一存在,只是用门隐喻道。其次,门作为现实世界的人为之物,道作为形而上的本体;道是通过门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功用来呈现道的具体运化之用。最后,道的运化过程是无形迹的,“门”在现实世界中虽然是具体的存在,但是人们往来于门之间,并不时刻感知有“门”的存在。正如道创生天地万物一般,天地万物并不直接感知道的存在。如果人们离开了“门”这一沟通内外的必由之路,那便无法往来互通。由此可知,门不仅从形上层面隐喻道之本体,还从创生万物的生成层面隐喻道之运化,更从形下层面隐喻道之不可分离。有国外学者在谈及桥梁与门时说道:“在分离与统一的关系中桥梁倾向于后者,桥墩两头间距可见可测,同时间距已被桥梁逾越;与此相反,门以其较为明显的方式表明,分离和统一只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14]3“门”在老子喻道中,便成为一与多的互通处。万物源于道,由道而分化成万物。当万物复归于道时,便是统一于道;当万物由道而出时,便是道之分散。
此外,老子以门喻道还与“根”连用,进而强调道作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上的意义。老子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5]18老子这里所言之“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门,而是“玄牝之门”,将“玄牝之门”与“天地根”等同是说明“‘道’为产生天地万物的始源”,[9]99并且内在蕴含着化生万物而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换言之,“门”亦可称之为道之门,是道的关键之处,由此门而入则进入道的内在,由此门而出则是道的运化。
(四)以水喻道之运化状态
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要素,水本身也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正如美国学者艾兰所说:“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水是最具创造活力的隐喻……包括‘道’在内的中国哲学的许多核心概念都根植于水的隐喻。”[15]63水在老子构建的道论体系中是十分关捩的隐喻。老子以水喻道,其核心在于以水之本质隐喻道之本质,以水之特性隐喻道之特性,以水之万象隐喻道之行迹。有学者指出:“老子比儒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将自然之水升为道德之水,而且又超越道德之水,提升到本体之水的高度以喻道。”[16]
水之本质在于水之就下,老子以水喻道正是水之本质契合了道之本质,水就下的本质正如同道处下的本质。道之本质并非高高在上、神圣而不可认知,道并不远人;老子以为道虽然不可直接认知,但是通过水的隐喻还是看可以把握道的本质的。正如老子所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5]175江海是水的一种具象形态,当水不作为抽象性的概念存在时,水的具象形态便是把握认识道的最佳隐喻。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万流最终的归属,正在于江海的处下本质与其无限性的存在。
老子以水喻道还体现在以水之特性隐喻道之特性,水所具有的特性是“利万物”和“不争”,对此,老子就“利万物”和“不争”的特性隐喻道之特性,具体展开如下。
其一,水“利万物”的特性,正是道“利万物”的特性的呈现。若从道物关系而言,水接近于道,亦可称之为道的具象化存在;水利万物时,便可称之为道利万物,道与万物不仅是主宰与服从的关系,更是一种道滋养万物的创生关系。道在利万物时,并没有对万物加以选择对待,而是将万物一视同仁,不因万物自身的好坏而加以区别对待。老子有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41道之于万物是创生与被创生的关系,万物由道所创生后,道对万物并非占有、控制、主宰,而是给予万物道性,使万物自由的发展,可见水“利万物”正是道“利万物”的展现。从物物关系而言,水亦是万物之一,水并没有因自身能够“利万物”而自我满足、自我夸大,水也没有因“利万物”而丢掉自身的善性,与之相反,正因“利万物”水之善性才得以呈现。同时,水也没有因物之间的差异性而有所分别的“利物”,水能守得住本心,守得住本性。就物与物之间而言,在道看来一切都是平等的,物与物本身之间并没有差别,这正是道的特性的彰显。
其二,水“不争”的特性,正是道之“不争”特性的呈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5]22水之善性在于能够呈现其自性,并以此展现道体,且水利万物而不居功,甘于处下。水“处众人之所恶”即水能处于常人不愿处之处,正是因为水具有“不争”的特性。由于水具有不争的特性,无论水是处于高山之源流,还是山谷之深渊,抑或是平原之江海,水皆能自然处之。水之“不争”所呈现的是道的自然性与道的自在性。如老子所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58。“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175在世俗世界中,人们总是以“争”作为处世原则,没有人能做到“不争”,只有道体才能呈现“不争”的特性。老子认为只有能够做到“不争”,在天下之内才能真正实现“莫能与之争”,然而,能够实现“不争”的也只有道体。水之所以“不争”在于水的自性与其本身甘于处下,故道体之自然性与自在性皆因水之自性而呈现。“不争之德”[5]178,是对“不争”之水的赞誉,更是对道体的概述。故而,老子云:“圣人之道,为而不争。”[5]200“为而不争”便是道体顺着自然的情状自在而为。因顺万物的自性与本心,使得万物皆能自然地生成,万物皆能自在地存在。对此,老子认为水之所以能够自在,正是因为水做到了“夫唯不争”,才能达至“故无尤”境地,这样的境地亦是圣人体悟道体之后呈现的“不争之德”。
此外,老子以水隐喻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七种状态,以此隐喻道在具体事物中的行迹,以及道的运化状态。“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5]22等七种具体状态,是老子以水的“七善”分别表示道在实际运化中的七种状态。“善”在这里释义为善于、擅长,引申为水的灵动性,水能“随物赋形”,但水却没有改变自性,变得同流合污。水的“七善”分别表示为择处、存心、待人、言谈、为政、处事、行动等七种状态。“居善地”意为水在择处时,是因顺自性而为;水之因顺自性,并无逢迎伪作之意。水之所善于择处,在于水能甘于处下,与人无争,“出众人之所恶”,即处于卑下之地,水依然能因顺自性达至自在。老子以水喻道,正在于水之自性能恰如其分地彰显道体。“心善渊”意为水之存心如渊之深静,亦如道体之深远沉静,难以把握,老子也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5]55,只能用“似乎”这样模糊的表意把握道体。“与善仁”意即待人如水一般,以大仁为本,正如道体对万物无私无偏一般,将万物都一视同仁。“言善信”意为言谈如水一般,交谈当以不着痕迹,如水润万物一般,坚守本性、坚守信诺。“正善治”意即为政当如水一般清明,亦如道体之运化不刻意、不妄为,道体呈现在政治上的运化,即是清明太平之象。“事善能”意为处事如水一般无所不至、无所不能,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具体形态;处事圆融无碍,一切皆能自然运化。“动善时”意为行动如水一般善于把握时势,因时而动;能够顺应自然之道,善于把握时机,应期而动。从水的“七善”特性可知,水并无具体的形态,亦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状态,老子将道体的无相性与灵动性,隐喻于水之上亦是十分自如的。
三、“道通上下”:老子的超越与隐喻
“道”是喻道思想的核心,老子喻道主要从两个维度隐喻,一是对宗教世界的超越,二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老子喻道思想中有着内在关联,老子之所以从宗教世界喻道,在于老子看到当时的原始宗教无法帮助人们认识“道”这一客观实在;同时,原始宗教还存在着对上帝等外在神化事物的崇拜,无法建立理性的信仰,也无法构建道论的逻辑体系。如果仅从对宗教世界的超越而言,则无法真正理解老子的道论体系,因而老子又通过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实物隐喻道论思想,对现实世界实物的隐喻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道”的具体展现及其运化。
老子喻道的内在理路则是以宗教世界中的宗教信仰与现实世界中的具象事物为其主要路径。从宗教世界中的宗教信仰而言,老子旨在构建超越于原始宗教的道论体系。其中以神喻道主要是从对上帝、神、谷神、玄牝等宗教之神的隐喻,论证“道”的超越性与主宰性,从而确立“道”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通过对原始宗教信仰对象的隐喻,将道建基于原始宗教信仰对象之上,使得道成为本原上的存在,成为天地万物产生的依据,从而构建了老子的理性信仰之道论。道在老子构建的理性信仰中取代了原始宗教里“神”的地位,原始宗教对象在老子的理性信仰中也逐渐褪去神秘主义色彩,走向客观理性的自然之义,从而实现构建超越原始宗教的理性信仰。从现实世界中的具象事物而言,老子以现实世界可感可见之物为隐喻,旨在阐述“道”之特性及其展现,以及“道”之具体运化。老子通过对根、母、门、水等具象化之物的隐喻,进一步说明“道”不仅具有超越性,而且具有现实性,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具体展现与运化。
老子以根喻道、以母喻道、以门喻道、以水喻道,在现实世界中将“水”“根”视为自然物,将“门”视为人为之物,又将“母”视为生命之本。老子以水喻道,在于以水之本质隐喻道之本质,以水之特性隐喻道之特性,以水之万象隐喻道之行迹。老子以根喻道则是隐喻道对万物的生养关系,同时还隐喻道之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归属性,在老子看来,不仅个体生命的最终归属要复归于道,自然界的万物最终也都要复归于道。老子以门喻道不仅从形上层面隐喻道之本体,还从创生万物的生成论层面隐喻道之运化。老子以母喻道则是以“母”之初始地位隐喻道之作为万物本原的原初地位,以“母”之慈爱精神隐喻道之长养万物的润化精神。
“喻道”是老子对原始宗教的超越与现实世界的隐喻,也是老子道论的展现。从宗教世界到现实世界,“道”是贯通其中的,也就是说“道通上下”。“道”贯通于宗教世界,是对宗教世界的超越,道本身并非宗教的化身。在老子的论述中,老子通过对宗教世界中神、上帝、天的隐喻,以此构建其理性的哲学信仰世界。老子依托宗教世界但却超越宗教世界,并由此进入道论体系的构建。老子认为宗教信仰并不能很好地指引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还需要建构一个理性的哲学信仰,这是立足现实世界的最佳途径。“道通上下”不仅是道对宗教世界的超越,还是道对现实世界中可感可知之物的具体运化。在老子看来这一隐喻则是通过根、母、门、水等喻道,老子对现实世界的隐喻意在说明:“道”不仅为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提供依据,保证万物的生长,“道”还为个体生命提供归属,为个体生命提供指引,以保证个体生命的圆满完成。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隐喻,展现了“道”之创生万物的功能,“道”之作为本原的原初性质,“道”之长养万物的润化精神。
无论老子以“神”喻道还是以“物”喻道,都是对其道论的阐发,通过喻道进而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老子构建的理性信仰。老子构建的道论不仅是哲学理式的突破,更为人们走向理性信仰、寻找精神归属开启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