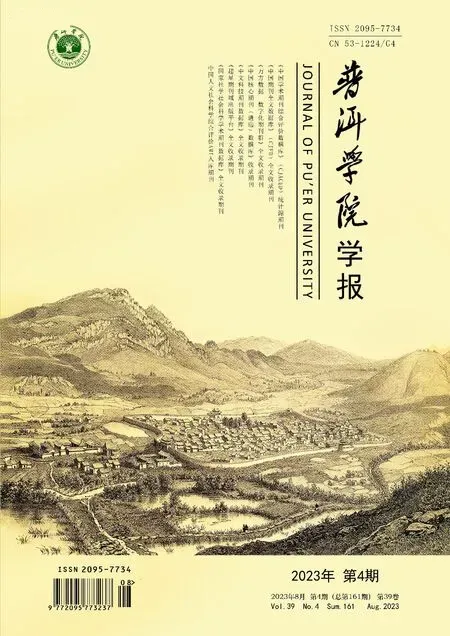存文学《悲怆之城》中区域灾难书写与集体创伤记忆
杨骁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灾难母题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之一,从春秋战国流传至今,在时间的推移中历久弥新。现代以来,例如丁玲的《水》、赵树理的《求雨》、石灵的《捕蝗者》等小说,真实记录了灾难中的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进入当代,作家们不仅继承灾难母题叙事的传统,而且赋予灾难写作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感和文明反思的新内涵。
存文学是当代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由于特殊的多民族地区成长背景,其作品的包容性与丰富性是他的最大特色。一方面,他将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融入到作品中;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打造出原始与现代碰撞、多元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间”。1999 年至2008 年间,他对区域历史题材小说进行了多次尝试,2003 年的《悲怆之城》正是其中最成功的作品。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他自觉地参与到区域历史书写和集体创伤记忆描述中,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创作思考。
一、 多民族记忆之伤:1918—1949年大瘟疫的创伤记忆
在心理学中,创伤记忆“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1],是一种主要关乎个人身体、心理与精神的伤害,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三大基本特征。但创伤记忆也并非是完全个体化的,其已从个体性的创伤记忆升级成为群体性的创伤记忆。
小说《悲怆之城》的历史背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1918 至1949 年间,历史上有“金腾冲,银思茅”之称的茶马古道重镇思茅,一改过去在人们印象里酒肆茶楼林立,夜夜笙歌不断的繁荣富饶景象,连年的鼠疫、疟疾、烂脚杆病泛滥,加之医疗条件的限制及居民思想观念的落后,使本来繁荣的思茅变成了一座“城池坍塌、百业凋零、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怆之城”[2]。
许多群体性的创伤记忆,在一代一代当地人心中留了不可磨灭的种子。他们将“老虎豹子大白天进城;夕阳西下时魔鬼们上房揭瓦;野马蜂在瞬息间就把一个小孩的肉叼去只剩一具骷髅;土匪们又如何耀武扬威的洗劫小城”[2]的故事口口相传下去,成为存文学创作小说《悲怆之城》的灵感来源。于是一本由“事件、事发环境、亲历者及其共同构成的已经过去的‘历史’”[3]书诞生了。
(一)灾难笼罩下的小人物们
“闪光灯记忆”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和库里克提出,指“就像闪光灯的意象所暗指的那样”的记忆。“闪光灯记忆包含了很多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许是偶然进入人们记忆中的,但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不的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的不同认识,最终也必然会将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记忆汇聚成一个整体,复原时间的轮廓和面貌”[3]。小说《悲怆之城》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们“闪光灯记忆”的汇总,一场历经30 年的大灾难。
故事从一场劫后余生的婚礼开始。新郎是大生堂熬胶作坊的乔生,新娘是大病痊愈的秀兰,连年的瘟疫、霍乱、战争使人们已经麻木于悲伤之中,这桩喜事给凋敝小城带来久违的快乐。此时,居民们得知抗日远征军要撤回思茅驻军的消息,往日已经失去生气的小城,又恢复了活力。可一切期盼在远征军到来之际落空,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带来了更可怕的灾难:他们以保护小城之名劫掠财富、强奸妇女,还从缅甸带回更可怕的疟疾。刚收获短暂幸福的新娘秀兰因被羞辱选择自杀,新郎乔生则变成游走街道的疯子,许多居民也因疾病的加速传播、无法就医而死亡。远征军队的指挥官朱旅长、县长徐世清与土匪杨三皮则互相勾结,在灾情严重的档口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最终因他们将国际救济团的药品高价倒卖给当地乡绅和富商,致使疫情无药可控,反噬自己。
小说没有笼统的给不同阶级人物贴上刻板标签,而是将亲历者口述的“闪光灯记忆”,以剪切的手法纳入到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中去,将碎片化的故事片段,拼接起一幅完整的小人物生活长卷,并把史料背后鲜为人知的人物性格和历史细节,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被小城居民奉为“救星”的医生郑济人因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他在深爱的女孩与疟疾缠身的病人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抱憾终身。妓女小芭蕉是县长许世清的情妇,她的内心虽然厌弃许世清,但为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一直依托于他。可当亲眼目睹居民们病魔缠身的惨状,她决然地离开了许世清,选择了从良,并加入到抗疫的队伍中。远近闻名的恶霸杨三皮,经常到小城中烧杀抢掠,后又勾结许世清盗取军械库武装自己,成为方圆百里的“山大王”。
存文学创作《悲怆之城》的素材,除了史料外,主要来源于幼年时期长辈对思茅大瘟疫的讲述与采访当年幸存亲历者。但笔者认为最后一位亲历者的离开,并不意味着一段创伤记忆的所有细节都会死亡,它可以通过口述、文学创作等介质活跃于后人的记忆中,成为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永远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
(二)死亡阴影下的真实人性
在任何年代,灾难都是一面放大镜,环境的高度压迫、资源的极度失调与物质的过度紧缺,使庸常生活中的所有矛盾集中化、扩大化。重灾区则成为人性的修罗场,真善美在这里发扬,罪恶也能在这里释放。
棺材店老板张四,做的是在死者身上发财的生意,他以免费提供送葬服务为由,把同一口棺材卖给不同的人家,白天送死者落葬,晚上又再悄悄派伙计将棺材板拆回店里组装后二次销售。国际救济团的药品送到后,他通过两根金条贿赂许世清,用市场价购买药品,最后再以十倍价格卖给病重的人家,赚取高额利润。许世清本来只是个出风头、贪图小利的官员,可他在得到土匪杨三皮的大额贿赂后,先与杨三皮勾结“监守自盗”盗取枪药库中的武器,后又将救济团的药高价卖给贿赂他的乡绅、富豪,最终导致小城医院无药可用,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结果他自己在逃亡的路上因身患疟疾而亡。朱旅长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派角色,为了得到金钱与小美人做出许多不可饶恕的恶事,导致自己成为“光杆司令”,只能用虎皮贿赂美国人出逃。
人物二分法理论最早是由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他认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没有孰高孰低之说,“一部复杂的小说经常既需要圆形人物,也缺不得扁平人物。”两者相互磨合的结果才“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生”[4]。存文学的小说《悲怆之城》中正是践行了福斯特的这种理论,通过“圆形人物”加“扁形人物”的描写手法,将灾难笼罩下世俗人生中的方方面面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充满复杂人性的角色外,小说还塑造出三个完全向善的人物:郑济人、刘兆一与杨阿狗。存文学对于向善的扁平人物的塑造,其意在于为黑暗的故事加上光明的曙光。杨阿狗是思茅小城里家喻户晓的英雄,他本随着舅舅跑马帮,在泰国、缅甸与思茅之间做小生意,后来因遇上侵入缅甸的日军,舅舅惨遭杀害,杨阿狗怀着为舅报仇的心愿加入了缅甸远征军,他在战场上砍掉过无数敌人的头颅。杨阿狗在远征军回归前一天返回小城探路,却看到年迈的父母惨死家中。但这并没有打倒杨阿狗,他表现出了坚韧、乐观的高贵品质。小学校长刘兆一则是小城里少有的文化人,他大学毕业后,不畏疾病的肆虐,选择回到家乡办学,即使自己染上“烂脚杆”病,也将治疗小城的居民放在第一位,甚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新治疗法的临床实验病例。
小说《悲怆之城》是探寻真实世界中人性的一个窗口。作品中,不同的人性在这最密闭的生存空间和最尖锐的物质冲突中展现出来。有的人朝着恶的深渊里越走越远,最终反噬自己;有的人在善恶之间苦痛挣扎,最终逃不过良心的谴责;有的人受尽命运的不公与折磨,却仍不放弃寻找希望。
二、区域性反思之痛:思茅地区居民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
小说《悲怆之城》并不止于刻画死亡的惨状,而是旨在通过小人物们的悲喜生活展示灾难下思茅地区的社会全貌。这可以唤起后人对现有生存状态的反思,与对未来理想追求的重新建构。
(一)共时性: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本描写灾难之下小人物的作品,存文学在创作小说时,通过将亲历者们闪光灯记忆的细节进行汇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一份不同方面、反映个体对事件的不同认识”,将“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记忆汇聚成一个整体,复原事件的轮廓和面貌”[3]。这种创作手法暗合了伦理学家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闪光灯记忆是个体记忆转向集体记忆的桥梁,并将集体记忆划分为共同记忆和分享记忆。
就集体记忆而言,强调记忆主体亲历性的共同记忆,即是不同闪光灯记忆的汇合。它意味着“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当这些亲历者的数量达到或超过一个限度”[3]时,共同记忆就能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集体记忆。思茅地区30 年“大瘟疫”的故事,也正是由当年亲历者们的记忆组合,并转化成属于亲历者们及其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作为过去的历史,后人要完全窥见当年的真实现状已属奢望,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同记忆会变得黯淡与模糊。书中出现的蔡阿婆这个带有共时性特征的人物,她与《望天树》中的波西、《牧羊天》中的老红奶、《碧罗雪山》中的阿邓多梨拔构成了存文学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人物类型——记忆老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时间的齿轮始终在向前运动,记忆也永远在变化和更替之中。
(二)历时性:世代人的分享记忆
赵静蓉在《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一书中写到:“记忆像一条流动的河流生生不息,记忆的主体承载着各自的使命也在永恒的演绎着生命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实践和完成自己所担负的记忆的使命”[3]。1918—1949 年的“大瘟疫”就是这个区域的居民乃至所有听说过、讨论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需要共同承担的记忆使命。就记忆的交流而言的,分享记忆“不单单等同于个体记忆的聚合,因为记忆被聚合并不等于记忆就能被分享”[3],它“意味着在聚合个体记忆之外,还要对那些分散的个体记忆进行‘校准’或‘修正’,使之从一种个体的言说上升为公共空间里可供开放性交流和自由讨论的话题”[3]。
小说《悲怆之城》中刻画了小芭蕉、老大嫂、小美人等形态各色的底层女性角色。小芭蕉的故事是关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史。她本是跟着四川戏班子来到思茅演出,后因整个班子的人马都染上摆子病死了,只能到凉粉摊前卖唱,结果惨遭土匪杨三皮强奸。小芭蕉为生存先是沦落为妓,后又做了许世清的情妇。但在救下疟疾缠身的秀兰、两次冒风险盗药、安慰照顾的病人有所好转之后,她内心的自我苏醒过来,并勇敢离开依附多年的许世清,成为小城抗疫的中流砥柱。小美人则是乱世中的悲剧女性,她虽为山寨神枪手,却只能成为杨三皮与朱旅长互相争抢的玩物而不自知。
除了底层女性外,还有郑济人、刘兆一、杨阿狗、张四等知识分子、士兵与小商贩的代表。一方面,他们逃不开许世清、朱旅长、杨三皮的“权力大网”;另一方面,在混乱的时局中寻求自我的价值。郑济人怀着一颗“医者仁心”,以“救死扶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刘兆一则把心都扑在教育上,即使自己染上了“烂脚杆”病,也与郑济人一起带着大家抵抗疫情,希望早日迎接复课。他们身上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身上浓浓的人文关怀精神。杨阿狗作为士兵,他表现出强烈反抗精神,违背出入令为死去的战友送葬、为病重的战友寻药、帮助战友们尝试“刮骨疗伤”的新方法,拯救了多位战友的生命。
作品中,小商贩赵四则秉承着“乱世出英雄”的信条,发灾难财。许世清、朱旅长与杨三皮分别代表了当时思茅城里的黑暗政治、腐败军队与混乱民间。小说中对灾难下各色小人物的描写,也恰恰暗合了共享记忆对个体记忆的修正与校准功能,使记忆在共享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代代相传。
三、人类责任感之思:从“文学创伤”走向“文化创伤”
(一)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与公共卫生事件书写
目前,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四部作品:刘震云关于河南大旱的《温故一九四二》,迟子建关于哈尔滨鼠疫的《白雪乌鸦》,阿来关于“汶川地震”的《云中记》与张翎关于“汶川地震”的《余震》。而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灾难题材小说则少有关注。存文学是当代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与学者们对其作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兽灵》《碧罗雪山》《望天树》等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作品之上,对《悲怆之城》这部作家隐藏自己的本民族显性特征,融入大历史叙事角色的作品一直没有过多研究。
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少数民族”标签对于作家而言既是肯定,也是束缚,它既意味着特别,也可能成为遮蔽。按照俆新建的“三重文学叙事”理论[5],自我、群体和国家可以分为“自我叙事”“族群叙事”和“国家叙事”三个层面。其中,“自我叙事”是仅关于个人的浅层。在许世清接受杨三皮贿赂的章节里,大老鼠鬼魅的声音让人难以忘怀,第一次与土匪打交道的许世清沉浸在越界的紧张与银元的快乐中,最后被拖着大尾巴的硕鼠们吓了一跳。“族群叙事”则是关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层面。在小说中存文学多次提到没钱买棺材下葬的平凡老人,睡前会穿上漂亮新鞋的细节描述。由于历史上的“大瘟疫”,亲历者们有了穿脏鞋的人去世后不能投胎转世、进入新轮回的习俗,于是为了防止自己在睡梦中离去,没人帮忙换上干净的新鞋,老人们一直秉承这个独特的习俗延续至今。
存文学在小说《悲怆之城》中,对于自我身份的考量已经不限于前两个层面中,而将“自我”与“人类”的两端连接起来,是一种文学经验上的超越。他将自己的本民族身份内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之中,这种书写手法是值得关注的。
(二)“文化创伤”的重新建构与再突破
从“文学创伤”走向“文化创伤”,是关于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交流,它意味着创伤记忆从一个文学主题,演变为哲学、道德甚至伦理主题。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在界定“文化创伤”时,认为其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是涉及到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6]。
小说《悲怆之城》的故事,与阿来《云中记》和张翎《余震》的区别之处在于,后者作为灾难的亲历者,其作品属于见证文学的范畴,情感激昂且带有倾诉的性质。而前者是对“大瘟疫”创伤性体验的事后重建,作家在获得了反思灾难的能力,认识到造成灾难逐渐恶化的根源之后,对社会危机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新思考。属于对“文化创伤”冷静而深刻的重新建构,其目的主要在于思考“后灾难、后创伤时代的人类应该怎么办”[6]。
思茅城的瘟疫是由天气燥热、环境恶化及卫生欠佳等外在条件引发所致,但恶化的根源还是在于人本身,无序的环境及紧缺的资源,使人性最深处的东西被发掘出来。许世清、朱旅长及杨三皮以救灾药物中饱私囊是灾难恶化的直接推手,张四则为了利益倒卖药品加速悲剧的到来,处于病痛折磨与生活打击的居民们,本来是这场灾难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但他们对治疗机会及药物无意识的抢夺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直至故事结尾,在郑济人、刘兆一、小芭蕉等人的努力下,灾难中幸存的人们开始清醒,并走上自救道路:唯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唯有团结才能战胜灾难。
存文学在后记中谈创作《悲怆之城》的初衷:“我国著名作家丁玲生前到过思茅,在座谈会上,老人家说,你们为什么不写思茅?这里发生的大瘟疫是人类史上的大悲剧,一部厚重的大书啊。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萌生了写一本书的想法。我想,用文学形式展示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可见,他在创作初期就已经意识到要将“文学创伤”深化为“文化创伤”,需要将其放置集体或者世界性的语境中进行考量。
四、结语
小说《悲怆之城》是一部值得重新审视和解读的小说,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身份认同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身份叙事的典型作品;另一方面,是灾难书写对“繁复的‘单声部现象’”与“即时性”的突破之作。特别是在当下的特殊时期,为小说中的灾难书写与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将个体创伤放到集体性的语境中考量与反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