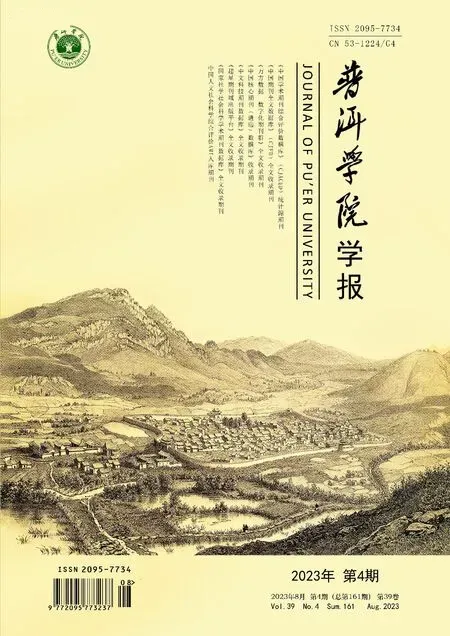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
韩焕忠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作为晚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和佛教居士,焦竑对儒道佛三家都非常精通。在他看来,“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①。”这一奇特的儒佛关系论在他对《论语》《中庸》以及《孟子》的理解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先谥文端,后改文宪。焦竑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十六岁应童子试,获第一,入应天府学。焦竑二十四岁举应天府乡试,但直至万历十七年(1589)他五十初度,才以会试第三廷试一甲一名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二年(1594)受命与修国史,出任东宫讲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被钦点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因蒙受谗言,被贬为福建福宁州同知,次年考评,受“镌秩”处分,遂辞官,隐居于金陵,以著述讲学为务,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无疾而终。焦竑著作传世者有《澹园集》《老子翼》《庄子翼》《易荃》《焦氏笔乘》《类林》《玉堂丛话》《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俗书刊误》等,可谓著作等身,对研究明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政治史,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②。黄宗羲将其列入泰州王学③,论者谓其有“对公安派骅骝开道之功”④,“上承心学之绪,下启实学之端,诚为明清间风气转换之嚆矢”⑤。其学术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焦竑对佛教非常欣赏,故而对理学家的排佛论颇为不满,时有反驳之言。其所著《读论语》《读中庸》《读孟子》等,被收录在《焦氏笔乘续集》中,堪称以佛教义理疏释儒家经典的杰作,为人们研究儒佛两种异质思想的融通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
一、对排佛论的强烈批驳
焦竑虽然笃信佛教,但作为由科举高第而步入仕途的士大夫,其儒家的立场也同样牢不可破。因此,在面对俗儒的攻讦和责难时,他对程朱理学家的排佛言论给与了强烈的批驳。
焦竑将佛教经典视为对儒家义理的阐发和注解。排佛者每以儒佛二家之迥异而是儒非佛,但在焦竑看来,佛教经典远比汉宋诸儒的注疏更有助于对儒家精髓的理解。他指出,孔孟之学乃“尽性至命之学”,但由于“言约旨微”,对其奥义阐发得不够充分;佛教亦为“尽性至命之学”,而且说理非常透彻,因此,可以将佛教经典视为“孔孟之义疏”。焦竑认为,“夫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则俎豆之,疏其精则斥之,其亦不通于理矣⑥。”这也是孔孟之学虽盛行但却很少有人把握其精神的重要原因。焦竑还认为,要通达儒家经典,理解孔子所罕言的性命之理,就必须通达极言此理的佛教经典。他说:“内典之多,至于充栋,大抵皆了义之谈也。古人谓暗室之一灯,苦海之三老,截疑网之宝剑,决盲眼之金鎞。故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⑥。”当然也有人以辞亲出家为理由而排斥佛教,焦竑对此反驳说:“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迟之请学;非妻子不续,而佛听比丘之出家。盖必有不举稼圃者,而后可以安天下之为稼圃者;亦必有不恋妻子者,而后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⑥。”
焦竑将断见邪禅与真正的佛教进行了区分。佛教蒙受攻讦和责难,除了俗儒识见陋劣之外,也与一些人假“无碍”“无我无作无受”之名而肆行无忌,使佛教蒙上了不白之冤大有关系。这些人本怀多欲之心,却借助佛教“无碍”之语,以行善利人为有碍、为执著,而以行恶作歹为无碍、为解脱。在焦竑看来,这些人名为禅宗,实系假托,禅宗是绝无如此荒谬之论的。佛经虽然有“无我无作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之说,但此“无作无受”是说“于有为之中,识无为之本体云耳,未尝谓恶可为,善可去也”⑦;佛经虽然有“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之谈,但此“不动”之“第一义”,是说“分别之中,本无动摇云耳,未尝谓善与恶漫然无别也”⑦。其义实即孔门“空空”之宗及子思“未发之中”“无声无臭”之“天载”。也就是说,在焦竑的心目中,佛教“无我无作无受”“于第一义而不动”等所谓“空”义,与儒家的“克己”一样,都具有非常崇高的道德内涵。
焦竑将对排佛者的批驳主要放在了程颢身上。他在给恩师耿定向的信中说:“伯淳斥佛,其言虽多,大抵谓‘出离生死’为利心。……以出离生死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则即生灭而证真如,乃吾曹所当亟求者,从而斥之可乎?……不捐事以为空,事即空,不灭情以为性,情即性。此梵学之妙,孔学之妙也。……伯淳人品虽高,其所得者犹存意地,乃欲以生灭之见缠,测净明之性海,难以冀矣⑦。”在焦竑看来,佛教的出离生死就是《周易·艮卦》的“止其所”之义,程颢辟之,正表明他造诣不高,难以窥见孔佛之妙。程颢指责,“佛氏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煞得尽”,意谓佛教彻底否定了人类的伦理规范。焦竑认为程颢所指责的也是佛所诃斥的“二乘断见”,不是真正的佛教⑧。程颢谓佛教虽然能够穷神知化,但却无法开物成务。程颢之辟佛实有昧于己心而为名利所束,此论可以说是非常尖锐而深刻的,也很能切中要害。
焦竑尝为《华严经》作序云:“司马君实知佛而不谈,曰:‘吾以为孔子地也。’余以为能读此经,然后知六经、语、孟无非禅,尧舜周孔即为佛,可以破沉空之妄见,纠执相之谬心。上无萧衍之祸,下无王缙之惑,其为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⑨!”其意谓读佛经然后能真正了解孔孟,能发扬光大孔孟之道。焦竑作为泰州王学的后劲,他站在儒家立场上为佛教进行精心的辩护和开解,于此反映出泰州王学与佛教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
二、对《论语》的禅学解读
焦竑对《论语》极为欣赏和推崇。《焦氏笔乘》开篇即记赵孝孙(字仲修)劝李彦平(李彦平即李延平,朱子之师李侗为延平人,学者尊为延平先生)读《论语》。谓读《论语》为“所以学圣人”,无论是“出入起居之时”,还是“饮食游观之时”,甚或“疾病死生之时”,都应学而不辍。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但行得其中三句,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便足以为州郡之长吏。
焦竑将孔子视为参破生死、证得空空,获得解脱的大自在者。世人以为生死之说创自于西天佛祖,而孔子早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等语。在焦竑看来,“原始反终”就是孔子参破生死的象征:“‘原始’则知无始矣,‘反终’则知无终矣;无始无终,而死生之念息矣⑩。”孔子因鄙夫之问而有“空空如也”之叹,实即孔子“无离文字说解脱相”的体现⑩。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在焦竑看来,这些言论无疑就是孔子对自己所证“空空之境”的表达。他评论说:“盖知体虚玄,泯绝无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处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此非空空何以状之?故子思谓之‘不睹不闻’,又谓之‘无声无臭’⑩。”以佛教修行的行位衡量,这自然是非常高妙的境界。颜回虽未证得孔子的空空之境,但已可以自觉运用之而随缘即空:“‘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屡空’者,颜子也。屡空则有不空矣。盖其信解虽深,不无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觉而归于空⑩。”颜子虽不能如孔子一样心恒住于空空之境,但一有微心之起,即自觉其空,故能优入圣域,为孔门高弟。
焦竑将孔子在动容周旋中体现的圣人气象归结为空空之境的体现。孔子非常重视仁,时常以仁教导弟子,并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论。焦竑认为,“此孔氏之顿门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当体而空,触事成觉,非顿门而何⑩?”由此断定,焦竑是将仁与空等同的:就空有觉义而言谓之仁,就仁无具体规定性而言谓之空,孔子不必起心动念,不用克制勉强,就能自然体现在自己的举动事为之中,故而焦竑谓之为“孔氏之顿门”。孔子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在焦竑看来,无论是为学、诲人,还是事父兄公卿、勉丧事、谨酒德等,“皆圣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应迹耳,而其心则一无有也。”孔子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故而出世不碍其日用之常,入世不妨其心境之空,故可以进退从容,中规中距。孔门弟子智不及此,反以为孔子有什么诀窍未向他们传授,孔子坦白地说:“二三子以吾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焦竑对此评论说:“非无隐也,欲隐之而不得也;非以行与也,欲不与而不能也。举足下足,无非道场;一咳一吐,尽成妙法,此岂可以名理求,言思测哉?学者真知行之一字,则六经为筌蹄,千圣为过影;释氏之棒喝,独属不亲,老聃之徼妙,皆属余食矣⑩。”
焦竑认为孔子的空空之境在其处理一多关系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焦竑认为,多能与成圣本不相妨,但太宰之智不及此,看到孔子博学多能,就怀疑孔子未达圣境,这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圣人应“用心于约”。与太宰不同的是,达巷党人看到孔子虽然多能,但见“其统之有宗,其会之有元”,于是称叹不已。焦竑对此评论道:“充太宰之见,则一尘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况于多乎?充党人之见,则游之乎群数之途,而非数也;投之乎百为之会,而非为也,无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欤?夫太宰得一,而以疑夫子之多;党人得于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说而圣人之道愈以发明于天下,则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⑩。”在焦竑看来,一与多虽然不同,但孔子却能使两者之间相互包容,互不妨碍。焦竑据《金刚经》“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之意,认为如果“能近取譬”,使人“豁然还其本真,则立达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⑩。”对人施予指导,使人领悟到仁的实质,相比于分人以财来讲,是更为真实的仁。
焦竑在以佛教义理解读《论语》时对曾子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孔子曾经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诺”。门人问其所谓,则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焦竑解释说:“曾子少孔子五十三岁,群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贯之唯,口耳俱丧,岂涉生死之流欤?迨门人问之,辄举忠恕以对,不动目前,全成正觉,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⑩。”焦竑将孔子之语看成了传道付法的凭证,将曾子之应看成了迥脱根尘的象征。可以说,孔曾之间的这则对话就成了焦竑努力参究的公案禅。曾子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焦竑认为这是曾子对《易·艮》之象词的称引。在焦竑看来,“不出其位”就是“止其所”,即让自己的思虑“当念而寂”,而不是“离念而寂”。他说:“离念而求寂,则思废,堕体绌聪者也,谓之断见;当念而不寂,则位离,憧憧往来者也,谓之常见。常应常净,而泊然栖乎性宅,此则非断非常,唯君子能之⑩。”很显然,曾子所谓的“思不出位”,通过焦竑的解读,就成了“于念而离念”“念念而不住”的禅门宗旨。
焦竑以参禅的方式解释《论语》,特别重视孔子的“空空如也”之境,将其作为孔子之为大成至圣的内在依据,将《论语》视为孔子这一境界的随缘呈现。可以看出,焦竑对佛教的诸法空义有深切的体会,对禅宗于念而离念、念念而不住的法门诀窍有独到的领悟,对那些能够破除执著而达到无执境界的成就者极为倾慕和赞赏。
三、对《中庸》的佛学解读
焦竑将《中庸》视为“孔氏之微言”。在焦竑看来,应运用《中庸》来诠释《中庸》,才不致失其宗旨。如,以“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诠释“天命”,以“自诚明谓之性”诠释“率性”,以“自明诚谓之教”诠释“修道”等。以往的诠释者思不及此,故而多失其宗旨⑪。其实,焦竑除了运用《中庸》本文诠释《中庸》外,还运用了佛教的经典和义理。
焦竑诠释“未发”时引用了《首楞严经》。在他看来,“圣人独能无情哉?喜怒哀乐虽其憧憧焉,皆未发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是也;不然,即喜怒哀乐而去之,不得言未发也,《首楞严经》曰‘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独为法尘分别影事’是也⑪。”也就是说,“慎独”并不意味着圣人没有情感,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中,始终保持无所执著的状态。相反,对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的消除,与《首楞严经》所说的“法尘分别影事”一样,也是一种执著,根本就谈不上是“未发”的问题。
焦竑诠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时引用了《肇论》。焦竑认为,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当喜怒无喜怒,当哀乐无哀乐”,当喜怒哀乐之时就顺其自然地喜怒哀乐,无需故意生喜怒哀乐之心。焦竑引僧肇云:“知恼非恼,则恼亦净;以净为净,则净亦恼。”僧肇之意,在破除众生对烦恼与清净的执著。焦竑认为,“知恼之非净,即知发为未发,可以触类而通矣⑪。”在焦竑看来,只要是破除了情感活动中的执著,就可以时时事事而中道。
焦竑诠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时引用了《维摩诘经》。焦竑认为,“天地万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为不位不育。《净名经》: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秽恶充满。’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譬如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是盲者过,非日月咎。众生罪过,不见如来佛国严净,非如来咎。’又云:‘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饭岂有异,异自天耳⑪。”在已致中和者看来,天地万物是自位自育,而在未致中和者看来,天地万物才不位不育,如《维摩诘经》上所说,因心有高下,国土遂有净秽,福德不同,饭色遂有差异。在焦竑看来,所谓致中和,就是对执著的破除。
除了《读中庸》之外,《焦氏笔乘》也有引佛典诠释《中庸》的记录。如其“诚明”条谓:“诚而明,‘天命之谓性’也;明而诚,‘修道之谓教’也。《首楞严经》:‘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孤山注云:‘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与此意合⑫。”在焦竑看来,《中庸》所谓的“自诚明”,就是“天命之谓性”,也即《首楞严经》所谓的“即寂而照”的“性觉妙明”;而《中庸》所谓的“自明诚”,就是“修道之谓教”,也即《首楞严经》所谓的“即照而寂”的“明妙”。
从焦竑对《中庸》的诠释来看,他所理解的“中庸”,就是将破除执著体现于百姓日用之中,而其极致,就是达到了天地万物位育的“中和”境界。
四、对《孟子》的佛学解读
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受到宋明理学家的特别尊崇。《读孟子》是焦竑对《孟子》中个别语句的理解和诠释,其中也有对佛教义理的运用。
在焦竑看来,儒佛两家在师资传承上具有一致性。据《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之意,在阐明孔子“道德明著,光辉洁白,非有若所能仿佛也⑬。”焦竑引用临济义玄的一则公案对曾子赞扬孔子的话评论说:“盖迷悟悉空,法尘俱净,非限量之所及,岂言论之能诠。……至是,虽夫子亦不能逃于曾子矣。临济初见黄檗,如登天也,一见大愚,辄曰:‘由来黄檗佛法无多子。’至此,黄檗亦不能逃于临济故也⑭。”圣人的境界是超越了限量和语言的,未臻其境便无法表达出来。曾子既然道出了孔子的境界,便表明孔子的境界已在曾子的掌握之中,因此说曾子能够被列入道统,是绝非偶然的。
在焦竑看来,孟子所说的“尽心”就是“复性”。《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焦竑解释说:“天即清净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复性,性不复则心不尽。不尽者,喜怒哀乐未忘之谓也。由喜怒哀乐变心为情,情为主宰,故心不尽。若能于喜怒哀乐之中,随顺皆应,使虽有喜怒哀乐,而其根皆亡。情根内亡,应之以性,则发必中节,而和理出焉。如是则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乐非哀乐,是为尽心复性。心尽性纯,不谓之天,不可得已⑭。”显然,焦竑的诠释具有融通《孟子》《中庸》与佛教义理的思想倾向。
在焦竑的体验中,《孟子·告子上》中所说的“夜气”“平旦之气”具有极为浓郁的禅味。当有人咨询孟子的“夜气”之说时,他却谈起了他与朋友僧寮夜谈的体验。“时春雪生寒,僮仆静默,因诵王摩诘之语:‘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真当日事也。久之,雨声暂歇,宾主嗒然;茗冷灯残,形骸忽废。故知善言未发者,无如孟子矣⑭。”夜谈发生在僧寮参禅之地,所诵王维之语又禅意充盈,其所谓“雨声暂歇,宾主嗒然;茗冷灯残,形骸忽废”也是一种禅定体验。焦竑认为此时就是孟子所说的“夜气”,也即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时的状态。
焦竑对《孟子》的佛学解读,与《论语》与《中庸》一样,非常强调对执著的破除,将没有任何执著视为圣贤境界的基本特征。
焦竑对四书的诠释,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大异其趣,因此他对朱熹在解经中囿于儒佛之辨深致不满。他说,“朱子解经不谓无功,但于圣贤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语,辄恐其类禅,而以他说解之,是微言妙义独禅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⑮。”在他看来,“夫道,一而已。以其无思无为谓之寂,以其不可睹闻谓之虚,以其无欲谓之静,以其知周万物而不过谓之觉,皆儒之妙理也。”可以说,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一方面将佛教思想纳入到对儒家四书的理解之中;另一方面也将儒家四书置于佛教义理的视野之内。他打破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壁垒,给人类的思维活动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