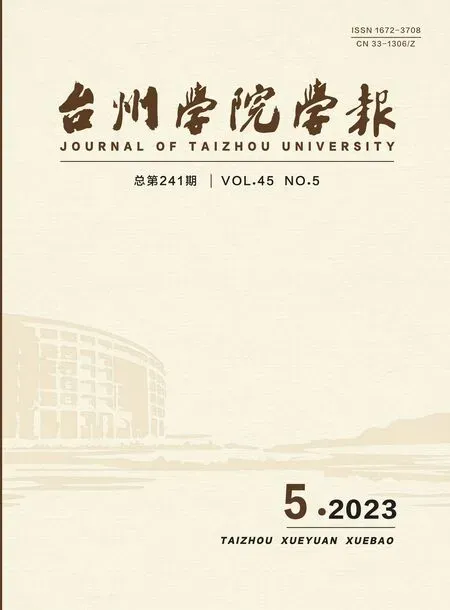戴复古诗歌中的理学色彩
贾先奎,盛凤娟
(1.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公共教学部,山东 菏泽 274000 2.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课教学部,山东 日照 276826)
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虽终身布衣,但诗名显扬,生前作品已多次被人编集刊行,一时名流贤士如楼钥、真德秀、刘克庄、吴子良等十数人纷纷为其诗集作序跋品题。包恢称其“以诗鸣东南半天下”[1]12,姚镛赞其“以诗鸣江湖间垂五十年”[1]18。戴复古一生广泛向前人和当时大家学习,学晚唐、学江西、学“四灵”、学杜甫、学陆游,集各家之长、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赵以夫评价为:“诗备众体,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1]13宋世荦评之为:“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2]陈衍《宋诗精华录》甚至推之为“晚宋之冠”,对戴复古的诗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戴复古一生历经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数朝,正是理学之风弥漫朝野之时,尤其是其成年之后,理学正当极盛。理学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和官方意识形态,几乎渗透到一切文学艺术领域,其思想价值和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出现了一大批理学诗人,而且弥漫和笼罩当时整个诗坛。观石屏一生经历,漂泊江湖数十载,交游官宦名士数百人,其中多有理学之士。如陈宓、赵汝腾等人是朱熹门下弟子,谢光中是吕祖谦好友,王埜师从真德秀,包恢出身理学世家,巩丰受业于刘安世。石屏少游于吕祖谦之门,又曾从朱熹学。石屏与西山先生真德秀尤其相交深厚。真德秀作为思想权威、台阁要员,其立德立功立言,深受石屏敬仰推崇。石屏不但多次登门拜访,而且屡屡赋诗投献,其现存诗词中尚有多篇与西山往来酬唱之作。如其《小孤山阻风因成小诗适舟中有浦城人写寄真西山》:“群山势如奔,欲渡长江去。孤峰拔地起,毅然能遏住。屹立大江干,仍能障狂澜。人不知此山,有功天地间。”此诗以小孤山为喻,赞颂真西山声望和功绩,寄予着诗人对他力挽衰颓国势的殷切期待。此外,石屏“登三山陆放翁之门”,作为陆游弟子,深受陆游诗文中的明道、养气和道德品格等深具理学意味思想的影响。综合以上因素,理学这一时代思潮,深刻影响了戴复古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纵观其现存近千首的诗词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理学色彩和理学意味,在江湖诗人中是非常典型的。
戴复古诗歌的理学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理学思想为旨归,直接表达理学见解
理学从根本来说,追求的是一种对宇宙人生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认识与把握,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体道悟理,明察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包含宇宙自然的存在运行法则,人类社会的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等,即朱子所谓“天理流行,触处皆是”,从而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心与理一、天人合一、天人一理的状态,最终成就仁者胸襟、圣贤气象,而诗文创作只不过是体现天理、性理、道理的手段和途径。因此,程颐曾批评杜甫的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说:“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3]认为它专务章句而有碍于道。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4]真德秀也指出诗文创作目的在于“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5]859。对于理学家文道一体、以文贯道的创作理念,戴复古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并接受的。其《谢东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其一云:“诗文虽两途,理义归乎一。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本朝师古学,六经为世用。诸公相羽翼,文章还正统。晦翁讲道余,高吟复超绝。”总结诗文创作之源流变化,强调要本之于“义理”,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学对儒家道统的承续,对朱熹富有理学味道的诗歌给予高度推崇。其《论诗十绝》之五又云:“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提倡诗歌要着意于吟咏性情之正,实际上就是在诗歌中要以伦理道德作为对社会人心的规范,将阐发义理、有益教化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目的——这也是理学对传统儒学诗论的一种超越,认为单纯追求言语奇绝、吟风弄月的诗歌缺少社会实际价值,乃是无用之诗。戴复古的这些诗学观点与理学家几无差别,可以看出他是赞同诗文创作要“贯道”、以理学思想为旨归的。
戴复古的诗歌中,有不少诗篇是直接阐发理学思想的。这类诗歌即便放置于理学诗人中也无甚区别,几可称之为理学诗。如《题胡立方思斋》:“每事再思过,参之以古今。唯求合天理,毋妄用吾心。”阐发躬身自省,凝心静虑,体悟天理的思想;《萧仲有遗经堂》又云:“一经传世宝,说与子孙知。欲作久长计,毋忘礼义为。”指出儒家经典、理学思想对家族兴衰存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遵从儒家礼仪制度方可保家族长久;《次韵胡公权》云:“日用无非道,人心实在平。果能行实学,何必问虚名。”揭橥理学日用即道,重实践,勿求虚名的观念;又如《寄清流王令君》:“朴直存吾道,一心唯向公。”《代书寄韩履善右司赵庶可寺簿》:“穷通安我命,一笑且持觞。”《雨后有感》:“天地有常理,古今无限情。”抒发持敬守正,正心诚意,洁身守志,天理恒存的思想;此外,《都中次韵申季山》“诗书岂为功名重,轩冕何如道谊尊。”《倚楼》:“贤愚不同道,用舍要知机。”《赠郭道人》:“灭性能安乐,深居绝是非。”也都反映了安贫乐道、淡泊名利、明于取舍、知足安命的人生态度,体现出自北宋邵雍以来理学为人处世的价值理念。
戴复古的这类诗歌作品,虽然阐释理学思想、体现人生哲理,有一定的内涵深度,但是从诗歌本身而言,由于过分追求理学思想的表达,议论较为刻板生硬,导致诗歌缺乏情感共鸣和生命律动,损害了诗歌的审美意味和艺术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理学的附庸[6]。这一现象,在江湖诗派,在整个南宋诗坛,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刘克庄在《吴恕斋诗稿跋》指出:“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7]其《竹溪诗序》又批评说:“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8]虽主要在于批评理学诗人,但包括戴复古在内的不少江湖诗人作品,也同样带有这种堆积理学术语、表现理学说教的弊病,读之令人不免生厌。
二、反映性情品格追求,蕴含丰富理学意味
宋代士人特别重视心性修养和道德人格。理学所提倡的正心诚意、格物明理,实质就是通过节制人的感性欲望,实现对天理、性理的自觉,在道德实践中强化个人自律,严守社会伦理规范,涵养中正平和的修身境界。理学的这种追求,成为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正统思潮,影响到众多诗人群体。周裕锴指出,宋人认为诗歌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为政治功能,包括由上而下的‘教化’与由下而上的‘讽谏’;其二为道德功能,包括体悟形上义理的‘明道’与表现人格精神的‘见性’;其三为心理功能,包括化激动为平和的‘自持’与化悲怨为旷达的‘自适’”[9]。就戴复古的诗歌而言,由于其江湖诗人的身份地位和经历,这三个层面中,诗歌教化讽谏的政治功能虽有一定体现,如忧时伤国、关心民瘼等,且历来对此多有论者;但整体来看,其“明道见性”的道德功能和“自持自适”的心理功能则更为突出。本文上部分所述石屏对理学思想的直接阐释,即属于体悟形上义理的“明道见性”。此外,戴复古更多的诗歌作品,则并非直接阐释天道义理,而是在写景叙事、生平经历、酬唱往来中反映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性情品格和道德追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学意味。
(一)安贫乐道、从容达观的处世态度
理学以体悟天理、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最高追求,而对于功名富贵概不放在心上。理学家认为,无论是困境还是显达,都不应穷愁牢骚或者自鸣得意,而要看破荣辱得失,除私欲,得和乐,保持情感的克制和规范。周敦颐令弟子寻孔颜乐处,二程讲曾点气象,皆是此类。《朱子语类》指出:“人之所以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10]1299真德秀《题黄氏贫乐斋》有句云:“濂洛相传无别法,孔颜乐处要精求。”[5]121观宋代文人士大夫,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二程、朱熹等,对于人生仕途的出处进退大多看得十分洒脱淡然,往往视功名如敝履,等富贵犹浮云,而对于前代屈原、韩愈、柳宗元等人动辄发愤世疾邪、失意牢骚之语颇有微词。应该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乃是理学逐渐熏染而成的一种社会文化风气,只要胸中充斥着义理之乐,就能够存心养性、安贫乐道,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戴复古尽管一生布衣,游食江湖五十年,有时甚至不免穷饿困窘,但诗歌中几乎始终表现出理学所倡导的穷达任性、洒脱从容的人生态度,保持了一种安贫乐道、宠辱不动于心的心境,具有冲淡平和、体格纯正之气象。其《曾景建得罪道州听读》一诗有句云:“饱参一勺濂溪水,带取光风霁月归。”濂溪是理学宗师周敦颐所居之所,黄庭坚《濂溪诗》序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戴复古此句借劝慰好友曾景建,表达了洁身守志、不因贬谪而悲怨愁苦的洒脱襟怀;其《题蔡中卿青在堂》:“几人富贵不能闲,夜运牙筹日跨鞍。役役一生忙里过,不知屋上有青山。”通过对富贵与闲逸的对比以及富贵不如闲的结论,体现出诗人安贫乐道、不慕富贵荣华、追求闲逸无束的人生态度;又如其《饮中达观》写道:“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寄上赵南仲枢密》:“贵为公相不如归,一夕飘然去不知。乐在五湖风月底,扁舟载酒对西施。”这种对人生出处进退得失的达观,怡然于饮酒读书、安于平淡的自在逍遥,显然是理学穷达任运思想的体现;再如其《和高常簿暮春》写道:“闭门读古书,聊以道自怡。桃李春盎盎,风雨秋凄凄。于春何足喜,于秋何用悲。”诗人在景物季节的变化中体会到天理生意之生生不息,无须因此或悲或喜,体现出一种摆脱功利目的后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这正是悟道之乐。戴复古有一首与白居易诗同名的《琵琶行》:“白乐天,白乐天,平生多为达者语,到此胡为不释然。”批评白居易愁思郁郁、作儿女态,心胸未免失于不通达。他批评说:“弗堪谪宦便归去,庐山政接柴桑路。”如果不能忍受仕途失意,何不挂冠而去呢!
基于这种安贫乐道、不甘拘束的心态,戴复古对隐居避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其《寄上赵南仲枢密》:“早向急流中勇退,归来闲伴赤松游。”表明了明哲保身、知足知止,早早舍弃功名富贵的思想;《题分宜县呈石子和知县》:“流水心何急,高山意自闲。”《舂陵山中》:“繁华凋性命,寂寞可全真。”正所谓心慕高山流水,意在保性全真;其《豫章东湖避暑》句云:“以我一心静,参他六月凉。渊明知此意,高卧到羲皇。”《阅世》:“自甘韬遁陶元亮,不爱赢余马少游。”这些诗歌,可以看出诗人意图效仿陶渊明避世隐居、甘于清闲寂寞的思想。事实上,不仅仅是戴复古,宋代尤其是南宋士人群体几乎无不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不但学习其作诗风格,而且效仿其处世态度,朱熹本人就有多篇诗歌表达对陶渊明的倾慕。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陶渊明的隐居避世适应了他们在国势江河日下时的心理需求;二是因为陶渊明的思想契合了理学家安贫乐道、摆脱尘俗势利的观念。因此,戴复古感叹说:“平生任达陶元亮,千载神交共一杯。”要看到,戴复古对陶渊明等隐居高士的追慕,与道家思想的隐居出世、忘怀世情非常契合,但这里又并非仅仅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许总曾指出,理学是统合儒道释文化观念构建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11]。自“北宋五子”以来,理学家多用以道入儒、儒道混融的方法构建理学宇宙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道家思想的不少内容被理学吸收为自身的营养。戴复古的这些诗歌,实际上在隐居避世之中又增含了一种体悟天道天理的追求,对陶渊明等前人隐世避居的心境与诗境有着自觉的超越,在诗学特色与文化意蕴上有着一定区别。
(二)清介自守、独立自持的心性品格
理学家将《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视为源自尧舜禹等古圣先贤的真传,认为“道心”即是天理,“人心”即是人欲,仁义礼智之心亦即“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便是道心。道心得于天地之正,发于义理之公,是至真至善至美,所以要体悟道心,必须持敬、涵养、省察、克治,培养主体坚定的道德信念、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性。自然,也就必须去私、去伪,积极发挥主观意志力量,立身、立志、立节,不因外部环境压力或诱惑而改变自己的良知、操守、品德和气节,凸显人性的庄严和道德的崇高,以敦化社会风气、劝勉世道人心。张载讲:“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12]130朱熹讲“学者要立大志”,循正道而行,陆游认为要涵养道德气节。这些思想,无疑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的普遍观念。
江湖诗人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经常耽于衣食名利之困,所以其中很多人把诗歌作为工具干谒权贵以求名利,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方回《瀛奎律髓》曾对此批评说:“盖江湖诗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13]对石屏也有微词,但石屏与其他一般江湖诗人尚有不同,其性格中本来就有“负奇尚气,慷慨不羁”的一面[1]3。石屏奔走江湖数十年,常怀厌倦之意,对游走公卿之门谋取利禄怀有悔吝之心,其《庐山》诗云:“老夫甘作无名者,不逐纷纷举子忙。”《衡山何道士有诗声杨伯子监丞盛称之》云:“自陶性情乐天真,一心不作求名计。”心声剖析得很明白,要保全性情之真,不愿求仕求名求利屈身事人。他“于广坐中口不谈世事”,出言严谨,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竭力保持一种清介自守、不甘屈身的心性品格。其《岁暮书怀寄林玉溪》有句云:“假合非吾道,幽栖了此生。”《饮中》诗云:“布衣不换锦宫袍,刺骨清寒气自豪。”不愿为功利而放弃尊严低声下气迎合权贵,宁愿布衣终老而以清寒自傲,于此可见其风骨;《都下书怀》写道:“读书增意气,携刺减精神。道路谁推毂,江湖赋采苹。从来麋鹿性,那作帝乡人。”诗人对干谒权贵感到屈辱自咎,损减精神志气,清醒地意识到江湖才是自己的归宿,并努力保持自己麋鹿一样的自由本性,坚守自己的品格操守。
事实上,石屏一生虽然交游良多,中间也不乏权贵大臣,但以道义以诗文相交相知者多,而以投献干谒相识者少。其相交者,有楼钥、真德秀、刘克庄、严羽、姚镛等名达贤士,至于像其他江湖诗人逢迎干谒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贵,则极少来往。其同乡林璧甚至有“怕得公卿知姓名,扁舟棹月过湖城”之句,赞颂石屏之风范。其《感寓三首》之二:“谊利不同道,盛衰何用疑。布衣甘寂寞,纨袴自矜持。”之三:“自觉心无愧,何须座右铭……菊花香到死,不肯就飘零。”均反映出其心怀道义、甘于贫贱、独立不移的道德操守;再如其《西江月·宿酒才醒又醉》一词下阕:“过隙光阴易去,浮云富贵难凭。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无名百姓。”这洒脱的一笑,尤可见诗人虽一介江湖布衣却傲对公卿、蔑视权势的品格。
(三)悠游泉林、静养其德的自得自适
理学着重格物穷理,以为万事万物莫不是生生不息流行运转之天理的具体体现。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10]499又说:“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天地之化流行发见。”[10]4439其《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诗作便是如此,借吟咏自然景色来寄托哲理,历来广为传诵。在理学的影响下,诗人往往寄情山水,“登山水以触发道机”,在实现天人合一、物我两谐的过程中,借吟咏自然物象来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体现自己从中感受到的理的启发。
戴复古的诗歌中,许多正是其悠游泉林、在对自然风景的描绘中寄寓理学人生志趣的,诗人在山水田园中时时处处感受到了浓郁的诗意,展现出一种去欲还本、自得自适的心境。如《麻城道中》:“三杯成小醉,行处总堪诗。临水知鱼乐,观山爱马迟。”《雁山罗汉寺省王总干之墓待和甫主簿之来》:“山鸟怪儒衣,游山我亦痴。叫云云不应,问水水相知。俗物刺人眼,春风发我诗。”山川入目,鸟兽有灵,美丽的大自然激发诗人的诗情诗意,这诗情诗意之中,更蕴含着对生生不息之宇宙万物的体察觉悟。又如《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时节,气候适宜,诗人游园醉酒,怡然自得,但这种愉悦比较温和,情绪有所克制,既不过于激动兴奋又悠婉不尽,可见诗人自持自足的情怀。
理学自周敦颐以来特别重视静养功夫,周敦颐谓“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之本,在于静虚”“圣人以主静立人极。”程颐认为:“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因此吕思勉认为,“主静”乃周子之学脉[14]。柳诒徵也指出:“盖宋之大儒,皆尝从静养中作工夫。故其所见所证,确然有以见万物一体,而有无朕无形、万化自具之妙。”[15]戴复古的诗歌,深受理学“心源澄静”思想的影响,特别追求这种静虚的精神境界,如《处世》诗云:“风波境界立身难,处世规模要放宽。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认为处世应超然泰然,何须奔波劳碌,虚静方能养身;《久寓泉南待一故人消息桂隐诸葛如晦谓客舍不可住借一园亭安下即事》:“昨日看花开,今日见花落。静中观物化,妙处在一觉。委身以顺命,无忧亦无乐。”诗人以理观物,静悟宇宙人生,内心宁静淡泊,体会到一种顺应天理、万物自化的超妙境界。
戴复古诗歌中这三个方面,虽然体现理学观念,但不涉理障而理在其中,于写景状物中自然而然让人体会到意境、情感之后的深层意味,景情理融合,故而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这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16]228理学与诗艺完美结合,使“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论,所谓冥合圆显者也”[16]231。正是石屏这样的创作特点,使他与一般理学诗人以及其他喋喋于义理性命之末流江湖诗人区别开来,艺术成就大大跃升。
三、诗歌风格平淡质朴,体现理学为文特质
宋诗自梅尧臣、欧阳修以来,特别注重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梅尧臣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苏轼倡导自然成文,力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境界;黄庭坚指出为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平淡而山高水深”。可以说,平淡平实平易是宋代诗歌的整体美学风貌,这一风貌的形成虽然有时代、社会以及诗歌自身美学风范变化等多种因素,但理学作为宋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主流,在较大程度上是造就这一风貌的根本底色。理学家文以贯道、中正和乐的思想,在创作中体物说理的理性思维与平和心境,自然而然地易使诗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上倾向并呈现出平淡自然的特点,如张载认为:“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12]256朱熹也指出:“平易自在说出底便好,说出来崎岖底便不好。”主张作诗应从胸中自然流出,不费安排。戴复古的老师陆游也曾高度推崇梅尧臣诗歌的平淡之美,反对江西诗派的雕琢。
戴复古对于诗歌,亦以平淡为宗,提倡朴实自然,反对浮华雕饰。其《论诗十绝》虽有“玉经雕琢方成器”之句,但实际上提倡的是作诗要用心,反复修改,并非提倡辞藻华丽。其《栗斋巩仲至以元结文集为韵》:“文章自一家,其意则古甚。大羹遗五味,纯素薄文锦。”赞美元结之文古朴不事雕琢,就如肉汁不和五味,素锦不饰文彩,明确地提出了以平淡质朴为美的诗学观点;《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举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望江南》词云:“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明确反对雕琢为文、堆砌辞藻,表达出对西昆体的否定以及对贾岛、杜甫的赞赏,可见其对真朴自然风格的追求和对浮华诗风的摒弃;其《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有云:“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澹,等闲言语变瑰琦。”对其师陆放翁高度推崇,认为放翁的诗歌虽平淡而瑰奇,乃是入妙文章。
戴复古的诗歌多用白描手法,较少用事用典,甚至用口语、谚语入诗,包恢称之为:“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1]13如其《洞仙歌·卖花担上》:“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以清新俚俗的语言和素描手法对重阳节风光进行了描绘;又如其《山村》:“雨过山村六月凉,田田流水稻花香。松边一石平如榻,坐听风蝉送夕阳。”景物描摹如画,意味隽永,清新自然,富有田园生活气息,乃是上佳之作;又如《九月七日江上阻风》:“云山多态度,水月两光华。白首吟诗客,青帘卖酒家。”《九日》:“黄花一杯酒,白发几重阳。”等,皆自然平易、明白如话而生动有味。同时代的姚镛评价为:“天然不费斧凿”;吴子良称:“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斫。”[1]10真德秀《石屏词跋》云:“戴复古诗词,高处不减孟浩然。”[1]15均指出石屏之诗具有古朴平淡、大巧不工的艺术风格。朱熹门人赵汝腾为《石屏诗集》作序说:“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1]8不但指明石屏之诗具有平淡质朴、自然流畅的风格和情感克制内敛的特点,而且指出这种风格和特点符合理学内在的宗旨要求——“尚理”,这正是石屏诗受到理学影响的体现。
不过,由于过于追求这一风格,戴复古的一些诗歌不免平淡过分而失之于俚俗。如《何季皋司理故人也作诗见相勉意二首》:“持身宜洁白,事上莫依阿。话别无他语,留心政事科。”《懒不作书急口令寄朝士》:“老病懒作书,行藏诗上见。一心不相忘,千里如对面……一愿善调燮,二愿强加饭。三愿保太平,官职日九转。”等等,虽是应酬之作,未免过于直白粗俗,失去了诗歌的美感。与其同时代的刘辰翁曾经就此批评过戴复古的“俗”。贺裳《载酒园诗话》也曾批评戴复古“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之句“酸陋”,认为是“村儿之语,徒供后人捧腹耳”[17]。方回《瀛奎律髓》评价石屏诗“苦于轻俗”。翁方纲《石洲诗话》评价说,石屏诗“纯任自然,则阮亭所谓‘直率’者也”[18],这个“直率”或不全是褒义。王永照指出,江湖诗派如戴复古等人贪多务得,“多率意粗率之作”[19]。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宋代理学重道轻文、不汲于辞、过分追求平易而导致的后果之一。
结 语
总之,作为南宋江湖诗人的代表,戴复古诗歌中的理学色彩反映出在理学风气笼罩下的南宋江湖诗派乃至南宋诗坛的某种普遍诗歌特色。理学家包恢于淳祐二年为《石屏诗集》作序云:“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来。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远,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备于经,经明则理明……故其为诗,正大醇雅,多与理契。”[1]12他认为戴复古的诗歌“主理”“尚志”“贵真”,体现性理之正,反映性情之真,其源来自理学,其“正大醇雅”之风格与理学追求一体,准确指出了戴复古诗歌中鲜明的理学意味和理学色彩。石屏自己也明确意识到“本朝诗出于经”。张宏生认为,这是戴复古“对宋诗的伦理教化、反映社会内容的品质的认可”[20]。显然,正因为戴复古对理学的主动选择和接受,在其诗歌创作之中,才会在多个层面体现出如此鲜明丰富的理学色彩。
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戴复古的诗歌虽然深受理学影响、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但却并非纯粹是理学的附庸,其人也不属于理学诗人。其《论诗十绝》集中地反映了他追求雄浑、创新、自然、直抒胸臆、重视苦吟、诗句丰满等多方面的诗学主张,其诗作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尤其是伤时忧国、关心民瘼、羁旅穷愁等诗作,风格近承放翁、远绍杜甫,继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体现了对压制情感、限制诗歌表达的理学诗论的突破与超越。故石屏之诗虽多理趣,但不可谓为理学所囿,前人对此已多有阐述,本文不再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