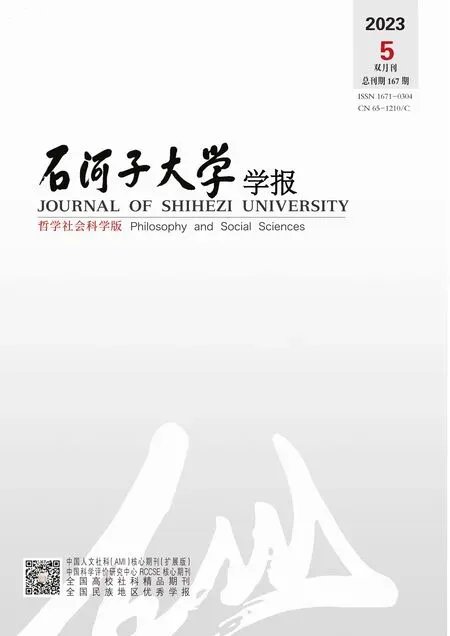论章德益的诗歌创作及其流变
胡新华,李倩倩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作为当代诗坛重要的诗人之一,章德益从事诗歌创作迄今已逾40 年。通常,我们对章德益西部诗歌的研究,关注诗人20 世纪80 年代的诗歌创作居多,将他定位于一位描摹西部景观、歌唱开拓精神的新边塞诗人,这些书写内容自然是其在诗坛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时代语境的影响、诗学理念的变化以及个体经验的丰富,章德益的西部诗歌创作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80 年代的创作,章德益以新边塞诗的现实性书写为主要呈现形态,着眼西部环境,摹写典型意象,诗艺尚处于探索的初期。随着新边塞诗的式微及诗人离开新疆、返回上海,20 世纪90 年代后章德益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对自然的描摹开始走向经验的书写,其书写方式也适时调整,整体倾向于超现实主义,展现出与前一阶段诗歌新异的艺术特质。2010 年以后,步入晚年的章德益虽然延续了对西部自然的关注,但与其早期诗歌创作相比,有意淡化了对景物的单纯复现,以温情脉脉的回望视角抒发自身情感;同时抽离于风景之上,从更高层面对西部、对人生展开哲学性思考。因此,以发展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位创作不断变化和精进的诗人,分析不同时期其诗歌创作特点,可以较为深入地把握章德益创作的总体风貌,较为全面地建立章德益西部诗歌的整体发展印象。
一、时代精神与边塞吟唱
我们知道,章德益是作为上海支边青年于1964年奔赴新疆的。来到新疆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从事农垦劳动,后又担任宣传队编剧和代课教师。1966 年章德益开始诗歌创作,1980 年调往新疆文联,与杨牧、周涛等诗友一起,竖起新疆 “新边塞诗” 的猎猎风旗,成为著名的 “新边塞诗三剑客” 之一,并由此开始了他坚韧豪迈、激情澎湃的西部写作。
在《大西北与诗人之魂》一文中,唐晓渡这样评价道: “章德益是个大幻想家,哪里有他的诗出现,哪里就迸出惊奇;而你读他的诗,最使你印象深刻的,也肯定是那些雄奇峭丽,飞落天外的想象”[1]153。诚如斯言,只要阅读过章德益1980 年代描写西部的诗歌,就很难不为其瑰丽而奇峭的想象所倾倒;并且与同为新边塞诗人的杨牧、周涛相比,章德益更 “醉心于制造奇特的意象”[2]171,其诗歌也更加充满着精彩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以至在以往的研究中,章德益的创作被评价为 “奇思妙想铸新诗”[3]134,或者干脆称他是 “一个典型的浪漫派诗人”[4]243,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应该看到,章德益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现实的方式来反映西部的,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他使用浪漫手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诗歌能够更加现实,将现实主义进一步审美化。因而,这仍属于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本位的诗歌创作[5]187。正如诗人在诗集《大漠和我》的 “集后” 中谈到的: “十几年前,我从上海来到新疆。那时,我充满了年轻人的幻想。幻想,是最容易与诗结缘的。于是,我与诗结识了,介绍我们结识诗的是瀚海,是天山,是篝火,是镢头,是青春,是理想……”[6]37在这段话中,章德益虽然指出了幻想与诗歌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究其根本,他之所以充满幻想并开始诗歌创作的原因还是在于瀚海、天山、镢头和篝火,在于西部边塞这片广袤而崭新的天地,其触发性的因素都源自现实,而这就恰恰表明,章德益从事创作的艺术态度是 “缘事而发” 、基于现实的。
研读章德益的新边塞诗作品,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就如同一根思想的红线,牵绕着他的整个诗歌。而当我们剖析章德益诗歌中这种现实主义表达时,就必然会发现其是以激情、高扬的时代精神为核质的基本构成。谢冕曾说,新边塞诗歌之所以拨动了我们的心弦,是由于 “在它特殊的艺术创造中传达了鲜明的时代共振的脉动”[7]102。这一确切的描述,不仅揭示了新边塞诗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且道出了其深层的现实意义——对时代精神的直接呼应和对现实使命的自觉把握。新边塞诗虽然可以说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诗人创作的边塞题材的诗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具体考察新边塞诗的生成,又俨然是章德益等诗人所处的20 世纪80年代的产物。1980 年代初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期。在经历了 “伤痕” 与 “反思” 之后,人们期待民族的复兴,期望能够拥有奋进进取的力量。作为一个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倾向的诗人,章德益始终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社会生活,将自我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在《我自豪,我是开荒者的子孙》一诗中,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诗句: “我蔑视,以一己胸怀作生命耕耘的田园/ 我蔑视,以三寸目光作灵魂之犁的绳纤/ 呵,耕耘着小小的悲欢,播种着淡淡的哀怨/ 这样的生命,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秋天/ 呵,人生之长,生活之远,/ 怎能把自己向隅而泣的影子,看作整个世界!”[8]4应该说,在刚刚恢复生机的新时期诗坛,章德益能够坚定而果决地写出如此激昂澎湃的诗行,是充满了豪情和勇气的。而这种自陈心迹的诗语,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位真诚关怀现实的诗人的操守,尤其表现了他对20世纪80 年代期待再生、崇尚恢弘的时代精神的深入理解。这是 “变革时期的社会素质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时尚”[9]56的集中体现,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当代色彩。
不过,章德益诗歌中这种时代精神的显现,并不是依据 “自白” 的方式直接点明的,而是经由对西部风物的吟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章德益非常注重表现西部的地理景观,在他的笔下,常常会出现高山、太阳、大漠等鲜明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意象。诗人通过对这些典型的西部地理意象的选择和书写, “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溶解”[7]102和寄寓其中,进而使得西部那些 “粗犷的、强悍的、坚韧的、乃至荒凉的、悲慨的一切” , “洋溢着当代人新的心灵渴望与吁求”[7]102。以 “高山” 意象为例,章德益偏爱大西北的山。在他的诗歌中,有很多关于山的描写,譬如诗作《山》,开篇用排比的句式描述了山的伟力,这是 “一种高踞太空的宇宙之力” “一派野性的狰狞” “一支向天空无限征服的力的军团” ,第二节顺势而下,描写了山辐射状的外观、线条的形状和铁青的颜色,第三、四、五节又用连续的排比句式描写了伟大的造山运动,说明了山之伟力的来源,它是 “以深陷造就崛起” “以深渊造就峰巅” ,最后一节再次发出了对西部山脉力量的慨叹:
真正的山/ 不是茸茸绿野上/ 那一抹青黛/一抹烟岚/ 而是赤裸裸的/ 力的暴起/ 而是蛮荒中崛起的/ 力的气概/ 而是险恶中雄峙的/ 气质的森然[8]92-93
在这里,诗人否认了青黛、烟岚这种对南国青山秀峰的想象,从他的用词,尤其是动词的使用, “暴起” “崛起” “雄峙” 可知,在他的眼中,西部的山是地壳无数造山运动造就的奇观,它冷漠而安详、高峻又伟岸,以自身的力量显示着自己卓越的存在。这种对西部山脉气概的直观描述,反映出西部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显示了诗人对一种绝对自然力的崇拜,进而暗示了诗人对 “蛮荒中崛起” 、打破一切束缚与禁锢,充满着力量与希望的精神的膜拜,契合了时代的主题。再如《西部山岳》一诗中,在诗歌首段,诗人先发表议论, “一切语言都只得在它的面前匍匐/ 只有它高踞云空/雄峙着西部的威严”[10]8,以无边的豪情直接奠定诗歌的基本气势,接着连续八个 “那是……” 的句式,激情澎湃、气宇轩昂,多层次的现实地描写了伟岸的西部山岳的气魄,这其中 “撑天的气概” “噬天的兽齿” “天地间蜿蜒” 等词语传神的使用突出了山岳的剽悍粗犷特点,一股雄浑刚毅的高山的气势从诗人的笔下扑面而来。然而诗人又不滞于写山,而是融进了现实的思索, “使一切匍伏者仰望/ 使一切攀援者振作” “哦,西部山岳/ 人类精神的山呀”[10]8,这段诗中的 “山” 显然不单指那种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而是它所象征的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在这里, “山” 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凝结和体现,显示了人类的尊严与信心,同时也成为了承载某种精神的载体,是时代开阔宏大情志的外在化、具象化。类似的诗作还有《大漠上的山》《天山的线条》等,在这些诗中,章德益都以 “山” 为媒,表现了时代特有的激情和壮丽。除山之外,章德益对太阳也颇为喜爱。在他看来,西部太阳拥有巨大的能量、崇高的理性,其 “包含深切的内心体验、蓬勃的时代情绪和明确的创造意识”[11]20。《西部太阳》等诗用急促的语气、强烈的气势,极尽太阳炽热、酷烈的特点,反映出诗人对壮大自我、寻求新生的当代精神的理解和追求。从高山到太阳,再到其他诗作中的大漠、绿洲等,章德益总能从代表性的景观中发现西部诗意的特质,展示西部独有的地域氛围与地理特征,同时又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对自然景观的赞美,而是在风物风习的外壳之下包裹着激昂的现实精神,从中我们能窥得20 世纪80 年代浓郁而深沉的时代光彩。
概言之,章德益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从整体上看是以现实为主要趋向。他在当代精神的表达与西部风物的描摹之间建立了某种平衡,使得新边塞诗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西部自然和景观的认识表层,还具有社会和时代所期待的崇高美和深刻的启示意义。而这也正是新边塞诗独特的历史价值之所在。然而必须承认,章德益的新边塞诗创作在后期已经出现了粗疏重复、表态叙说等问题。但伴随着理论素养的提高、生活经历的累积,他也逐渐突破了写作的瓶颈,迎来了自身西部诗歌创作新的阶段。
二、以梦写实和超现实想象
如果说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之前,西部作为章德益支边、工作的实践场域和生活背景存在,其诗歌主要表现为对山川风物的现实描绘和对时代精神的自发歌唱,那么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新边塞诗的落潮,以及诗人的离疆返沪,他的诗歌走向了沉潜和自觉。在《孤独是孤独者的宗教》一文中,沈苇指出, “西域风物、意象,是他细察内心、沉思世界的一种方式”[12],这句话提示我们,较之前一阶段,章德益的诗歌创作发生了转变。由于离开了新疆,此时的创作更多立足于作家先前直接或间接积累的西部经验中。相较于前,这样的书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是跨越地域和时空的,而这正是通过诗人对 “超现实主义” 的自觉追求和娴熟使用来实现的。
章德益很早就注意到了超现实主义,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他就已经明确表示, “我所追求的诗歌风格:正在追求中的是:把现实感受以超现实手法加以表现”[13]265。章德益那时的关注点主要是作为技艺的超现实主义,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创作追求,是由于受到了西方诗歌和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曾多次表达过自己受到外国诗人诗歌深刻的影响,他在相关随笔中直白袒露了对圣—琼·佩斯、聂鲁达、埃利蒂斯和帕斯等诗人的欣赏与喜爱。以上这些诗人尽管不都是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但其诗歌都不同程度地流露着超现实主义梦幻、华彩和奇崛的风采,体现了诗人在诗学追求上对超现实主义的自觉趋近。章德益对超现实主义更自主的趋向,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和他返沪之后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章德益曾在随笔《城市户籍》《动迁一念》中记录了自己返回上海的情绪体验,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 “在而不属于” 身份的悬浮以及 “归而不至” 的 “异乡” 漂泊感受。在生活和精神双重孤独和边缘的状态下,章德益不再拘泥于外部世界的外在表象,转而开始向更深的心理层面掘进。他与 “超越” 现实、注重内心探索的超现实主义达成默契,不仅使诗歌更多地 “回归自己的灵魂” , “更多的楔入自己的生命”[14]106,还因此萌生出 “做梦与冥想” 的创作方式,形成诗歌创作新的面貌。
“做梦与冥想” 是章德益 “超现实主义” 诗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所倚重的重要技法。他在相关文论中对 “做梦与冥想” 作了阐释:诗歌应该是现实性和梦幻性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现实的生活经历是诗歌的土壤,是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然而现实又是庞杂、功利,且缺少诗性的,如果仅以描绘现实为旨归,那必然是直白乏味的,因此诗人们应该要找到超越现实的方式,即 “做梦与冥想” 。章德益认为, “做梦与冥想也是诗人的一种内心状态与精神优势,是诗人介入世界与介入自身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深察岁月,深察生命,深察灵魂,有利于使自己介入现实与生命之间,介入世界与冥想之间,有利于自己在它们之间作诗性的多姿态的飞翔”[15]21。在他看来,做梦与冥想是沟通诗人内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不仅可以帮助诗人认识现实存在的本质,还可以通过梦的变形和冥思的幻化改变诗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更好地表现外在现实。章德益看重梦和冥想,他的很多关于诗的论述都离不开这一基点,同时他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创作的很多诗歌也多是以 “做梦与冥想” 为核心,不断书写和创新的。
先来看梦在章德益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呈现。我们知道,章德益是以支边青年的身份来到新疆的,在支边时期,他的生命精神呈现出雄壮、进取的姿态,其诗歌作品也显露出明朗刚健、激情豪壮的特点。而除了必要的激情以外,在章德益的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作为个体生命丰富的情感和体验。燎原在谈到章德益早期新边塞诗创作时试着针对这种现象分析了原因, “尽管现实生存进入他们情感的不仅仅是冲动的喜悦还有十倍于这喜悦的困苦乃至狞邪。但是那种劳动者诗意的青春晕眩,足以使那一切被消解,而达于暂时的遗忘”[16]92。燎原的判断是鞭辟入里的,然而 “暂时的遗忘” 并不等同于真正的 “遗忘” ,或者说当初的那份 “困苦和狞邪” 只是被诗人隐藏和压抑在潜意识中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意识中的内容,会在梦中释放出来。深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超现实主义也认为, “梦是人的思想得以自由表达的方式……使人最深层的欲求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17]111。因而,章德益在诗歌中就借由梦境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如《我在我漆黑的诗行里醒来》一诗,虽然诗作题目 “醒来” ,但实际上是在描写梦境和潜意识:在落叶飞尽的梦境, “苍鹭的回声” 满布, “涉水的红鹿一群群淹没” ,四十九朵犹如诗人四十九岁年龄的桃花依次飘落, “从光明里啄壳而出的黑暗” 在灵与肉之间肆意飞翔。接着诗人出现,他注目在他诗歌深处,一间滨水的木屋粼粼照亮, “一树桃花在黑水深处怀孕成/金鱼状的太阳”[18]51-52。至此,这首诗一直都在描述梦境抑或幻觉,各种景象变形、叠加在一起,呈现出一个虚拟的无理性的超现实幻境。然而尽管这一梦境显示的是无序的逻辑,但是结尾处的 “中年的血” 为看似神秘的梦附上了解读的密钥。原来在这首诗中,诗人是想借对梦的表现,用这种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人到中年之后灵魂的怅惘与不安。这种怅惘与不安与其他诗人诗歌中中年的感受不同,章德益是在经历了西部光辉的青春年代之后形成的,带有那种强壮的生命精神阶段性结束后的内敛与松弛。并且不同之前直抒胸臆的激昂、炽热的情感,在这里诗人以梦境的形式引向了内化沉淀之后的个人经验,表达了自我内心的真实。在此已经能察觉章德益诗歌书写方式和主导情绪的变化,而在《伤口》一诗,诗人将这种灵魂不安的生命经验表达得更加明显。 “爪子刨食心脏” “树叶” 长成 “眼睛” “黑柏枝” 点燃 “火炬” ,还有 “沉沦的红石头” 和 “兽语的太阳” 。比起之前的梦境,在这首诗中,诗人呈现了一个更不符合现实,更加抽象、诡谲的梦幻场景。然而表面上虽不能理清梦境的逻辑,但还是可以大致猜测引发这个梦境的源头,和章德益本人的生命经历有关。实际上,章德益是有意制造这种离奇、诡怪的梦境氛围,因为这个梦境本就是对青春年代 “伤口” 的变形投射,隐藏在其中的是诗人经历了飘摇坎坷的十年所形成的巨大的生命隐痛。诸如此类的还有《风暴》《梦中的镰刀》等诗。在这些诗中,他都对青年支边岁月进行了回首与指认。而这种种都源于诗人通过梦境对隐秘内心进行的追踪与探寻,它不仅在诗歌中生成了一种奇异变幻的模糊之美,还开辟了一条曲径,通往了诗人幽深的经验世界。
冥想是章德益这一时期超现实创作所使用的另一重要手法,也可称之为想象或幻想。如前文所述,章德益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在 “新边塞诗” 时期写下的众多诗篇就饱含着巧妙的联想和奇特的想象。超现实主义一开始也重视想象,然而与 “在事物表象属性相似相近的地方寻找落脚点”[19]58的一般想象不同,超现实主义宣扬想象的任意驰骋,不受批判精神的束缚,表现出一种超然于桎梏之外的神奇性。章德益这一时期创作的西部诗,就融注了超现实的想象,进而使得诗歌呈现出神奇超拔的效果。如《中亚高原》一诗:
中亚高原/幻灭的骑队已消逝于永远的尘土中/一支穿越蜃楼的幽灵大军/已消隐进 层层峰峦的/ 典籍中/ 落日依然如 铠甲/ 静静卸下 血浸的沉重/千山万水间冲天的晚霞/依然悲焚如马鬃/指向 历史的遗踪/只有年年呵 山脚下/怒放的野菊花是一朵朵/ 汗血马的胚胎 蜷曲于/ 蓝天的子宫中……[20]67
这首诗充分显示了诗人自由而奇崛的想象力。和之前取材于现实、用丰富的想象来突出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形象地表现西部自然地理风貌的诗歌不同,在这一时期,诗人不再满足于对已知事物的再现,而是通过一些未曾尝试过的意象组合,创造了新的艺术形象。西部高原是幻灭的骑队、是幽灵的大军,落日是铠甲、是悲焚的马鬃。在这里,诗人的想象新奇瑰丽,展现出了奇妙的异彩,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诗人将怒放的野菊花想象成 “汗血马的胚胎” 一句,这两个意象之间原本并没有必然的相似性,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比喻,则是因为野菊花怒放时蓬勃的姿态,和汗血马激情、昂扬的生命状态之间的联系,委婉地暗示了一股内在的生命力量,由此也显示出诗人极强的想象张力,形成一种动人的诗意。在早期的新边塞诗创作中,章德益多是以白描的手法描写山的线条、外观,将西部的山比喻 “大地的坚盾” “地球的鼓面” ,其想象有迹可循。而在《黥面的山》中,诗人把自然人格化,打破现实和幻想的边界,将山比作秦朝的死囚,天色比作狱卒,风声比成檄文,裸石比成闪电的骨头,意象之间的跨度极大,呈现出新异、奇丽的想象色彩。
事实上,在章德益的创作中,更多的还是运用超现实的想象,叩开早年西部生活的大门,传达自己的经验感受。在章德益的笔下,早年的草帽是被太阳疯狂 “抽吸的烟斗” ,知青一代人的血汁被抽吸成一缕缕虚幻的烟,至今还飘荡在 “我” 的记忆里(《早年的草帽》);早年的镰刀是在诗人汗珠里高飞的 “金属候鸟” ,带着三十年沉沉的往事迁徙降落在流过血汗的西部(《早年的镰刀);早年的篝火是一座熊熊的金字塔,里面龙钟的太阳如 “法老的心脏” ,主宰着 “黑纱的律动” ,时代所形成的 “日蚀” 裂变成一个疯狂的黑洞,飘满 “火与血的冤魂” (《早年的篝火》);还有描写早年八月劳作的夜晚, “汗珠叼着一轮一轮/ 月亮 在植物的皮毛里/ 疾跑 跌倒又爬起/ 镰刃上崎岖的道路/ 葬满 炼火与麦芒”[21]63(《在八月的夜战里》);描写早年间夜磨镰刀的景象, “陡峭的磨刀石下 雷鸣电闪/ 一滴汗水骑着月亮/ 下山去了 冒烟的月亮啊冒烟的/白狮子 千山万水间一条/ 镰刃的道路 上面飞满/麦芒的祭火与 血滴的烛焰”[22]55(《夜磨镰刀》)。在这些诗中,章德益都以超现实的想象将个人早年的西部体验融入诗中,以当下的视角回望了过往30 年的西部岁月,将一些看似毫无逻辑联系的形象或意象在诗中作了感性的抽象链接,增添了诗歌的意蕴和张力。
无论是以梦写实还是超现实想象,在超现实技法的使用下,章德益诗歌一方面情感更加细腻深沉,有了更多的个人色彩,能够更加真实且自由地表现自我的经验感受;另一方面,又区别于 “新边塞诗” 时期,呈现出新的美学特征,写的是西部,但又不完全是西部,显示出艺术特质的新变,诗歌进入到一个成熟开放的艺术创造阶段。
三、风景回望与哲学沉思
考察章德益的前期创作,20 世纪90 年代及新世纪以来无疑是他创作的重要时期,此时的他告别了 “青春写作” ,放弃了直白抒情,凭借先前不断积累的西部经验和逐渐孕育成熟的诗歌思想,创作出与20 世纪80 年代 “新边塞诗” 现实审美大相径庭的具有超现实意味的西部诗歌,凸显了自身诗艺的突破与新变。然而这一时期并不是章德益诗歌创作的终点,到了2010 年以后,章德益更是凭着自身丰富的艺术底蕴、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豁达的人生境界,迎来了西部诗歌创作新阶段。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西部生活,十余年的上海生活,章德益如今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晚年。美国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心理发展分为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晚年时期是一个自我调整和适应的时期,其面对 “过去的岁月和经历,走向死亡的必然性”[23]81,会呈现出晚年阶段特有的心理特征。对章德益而言,人生的余数意识是他晚年表现出的主要心理趋向,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余生的日子》《临终》《晚年印象》等能够明显感知到,苍老的迟暮之感氤氲在这些诗歌中,这是诗人对自己晚年余下不多时日的凭吊,亦有一种 “逝者如斯夫” 的凄凉。或许正是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处于正在消逝的余数状态,章德益叶落归根、皈依西部的情感油然而生,表现在创作中即潜藏在前期诗歌中的社会历史话语全部飘散,主要集中于表达自己早年游历的所见所感,抒发对西部山水的回忆和眷恋,并且也正因为这种渐趋高龄的消逝意识,使诗人在重温往昔的同时又增加了对人生与存在、对自我与西部关系的思考,写下了一些意蕴丰富的哲学诗篇。
在随笔《远眺伊犁 遥想诗歌》中,章德益表示,这一时期的创作素材是基于他1970 年代中后期为编选反映在疆知青生活的诗集,去伊犁和边疆各地走访的经历,之前 “想写,但又不敢写,也确实没有写过”[24]119。然而虽然没有写过,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但那份边疆自然风景带来的震撼和惊叹深深地影响着他。于是,晚年时期的章德益就通过诗歌对深埋在心底的边疆风景进行了呈现和还原。如《伊犁河小品》《回忆:伊犁新源深山杏花》《库尔德宁山谷印象》《昭苏一瞥》等就是描写伊犁景致的作品。这些诗的命名直接取自伊犁的各个景点,诗中的风景连缀起来就是一幅隽美的伊犁景观图:伊犁的河谷 “溪流松散像月亮的长辫子” ,满地散落的野花都是 “河川的叹息” ,河边饮水的马长鬃飘飘,似 “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在演奏/ 孤独的/ 吉他” ;河水潺潺,群鸟向山谷冲飞时,深谷里层层叠叠的云杉林拍溅响 “翠玉的涛声” ,头顶的雪峰 “缓缓膨胀” ,似一滴水滴 “装饰着梦幻的星空” ; “万里的夜空” “冷寂的银河” ,星光是婆娑枝叶上露出的音符, “空灵而澄明” “鸦影与霜影 雀影与树影” 随风摆动交相辉映;夜晚宁静,清朗的寰宇、平缓的草甸,清冷月光照耀下的昭苏草原 “呈现一袭 僧衣的蓝” 。在这些诗中,章德益使用大量细致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伊犁的风光景致。字里行间充盈着伊犁山水的轻灵俊秀,流露出诗人的喜爱之情。还有《秋天的阿勒泰》《在阿勒泰怀想柳宗元》等诗,在这些作品中,章德益同样用极细腻的工笔书写了阿勒泰金秋时节的绚烂沉寂以及冬日雪后万籁俱寂的景象,体现出诗人对西部深深地热爱和眷恋。而无论是清丽俊秀的伊犁,还是孤寂静谧的阿勒泰,从这些风景的描写中,我们似乎觉察到诗人又回到过去对西部自然景物外观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早年新边塞诗的一种延续。然而倘若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便会发现,与那些极具写实和象征意味的新边塞诗相比,章德益此时的书写更偏重自然、反对雕饰,他不再拘泥于对西部典型意象的复写和对地理特征的提炼,而是凭借自己的回忆去体悟、感受,重构一张张碎片,让西部的诗意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因为融入了记忆的 “回望” 视角,还使得他的书写带有淡淡的怀旧色彩,氛围温情,情绪舒缓,充溢着诗人对曾经造访之处最珍贵的情怀。
除却这些写景、抒情之作,章德益这一时期的部分诗作还透过自然流露出深邃的哲学性思考。晚年的章德益时常怀想西部,思索关于西部美的本质,他认为,西部之美不在于外在的自然景观,而应该是这些自然表象背后蕴含的美学意蕴和哲学意义,是有关于遥遥无尽的时间和空间的叙述、阐释和演绎。以《阿勒泰记忆》一诗为例,这首诗的传达,全是以西部自然景物构成的意象为基础的。诗歌的大部分,讲的都是自然生命的抒发,林蛙到湖边产卵、黑鹰向草原飞去、马儿在山谷里吃草、土拨鼠窥望星空、云杉林喃喃私语。然而 “人类的边界” ,建构了一个自由自为的空间,原来这些自然的事物都是独立于人世之外,在另一个无限开阔的空间中兀自生长的,结尾的一句 “已然亿万年过去/ 仿佛地球上什么都未曾发生”[25]115,又将时间定位到永恒,由此西部被放置到一个形而上的位置。即使万事万物在这块土地上不断生长与死亡,但西部就是西部,它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并以无穷限的时空意识和格局包容着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再如《深秋的草原》一诗,在诗歌的第一小节,诗人以设问开篇,提问在深秋的草原上,绿色和花朵、虫子和毡房都去向何处,接着在下一节中诗人给出了回答, “都被草覆盖 被草掩埋/被草吸收 在草的汁液里循环/在草的轮回中生死/在草的灰烬里湮灭”[25]115-116,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到,诗人已经不仅仅在写季节变换后的草原了,他是以季节的循环暗指草原的亘古不变。即使朝夕更替,但草原自成章法,它 “俘虏了炊烟 栅栏与摇床” “俘虏了新婚者的戒指与死者的马鞍”[25]116,它是一切事物的见证者和埋葬人。人类活着,是草的人质,人类死去,是草的替身,人世的沧桑变换和时间的切割划分在这里没有切实的意义,从中亦体现出一种永恒且永在的非线性的 “循环” 的时间观念。由以上两首诗的表达来看,诗人的着眼点已经不是地理学角度的西部了,而是从存在学角度深入思考,探究和阐释了西部的永恒本质,进而使得诗歌抽离于风景的定义,充满着哲学的意味。
事实上,章德益在阐释西部自然的永恒存在之外,还追问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那就是人类生命与西部自然的关系。在早年的新边塞诗中,章德益对自然的把握多表现为开拓者的激情,诗歌中充满了征服与改造,明显带有显示人类自身力量的意味。而在这一时期,随着生命逐渐步入杖朝,诗人对西部存在的永恒性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对人类关于自身过高的评价与估计也有了更清晰的洞察,于是他诗歌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譬如《回忆:昭苏高原》一诗中,诗人分别 用 “露珠” “尘埃” “松果” “蚂蚁” 和 “我” 进行对比,前者是何等微小的生物,可是诗人却说,他们比 “我” 有着 “更璀璨的光阴” “更古老的辈分” “更辽阔的宁静” 和 “更永恒的光阴” 。该诗使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表达了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当面对不朽的西部与自然,人类的个体生命不过如同蜉蝣,沧海一粟而已。《初春北地》一诗同样表达了这种意蕴, “远远 三粒马与一粒人/ 正在蹚过 夕光横流的/ 深水洼 溅起一片金黄/ 马影与人影/倒映在每一滴深蓝的雪水里/ 精美细致 竟像四只/ 刚刚苏醒过来的 宇宙之草履虫”[26]。这首诗虽然没有引入对比视角,但用了诸如 “粒” 和 “草履虫” 这类的词语, “粒” 是计量的单位,一般用来形容小的颗粒状事物, “草履虫” 也是一种体型微小的原生动物,诗人使用这样的词语修饰和形容人,意欲表达的是在永恒而伟大的自然的视野之下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审视和怀疑,显示了自身自然观的变化和成熟。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章德益 “超越了粗陋的利害之感与庸俗的功利之思” “扬弃了审美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具体的利害关系”[27]29,从更高的层面和角度观照和描写了西部。他在广博辽阔的景观中展开了对于西部自然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之归途命运等一些深刻而重要问题的不竭追问,从而领悟了万事万物存在的意义,在西部的坐标系中为自己绘制了一块心灵的版图。
四、结 语
在将近一生的西部诗歌创作中,变化似乎是章德益创作的主要特征。他从没有拘泥于某一固定的内容和方法,主题表现上不断进行着深化和拓宽,艺术特质方面也不断追求着丰富和拓展。然而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其创作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无论是早年的新边塞诗写作、转折时期的超现实诗学,还是晚期的哲理思考,在章德益的诗歌中,一直贯穿始终的是他对西部的坚守与热爱,是他对西部由衷的仰望与歌赞,这是寓于诗人创作变化中始终不变的本色,也是诗人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创作、坚持创新的动力源泉。
诚如艾青在《诗论·诗人论》中所言, “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28]68。倘若真有所谓诗神,那么对章德益来说,他的诗神一定是西部这块辽阔的土地。倘以十年为一代际,纵观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西部诗人群体阵容,几经更迭。与众多从事西部诗歌创作的诗人相比,尤其是与当时同属新边塞诗派的其他诗人进行比较,章德益的创作姿态显得尤为不同。他一直执着地走在西部诗歌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对西部诗歌的探索与书写。从这一层面来看,章德益可以说是一位逆着时代潮流,用生命坚持西部诗歌书写的诗人,并且不仅是在西部诗歌领域,就算放眼整个诗坛,章德益及其诗歌也是其中非常坚定而有力量的存在。他没有过多被社会、时代、市场等外界的声音掣肘,他所展现出的是不向世俗妥协的真诚而独立的创作姿态,他的写作仍然坚守着对艺术本性和诗性精神的追求。因此,从诗歌本体的层面,章德益及其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对20 世纪90 年代和新世纪以来诗坛的有力补充,其创作对于诗歌精神和审美品质的复归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