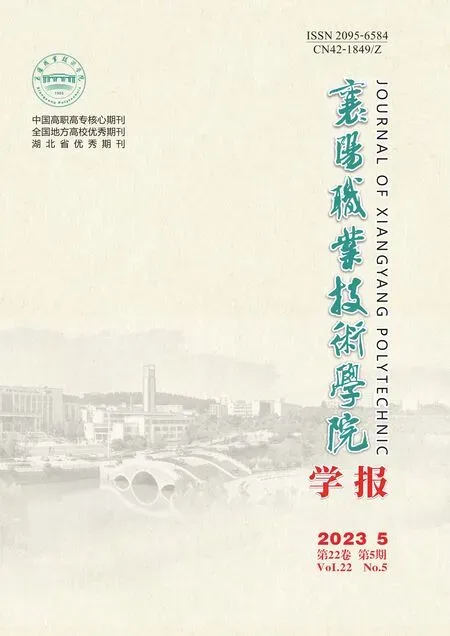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的创新意识
黄佳妍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南宁 530000)
王安石个人以及其作品都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学界大体更加专注于对王安石诗文的研究,对于其词作的研究则关注较少。王安石词作关注度较低原因之一在于相对于诗文创作而言,王安石并不重视词的创作。在《全宋词》收录的王安石词作一共二十九首,在数量上远不及其诗文的创作数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安石对创作词的轻视。另一原因则是在其词作中有两种类型的词作较有争议,即佛理词与集句词。相较于王安石词作中咏史词及其他抒情词作而言,其佛理词与集句词在艺术审美价值上普遍不如前者出色,但是这两类词作却展现了王安石词作中明显的破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对此后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王安石集句词体制的创新
集句是一种“改造型”的创作方式,而非“创造性”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形态是基于他人的作品内容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再创作。从狭义的文学创作定义角度出发,集句作品很难被归结为文学创作,因此也容易受到非议。集句这种创作方式并非自宋代而始,先秦时期亦有作品初见端倪,并且在此后的诗文创作中也屡见不鲜。清代梁绍壬于《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六集诗袭诗一条云:“鲁哀公诔孔子曰‘昊天不吊’,《节南山》诗句也;‘不慭遗一老’,《十月之交》诗句也;‘嬛嬛在疚’,《闽予小子》诗句也,说见《路史发挥》五,此当是集诗之祖。又‘毋逝我梁’四句,《谷风》《小弁》凡两见,可见诗人亦相蹈习,则曹孟德之‘呦呦鹿鸣’四句,其生吞活剥,有以藉口矣。”[1]从条目名“集诗袭诗”来看,梁绍壬将“集诗”等同于“袭诗”,认为曹操《短歌行》是对《诗经》的一种生吞活剥,这种对于集句创作方法和体制的否定和非议可见一斑。当代学者吴承学认为先秦时期的这种集他者语句而自成诗文的现象是“先秦时期赋诗明志、断章取义风气中悄然萌芽的……只是某种程度上暗合集句的形式而已”,而“西晋傅咸所作的《七经诗》是现存所知最早的集句诗”。[2]《七经诗》的内容皆摘儒家经典中的四言句,以韵加以编排,当中语句并无傅咸个人所作,从此模式上可以窥见起初的集句形态,即再创作者的个人创作部分甚微,更多是在以韵串句上进行构思,目的是言以载道,宣传儒家思想。可见早期集句作品仍然是一种有现实功用性的严肃文学。集句之风、集句之名皆起于宋时,《说郛》卷八十一引宋蔡绦《西清诗话》记:“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3]宋人标举的开端人物是石延年,此时宋人已经摆脱原本集句诗文言以载道的严肃目的,转而变为游戏的性质。王安石对集句形式的完成和创新,尤其是对集句词的创立成为一种共识。王安石首先将集句形式大量加入词的创作当中,有些词作与此前典型的集句型诗文在形式上高度相似,如《浣溪沙》一词展现出非常明显的集句特征。《浣溪沙》一词中每句皆有原句出处,且改动较小,仅第二句“门前白道水萦回”[4]在原诗句“门前白道自萦回”的基础上改动一字之外,其余句子皆保留诗句原貌,同时被改动的诗句也是荆公自作而非前人之作。这种保留原始集句风貌的荆公集句词仅《浣溪沙》及《甘露歌》其二,在其余的集句词中则展现出了更多新的样貌。
首先是增加集句词中的个人创作比例,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打破词作全词皆集句的整体构造;二是对所集句子进行个人的小部分改造。以《菩萨蛮》一首为例,整首词中借用了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韩愈《次同冠峡》和《南溪始泛》以及宋之问《灵隐寺》中的诗句。虽然从摘选诗句以及全词的呈现状态而言,王安石还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来字词的组合风貌,然而区别此前其他集句作品而言,其个人创作比例有了很大提升。在《菩萨蛮》一词的八个小分句中,集句部分是四句,集句比例与个人创作比例达到了一致,在《南乡子》一词中也是同样的比例。并且《南乡子》中“上尽层楼更上楼”[4]一句是对李商隐《夕阳楼》中“上尽重城更上楼”进行了更改,而非照搬原诗句的风貌。“层楼”与“重城”意义虽相近,但“层楼”更符合词牌音韵,且更有攀登楼上楼的登高之感。这无疑是作者用心之处,也是王安石将集句手法应用至词的适应性创新。二十九首王安石词作中也有非典型的集句词作品,即无完全搬用诗句,却保留句子基本句意和组成意象,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中“千里澄江似练”[4]一句改自谢脁“澄江静如练”一句,“门外楼头”一句改自杜牧“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末句“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一句改自“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种改动是为了使句意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词体,而非打破词的外衣去迎合古体诗与格律诗的样貌,但他依然能让观者感受到原句风貌的影响。尽管王安石对词须合乐而歌持反对态度,但从他对创作集句词及改诗入词的做法可以看出王安石并未完全否定词的创作。虽然其词的数量不及诗文,但在集诗入词中仍得见王安石对词基本创作规范的尊重。
其次从集句的选择对象上看,宋代文人是由儒家经典扩展到前人诗歌,而王安石则再扩展到前人词作以及本人作品。不仅扩展了集句的体裁,也扩展了集句作品选择的时代。如《谒金门》中“春又老”一句集自宋柳永词“看看春又老”一句;“遍地落花浑不扫”一句集自晚唐温庭筠词“帘外落花闲不扫”一句;“梦回情意悄”一句集晚唐冯延巳“情悄悄,梦依依”一句。[4]一首词中连集三首不同的词以成句,且皆收唐宋之作。此外在其诸如展现佛语禅理的词作中亦集取佛家经典语句,体现出王安石宽泛的集句选择面。王安石尤爱选唐诗,以中晚唐诗歌居多,这与其集句诗是相同的。王安石对杜甫、韩愈、刘禹锡及杜牧集作甚多,杜甫为先。王安石通过对杜甫诗歌的摘选改造,将杜诗中的家国风骨转嫁到词上,对其词作的整体风貌产生了较大影响,摆脱了词原先的软媚词风,抒写儿女风情不再是词的唯一表现对象。王安石词作中集有杜诗的词作分别有《清平乐·云垂平野》《浣溪沙·半亩中庭半是苔》《菩萨蛮·海棠乱发闲临水》,以及《甘露歌》其三。其中《菩萨蛮》一词集杜诗数量最多,分别集四首杜诗中的四句:词第三句“君知此处花何似”集杜诗《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九诗句;词第五句“啭枝黄鸟近”集杜诗《遣意二首》其一诗句;词第七句“随意坐莓苔”集杜诗《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诗句;词第八句“飘零酒一杯”集杜诗《不见》诗句。[4]杜诗中多种景色也是词人自己的亲身见闻,表现出事物永恒,人当泰然处之,一酒浇尽千愁的旷达。词作的风貌焕然一新,抛却了以往词作的闺怨柔情,又不同于《桂枝香·金陵怀古》中怀古伤今的悲悯怀世情怀,转而表现出文人内心所向往的潇洒自如。王安石集句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他创新了集句的创作方式,增添了集句对象,从而在保留诗词之别的基础上,扩大了词的描写对象,丰富了词作的整体风貌,是其文学创新的重要展现。
二、王安石佛禅词的内容创新
王安石创作的佛禅词一共是十一首,包含《诉衷情·和俞秀老鹤词》四首、《诉衷情·又和俞秀老鹤词》一首、《望江南·皈依三宝赞》四首、《南乡子·喈见世间人》以及《雨霖铃》,佛禅词数量占据所有词作近一半,可以看出他对佛禅主题的喜爱。这种喜爱在其诗歌创作中也可见一斑,但是就研究现状来看,其佛禅诗受到更多关注且评价较高。与此相反,研究者们对其佛禅词关注较少且评价较低,如李清照认为其令人绝倒,其余评价也多认为此类词作艺术价值较低,不过是借用词以宣扬佛禅教义。但王安石的佛禅词作为王安石词作的重要内容,其佛禅词也是王安石文学创新的重要体现。
首先是以禅典入词,即将佛学经典和禅宗经典中的语句直接运用或稍加改动为词的语句,正是前一节所论述的集句创作手法,如《南乡子·喈见世间人》中末句“幻化空身即法身”一句直接摘取唐代高僧永嘉玄觉大师的《永嘉证道歌》中“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5]后半句,其表达的内容都是在强调不要执着于外在的虚妄,执妄于个人无益,要自悟真性不变,表现王安石晚年心态渐趋平静的状态。相较于诗而言,这种集前人经典中的长短句的方法在王安石的佛禅词中运用并不多,王安石更多是将佛禅经典中的关键概念融入词句。如《雨霖铃》中写及“轮回”“明空妙觉”“缘”等,这些都是佛经教义中常见的概念,在此之前甚少被运用到词的创作中,这种尝试实属创新之举。《雨霖铃》可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相较于《南乡子》直接引用佛典,让人只有阅读佛经教义之感,《雨霖铃》在阅读时仍然能保留词的艺术美感。《雨霖铃》所选取的佛禅典故较为通俗易懂,也保留了传统词中的意象,如在描绘词人先前声色犬马的生活时写道那些都是“浮名浮利”,那“堪留恋处”无非是“贪他眼花阳艳”,而识破一切虚妄才能回归“明空妙觉”的空灵状态。
以禅理入词也是王安石佛禅词的重点,也是其佛禅词最普遍的一个创作手法。如《诉衷情》五首运用大量佛语佛典来阐释“过往不过云烟”的人生感慨,借此展现自我不愿为尘世所扰,追求闲心自性。《南乡子》也是将过往当作“幻”,强调个人要“除妄想”追求破幻求真,在语言上和佛典上极为相似,其表达的主题内容与《诉衷情》五首也非常相似。值得单独提出的是《望江南·皈依三宝赞》四首,词名上已有浓厚的佛语韵味,这是王安石仿效佛家赞歌宣扬佛理一种有意的词体创作。于诗而言,佛理入诗并非自宋而始,玄言诗在魏晋发轫,唐代王维也善于将佛理融于诗中,唐代更出现了大量僧诗。王安石在词中表现佛禅之理在北宋初期亦可称为创新之举,但其“以禅理入词”仍较为直接生硬,《望江南·皈依三宝赞》此类与佛唱高度相似的词作,使词与原貌已相去甚远,仅是保留了“长短句”的形式,反而是体裁的混淆,损害了词的艺术审美效果。
“以理趣入诗”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而王安石的佛禅词中亦有“以禅趣入词”。“以禅趣入词”与“以禅理入词”相比,“以禅趣入词”更强调“趣”的层面,强调生动传神地说明事理,而非直接说教。王安石“以禅趣入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说理具象化;二是保持词的协律可歌,避免晦涩无趣。这两个层面在《雨霖铃》一词表现最为明显,如“幸有明空妙觉,可弹指超出”一句中将佛理对人的超越作用以“弹指”形容,将不可眼见的佛法奥妙通过具象化的夸张展现出来。再如“缘底事、抛了全潮,认一浮沤作瀛渤”一句将变化无常的人间世事比作海水上易生易灭的浮沫,将佛法中“幻”与“虚妄”以泡沫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更具艺术审美感。王安石也保留了《雨霖铃》词牌协律可歌的特点,保留运用了叠字叠词,如“孜孜矻矻”“浮名浮利”“衹些些”都使词整体朗朗上口,与柳永《雨霖铃》异曲同工,吸收了柳词协律可歌的优长,使说理更添意趣。
综上而言,王安石的佛禅词如其佛禅诗一般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这都是对词创作的突破与创新。虽然佳作较少,难免有诸如《望江南》一般完全成为另一种“佛语赞呗”,失却词艺术特色的作品,但亦有如《雨霖铃》一般音韵和谐、通俗易懂且富有禅趣的作品。因此,评论王安石的佛禅词不能止步单独的批判或赞美,而应予以全面深度的挖掘研究。
三、王安石词作中的艺术创新意识
虽然王安石的集句词和佛禅词通常会因为其艺术价值较低而受到非议,但是这两类词作却能够反映王安石词学观念中的艺术创新意识。
王安石有明确的破体意识,从其集句选择的范围之广来看,王安石的集句词将传统的诗文、佛典和词都作为其集句的对象,展现了词的多种风貌,无疑对此后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提供了一个范本,甚至于词也有类似于佛语赞呗的面貌。从作词的目的性来看,突破了原先抒发美人闺怨柔情的功能。王安石的集句词以及佛禅词中很少沿用传统的艳情题材,转而同诗一样去抒发文人的心态,甚至于阐发佛典禅理,减少了词的娱乐性,也提高了词体地位。其次从词创作的艺术手法上看,王安石也进行了多种尝试。首先是集句创作形式的使用,可以是此后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前奏,这种创作手法虽有前人之功,但也需要集句创作者的阅读储备和编排巧思。正如明代徐师曾认为集句诗要求创作者“必博学强识,融会贯通,如出一手,然后为工。若牵合附会,意不相贯,不足以语此矣”。[6]这个要求与词亦是相通的,而集句词更要面临适应“长短句”形式的要求,因此集句词比集句诗难度更甚。清代沈雄总结了集句词创作的“七难”,即“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余更增其一难,曰打成一片。稼轩俱集经语,尤为不易”。[7]集句词必须符合格律偶对的规范,在编排过程中更要考虑词总体结构的和谐。因此王安石在其为数不多的词作中选择集句的创作方法也是其敢于创新尝试的体现。沈雄同时关注到“集经语”更为困难,其中原因包括佛教经典中包含着许多专有概念的语汇,并且佛教经典大多注重教义传播的功用性而非文学性,因此较难在诗词当中体现,因此辛弃疾俱集经语之不易当显于此,而王安石佛禅词采用集句手法早于辛弃疾之词,其难度和新意更是不言而喻。正是由于集句创作的困难度,王安石在词与诗的创作上对集句手法的大量运用,也展现了宋代文人在文学创作心态上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文以载道”“立言立身”的严肃心态到游戏心态的转变。当代学者汤江浩也看到了这一点:“王安石一部分词作具有一种游戏、消遣的创作心态。……效颦者颇多,即使是苏、黄亦因技痒而不免。”[8]集句手法虽非宋代而始,却在宋代兴盛,再联系到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王安石无疑也展现了宋代“好才学”的时代特色。
王安石词作对艺术手法的创新还体现在语言通俗化的实践上。前文提及王安石佛禅词在词的意象和选词遣句上增添了许多来源于佛经教义中不晦涩难懂的词语与概念。此外王安石佛禅词表现出明显的非书面化特点,追求词的协律可歌。这种可唱性与词产生初期不同,以花间词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更多是考虑传唱对象即歌女的可歌性,配合闺情的主题内容,晚唐五代词的可歌性以软媚为主。而除了《雨霖铃》之外,王安石的其他佛禅词的可歌性并不局限于让歌妓歌唱,而有明显的便于大众传唱的目的性。王安石的佛禅词中有五首是与俞秀老唱和之作,王安石与俞秀老有着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也影响着王安石佛禅词的创作。黄庭坚《书王荆公增俞秀老诗后》中载俞秀老:“病在好说俗禅。秀老以为知言也。秀老作《倡道歌》十篇,欲把手牵一切人同入涅槃场。”[9]从黄庭坚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俞秀老喜以俚俗说禅,且喜以禅理写作诗歌。王安石支持这种好以俚俗唱禅理的特点,在黄庭坚《书元真子<渔父>赠俞秀老》中载:“荆公乐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与荆公往反游戏歌曲,皆可传。长干白下,舟人芦子,或能记忆也。”[8]从黄庭坚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荆公与秀老二者所创作的作品传唱度很高,并且是在民间普通民众中传唱,其俚俗程度和传播度可见一斑,这种创作也是推动词走出闺阁、走出文人书苑重归民间的重要尝试。
四、结束语
北宋初期的词是在晚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的,具体表现为词艺术性的提高,在柳永等人的努力下词也进一步提升了俚俗化程度。但此时词的格调仍然未开,不受文人重视,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打破了这种局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前人的评述中亦可窥见一二,如: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
俞文豹《吹剑录》:惟荆公诗词,未尝作脂粉语。
龙榆生《唐五代宋词选》:笔力豪纵,不为妖媚语,一如其诗文。[10]
这些议论都看到王安石词作对于打破旧有软媚词风、开拓词的境界的贡献。这种开拓不仅表现在备受赞誉的咏史词中,亦可见于集句词和佛禅词中。王安石的集句词和佛禅词不仅在体制上丰富了集句词的集句方式,丰富了词的体制,同时也丰富了词的内容,使词不局限于描写风花雪月,而可以表现文人心绪,也可展现佛理禅理。在词的艺术特色上也进一步推动词的通俗化,扩大词的受众面。王安石的这些创新之举也是之后苏黄词“以诗为词”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