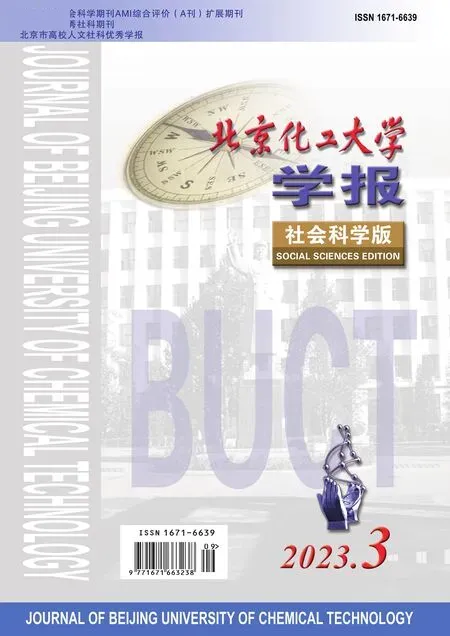程颐人性论研究
伊雷
(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29)
一、引言
北宋儒学复兴的主题并不是由宋儒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他们对中唐时期韩愈、李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韩、李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与所借助的经典资源引起了宋儒的高度关注,他们正是在深入探讨韩、李所提问题基础上形成了若干新的哲学体系,进而实现了儒学的复兴。韩愈坚决排斥佛老,捍卫“儒家之道”,他的“五原”对宋儒影响巨大,尤其是“原道”和“原性”的影响更为深远,北宋中晚期那些著名儒者所关注的哲学主题,无不是韩氏“原道”与“原性”等的继续。李翱在韩愈“原性”基础上发展了人性论,并以此来论证人之如何成圣,这对程颐影响巨大。“原道”和“原性”后来被宋儒所普遍关注,北宋中晚期的那些著名思想家无不研究这两大主题,并最终将其合二为一,浓缩为“穷理尽性之学”。宋儒之所以会持续关注这两大主题,乃跟韩、李一样,都是为了回应佛老在本体论、心性论上的挑战。二程所关注的核心哲学问题仍然是“原道”和“原性”这一基本问题,而随着他们使用“理”越来越多,他们已逐渐倾向于用“理”来诠释“道”。在他们看来,“道”之所以为“道”,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理”,因而他们又将“原道”这一儒学复兴的基本问题再转进一层,追问“何谓儒家之理?”从而实现了儒家哲学范式的转换,进而为“理学”的发展打开了空间。二程在“原性”上的最主要贡献,一方面固然在于他们能够从本体论的高度阐发这一主题,进而能够将其理学思想贯彻到底,从而实现了对汉唐儒者的超越;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工夫”上发展出了一套“涵养”体系,从而为后世儒者在“成圣”的实践上提供了抓手。
二、程颐人性论的问题意识及其实质
程颐人性论的问题意识与韩、李的思想密切相关。如果说韩愈的“原性”是后来北宋儒学复兴的主题之一,那么李翱的“复性”则让这一主题更加深刻。李翱对“性”“情”关系的讨论是宋儒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对于人之如何成圣的论述,更是引起了程颐的积极响应。李翱言“性”不是直接从《孟子》来,而是由《中庸》始,这一思路与韩愈不同,这对宋儒影响更大。值得一提的是,李翱在论证人之如何“复性”时所引用的经典正是后来二程创建其理学时所使用的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宋儒言“性”,不单是对韩愈、李翱思想的继承,也不仅是受先秦《中庸》《易传》《孟子》等经典的影响,还与禅宗“心学”的刺激有关。先秦儒家虽在人性论上着墨颇多,但真正将“心”“性”结合来讨论的其实并不多,唯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但孟子所讲的“不忍人之心”、“四心”缺乏本体论高度。《中庸》和《易传》言“性”虽不乏本体论高度,但没有将其与“心”相结合。《中庸》言“性”的思路与孟子不同,其特点是立足于“天命”来言“性”,也即从“物之性”讲到“人之性”,最后将“人之性”与“物之性”相统一。《易传》言“性”的逻辑与《中庸》颇有相似之处,从“天道”讲起,正如《说卦传》所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636从“天道”、“天命”的高度顺势讲“人性”,先秦儒家虽多有涉及,但仍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在言“性”与言“心”上未能做到有机融合。汉唐儒者言“性”也基本上没有同言“心”相结合,真正做到将言“心”与言“性”相统一的是禅宗。可以说,是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将“心学”上升到了第一哲学的高度,并将佛性论纳入其心学体系。而正是在禅宗心学的刺激下,张载、二程等人才再次聚焦“心性”问题,从而为儒家的心性论在宋明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禅宗虽然能将心、性结合,但其所讲的心、性并不具备道德属性,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道德”的依托(1)禅宗所讲的“性”,往往指“空性”,而其所讲的“心”又往往指“无相真心”。“无相真心”在本质上是“湛然空寂”的,因而没有任何道德属性。。从实质上来说,禅宗与儒家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哲学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儒家更关心这个社会是否有秩序,因而他们往往更注重维护群体的“人伦”,而禅宗更关注个体的“解脱”,因而在其看来儒家的所谓“人伦”不过是“世网”。禅宗“心学”的优势在于他们注意到了“心”的主观能动性,而张载、二程的特点则在于他们突显了“天理”的客观实在性。张载、二程都试图通过强调“天理”的客观实在性来克服禅宗“心学”的主观随意性。
从言“性”的角度来看,儒学复兴从北宋中期到晚期正逐渐深化。尽管在北宋中期,欧阳修认为:“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恶,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者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2)参见:[宋]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卷四)[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公是先生弟子记》记载的这段话,很可能源自欧阳修的《答李诩第二书》。欧公曾于庆历初年针对李诩的《性诠》三篇回信对方说:“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当时“言性者多矣”,而欧公之所以反对学者们“言性”,其理由是“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欧公还认为,当时学者们的各种“性”说,都是“儒之偏说,无用之空言”。参见:[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668.但在北宋晚期,儒者们普遍重视“性命”问题,以致于司马光抱怨说:“性者,子贡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3)司马光所说的这段话,虽主要针对当时的科场而言,然从中亦可窥见北宋中晚期学风之一斑。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第二册)[M].李文泽,霞绍晖,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973-974.此札写于熙宁二年,十几年后,也即元丰八年二月十三日,温公在废纸中重得此札,并说“然观今日之风俗,其言似误中,故存之”,从这句话来看,北宋熙丰期间,学者言“性”已蔚然成风。对于这一点,从苏轼同样写于熙宁二年的《议学校贡举状》也可看出。苏轼说:“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 参见:[宋]苏轼.苏轼文集(第二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725.冀洁根据《宋朝诸臣奏议》《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玉海》等的记载,认为苏氏此状撰于熙宁二年,而非熙宁四年。参见:冀洁.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并非熙宁四年奏上[J].北京大学学报,1982(5):97.北宋诸儒研究“性命”问题的高潮之所以会出现在熙丰年间,与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受韩、李及禅宗影响,在北宋中晚期儒者们研究人性等问题已成时代风潮,非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所能阻止。从本质上来说,北宋儒学复兴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思潮、变法运动息息相关,作为北宋儒学复兴主题的“原道”与“原性”,在实质上都是当时改革变法运动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正是在“庆历新政”的直接影响下,北宋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成功,而欧阳修等人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乃是北宋儒学复兴的前奏;正是在“熙丰变法”过程中,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二程洛学等才得以砥砺成熟,这几大思想流派在北宋中晚期影响最大,他们在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的成就代表着北宋儒学复兴的主要成果。故而与其说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4)牟宗三先生曾反复强调宋儒的兴起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参见: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130-132.从时间上来看,北宋儒学复兴实际上主要发生在北宋中晚期,若真如牟先生所说,那么北宋儒学复兴的时间节点就应该在北宋初期。到了北宋中晚期,儒者们时隔百年之后是否还有必要那么迫切地去反思残唐、五代人的“无廉耻”?事实上对唐末五代乱局的反思主要是宋太祖、太宗两朝君臣的议题,到了北宋中晚期这一议题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倒不如说是北宋中晚期改革变法运动的意识形态。
三、程颐对人性内涵之理解
宋儒言“性”无不受韩、李影响。韩愈以“五常”为人性之内在根据,分人性为上中下三品[3]。二程虽反对韩氏“性三品”之划分,却接受了其以“五常”为人性本质的观点。对此,程颢曾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4]14程颐认为:“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4]273,“万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4]105。李翱言“性”的思路与韩愈不同,他受《中庸》《易传》影响,主张“性者,天之命”。受《中庸》《易传》及李翱影响,宋儒普遍主张人性来自“天命”。对此,司马光曾明确说:“性,天命也。”[5]刘敞认为:“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6]卷二刘敞人性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天命”、“人性”与“道”进行挂钩,强调“所谓命者,道而已矣”[6]卷一,后来张载、二程也是这个思路。韩愈虽没有直接说“道即性”,但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这一观点。其在《原道》中提出以“仁义”为“儒家之道”,又在《原性》中说“五常”为人性之根据,那么他就在实质上为后来张载、二程提出所谓“道即性”等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儒虽普遍以“五常”为“性”,但对“仁义礼智信”五者的重视程度并不均等。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主张以“礼”为本,李觏甚至认为“礼”是仁、义、智、信之本,而二程则主张以“仁”为本。程颐虽同韩愈一样,重视“仁义”(尤其重视“仁”),但对“仁义”内涵之理解,特别是在对“仁”的理解上,与韩氏却有着根本区别。韩愈主张以“博爱”训“仁”,但在程颐看来,“博爱”乃是“情”,不是“性”[4]433。程颐说:“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4]182他主张以“公”训“仁”,他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4]153在他看来,“公”是仁之“理”,其层次要比“仁”更高。
程颐认为,“公”与“私”相对。他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4]144他主张:“合而听之则圣,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4]145所谓“天心”即是“公心”。程颐坚持“道”的统一性,既然在他看来,“公”是仁之“道”,而天、地、人三者又是一“道”,那么就可以推论出,“公”就是万物之“道”。既然“公”、“公心”、“天心”就是“道”,而其又主张“性”与“道”的同一,那么由此就可以推论出,“公”、“公平”、“公心”才是其所言“人性”之真正内涵,这与韩愈所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程颐还特别强调“五常”无论分而言之还是合而言之都是“道”[4]318。他说:“仁既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学道,则仁在其中矣。”[4]283其“仁即是道”的观点主要来自《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同时,他又接受了《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将《易传》的“仁义”思想与《中庸》的“仁义”观点进行了融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人道”主张。他认同“仁者”以“亲亲为大”、“义者”以“尊贤为大”的观点,主张唯有在“亲亲”的基础上,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有在“尊贤”的基础上,才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所以他才会说:“唯仁与义,尽人之道。”[4]326
四、从“道即性”到“性即理”
从韩愈的《原道》和《原性》来看,其已有将“道”与“性”直接挂钩的意图,只是尚未明示。对此,张载、二程则直接将其点破。张载曾明确说:“天道即性也。”[7]234然张载所谓“道”,主要指“气化”,二程反对以“气”训“道”。程颢曾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4]118程颐则直接说:“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4]162二程不满意儒者们将“气”看作这个世界的“本体”,他们最后选择的是“理”。
二程都强调“道”与“性”是统一的关系。程颢曾对韩维说:“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4]1对于这一点,程颐也深表认同,他曾明确说:“道与性,一也。”[4]318从元丰四年(1081)程颢提出“道即性”观点(5)这句语录为李吁所记,李吁于元丰四年(1081)四月韩持国知颖昌府时从二程学,故知此段语录当为明道寓于颖昌时所说。参见:[清]池生春,诸星杓.程子年谱·明道先生(卷四)[Z].清咸丰五年味经室刻本.伊川曾说:“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目录)[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1.,到十几年之后,也即绍圣三年(1096),程颐将其翻转为“性即理”,从中不难看出在程颢死后,程颐对其兄之人性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万物一体,生生不已”是程颢的第一哲学。程颢言“性”以《系辞》的“生生”思想为根基,兼容《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在他看来,“天只是以生为道”[4]28-30,“生生”才是评价万物善恶的根本标准——有利于“生生”的,就是“善”,阻碍“生生”的,就是“恶”。而所谓“性”,乃指“生生”从潜在走向现实。换言之,“性”就是“生生之理”通过万物展现出了其自身,也即万物现实了其自身的“生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会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表达了认同[4]29-30。在他看来,既然“性”的本质是“生生”,那么告子所谓“生之谓性”的观点则有其合理性。
如果按照程颢“生生之谓性”的观点来推论,那么“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就是合理的,因为这是“通人物而言”的。但对于儒家来说,“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程颢借助了儒家传统的“气禀说”。“气禀说”不但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主张“性善论”的二程在解释“恶”的来源时提供了新的辅助工具。程颢认为:“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6)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10.此条语录《近思录》卷一作明道语。参见: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朱子语类》卷四、卷九十五皆作明道语。参见:[宋]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明道学案》亦收有此条,参见:[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4-565.也就是说,万物的“生生”需要借助于“气”,这是其“生生之谓性”思想的深化。至此,程颢“生生”观点的另一层含义——“性即气,气即性”,得以展现。
程颢认为“人生气禀”就必然有“善恶”,“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这都是“气禀”的结果。他认为“善”固然属于“性”,但“恶”也属于“性”。“生之谓性”以上不容说“性”,“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这是程颢言“性”的重要观点[4]10。他又强调,并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他认为人们只要言“性”,就都是在言“继之者善”,孟子言“性”也是如此[4]10。程颢对“继之者善”作了一个比喻,认为所谓“继之者善”,就犹如“水流而就下”,虽然都是水,“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4]10。他强调“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主张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4]10。他认为“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而不是“将清来换却浊”,更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4]10。他说“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4]10。
不难看出,程颢正是整合了《易传》《中庸》及《孟子》等的人性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他在整合先秦儒家“人性论”资源时,将吸收与批判相结合,他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排斥告子的思想。他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整合了孟子和告子的观点,也即从《易传》和《中庸》的本体论出发,对孟子和告子的人性论进行了重新定义,这既是对孟子与告子思想的超越,也是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发展。
程颢实际上是以“生之谓性”为基础重新解读了孟子的性善论,也即把孟子所说的“性善”理解为“元初之水”和“气质之性”。然而程颐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与告子的“生之谓性”主张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孟子言人性善,说的是“极本穷源之性”,而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说的则是“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4]63。他认为“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在“极本穷源之性”这一层面当然是成立的。在他看来,犬、牛、人,其“性”本同,由于“气禀”的原因才导致其“形”各异。为此,他借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譬如“隙中日光”,虽然“方圆不移”,然“其光一也”[4]312。但“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的结论,在他看来,在“受生之后”并不成立。他认为“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即“生之谓性”,而“极本穷源之性”乃“天命之谓性”,他虽将二者并举,却强调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生之谓性”讲的是“气禀”之后的“性”,而“天命之谓性”讲的则是“性”之“理”[4]313。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人性至少分为了两个层次:“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天命之谓性”是从“源”上来讲的,而“生之谓性”则是从“流”上来说的。他认为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是在说“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也即“生之谓性”,而所谓“性急性缓”也都是在讲“气质之性”。在他看来,孔子所讲的“上智下愚不移”并不是在说“性”,而是在说“才”。“才”与“性”不同,人禀气之后形成所谓“才”。他赞同孟子的性善论,批评荀子、扬子不知“性”,强调“性无不善”,“有不善者,才也”[4]204。他还说:“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4]255
程颐在“生之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气禀说”,反之又用“气禀说”来诠释“生之谓性”,进而又将“生之谓性”定义为“气质之性”[4]207。程颢虽也借助“气禀说”,但其人性论的核心概念始终是“生之谓性”,而程颐则将“生之谓性”理解为“气质之性”,与程颢不同,“气质之性”在程颐的人性论中,相较于“天命之性”始终居于次一等的位置。
程颐64岁时提出“性即理”观点,认为“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4]204,“才禀于气,气有清浊”,而“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7)上述语录为刘元承所记。据卢连章研究,伊川所语当发生在宋哲宗绍圣三年,是年伊川六十四岁居于洛阳。参见:卢连章.二程学谱[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39.。他将孟子的“才”论与“气禀说”相结合,用“气禀说”来解释“才”的形成,这实际上是对孟子“才”论的发展。程颐的“性即理”观点,与程颢的“道即性”思想有着很大差别。程颢“道即性”观点的主要内涵是“生生之谓性”,在他看来,“生生之谓性”以上部分是不可言说的。但程颐却不这样认为,他对“极本穷源”的探讨正是程颢认为不可言说的部分。程颐言“性”的最主要特点也是将“性”与“气”相结合。他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8)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81.这条语录《近思录》卷二作伊川语,参见: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9.《伊川学案》亦收有此条,参见:[清]黃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程颐晚年又重申了其64岁时的主要观点,并继续强调“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9)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291-292.此段语录现收在《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伊川杂录,宜兴唐棣彥思编。姚名达将此段语录系在崇宁元年,其理由是唐棣所记语录中多周伯温等问语。参见:姚名达.程伊川年谱[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79.然根据周孚先所记,其兄弟二人与伊川初见应在建中元年庚辰冬,故伊川说这段话时也可能在建中元年。唐棣所记伊川语录中多次提到周伯温的问语。周伯温是晋陵(常州)人,乃周孚先之弟。周伯温初见伊川,曾问颜子如何学。据周孚先回忆:“孚先旧讲习太学,建中靖国庚辰冬过洛阳,游伊川先生之门,预群弟子之列,亲炙模范,时闻诲语。越明年暮春,归省庭闱,期岁复入学,以所疑为书,请质于先生,皆得亲笔开谕,逮今几四十年矣。”(《答周孚先问》(并跋),《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615.)从周孚先的这段话来判断,上述唐棣所记那句语录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庚辰冬或崇宁元年伊川69岁或70岁时所说。。
从解释力的角度来看,用“气禀说”来解释人的智愚问题要比解释善恶问题更为合适,刘敞、王安石、程颐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对于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刘敞认为这是在说愚智问题,而不是善恶问题。他说:“愚智非善恶也,虽有下愚之人,不害于为善。”[6]卷四这一观点可谓相当深刻。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其《原性》云:“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8]程颐则强调孔子所讲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在说“性”,而是在说“才”。如果从“知”“行”关系角度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程颐的思路。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作恶或犯错,本质上是“识不足以知之”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4]320,而气的清浊会影响到人的智愚,进而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判断,从而使人犯错或作恶。反之,如果人“识足以知之”,那么就不会作恶或犯错,所以程颐才会说:“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须理事,本亦不难,但为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难也。”[4]188这就是为什么他非要从“本体”上说清楚人之善恶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他看来,人若真能“知”,则必然会“力行”[4]187,并且“知之深,则行之必至”[4]164。他强调“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4]164。他这样说,就把人对善恶的认识问题和其行为统一起来了,这也是其言“性”必然会涉及“工夫”的根本原因。
“气禀说”的引入,表面上看来解释清楚了“恶”的根源性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深层次问题。首先,韩愈认为“性”是“与生俱生”的,如果以“气禀说”来解释“恶”的根源性问题,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恶”也有可能是“与生俱生”的。其次,程颐一生坚持“理一元论”立场(他曾反复强调“万物一理”),并希望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然而他却在人性论上事与愿违。显然“气禀说”的引入,对于其“理一元论”立场构成了威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其对“理”的根本属性的规定有着直接关系。这里试举两例:其一,程颐早年认为“理必有对待”,他曾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4]161-162既然“天地之间皆有对”,那么说“有阴则有阳”可以理解,然又说“有善则有恶”,“有善则有恶”涉及人的价值判断,一旦涉及人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善、恶问题,就必然会陷入矛盾之中。因为程颐将“理”的根本属性规定为“未有不善”[4]313,而“未有不善”之“理”既然是万物背后的“所以然”,那么又怎会产生“恶”呢?这就如同禅宗以“真心”为“本”、以“妄心”为“用”,“真心”为什么会产生“妄心”的问题一样,令人难以回答。为此,程颐不得不诉诸于“气禀说”。可这样一来,他的哲学就从“理一元论”滑向了“理气二元论”。其二,程颐晚年主张“物理极而必反”(10)程颐说:“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这句话虽然是在解释“否”“泰”两卦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如果从伊川之学的整个体系来看,“物理极而必反”也是“理”的基本属性之一。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762.,强调:“极而必反,理之常也。”[4]762他一方面坚持“理”的统一性,也即坚持了“理一元论”,并强调“理无不善”,另一方面又认为“物理极而必反”,那么纯善之“理”会向哪个方向转化?按照其“极而必反”的逻辑,纯善之“理”必然会向“恶”的方向转化。如果纯善之“理”有转向“恶”的必然性,那么“理”也就必然不是纯“善”的。如果“理”是有善有恶的,那么“理”就必然不是“一元”的。也就是说,程颐只能在“理一元论”和“理无不善论”两个命题之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整个理学体系的大前提。而为了解释清楚“恶”的来源问题,他诉诸于“气禀说”,也即他不得不在“理”之外寻找“恶”的来源,这就导致其在人性论上最终由“理一元论”走向了“理气二元论”。
五、正其心,养其性
程颐不但主张“性”与“道”的统一,而且认为“性”与“命”、“性”与“天”、“性”与“心”、“性”与“情”都是统一的关系。对此,他说:“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4]318这里围绕“性”,他对儒家所谓的“道”、“命”、“天”、“心”、“情”等都进行了重新定义。从时间上来看,程颐对“心、性、情”问题的关注要比“道、性、命”或“理、性、命”问题早得多,并且从“心、性、情”的角度来看,人之“恶”有着不同的产生机理。程颐认为,“情”之炽荡是导致人之“恶”的重要原因之一。韩愈认为“情”是“接于物而生”的,程颐接受了这一观点。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提到了“情”,但对于“性”“情”之关系并没有给予太多说明。而“性”“情”之关系问题则是李翱《复性书》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从对“性”“情”关系的处理来看,程颐更多地受到了李翱的影响。
首先,程颐与李翱都坚持了“性”“情”统一的立场。李翱强调“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9]13。李翱的“性情统一论”被北宋儒者们所普遍接受。尽管刘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言“性”的观点不同,但他们都以“性情统一论”作为自己人性论的基础。程颐早年受《中庸》影响,认为“心”的未发状态就是“性”(他也把这种状态理解为“中”,其特点是“真而静”),他强调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五性”具焉。然而在“形”产生之后,外物触“形”导致“中”动,于是“七情”出焉[4]577。这是他年轻时对“性”“情”的本质及二者关系的基本看法。程颐强调,如果“情”炽而益荡,其“性”则凿矣,所以要控制“情”,使其合于“中”,也即合于“性”。为此,他主张“正其心,养其性”,也就是所谓“性其情”(11)程颐所谓“性其情”,指的是心的已发状态的修养方法,其主要含义是“正其心,养其性,约其情”使之合于“中”。他认为如果纵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亡之,则是“情其性”,故而“正心”、“养性”、“约情”是“性其情”的最主要含义。参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577.程颐早年所讲的“性其情”受到了胡瑷的影响。胡瑷认为:“性者天生之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具备,故禀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周易口义》卷一)他认为情欲之发虽有邪有正,但圣人能“性其情”,所谓“性其情”系指“以正性制之”而“不使外物迁之”。参见:[宋]胡瑷.周易口义(卷五)[M].倪天隐,整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其次,程颐与李翱都坚守了孟子的“性善论”。李翱与韩愈的另一不同点是,李翱坚持了孟子的“性善论”,强调“性无不善”,“情则有善有恶”[9]22,这一观点后来也被程颐所接受,并成为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在“性情统一论”的立场之下,坚守孟子“性善论”的李翱,为北宋诸儒提出了一个理论难题——既然性、情是统一的关系,如果“性”是“善”的,那么“情”为什么会是“恶”的呢?面对这一难题,刘敞认为:是“形”而不是“情”导致了“恶”[6]卷三。刘敞强调“非情无性,非性无善”[6]卷三,“性”“情”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他说“仁义,性也”,“礼乐,情也”[6]卷四,“非人情无所作礼乐,非人性无所明仁义”,“性者仁义之本,情者礼乐之本”[6]卷四。刘敞认识到了“情”的积极意义,这一点要比李翱的看法更深刻。程颐虽然没有像刘敞那样强调“情”的积极意义,但对其“性情统一论”和“性善论”的立场是认同的,他不但运用“形”,而且也用“才”来解释“恶”的根源。
再次,程颐与李翱都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李翱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9]13程颐则说:“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4]318儒家的圣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韩愈所说的“救世主”(12)韩愈认为正是圣人教会了人们“生养之道”,他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参见:[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二是李翱所说的“道德”典范[10]。韩愈的“圣人观”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他力信仰”,而李翱的“圣人观”则代表着一种“自力信仰”。李翱的主张后来得到了程颐的积极响应。程颐极力主张“学至圣人”,也是“自力信仰”的圣人观。程颐虽认同韩愈以“五常”为性的主张,但对于其“性三品说”却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对性之上品与下品之间不可移的观点更不认同。程颐不但主张“上智与下愚可移”,而且指出了“可移”的方法,即只要人们肯去“学”,就“可移”。在北宋中期,刘敞虽也非常重视“学”的作用,但他却强调“圣人之性不可及”,认为“性者受之天,道者受之人”,二者都不能够随意改变,而程颐则强调圣人之性可及。
李翱认为:“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9]13在他看来,人之要想成圣,就必须要排除掉“情”的干扰。为此,他主张首先从“心斋”做起——先做到“无思无虑”,然后是“动静皆离”,最后是心之“寂然不动”[9]17。李翱所主张的成圣方法明显受到了佛老的影响,而程颐则将之完全儒家化。程颐认为:“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4]273为了排除“情”的干扰,程颐走了一条“穷理”与“涵养”相结合的路子。其所谓“穷理”系指“格物穷理”,所谓“涵养”指“义理养心”、“正心养性”、“敬以直内”等。
第一,程颐认为要想实得“儒家之道”,“格物”是必由之路。他说:“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4]365这一说法与李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完全不同。李翱认为“致知在格物”是指“物”至之时“心”不应于“物”,从而保持“心”的“昭昭明辨”状态[9]20。根据这一观点,“致知”与“格物”已经失去了内在关联性,“格物”反而会干扰“致知”。
第二,在“心”的已发状态,程颐主张“义理养心”。晚年他曾说:“古之学者易,今之学者难。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4]268此段语录为张绎所记,张绎乃伊川晚年所收弟子,其所记语录代表着伊川晚年思想(13)张绎年三十始见伊川,时间应在元符三年,伊川自涪陵归后。是年,伊川六十八岁。(参见:[清]池生春,诸星杓.程子年谱·明道先生(卷七)[Z].清咸丰五年味经室刻本.)同时,张绎《祭伊川先生文》云:“自某之见,七年于兹。”此也能佐证他见伊川,应在伊川六十八岁时。。这里所谓“义理养心”,其实指的就是“以义制心”,也即“性其情”。
第三,在“心”的未发状态,程颐主张“涵养用敬”。“涵养”与“格物”不同,“涵养”主要是人们未接触事物时的做法,“格物”则必须与外物相接。因此,“涵养”与“格物”是不同的入道方式。“涵养”旨在“敬以直内”,而“格物”的目的则在于“穷尽物理”。程颐认为在未接触事物时,主于“敬”便是“为善”[4]170。他强调:“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4]188有时他也将“涵养”看成是“入道之门”,并且强调“涵养”和“致知”之间有密切联系。为此,他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4]66,“格物亦须积累涵养”[4]164。“涵养用敬”虽然主要是在心之“未发”状态下的修养方法,但在“已发”状态亦可使用。程颐认为:“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4]155他强调“敬以直内”在本质上就是“养志”,因为“率气者在志”[4]151。为此,他说:“志,气之帅。”[4]143“养志”与“帅气”是不同层面的概念,“帅气”以志,“养志”则以“敬”,所以“涵养用敬”主要指的是“养志”。
六、余论
在北宋中晚期,张载、二程逐渐将“原道”与“原性”这两大哲学主题合二为一,形成所谓“穷理尽性之学”。可以说,“穷理尽性”才是北宋儒学复兴的真正主题。《周易·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634,这一命题在宋儒中引起强烈反响。王安石早年所著《洪范传》认为“穷理尽性”是国家兴盛的前提[11]。荆公早年在“穷理尽性之学”上坚持了儒家的立场,而其晚年的思想则逐渐体现出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倾向。如他在《老子注》中用《说卦传》的观点来诠释老子所讲的“为学”与“为道”,以“穷理”训“为学”,以“尽性”训“为道”,其所体现出的思想则明显是儒、道二家相融合的产物[12]。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伊川之学是北宋晚期最具影响的三大学派,与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相比,伊川之学始终坚守了儒家立场。
除了王安石,邵雍、张载等亦是研究“穷理尽性之学”的大家。邵雍将“穷理尽性”定义为“人能知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13]。张载认为:“知天知人,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同意。”[7]234张载“穷理尽性”的独特之处在于主张先“穷理”,后“尽性”。同时,他强调只有将“穷理”与“尽性”相结合,才能最终“至命”。二程在“穷理尽性”上与张载有很大不同,他们并不赞同张载将“穷理”“尽性”“至命”三者截然分开的观点。程颢说:“横渠昔尝譬命是源,穷理与尽性如穿渠引源。然则渠与源是两物,后来此议必改来。”[4]27他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物也。”[4]121他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4]15对此,程颐亦深表赞同,他说:“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才尽性便至命。”[4]193
程颐强调“理、性、命”三者是统一的关系。他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4]274他认为“命”就是“造化”,“天命”就是“天道”,更确切地说是“天道”之用。他还说:“天之付与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于物之谓理。”[4]91他又说:“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贵贱寿夭命也,仁义礼智亦命也。”[4]315既然“理”“性”“命”三者是统一的关系,那么在他看来,“知天命”就是“达天理”[4]161。
程颐认为,“心”“性”“天”具有共同的“本体”,三者背后只是一理。他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4]204据《程氏遗书》卷二十二载:“伯温又问:‘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秉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4]296-297程颐主张“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恶之别。他强调“心”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再谓之“心”[4]204。他认为人之为不善,是“欲”诱之的结果。由于“欲”的存在,他又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道心”直通“天理”,“人心”乃有“私欲”。他将“人心私欲”与“道心天理”相对立,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4]312。“人心”之所以“惟危”,乃因“人心”有“私欲”,而“道心”之所以“惟微”,是因为“道心”即“天理”。
需要指出的是,“人心”与“道心”并不是两个“心”,而是同一个“心”的不同侧面——就其“本体”而言,“人心即道心”;就其弊于“欲”而言,“人心即私欲”。因此,程颐强调“心”是道之所在,“心”与“道”浑然为一[4]276。他认为“道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然而既发于思虑则谓之“情”,不可谓之“心”。他说:“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4]321既然心、性、天三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那么他强调能“穷理”便能“尽性”,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他说:“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4]204他认为孟子所讲的“尽其心”是“我自尽其心”的意思,若能“尽己心”则能“尽人、尽物”。所谓“尽人”指的是“尽人之性”,所谓“尽物”指的是“尽物之性”[4]292。他认为能尽“人性”则能尽“物性”,能尽“物性”则能“参天化育”[4]158。他所谓“尽性”,其实指的就是“尽心”。“尽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