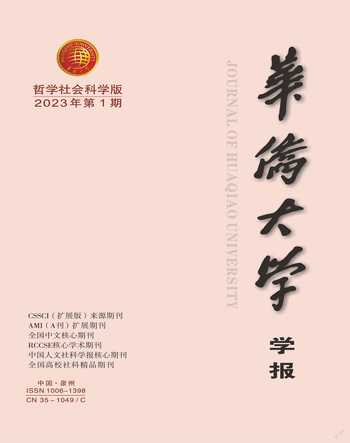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
摘 要:
中共起草《關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非源自外发性的国际肇因,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对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猜忌、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指责以及对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期冀,为起草工作既提供着由外而内的异域视角,亦提示着由此及彼的阐证路径。中共及时回应关切、郑重表达立场、反复阐证观点,饱含着对评价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相关原则、方法、观点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功过等三大核心论题的“论证、阐述和概括”。中共此举,既有助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有利于建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崭新形象,为助益于成功书写党的第二个重大历史决议,以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重要政治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因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书写
作者简介:许冲,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zsuxuchong@163.com; 广东 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百年记忆建构研究”(22ADJ004)
中图分类号:A811;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1-0005-13
2021年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正式通过40周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党的百年历史上第二次以中央名义就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共“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并在历经起草、修改、讨论、完善以及中央会议审议通过的繁复过程后,成就了一份兼具“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经典文献”【龚育之:《党史札记》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3、196页。】。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虽从文件起草过程、党的历史经验总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党史和国史研究的推进等维度进行了有益探索,【相关成果主要包括陈东林:《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国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导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沙健孙:《科学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李晓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李捷:《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之作——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夏春涛:《从百年党史看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3期。】但多侧重于历史史实的线性爬梳和经验总结方法的抽象归纳,较少系统研辨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件起草影响因素,特别是对其中着墨不多却考量再三的国际因素考察更是尚付阙如。众所周知,起草《决议》涉及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与阐释,“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84页。】。究其要义,“对待毛泽东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问题”【《胡耀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这就意味着,缺少国际因素考量的《决议》起草论题及其相关研究,恐将是难以想象,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有鉴于此,本文就该论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 关切与考量:《决议》起草的多重外部语境
作为一个将“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9页。】,对于《决议》是否写入国际问题,在起草之初就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一方面,国际问题直接涉及外交工作以及对某些国内问题的书写;另一方面,在写法上即便从正面写,最后也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页。】在开始《决议》起草之前,为说明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讲话的起草情况,胡乔木就曾转述邓小平对国际问题写作的类似担忧:国际上重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讲法,不讲以为我们不关心,少讲容易使人不满,讲了还有可能被人利用。【《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2页。】为此,胡乔木提醒《决议》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要涉及国际问题,我们答复不了。但国内问题包括我们的对外政策一定要讲清楚。”【《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4页。】也就是说,在《决议》中即便能够对国际问题秉笔直书,也恐将面临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但不容忽视的是,《决议》虽然可以回避对国际问题的直接评议,但就所涉历史、理论以及现实问题来看,它既不可能规避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漠视国际社会的关切,更不可能舍弃对外政策的考量。基于此,所谓《决议》起草中必须考量的国际因素,并非针对具体的国际议题做出评价而论,却是源自国际社会对个中所涉重大论题的复杂认知和多重关切,以及中共根据内政外交需要所须因应的国际诉求和所应考量的政策方案。
基于上述研判,并综合检视拨乱反正时期国际上的涉中舆论,首先被纳入《决议》起草考量范围的域外关切,乃是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在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核心担忧,毫无疑问是能否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事实上,这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同情或者国际友谊,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多重考量。从《决议》起草前后的中国政策背景看,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不仅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因此,能否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就成为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从内部来讲,“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从外部来看,“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2页。】。日本团体在讨论对华投资风险时,就曾发出两种声音:一是中国政局稳固,可放心投资;二是以段祺瑞政府时期对华贷款无法收回为鉴戒,现实地担心“四人帮”会卷土重来。【《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1页。】因此,为切实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共务须直面国际社会的两大关切:一是中国是否具有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偿付能力,二是中国的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暨稳定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95页。】与此同时,党内高层人事变动是否会造成权力斗争的外部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55页。】,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收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23页。】或“后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4页。】,以及动议起草中的《决议》能否最终通过等种种担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72页。】,也均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局势的研判。
可见,安定团结因素确系中共起草《决议》时务须倾听的“域外之音”,但它背后还潜藏着国际社会的“弦外之意”,也即是对评价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猜疑。作为安定团结问题的重要肇因,它随即成为国际关切的第二个焦点。整体考量拨乱反正时期中共政治运行的逻辑,基本政治操作是先批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再起草、修改、审议和通过《决议》,最后以此为基础召开党的十二大。其实,此举不仅是为了确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犯了错误,而“四人帮”等是在犯罪【《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更在于划清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借以统一思想和集中全党力量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中共精心擘画的政治操作,实际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认可。只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无论是为天安门事件和刘少奇同志平反,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抑或推行旨在消除个人崇拜的政治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拆除毛主席塑像和挂像)等,无不在國际社会引发种种猜疑。单就邓小平在《决议》起草阶段虑及之处,既有国际上“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 的直接质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35页。】,也有对中国在搞“非毛化”的各种非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74页。 】,还有所谓“赫鲁晓夫时代又杀回”中国的胡乱猜测,甚至连港台报刊也大肆鼓噪“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对于国际社会的纵声喧哗,邓小平严正地指出:“国际上很关心”对毛泽东功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但存有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毛主席的两种声音,【《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共不打算起草《决议》,也必须以“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因应国际社会的猜疑【《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从本质上看,上述猜疑实属于历史向度的现实关切,更多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现实政策和政治走向的一种担忧,但这不代表他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就毫无疑惑。其中,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误读而催生的所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论,也随即构成国际社会的第三重关切。胡乔木曾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千年不遇”的【《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4页。】。对此,国际上特别是一些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认知与中共多有分歧,并因政治理念冲突而屡加责问中方。在起草《决议》期间,胡乔木反复告诫起草小组成员: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既有“拥护”和“赞颂”的,也有“同情”和“惋惜”的,还有因其所谓以失败告终心生“失望”和“迷茫”的;具体来说,他们或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和劲头,是全世界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唯一在搞社会主义的(其他政党都在搞经济建设),或是强调毛泽东借“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现实政治问题并力图加以解决,既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化”,又“铲除了官僚阶层”,所以是个具有“好的方面”和“好的理想”的“勇敢的尝试”【《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9、76、80、135、137、84页。】。及至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原先因由国际反修和防修而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的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们,不仅质疑“中国是否走到跟苏联一样的道路去”,甚至还指责“中国已经叛变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当中国彻底打倒“四人帮”,他们又再度指责世界工人运动的前途因此破灭了。【《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1—62页。】客观而言,国际社会的诸种误解与责问,与中共过往的政治宣传和毛泽东的崇高威信也不无关系。【《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2页。】所以,中共确有责任借起草《决议》为契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正面的回应与解释,并藉此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现实的”和“理想的”力量【《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3页。】。
与此相对,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问题的核心关切,与欧洲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责问可谓大相径庭,而是特别表现出对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殷切期待。究其缘由,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不无关系。其实,早在动议起草《决议》前,对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国际价值,胡乔木就曾主张不要“自说自话”,因为“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党以外,已掌握政权的国家的党没有一个接受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过分的提法”【《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45—46页。】。所以,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应由各国、各党根据自身实际和实践加以评价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就曾告诉邓小平他不赞成“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接受中共对其展开批评,但强调“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也指出: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但津巴布韦获得独立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是易懂、管用且符合实际的《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内容指导着津巴布韦获得胜利,因此他特别关心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领袖,并希望中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毛泽东思想。【《邓力群文集》第1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545—546页。】与此相对,国际上还有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报以同情,也不赞成过分批评和否定毛泽东。比如,埃及理论家就曾提出既不要把毛主席说得太坏,也不要把“文化大革命”说得太坏。显然,此中的期冀明显缺乏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个内乱”的清醒认识,但它也会同前述关切代表着国际社会的一种声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无论是“错误讲过分”,还是“评价不恰当”,均“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37—138页。】。
除上述四种关切外,在部分国际人士中还存有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客观规律、“文化大革命”中实现了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的晚期思想等理论误读【《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7、80、83、140页。】。凡此种种,也均被纳入《决议》起草的考量范围。不仅如此,这些表面看似互有差异的外部关切,并非是单向度的存在,内在里均有着高度互联的复杂关系。如邓小平所言,外国人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与否,但实现安定团结的首要前提是看中共能否“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而这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93、445页。】;特别是,论及“国际上很关心”的“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其实也“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可见,基于由外而内的视阈来审度国际关切中的重大议题,其实与中共起草《决议》的“中心意思”是基本相符的,單就个中差异看,也仅是国际社会未能从“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以及“基本的总结”的维度来提问而已;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来提问,均须中共作出及时回应和合理解释,只因这不仅是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大局”和符合党、国家以及人民利益的要求,而且还能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放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10、495页。】
二 回应与擘画:《决议》起草的现实政治考量
如何因应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共同关切,中共原本有着不同的考量。相比较而言,鉴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外交层面对中国问题的热切关注,中共务须作出及时回应,甚至予以郑重表态。事实上,这与邓小平最初的构想大有不同(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共高层在涉外场域的回应与表态,实际蕴含着解答和评价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原则、思路、方法甚至核心观点。至中央正式动议起草《决议》,国际关切与中共高应间的思想共振也并未停止,而是循着满足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对《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施以论证、阐述和概括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继续提供着由外而内的广阔视野,以及提示着由表及里的论证路径【《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2页。】。
在动议起草《决议》前,面对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非毛化”议论,邓小平就曾一方面向美国作家罗伯特坚称“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另一方面又历史地肯定“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直言中共将沿用毛泽东本人所提倡的“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据以“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38页。】。而在做出上述表达的同一天晚上,邓小平还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重申:毛主席的伟大功勋不可磨灭,缺点错误也不能回避,对他的评价绝不可以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5页。】不仅如此,随后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代表时,邓小平再次就所谓“非毛化”问题郑重表态: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旧是党的指导思想,不应苛求伟大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当前根据现实提出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是完全应该的,这并不是什么“非毛化”,而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确定的原则和绘制的蓝图来建设国家与实行对外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74页。】至于国际上高度关注的安定团结等问题,邓小平也对到访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再度强调:中共是“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来拨乱反正,据以创造良好政治气氛和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7页。】借助频繁的外事活动,邓小平直接回应了国际关切,同时也逐步明确了中共对待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原则和方针,这就为择机起草《决议》做了必要准备。
至1979年10月下旬,中央正式动议起草《决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为纲要,并作进一步的具体化和深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574页。】客观而言,尽管该讲话在发表后曾引发国内外的积极评价【《邓力群文集》第1卷,第269页。】,实际上它仍不足以给建国三十年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做出全面和具体的总结。对此,胡乔木最初设想是先确定“究竟要写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再研究整体写法和对国际问题的说法,进而专注于对重大事件发生背景的分析,以及对发生问题作理论上的评论【《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4—55页。】;至于所谓的核心问题,他在同《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基于“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严重性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必须阐明前者发生的原因和后者的本质内涵以及现实价值。【《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4—56页。】如若不然,中共既难以消解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误读,也可能因为缺少对中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权威表达,而使人误解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00页。】。基于上述考量,《决议》起草小组拟定了写作提纲,但邓小平在看后却指示:应采用集中写法对重要问题做出论断,针对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着重写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和形成的过程,对其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要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2页。】由此,从胡乔木的“最初设想”到邓小平的三点“中心意思”,中央逐步厘定《决议》写作的核心论题。它既涵盖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也囊括了国际社会所“关心”“议论”和“注意”最多的问题,从本质意义上看,这两者实际具有着明显的论题一致性。
藉由上述铺垫,《决议》的起草工作有序推进,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与起草小组保持即时沟通的同时,仍不忘借助外事活动继续申明中共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立场、态度与观点。在1980年4月至5月间,邓小平先是向起草小组建议《决议》起草的“整个设计”应包括前言、建国以来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和结语等五个部分,后是再度强调论证、阐述和概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已成为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91—292页。】紧接着,面对欧美以及非洲各界人士的关切,邓小平再度对外重申:一方面,中国现行的政策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的,也是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19页。】,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应重视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概括中国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其中的关键,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以及坚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54—155页。】。邓小平的如此回应,已不止“向客人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实际蕴含着对同期《决议》起草“难题”的具体思考与破解。究其缘由,也正如邓小平在外事活动中所言,不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是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仅从好听的“名字”或“名称”出发,既难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更不可能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29页。】
客观而言,藉由起草《决议》系统总结经验和解释历史原委,绝非直接回应国际关切和评论历史功过那般简单,也更非撰写党政报告或节庆纪念讲话所能比拟。胡乔木曾言,《决议》若不能答复“文化大革命”为何发生之类的重大论题,这“就等于不作”;即便从中得出了经验教训,也将是一场“空论”【《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4页。】。由此可见《决议》起草工作之不易。所以,当邓小平看到《决议》初稿时,直言它“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没有抓住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和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写作“重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94页。】,自然也就无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不妨设想,如果连《决议》起草者自身都不能将毛泽东晚年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与对照,那么国内外各界人士又如何能形成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的客观评价,进而正面回应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之后的中国是否已经失败的质问呢?这就意味着,中共对上述问题务须做出更权威、更科学和更客观的评价。因此,当面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关天安门城楼是否继续悬挂毛主席像的敏感提问时,邓小平不仅给予了肯定答复,而且借机再度声明:客观评价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继续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它在过去引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中共将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65—666页。】藉此涉外场域,特别是面向媒体人士的“慎重”表态,看似在直面历史问题和回应国际关切,但它已远超从常规意义厘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基调,确是在本质意义上标定了《决议》行文运思的政治逻辑甚至最终结论。可以说,如此因应也并非仅为回答法拉奇的一时提问,随着邓小平本着“真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向竹入义胜再度重申上述观点【《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他业已向党内和国内彻底阐明了“写不写、怎么写”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299页。】。
邓小平向法拉奇和竹入义胜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对完成《决议》的起草工作,特别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论题而言,实际具有着标志性的政治意涵。由此,《决议》起草小组的基本工作就应是以“写好这个问题”为前提,“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21页。】。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由此亦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国际社会:建国三十年来“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700页。】,“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09页。】,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有保障。甚至于,还可以继续借外事活动向亚欧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它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92页。】;抑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的,随后经由党的七大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且“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34页。】。
言及至此,可以确证邓小平所言不虚,“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而藉由外事活动中的直接回应来助力《决议》的起草工作,其价值远不止于解疑释惑或增进互信,更在于对外消除误解、建构形象和树立信心,对内省察问题、启迪思路和总结经验。更何况,循此由外而内的政治逻辑来消解中共的历史难题,不仅有助于“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而且更有益于拓宽中共《决议》起草工作的国际视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09页。】。在此基点上,《决议》起草工作的核心内容,就应当以客观的论据为基础,系统论证国际关切与国内瞩目的重大论题的真实性,据以做好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的系统阐述,以及形成对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评价。
三 论证与阐述:《决议》起草的核心论题求解
藉由前述梳辨可见,中共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务须论证并阐述清楚三大基本论题: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二是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三是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50页。】能否对此做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论证,特别是在理论上予以阐明和解释,将不止影响对国际关切的深度回应,更关系《决议》能否最终出台以及发挥类似《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作用,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可见,在拨乱反正期间做好此项工作,将是综合考验中共历史自觉、政治智慧和科学精神的重大政治工程。
如前所述,起草《决议》虽不同于撰写历史文本,却也同样是从历史结果出发的,需要对相关论题做回溯式研究和前瞻性叙事。从政治历史思维和论证技术路线看,邓小平在开始起草前就已认识到“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既应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还应秉持服从大局和“向前看”的思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45、451页。】。进入正式起草阶段后,胡乔木与邓力群进一步主张“要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能陷入具体的历史事件之中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换言之,可以采用“回顾历史的形式”来讲清问题,但无需把每个“问题说得很详尽具体”,重点是“在原则上把问题讲得更透”【《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1—62页。】。所以,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具有前提性的宏观历史评述问题应当率先敲定,这也是邓小平向起草小组反复明确的。具体而论,就是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阶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有曲折也有错误,但基本方面是对的,毛泽东在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入建设阶段后,也有好的文章和好的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14页。】。若单就后者而言,前七年取得了公认的成绩,社会主义改造获得成功,虽然部分工作急了一些,但确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后十年也应当肯定,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中间虽有曲折甚至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至于“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在此期间也有健康的方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21页。】。仔细考量可见,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历史的阶段性判定与整体性评述,实际已经涵盖了对《决议》“整个设计”的全部内容。同时,胡乔木作为具体领导起草工作的负责人,也逐段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历史,还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原因和发展演变过程,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和形成条件等重大论题,或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或将其置于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甚至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维度加以比鉴和判定,这就为“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论证和阐释前述论题提供了历史依据。【《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48页。】
若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论证与阐述看,在《决议》起草工作开始前,邓小平对此已经多有论述,既将其视作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亦强调它关系到安定团结和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全党应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予以重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35、493、537页。】在与陈云的讨论中,二人均强调毛泽东思想不仅绝对不能丢掉,而且在起草《决议》时“这项工作要做细。苏联丢了(党的指导思想),结果吃了亏”。【韩泰伦主编:《红墙档案》第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3页。】至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他再度强调应从“原则”的高度上加以“觉悟”和“认识”,只因此论题乃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转自程中原:《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比较而言,前后两个阶段论析的政治意指是基本相同的,但后者更为严谨和明确。在涉及具体内容的论证和阐述方面,邓小平强调应以“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据以在《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14页。】。与此同时,胡乔木也历数党的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解释的变化”,先是主张不采取“过分的提法”,后是强调要抓住“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46、56页。】。如此论证思路,彰显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要求,但它距离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还远远不够。其中,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界定就是个难题,邓小平在与胡耀邦等人讨论后,基于严肃历史和理论表述的考量,商定将其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46页。】。但即便如此,《决议》初稿也未能完全实现对毛泽东思想的“充分地表达”,自然也就无法为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书写和理论表达“提供一个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49页。】。
有鉴于此,同時也为深度因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误读,胡乔木提出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前者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对后者加以肯定。【《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84页。】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已然形成“两种形象”,他强调要继承和发展中国革命为世界展现新的光明前景和提供新的前途的形象。【《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0页。】基于此,从国际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出发,阐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从国际社会混同毛泽东主义即毛泽东同志的晚期思想出发,阐明中共并不是坚持毛泽东主义,“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05—106、126—127、140页。】,对树立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无疑具有内外双重价值。如此界定毛泽东思想的意涵,与前述邓小平的涉外回应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再至罗马尼亚政府总理维尔德茨到访,他又将对前述论题的阐析升格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进一步区别于毛泽东后期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言及至此,本论题看似已得到缜密而又严肃的论证和阐述,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它还缺少一个“全面的根据”和整体的“分析”作为历史支撑和理论依据。对此,陈云关于“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的重要建议,无疑为从党的整个历史(特别是毛泽东在这六十年中重要关头所作出的贡献和成绩)出发,评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奠定了更令人信服的基础,由此“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根据【《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而与此同时,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也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生、经验根据、内容体系、思想地位、文本呈现以及理论发展等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了“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六个方面内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要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历史的形成的和为全党所公认的;二是要肯定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总结,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三是要看到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通过中 国革命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实践逐渐形成的;四是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有科学体系并应当加以总结好的;五是毛泽东思想主要表现在《毛泽东选集》、党的文件和党内同志的重要著作上;六是毛泽东思想是需要继续发展的。参见《胡耀邦文选》,第213—216页。】上述两个层面,无疑从文本结构和理论内容上补足了《决议》草案存在的缺失,这就为更加完整地和准确地把握、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完成对树立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相关论题的论证与阐释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进一步而言,困扰前述论题论证和阐述的核心因素,确系毛泽东晚年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所犯的错误,以及由此在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引发的认知冲突和理论紧张。其中,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论题尤为典型,邓小平在《决议》起草工作开始前既主张应“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又强调“不能勉强”和“不必匆忙”去解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51、435页。】,足见该论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至《决议》起草工作开始,胡乔木也将其作为需要重点破解的难题,强调要讲清楚犯错的原因,若从国际层面上来看,主要是反霸权主义斗争范围扩大化影响至国内斗争加剧,以及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所致。【《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57、148页。】不仅如此,鉴于前述国际社会的复杂情绪和错误认知,他还强调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它与所谓反修正主义道路、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关联,借以让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中共不仅没有抛弃自己的理想,而且更不会走上苏联的道路。【《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1—63页。】胡乔木还认为,论证和阐述本论题还应做时段上和性质上的判别,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只应讲“错误”,在此之后的阶段才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犯下了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重犯的错误,它不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革命”,而且需要永远铭记其深刻教训。【《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76页。】
基于上述铺垫,1980年8月胡乔木又两次就本论题发表讲话和谈话:首先是作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的性质判定,确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其全面发动的标志,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负有责任,但毛泽东在基本维持解放军、国务院和党的统一等方面是有功劳的;其次是阐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既缺少经济和政治基础,也没有找到革命对象、依靠力量和提出革命纲领,不但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上没有指出前途;再次是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肇因,其中社会主义发展经验不足、规律认识不清,毛主席个人权威达到极点,以及国内和国际社会历史背景等均应考量。【《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17—127页。】胡乔木的上述论析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并且,邓小平本人也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历史中的错误,再度确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通过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实质分析”,开启了党内“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的先例;通过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仍存有健康的方面(如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粉碎了“四人帮”等),否定所谓“党不存在了”的说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308、304页。】基于如此论证和阐述,有助于达成对“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地和历史地评价,而其中秉持的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的评价指针,也成为评价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基本遵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直接回应国际关切时,实已确立评价毛泽东的基调、思路甚至是核心观点。在起草《决议》过程中,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也从多个维度对此展开了论证和阐述:一是着重说明“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25页。】,强调这不仅是针对其个人,而且是关乎党的整个历史及其评价,千万不能“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那样一棍子打死”【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陈云人生纪实》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74页。】;二是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页。】,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以及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92页。】;三是客观判定毛泽东所犯错误的事实及原因,认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确实存有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原因包括违反毛泽东思想、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国际社会背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25、742、719页。】,尽管他自己曾觉察并力图改正,无奈对情况作出了错误估计和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最终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50页。 】;四是综合评价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认定其晚年确有错误,但他的一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13、751页;】在毫不含糊地批评其错误时,不应过分损害或把所有錯误都归咎于其个人或个人品质,党中央和集体层面上也应承担一些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84页。】。
在做出上述论证与阐述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25、709页。】,特别是要藉由《决议》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做个了结,不再纠缠,一心一意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684页。】。针对毛泽东犯错及其责任承担问题,陈云特别强调要着重从破坏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错误加以界定,从毛主席和党中央两个主体维度判定主要责任与集体责任,甚至地方领导人也应担负一定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统观中央对上述三大论题的系统“论证”和权威“阐述”,着实有助于达成“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目标,这就为《决议》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历史经验夯实了政治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基础。
四 概括与总结:《决议》文本的政治历史书写
在起草《决议》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多次强调:“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既要写得集中,又要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不仅要做到“寓繁于简”,而且要将史实与理论互相穿插【《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67页。】。如此要求,既是源自对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认识【《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92页。】,也是基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诉求。循此路径,《决议》成稿既有对三大论题的科学概括,亦有对国际关切的最终因应,同时也融入了党对历史问题国际成因的客观考量。
最后通过的《决议》主要由八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总分总”的结构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前的革命历史,并从五个层面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意义,意在立足党的六十年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性维度,彰显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至第六部分采用同样的叙事结构,先总结建国以来的十项成就,后概述其间存有的认识偏差和实践错误,再分阶段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与意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成就、经验与失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错误性质、发展阶段和产生原因,直至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其中,对建国后的前两个历史阶段而言,《决议》借助历史贡献与重大失误的对比来确认毛泽东的功劳大于失误,以及说明毛泽东思想处于继续发展当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专章总结中,既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又作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政治定性。以此为基础,第七个部分先是立足毛泽东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立与发展,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朽功勋来肯定其历史地位,后是从历时性维度界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概括出毛泽东思想的六个方面内容以及三个方面的“活的灵魂”。《决议》的第八部分重申概括建国三十二年经验的目的,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来,此乃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十项经验基本总结的客观要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55—121页。 】
正如胡乔木所言,党要通过《决议》的起草和發布,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说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说明社会主义的革命不仅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给予革命的口号一些新的明确的内容。【《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85页。】《决议》作出的上述论证、阐释和概括,已完全不止于对外回应国际关切或对内解疑释惑,而实际具有着深刻的政治发展意涵,一是具有推进拨乱反正的社会政治功能,二是具有推动继往开来的社会发展价值。这是中共秉持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67页。】,继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从总结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转向进一步总结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政治自觉。从《决议》发表的社会政治效应看,对内说服了众多党内人士和起草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并把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真正说到了普通干部和群众的心底【《邓力群文集》第1卷,第553—554页。】,对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美国人曾高度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件,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不仅思路很清楚,而且事实阐述得也很明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204页。】。基于此,当邓小平在《决议》通过后向国际人士“重申在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或者向港台人士阐明不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就无法统一思想和统一认识,以及向布热津斯基强调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足以证明中国政策的连续性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754、759、760—761页。】,前述国际关切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权威性解答。
言及至此,或可做一个基本小结:尽管起草《决议》并非是源自外发性的国际肇因,但来自国际社会的担忧、猜忌、指责和期冀,确为中共开展政治历史的自我省察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场域。就其对解答内生性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价值来看,它或已完全不止于提供一种他者视角,而是切实推动着中共将自身重大历史问题置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时空,进而从单向度的消解历史问题走向更为深刻的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现代性思考。从历史问题到现实政策,从领袖人物到重大事件,从政治理论到社会理想,这些触及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敏感神经的重大论题,在任何时候都需中共历史地和科学地面对,不只是因为它们具有重大的国际国内影响,更在于高度关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性与革命信仰。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the CPCs Historical Resolution
in Historiography focus on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Chong
Abstract: The drafting of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d not originate from an external international cause, but the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suspic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the accusation of the so-called failure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s well as expectation for affirming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not only provide a foreign perspective for the drafting work from outside to inside, but also suggest an interpretation path relating to the CPC from one to the other. The CPC responding to the concerns timely, expressing its position solemnly and repeatedly elaborating its views were full of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viewpoint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monstration, elabor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ree core topics, namely,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Mao Zedong Thought, practically and properly evaluat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Mao Zedongs merits and demerits. This action of the CPC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umming up experience, unifying thoughts, and looking forward together, but also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new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hich lay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ful writing of the second significant resolution of the Party, and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CPC; international cause;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ography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