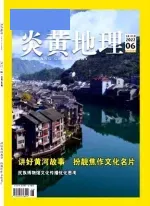基于三层视角下蒙古敖包内涵变迁的探析
胡峻雄
敖包作为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蒙古人文化的载体,同时也在现实生活发挥着实际功能。起初敖包具有指示方位、祭祀、确立边界的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它也产生出新的文化内涵。在个人层面上,人的理性化完成了敖包的“祛魅”,集体层面则是空间认同到文化认同的转向,对于整个乡村社区来说,敖包成为共建共享的文化实践地。敖包俨然成了一个更丰富且更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
敖包内涵的演进
敖包在蒙古语中又叫做“鄂博”,有“堆”或“石冢”的意思,是内亚草原上最为常见的人与自然互动产生的景观。一般敖包由石头垒制而成,上面插满松柏枝杈,树枝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哈达。它不仅是北方草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并且也与蒙古族的传统生计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
Isabelle Charleux通过对大量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蒙古旗图中的敖包进行分析,将敖包分为崇拜敖包和边界敖包两大类[1]。崇拜敖包来源于蒙古族早期对自然、祖先、萨满的崇拜,“敖包”祭祀从最初的山神崇拜演变为包罗万象的祭祀场所,如祭天神、地神、河神、雨神,祈求人畜安宁和兴旺,“敖包”成了各路神灵的汇聚之所[2]。由此可见早期敖包是人与神、自然沟通的媒介,是神灵在现实世界综合的体现,是人们与自然达成互惠交换的实践对象。除此之外,敖包还具有实用功能,许多敖包往往会建立在醒目且背风的位置,方便摆放供品和祭拜,同时还能起到指示地理方位的作用[3]。总的来说,崇拜敖包具有现实生存作用和文化符号象征的双重属性。边界敖包则是清王朝建立之初,对蒙古民族管理过程中所实施盟旗制度的具体表现。盟旗制度将众多蒙古贵族进行划旗编佐,各旗管辖地域按照山川、河流等地理走势固定下来,如果没有山或河,则设立敖包作为边界标志,并且清政府命令各旗之间互不侵犯[4]。因此边界敖包的产生是为了让蒙古各部众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方便管理所实施的一种政治手段。
从敖包的发展路线来看,敖包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复合体。它因社会的需求进行价值的再生产,但旧的价值并未就此消失,新旧价值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在一个敖包身上。边界敖包也可依据现实中的情景,赋予其神圣、吉祥的内涵,例如在过去旗内寺院的僧人有时会沿着该旗的边界念诵佛经,为了将祝福传递给境内的居民,而僧人举行仪式的地方往往就是边界上的敖包。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边界敖包不进行祭祀活动,这表明两种敖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现实情境的需要,边界敖包有可能具有行政和宗教的双重功能。显然Isabelle Charleux对敖包的分类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依旧为研究敖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工具,因为崇拜和边界凸显出敖包的神圣和政治两个内涵,基于这种分类体系有利于把握当下敖包内涵变迁的走向。
此次的田野调查点汗德尕特蒙古乡位于阿勒泰市东部,乡政府驻汗德尕特村,距城区23公里。以山地为主,大部分处于汗德尕特河流域,小部分在额尔齐斯河河谷平原。北高南低,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平原地带海拔540米左右。有哈萨克族、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聚居此处,乡上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为主,共占全乡总人口的80%,汉族占15.37%,其他民族占1.94%[5]。在调查期间通过亲身参加乡上举办的敖包节,并对村民進行访谈,深刻感受到敖包内涵在村民心中变得丰富且实用。主要通过崇拜和边界两种类型的敖包,从个人、集体、社区三个层面对敖包内涵的变迁展开相关探讨。
个体理性化对敖包的“祛魅”
早期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需要面临自然力量的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在生产或生活陷入困境或遭受不测时,牧民会借助敖包祭祀进行自我调适。兼具宗教和世俗功能的敖包祭祀,具有协调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功能[6]。
起初大部分敖包的祭祀目的都是为了求雨。人们向敖包献上牛羊、酥油、牛奶、美酒等祭品,希望栖居在敖包的神明给他们带来阳光、雨水、肥沃的草地,人们希望通过敖包祭祀实现人、群体与自然三者的和谐状态。面临雪灾、虫灾、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时,在人们的观念里一样可以通过祭祀敖包得到调和。现代社会当中,对敖包祭祀所依托的情感并没有过去那么复杂。汗德尕特乡蒙古族村民们祭拜敖包的驱动力更多归结于祈福、传统习俗和对故人的缅怀。过去草场对于维持家庭生计是关键因素,但如今即使草场不肥沃,他们仍可以通过田里种植的青贮、苜蓿,来解决牲畜饲料的问题;面对缺水的情况可以通过引水解决,甚至有能力的乡还会修建水库化解难题;碰上雪灾,人们可以用棚圈技术饲养牛羊;而虫害的问题,在科学的指导下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村民解释道:“现在家家户户都会种植草料,一般春种秋收,其间牛羊赶上山,可以把精力放在田地里,即使草料不够也可以去市场购买。现在冬季的时候,还会开翻土机将土犁一遍,把藏在土里过冬的虫子翻出来,来年的时候,就几乎没有虫害了。”因此,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计方式的改变,牧民们对畜牧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风险具有了较高的可控性。
在科学观念和技术革新的影响下,许多隐藏在敖包背后的面纱被揭开,人们的思考逻辑并非依靠过去的“相似律”和“接触律”。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概括与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依据。或者说现代性的后果在汗德尕特乡敖包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祛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理性思维对周围事物做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各种社会规范对自己的要求,建构起自己的社会角色、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在文化上,村民表示大年初一的个人祭祀敖包与清明节的祭拜先祖并无很大的差异,他们把这种祭祀看作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建立在鬼神观念之上。生产上,在农作物施肥时间的选择上更讲究周期性和科学性,而不是通过占卜选取日子。汗德尕特乡的蒙古族村民依靠现代技术,通过理性思维将生计生活的维持方式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也令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转向世俗化和理性化。
从空间认同向文化认同转变
过去边界敖包是各旗成员识别自己身份的重要空间标志。清政府明确规定蒙古人禁止越过本旗的边界,如果他们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在本旗之外被抓到,会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起初这种规定只停留在文书上,各旗管理者并未去实施。一直到了1864年清政府颁布新的法规,才成功在各旗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线,并且在各旗边界上设立相应的敖包。之后由于对各旗地区内自然资源的需求,1907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和各旗按照农业、林业、牧场、矿产等资源分布,重新绘制各自领土地图,这进一步加强了各旗成员依靠空间界限的身份认同。地图遂进入了一个可以无限再生产的系列之中,能够被印制到海报、官式图记、有头衔的信纸上,因其立即可以辨认与随处可见的特质,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深深地渗透到群众的想象中[7]。因此,敖包边界的设立和地图的制作,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社会成员产生了各自的空间认同。
在当下边界敖包的功能被乡与乡之间的行政划分所代替,草场的界限也由畜牧局划分,因此,边界敖包所带来的空间认同也发生了转变。汗德尕特乡通常会在5月份举办敖包节,该节日的举行促进了群体内部成员关系的维护和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对于乡上蒙古族村民来说,虽然不同年龄层对敖包节的参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彼此对敖包文化都有很高的认同。年轻人由于学业、工作、家庭等原因,虽然参与敖包节的人有所下降,但他们仍十分关注亲朋好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节日内容。中年人则依旧对敖包节保持着相当高的关注度,但因劳作的原因,往往会派家中的代表前往参加。老年人尽管腿脚和身体不像以前方便,他们依然热衷参加敖包节,在敖包节的现场甚至能看到不少老人骑着马来参加活动。对于处于蒙古文化圈外的其他民族,每年举办敖包节时,他们的目光都会有意或无意地集中到这项大型活动身上。一些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村民都表示参与过敖包节活动。另外对于在乡里开商店和饭店的村民,每年这个时候所吸引的游客是他们增加营业额的关键对象。在敖包节圈内的个人与集体依靠的现代科技手段缩小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个人情感在信息的分享当中找到了归属,同时节日的参与也增强了圈内人的集体认同与凝聚力。虽然这种认同也存在边界,但是地理空间的边界相较于这种社会边界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促成了圈外人向敖包文化圈内流动。总之,如今敖包节的举办,从过去的以空间为基础的认同转向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认同,为小群体和社区群体塑造了团结感,也缓和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疏离感。
从敖包的权力彰显到敖包共建共享
在清代人们拥有的土地权力因社会角色的不同而不同,土地的所有权归皇帝,旗中的执政管理者拥有占有权,牧民仅有使用权。地图的绘制过程往往也成为各旗权力相互博弈的过程,边界敖包的建立、标识具有权力表述的功能。当旗内执政者将中央赋予他的印章盖在地图上时,其抽象权力通过现实中的领土得到体现,有争议的土地的归属得到确认,而牧民在放牧时不得侵犯其他旗的土地,换个角度说边界敖包本质上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崇拜敖包来说,在过去它的所有权虽然属于民众和执政者所共有,但是二者在崇拜敖包面前所展示的关系截然不同,对于民众来说强调的是敖包与个人的关系,而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彰显着权力。英国学者Pollard-Urquhart于1935年经过锡林郭勒盟(内蒙古东部)的时候,被邀请参与盟长组织的敖包祭祀。他观察到盟长在随从簇拥下的政治表达,反映了地区领袖和政治下属之间的关系[8]。领导人现身敖包祭祀的场所强化了他们对土地以及下属的权利,由此看出,在过去集体敖包仪式具有很强的政治话语表达功能。由此可见,在过去无论是边界敖包还是崇拜敖包都具有某种权力的表述,因为对空间的指挥是社会权力的一个基本和普遍来源[9]。
如今敖包的权力话语,从特有、专有的等级区分转向共建共享的文化实践。在2006年祭敖包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敖包文化成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当地政府更多是将敖包节作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对象,例如2021年夏季举办的汗德尕特文化旅游节,2022年的“驼鹿之乡”汗德尕特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围绕敖包节展开的节日。这些节日在举行完敖包祭祀活动后,往往有赛马、射箭、摔跤等民族体育赛事表演,还有传统的奶制品、特色手艺品等商品的销售,表演者和销售者都为乡上的村民。敖包节举辦对官方来说,是为了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文旅资源,发展汗德尕特乡独特的旅游文化优势,提高汗德尕特的知名度,同时吸引八方游客,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作为文化继承者的蒙古族村民通过敖包节,一方面实现了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自身收入。在与蒙古族村民交谈当中,人们说道:“敖包节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蒙古文化,另一方面如果人来得多,也能促进乡里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面向大众的敖包节,不仅让乡上的社会成员可以加入敖包文化的共建之中,同时也增大了蒙古族传统文化分享范围。如今,当地政府和村民都将开发作为敖包的表述核心,一方面是蒙古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适应所做的地方实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敖包成为社区成员共建共享的集体文化资源。
当下的敖包是人们理性化的后果,是空间认同到文化认同的转向,是神圣空间、行政边界和政治话语的场所,还转变为了共建共享理念的实践地。敖包作为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媒介存在,这种互动难免会置身于一种局域性的情景之中,从而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衍生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正如格尔兹所认为的,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生成并且得到辩护,变化既是一种继承又是地方群体对未来的能动选择[10]。未来敖包对于汗德尕特乡村民,尤其对于蒙古族的意义还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发生何种改变,其依旧是蒙古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敖包成了一个复杂且有生命的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Charleux I,Marissa S.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oints of transition:Ovoo and the ritual remaking of religious, ecological,and historical politics in Inner Asia[J].Points of Transition,2021(52).
[2]迪木拉提·奥玛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3]杜卫红,蒋玉华.呼伦贝尔地区敖包分布及旅游文化价值研究[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2,30(04):17-20+31.
[4]包春丽.敖包的起源与盟旗制度[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8.
[5]马祥琛,恽芝艾.阿勒泰市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6]滕驰.蒙古民族生存智慧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以敖包祭祀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7,26(01):23-29.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Arthur Lewis Pollard Urquhart A L.An Oboo Festival of Western Sunit[J].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7(24):459.
[9]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