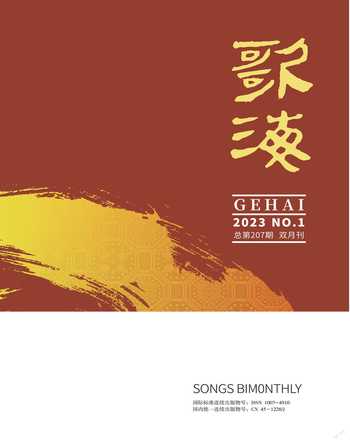“非遗”保护过程中内外价值的实现与冲突
李向振 马骁
[摘 要]辉南县的“非遗”工作呈现两种态势:一方面,以“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得到良好的推进与发展,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得到共同实现,即内价值与外价值达成和谐统一;另一方面,以“抬参文化”和“霸王鞭舞”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则呈现出停滞与建构问题,其原因正是内价值与外价值产生冲突,即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内外价值的统一与互相促进是实现“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内价值;外价值;多元主体
辉南县地处吉林省东南部,东邻长白山支脉龙岗山脉,东西流向的辉发河横贯县境,其建制沿革可追溯至9世纪中叶辽国在此设立的回跋大王府,16世纪中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的辉发部在辉发山筑城建都,后于17世纪初被努尔哈赤所灭,并将当地封禁为林场,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将海龙府东南八社划出成立辉南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辉南县,其建制延续至今。1截至2021年7月,该县共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涉及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舞蹈等多个门类。其中省级“非遗”四项:“辉发满族剪纸”“东北高跷双面人”“朝鲜族说唱歌舞乞丐谣”和“鹿肉食品制作技艺”。市级七项:“辉发琥珀木根雕”“霸王鞭舞”“百印堂平刀微刻”“玄武岩雕刻技艺”“殷氏蛋雕”“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和“古法封酒”。县级五项:“样子哨草编”“刺五加炒茶”“抬参文化”“凤爪山野山参栽培技艺”和“李氏混元膏”。2021年12月,随着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原属市级“非遗”的“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和“霸王鞭舞”进入这一批名录当中,成功申报成为省级“非遗”。
多年来,县政府部门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尤为关注,“非遗”作为既能带动旅游业发展的“文化资源”,又能彰显地方软实力的“文化名片”,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关注。然而,与申报数量的成果“颇丰”不同的是,当地的“非遗”保护工作目前正陷入瓶頸阶段,许多问题纷纷涌现出来,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地方财政难以支持、专业人员缺失、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传承人不愿继续配合申报、“非遗”保护阶段面临的主体缺位,等等。辉南县在“非遗”申报与保护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并非个例,事实上,这些问题几乎已成为现今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非遗”保护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何在?换言之,这些在各地都可能出现的共性问题是否有着相同的驱动因素?
在这里,刘铁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内价值与外价值这对概念有助于本文回答这一问题。他指出,所谓“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的时空中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1基于这一对概念,李向振进一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一场由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事件,国家通过“非遗”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也提高了社会文化治理能力;学者通过“非遗”满足其“精英意识”,同时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民众通过“非遗”满足了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又能将“非遗”“资源化”从而获得经济利益。2从本质上讲,“非遗”是由不同主体参与的文化事件,每一位“非遗”的参与者都希望通过这一文化事件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本文认为,当前各地在“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中出现的这类共性问题,其原因之一正是内价值与外价值的错位,即内价值与外价值产生矛盾并引发冲突。如果参与“非遗”的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能够和谐统一,那么承载这些诉求的“非遗”项目在申报和保护工作上就会进展顺利,反之,一旦内价值与外价值无法和谐统一,所产生的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便会导致这一“非遗”项目在申报或保护工作上遭遇停滞或终结。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学者关于内外价值的讨论,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分析辉南县“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中呈现的两极化态势,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予以阐释。
一、火热的“扒鹅”:内外价值的有效实现
(一)“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的概况
“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晚期,在“闯关东”的大移民背景下,创世人包洪海一家从山东招远地区来到长白山区,在今磐石市黑石镇落脚。黑石镇位于辉发河北岸,水草丰美,当地素有养鹅的传统,包洪海受到山东招远地区制作扒鸡的启发,便开始在他窄小的家庭作坊里制作扒鹅,制成后每日提篮沿街叫卖,养家糊口的同时以家庭传授的方式进行着这一技艺的传承,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民国时期,第二代传承人包庆元子承父业,为改善生计和扩大经营,他举家搬迁到朝阳镇(今辉南县县政府所在地),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此购置了一处店面经营扒鹅,取名“包氏扒鹅店”,这一店名延续至今。在该技艺的传承历史上,包庆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仅使其营生实现从“行商”到“坐贾”的转变,更是着力于制作技艺的改进和配方的研发。第三代传承人包长富则在父辈们创制的扒鹅技艺的基础上改进切割刀法,对扒鹅的制作技艺进一步完善。第四代传承人包丽梅是这一“非遗”项目申报时的主要传承人,她在制作技艺上与时俱进,并以文字形式撰写出来。在申报市级“非遗”名录时,将“包氏扒鹅”更名为“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包丽梅又将这一技艺传授给她的儿子高乐书,侄儿包清尹、包池,侄女包昂,外甥吴宝君等人。近几年来,包氏家族制作的扒鹅产品不仅在当地极具市场,受到广大民众喜爱,还远销长春、吉林、通化、天津、北京等地。
“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作为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分别于2015年12月、2019年11月、2021年12月被列入县级、市级、省级“非遗”名录,其技艺分为四步。
(1)宰杀:落雪后,将750克以上的活鹅宰杀,用85摄氏度左右的热水翻烫,褪掉鹅毛,剥净腿、嘴、爪的老皮,然后从臀部剖开,摘去内脏。
(2)清洗、去腥、改刀、入味:放在温水中洗净,然后在鹅体不同部位明刺,再用冷水浸泡3~4个小时,待鹅体内血水被浸泡出来后擦净,用刀把鹅体拍松,再放到小开的水中翻滚两下,捞出后将鹅身、鹅腿、鹅脖改成V字刀形,用专用佐料搓擦,使料味浸入鹅体,待2小时后上色。
(3)烹炸:用熬好的糖色将鹅全身涂匀,然后入沸油锅中炸至鹅身呈金黄色时捞出。
(4)配料焖蒸:将处理好的鹅放入蒸锅内,配以料汤,制作料包放入鹅体内,再将葱、姜、酱油、白糖、食盐等配料放入蒸锅内,蒸时用旺火蒸,微火焖,浮油压气,当年的鹅焖蒸3小时,老鹅焖蒸4小时。1
作为当地近年来“主打”的“非遗”项目,相关部门尤为关注,据当地“非遗”部门工作人员讲述,“辉发扒鹅”之所以能够成功申报成省级“非遗”项目,与其自身价值密不可分,在这一项目的申报书中,工作人员举例了三类价值。
营养价值。鹅肉含蛋白质,脂肪,A、B族维生素,烟酸,糖。其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同时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脂肪含量很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社会价值。一是促进养鹅产业的发展。目前辉南县养鹅业多半是农户自家小规模养殖,效益不高,鹅产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发展“辉发扒鹅”有助于调动和刺激农民发展规模养鹅业。二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力。辉南属半山区,牧草丰盛,水源充足,发展养鹅业大有潜力。
文化价值。目前,辉南县朝阳镇人冬季吃“辉发扒鹅”的习俗已经成为餐饮文化,加上东北人每到冬季吃“酸菜炖大鹅”的习俗,或再加上鹅的其他做法,鹅的餐饮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如此看来,发展“辉发扒鹅”,既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又刺激了养鹅业的繁荣,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1
当地人素有吃鹅的习惯,“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申遗成功后,在当地引发了一股经营各种“鹅”的风潮,许多经营扒鹅和烧鹅的店铺陆续开起来。甚至某些不是包家的店铺也在门外打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语,可见其影响之大。在经历“非遗化”后,扒鹅从过去老百姓饭桌上的一种吃食摇身一变成为一张当地的“文化名片”。许多外出务工和求学者在离乡前通常会购置一些扒鹅,一方面是在返校返工途中打打牙祭,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无论是满足口欲、提供就业或是文化传播,扒鹅表现得近乎完美,就算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也不过是因为“口味不合”。可以说,经历了“非遗化”的“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不仅更好地得到传承与保护,更获得一次扩大发展的机遇。借助政府支持,“包氏扒鹅”扩展店面、增加养殖,并将产品作为旅游食品向外推广。在负责申报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一项目从县级到市级再到省级的三次跨越,相对来说比较顺利。“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的“非遗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内价值与外价值在这一项目的具体实践中和谐统一、互相促进。
(二)“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的价值实现
在“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这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实践中,其内价值与外价值是如何实现统一的呢?如前所述,内价值是属于局内人的价值。作为一门以家族形式传承的传統技艺,它是持有者的生计选择与谋生手段。因此,传承手艺与扩大利润便成为该技艺持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非遗化”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和组织为这一技艺的申报与保护提供了许多方面的支持:辉南县免除了“包氏扒鹅店”的税费,降低了传承人的生产成本;辉南县广播电视台对“包氏扒鹅店”进行专题报道,扩大了其知名度;辉南县创意协会为其录制了视频,并发布在网络媒体上。可见,过去仅由包氏家族传承经营的扒鹅制作技艺,此时已有多种主体参与其中。相关部门和组织对“包氏扒鹅店”提供的帮助,一方面是为了项目能够成功申报,另一方面也使得该技艺的传承人追求的内价值得到良好实现。作为由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事件,申报过程中多元主体互相表达诉求与互相给予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局内人的传承人为追求内价值而向外“索取”,作为局外人的相关部门与组织则为了未来的外价值更好地实现而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与媒体宣传。通过这些帮助,局内人的内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被强化后的内价值也会对外价值进行反哺,实现“双赢”。
该项目的申报书提到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自然属于外价值的范畴,这些价值是由作为局外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学者、商人和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一项目的。他们将期待的眼光投射到这一项目当中,并希望该项目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这一点从申报书中的“促进养鹅市场的发展”“解决农村富余劳力”“促进饮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便能看出当地相关部门对这一项目的经济性与政治性期望。换言之,原本只为当地民众生计和生活服务的扒鹅制作技艺,通过“非遗化”而被赋予振兴当地经济以及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作为技艺持有者的包氏家族通过“非遗化”获得“非遗”传承人的身份,这一身份在为其个人和店铺带来名气和声望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所传承的扒鹅制作技艺在过去仅为谋求生计的基础上被赋予传承地域文化、振兴当地经济和协助当地人口就业等诸多责任。事实上,这些被局外人赋予的外价值非但没有阻碍局内人的内价值的实现,反而对其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辉南县对“包氏扒鹅店”税费的免除为其发展提供了政策性扶持,媒体对“包氏扒鹅店”的宣传一方面扩大了它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制作了一张优质的“文化名片”,在对内价值的强化过程中,外价值也有所收获。
综上观之,各方主体在“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申遗工作中实现了良好的互动,属于局内人的内价值与被局外人赋予的外价值达成和谐与统一,多方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共赢,各个主体的诉求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满足,这也是这一“非遗”项目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从县级到市级再到省级的三次跨越,而且在现今的传承保护工作上仍一派欣欣向荣的根源所在。
二、“抬参文化”与“霸王鞭舞”:内外价值冲突中的停滞与建构
内价值与外价值的和谐统一与互相促进是“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得以申遗成功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当地的一些处于“申报—认定”或“传承—保护”阶段的“非遗”项目一度陷入中断与停滞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正是在具体实践中内价值与外价值发生了矛盾,进而引发冲突。
辉南县东靠长白山支脉,是进出长白山的重要门户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人参的主产地之一。当地以林下参栽培为主,属半人工半野生的栽培模式。当地“非遗”部门曾想将县级“非遗”项目“抬参文化”继续申报为市级“非遗”项目,但遗憾的是,这一项目非但没有申报成功,反而作为县级“非遗”项目也已经名存实亡。究其原因,当地“非遗”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着这样的说法:
咱们这儿的“抬参文化”传承人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刚开始这个项目做得还挺好,后来做着做着就没钱了,因为这个申报中的资金一部分是我们(指非遗部门)出,一部分是传承人出,后来他(传承人)就不想干了,我们也就联系不到他了。1
这东西(指“抬参文化”)只有他(传承人)会,他要是不想继续申报,我们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现在连联系他也联系不上。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资金不够,他也是不想在这耗费精力了。2
目前,这一“非遗”项目的申报与保护皆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传承人的“失踪”、资金不足等原因,“抬参文化”只留存于当地“非遗”名录之中,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甚而因名存实亡而无保护之实。传承人的积极性不足且传承群体单一、当地政府资金的缺失、申报定级的困难都是这一“非遗”项目难以维持的问题所在。而且,这些问题几乎已成为现今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非遗”项目“难产”的通病。产生这类共性问题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内外价值的冲突导致的。在“抬参文化”的申遗过程中,作为局内人的传承人希望通过向局外人求助而获得资金帮扶,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满足。局内人希望借助局外人的力量对项目内价值进行“增值”,而局外人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这一期待,且局内人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迟迟不见“回转”,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他们便会退出这一事件,另寻他法。
除了无法继续推进而陷入停滞的“非遗”项目,已申报成功的“非遗”项目也存在许多问题。与“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同年一起被评定为省级“非遗”项目的“霸王鞭舞”,本体上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建构问题。
查阅资料可知“霸王鞭舞”项目申报是硬往上靠的。吉林省双阳、伊通两个地方都有,陕西、云南某地也有,具体是哪里起源的不清楚。1
笔者曾向相关人员追问“霸王鞭舞”的历史渊源问题,对此,相关人员大方地表示,这一“非遗”项目就是被建构出来的。据史料记载,“霸王鞭舞”应起源于清代,而后他们又将这一舞蹈与女真部落的战舞联系起来,从而强化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传统。这一技术性的处理手段与岳永逸所说的“非遗”申报叙述中遵循的神圣叙事原则类似。岳永逸指出:“一是要将原本传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创始人坐实,并考据出其生平、撰写其家世与家谱;二是渲染创始者的功绩、伟力,将其虚化,进而神化;三是强调与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之间的关联,有时难免将大历史叙事中被定格为负面形象的历史人物反转成为眼光独到并具有前瞻意识的文化保护先驱。”2“霸王鞭舞”正是为使“申报—认定”环节的叙述臻于上级官员与评审专家认可的“完美状态”,基于神圣敘事原则而对大历史的附会。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建构行为极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目的性的”书写行为,是对传统文化本真性的一种“亵渎”。我们且不说这样的话语背后体现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单从内价值与外价值的讨论出发,就能发现这一建构行为背后的某些“合理性”因素。
“非遗”申报要求所申报项目在一定地域内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同时,该项目应在一定群体内世代传承,且呈现出活态性的特点。在“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中,并非每一个“非遗”项目都能满足以上要求,有些因资料缺失而导致历史渊源不可考,有些则因传承人断流而导致保护难以接续。在内价值难以支撑起一个“非遗”项目的时候,为使项目能够继续推进下去,相关人员就难免使用某些“技术性手段”予以维持。在这里,以神圣叙事原则进行的历史建构成为最为便捷的手段之一。外价值通过这些手段被局外人赋予“非遗”项目,以弥补其内价值的不足。换言之,建构与附会行为使得申报文本的叙述得以“神圣化”,以便于更好地推进申报—认定的进度。而从内价值与外价值来看,正是因为作为局内人提供的内价值无法对局外人所需要的外价值予以供应,为使申报与保护工作得以持续进行,使得内外价值皆得以实现,局外人就需要通过这类手法对内价值进行建构,以满足其外价值的需求。一些崇尚文化历史性的人认为,这些“虚假的”手段破坏了世代传承的文化,是对文化的历史价值的“曲解”。然而,正如菅丰指出的,“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变化才是它本来注定的命运,历史越是悠久,其所发生变化的频率就越高”。1我们这里并不对这一建构行为的伦理或合适性做评判,这里要说明的是,建构手段的产生源自内外价值的矛盾,是内价值不足时,由局外人赋予持有内价值的局内人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局外人追求的外价值。
综上来看,以“抬参文化”和“霸王鞭舞”为代表的“非遗”项目所面临的停滞与建构问题,正是因为内价值与外价值产生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只有内价值与外价值都得到有效实现,即参与其中的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皆得以满足,“非遗”的申报认定与传承保护工作才能得到持续和稳定地发展。
结语
辉南县的“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呈现出两方面的态势:一方面,以“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在“申报—认定”与“传承—保护”过程中都得到良好的推进与发展。这固然是因为相比于其他类别,传统技艺更能适应当今市场环境和政府期待,同时也是由于参与这一项目的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得到良好的实现,即内价值与外价值达成和谐统一。换言之,作为“非遗”项目的“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之所以如此成功,得益于多元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内价值与外价值的互相促进,外价值借助内价值实现了扒鹅由食品到文化名片的转变,既有助于振兴地方经济又提高了当地声望,内价值借助外价值的宣传和扶持既提高了技艺知名度,又扩大了经营规模。由此,双方在一场“非遗”事件中实现了共赢。
另一方面,以“抬参文化”和“霸王鞭舞”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在申报和保护工作中产生了内价值与外价值的冲突,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建构的出现和项目的搁浅。“抬参文化”的局内人向持有外价值的局外人寻求帮助,无奈这一诉求落了空,因长期“收益甚微”而退出申遗,失去了局内人的局外人也因之没了抓手,项目只能搁浅。此外,在“霸王鞭舞”的建构问题上,我们若将局外人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搁置,仅从行动机制考量,那么这一看似“篡改”历史的书写行為自有其缘由,这是参与“非遗”事件的多元主体为追求内外价值的结果,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
“非遗”保护作为一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性文化事件,我们不能忽视参与其中的多元主体以及这些主体的不同诉求。离开了多元主体的这些诉求,“非遗”便失去其存在的合理依据,而离开具体的人谈“非遗”的价值,“非遗”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菅丰所说:“与其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价值,还不如说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发生关系才生成价值。”1同时,对待参与“非遗”保护的每一个主体,我们都应该同等看待,“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所有参与者都应该被视为参与主体,都应该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因为正是不同参与主体赋予非遗以多元价值表达,才使得非遗具有保护传承的意义”。2所以,无论是站在官方层面对“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的审视,抑或是站在民众角度以传承人为主的视角,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片面性。这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参与“非遗”保护的任何一个主体,且要以同等的视角看待他们。不管是作为局内人的当地民众所赋予“非遗”的内价值,还是作为局外人的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商业从业者所赋予“非遗”的外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存在。因此,从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出发,注重内价值与外价值的良好实现与互相促进,应成为“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的重心所在。
作者简介:李向振,博士,武汉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骁,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1辉南县县志办公室:《辉南县志》,深圳海天出版公司,1989,第1页。
1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2李向振:《作为文化事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外价值实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通化市辉南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书——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内部资料,2021年。
1通化市辉南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书——辉发传统扒鹅制作技艺》,内部资料,2021年。
1讲述人:张丽,55岁,访谈人:马骁,访谈时间:2021年7月16日,访谈地点:辉南县朝阳镇文化馆。
2讲述人:张丽,访谈人:马骁,访谈时间:2021年7月16日,访谈地点:辉南县朝阳镇文化馆。
1讲述人:张丽,访谈人:马骁,访谈时间:2021年7月16日,访谈地点:辉南县朝阳镇文化馆。
2岳永逸:《“非遗”的雾霾》,《读书》2016年第3期。
1菅丰:《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1菅丰:《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2李向振:《文化资源化: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理念转换及其价值实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