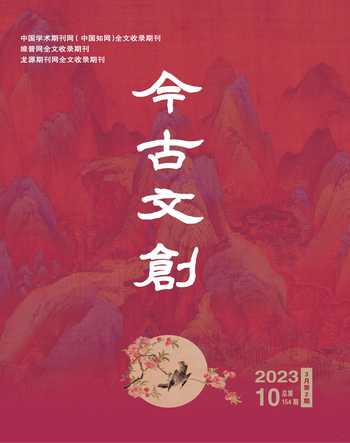浪漫神秘的想象之境
【摘要】 纳博科夫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大师,其作品中的东方主题却鲜少被挖掘。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东方书写传统,借助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一个浪漫神秘、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之境,在其间找寻自己的心灵乐土。在纳博科夫的东方书写中融合了作者的人生体验,浪漫主义激情与对美的追求跳跃于文字间。纳氏创造出的独特艺术世界丰富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东方主义。
【关键词】纳博科夫;东方;东方书写;中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3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10
一、前言
纳博科夫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在俄罗斯与美国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纳氏作品里的东方元素作为其创作出的璀璨星河中一粒亮眼的明珠,也应被纳入对他的文学研究范围内。而截至2022年9月,国内收录进知网的论文里没有一篇专门研究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东方主题。本文将从浪漫神秘的想象之境角度出发,分析纳博科夫创作中的东方书写,以期抛砖引玉,让更多研究者能关注并探索这位文学巨匠作品中渗透出的东方意蕴。
作为一位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一生都在流亡:他在俄国度过了青年时期,随着时局动荡辗转于欧洲与美国,晚年定居瑞士。可以说,纳博科夫几乎没有到达过东方;但他笔下饱满立体的东方古老、充满野性,弥漫着神秘的浪漫情致,这使他作品流露出独特的异域风情与东方气质。纳氏对东方的兴趣和探寻可在其文学创作中觅得踪迹。借助东方相关作品和地理科学资料,纳博科夫在想象中的东方自由而畅意地旅行,饱览她或绮丽旖旎或雄伟浩瀚的异域美景,考察她古老的文化记忆,书写关于她的诗歌与小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书写。
二、俄罗斯文学东方情调的继承
东方自古就是浪漫的象征,遥远之境充满着神秘感与异国风情,每一个旅居东方归来的欧洲人都会带回非凡奇妙的经历与终生难忘的回忆。对于东方的想象屡屡出现在欧洲文学中。俄罗斯文化更是由东西方两种元素组成,书写东方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传统。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方在欧洲文明与俄罗斯文化发展中愈加活跃,后者对东方的兴趣也愈加浓厚。普希金的东方主题创作出现在《仿古兰经》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29年远征期间埃尔祖鲁姆旅行记》《南方组诗》等作品,其中《仿古兰经》更被视为东方主题的里程碑之作。随后莱蒙托夫也在《当代英雄》《童僧》中展现高加索地区的壮阔风景与独特的文化风情。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中心论的创作意识出现了危机,学者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人文理想,以克服人类的精神分裂,实现个人与世界的新的和谐。[1]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皆在内容或形式方面从新的角度揭示了时代新的要求,意识观念的更新驱使着创作者探究未知的陌生现象,欧洲和俄国掀起了对东方精神文化传统的探索与研究热潮。白银时代的一些诗人也在笔间挥洒出对东方文明的喜爱与追求。古米廖夫通过诗歌《中国之旅》《中国姑娘》创造出欧洲人眼中东方情调的代表——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阿赫玛托娃潜心学习中国古诗的音韵,翻译出规模宏大、文采绚烂的《离骚》,译文备受称赞。20世纪初爆发的日俄战争更加速了俄国人迫切认识相邻东方神秘世界的进程,东西方文化彼此渗透。人们不断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进行深入研究,并游历其间。
纳博科夫出生在俄国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忠实守望者,对它的继承与发扬贯穿了自己的文学生涯。纳氏东方书写的文学创作正植根于普希金文学的深厚土壤中,成长于白银时代兴盛时期。其中普希金和古米廖夫对其影响最为深刻。
普希金两次高加索之旅开启了对东方世界的深入探求,对《古兰经》、伊斯兰文化的崇敬以及高加索之行带来的新认知使他的东方书写涵盖着丰富的东方文化。对于年轻的纳博科夫而言,普希金的古典东方风格成了一种创作典范。正如苏联文学评论家古科夫斯基评价道:“这是一种辞藻华丽、包含享乐的世俗理想的风格,它结合了俄国浪漫主义在其他民间文化中一直找寻的——野性的尚武精神与对坚强意志的渴求。这正是《古兰经》的风格,也是伊朗诗歌与高加索神话的风格。”[2]后来的纳博科夫把普希金创作的东方特色作为他联想游戏的部分,独特的东方情调也延续在这位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
古米廖夫是第一位将异域题材引进俄罗斯诗歌的诗人,他一生听从“云游的缪斯”召唤,多次游历西亚、非洲,這为其诗歌提供了大量新鲜素材。充满神秘感的东方逐渐成了他实现心灵探险与体悟存在之激情的圣地。他创作中非俄罗斯传统形象的引入也为白银时代的俄国诗坛带来了新的艺术意象。纳博科夫对这位诗坛偶像推崇备至,激赏他的英雄主义情怀与浪漫主义激情,其坚定、勇于探索的“征服者形象”深入人心。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纳博科夫也在表达对古米廖夫的爱:“我多爱古米廖夫的诗篇/它们的印象,犹如/留在脑海,余音不断/我既不会死在夏日凉亭/也不会因暑热而暴饮狂餐,而是与扫网中天国的蝴蝶一道/死在荒山之巅。”古米廖夫诗歌中的异域色彩也影响了纳博科夫的创作,他将这种古老神秘的浪漫元素与豪放不羁的人生态度融入了自己的诗行。
纳博科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自古以来的东方情调,尤其吸收了普希金与古米廖夫的东方书写经验。新奇玄妙的异域风格出现在其作品里,纳博科夫逐渐演绎出自己的东方书写特色。
三、诗歌中的归乡寄托与神秘风情
在纳博科夫笔下,古老的东方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有时纳博科夫也会对其寄托自己流亡的痛苦与归乡的依恋。他在这片神圣乐土上一直寻求着内心的快意洒脱。东方元素使纳博科夫的诗歌别具一格。
诗人将自己对东方主题形象的理解揉进文字里,正如回忆集《说吧,记忆》里有关克里米亚的片段所展现的:“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邦;气味不是俄国的,声音不是俄国的……整个很不自然的景色给我的印象是这是出自《天方夜谭》的一个插图美丽但可悲地删节了。突然我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普希金流放时曾在这里、在那些引种的柏树和月桂间漫步……”[3]克里米亚的异域风情、普希金的身影、对生活深刻变化的焦虑、与俄罗斯的告别,后来在纳博科夫的潜意识中都会与东方世界联系起来。
异域流亡一直是贯穿纳博科夫艺术旅程的主题。在俄国度过的青春、俄国的白桦林、沼泽湖泊、俄语、初恋,都在诗人内心最遥远的角落悄悄颤动。被放逐国外,诗人一直渴望精神上还乡,这种情感促使纳博科夫移民初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过往的画面被笼罩在记忆的面纱中——甜蜜又无比亲切。这些景象幻化成梦迸发在诗意的灵感中,有时又成为令人痛苦的谵妄与幻觉。
诗《活下去,不要抱怨……》(1919)建立在死亡与存在的永恒对立之上。普希金的《仿古兰经》散发出对精神真理的追求、昂扬的反抗意识、因真主意志而团结的部落的粗犷诗意:
振奋精神,蔑视欺骗,
昂首挺胸走向真理之路,
怜爱孤儿,把我的古兰经
向懦怯的心灵宣读![4]
纳博科夫模仿其起誓的命令式,并流淌出自己的诠释:
活下去,不要抱怨,不要计较,
没有过去的岁月,没有星星,
与纤细的思绪融合为一体
生成唯一的答案:没有死亡。
保持仁慈之心。不再渴求称王。
要去欣赏世间万物。
向万里无云的天空祈祷,
向黑麦浪中的矢车菊祈祷。
不要忽略构思很久的梦想,
而要努力做到最好。
在鸟儿身上,颤动的小鸟身上,
要学习,学习祝福![5]
纳博科夫将普希金对公众的大声疾呼转化为自己主观的心声,消解了社会层面的意义。他似乎正在为痛苦的灵魂寻求慰藉的秘方。诗人把自我经历与思考、灵魂的孤独放到了第一个特写镜头。对纳博科夫而言,在这个艰难时刻,东方神圣的美与和谐代表了救赎。沉浸在永恒世界的宏伟壮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学会仁慈与耐心——得益于此,他找到了保持心灵宁静的钥匙。这种普世的神圣之爱指引他去生活,去爱,去祝福存在的每一刻。只有这种爱会孕育希望与自我救赎的能力。这首诗的个性传递、在宇宙背景下对“我”的夸张认知、从普希金诗作中汲取到的严肃语调与精巧结构——都是纳博科夫的创新,也是对19世纪與20世纪初俄国诗歌中东方书写的创造性诠释。正如苏联学者卡缅斯基所言:“俄罗斯作家在古老的东方遗产中发现了生命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感情高于理智。这些构成了任何高雅艺术的先决条件。”[6]
朝圣者主题在白银时代诗歌中非常流行,布宁和古米廖夫都从《古兰经》中获得过灵感。纳博科夫也创作出自己的《朝圣者》(1927),献给他的朋友、同为柏林移民的评论家艾亨瓦尔德:
星星的主人,呼啸的风,
和弯曲的门槛,
葡萄之神,咖啡之神,
我微笑的上帝,
让黎明挤进我的玻璃杯,
让天堂微醺我,
……
那时我会听到:请记住
啜泣的火车
和陌生朝圣者的幸福,
他所在的地方是麦加。
他很快乐,在世界各地游荡,
游览月下的湖泊。
走过轰鸣的火车站,
和深夜的酒店。
哦,他是如何被吸引到光明的
异乡,到遥远的旅程,
我将努力走到窗前,
我想带回
所有震颤,春日的气息,
在我体内哭泣的气息,
而且——祖国的梦——
比任何梦都完美。[5]
诗人将归乡的强烈愿望与竭力到达圣城麦加的朝圣者的幸福对照,两者皆是自我漂泊的路上怀揣已久的激情梦想,是人生的最高礼赞。纳博科夫的心也飞向了那片从未涉足的神秘土地。对他而言,祖国化身于通往麦加的神圣之路,那是虔诚的穆斯林信徒生命的最后归宿,也承载着异乡人的痴心守候。
此外,纳博科夫的诗歌也体现出波斯文学苏菲派的传统特征,即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代表着美丽与真理的神圣化身,如作品《眼睛》(1920):
在昏暗的月夜下,在遥远古老的国度里,
诗人笑着这样对公主说:
鸣唱的蝉终会在橄榄树的叶子里死去,
皱巴巴的风信子上的萤火虫也将熄灭,
但你椭圆形缎子般的黑色眼睛
它们的甜美剪影,它们的爱抚
以及全白中透出几点蓝的色调,
下眼睑的光泽,
与上眼皮的柔软折痕
将永远留在我明亮的诗行。
人们会喜欢上你长长的、快乐的眼睛,
只要在大地上有蝉和橄榄树
有钻石般闪耀的萤火虫和湿润的风信子。[5]
在该诗中纳博科夫创作了一个迷人的波斯缩影,灵感来自波斯诗歌、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与古米廖夫的抒情诗集。东方世界的安乐、慵懒、鲜花和珠宝使人沉醉,爱情作为通向永生之路,与诗学的优雅相辉映,把读者带到一个遥远又古老的国家。
在纳博科夫的诗中也能听见古米廖夫《埃兹别基耶》的回声,波斯属于古米廖夫心中“温柔而灿烂的东方”。纳博科夫有意以他的风格入诗,用其描绘树木、鲜花与瀑布神圣之美的手法将美丽的花园变为天堂的化身。夜园的低语、蝉鸣、爱情的永恒誓言、湿润的风信子,萤火虫如钻石般闪着荧光——这一切都再现了迷人的东方之境。诗中公主的俊美容颜与极乐天堂都将通过艺术被永久保存。遥远异邦的浪漫情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充满亦真亦幻的色彩。其中也可窥见纳博科夫对神秘东方的神往。
诗歌《统治者》(1923)大量运用了古米廖夫东方诗歌的传统形象——孔雀、豹子、棕榈树、繁星天空:
我拥有隐形的印度:
请来到我的蓝色天空下。
我将命令赤裸的巫师
把蛇缠到手腕。
对你,美得不可方物的公主,
我将献上锡兰般的吻
为了爱,为了我所有的古老与奢华,
以及繁星点点的天空。
我的孔雀和天鹅绒般燃烧的雪豹
在想念;宫殿周围
棕榈树丛像暴雨来临般沙沙作响,
我们都在等待你的脸庞。
我将送你耳环——两夜流淌的黎明,
我将送你心脏——来自我的胸膛。
我就是国王,如果你不相信,
即使不相信,还是请来吧![5]
“我拥有隐形的印度”与古米廖夫的神话元素“精神的印度”遥相呼应。古米廖夫在对兰波《醉舟》的评论中描绘了一个火车站:“在那里你可以买票/前往精神的印度”。他兴奋于印度神话及其灵魂转世的思想,将过去的理想空间称为“精神的印度”——它基于时间的“反向”流动,主人公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转变回到“精神”的过去,寻找另一个奇迹般的世界。通过对它的找寻体现了至善至美的理念。
纳博科夫想象自己踏上了东方之疆,内心的热情与野性从诗行间澎湃而出。沉醉在印度的绮丽风光,诗人构建了一个神圣的彼岸世界。这里是诗人的王国,是未经探索的人间乐土,也是梦幻的自由空间,具有了乌托邦性质。他在这里寻求超然洒脱的诗意,并寄托了永恒爱情与美好理想。这些元素构成了诗作《统治者》独特的艺术世界,体现出纳氏对东方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认知思考。
纳博科夫诗歌中的东方具有神秘浪漫的色彩,同时也是诗人的心灵慰藉之地与实现爱与美的神圣净土。幻想的东方形象吟唱出迷人的异国情调与旅人的万千心绪,为纳博科夫的诗作注入新鲜与奇幻活力。
四、小说里的神秘国度与静心之地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东方元素体现出作家对这片遥远土地的探索,不仅透露了他对东方文化风情的兴趣与认知,也寄托了其浪漫情怀与美好愿望,为白银时代小说的东方书写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章节以《天赋》为例证,通过文本细读分析纳氏小说创作中的东方印象与别样风情。
《天赋》主人公费奥多尔是位具有文学天赋的俄裔流亡者,小说讲述了他在柏林的心灵历程与文学上的成长之路。其父是位著名的旅行家与昆虫学家,经常周游世界进行探索,最后一次前往中亚考察后再也未归。小说第二章节中,费奥多尔看着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的画作,在追忆父亲的同时跟随他的足迹展开中亚的想象之旅。
小說描绘的想象之境——中国被蒙上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这里的现实具有流动性与多变性。整个世界的样子都是半透明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中。现实中的事物与其“倒影”相融合,通过艺术感知的游戏性互动,形成了小说中的新现实:“只有中国的晨雾才能摄人心魄,使万物颤动——那简陋茅舍的古怪轮廓,拂晓的峭壁!仿佛跌进一个深渊……树仿佛成了一位植物学家的谵妄……”[7]有时,雨水将物体的凌厉线条被冲刷掉,现实成了一种无边界的、流动的多样化存在,不断改变着形态。“霏霏细雨仍在飘洒,但是带着天使降临时那种难以捉摸的突兀。顷刻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处于懒洋洋的、自身茫然的状态……”[7]有时,现实变成了一种幻觉,表现为一种欺骗性的“倒影”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无法准确判断事物与其“倒影”之间的界限。“还有蜃景——大自然,那个手法老到的作弊者,创造出不容置疑的奇迹:水的幻影异常清晰,映出了附近真实的石块!”[7]小说中也存在着幻想与现实中幻觉的形象交叉。“在一八九三年戈壁瀚海的死亡中心偶然邂逅——起初将其视为七色光线投射的幽灵——两个脚穿中国凉鞋、头戴圆毡帽的骑行者……”[7]
《天赋》的中国书写不仅营造出浓浓的异国情调,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全新感知,它是神秘、难以界定又不断变化的。纳博科夫借助中国元素,为不受限制与模糊隐约的存在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与此同时,费奥多尔想象的中国之行可看作是纳博科夫对自己未能成行的中国探索之旅的补偿。1916年,年轻的纳博科夫打算资助博物学家格鲁姆-戈尔日的昆虫学研究队伍并随其前往中国西部考察,但计划因革命爆发而夭折。而在《天赋》中,随着费奥多尔小说创作的推进,主人公成了这部小说的作者。人物费奥多尔变成纳博科夫其人。[8]费奥多尔以及他背后的纳博科夫以身临其境的第一视角想象在西藏的流浪生活。古老东方的神秘国度一直吸引着纳博科夫亲身前往探索。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与无趣的移民生活中,纳博科夫的主人公仿佛失去了个性,国际大动乱打乱了个人的命运,他们没有机会表现出自身潜力便带着梦想与对祖国的回忆逃到一个想象的世界。纳博科夫在其创作中再现了普希金东方浪漫主义作品的风格。故事的底色是奇特极端的自然景观:荒漠、山路、异域动植物、疾风、暴雪与沙尘暴。
同时,纳博科夫在东方描绘中运用了时间的相对性,加快或减慢了时钟速度。小说里的侨民生活是一种无意义的生存体现,对它的记叙便被加速。而这个想象的世界被慢动作般展现出,其核心主题是父亲穿越亚洲山脉和沙漠的旅行、对从前生活在俄罗斯时的记忆复苏与幽灵般的回家之路。在这趟想象之旅中,每一个细节琐事对费奥多尔都很重要,它们证明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真正“现实”的存在。在某个瞬间,纳博科夫也会穿插大量细节。东方国度的美丽令费奥多尔着迷:“前面出现了戈壁沉寂的沙海……丝绒般柔软的空气里唯一能听见的是骆驼吃力急促的喘息和宽脚掌的刮擦声……维纳斯的五克拉钻石在西边天际消失,与它同时消失的落日余晖,在它苍白、橘黄和紫色的光线里,扭曲了一切景物。”[7]
这个鲜活、浪漫、热情的东方世界再次映衬了费奥多尔的现实生活寂静得可怕。“第一性”和“第二性”世界在他的认知中紧紧交织。他赋予了这片想象之境乌托邦色彩。在这里,主人公找到了令人兴奋的“第二性”生活,比他存在的现实更真实、更令人向往。他的偶像——父亲、诗人古米廖夫、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其他真正的旅行探险家们都蔑视命运,把生活过成一种壮举。费奥多尔同他们一起,创造了自己的命运——另一种浪漫积极、充满朝气的生活。
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并非实际的中国,只是他想象中的东方世界。对异国动物群和植物群的描写、具体地理细节均借鉴了博物学家普热瓦利斯基的著作。但纳博科夫渴望探索这个古老的神秘國度,这片浪漫又充满未知的土地承载着他在局势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流亡他乡的漂泊生活中的美好幻想与对心灵平和宁静的追求。
五、结语
纳博科夫作品里流淌出的东方情调富有诗情画意,给予了美的感受。借助于东方元素,作家在诗歌的自由疆土上构建自己的神秘王国,在小说的遥远国度里找寻一片心灵乐土,东方有时也被赋予几分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纳博科夫笔下的东方书写既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东方写作传统,又创造出自己的东方诠释。在这个浪漫神秘的想象之境,他将自己对人、自然、爱情和生活的体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玄妙新奇的艺术感观。纳博科夫创作中的东方主题、意象与美学丰富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东方主义,成为世界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武晓霞.“第三王国”的理想——《皇帝与加利利人》与《叛教者尤利安》比较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
[2]Гуковский Г. А. Пушкин и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J].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1940,№ 2.
[3]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普希金.普希金诗选[M].高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Набоков В.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M].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кад. Проект,2002.
[6]Каменский З.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чала ХIХ века[M].М.:Наука,1980.
[7]纳博科夫.天赋[M].朱建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8]郑文东.一条永不间断的“莫比乌斯带”——纳博科夫《天赋》的叙事结构分析[J].外国语文,2009,(2).
作者简介:
李怡帆,女,汉族,河南焦作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