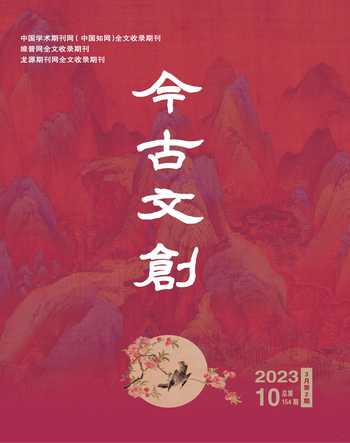“反了+人称代词+了” 结构形成过程考察
【摘要】 “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不同于一般的“V了O了”结构,其特性主要表现为动词“反”与宾语位置的人称代词无法直接组合,且呈现出“动作+施事”的语义关系。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该结构经历了“施事+反了”“反了+施事”“反了+人称代词”“反了+人称代词+了”形成过程;同时“反了”也经历了主观化过程。从形成机制来看,整个“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是说话人为了凸显重要信息,依据“V了+人称代词+了”结构类推形成易位句形成的。
【关键词】“反了+人称代词+了”;双“了”句;类推機制;主观化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11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38
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经常见到如下表达:
(1)老荒听到了老健在说什么,在花鲇身后一个劲儿蹦跳,喊:“你等着我怎么跟你算账,你等着!真是反了你了!”(张炜《你在高原》)
(2)“反了你们了,小东西!”老兰拉下脸来,恼怒地喊,“黄豹,把他们弄出去!”(莫言《四十一炮》)
以上句子的画线部分可概括为“反+了+人称代词+了”,有人将其看作“V了O了”结构的一类(靳丹琪,2015)。但从形式上看,一般的“V了O了”结构中的“V+O”都可以组成述宾式复合词或述宾式短语。前者如“发了财了”“结了婚了”,后者如“吃了饭了”“进了城了”;而“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中的“了”是不可或缺的。从语义上看,一般的“V了O了”结构中的动作和宾语的语义关系大多数为“动作+受事”关系,而“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中的宾语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施事,和前面的动词“反”构成“动作+施事”关系。有人将施事作宾语的句子称为施事宾语句,但施事宾语句中的宾语往往具有无定性(张伯江,1989),“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中的人称代词一定是有指的,且很多时候都是定指的。因此“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施事宾语结构。
综上所述,“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跟一般的“V了O了”结构有较大区别。其动词与宾语的组合无论是组合形式还是语义关系都不同于一般的“V了O了”结构。同时,这一结构意义整合度较高,已经实现了熟语化,在语言表达中被广泛使用。文章尝试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其形成的过程,以解释为何非常规表达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接受度。
本文语料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及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①。
二、“反了”结构的历时考察
语言类型学中的一个主流观点是汉语属于SVO型语言,“施事+动作+受事”应该是汉语的常规语序。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施事+动作+受事”也是现代汉语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凡是违背这一语序的就应当看作是有标记的句式(朴珍玉,2014)。也就是说,“施事+反了”与“反了+受事”结构是常规的、相对无标记的;而“反了+施事”结构则是非常规的、相对有标记的。本章将着眼于“反了”搭配对象与语义的变化,分析“反了+人称代词(施事)+了”这一特殊语序的形成过程。
(一)“反了”后出现施事
“反+了+NP”结构最早见于宋代,语序全部为“反了+受事”。即受事全部分布现在“反了”之后,施事往往隐现,如:
(3)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说“皆天理也”?(《朱子语类》)
(4)便若桀纣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这个道理。(《朱子语类》)
到了元代,开始出现“反了+施事”结构,如:
(5)如今见有破不尽黄巾贼,尚自极多。又反了刘备,若相合一处,怎生奈何?(《三国志评话》)
(6)有上大夫言:“街亭诸葛反也!”帝问文武:“倘反了军师,西川不能作主?”(《三国志评话》)
例(6)很具有代表性,前面说“诸葛反也”;施事在前,动作在后。但与“反了”搭配时,语序变为“反了军师”;动作在前,施事在后。
对语料中“反了”与施事组合的用法进行统计,共找出元代语料10条,其中“反了+施事”与“施事+反了”结构各5条;可见“反了+施事”和“施事+反了”两者共存。明代语料有55条,其中“反了+施事”31条,“施事+反了”24条;更能够看出这种共存不是一时的现象。在明代,同一篇文献中经常同时出现这两种结构,如:
(7)晁田、晁雷听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吓的魂不附体。(《封神演义》)
(8)话说众多文武见反了方弼、方相,大惊失色。(《封神演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还出现了如下例句所示的结构:
(9)不料沁州已反了存孝矣!(《五代秘史》)
王力(1999)将“矣”归为陈述语气词,用于已经发生的状况,表示一种过程;同时指出语气词“了”继承了古代汉语中“矣”的用法。例(9)的“矣”可以译成“了”,与句末语气词“了”的功能基本相同。因此这类“反了×矣”可以看作是“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的早期形式。
(二)“反了”出现主观性表达
前面列举的这类“施事+反了”或者“反了+施事”结构,都是叙实的用法,即表述发生了造反事件。从明代开始,“反了”开始出现明显含有主观义的用法,比如《水浒传》中有如下用例:
(10)孔明也恍然叫道:“啊呀是了,这样一说,就满都对窍了。今日中营满加更动风言风语,要二王卢俊义挪进寨来,名是同居,暗行监管。要燕青、蔡庆等归六尚局。带了吕方往南边去,查其心意,要面会方七佛,先取荆襄。天寿也进兵徐州,派李铁牛先打东京,这样看来,真要反了。”
(11)李逵大叫:“反了罢!”宋江曰:“军马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
(12)大化急着喝叫道:“吴德,吴德!你待要反了怎的?生个人来没有人行!你道天下事,没有良心天理吗?”
(13)那几个随从的叫声:反了!揎拳捋臂,一拥上前,邹润使起拳脚,纷纷跌倒,都跌得鼻青嘴肿。
例(10)中的“反了”出现在“要……了”结构中,表示未然事件,表达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即由前面陈述的事实,推测造反事件即将发生。例(11)中的“反了”同样是未然事件,后跟语气词“罢”用在祈使句中,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建议。例(12)中的“反了”用在疑问句中,表达了说话人认为听话者行为违背常理的主观认识,以及对听话人强烈不满的主观评价。不过这里的“反”仍是“造反”义,从后文“相公不好,吴德果然反了”就可看出。例(13)中的“反了”加上感叹语气独立成句,已经完全是主观义的表达,不再表示“造反”这个事件。这里的主观义已经十分接近于“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的主观义。
明代类似于上述例子的用法还是较为少见,语料中“反了”在明代的用法共有103条,其中有3条体现出主观判断义、4条体现出了主观建议、7条体现出主观评价义,占比只有一成多。到了清代,主观性的用法大幅增加。在236条清代关于“反了”的用法中,有163条非叙实的用法,占比接近七成,而且全部是表达强烈不满的主观评价义,如:
(14)好呀,嫂子你哪招的这么个野男子在屋里,我哥哥不在家,你真要反了。(《彭公案》)
由于带有显著的主观性,这类“反了”可以受“简直、真是”等评注性副词修饰,如:
(15)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桃花扇》)
(16)福田怒道:“难道要我不听玉帝的话,倒听你们的话么?真是反了!来人,把这一起不知轻重的混帐东西,捆出去斫了。”(《红楼梦》)
此时的“反了”开始有明显独立成句的倾向,在163条表主观义的用法中,有99条是独立成句的,占比达到六成,如:
(17)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说。”(《红楼梦》)
(18)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这股无名火哪里按耐得住,大叫:“反了!”(《七剑十三侠》)
(三)“反了”后出现人称代词
到了民国初期,语料中开始出现人称代词作为施事出现在宾语位置的用法,如:
(19)张放被拿,还破口大骂道:“反了你,敢拿天子侍臣么?”(《汉代宫廷艳史》)
现代汉语中,“反了+人称代词(施事)+了”结构完成定型,其例句俯拾即是,如:
(20)小杂碎,反了你了,没有我这个老子谁给你抡镐?(莫言《白鸥前导在春船》)
(21)秦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反了他了!(莫言《蛙》)
经考察,此时的“反了+人称代词+了”所表达的皆为对人称代词所指代对象强烈不满的主观义评价。
根据上文对语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宋代,“反了+受事”为主流表达。到了元代,“反了”结构后开始出现施事,“施事+反了”与“反了+施事”两种形式开始共存。到了明代,“反了+施事”结构被普遍使用,出现了“反了×矣”这种可以看作“反了+人称代词+了”早期形式的结构。同一时期,一部分“反了”开始用来表达批评指责等主观情感态度而非客观陈述。到了清代,“反了”用来表达强烈不满的主观评价义成为主流用法,一部分“反了”开始受到评注性副词的修饰,“反了”独立成句成为普遍现象。民国初期,人称代词开始进入到“反了+施事”结构中;在现代汉语中,“反了+人称代词+了”快速定型。
三、形成机制
张伯江、方梅(2014)从功能语法的角度讨论了汉语中的主位结构,指出一般叙述语体中主位在前述位在后的语序体现了语用学的可处理原则(processibility principle);而述位在前主位在后的易位现象则凸显了简练原则(economy principle)。“反了+人称代词+你+了”结构体现的正是这一点。在一般的叙述语体中,说话人都是先从听话人熟悉的情况(人称代词)说起,再引出新的信息(反了)。这是在最符合听话人心理认知过程的信息结构处理方式。但是在简短的对话中,重要的新信息(反了)是说话人急于说出来的内容,次要信息(人称代词)放到了不凸显的位置上。从考察的语料来看,这类结构全部出现在对话之中,且往往表达强烈的主观情感。“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正是说话人为了凸显新信息而对常规语序进行调整的易位句。
陈前瑞(2006)将“V了O了”结构称为双“了”句,并认为最早的双“了”句出现于北宋的《朱子语类》。根据语料的考察结果,最早的“反了+受事”结构也是出自于此。陈昌来(2021)指出,双“了”句在元代趋向于固定;这是“反了+施事”结构出现的时间。该文同时提到明代的双“了”句有了四音节的倾向,且开始出现凸显主观义的用法;这与“反了”出现凸显主观义用法的时间相同。陈前瑞(2006)指出,双“了”句到了清代的使用频率大幅增长;同一时期“反了”的主观义用法也是快速占据了主流。到了现当代,双“了”句的能产性大幅增加,很多人认为已经出现了构式化的倾向;也正是这一时期,“反了+人称代词+了”定型并逐渐熟语化。因此有理由认为,“反了+人稱代词+了”结构的形成是“反了+施事”结构向双“了”句类推的结果。
引言部分已经指出,典型的双“了”句中的动词和宾语在语法上应该可以直接组合成述宾式复合词或述宾短语,在语义关系上应该为“动作——受事”关系。这样看来,“反+人称代词(施事)”类推形成双“了”句的阻力似乎较大。但随着“V了+人称代词+了”结构的演变,能够进入带该结构的成分也是在不断扩大,其范围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V了+人称代词+了”中出现弱受事性宾语
根据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V了+人称代词+了”的用法最早见于元明时期,如:
(22)方才要送你性命,我替你说着,饶了你了。(《全元曲》)
(23)不长俊的小花子儿,剃头耍了你了,这等哭?(《金瓶梅》)
到了清代,出现了如下类型的表达:
(24)你這会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进来,你就当着我们大家伙儿,拿起他那根烟袋来,亲自给他装袋烟,我就服了你了。(《侠女奇缘》)
(25)好王爷,我知道你的本领强。实在的怕了你了。(《绮楼重梦》)
例(22)(23)中的画线部分都可以改为“把”字结构或“被”字结构,即“把你绕了”“你被耍了”。而例(24)(25)中的画线部分不可改为“把”字结构或“被”字结构。“把”字句在意念上主要表示对人或事物的处置,实际上是表达一种“致使”关系,后面的宾语通常是动词所影响的对象,即受事。“被”字句主要表示“受到影响而产生结果”,同样表达“致使”关系。例(24)(25)中的画线部分不可改为“把”字或“被”字结构,说明这类表达所强调的并非致使关系。换句话说,例(22)(23)的人称代词受事性较强,例(24)(25)的人称代词受事性相对较弱。
(二)“V了+人称代词+了”中出现不能直接搭配的成分②
“V了+人称代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其两个变项都可以直接组合,如上述四个例句中的“饶你”“耍你”“服你”“怕你”在语料库中都可以检索到相关用例。在元代所有的语料都属于这种类型,而明代开始,出现了少量动词和宾语不能直接组合的情况,如:
(26)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陷了你了!(《金瓶梅词话万历本》)
句中“陷了你了”去掉两个“了”后,“陷你”一般不能直接组合③。
清代开始,此类情况有所增多,如:
(27)“你每日极好,也想着你做不出这样事来。只是我没处怨了,就屈了你了( 《聊斋俚曲集》)
句中的“屈你”也不能直接组合。
明代开始,一部分“V了+人称代词+了”结构中的人称代词出现了弱受事性的用法,整个结构不再强调致使关系。同时“V了+人称代词+了”结构开始接受无法直接搭配的两个成分进入。除此之外,前面提到自元代开始就有“反了+施事”这种结构的存在,“反了”自明代开始就出现了主观化,清代出现了“V了+指人名词(施事)+了”。由此看来,“反+人称代词(施事)”类推形成双“了”句并不存在太大的阻力。
四、结语
“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是一类特殊的“V了O了”结构,这类看似反常规的结构之所以能够广泛为人们所接受,是由于自身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
从“反了”的施受事位置来看,“反了+施事”的格式最早在元代出现,明代出现了“反了×矣”这类“反了+人称代词(施事)+了”的早期形式。从“反了”的主观化过程来看,明代“反了”出现少量凸显主观义的用法。清代开始“反了”表主观评价义的用法大幅增加,同时可以受评注性副词的修饰;而在现代汉语中“反了+人称代词+了”已经完全不表示客观陈述,并实现了熟语化。
从“V了+人称代词+了”结构的演变来看,清代开始一些受事性较弱的人称代词开始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同一时期又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直接组合的成分出现在了动词和宾语的位置。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再加上“反了+施事”结构的广泛使用与“反了”的主观化,为“反+人称代词(施事)”向“V了+人称代词+了”类推形成双“了”句降低了阻力,最终形成“反了+人称代词+了”的用法。
注释:
①这里将语料库中包含“了”的合音语气词,如“反了你啦”也算作“反了+人称代词+了”结构。
②依据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检索范围包括了古代汉语库与现代汉语库。
③“陷你于不义”之类的用法中的“陷”为“设计害人”之义,与这里的“使人受到损失”义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1]靳丹琪.“V了O了”构式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2]张伯江.施事宾语句的主要类型[J].汉语学习,1989,(01):13-15
[3]张云秋,王馥芳.概念整合的层级性与动宾结构的熟语化[J].世界汉语教学,2003,(03):46-51+3.
[4]朴珍玉.现代汉语施事宾语句与基本句的偏离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2(04):33-36.
[5]沈家煊.不对称与标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陈前瑞.汉语双“了”句的兴衰及相关的理论问题[A].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陈昌来,陈红燕.主观极量义构式“A了去了”的来源及双“了”构式的历时演化[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2):126-136.
[10]李传军.类固定短语生成的类推机制[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02):11-13.
作者简介:
刘儒昊,男,汉族,山东济宁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法理论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