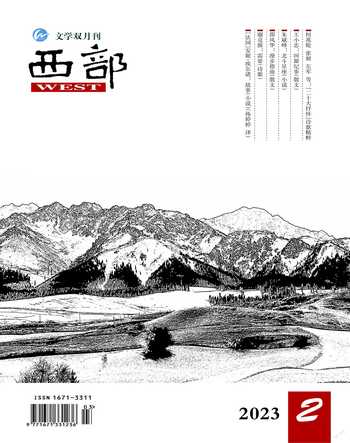入侵
吴莉
静默几日之后,我们要去调查外来入侵生物。电话是孙教授打来的,他说,虽然庄稼快收完了,但也得抢时间,扩大队伍,分三个小组分头行动。
这是农业农村部下达的任务,地方农村农业部门委托河西学院和县庄稼医院去调查,时长为一年。调查对象是外来植物入侵、农林业外来病虫害入侵、水域外来生物入侵。
我与孙教授、大学实习生吴文静一组,调查县城以西的十六个点,包括田间、公路两旁、水库、温室、林场等地。
点与点之间尽量不要调查相同的生物。孙教授说,要把典型的选上,如果没有新发现的入侵物种,一个点调查一种就可以了。另外两个小组接到任务以后,向东去了,我们小组向西走。
孙教授带我们寻找,同时负责踏查标本。吴文静操作手机程序,设点、选项、拍照、录入。我负责开车,做表上登记。我们都做了二十四小时内核酸检测,这是近段时间的生活必备。
在城郊的花海,找到了第一个入侵生物——灰绿藜,藜科,一年生草本。就是我们叫的灰条,小时候当猪草往家里背,到了庄稼地里当杂草往掉除。可其繁殖力已经失去控制,在农业以重点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后,水肥像猛兽一样施进土壤,灰条和其他杂草与庄稼拼着长。最野蛮的地方长出了排山倒海之势,水沟里和地埂子上无处插脚,人气急了就用火烧。田里的灰条和其他杂草长了一茬又一茬,农药打了一次又一次,一直打到庄稼成熟,它们的第N代子孙又长出来。农民对庄稼医生说,你能得很,你的科学再发达,能发达过野草吗?
灰绿藜也是杂粮之一,叫藜麦,能长一人多高,成熟期红得像火,能够点燃一个秋天。
孙教授放好样方框,让吴文静拍照、选项、录入。吴文静设探查路线为312国道两旁,具体位置为双桥村,海拔和经纬度便自动跳出来了。生境类型属水浇地,踏查面积为二百亩。再选择入侵类型、入侵物种、危害对象,填上盖度,拍照取了五个样方,录入系统。
孙教授采了标本,我做好登记,又走着看看,还发现反齿苋、小藜等外来物种。再扩大面积应该还有,但没有发现新的入侵者,调查一个即可。无论灰绿藜,还是反齿苋和小藜,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有的还当野菜吃过,我纳闷它们是什么时候入侵的。
地上有干活的人,友好地与我们搭讪,得知我们调查外来入侵生物,惊讶地过来看。想不到我们这里也有外来入侵的东西,大西北这么偏僻,究竟是咋入侵来的?他们问的兴趣盎然,我们听的云里雾里。他们又说,都是我们经常见的,你们要说是外来的。
还认识了锦葵和龙葵,属本土植物,虽都是葵,天壤之别。锦葵也叫冬葵,锦葵科。龙葵属于茄科,尖叶,叶子与辣椒的叶子像,藏着某种刺激。外来植物和本土植物一起生长在我们的本土,不做调查,谁也不会去想,哪个是入侵的,哪个是本土的。
而后到清泉村,在熊掌菊制种田里发现圆叶牵牛,和熊掌菊都是外来物种,都在开花。圆叶牵牛开得隐忍而明媚,熊掌菊开得张扬又恣意。其他地里有干活的人,拉草、挖葱、犁地,生活秩序井然,历年景象依旧。
熊掌菊不高,一半正开,大红。花瓣与大丽花的相似,稍长,燃烧的火苗一样往上蹿,却抑制不住成熟,将要为种子而枯萎。一个年轻媳妇在地里摘花籽,一撮一撮把残叶抖掉,小心放入塑料桶内。花籽又轻又碎,不小心风会吹走。她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不戴手套的手上似有魔力,稳稳地摘下花籽,放入桶内。她不看我们,却与我们搭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农业部门派来做调查的。调查啥?我们给她说明白,然后在她的地里采样。一边采样一边向她了解,一天能摘多少?摘不上一斤。一斤能卖多少钱?一百多,两天才能摘够一斤,刚够工地上一天的工钱。那么少?你以为呢,她说。她显然也嫌少。我们以为比打工的钱多。我说,那怎么还种?她说,和种子公司熟了,找上门来让种,就种了一亩多地。
每年都种吗?
她说,人家说了就种,不说也不一定。我们说,相当于帮忙了。她没作声。
我说,听说以前种子公司在这里吃香的很,不是谁想给人家制种就能制的。
她说,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工比种地好,不担风险。种地防不住就会赔,人少了不行。我们的熊掌菊摘籽的时候,一个帮忙的都没有,雇人又划不来,摘不及的就落到地里了。
我问,人呢?她说,年轻人都在城里工作,年老的干不动,自己都没人照顾呢。
那你是专门种地的吗?我问。
也打工,抽空照管这些制种。她说。
非要种吗?种地不耽误打工?
她说,外面来的制种公司,这几年疫情影响境况不好,到你的地方了,找到你的门上来,不帮着种点也不好意思。再说,他们也不会让我们赔的。
吴文静打趣,外来者就是這么入侵的啊,多么友好的融入,嘻嘻。
从熊掌菊地出来,孙教授说,制种是很赚钱的,种子公司给农民一斤一百多块,他们出口能卖一千多块。农民是最辛苦的,也是挣钱最少的。不过这几年出口不利,种子公司也不好过。
下一个点是南湾村,村口挡了一辆大卡车,以为是收洋芋的,路口设了收购点。看摩托车和步行的人从小道口进出,也不见洋芋,才知道为了防疫,拒绝外来车辆进入。由于距调查点还远,我们只好返回,绕三公里到第二个入口,蓝色彩钢房又挡住了路。旁边仍有小道,摩托车和步行的人进进出出。我们也步行过去,走进玉米地做调查。取样四翅滨藜,我们叫的另一种灰条,灰白如银,种子四颗四颗挤在一起,微微仰头欲要分离,像四个方向展开翅膀,因此得名。
玉米田是今年多起来的,庄稼医院引入进口新品种推广种植,经测,亩产收入远远大于马铃薯和洋葱,以后可以大面积推广。玉米作为主粮之一,需求量大,耐储运,又是家畜的最佳饲料,营养丰富,受市场影响一直平稳。
玉米算不算外来入侵,不是进口了新品种吗?吴文静问道。
孙教授说,外来入侵只是一个相对词语,大多数物种追根溯源可能都属于入侵者。玉米四百多年前传入中国,可在中美洲已有几千年历史。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就是本土物种,即使入侵者,那也是很久远的事了。比如河西走廊种的大多数玉米,还是河西走廊繁育的。就因制种公司总部在国外,被称作进口品种,这当然与商家的宣传推销也有关系。所以,即使外来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界线也会慢慢模糊。
吴文静说,比如新冠病毒,也是一种新的入侵,无论从哪里来,它都是人类中新出现的一种生物。
孙教授说,没错,除非消亡,否则迟早都会成为常见生物。人也一样,中国男人取了外国媳妇,生下的孩子在中国,那就是中国人。外国媳妇的户口落到中国,媳妇也是中国人,只是出生地不在中国而已。等他们的孙子、曾孙、玄孙一代代出生了,谁还会说他们的祖母是外来的。
吴文静笑道,是啊,气象专家能说清楚风和云是哪个国家的吗?
进祁店村时,路被土堆挡住了,土堆那边是祁店水库,再往前走是祁店休闲园,平时旅游的车就是从这儿经过的。我们从土堆上步行过去,做祁店水库的调查,发现了非洲虎尾草。尺把高,花扁平,有虎色斑纹,中间分叉,像老虎的尾巴,应该像非洲虎的尾巴。见过狗尾草、猫尾草,还是第一次见虎尾草。植物也有长成动物相的,一定也有动物长成植物相的。长相这东西有没有入侵呢,若是没有,那些没有血缘关系而长相一模一样的人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夫妻相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世界太复杂,缤纷交错,自然界的东西在自然界漂流,飘到了人的地盘,人便把它视为入侵。岂不知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
由于步行到祁店村的踏查点太远,我們只好返经北湾村,到拾号村上312国道,从野猫山子的那条路上去祁店村。一路上有放羊的,还有坐在放羊人身边来聊天的,一人坐一个马扎凳,一只手放在大腿上,另一只手夹根烟,胳膊肘支在另一个大腿上,眼睛盯着羊,嘴里聊着天,样子像在衡量江山。这乡野人间出入自由,来去逍遥,西北风把什么都能刮来,也把什么都能刮走,山河依旧,岁月难测。儿女们喜欢城里的生活,我们这些老家伙下世了村里咋办。我们住过的房子咋办,村里的那个大戏台谁演谁看。另一个说 我和你能守了冬夏,守不了春秋,以后的日子是他们的。
上了312国道行驶到野猫山子,看到祁店村的牌坊拐进去,村村通的水泥路延伸到村里,村口的疫情防控执勤点挡住了我们。蓝色的民政救灾帐篷在路的一边,红色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路的另一边,红马甲的执勤人员向我们走来,让我们扫路边的健康码。我们一边拿手机,一边又说,不用扫,都是绿码。执勤人员笑一笑说,扫扫吧,为了村里的安全。我们扫过,都是绿码,语音自动报出,你的核酸健康码为二十四小时阴性。执勤人员才到帐篷边,打起横杆让我们通行。
我们走在安全的村子里。白杨树密密地长在沟沿上,护住了沟沿帮子,也为村子带来清凉的风。村里的一段路原本宽阔,一半堆着砂石和砖,车辆只能从另一半通过。新农村建设正在进行,路沿上的砖还没有镶好,不知何故正在停工。庄子前修了丝路广场,模拟的长城和驼队,一个从村里走出去,一个从远方走进来。几个老人坐在丝路广场晒太阳,仿佛晒着丝绸之路,也晒着他们古老的岁月。
踏查点在休闲园内,只有鸦雀声叽叽喳喳,半天喊不出一个人影。围墙上挂着“齐心协力防控疫情”的条幅,人可能因着疫情走了。穿过休闲园的通道空空荡荡,平时来吃饭的人就在这里排队。我们径自走进温室大棚,成熟的番茄和辣椒生了病,不知何故没有防治。有的果实正在掉落,以自我腐烂的方式回归土壤。还有其他蔬菜,平时供园里的餐厅使用,今年归还给了土地。见到守园人吴多明,依然那么敦厚朴实,问园里的蔬菜为什么不卖。他说,卖不上几个钱,走街串巷影响疫情防控。又问园里卖饭吗,我们还没有吃午饭。他说,停业中,等疫情过了再营业。我说只好到东乐碰运气了,早知道就带点馍馍啥的。他说,东乐也在停业中。我说,312国道边的饭馆也停了吗,那在村镇以外。他说归镇上管,肯定要停,外地的过路车多得很。我找电话问东乐。吴多明说,如果东乐也没有,我让家里做点吧。我们说不行,太麻烦了,往前走走再看。吴多明说,有啥麻烦的,一顿饭嘛,都到家门口了,又不是到了没人烟处。电话打通,东乐饭馆的老板是我同学,他说,你们到来就做好了,在家里一起吃吧。那就到同学家吃吧。
吴多明陪我们调查园里入侵情况,没发现新的物种,最多的还是灰绿藜,一季长好几代,又怎么能除掉呢。做了登记与采样,告别了吴多明。
由于路不通,去很近的静安村只能回到312国道,经过执勤卡口扫码进入村里。到静安村走乡道可以直通山羊堡。山羊堡有两个点,山羊堡村和山羊堡林场,与甘州区相邻。
沿路调查静安村、大桥村、小寨村、大寨村,又一次发现非洲虎尾草,从祁店水库跑到小寨村了?又看到几个庄门口的洋姜,正在开花,黄色的太阳花像金色的门神,替小寨村的人家守护着家门。孙教授讲,洋姜的学名叫菊芋,又名鬼子姜,是一种多年宿根性草本植物,菊科,典型的外来物种,名带个“洋”字不言而喻。洋姜的根会无限繁殖,只种一次每年生长,遗留在土里的根茎和根块都会发芽。即使春天用除草剂处理土壤,洋姜也会又长出来,因为土壤处理只能处理胚芽,除不掉根块。而且这东西吃法单一,除了腌制再没有更好的吃法,所以一般不种,种一年烦几年。
我在庄稼医院工作多年,知道顽固性杂草可以用内吸传导性除草剂除掉。比如,草甘膦,在植物活力旺盛时注入或喷施,药量充足的情况下会传导到根部,从而破坏生长点,导致整株死亡。吴文静又一次打趣,一物降一物,总有降住它的东西。
孙教授说,别说科学,宇宙万物相生相克,总有与你相克的东西。那些庄门口的洋姜若不浇水,几天就死亡了。
说话间到了城西村,大部分庄稼已经收完,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们像麻雀一样飞来又飞去,麻雀在快乐中飞翔,他们在需要中奔走。
燕麦草长在地里,为给家畜种点青储的草,麦子收完又种上的。由于缺水,现在很少有这种一年两茬的种法,春夏种粮食,秋季种牧草。我们在燕麦地里发现了异样的燕麦,不是人工种出来的,是那种混杂在其中自己长出来的。虽然也是燕麦,但农人并不喜欢,产量低,适口性差,还欺田。专业上把这样的燕麦叫野生燕麦,简称野燕麦。野燕麦与人工种植的燕麦都是外来物种,本质上没有区别,野生的适应性更强,人工种植的产量更高。
我们在人工种植的燕麦地里调查混杂的野燕麦,盖度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三十。毫无疑问,带了野性自然顽强。野燕麦抗逆性强,抵抗病虫害的性能会影响同类,使其特性也趋于顽强,杂交育种也是这个原理。大多数情况下,野燕麦不被农人喜欢,主要是牲口挑拣,口感差,缺乏“催”的暴力,达不到养殖的满意度。
而长在其他庄稼地里,野燕麦就成了彻彻底底的异类,想方设法也要除掉,除燕麦的化学农药多种多样。记得刚刚包产到户,我们的承包地里主要杂草就是燕麦,其他杂草很少。我们一家人蹲在地里除燕麦,燕麦和麦子一样多。麦子是人种下的,顺着篓沟儿长,也顺着人意长。燕麦沟儿里沟儿外地长,自由散漫得比麦子猖狂。至于燕麦是哪里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就赖给地和种子,好像他们走了私货。我母亲常常说,那时候的燕麦咋恁多,我们一铲一铲地除,除不净了再拔,拔不净了再捋,后来干脆不捋了,一直拔,一直拔到庄稼成熟,整整拔了三年才拔净。其实哪里拔净了,燕麦躲到地埂上了,躲到水沟里了,躲到空闲处去了。几十年来,谁也没有把燕麦拔净,谁知道燕麦是怎样和人斗智斗勇的。不仅没有拔净,人还用它杂交出了优良品种,大面积种起来,不但成了我们的粮食之一,而且还是畜牧的上等牧草。只有专业上说它是外来的,老百姓喜欢还来不及呢,管它是哪里来的。
到东乐饭馆错过了午饭时间,我同学专门为我们又做了一顿。饭后给他付钱,他说不营业不收钱。我们说不能白吃,你这是饭馆。他说,饭馆又咋了,卖饭的不能让吃饭的饿着肚子,又不是饥荒年。我扫墙上的二维码付了过去,他白我一眼说道,钱多了就付下。不要说乡亲,就是过路的外地人吃不上饭了,也不能不给口饭吃。我这同学,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长。
到西屯村发现了荠菜,孙教授说荠菜也叫独行菜,也是外来物种,开过花已经结籽,在葵花地边。葵花秆子已砍倒了,堆在地里等着拉走。有荠菜从秆子堆里长出来,像葵花秆子直起腰来,变成了荠菜,重新开始了新的生长。一个女人在不远处割燕麦,就她那块地格外绿,衬着她粉色的头巾,像春天开的一朵花。她没在意我们,自顾自割草,她此刻的世界没有来人。我被她的专注吸引,什么样的节奏促使她急着干活,全神贯注到无人入侵她的视线。这样的农人不要打扰,她的心里只有干活。
调查完西屯村过沙河,宽大的沙河是我县的母亲河中下游,一直到张掖入黑河,可惜在九十年代就干枯了。随着祁连山积雪减少,我县的用水出现了危机。
到了十字路口塑着三只山羊的地方,是山羊堡村。村里全是移民,来自河东地区,听说大多是懒汉、败落的人、异想天开的人。但都是日子寒酸的人。来这里开荒种地,寻求梦想的生活,居然定居出了河西最长的村道。庄门口的花卉和果树告诉我们村里有人,院里院外晒着玉米,好像人们盼好的日子,披上了秋天金色的外衣。
乡道上有钢磨房,自动钢磨正在推磨,磨房外坐着一堆男人,头挤在一起炸着金花。吵嚷声忽炸忽静,像是金花不炸,他们要炸。这样的情景很少见了,年轻人去了城里,偶尔回来也玩着手机。只有这些老男人才炸金花,坐在大街上,也不怕谁笑话,反正大伙儿都玩着。
我们让吴文静下车去问路,山羊堡林场的路怎么走?半天了一个人抬起头来,回了回神,还没说话另一个人又抬起头来,向西一指,说,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说完又扎进了人头堆里,不知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他拉了回去。
我们一直往前走,在一块苜蓿地里发现了野苜蓿,车停在路边,下去采样。苜蓿也是外来物种,和燕麦一样,人工种的叫苜蓿,自己长出来的叫野苜蓿。野苜蓿小茎小叶,格外高,收拾不住长势。藏在大田里显而易见,不太绿,像个另类,灰不溜秋地暴露了自己。如果不是人工种植,谁还去分野生不野生的。人本来带有歧视性,听起来好像野生的死皮赖脸一样。
突然,开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满满当当拉着玉米秆子,唯恐拉少了,左右两边码得比路宽。那一车玉米秆子像一座山,缓缓地向我们移来。谁在路上,谁就会和他一起排山倒海。谁不让路,它就让谁尝尝劈头盖脸的厉害。我们的车掉头是来不及了。那人喊,快点,刹车不灵。我飞快倒车,幸亏有导航,不然半公里长的路,我可能要把脖子倒歪。好不容易倒在了岔路上,那人又绕着手喊,让开,让开,我要从岔路上走。我们的车就像一匹被追赶的惊马,没路了就翻山越岭,我从路肩上开过来,最后一刻避开了那车。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上了岔路,后面跟著骑摩托车的女人,头上是蓝头巾,胳膊上是黑护袖,黑色的口罩,像押车的,英姿飒爽。
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出了水泥路,还看不到山羊堡林场。便顺着土路走,像瞎子摸象,也不知摸到了哪里,却发现了一埂窝麻子。麻子在玉米地边,直着脖子比玉米还高。小时候生产队里种过麻子,有时候收麻籽儿,有时候不收麻籽儿。麻秆子非被女人们刮走不可,拿到水沟里压上石头,渥上几天,等渥软了拿出来晒个半干,剥下麻皮子纳鞋底子。麻子是典型的外来物种,孙教授给我们介绍,麻子叫大麻,不是毒品的大麻,名字相同,但是两种大麻。这种大麻也禁种,内含什么成分忘记了,张掖禁止种植,再没有人去种了。
我后来查百度,发现麻子和大麻长得像,释义也像,思前想后没想明白。明明一模一样,孙教授却说不是同一种大麻,不是同一种也会被禁种?禁种了也还有野生的,人又怎么能够禁住野的呢。
大麻比玉米高,长在玉米边像玉米的贴身护卫。可又能护住什么呢,西北风吗?还是日头?玉米怎么就接受了麻子,别的地埂窝里也接受吗?
折断麻秆子剥下的麻皮子又韧又长,麻皮子可以搓成麻绳子,麻绳子可以纳鞋底子。那时候我母亲把麻皮子剥好,坐在小板凳上伸开一条腿,卷起裤子,手里一吐唾沫,就开始搓麻绳子。麻皮子很干,时不时往手心里吐一下唾沫,手便增大了搓力,再也无敌了。山丹方言里常在名词后面带个“子”字,大致是小、细或稀罕的意思,麻秆子、麻皮子、麻绳子、鞋底子、板凳子……母亲把麻皮子搓成麻绳子纳鞋底子,鞋帮子烂了鞋底子还不烂。有时大妈、婶婶、和我母亲,坐在太阳弯弯里搓麻绳子,一搓就是一下午,腿都搓红了还说不疼,搓麻绳子的腿比麻绳子还皮实。
眼前几百亩就这点麻子,确实也挺稀罕的。麻籽儿看上去绿着,捻几颗微微黄的放嘴里嚼,香喷喷的味道让人不由想起麻腐包子。麻腐包子就是麻籽儿做的,我们这里种的叫小麻子。麻籽儿皮薄,拿到磨上连皮磨碎,闻起来香,看上去油旺旺的就是麻腐。麻腐掺土豆、糖萝卜、胡萝卜馅儿,包的包子让一个冬天都是香的。现在很少见麻籽儿,超市里卖的是大麻籽儿,皮厚,即使有老式钢磨,也磨不出麻腐了。麻腐包子差点就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今天的麻子又让我想起了它。
我们给麻子拍照、采样,录入系统,然后寻着山羊堡林场而去。土路难走,颠颠簸簸,车里带进来尘土,加上后仓里麻子标本的味道强烈,混合在一起,让人头晕恶心。记得小说里写过大麻,亦仙女亦魔鬼,难道魔鬼的魔力使出来了?我打开车窗透透气,一阵尘土乘虚而入,车内顿时成了土洞,我们顿时成了土人。又关上车窗,尘土从后向前继续侵来,才发现后仓没有关上。放了大麻标本关上的呀,怎么又开了?停车下去关仓,关仓的人上来成了重量级的土人。我们忍着麻子的味道,在狭窄的田间小道上拐来拐去。山羊堡林场在哪里呀?我们拖着长长的土龙的尾巴也找不到,一个林场能藏起来它的绿吗?
庄稼收掉一片荒凉。除了尚没砍去的玉米秆子,茬板子地和犁了的地空得让人发慌,不知多久没下雨了,这里似乎一直旱着。我们摆脱不了车后的土龙,车轮陷进溏土里碾过,也被溏土碾埋着。突然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赶快停车走下去看,孙教授说土里有个石头,从车的底裙上刮过去了。他说不要紧,已经过来了。于是我们继续再走,再一次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孙教授再次下去看,发现又是一块石头,车的底裙刮出了伤痕。
鬼路,魔鬼之路。我骂着。我像炸金花炸输了一样,又骂魔又骂鬼,魔鬼刮伤了我的车,也刮疼了我的心。炸金花炸输的是钱,魔鬼刮伤的是车。车是兄弟,载人上路,即使半夜三更一个人开车,不下车我都不怕魔鬼。这鬼路刮伤了我的兄弟,也刮没了我的耐心。伤就这样侵袭而来,伤的是车,也伤了我的平静。我们像入侵者一样疯天魔地,找不到目的地,也回不到出发点。农村的路为什么这么难走,指路的只指给大概的方向,走路的走出了村庄,被搁在半道上。外来侵入的生物尚且有去处,走在村子里的人却走没了方向。
炸金花的人说,一直往前走,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可我们走得艰难,颠沛流离,迷失方向。有村子没路,有路没人。指路的人脑子被金花炸昏了,只听话不听音,指路只指大概的方向。既不指左,也不指右,既不具体,也不明确。我们把天走荒了,路走没了,既走伤了车马,又走伤了人,可我们不得不还要走下去。
我们走得昏昏沉沉,走得迷天魔地,只跟着主路走,忽视了理想国不一定就在主路上。不知又走了多久,又走了多远,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废墟。废墟上耸立着无数城墙,城墙比烽火台高大,比真正的城墙坐落凌乱。城墙是墙又不像墙,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像一个神秘古国,又像一座曝光的鬼城。城墻前立了牌子,看不清上面的字,明白是保护单位。保护单位四周有绿色围栏,一人多高,只有鸟儿能飞进去。这就是一直往前走到的头,绿色围栏画上了句号。
这是哪里?这不是山羊堡林场,山羊堡林场不是这样,林场里种着果树和粮食,而我们眼前……
凝固的气氛被孙教授打破,只听他喃喃地说,怎么跑到甘州的碱滩镇了,这里是碱滩镇的汉墓群呀。
我的天呐,进入甘州区地界了。我们还没走到山羊堡林场。难道山羊堡林场去甘州了?
回吧。孙教授说,我们走过了地界。
一直走的路会走过地界,没错,再走下去就是南辕北辙。可我们连再走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把一直走的路走成了绝路,古人已经埋在了这里。
原路返回不可能了,只有重新找路,既然找不到山羊堡林场,那就去312国道吧。上了国道,就有了方向。后退一段路后,向北的岔路出现在眼前。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这条路的前方能看到312国道,也能看到甘新铁路。
岔路两边还是玉米,玉米地里有人干活,或许是偷玉米的。两个媳妇在掰玉米,拿着大大的袋子,一人一只手拿住袋口,另一只手往下一掰,纷纷装进袋里了。孙教授下车去问路,她们指着前面路说不通,建议我们找别的路。正准备走,孙教授又问,你们怎么掰那么多。媳妇诧异地看过来,随后一笑,或许听出了话里有话,说道,多偷些回去存起来吃,你们偷不偷?
我们刚要说我们不偷,俩媳妇又爽朗地笑起来。这是我们家的玉米,找人来收棒子,按亩数算工钱,你瞧,亩数收下了,棒子却没有收净。你们想吃了掰上些吃去。
孙教授问,真的吗。媳妇说,谁跟你开玩笑,到地头了还稀罕你吃的那点。我们乐了,进地就掰了起来,每人掰了一抱子,没有袋子可装了。又问媳妇要袋子。不行,我们的袋子也不够,你们自己想办法。说着,孙教授还是拿了她们几个袋子,媳妇看着,也没说什么,和一个大婶说话呢。大婶从哪里冒出来的,刚才只有两个媳妇,是不是我们进地那会儿,她提着个尼龙袋风尘仆仆过来。
大婶说,你们掰的都是人家的大棒子。我们愣住了,要付钱,两媳妇不要,对大婶说,是我们让掰的。她们问大婶,这地上的路能通到312国道吗?大婶给我们指,能,一直走,一直往前走,路就把你们带到了。又是一直走,指路人也只能让你一直走了,关键还得自己走。我们没有选择,一直走只是一个方向,走便是了,大不了走错了返回来重新再走。
我们一直走着,才发现田间小道有多复杂,隔几块地就有一个岔路,看不出哪条是主路哪条是岔路。走错了几回,返回来再走另一条。终于,走到了一条居民街上,门口有车,路上无人,可我们上不了312国道,路口都被堵上了。绕到另一条街上,问了坐在庄门口、戴着老花镜、拐杖放在一边、腿上放着厚厚一本《聊斋志异》的老人,才从他们走的一个隐秘出口上了312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