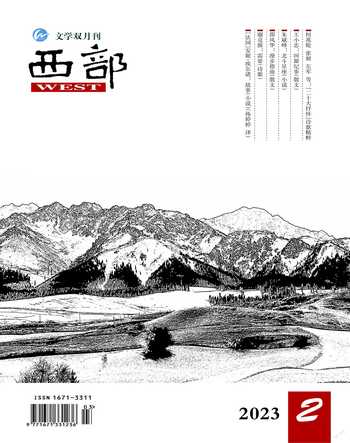对谈:“写作是一种奢侈的痛苦”
皮埃尔·路易·福尔 安妮·埃尔诺〔法国〕 孙婷婷译
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书评、研讨会、博士论文……评论界的兴趣始终没有离开这位作家的文本书写。
然而,安妮·埃尔诺的辉煌并不局限于学术圈内。她的一些作品已经逐渐获得“经典”的资质,成为中学生学习的对象。埃尔诺的出版商甚至决定:将《一个女人》收入专门为高中生泛读而策划的“伽里玛书架丛书”。
正是在这个版本问世之际,我们得以约见安妮·埃尔诺,与她探讨了其全部诗学并能从崭新视角阐明她与写作关系的相关问题。我们从献给作家母亲的小说《一个女人》出发,进而谈到许多不同的领域,兼顾了这部具体作品的产生以及作家全部的文学创作。诸如“失却”、对死亡的恐惧、题记的重要性、女性主义、将写作视为“荣耀的身体”的诞生等等问题在这次访谈中汇聚,囊括了埃尔诺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作品——从《空衣橱》(1974)到《占有》(2002)。
皮埃尔·路易·福尔(以下简称皮):在您的笔下,您的母亲占据了重要位置。有两本书完全是写她的——《一个女人》和《“我没有走出暗夜”》。您的上一部作品《迷失》里,也能找到对您母亲的大量影射。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先从专门写她的第一本书《一个女人》以及该书的成因开始。您在《“我没有走出暗夜”》这本书的前言中也谈道:母亲逝世后,“处于震惊与混乱中”的您马上就着手《一个女人》的写作了。
安妮·埃尔若(以下简称安):是的,关于这本书的“孕育”,我在《“我没有走出暗夜”》里的讲述都是真实准确的。《一个女人》绝对是出于紧迫而在服丧期内动笔的作品,远非我父亲过世许久我才拟定写作计划的《位置》可比——在动手准备《位置》之前,我足足等了好几年。母亲离开后,某种紧迫感明确无误地显现。我必须马上写出这本书。能和它相比的只有一部作品——哪怕看上去很是奇怪,这便是《纯粹的激情》。对,也许显得奇怪,但它们的写作过程的确相似。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追根溯源,都是一次离开、一种终结。对《纯粹的激情》来说,是一个男人的离开,然后过程基本相同。除去一点:我是刻不容缓地投入《一个女人》的写作中的。因为这个“项目”更名正言顺。《纯粹的激情》则并非如此,我几乎是蒙着自己的眼睛把它写完的。
《一个女人》的动笔很仓促,并没有写作规划。实际上,它的开头部分正是日记《“我没有走出暗夜”》的结尾。我其实是把二者连接起来,有意识地从日记过渡到小说,同时,我也有一股冲动,要书写刚刚过世的母亲。
皮:就您的所有作品——具体到《一个女人》——而言,其中“元文本”的比重不小。对您来说,随着写作的深入,质询写作行为本身是必需的吗?
安:绝对是的,我遭遇的写作难题与文本紧密交织,尤其是在《一个女人》里。当然,有几次我也写过很长一段文字描述这些难题,然后便意识到“太长了”。最终我把那段文字切割成几个部分,分别放入文本不同的地方。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数时候,难题在我笔下出现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例如,“让母亲再生”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了一段时间。“句子排序”的难题——我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功夫——也是如此。写作让我见证了一些奇迹。
皮:您说《一个女人》是“服丧期内动笔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您有一种要写出它的执念?
安:是的,我始终处于对文本的执念中。只有《外部日記》和那些纪录片断的文本除外。而片段就其本身来说很像诗歌,只占用你把它写出来的时间,随后便完事大吉(此处不谈偶尔会费时较长的修改润色)。总体来说,我确实对自己的作品抱有执念。《一个女人》尤其如此。
皮:您回忆自己的母亲,回忆她的去世和整个患病过程。我有种感觉,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倾向于规避死亡。比如在您的书中,父亲的去世发生在非常亲密的氛围里,母亲的去世人们却避而不谈,二者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
安:我想表述这种区别,在我看来这很重要。写出太平间快速处理母亲遗体的这个过程,与写出与父亲的过世——地点是在家中——相比,这个过程可怕的一面。医院对死亡的抹除和隐匿确实让人不安,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塞尔吉·蓬图瓦兹这座新城息息相关。没有名气的新城、故土的远离、太平间(母亲去世前我从未去过)……一切都相辅相成。反观父亲下葬后,盛大的家庭聚餐沿袭了旨在交流的古老传统:感谢前来瞻仰和祭奠死者的亲朋,感谢他们分担了家属的悲痛,将死亡纳入变动不居的生活——通过聚餐的方式。
皮:从前有守灵的习俗。如今,多数情况下流程都在殡仪馆进行——还是在有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大家也不穿丧服了,不再“表露”死亡。死亡的维度被抹去了。
安:每个人服丧的方式都极为孤单。不能说“我母亲去世了”,否则几乎就是伤风败俗。正因如此,我的《一个女人》便以这句话开头,当时的我无法言说此事,说了会让人尴尬。法国人不“穿”丧服已经很久了,所谓的“半丧服”——那种接替黑色丧服的深灰或紫色的丧服①——也不再穿,而丧服却可以让“丧亲/失却”一事表露出来,是向同样承受“丧亲”之痛的群体做正式的告知。
皮:所以有些习俗正趋于消失,尤其是那些贯穿并区分了丧葬不同阶段的宗教仪式……
安:的确。因为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摒除了所有宗教,在为我母亲举行的殡葬弥撒上,孩子们完全不知所措。有社会学家认为,没有受过任何宗教熏陶的第一代如今已经长大成人。这是事实——我丝毫不为此感到遗憾,但它打破了惯例,迫使我们制定新的规则。
皮:在《一个女人》的结尾,您注意到母亲逝世的日子比西蒙娜·德·波伏娃去世早了一个星期。翻看您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您经常提及波伏娃。尤其是《迷失》,您在里面好几次都谈到了她。
安:是的,我得声明是为了她才在电视上露面。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讨好皮沃②,而是为了她。我讨厌上电视。我觉得是出于义务,我有信心使用“义务”一词。甚至是迫于还债,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方面的债务——如某些人所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影响了我”。比起其他作家,她对我写作上的影响肯定要小得多。她的重要性,是让我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中都渴盼自由,渴盼着顶风冒雨也要坚持写作、写下自己想要书写的一切。一种存在主义的债务。
皮:谈到波伏娃,只消几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引向“女性主义”问题……这对您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面前,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当您写作的时候,这个问题对您重要吗?
安:我写作时完全没想过这个。但是鉴于男女之间存在统治关系的现实,我完全相信,自己在落笔时会显露女性写作的某些特点——哪怕不是有意为之。就算只是捕风捉影的指责——其理据可能仅限于“女人不写这个或者不应该写这个”,一旦被我发现,我也要强迫自己把它精准地描写出来。毋庸置疑,我身上覆压着一整套自己都未必意识到却又试图摆脱的神话。对我来说,女性主义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一种必需,行动层面的必需、政治层面的必需。我在写作时彰显出女性主义,不是通过提醒自己是个女人,而是通过尽可能地深入人类的现实。这现实包含了妇女、妇女的处境以及诸如母女关系的某些特殊情况。
皮:说句实话,我是就整体而言的“性别研究”潮流提出了上述疑问。
安:我始终和这股潮流保持距离……有几个跟我谈论女性写作的人,甚至被我比较强硬地打发走了。
需要把女性的作品独立出来,为研究它做好“储备”吗?对此我不大确定。而且,我心里尤其确信一点: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比性别划分更具决定性作用。哪怕后者也很重要,但我会把社会性放在首位。
皮:是啊,谈到社会性,您在《世界报》上发表过纪念文章(《布尔迪厄,忧伤》,2002年2月6日,星期二),向皮埃尔·布尔迪厄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文章伊始便是您对“知识分子的介入”的一番思考。您会在什么情况下称自己为“介入的作家”或者“介入的知识分子”呢?
安:我将知识分子与作家或者艺术家区分开来:知识分子将大部分的研究用于创立一门客观而普遍的学问;作家的作品则首先调动了一种主观性。我从未想过用“介入的作家”一词来定义自己,因为非常明显,写作于我而言是一种旨在对世界发生效力的行为。我不想迷惑读者,让他们进入动荡或者幸福的奇异世界而不能自持,而是要像在《事件》③中我对另一情况有感而发的那样,把读者拉入“令人惊愕的真实”。让一直被忽视的东西暴露于人前,让我自己在动笔之前都没有看到,其真实的影响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的现象显露出来。重点有二:一是尽量多挖掘一些真实,二是要选择——哪怕是在文学写作中——最可靠的“方法”以达到这种真实。佩雷克④将马克思的一句话选作《物》的题记,即“方法也是真理探求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正与我的观点呼应。
皮:您在自己的大多数作品里也喜欢使用题记。被您选为题记的作者,无论是从年代还是国别来看,类型都非常多样。您是如何筛选这句或那句引语的?为什么有些文本就没有题记?而且我觉得,近几年被您选中的题记有某种增多的趋势:《羞耻》是两句;《事件》是三句,出自两个作家;《占有》只有一句,却是很长的一句。这些题记的选择对您意味着什么?它们的重要性何在?
安:写完《空衣橱》那本书的草稿时,我还没有确定标题,同时也在寻找可以作为题记的名句。我想,这两个任务当时是共存于脑海中的。我翻看了艾吕雅的一本诗集,艾吕雅是我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诗人。然后,《公共的玫瑰》中的几句诗吸引住了我的视线:
我将假珠宝收进几个空衣橱
无用之舟将我的童年和烦恼
以及我的游戏与疲惫相连
我马上意识到,它们也许概括不了全书,却可以概括让我写下该书的那种感觉以及这本书之于我的意义,于是标题和题记一下子都有了。我就没再深究,也算是遵循了某种文学惯例——将自己置于某位名人的庇护之下。接下来的两本书都没有题记,但有献辞,分别题献给我的两个儿子(即“调皮蛋们”,这是他们在家里的称呼,取自鲍里斯·维昂⑤的《夺心记》——我在第二次怀孕期间阅读的一本书)和我的丈夫。我不记得自己是否为这两本书找过题记,相反,我知道写《外界生活》的时候,我确实找过,但除了凡·高感叹现代生活中万物转瞬即逝的那句话⑥,什么也没找到。因为这句话赫然写入了文本,我最后就没有在题记中再次使用。
(引言式的)题记完全不适用于《“我没有走出暗夜”》:母亲生前写下的这最后一句话是全书唯一的引语;作为标题,是“她”——我的母亲——在此代表了文学的全部……
其他的题记都非常重要,几乎和标题同样重要。我经常在几个选择之间踌躇不决。比如《位置》的卷首语,同时备选的除了卢梭《爱弥儿》中的一句,还有分别来自萨特和热内⑦作品的两句话。三者之中我最后选定的虽然不是自己偏爱的那个作家⑧,但《新观察家》上转载的一篇采访中他说的那句名言⑨还是让我觉得,这句话给《位置》增添了某种语义——只是“言下之意”的语义:对阶级的背叛。我认为这个题记比十页纸的论证强过百倍,它揭示了写作此书的全部意义——以“画外音”的方式。同时,较之(题记通常具有的)担保作用,它更传达了某种“休戚与共”。
我给《一个女人》选择的题记⑩出自黑格尔。找到一句适合的引语非常困难,我完全忘了自己是如何以及为何在加洛蒂关于黑格尔的一本著作11中撞上了这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了加洛蒂的书。我知道这句话非常抽象和晦涩,但它超越了《一个女人》的具体语境,与我对世界的看法相符。摘自卢梭的《对话录》、被我用作《外部日记》卷首语的那句——“我们真正的自我不完全存在于己身”——也是如此,还有《事件》中对雷利斯12和日本女作家津岛佑子言论的引用13,《羞耻》中对保罗·奥斯特14以及《占有》中对简·里斯15的引用16:除去表面彰显的意思,这些引言还包含了一些我对世事、文学和语言的看法。我对它们的引用绝非无懈可击。但是显然,我要么对被引用的作家感到亲善、与之意气相投(比如卢梭、雷利斯和简·里斯),要么至少對他的才能有种由衷的钦佩(比如奥斯特)。不真心喜爱的作家我不会引用。引用,永远是编织一根连接那个作家的纽带,向他/她伸出手去。
《纯粹的激情》的题记是罗兰·巴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俩》杂志比萨德的作品还要色情”,这个题记产生的效果相当复杂,而且经常被人误解——或者确切地说,经常从知识分子的共识的角度被加以理解:人们认为,我是在抨击《我们俩》这份主要刊载言情故事、基本排除了性和色情内容的妇女通俗杂志,认为我是在恭维萨德。然而,在这句被我抽离了语境的引言中,巴特原本想说的是:看见和阅读爱情与激情,远比看见和阅读“性”更让人无措和难以忍受。巴特于1977年写下此语,而在我发表《纯粹的激情》之时,他的这番高见更是有目共睹。激情的处境正让人心生不忍。伊丽莎白·巴丹特17在其著作《一个是另一个》中明确表示:爱情的混乱无序注定会消失,不同的性别与个体之间只会剩下平和、理性的关系。巴特的引言因此可以帮点儿小忙,让我略过读者的某种不无傲慢的阅读,警告他:他要读到的东西有伤风化,即使在二十世纪末,也比萨德的作品更让人难以接受。这是个既失败又成功的策略:有些读者和评论家的确对该书冷嘲热讽……
皮:《纯粹的激情》和您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作品《占有》,都是围绕爱的束缚这个问题展开,都是一开始就追忆勃起的男性性器官。《占有》的结尾更是返回对男性性器官的描写。您在《迷失》里将“性”写入文本而使之文本化,对此您有何看法?
安:在我的作品中,性描写占据的位置很难加以解释。总体来说,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想“写”性。也许因为我那些关于性的最顽固的印象来自十三四岁时候的阅读,来自那些“信教的”所说的——比如在教义问答课上——“坏书”。我感觉得到,自己经常围绕写作和性之间的某种联系转来转去,这种联系可能颇具蛊惑力——十三年前第一次看到(根据原文翻译)电影的某一幕时,我感受到的那种蛊惑力——《纯粹的激情》的开头对此有过描写。同时也不排除在 “社会罪”(根源于社会)和性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皮:我们再谈谈《占有》。《世界报》去年夏天登载的文学副刊里,《占有》的文本形式(与后来的成书)有些许的不同。您在正式出版的书中做了几处修改,调整了若干段落,增添了一些内容并扩充了结尾。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排版印刷上的变动——成书要“透气”得多、零散得多。这种切割和在文本空间上所下的工夫从《位置》以后就出现了。请问此举的重要性何在?
安:空白于我而言至关重要,我在今年夏天投给《世界报》的那个文本里也留有一些空白,发表时却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就全部删掉了!不得不说,我非常沮丧和气愤,立刻决定申诉,要求明年春天的刊载必须与成书里的形式相同。留白是在我自己感觉特别稠密——稠密得近乎“激烈”——的作品中打开的气孔和出口。而且,《位置》里我第一次使用留白,是依照自己拟定的人种学写作计划,有意避开小说。该书原本的题目是“家族人种学资料汇编”:只是基本资料,不是脉络连贯的语篇。正如在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中一样,空白的作用是无需添加过渡、无需阐明因果,是既可以并置又可以突出若干观点,是彰显某些细节的重要,是进行清查盘点……
皮:我在《占有》里再次发现了一处脚注。《一个女人》《纯粹的激情》和《事件》都使用过脚注。您为什么求助这种方法?
安:如果觉得某段文字让叙事过于撕裂——构成了外在于文本的一种思考,我就会在页下做注。但是我心里明白,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也是某种断裂的内容还是被我纳入了文本的正文,我于是安慰自己还有一种理由——它们类似在文本内部打开的几个通往外部的大门,走不走这些大门则是读者的自由(因为这需要付出努力,且在文学写作中并不常见)。
皮:一般来讲,外界认为您和加缪、波伏娃的作品之间存在互文性。您自己却说受到其他作家更大的影响。您指的是哪些作家?除此之外您还欣赏哪些作家?
安:纵观人类写作的全部历史,我认为萨特和他的《恶心》对我而言尤为重要。还有塞利纳、普鲁斯特和福楼拜——在我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的成长阶段,之后我才正式开始写作。我由衷地崇拜这些作家的写作风格。我也喜欢过佩雷克、娜塔莉·萨洛特(深刻的精神上的愉悦)和雷蒙德·卡佛。在我看来,卡佛的文本绝对是卓越不凡的。我也很喜欢切萨莱·帕韦泽18,他的《同志》《美好的夏日》等作品都非常精彩。
皮:您谈到了娜塔莉·萨洛特,让人立刻想起新小说。我大概知道,新小说对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安:千真万确。我的第一本习作(没有发表)就属于新小说。非常复杂的结构,杂糅在一起的片段:梦境、想象境、童年和现在。共有四个层面,想在其中找到方向可不容易!实际上算是一首长诗。但我当时受新小说的影响太大。时任瑟伊出版社发行人的让·凯罗乐在来信中说,我的设想很有意思,设想的落实却未达到相应的高度。的确如此。不过,我却第一次完整地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置身于连贯的情节之中的乐趣,以及每天以此为业的乐趣。体验另一种人生的感觉。我自此明白,写作是另一种人生。后来,这段过往让我很是怀念。偶尔的试笔已无法让我满足,我要彻底地投入写作。然而十年过去,我才得以重新开始——这便是《空衣橱》,尽管写作的方式已大不相同。
皮:您在《一个女人》中说,写作是一种“奢侈”。我们却觉得写作还有一个维度——痛苦。
安:对,是有痛苦。但是同时……
黑:……可以称之为“奢侈的痛苦”吗?
安:完全可以。要知道,不奢侈的痛苦比比皆是:有一种不奢侈的痛苦,叫作社会性的穷困和心理上的悲惨。有那么几次,我就处于这种痛苦的边缘……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日子,我过得不好,很不好,也许挺过来的我因此成了作家……是的,我还在坚持,写作是一种奢侈的痛苦。
皮:在《一个女人》里,您想把这种奢侈的痛苦放置到某个奇特的地方——“文学之下”。
安:“文学之下”的表述是我无意中想到的、出自契诃夫作品的一句话:“……在爱情之下”19。我还要引用契诃夫,不过这次是他关于写作的论述:“首先要合理,其余则水到渠成。”我是后来读到这句话的,它表述的意思非常重要,即我们不能以“咬文嚼字”为先。我还想到纪德在《论那喀索斯》中写到的一句话:“艺术家/科学家的自恋不应该超过他想表述的真实”。有一种注重辞藻的文学形式……
皮:……追求美,唯美化的文学形式……
安:是的,以追求唯美为要务。重要之处不在于此,而是应该力求真实。当然,没有对字词的认真推敲也不行。“文学之下”还意味着:不要待在作为崇拜对象的文学之内,而是要走得更远。“待在文学之下”几乎就等于“(待在)文学之上”。走得更远,更强而有力。这种姿态不是卑微,相反,它很是高傲。的确,《一个女人》让我有种走出很远的感觉——向着我母亲的“荣耀的身体”。我在书里谈到过“荣耀的身体”吗?
皮:没有,我没有见到。
安:我接受过严格的基督教教育,身上还残留着很多神话的影响。在这些神话故事里,俄耳甫斯下地狱寻找欧律狄刻的故事没有“荣耀的身体”给我的印象深刻……尽管说到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我还做了个相关的梦……我不记得自己写过或者删掉的东西了……我写过这个梦境,但是忘了写在哪儿了……梦里,圣拉扎尔车站附近,说不清楚母亲是否坐在公交车上……总之我是在等公交。汽车到了,母亲出现,我想和她说话,她却并不理我,她的身影逐渐消散,同时她示意我她无法和我说话,直至彻底消失。我失去了她。我看見了她又失去了她。就像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还是回到“荣耀的身体”吧。它讲的是什么?在基督教里,人死以后,经过最后的审判在最后一天复生,但复活的不再是我们的肉身,而是“荣耀的身体”。它确指什么?我不知道。总之不再是原来的肉体。《一个女人》的书写让我产生了创造出母亲“荣耀的身体”的感觉。她本真的自我、她的身体通过进入他人意识和记忆的方式,变得光辉灿烂。她分解并融入人们的精神,像灵魂一样存在(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我竟有这样的唯灵论想法!说实话,我是唯物主义——也就是“此时此地”——内部的唯灵论者)。现在和您讲起这些,我不禁想到自己在《事件》最后写下的、关于我的存在消融在写作之中的那段文字。
皮:对,就是全书末尾返回卡迪内甬道20之前的一段。我读一下:“……世事纷至沓来,让我将之录下。我人生的真正目的,也许仅仅在于:让我的身体、五感和思想都化为写作,亦即化为某种易懂而普遍之物,我的存在完全融入他者的头脑和生命。”
安:我是因为跟您讲到母亲才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对照的。她的复活是通过散播的方式、通过在阅读过程中变成读者的母亲或者祖母的方式。还有一个隐喻:关于“遗失”的隐喻。我的所作所为,让母亲像我一样遗失在作品之中。我知道自己笔下的一切极为错综复杂。十多年来始终知道。当一个人开始写作,他便无法了解、他不了解自己会写些什么。
皮:作为结语,我想让您再谈谈这个关于遗失的隐喻,谈谈“失却”的问题,您的作品对这个问题总是在不断修正——直到2001年,您发表的小说题目还是《迷失》。您的文学创作是借助某种不断“失却”的经历而得以进行的,可以这么说吗?
安:不用到达“(亲身)经历”——正如对我的情况比较快速地进行一番“自我-社会性-心理分析”后,大概就可以经历和体验“失却”(我的父母在我之前夭折/失去过一个女孩儿,我通过进入知识分子圈层摆脱/失去了自己的出身阶层)——的地步,我想也有可能建立某些关联:
﹡过错、犯罪——社会的、性的、宗教的——与“迷失”的欲望或恐惧
﹡“迷失”在激情和性欲里,以相当神秘的方式(我想起1960年观看的一部电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迷失的风险》,讲的是个修女的故事)
﹡“迷失”在写作中,因为写作是“重新赢得”一切的手段,是“荣耀的”以抽象的形式——字词的形式——呈现的真正存在,“自在”(être)并且“使在”(faire être)21,把一切奉献给世界而非上帝。
﹡“迷失”,也就是一直走到XX的尽头,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抵达事物的“本质”……
谈论“失却”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很难组织一段连贯流畅、因果相续的措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空白”是写作——我的写作——的理由和意义,但近一两年来,我觉得更应该是“失却”:它是心脏、是中坚,是抓住了文本之间所有线索的东西。
注释:
①按照法国习俗,丧服通常为黑色,守丧半年后才可加穿白﹑灰﹑紫或淡紫色(称半丧服)。
②当指贝纳尔·皮沃(1935- ), 法国当代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法国《读书》杂志主编、龚古尔奖评委会主席(2014-2020)、法国电视二台读书节目主持人。
③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21),电影名在国内一般译为《正发生》。
④乔治·佩雷克(1936-1982),法国当代著名的先锋派小说家,其作品《物》(1965)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
⑤鮑里斯·维昂(1920-1959),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夺心记》(1953)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本小说。
⑥《外界生活》:“凡·高在一封信中说过:‘我力求表达现代生活中万物的令人绝望的转瞬即逝。”
⑦指让·热内(1910-1986),法国作家和剧作家。
⑧暗指最后选定的是让·热内,因为下文提到的引言出自热内。
⑨“我斗胆解释一下:人在背叛时写作是最后的依仗。”
⑩“矛盾是难以理解/想象的——这种断言是个错误,因为矛盾就真实存在于生者的痛苦之中。”
11当指罗杰·加洛蒂的著作《黑格尔思想研究》一书。加洛蒂(1913-2012),法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12当指米歇尔·雷利斯(1901-1990),法国人类学家、艺术批评家和作家。
13引用的两句话为:“我的两个愿望是:大事都化为书面文字;书面作品都是有影响的大事。”“谁又知道,观察事物直到它最后结束是否就等于记忆。”
14保罗·奥斯特(1947- ) ,美国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
15简·里斯(1890-1979),英籍女作家。
16引用的两句话是:“语言不等于真实。语言是我们在世间存在的方式。”“要知道,如果有勇气将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探究到底,我最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真实情况,发现宇宙的真相,发现所有那些不断突袭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伤害的事物的真相。”
17伊丽莎白·巴丹特(1944-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女权主义作家。
18切萨莱·帕韦泽(1908-1950),意大利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19在契诃夫的喜剧《樱桃园》里,女主人公柳波芙·安德列夫纳说:“我却被迫处于爱情之下。”(第三幕)
20卡迪内甬道位于巴黎十七区。《事件》中的“天使制造者(做地下人流手术的江湖女医)”就住在甬道内。
21相当于英语的be 和make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