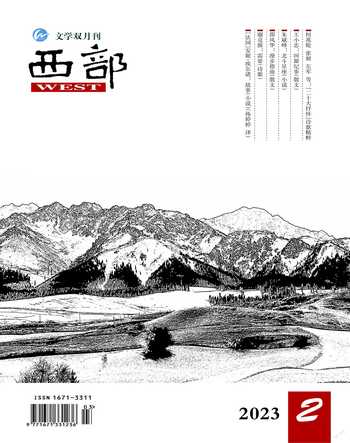故事(小说)
安妮·埃尔诺〔法国〕孙婷婷译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利勒博纳市,父母均属于工薪阶层。童年和青年时期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度过。曾就读于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当过中学教师,后就职于法国远程教育中心。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空衣柜》《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没有》《冷冻的女人》《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外部日记》《耻辱》《事件》《占领》《悠悠岁月》等十余部作品,《悠悠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并获得“21世纪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22年10月6日,以“勇气和冷静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她的每部作品都依据真实的经历,有着浓郁的自传色彩。
那一年复活节假期过后,学校在四月底开学。教室里已然很热,十一点半钟,我们使劲儿唱起《圣母喜乐哈利路亚》,心里却急着想冲下楼梯跑向户外。大家又穿上了夏季连衣裙,又可以玩那种在地上划线的“躲避球”游戏了。很快就是“圣母月”(五月),有十来种祷词的诵读要在室外——圣母像前由枝叶搭建的“洞穴”里——进行。相当于一场小联欢,然后再上楼学习。
家长们经常把复活节后的这个开学季作为让家中幼女适应学校的过渡期——每天下午,女童们会被送进古蒂耶小姐的学前班。需要出门工作或者被太多孩子拖累的妈妈,没办法亲自把女儿送到学校,便央请家附近大一些的女孩子帮忙。有时会托付给好几个小姐姐,但最好是一个:女孩子间笑闹喧哗,很容易出事儿。
玛丽·宝儿年仅五岁,下面还有三个弟妹。临近下午一点,她被妈妈领进厨房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尽管天气晴暖,身上却穿着件棕色的插肩大衣,让我想起自己为了节俭而故意买大、穿了好几年的那件大衣。女孩儿扁平的金发修剪得短而整齐,侧面别着只发卡,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小书包。我牵起她的手,在父母赞赏的目光里走向学校。父亲看上去很是骄傲:我也成了担起责任的小姑娘。当初我刚上学的时候,负责照管我的是个已经上了初中的姐姐——一个车行老板的女儿。我的身高刚到她腋下夹着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晚上放学,她和另一个姐姐搭伴,两人叽叽咕咕一路上不时爆笑。于我而言,这种(被冷落的)折磨一直延续到学年末的颁奖典礼①。第二年,车行老板卖掉产权搬走,父母才开始轮流接送我上下学。
我刚上五年级,玛丽·宝儿应该不会怕我。她走路时身板挺得笔直,我垂眼就能看见她头顶上的发缝,几块乳痂黯淡了那头秀发。我问了她一堆问题,她只是晃动脑袋表示“是”或“不是”,两眼始终直视前方,身体紧绷而僵直。“你把自己的舌头吃了。”一到学校,我立马把她交给古蒂耶小姐,然后赶紧跑去玩“躲避球”游戏。
傍晚我去接她的时候,她正混在其他小朋友中间,坐在风雨操场的长凳上等我,一只手按着立在膝盖上的书包。她极快地跑过来,充满信任地将那只空的手递给我。我问她课堂上都做什么了,她好像记不起来。画画。她妈妈很想知道她听不听我的话。我却不想多说。
玛丽·宝儿都是在播午间新闻的时候赶到,穿着那件扣得严实的大衣,拿着她的书包。我妈妈总是给她一只苹果、几块华夫饼干——家里多余的饭后甜品。她郑重地说:“谢谢,太太。”“这孩子真有教养!”母亲每每赞叹。因为玛丽·宝儿家不属于那种“需要担心的类型”,而且她家总是入不敷出,与我家正好相反。
我们上学走的是共和国大街——为了在最后几百米接上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放学回家则取道罗歇·萨朗格罗街。圣母月已经开始。领诵者纤细的声音沉稳地响起:“玛丽我向您致敬。”所有女生迅疾地朗声回答:“圣母玛利亚。”女孩子们偶尔你掐我一下、我胳肢你一下,欢笑阵阵。学前班的孩子不能这样玩闹。一点半钟,我把玛丽·宝儿撇在操场上,直至放学都将她忘诸脑后。
罗歇·萨朗格罗街非常安静,几乎空无一人,街道两边要么是库房的后墙,要么是屋舍不透光的背面——正面朝向旁边平行的共和国大街。只有一家咖啡馆,刚刚因为“有伤风化的买卖”而被关停,还有一家牙医诊所。玛丽·宝儿轻快的小碎步表达着回家的喜悦。她几乎一言不发,哪怕受到我的些许纠缠。有她作伴自是無趣,我反而没法像从前习惯的那样,在放学的路上天马行空地做梦。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以及何时开始的,但我记得那个地点:咖啡馆前。咖啡馆的窗户上乱涂着白色颜料,让人看不见内里。我大概刻意变换了声音模仿着老师——在我决定开始的那一刻。但与老师不同,我没说自己要讲些故事。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我说什么,玛丽·宝儿都会确信不疑。歇业的咖啡馆启发了我,让我幻想有个姑娘被一伙强盗关在里面,正饿得要死、哭个不停。第一次,我大声说出自己的想象,心里很是激动。玛丽·宝儿立刻跟上我的思路,好像她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个。她的问题甚至有点儿偏多,为啥这样为啥那样,没完没了。
她什么都信,这是乐趣所在。只要将街上看见的东西和沿途遇到的行人指给她看,再加以发挥就够了。水到渠成的办法。我玩得不亦乐乎,归途也有了生气和活力。一天晚上,父亲看见了我们,说:“你的样子像个小老师。”
然后我厌烦了总是编造同样的人物。而且我看到,玛丽·宝儿又恢复了那种只想钻回妈妈裙摆下的幼稚的执拗表情。她身上有种“丧”的东西,哪怕是笑的时候。我永远无法让她把大衣脱掉,顶多让她解开扣子——还得借口她妈妈只是为了让她出门才给她穿上的。那年的春天很热。终于有一天,我胡诌出个黑人婆子,留着长长的指甲,就在咖啡馆后面等着我们。一个专挑孩童下手的女拐子。她用手抓住她们,把她们带到很远的地方,父母就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女儿了。玛丽·宝儿一声不吭,然后我感觉她放慢了脚步。她的脸孔变得紫胀。她开始尖叫。高昂、刺耳、持续的尖叫,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这么单纯的小人儿能发出这样的叫声。她拼命拉扯我的胳膊,让我不得不松开她。她滚在地上,书包压在身下。我非常费力地扶她起来,她用力挣扎还要往地上倒去。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她尿湿的短裤。我从她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给她擦脸,给她擤鼻涕,把她拥在怀里。到家的时候,她已经看不出什么异样。
第二天我要是改走共和国大街而舍弃罗歇·萨朗格罗街的话,也就不会有后续了。然而改变路线是不可能的。我俩各自背着书包安静地走路,仿佛前一天什么也没发生。我示意她看那个黑婆子——那个埋伏在咖啡馆涂白的窗户后面的女拐子——的时候,我俩可能都在心无旁骛地想着这事儿。所以像头天一样,我只说了一句,哭嚎和顿足立刻就发生了。
此后上学的日子都是如此。去学校的路上,我们沿着共和国大街向北,因为要接上我的那个同学,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我和同学另有一套习惯。那事儿应该在放学以后进行,从容不迫地进行。白天我从来不往上头想。我玩“躲避球”游戏,认真地上语法课和算术课。钟声一响,我就冲向枝叶搭建的“洞穴”,以便在开了天窗的靠边一排找到个好位置:祝祷声低鸣的时候,仰视天上的白云,会有置身摇篮的感觉。下午四点半,我把玛丽·宝儿从长凳上叫起,手牵手回家,我没事儿人似的,她没记性似的。扁平的头发和棕色的大衣让她看上去很像圣女贝尔纳黛特·苏毕胡②。
当然,女拐子不是孤身一人,残暴的克罗诺克熊、手持尖刀的屠夫,也出现在萨朗格罗街的拐角。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我建议玛丽·宝儿低下头踮起脚尖走路,尤其不要哭。然后,喊叫和哭闹的“信号”突然发出,她便滚到地上,怎么也不愿再往前走。我给她拭泪,拥抱亲吻她,总算能让她乖乖地重新上路。
我不担心玛丽·宝儿向她妈妈告状,我觉得这是她和我之间的一个秘密。她能告发什么呢?我既没打她,也没掐她,过马路的时候还极尽小心地照看她。她是因为某些并不存在的威脅而哭。就像家长们说的那样,她哭得莫名其妙。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文字加持,做什么都不算错。偶尔有女人路过,小心翼翼地靠近我们,以为哭成这样的准是我的妹妹。玛丽·宝儿的叫声于是愈发高亢,那女人便耸耸肩膀无奈地走开。唯一的烦恼,尿湿的短裤。
一天中午,午间新闻照常播放,玛丽·宝儿却没有来。下午在“洞穴”里唱诵祷词的时候,我煎熬得不行。回到家,母亲告诉我玛丽·宝儿十月份之前都不会再去上学,她太小,无法适应课堂。她父母更想送她去离家很近的镇上的学校。
时间到了五月底。我将要离家避静,准备去初领圣体。一个尘土飞扬的傍晚,我独自走在罗歇·萨朗格罗街上,想象着即将在教堂里度过的时日,以及那些会打量我们、挤撞我们的男孩子。咖啡馆的玻璃已被擦拭干净,内里显现出来,空无一人。我麻木地挪着脚步。玛丽·宝儿再也不会牵住我的手。我早已失去了她。绝望的泪水潸然而下。
时至今日,我还能看见花园边上的那个“洞穴”,看见萨朗格罗街——灰扑扑的望不到尽头,看见两个行进中的女孩儿、一大一小……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自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物。讲述十岁时候的这段过往,是为了对我始终想要写作的原因稍作探究,然而此举终归只是又增添了一个故事。
注释:
①在法国的城市或者比较富裕的乡镇,每逢学年结束,学校会举办仪式,给优秀勤勉的学生颁发礼品(以书为主),此风俗一直持续到1968年。
②贝尔纳黛特·苏毕胡(1844-1879),天主教圣徒,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省,据说14岁时见证过圣母显灵。
——战斗的圣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