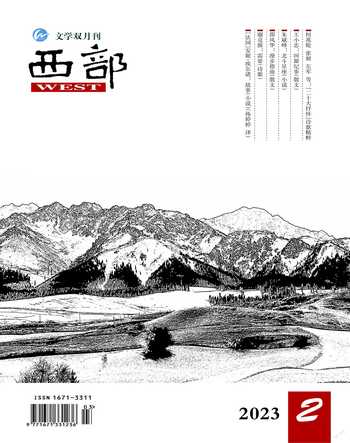老照片(散文)
安妮·埃尔诺〔法国〕 安吉拉译
在我为数不多的家庭老照片中,有一张是我父母一九二八年举行婚礼时的合影。照片里可以看到两家人,“两方”人,分成三排,第一排坐在椅子上,第二排站着,第三排大概是站在长凳上。男士和女士身影重叠交错。两个家庭的成员分别由佃农(我的祖父母)和工人(我的双亲,叔叔和阿姨)组成。每个人都盛装打扮,衣着得体。女士们穿着浅色连衣裙,男士们身着深色西服,双眼直视前方,双唇紧闭,神情在镜头前很专注。坐在前排的人,双手清晰可见,全都硕大而强壮,或放在膝盖上,或交叠在一起,手指捏在掌心,空闲下来的双手紧握着,对突如其来的闲暇感到无所适从。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都难以从那些手上挪开视线,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他们的手都宽阔、有力。我来自这些人,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作唯有一种形式,唯有一种意义:用双手劳动。
我又看了看所有这些照片:干活的孩子,车间里身穿工作服的妇女,套着轭俯身于铁铲上的男子。这些不知名的生命,活在我尚未存在之时,却打动着我:我认出了他们。我想说的是,他们的身躯,他们的姿态,他们的手势,已成为我所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写在罢工牌子上的文字已成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些照片唤醒的几乎是一种物理记忆。这种记忆,深刻的劳动记忆,是博物馆所有的藏品和史书上所有的记载都无法恢复的。它装在我祖父母和父母假日餐桌的故事里,那些故事将生活勾勒为两个空间——田野和工厂,讲述他们十二岁辍学,被送到农场干活,然后进电缆厂、纺织厂,忍受工头的咆哮和欺凌,在寒冷的建筑工地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一种存在于语言中的记忆,存在于那些脱口而出的话语中——“我们没班上了!”——将平凡的日常生活与需求交织在一起,以一己之力构建起整个世界,这记忆的分量,一个从未反复听过那些话的人是永远无法感受到的,他不知道“干净活儿”“室内工作”“恶劣天气停工”是特权,不知道“débauche”①意思是一天的活儿干完了,而“être débauché”②则表示下岗了,与“花天酒地”毫不相干。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对十几岁的女孩则威胁说 “我要把你送进工厂,等着瞧吧”。这是一段在屈辱和骄傲之间摇摆沉浮的记忆。
正如其他类型的照片一样,一张记录个人在工作的照片,比其他照片都更容易带给看照片的人那种转瞬即逝的身临其境感,他们被照片中的姿势或环境所攫住,短暂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照片并不与我们共享噪声、气味、节奏、工厂的哨声,不会告诉我们薪酬多少,工作完成得好坏。然而,这类照片强过其他照片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社会的经济结构。它体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业生产的秩序和纪律,即泰勒科学管理制度的基础。该管理制度旨在给每个人在分工中一个特定的位置。就像在修道院里,世俗的迹象被驱逐,一切都必须指向上帝一样,车间四壁之内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其他任何生活都不能有。那些精简而又朴素的装饰只能指向生产。相似的身影、姿势,甚至是深深陷入工作中的视线都与排列整齐的机器微妙地一一对应。衣着强调工人对工厂的归属,一切都得统一起来,就像帽子,与工作服、帆布袋和午餐盒一起,都得象征着男性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是“白领”的地位。如果在照片中,在一种凝固的瞬时状态中看不到时间,那么在这种空间组织中,在这种对称性中,可以感受到无限的重复与缺乏未来,似乎永远把每一个人都钉在了他们的织布机或其他机器上。矛盾的是,生产场所的封闭,那种对工人们的限制则更加明显,着实令人不安,为了拍照,男人们和女人们中断任务,暂停动作,转向镜头,或惊讶,或微笑。在这个短暂而残酷的空虚中,他们不再是表演的主体,而是成了被看的客体,观看的人则来自另一个世界,公司以外的世界。
最让我感到心酸的是那些操弄机器日久的孩子,他们近乎成了那些机器的一部分,脸上有着与稚嫩的线条相冲突的沧桑和古板,与此同时,生于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正在卢森堡花园中嬉笑打闹,过着普鲁斯特和萨特笔下所描绘的、被文学润饰过的生活,享受着那黄金般的孩提时代。对于那些听完校长的哨子再到工厂听哨声的学生来说,嬉戏的时间早早结束了,就像今天台湾八岁的小孩在为西方世界的孩子们加工T恤衫那样。诸如“父母养不起吃白饭的”和“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已经工作了”之类的话语至今在我的耳畔盘旋,这些话全部都在强调进厂打工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没人起來反抗,因为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秩序和纪律原则,已经被灌输到完美的第三共和国公民的圣经《爱国二童子传》一书中。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处心积虑地隐去了“罢工”一词,强调工作的价值所在,鼓吹人有贫富之分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所有人都各就各位:“当你路过城市的郊区时,有没有看见那些挺拔、简陋的房屋?有没有听见活跃的商贩的声音?那就是不计其数的工人生活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居所或车间,往往在五六楼,也有人蜗居在地下室里,他们成天劳作,让梭子在丝线中往来。那些闪闪发亮、图案精妙、色彩鲜艳的织物,就是从这些毫不起眼的住所输送到世界各地的。”格塔尔先生——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对未来的劳模小朱利安如是说。
这是摄影的扭曲效应,它的底片同时印上了我们的神话和现实。一群聚集在密闭的厂房中的工人们,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囚徒或是身处地狱的殉难者,这点我们无法否认,但同样令我们无法反驳的是,在田野中辛劳的收割者看起来就像圣经中所描绘的诗意景象,烘焙房中的面点师挪动的身姿看起来更加优雅,至少他们在干一件比在流水线上的工人更有创造力的工作。从某一方面来讲,工作的意义在于防止社会失范。机械重复的工作带来的疲乏抹去了混乱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世纪伊始,很多人,至少是我们这些人,心中会泛起离开地球的涟漪,渴望逃离晴雨风雪的循环。我们不能忘记,在厂房和车间的庇护下工作,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表,工人们摩肩接踵,听从工头的安排,这一度代表着进步。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工厂和车间在女孩和妇女们被逼维持生计时扮演的解放者角色。就算这个空间将她们禁锢,相较于她们作为“家庭佣人”的那个家、那个家庭,她们自己的家或别人的家,这个逼仄的空间已然是她们的“外部世界”了。当女人的天职还被定义为相夫教子时,当优秀小说还在描写年轻女孩出门时一定得带个监护人时,一个能将头发散下、自由走动的女工已经体会不到孤独和足不出户的滋味了。她在男女混杂的地方收获了同志情谊,在斗争的生活中和同伴团结在一起。对工厂女工形象的污名羞辱(米什勒说:“ouvrière(工厂女工),一个亵渎上帝的词!”)与 grisette(轻浮女子) 或 midinette(轻佻少女)这样的词汇不同,它还没有被文学概念化,这点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及其作用是触犯社会准则的。往前几个世纪,寻常人家,如佃户的女儿,无疑都要工作;但直到二十世纪,女性才开始从事有报偿的工作,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涉足某个领域里的职业,开始攻入此前专属于男性的领域。1908年,第一位海报悬挂女工已被载入史册,因为她打破了弱柳扶风、娴静温柔等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她在静默中坚定地向前挪动,桶和梯子稳稳当当地被她扛在肩上。你可以在脑海中这样描绘她的形象:坐在梯子的横木上,屏息凝神地把最新的节目广告贴在墙上,对脚下的奚落声不屑一顾。她就像一名点灯人——她在城市中对应的身份,拥有这整个城市。她有权占有它,她不像那些买东西或闲逛的妇女,或是那些如同妓女一样出卖自己身体的妇女,只把它当作一个通道,相反,她是把这座城市视为一个作业空间。到二十世纪末,女公交车司机也将以同样安静的方式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
然而,这些征服的画面并不能掩盖劳动性别分工现象的持续存在。虽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在各行各业都顶替了原本属于男性的位置,但当和平到来时,她们又被请回到她们的“自然”地方——家庭。在巴黎较大的咖啡馆里,她们的围裙和托盘被男人一并“回收”,因为咖啡馆以“仅拥有男性服务生”为特点往往能收获更高的声望。我们见过女人制作矿工灯、开飞机,可我们几乎从未见过男人熨烫衣服,很少有男人在缝纫机前俯身,后来在打字机前俯身的就更少了。计算机发明出来后,这类工具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性别平等,但在利用它进行开发的任务方面并没有多大变化。女性往往迫于经济压力而渗入男性的工作领域,可男性从不与女性分担那些分配给女性的工作。因此,毫不奇怪,我在对二十世纪的工作进行审视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些重要的东西遗漏了,那些没有报酬的、看不见的工作,融入社会背景的工作,仍然保留着、延续着,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女性完成的,包括烹饪、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
这些私人领域中的分工做法已悄悄转移到了制造业的世界,一切都照此发生。男人与木材、金属打交道,女人与织物为伴。相比起男人,女人总以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出现在照片里,她们坐在桌子旁,眼睛低垂,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她们灵巧翻飞的手指与被迫一动不动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女性被暗地里要求去表现她们作为女人的天性,以匹配她们的活动和那个软弱易碎、奉献甚至自我否定的形象。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女性大量进军教育和服务行业,以迎合保持女性气质、拥有“适当的女性工作”的需求。可是,这些所谓的女性形象,被照片捕捉到的健壮躯体所展示出的现实给粉碎了,我们从而得到警醒:在农民和工人的世界中,女性的力量和耐力都十分被看重,“健康状况不佳”这样的词则听起来像是一个诅咒。(如今,在扎伊尔,被称为“代孕母亲”的女人们背上背负的重量可达五十到八十公斤)。罢工游行中不乏大量女性脸庞,她们以法律而不是自己胴体所产生的诱惑为武器,展现出与男性并无二致的、混杂着庄严、坚定和骄傲的面貌。
用“双手”劳作实际上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或者说过于片面。我们应该说:我们用躯体劳作,身上每一块肌肉带着骨头一起律动,我们的思维也不例外(事实上,认为脑力工作脱离了身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些照片华丽地展示了工作中的身体抑或作为工作一部分的身体。今天,当愉悦的或被迫愉悦的身体、富有运动天赋的身体,还有那些有趣的、自我参照的身体,当它们都成了头号话题时,展示并感受身体在世上发挥作用,就大有裨益。双臂压低,双手确保抓握,双腿迈开,身体保持平衡、准备提起袋子,双肩扛起压弯一个男人脊背的重负:所有这些努力、平衡、紧张的姿势,都被所谓的体力劳动者用来与物质搏斗(没有修辞来引导它,没有隐喻来转换它),因而变得更加明显、引人注目。相机在本世纪初捕捉到的这些与物质世界展开的肉搏,渐渐让位于工作中呈现出的优美姿态,让位于这些姿态不同寻常的象征性特点。摄影大师杜瓦诺的作品《画家》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那位画家一只手画画,另一只手勉强支撑住自己,就像一只飞翔在天地间的小鸟,他的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境况:具有帕斯卡式的思想、自负、脆弱。
随着体力工作难度降低,体力劳动者数量减少,这种美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体力劳动者这个类别已然从语言中消失了,好像取代本土劳动力、从事脏活累活的移民劳工不值得讴歌似的。技术繁荣、工作稀缺,以低廉成本将体力工作转移至第三世界,所有这一切都助长我们去掩盖人类活动中产生的利害关系与其意义,并最终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将其抹除。经济和市场变成了主导价值,它们摆脱了与劳动的关系,从此我们的脑海中不再存有工人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清洁员”“安保人员”或“客服人员”。孤立和焦虑,与着了魔般的否认相伴相随,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今夜,超市收银台十分拥挤。收银员会微笑著跟顾客打招呼,用右手推开分隔每个顾客物品的横杆,同时用脚踩动传送带,然后拿起包装盒,在扫描仪前挥动一下,紧接着敏捷地把它从右手递到左手,再从旁边成堆的购物袋里抽出一个塑料袋,猛地向下甩,让空气冲开紧闭的塑料袋口,再把包装盒塞进去。当塑料袋装满时,她把它从支架上取下来推到顾客面前,然后打开另一个袋子。如果商品的条形码没有触发扫描仪发出嘟嘟声,她会用两只手托住那件商品,将其慢慢挥动几次。如果这样仍然不行,她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条形码上所有的数字。最后,她会按下收银机上的一个按钮,再根据顾客的支付方式按下另一个按钮。支票支付的流程最繁琐,收银员首先需要把它插入收银机上的插槽,然后给顾客看一眼,在支票的背面记下顾客的身份证号码,最后把它取出,存放在扫描仪下面的抽屉里。她道完再见后,又跟下一位顾客打招呼,推开分隔横杆。
在我心目中,我可以在我父母的结婚照里看见无数双属于我祖先的手。我突然意识到,不管是最遥远的过去还是当下,工作作为主线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了几代人的生活。而劳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我们应当再次肯定其价值。
注释:
①être aux intempéries,在法语中“意为在天气恶劣到无法工作的日子里仍然能得到薪酬”。
②débauche,在法语中意为“骄奢淫逸,花天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