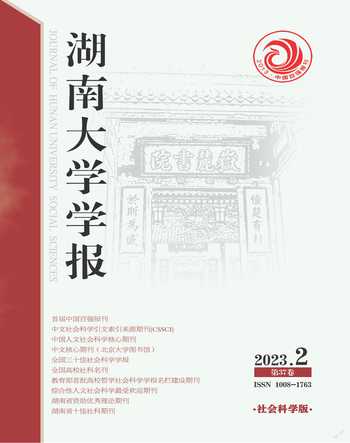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高一飞 宋随军
[摘要]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現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关键词] 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法治认同;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 D9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2-0153-08
Structures and Connotations: the Cultivation of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GAO Yi-fei, SONG Sui-jun
(1.Law School,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2.Institute of Public Legal Servic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201620, China)
Abstract:In secular society, the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can be regarded as a “structural complex” that includes consciousness identity and spirit. Contex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pure sense. Consciousness of rule of law leads to the comprehensive, sufficient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ule of law by social members, it determines the means of “rule of law” in the belief of the rule of law on ontology. Identity of rule of law belongs to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which determines the attitude towards rule of law. Spirit of rule of l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rationality and emotion, it also shows the core content of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The cultivation of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is external, inductive and realistic.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follow the gradual path of “consciousness-identity-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ltivation of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based on the legal practice.
Key words: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consciousness of rule of law;identity of rule of law;spirit of rule of law
作为对“法律信仰”的反思和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期许,“法治信仰”这一替代性、本土性、进阶性的概念应运而生,其根源依然在于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3的论说。然而不同于“法律信仰”的学术传播路径,法治信仰首先是作为政法话语兴起的,不仅其间的确切理论内涵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也未全面回应法治或法律是否能够被“信仰”这一根本性论争。而在笔者看来,世俗语境下的信仰理应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转而理解为一种代表着对社会交往中合理性关系的认同和确信的社会信仰[2]。由此在当代中国,法治信仰不啻“信仰工程”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交集,意在将社会信仰在法治领域具体化、系统化。沿此进路,本文将法治信仰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间三者的勾连、交叠、互动、转化不仅描绘了法治信仰的基本面貌,也初步展现了法治信仰的生成原理和培育路线,最终有助于架构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治信仰理论。
一法治意识:法治信仰的“本体论”
从信仰本质上看,其意味着“内心深处对某种事物或理念的一种朴素的、坚贞的信念”[3],前设基础在于“意识”。申言之,意识代表着个体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意识不仅是事物认知的起始阶段,可以视作信仰的最初级阶段,也意在探索与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构成了认知过程的高级阶段。而法治意识不仅是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法治的思维起点,也是生成敬畏、认同、尊崇等情感,乃至最后达到信仰程度的必经之路,即法治意识构成了法治信仰的基础层次,或曰“初阶”。
(一)法治意识的表征与内涵
通常认为,意识是人类解决与自然界矛盾关系的产物,其展示和促进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自觉认识与自由支配的能力增长。法治意识作为人类的高级意识之一,可以定义为“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突出了意识之于行动的意义,认为法治意识意味着“以法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积极主动地服从法律, 遵从法律秩序”[5]。而在法治信仰的语境下,法治意识更多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对法治及其价值内涵、外部形态的了解、认识、领会和理解,近似于一种理性的审视过程,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法治意识指向一种主体性。法治意识内含着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即个体不仅是法律规则的服从者,更是法治建设的参与者,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受益者,于是对法律的认知就会逐渐从自发性转向自觉性、由受动性变为能动性,这种主体意识的萌生不仅可以避免法治认识误区,还可抑制法治实现过程中的法律工具主义。进一步而言,法治意识又可分为主体权利意识和主体规则意识:前者强调将主体的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的承认、保障与救济作为法治的基准点,主体则基于权利意识而接触法治、了解法治,介入法治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运行过程;后者则突出了法的遵守意义,有助于将主体规则意识转化为守法行为。
第二,法治意识具有鲜明的能动性。能动性乃是法治意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即社会成员对法治的认知、理解和印象能够指引其法律选择和法律行为,由是法治意识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理念层次的概念,而是包含了前后相继的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基于对法治的认识而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认识和知识体系,这种认知和知识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社会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关涉到普通民众对法治最为基础的理解;另一部分则是社会成员运用相应的法治知识,如价值原则、法律规则、适用方法等,对具体社会现象或法律事件进行阐释、评价,或将之作为行动的依据。在这一层面上,法治意识塑造了公民的法律品格,也构成了指导法治实践的重要力量。
第三,法治意识在内容形态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意识本身就具有多方向的扩展性,法治意识则可表现为对法治的理解、参与、思维等多种形式,并且包括了“守法意识、契约意识、理性意识、人本意识、程序意识” 关于五种意识的内容,可参见夏丹波《公民法治意识之生成》,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60页。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同一法律活动或法律行为当中,法治意识亦有可能同时呈现出“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对抗法律”三种形态,由此表明了法治意识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建构性[6]。而更细致地看,法治意识又可细分为下述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规范和法律手段的定位和价值,即主体能够意识到法治中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二是法律赋予的主要权利和主要义务,即主体能够意识到法治对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三是法治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用以及实际运行效果,即主体能够意识到法治的现状、功能和不足;四是涉及法治的社会现象的评价和反应,即主体对法治能够产生出一种反思意识和应用意识,而非将法律作为需要一味服从的对象。
(二)法治信仰的意识基础
不难看出,法治意识虽然直接表现为感官体验,但本质上还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也只有在法治意识基础上对法治进行认识,才能够明确法治信仰的起点。于是法治意识决定了社会成员观念体系中法治的本体形态,即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法治信仰以法治意识的生成为前提。法治信仰通常以“法律至信、法律至理、法律至威、法律至诚”为特征[7],法治意识的萌发则是服从法律、确信法治的前设条件,依此才可能迈向以理性为底色的法治信仰,而非一种盲从。质言之,意识蕴含的充分认知和全面理解,主要限于法治的本体论,如法治“是什么”和“代表着什么”,以及法治的特征和定位、功能和意义,而未必带有情感色彩和价值倾向。所以,正确的法治意识土壤不一定生长出法治信仰,也不必然指向法治信任或法治依赖,甚至还可能同法的遵守无涉。然而,这种非充分性并不能消解法治意识之于法治信仰的基础性意义,而是先有法治意识,才可能有法治信仰:法治意识基于能动性同法治实践不断互动,产生正面的法治情感(如信任感、认同感),这种情感不断稳固、升华,最终达到“信仰”的层级。
其次,法治信仰的培育有賴于法治意识的指引性。正所谓“没有德治辅助的法治实难称之为善治”[8],法治意识作为一种内在指引,有助于“把法治落实到人们的日常行动中,推动人们日常行为的法治化”[9]。这一论断和法治信仰并不直接相关,但却展现了从法治意识到法治信仰的一般路径,也就是利用法治意识所指向的法治思维解决问题,逐渐形成“法治方法运用的思维”[10],将法治意识内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循此而论,如果将法治信仰视为“法治金字塔”的“塔尖”,法治意识则是“塔基”,其间在反复持续的法治意识作用过程中,对法治产生习惯性的敬畏、尊崇等情感。
最后,法治信仰的生成以法治意识为基础构成要件。法治意识主要通过“观念—制度”的互动促成法治信仰。而鉴于法治意识往往具有特指性,其之于法治信仰的本体意义又可细分为二:一是“法治意识—法治情感—法治信仰”的路径,即法治意识能动地作用于法治实践过程,对于法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不断积累,最后生成带有尊崇性和信服性的法治信仰;二是法治意识—法治实践—法治依赖—法治信仰,即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人员在工作中树立法治意识,继而逐渐产生对法治的依赖,并产生带有习惯性和敬畏性的法治信仰。显然,后一种法治信仰路径因为身份指向,带有更多的外力限制和被动色彩,但对社会运转和现实生活的影响却更为广泛、直接。
二法治认同:法治信仰的“认识论”
如果说法治意识以理性为核心,可认定为法治信仰的本体论基础,意识之上的认同则可视为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基础,昭示出理性与情感交互的趋向。在此层面上,社会成员有关于法治的认知和观念又更进一步,构成了法治信仰塑造的核心环节。
(一)法治认同的形态与实质
按照一般理解,认同(identity)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可或同意,意味着在知晓的基础上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好感和赞同,从而带来行动上的一致。在社会科学领域,认同体现出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即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11]12,从而展现出主体选择与社会关系的交互,并由此带来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比较而言,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12],可以简单定义为“对法治建设实践成效的承认与认可”[13],主要包含了对于法治的承认、认可、尊重、服从、拥护等一系列稳定性情感。而对法治认同的进一步阐释,还可从内容、特征以及形成机制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法治认同的主要内容。法治认同以“法治”为客体,因此内容指向也具有广泛性,而究竟认同的内容为何,还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结合认同的内在结构和法治内容的分类,法治认同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法治的利益认同。从现实出发,首先触及社会成员感官的必然是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即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态度首先取决于,法治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承认、尊重、保护促进和救济。显然,利益认同显示出鲜明的功用性和现实性,虽然有可能随着时间和事件的变化而变动不居,但却是法治认同的基本要件:只有先认可法治之于正当利益保障的重要性,才可能逐渐在后续的法治实践中积累认同的基础。(2)法治的价值认同。与利益认同相比更进一步,价值认同强调社会成员对法治的价值目的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其中既包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一以贯之的法的价值,也包括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法治追求,同时还突显了良法善治、法律至上的意涵,由是价值上的契合构成了法治认同的关键。(3)法治的道路认同。法治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结合,所以在共通的价值体系之上还具有本土性,道路认同因之集中体现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方略、目标和任务的认同。以上三个层次形成了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法治认同内容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治认同并不直接指向法律文本和法律规范,而是关涉到法治框架和法治内核,强调对整体性的法治价值和制度运行原则的认同,而非对每一具体法律规范和法律事件的认可。在此层面上,法治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还会伴随着个体吸纳不同的外界信息、经历不同的法律实践随时进行调整和改变,既可能不断地巩固加强,也可能同原有法治认同固定下来的法律认知发生冲突。
第二,法治认同的特征。根据法治认同的主要内容,其特征相应地指涉以下三端:(1)法治认同兼具工具性和价值性。站立在社会成员的角度,法治认同的生成既可以是工具性的,也可以是价值性的。前者强调法治因为能够满足一定的实用性目的而获得认同,尤其是法治可以作为维护利益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工具,使得社会成员会逐渐产生对法治的依赖,并经由依赖性产生认同性
在此层面上,法治的工具性不仅是法治认同的前提,也是法治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按照德沃金的观点,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相关论述可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与之相应,法治的价值性认同意味着对于某些法治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形成共识,并筑建起相互之间情感层面的“归属感”,体现出对正义、人权、自由、平等、秩序、效率等一系列公认人类价值的期待和希望,由此法治因为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而获得正当性基础,并增加为普通民众认同的可能。(2)法治认同是义务性认同和权利性认同的结合,主要指涉消极性的守法和积极性的“用法”。沿循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守法乃是法治认同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其中的义务性特征又可一分为二——基于外在强制力、威慑力的守法义务和出于自觉性、主动性的守法义务。权利性认同则以自身权利实现为法治认同的主要标准,强调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通常指向“立法上的平等性、守法上的普遍性、执法上的严肃性、司法上的公正性、监督上的有效性”[14]。因而权利性的法治认同实际具有超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15],可以凝聚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人们之所以认同法治,是基于一种普遍的需求和希望。(3)法治认同体现了客体性认同与主体性认同的融合。依照社会成员在法治运行中的角色,客体性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作为法治认同的主体,单纯把自身看成法律调整的客体,于是法治认同实质是认同遵守法律、避免违法的义务。引申来说,客体性的法治认同强调的是对良法之“普遍服从”,指出了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尤其突出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从而产生对其他社会群体法治认同的示范作用。相较而言,主体性的法治认同则突出了认同主体在法治建设参与过程中产生的认同情感,类似于公民服從基础上的“公民美德”,据此着重昭示形成于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的法治理性认知和法治认同情感。以上三类范畴的交互融合,大致描绘出了法治认同的基本轮廓,进而初步展示了法治认同形成的来源和路径,也为讨论“从法治认同到法治信仰”提供了理论资源。
第三,法治认同的形成。通常认为,“法律认同的生成应是一个交互式的情感过程,历经认同对象的完备到认同主体的信任与服从”[16]。而在法治信仰这一主题之下,笔者将法治认同的形成界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1)内部机制以“法治”本身的质量为落脚点。其基础在于,法治认同发生在社会成员与法治的交往过程之中,并以“人”与“法”的联结和沟通为基本路径,是一种社会性的法律观念或法律情感,所以法治建设越深入、质量越高、效果越显著,法治的认同程度自然会得到增加。这一过程涵盖了法治对社会成员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满足,还涉及法治本身的优良性,其中既包括某些基本的形式标准——“可见性”“可审视性”构成了社会成员认同法治、自愿遵守法律的最基本前提条件 [17]1,也强调诸多实质标准——“只有贯通公平正义的理念,法律才是受到普遍尊重的良法”[18]251。(2)外部机制以“认同”为重心,意图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型塑、群体建构和个人认知等多种方式“干预”认同情感的产生,并培育和营造法治文化,促进法治认同。大体而言,途径可归纳为二:一曰体验性路径,鼓励和推动社会成员以法治主体身份投身于法治实践当中。其逻辑在于,法治认同“需要公众在社会交往和实践中形成对法治理性化的情境认知,并把这种情境化的理性认知内化为自身的理性选择和理性行动”[19],之后才能产生对法治的理解、授受、支持与服从。二曰引导性路径,将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作为法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并强调法治宣传教育不是一个单向的法治知识和法治理念的灌输过程,而应该是一个渐进性、互动性的法治文化培育过程。
(二)法治信仰的认同基础
法治认同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如何看待法治,以及应当对法治持有一种怎样的情感。某种意义上,认同文化乃是社会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唯有形成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任,法治信仰才能更加稳固、更加真切。
首先,法治认同阐释了法治信仰的具体内容。法治认同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又是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思想动力,所以有学者认为:“对法治的认同程度越深,就越会自觉地支持和拥护法治方向,就越会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就越会自觉地追求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就越会自觉地产生法治信仰。”[13]在此意义上,法治认同的养成不仅有助于巩固业已产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更有助于树立法治精神、形成法治信仰。一方面,法治认同意味着对法治的理解、接受、支持和服从,且这一过程形成于长期的法治实践和自身体验,一旦逐渐生成就会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稳定的认可与敬畏情感恰恰是法治信仰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另一方面,法治信仰显然无法仅靠情感动员和意识宣传来实现,终归还是取决于法治本身的运行效果。于是通过对法治实践的促进作用,法治认同还间接促进了法治信仰的培育——法治认同反映了社会成员对法治建设成效的态度,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法治情感,故良好的法治认同既可以凝聚法治共识、夯实法治基础,也能有效地促进法治建设实践更加深入。由此法治认同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情感基础。
其次,法治认同表达了法治信仰的主体态度,展现出一种“制度性信任”。其中的机理在于,社会主体充分了解法治运行、基本认可法治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治保障权利进行制度性承诺形成合理预期。易言之,法治认同作为社会主体的法治态度、法治理念和法治期待,内含了价值规范、精神理念、意义内涵和理想图景,这种对实质性法治的相信和期许指向的正是法治信仰。相应地,也只有在法治信仰追问中国法治之精神维度和方向的背景之下,法治认同才齐备实质性的根基和价值依据。
最后,法治认同结构中的“认可—信任”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基础。法治认同作为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正向、积极情感表达,其对法治信仰的关键意义主要体现于三个层次:(1)“认可—信任”是一种依托于制度的情感。这一过程的产生逻辑以制度为基础,即先有角色認同和角色信任,才会有“认可—信任”情感的升华。所以法治普遍信仰的情感生产机制是依托于“认可—信任”,而“认可—信任”则是以法治所外化的制度为载体的,一旦缺乏相应机制的有效保障,法治信仰也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法治信仰也可以视为一种由制度承载的情感,这种社会信仰与个人利益及社会运转息息相关,而非纯粹与公共和他人无涉的个人信仰,所以也就必须以理性认识和较浅层次的情感为基础。(2)“认可—信任”是一种源于实践的情感。无论是法治认同,还是法治信任,都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不断探索的法治建设实践,故 “认可—信任”可视为一种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即社会成员对法治中国建设客观历史进程和成就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判断,情感则是这一链条中形成“认可—信任”成果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这种“认可—信任”所指向的法治实践同样也是法治信仰的现实土壤:法治信仰既无法完全建立在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价值理念之上,也不可能直接从“实践”跳跃到“信仰”层次。将法治实践转化为法治信仰有赖于层级式的演化,即先在法治实践中产生“认可—信任”,再经主观和客观的互动进阶为法治信仰。(3)“认可—信任”是一种源于自然积累的情感。法治认同是自生自发性的情感,虽然法治情感的源头一般在于外力,但这种发端的强制性并不能直接塑造出“认可—信任”机制——外在力量至多传输到内在的心理活动层面,影响“认同—信任”的形成进度和方式,而不能诉诸强制力来寻求“认同—信任”。申言之,认同理应是“润物细无声”的,由社会习惯和文化意识塑造出来,因此法治认同和法治信任也就无法被纳入正式制度体系当中,而只能是一种和法治制度相互作用的因素,否则“无条件屈从于规则来培育道德性 ,都会导致同样的道德虚无主义”[20]139-140,即法治信仰亦无法依靠强力,并不是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而是一个过程,必须在认同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即法治信仰实际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三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价值论”
在通过法治意识对法治本体予以充分理解、认知的前提下,以认识论意义上的法治认同为情感基础,法治信仰语境下的法治精神更多显现出价值论的色彩,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并构成了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
(一)法治精神的功能与结构
在哲学意义上,精神往往被视为与“物质”相对应的概念,指向人的内心世界,既包括“思维、意义、情感等有意识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21]21。基于这一最广义的界定,笔者认为与法治信仰相关联的“法治精神”,主要指涉的是“法治的内在品质、内在价值、内在要素”[22],并表达出社会成员对上述品质、价值和要素的追求,以及前验的对法治的尊崇和敬畏,即法治精神既包括精神本身的内容,也涵盖了社会成员“弘扬—践行”的行动意向。易言之,法治精神具有主客观统一的性质,且其中客观性质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一特性从党中央各类文件的表述中也可看出端倪:文件中通常采用的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弘扬”显然迥异于主观色彩鲜明的“培养”或“建构”,词语的差异因之折射出法治精神客观属性的主导立场。,从而对应于信仰本身的“超然品质”[23]。根据这一界定,法治精神还可从下述三个方面加以系统理解。
首先,功能上的基础性。法治精神不仅代表着社会成员基于对法治本质的理性认识与全面把握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模式,也内含了“人们尊重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意向和价值追求”[24]。而在当代中国,法治精神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石,即当法治精神居于支配地位时,社会成员必然会对法治产生尊崇感和敬畏感,也会倾向于将法治视为安排社会行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进而主动追求良法善治。尤其是在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中,“法治精神”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也是判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有效的标准,更是铸造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
其次,内容上的多样性。基于法治历史的持续性、法治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法治话语的普遍性,法治精神往往被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涵盖着各式各样的价值内容,其间则可以将法治精神的内容细化为两个层次:(1)关于法治地位,集中体现为法律至上精神。基于这一法治精神意旨,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法制保持高度统一,一切社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加以调节,权力约束和权力监督精神因之也得到体现。同时在我国,法律至上还可以推演出“作为法律至上实质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人民至上——“如果说法律至上是形式上的,那么人民意志至上就是本质上的”[25]。(2)关于法治目的,此层面法治精神的内容趋同于法的价值,不仅包括实体上的平等自由、良法善治以及尊重保障人权,还关涉程序正义、司法权独立行使等形式内涵。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精神是一种稳定的情感,但法治精神的内容具有开放性,不同时空条件下重心、侧重点以及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从而展现出法治精神内核的确定性与内容的动态性。
最后,主体上的差异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并将之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当中。从党中央的表述来看,法治精神是面向全体人民的,重在“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26]。与此同时,法治精神也会特别指向领导干部,要求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27]107-108。显然,身份的区分也意味着法治精神主体的差异,即在全体社会成员尊崇感和敬畏感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法治精神还包括“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在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28]。
(二)法治信仰的精神动力
法治精神构成了法治信仰的最高层次,即在意识的理性基础和认同的情感基础之上,一旦法治和精神相结合,就意味着实质上确立了法治信仰的内涵,在实质上塑造出了法治信仰。
其一,法治信仰作为一种情感,不是任意的、易变的,也不是一种空洞、虚无的情感,而是以法治精神为内在支撑的——更为重要的是,伯尔曼“法律信仰”提出的背景就在于西方现代法律的精神危机。一方面,法治精神不仅体现出“精神”所必需的堅定性和稳固性,也内含着“法治”的价值秉性,这种价值取向充实了法治信仰的内容,使得法治信仰的客体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追求和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实质也是塑造与培养法治信仰的必经过程,二者在目的取向和目标导向方面具有一致性,即法治信仰必然包含着一种对法治精神的信奉和追寻,而法治信仰也构成了追寻法治精神的重要动力。
其二,法治精神所展现出的“需要”动机,正是法治信仰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精神虽然兼容了理性和情感,但其归根结底还是源自生理或心理层面的“需要”。且在法治语境下,这种“需要”作为情感动机,既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空洞意愿,也不可能是时而趋善、时而趋恶的随机偶然,而是意味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和融洽。正是基于此,精神的支配力和意志力直接型构了法治信仰的行为选择与心理状态,甚至可以认为“信仰是意志自由的表现”[29]。
其三,法治精神的能动性契合了法治信仰的基本心理机制。通常而言,精神所指向的内涵非常丰富,对于行为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引导性和指示性方面,其所固有的坚定性是主体之行为的直接性内在动机。所以法治中的“精神”恰好塑造了法治信仰的应然心理状态:“精神”构成了法治精神转化为现实动力、付诸法律行为和法治实践的关键要素,昭示出一种坚固稳定、具有行动力的、旨在遵奉、维护和促进法治的心理取向——这种心理取向乃是法治信仰所欲达到的最终心理状态。
四法治信仰培育的因应之策
显然,法治信仰既是“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追求目标” [30],其间法治意识、法治认同和法治精神构成了法治信仰的三个层次,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揭示出法治信仰所蕴含的丰富心理元素和多元化构成要素,并在整体上层次递进,情感强度上渐次加强,最终互动型构出契合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求的“世俗化”信仰。依循这一原理,法治信仰的培育展现出显著的外在性、诱导性、实践性特征,甚至夹杂着“奉法强国”的功利性考量,相应的方式方法则体现出内外两个层面的逻辑,一是“意识—认同—精神”的内在逻辑,二是“实践—认知”的外在逻辑。
(一)内在逻辑:法治信仰的“三阶层”
正如前文所述,以宗教为底色只会将法治信仰置于“不可能”的境地,法治信仰作为一种社会信仰,并不要求类似于宗教信仰式的纯粹性,也不以神圣性和终极性为必需的要件。基于这一认知,法治信仰实际是理性与情感共生的心理状态,而“意识—认同—精神”则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分别描绘出法治信仰的可能性图景,增加了法治信仰培育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方面,意识、认同和精神作为法治信仰的主要构成要素,共同刻画出法治信仰的基本面孔,展示了法治信仰的主要表现形态。根据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法治信仰中的神圣性和终极性色彩被消减,转而强调了法治世俗层面的一系列理性和情感。这种理性和情感耦合所带来的心理状态,兼顾了法治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核心要义是一种稳定、持久的法治尊崇感和法治敬畏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法治价值准则和法治生活方式——显然,当我们谈论法治信仰的培育时,更多涉及的是法治意识、法治认同与法治精神。当法治中的意识、认同、精神层层“叠加”、相互影响,实际上已展现出法治信仰培育的实质和现实社会对“法治信仰”的需求。
另一方面,意识、认同、精神三个层次是逐阶递进的,程度亦是不断加深,大体反映出塑造法治信仰的一般规律和主要步骤,也表明了“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培育法治信仰将成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31]。因此三者的承继关系为法治信仰的培育提供了一条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可行路线图:培育法治信仰首先应当以法治意识为前提,并逐渐培育社会成员对法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然后再将认同、信任等情感上升至能动性更强的精神层面。依循这一思路,法治信仰的培育目标实际是在保留法治核心意义的基础上,适度降低了信仰的“门槛”,不啻于在某种程度上把“法律信仰”简化理解为世俗的信心和信念,避免以“法治信仰”之不可能为借口而否认培育法治信仰的构想和努力。
(二)外在路径:法治信仰的实践基础
法治实践意味着,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活动必须“以现代法治理念为观念指导,以法律制度为行为准则,以良善的法律秩序形成为标志,以人的权利保障为依归” [32]。而法治信仰重心在于对法治价值内核与法治精神的认同,以及由此所指向的对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的遵从和信任,所以法治信仰虽然是对法治价值的一种超验追求,但在现实层面更为注重“从对超验之维的神圣体验演化为对实证规则的理性确信”[33]。据此,法治信仰的超验情感不是价值凭空构造的“空中楼阁”,与之相关的意识、认同和精神亦根植于法治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法治体验,是一种内省萌发和外源诱导共同作用的产物。所以唯有在良法善治的基础上,将法治的价值追求同社会成员的法治需求结合起来,法治信仰才会获致更加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法治实践于法治信仰培育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可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法治信仰的源头在于法治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就决定着人们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内容结构、发展变迁和性质特征。”[32]法治信仰所依托的社会成员法治理性认知和法治感性态度,归根结底是由法治实践所决定的,即法治信仰作为“较之法治制度与法治道路构造本身更为根本的要素”[34],其形成既有赖于整体性的法治效果和法治评价,也指涉个体性的法治经历和法治观念,在法治运行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法治信仰培育工作也更为容易推进。
其次,法治实践之于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决定了法治信仰的培育过程也是一个法治建设不断深入的过程。展言之,培育法治信仰是法治实践不断完善的动力,以培育法治信仰为目标来推进法治实践,必然对法治及其运行提出更高的标准,促使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符合社会成员的普遍期待,继而潜移默化地积累法治信仰所必需的元素——“公民个人的行为选择并不都是接受国家法律的指引,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公民个人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所形成的法律价值观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35]129。所以将法治信仰培育置于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审视,实际是突显了人对法治的感知、体悟以及思维抽象活动的重要性。此时,法治信仰培育亦是一项特殊的法治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兰芬,李西杰.社会信仰:社会资本的权威内核[J].人文杂志,2003(3):131-136.
[3]上官莉娜,戴激涛.论宪法信仰的价值及其树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833—836.
[4]柯卫.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J].河北法学,2007(8):47-50,55.
[5]姜素红.法治意识的培养与强化[J].湖湘论坛,2006(3):81-83.
[6]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M].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肖海军.论法治意识[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2-96.
[8]徐亚文,郁清清.法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特殊作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26-133.
[9]杨建军.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J].法学论坛,2013(5):15-21.
[10]彭中礼.国家治理能力是什么:现代法治理论的框架性回应[J].东岳论丛,2020(4):126-137.
[11]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2]朱国良.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J].东岳论丛,2016(6):106-111.
[13]陈佑武,李步云.当代中国法治认同的内涵、价值及其养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9):16-21.
[14]李春明,張玉梅.当代中国的法治认同:意义、内容及形成机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31-137.
[15]陈金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意蕴[J].法学论坛,2013(5):5-14
[16]郑鹏程,陈力.法律认同内在意蕴的生成逻辑[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0-94.
[17]泰勒.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M].黄永,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18]张文显.法治与法治国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9]尹奎杰.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J].北方法学,2016(3):113-121.
[20]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1]余培源,等,著.哲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2]江必新.法治精神的属性、内涵与弘扬[J].法学家,2013(4):1-10.
[23]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3):53-62.
[24]张瑶.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魂[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25-31.
[25]高振强.论法治精神的逻辑内涵和外延[J].贵州社会科学,2009(5):82-86.
[26]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EB/OL].(2015-07-20)[2022-06-15].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672.html.
[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28]莫纪宏.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精神”[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5-20.
[29]魏长领.意志自由:道德信仰的形上基础[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62-64.
[30]孙登科.论法治信仰的生成逻辑[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4):83-91.
[31]徐蓉.法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与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J].思想理论教育,2015(2):16-20.
[32]龚廷泰.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J].北方法学,2013(2):16-22.
[33]许娟.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5):3-12.
[34]宋随军,胡馨予.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方针的发展[J].中州学刊,2021(5):54-62.
[35]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3.02.020
[收稿日期] 2022-09-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17@ZH014)
[作者简介] 高一飞(1988— ),男,河南新乡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