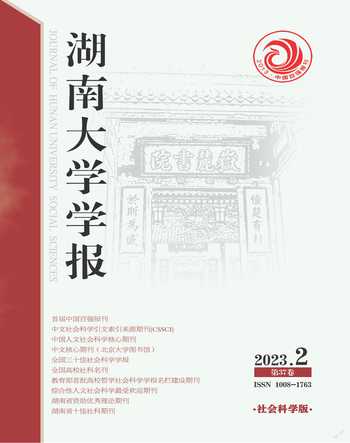岩彩画的现代复兴与跨文化传播
田卫戈 杜星星
[摘要] 岩彩画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美术的一部分。历史上由遣唐使传输至日本,日本画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从材料研发到表现语言都有新的发展。新时期以来,中国留日画家在秉承前辈改良中国画的愿景中将这一绘画重新带回中国。经过不断的推广与创新,最终完成了岩彩画在本土的现代复兴,从而使岩彩画成为中国美术中一次成功的推陈出新。在各高校内开展的岩彩画教学,更是依托本土石窟艺术资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持续深入的岩彩画理论探讨中,对这一绘画的来源生成及历史追溯有了清醒认识,岩彩画更成为凸显民族文化基因及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表征。对岩彩画发展历程的追溯和文化基因的解析,都是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理解岩彩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衍生、演变和传播,岩彩画也由此成为当代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创新的艺术典范。
[关键词] 岩彩画;现代复兴;跨文化传播;艺术基因
[中图分类号] G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2-0027-09
The Modern Renaissance and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Rock-colored Paintings
TIAN Wei-ge,DU Xing-xing
(Academy of Fine Art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Rock-colored Painting i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It was transmitted to Japan by the Tang envoys in history.And Japanese painters explored and developed it through long-term practice, from material research to expressive language. In modern times, Chinese painters who studied in Japan brought this painting back to China while adhering to the vision of improving Chinese painting. Through continuous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Rock-colored Painting has been modernized in China, making it a successful innovation in Chinese art. The teaching of Rock-colored Painting in various art colleges relies on local grotto art resources to construct a relatively complete teaching system, achiev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inuous and in-dep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Rock-colored Painting, there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origin, generation, and historical tracing. Rock-colored Painting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genes and traditional art transforming into modernit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ock-colored Painting and analyzing its cultural genes is to understand its derivation, evolu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from a more open perspective. Rock-colored Painting has become an artistic model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exchange, mutual learning, symbiosis,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Rock-colored Paintings; modern renaissance;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artistic genes
新時期以来,岩彩画在美术界引起颇多关注,体现了特定时期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明确要求。1978年,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人以岩彩为材质创绘的日本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加速了中国美术界对岩彩画的学习与研究,画面中的色彩视觉呈现、颜料的质感及制作技艺,为长期以水墨为主的中国绘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唤醒了中国美术界寻找色彩绘画的决心。1985年,李小山在《江苏画刊》第7期发表《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尖锐地指出“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引发绘画界多年的大讨论。在艺术评论家尚辉看来,“虽然中国画‘穷途末日论不是对传统美术现状和未来中国画历史和现实富有学理的分析与论断,中国画也没有从此穷途末日,但也正是这种思想突围,才唤起了人们对于中国画前途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中国画现代性转向的渴望,从而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画的变革与超越”[1]。1998年7月24日由《美术观察》杂志社与天雅画材公司开展有关中国画色彩问题的研讨会,其中色彩作为中国画变革的突破口,岩彩画正好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也成为重新研讨岩彩画的前奏。30年来,岩彩画作为洞窟岩画及石窟壁画等绘画类型的当代新事物,在岩彩画家个体创作过程中对岩彩画观念、技艺改革等的相似性认知,共同促成了岩彩画的复兴。同时在中国画的变革中成为一场典型性的活动案例。当然,直到今天,艺术界在对岩彩画的历史基因、命名等方面的讨论中仍然各执一词,争鸣不断。因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岩彩的回归之路”[2],厘清岩彩画的发展道路。
一岩彩画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作为东亚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深刻影响着周边各国。日本美术史论家大村西涯指出,从日本美术史的三分之一作品可见,中古时代以前的日本文化多由中国输入。若谈及东亚艺术,只需注重中国,便能纲举目张,不涉支蔓[3]3。从初唐开始,日本便不断地派送遣唐使者向中国学习唐朝文化,中国文化渗透到日本封建上层的方方面面,真正实现了“唐文化花开日本”[4]141的局面。在这种文化传播大潮中,一些遣唐画师以留学生及寺院僧人画师的身份被選拔、派遣至中国,扮演着中日绘画交流的角色,一些留学生被唐政府安排至国子监的后三馆学习书画艺术,僧人画师则通常被供养于寺院学习中国唐代绘画的技艺。至今,在日本正仓院仍藏有大量的唐代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多以矿物质颜料着色,是当时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见证,体现了中国作为岩彩画输出者的身份。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绘画为日本画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在促进日本美术发展的同时,日本美术“逐步发展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题材”[5]95-96,形成了以矿物质颜料作画的民族风格,在东方美术的画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唐代岩彩画的重要传承者,也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岩彩画才得以真正传承和发展[6]。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方现代绘画的涌入,一直以东方传统为基础的日本画坛备受冲击。日本美术界为复兴民族绘画艺术,在世界美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眼光转向西方画坛,提出吸收西洋油画元素,以现代日本画、油画等取而代之的理念,并刻意与中国绘画划清界限,主张不开设水墨画,放弃传统绘画材料。可以看到,日本画坛在运用东方美学积极探索本民族柔、静、秀等艺术意趣的同时,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审美转化,创造出以线作形,颜色鲜明,不重视距离,树上有树,石上有石,不讲几何学[7]58的作品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色彩已成为它的基本语汇”[8]70。长期以来,日本美术界认为“放弃了色彩就等于放弃了现代绘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8]66。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以及自身迫切跻身于世界的努力,日本画很快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并成为现代东方美术的代表,形成了与西洋油画相匹配的色彩表现技法。在这一坚守和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代表画家。首先是狩野芳崖,作为日本画草创期的代表画家,以传统日本绘画为基础,在吸收西洋画艺术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尝试创新与发展,画面虽“令人觉得土不土,洋不洋”[9]180,但为日本画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意义。其次是冈仓天心、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他们于1898年成立日本美术院,将浓淡、明暗写生的技法运用于日本画中,从局部折衷地运用西方画法,到最终形成弱化、排除线条的色彩画风,最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另外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还从色彩的晕染技法出发创作出了“朦胧体”,使得画面产生统一的视觉效果。在此基础上,评论家高桥太华就朦胧体中色彩处理所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琳派”的重彩装饰风格,解决了色彩的独立性问题,最终完善了现代日本画形式语言的基本范式。
不难看出,自唐代以来,日本画坛对中国传统矿物质绘画的吸收与传承是持续不断的。在此过程中虽受到不同文明的冲击与影响,但整体来看,长期秉持以色彩入画的绘画风格,这正是对大唐矿物质色彩绘画的延续和革新,把握了中国唐代传统色彩绘画的精神所在。从另一个角度讲,矿物质色彩绘画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弥补了中国文人绘画兴起后中国绘画界对岩彩画的忽视。
二中国绘画界对岩彩画的重新发现与重视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留日学习的兴起,传入日本的中国矿物质颜料绘画成为中国绘画界关注的对象之一。此前日本以中国为楷模的学习形式,逐渐转换为中国画家向日本学习先进文化及先进艺术的浪潮,日本摇身转变为矿物质绘画的逆输者。这一时期中国画坛对日本画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1918年吕澂、陈独秀在通信中第一次提出“美术革命”[10]27和“中国画改良”[10]29这一概念。在美术思潮的震荡和嬗变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新一代的美术实践者迫切关注着中国画的改良问题,他们在“保守”与“改良”的长期争论中,除选择向中国传统绘画、西洋画学习外,画家们还转向对日本画的学习。如前所述,日本画为中国画的近亲画科,长期受到中国自然观、生命观的影响[11]96,当其独特的亲和力、突出的色彩语言、颜料材质展现于画家的视线中时,很容易被中国留日画家们所关注。徐悲鸿在日本留学时,就清醒地认识到色彩的运用对中国画的革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材料所限,最终在色彩上未能取得较大的突破,更多地将视角转向对造型语言的探索。在林凤眠的作品中,对绘画色彩的探索虽向前迈出了一步,但对颜料的矿物质属性并未有过多的关注。可见,这一阶段的中国画家因在日本接触到岩彩画,其强烈的色彩视觉语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中国画家深刻认识到色彩也可成为中国画改良的道路之一。
其次是在跨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中,中国留法画家在展览会中对日本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庞薰琹在参观巴黎日本展览会时,被日本画家土田麦僊的作品《京都舞妓》(绢本,岩彩)画面呈现的色彩所吸引。土田麦僊的作品画面色彩强烈,颜料属性独特,材料制作工艺特殊,令人叹为观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庞薰琹后期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创作。
不难看出,20世纪初期中国留日、留法学生在他国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遗忘多年的传统岩彩绘画所体现出的陌生感,折射出中国岩彩画因传统文人画审美意识的长期盛行所造成的失语。中国新一代的画家对日本画厚重的色彩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及审美倾向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画家对传统艺术的回溯以及对中国画改良道路的回应。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画家在跨文化的艺术交流中对日本岩彩画的色彩、颜料的属性已有了初步的体认,体现了中国画家在跨文化视野下对现代中国画审美走向的深刻反思。但由于条件所限及特殊的时代背景,当中国画家在面对日本的岩彩画时,仅停留于对画面色彩的关注,对色彩颜料的材质、属性等并未有过多的探索。画家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西洋色彩学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的笔墨、书法、留白、题跋入画及传统设色方式的延续上。
与此同时,“二战”后日本美术界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逐步恢复活力,绘画风格与中国绘画渐行渐远。长期以日本风土人情为题材,风花雪月、恬淡、温弱抒情的风格受到冲击,逐渐转向对巨大规模、气势恢宏、自然哲理精神世界的展示。值得一提的是,画家们在注重作品自身美感的同时,还极为注重颜料工艺的精良性制作。正是这些转变,使得二战以来沉寂已久的日本画坛在绘画风格上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转变,并在东方美术画坛中全面逆袭,真正步入了现代新篇章。可与此同时,日本画以全新面容逆输于中国画坛。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第二代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东山魁夷、高山辰雄、加山又造在画坛的崛起,无疑是对现代日本画的激活与开创。平山郁夫作为东方艺术复兴的实践者,将日本的法隆寺、正仓院与丝绸之路艺术再次连接在一起。他以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宗教艺术为题材,运用青、绿、土黄、熟褐为基本色,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日本画的发展寻到了源头,将东方艺术的特点展现于受众面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国家交流的正常化,平山郁夫多次访问中国,东山魁夷在“色彩、意境的渲染上都将现代日本画推向了一个高峰”[8]47。1978年,东山魁夷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展出。随后数十年,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也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在对日本画进行宣传的同时,也为中日艺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画家作品中所运用的矿物质色、人工合成颜料及金银箔等给中国绘画的革新提供了不同的探索道路。1983年,日本政府实施“留学生10万人计划”,大批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岩彩画,岩彩画真正复归于中国,在中国遍地开花并进一步发展,在表现手法、材料等方面均有创新与突破。
三岩彩画的复兴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中央美术学院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友好建交为契机,各大院校艺术教育群体及画院画家陆续赴日学习。在此期間,画家们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岩彩画的技法,深入思考岩彩材料的研发与推广、岩彩画的教育与传播、岩彩命名等问题,并逐渐借鉴和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整体来看,这一过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探索期和90年代中期至今的发展期。
(一)探索期的岩彩画
首先是对岩彩画技法的学习与探索。从1987年开始,各大美院的教师、敦煌研究院及画院的专职画家如胡伟、王雄飞、侯黎明、胡明哲、卓民、陈文光、张新武、张小鹭等先后赴日留学,并成为新时期以来第一代岩彩画家。在岩彩画的接受过程中,这一画家群体在国内绘画界已崭露头角,但他们仍然从纯熟的国画、油画等画种逐步转向以岩彩为媒材的综合材料的创作。如侯黎明、陈文光、张新武、闫振铎等从油画转向岩彩画创作,并尝试各种可能性。在闫振铎看来,岩彩相较于油画颜料“干湿自如”“随心所欲”,并能呈现“晶体之美”[12]。胡明哲放弃在国内工笔人物界获得的崇高声誉,重新探索路向,逐步尝试将有色宣纸、墨与岩彩结合或使用亚麻布等作画。从国画、油画向岩彩画的转变,使得中国画家对传统绘画观念认知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也产生了与当代艺术相协调的绘画语言及视觉审美经验,其行为动机既具个体性,又具民族性。此外,在经验分享和理论探索方面,他们对岩彩画的技法及创作表现进行思考,如蒋采苹的《中国画材料应用技法》,王雄飞的《岩彩画教材与技法研究》《中国岩彩画材料与表现》等。在冯远看来,岩彩画“开掘和拓展了中国当代绘画表现的新途径,丰富了当代视觉艺术的形式语汇,使绘画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于反映时代精神和当代生活以促进国际交流。从水色到岩彩材料的转移,催化了中国当代绘画在创作理念、审美追求和形式美感方面的新变化,增强了现代艺术的视觉冲击力,加快了中国绘画由传统表述方式向当代表现转型的进程”[13]。由此可见,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依靠材料的探索与突破来寻求绘画的创新与发展,岩彩画是继宋元水墨画之后进行绘画变革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其次是对岩彩材料进行研发与传播。岩彩材料在一开始就引起画家群体的高度关注。如王雄飞于1991年回国后在北京创立天雅画材公司,蒋采苹于1994年申请人造矿石颜料——高温结晶颜料专利,至1998年在中国建立老姜思序、美院附中颜料厂、天雅美术商社三家颜料厂,共生产了五六十种石色,拓宽了中国传统矿物质颜料的种类及色域,并将颜料颗粒从粗到细拓展为14种不同的规格。从水性颜料、广告颜料到颗粒颜料的转变,引发岩彩画家从对色彩的关注拓展为对颜料“物质性”的关注。此外,通过对材料进行科学的介绍,将其引介于更多的岩彩受众群体之中。主要代表著作有王雄飞、俞旅葵的《矿物色使用手册》,王雄飞的《岩彩画材料与技法》《岩彩画材料》《中国岩彩画材料与表现》、张小鹭的《现代重彩画技法》,胡明哲的《格物致知》《中国岩彩绘画概论》等。这些著作,分别对矿物质颜料的种类、生产方法、矿物色的辨识、色标等进行详细介绍,为岩彩材料的传播提供了翔实的文字依据。新时期开始,画家群体对矿物质颜料的研发及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明显的主动性,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巡礼,更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思考中国画的创新问题。
再次,岩彩画在新时期还通过高等院校的教学与创作,向国内推广与传播。古代岩彩画最早在巫术、礼仪等活动中传播,在墓葬、生活器具、石窟寺观壁画、绢本绘画中多有体现,以服务统治阶级为目的,具有鲜明的观念性、宗教性及装饰性特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岩彩绘画风格的演进具也有传承性和序列性。随着新时期岩彩画的复兴,在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快速发展,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追求个性化特征。新时期岩彩画主要在高等院校美术教育、画家群体及石窟壁画的保护与研究中传播,在拓宽中国绘画画种的同时,更多用于专业美术教育、艺术家个人观念的表达及石窟壁画的保护与研究。这一时期,在专业美术教育中做出相关探索的美术家有胡伟、张小鹭、胡明哲、王雄飞、林强等人。胡伟在1997年留学回国,成立胡伟工作室,并以当代艺术表现与绘画材料语言为方向在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张小鹭于2002年成立我国第一个岩彩与综合材料工作室;胡明哲、王雄飞在各地建立岩彩画工作室,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广州美术学院的林强沿袭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岩彩画教学体系,结合中国传统水墨绘画技法进行实验性教学。此外,日本完备的岩彩画教学体系及相关理论著作对中国岩彩画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等对中国宋元以前岩彩画的发展脉络和教学体系进行探索,其研究成果影响了中国岩彩画教学。在此之前,石窟壁画临摹课程体系中,中国还处于争议状态,但受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中国高校也逐步开设了丝绸之路壁画岩彩艺术的考察学习课程,同时影响了岩彩画家自身宏观知识体系的建构。如胡明哲基于实践及教学理念,带着问题到克孜尔、敦煌、麦积山等地考察,重新挖掘传统[14]。此外,这一实践模式及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教学体系,打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师徒传授自学结合、教师“手把手”的示教学模式,从私人画塾的教学场所转变为国家美术院校的办学机制的真正成熟,教师从艺术思想上宏观地影响学生,并培养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仔细观察的学习能力。在理论研究方面,胡明哲出版了《岩彩画艺术》,全书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探索,系统全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岩彩画的历史渊源及创作过程,对岩彩画学习者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可以看出,岩彩画在传入中国后与高校美术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拓展了高校美术教育中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关注。
(二)发展期的岩彩画
经过前期的实践与探索,岩彩画家开始自发地深入思考岩彩画的命名、传承及创新等问题。画家们通过刊发文章,出版画册,举办国际、国内展览及学术研讨会,展示创作和研究实绩,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具备了国际视野和宏观的思考能力”,同时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比较中”[15]确认了自己的位置。这一阶段,美术界尽管对岩彩和岩彩画的命名、岩彩画的创作等相关问题仍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但岩彩画的实践和创作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岩彩画也逐步被学界接受和认可。
首先是关于岩彩和岩彩画的命名。1997年,胡明哲在《美术观察》发表题为《以岩彩为契机》的论文,“岩彩”一词正式进入中国美术界。胡先生的文章对岩彩的材料、底色、黑与白、线与面、工艺制作和整体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将中国的岩彩画与日本绘画进行对立区分,指出中国的岩彩由于传入日本被精工细作,色彩被分出粗细不等颗粒,“本是同源的中日绘画也拉开了极大的距离”[16]。可见中国美术界从一开始对岩彩的命名就明确指出中国岩彩画与日本的岩绘具有着极大的不同。2002年,胡明哲编著的《岩彩画技法》出版,其通过多年的思考,以《谈“岩彩”命名》为题,清晰地介绍并厘清了“何为岩彩”“为何创造‘岩彩新词”“岩彩画与工笔重彩画的关系”“岩彩画与日本画的关系”等问题。王雄飞也在《中国岩彩画材料与表现》中对岩彩画的发展历史、概念及内涵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岩彩的概念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中逐步清晰,而且期望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能够“跨越一切表层的界线”,“回归艺术以人为本的理念”[17]。这一理论导向对后期岩彩画的发展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同时,有关岩彩命名引发的争论也非常激烈。新时期岩彩画从日本而来,其视觉呈现方式有异于中国传统水墨绘画,以注重色彩及材质的表达手法被界内人士认为是“日本画”,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引发争议在所难免。从现有争论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潘洁滋认为,“叫岩彩画好,是传统的沿袭,是工笔的新花,走向大环境,前途无量”[18]。是对岩彩画新画种的肯定及中国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所给予的新厚望。此外,刘新华在《勿忘民族性》一文中认为岩彩虽源于日本画,但从“岩彩”“石色”“重彩”等称谓来看虽概念相同,但要明确中国画家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要以中国的“民族艺术为母体”[19]去思考岩彩画的创作走向,最主要的是通过岩彩画来警醒艺术家深入思考民族性等问题,通过岩彩画来塑造国家艺术形象。由此,潘世勋在《“岩彩”作为画种的提法不妥》一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以岩彩表明新画种会引发认识的混乱,甚至误解为古代岩画[20]。还认为“岩彩”是日本语的翻译,而中国早有“石色”之称,没有必要再创新词。尤其是2003年,胡明哲岩彩画作品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中获奖,更引发了“什么是中国画”的大讨论,并在《中国书画报》上持续进行了3个多月的大辩论[15]。杨劲松在《岩彩是个话题,也是个问题》中即问道:“岩彩作为一面我们文化复兴的镜子可以吗?”[21]这显然是对胡明哲提出岩彩的“物质性”“道与器”的质疑。在杨劲松看来,岩彩画的复兴并不是为了彰显其“纯粹的物质性”,将岩彩画放置于“道与器”的层面是没有出路的。文章还思考了岩彩画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认为要从艺术家本身出发,注重对生命的体验,寻找“当今社会缺失的人道精神和新的文化价值观”,而不是将视角放置于媒介的材料。以上种种从岩彩画的命名,岩彩画在官方展览中是否具有认可性,岩彩画能否肩负起中国画的复兴等问题客观来看,出现对立的观点在岩彩画探索与发展的进程中无疑是好事,只有在争鸣和辨析中,才能够以传统岩彩为镜子,照清新时代岩彩该有的模样。
当然,有关岩彩争议的实质也体现出美术的发展格局问题。格局既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核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岩彩”一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中国古代的石色、丹青、矿物质颜料,日本的岩绘具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承继关系脉络清晰。从新词汇产生的规律来考察,“岩彩”一词隐含着“词义的引申、扩大”[22],并包含着社会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岩彩作为新的名词出现于新时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旧有的“石色”“丹青”“岩绘具”等已不符合新媒体、新视觉冲击下的呈现方式。因为以传统命名为基础的绘画形式是产生于以文人雅趣为基础的社会语境之中,其作品最终的空间陈设与当下时髦明亮的现代美术馆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岩彩”一词的自然物质性在无形之中与当下的时代精神及文化的变迁相契合,因而,具有存在的可行性和不同格局下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岩彩画在争鸣和发展中逐渐被学界认可。这一时期,范迪安、牛克诚主编的《东方岩彩》学术刊物在《今日艺术》杂志社发行,通过理论思考、岩彩作品展示等形式探讨相关学术问题。刘大为和冯远在“同一个世界”大型画展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画不仅有水墨画、工笔画,还有岩彩画”,从画种上进行了拓展与认可。“中国画不仅有水墨的韵味,还有色彩的世界和材质的表现”[15]是从材质出发,因材质的改变引发对中国画的本体性问题的思考。2008年岩彩画被《中国美术大事记》作为重点画派记录。在“高端访谈——平山郁夫”电视节目和日本的相关学术论文中也在频繁使用岩彩一词。不难看出,在中国美术多元化的探索中,岩彩画在各方面逐步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可见,岩彩画从新时期被再度引介到中国,体现了跨文化传播的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岩彩画被中国绘画界所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不断地面临从“遴选”到“转义”再到“输出”的过程[6]。正如潘洁滋所说,岩彩“如同一颗老树,需要嫁接新的品种,使它结出更甜美的果实。我们不拒绝外来文化,但我们的艺术之根应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19],只有根扎稳了,民族自信树立了,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来树立文化大国形象。
尘封久远的巖彩画在新时期引进和回归中国后,逐步寻找和适应了其发展的土壤。尽管它在逐步认可的语境中仍然不断遭受质疑,但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客观对立性使得它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对于岩彩的命名等问题应放置于时代的语境中客观看待,才符合“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的理论。当然,也要客观地看待用矿物质颜料画、丹青、水墨绘画等命名的问题。当岩彩画这个新事物出现时,其命名不一定被大众所接受,甚至引起纷争,都是正常现象。岩彩一词作为新时期美术界的新语词,仍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检视。但是,必须明确岩彩一词作为新事物的出现是语用的要求,关键要清楚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是有生命力”[23]。
四对岩彩画历史基因的追溯
随着时代的变迁、空间的变化、人类心智的教化,岩彩被赋予不同的称谓,是特定时期、特定文本的显现与变革,不仅表达着不同的形式与意味、分歧与冲突、对比与差异,同时,也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再现。
(一)“岩彩”一词的溯源
中国很早就有對矿物质颜料的相关记载,是不同视觉文化意味的体现。王雅观在《山海经颜色体系探究》中对《山海经》的用色体系进行梳理总结,整体分为“赤、朱、红、赭、彤、紫、茈、青、碧、绿、黄、黑、幽、玄、苍、白、缟、素”十八种颜色,并将诸多颜色归纳到中国传统的“赤、青、黄、黑、白”五色体系之中[24],其中不乏大量的岩彩色。可以看出,色彩是古人传统世界观及人文主义思想的视觉呈现。也正如西方哲学家翁贝托·艾柯所说:“每一个人说出某个颜色词时,他不是要指世界的一种状态,相反,他是要把这个词与一种文化或理念联系起来,纵然在特定知觉下,该词的使用是确定的,但是,把感官刺激转化为一种认知,在某种方式上是由该词的语言学表达与文化意义或文化语境之间的符号学关系决定的。”[25]278由此可见,岩彩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越往前回溯,其文化性、理念性及符号性越强,从另一层面来看,“它不仅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而且更有助于文化的稳定”[26]67。
同时,中国古人对岩彩的喜爱还体现在对绘画的称谓及细致的分类上。如以“丹青”称谓绘画,最早出现于南朝姚最的《续画品并序》中[27]369。可见丹青在古代中国绘画界的重要位置。在宋元之前,中国古代绘画主要以矿物质颜料的色彩方式来呈现的被命名为丹青绘画,并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出现以设色为基础的绘画流派,形成积色体与敷色体的表达形式,且广泛运用于人物、山水、花鸟画之中。另外,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武陵水之丹,磨嵯之沙,越隽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炼、澄汰、深浅、轻重、精粗。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蚁铆,云中之鹿胶,吴中之鳔胶,东阿之牛胶,漆姑汁之炼煎,并为重采,郁而用之。”[28]22可见,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关系的建构以丹、青矿物色为原始色,此种用色体系普遍存在于各地石窟壁画之中。岩彩的视觉呈现从原初就被赋予了本民族的文化观、色彩观。对矿物色的运用及细致分类,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色彩的重视,是本民族文化符号的外现。
新时期开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岩彩在原有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宽泛的含义,是多元文化发展的艺术体现。西方色彩系统的涌入,冲击着中国绘画的色彩表达,中国岩彩画家借助东西方哲学思想思考岩彩的当下发展。运用“幻想或想象、表现、情感、动机、转化”[26]4去探究岩彩的创作目的、如何创作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胡明哲提出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思考,并从岩彩的物质性去探索,岩彩虽是“形而下之器”,却是“精神观念的载体”及“民族心理”“文化”的结合[29]。因而,从现代岩彩发展来看,在观念性、文化性等基础上,岩彩艺术的精神性逐步脱胎于礼仪性、功能性,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审美共性,逐步转向注重生命体验、走向审美个性的情感表达。然而,岩彩作为视觉文化的载体,若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往前看,一些岩彩画家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开始自发地回头,从根源上去追溯、梳理中国岩彩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二)有关岩彩绘画兴起的讨论
在古代,岩彩绘画主要体现在原始岩画、石窟壁画中。原始岩画分布广泛,在人类之初普遍存在,或因早期人类的迁徙,其艺术特征的表达共性大于个性。在石窟壁画中,印度阿旃陀壁画、新疆克孜尔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借助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尤以敦煌莫高窟壁画堪称世界古典岩彩画的高峰和典范。岩彩画在各种形态的发展及演进过程中所遗留的印迹因前后顺序、社会的动荡等原因,风格和题材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对岩彩画历史基因的追溯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岩彩画共同兴起于东、西方[30]。此种观点,是将岩彩画放置于全人类共性的视角去审视。岩彩画作为视觉艺术,在人类早期绘画的地点、环境、题材、色彩、符号、图形、表意等方面都出奇地一致,如在南部非洲、北部非洲、欧洲、中东、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普遍存在。在王雄飞看来,人类早期岩彩表达是对“大自然的敬畏”“自卫”“震慑敌方”“模仿”和“自娱自乐”[31]4的体现。法国史前学家埃马努埃尔·阿纳蒂将此种现象解释为“单一的母型”和“相同的概念原动力”[32]318。通过东张西望,发现岩彩共同兴起于全人类的观点,在各专业几乎达到共识: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玆曾谈到,在创造性的文化中,不同的民族都具有相似的需求[33]126;在心理学家蔡曙山看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及认知世界的工具及策略具有一致性[34]719;马努埃尔·阿纳蒂更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早期艺术都表现出“相同的类型、相同的主题选择、相同类型的联想,以及相近的风格”[32]97,是早期人类气质的浓缩。由此,岩彩画兴起于全人类不言而喻。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早期对岩彩画的关注点似乎更注重岩彩色彩的隐喻性。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人类最早、最普遍使用的岩彩为赤铁矿粉——红色[35]226。对红色的大量使用可以看出,色彩在人类之初并非只是作为装饰或突显色彩的色相而存在,更多与“生存观念相联结”,是对生命起源的好奇,对死亡世界的敬畏[36]16。因而早期人类对色彩的选择与“原始人的生存行为和自然的恩赐”有关[35]227,他们通过相似联想来表达某种神秘力量,并运用神秘力量将患有黄疸病人的黄色转移到黄色牲畜的身上,从具有生命力的阳光或神牛身上汲取红色,转移到病人的身上[36]13。因而,对于岩彩在不同时期“正在言说什么”[37]31,应更多被关注。正如贡布里希所说:“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38]21在岩彩画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去模仿或重复过去的岩彩技艺,而是进一步对观念演进的明晰,及不同场域空间的社会性、人类性的思考。尤其在当下,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视觉呈现方式不再是共性的语境的催生物,更多是多元发展下的视觉倾向,是岩彩画家创作动机、人文关怀及精神状态的真实体现,是主体审美意识对客体的建构。
二是认为印度佛教的传播带来了岩彩画。此种观念是从宗教壁画传播的角度来审视岩彩画的流变。印度的阿旃陀壁画是现存最早、最负盛名的印度古代壁画,其制作颜料取自当地火山石矿物质,主要有朱砂、土绿、土黄、石灰白、紫色、群青等,绘制画笔为不同尺寸的兽毫,在绘制过程中,首先用红赭石起稿,随后以浅灰绿打底,再染专属色,完成后分别用棕色、暗红色或黑色线条复勾完成[39]193。从色调来看,有早期的暖色调及后期的冷色调。壁画审美情感基调因基本主题的改变,在“艳情味”与“悲悯味”之间不断发生转化[39]195。同时,在人物设色观的表达上,已有主观色的呈现。张小鹭明确指出,中国岩彩艺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美术,并受到犍陀罗、秣菟罗、笈多佛教艺术及波斯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40]。同时,吴焯在对克孜尔壁画岩彩色彩的考察中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吴焯认为克孜尔壁画皆矿物质颜料,有土红、赭、青、绿、朱、白,但以青、绿为主[41]。从岩彩的技法表达来看,早期克孜尔石窟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仍然沿用阿旃陀的用线方式,通过线条来勾勒区分形体,但并不注重线条自身的变化。到了中、后期,因中原文化的回流,对线条的形态的重视才发生了体现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线性转变。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大量运用青金石来绘制壁画,尽管与丝绸之路的贸易有关,但从岩彩用色的范式来看,也是阿旃陀壁画用色的延续,包括凹凸画法的传播,都属于“宗教绘画体系”[42],只是在发展的脉络中能明显看到岩彩画的传播方式。因而,明晰岩彩画的发展,对研究及回溯阿旃陀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敦煌莫高窟等石窟壁画是必要的。
三是认为岩彩画来源于日本[43]。此种观点是以矿物质颜料的种类、色域的拓展来立论的。何鸿认为,“日本岩彩的观点有它的合理性,那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矿物质颜料绘画基础上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功劳非日本人莫属。”[44]用矿物质颜料作画在中国虽历史悠久,但从吴、晋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吴晋本草)》记载来看,主要的矿物色有:丹砂、空青、白青、曾青、扁青、雄黄、石灰、铅丹、粉锡、岱赭、白垩等。[45]68从莫高窟石窟壁画来看,有石青、石绿、朱砂、朱磦、雌黄、石黄、铅粉、高领土、赭石等色。整体来看,色类稀少,色域单一。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岩彩画在绘制过程中对色彩层次的区分,以水分的干、湿、浓、淡,积色体或敷色体的表达手法来区分,并没有从色彩自身的属性进行探索。相反,在日本的岩彩画中,自飞鸟、奈良时代矿物质设色技艺的传入及破土,日本画家在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在中国原有矿物质颜料色彩的基础上研制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岩彩材料,使得矿物质色划分更加细致。如有天然矿物色、化学合成矿物色、人工矿物色(新岩)、水干矿物色、水性色、金属色等,种类繁多、色域丰富。最具革命性的是将矿质颜料研磨成1-18个粗细不同的等级,并将岩彩材料作画的单一方式拓宽到不同综合材料的运用,还在“脱中吸西”的时代语境下,结合西方美学理念,从绘画表达形式、金属材料等的运用上探索,带来不同以往的视觉呈现形式。不难看出,对岩彩色彩浓淡的区分不再以用水的多少来体现,更多从颜色的不同等级来区分是取得的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冲击及影响下,视觉文化形态的转变,使得岩彩画的功能性从“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趣味”[46]86转变为艺术观念、哲学意味、物质属性传达的媒介。因而,新时期以来中国岩彩画的复兴正是站在日本岩彩画的肩膀上,探寻发展而来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岩彩在当下的语境中有一部分已转换为当代艺术,急需思考国家形象等问题。
岩彩画作为古老而又当代的视觉艺术承载体,在新时期新的发展过程中,岩彩画家的探索成果值得由时间检视。同时,岩彩画在从古至今的演进及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是早期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承载体,从共性向个性的更迭,既有民族的迁徙、宗教文化的传播,也有沉沦多年后的脱胎换骨。总体来看,岩彩从源初的观念色到自身物质属性的转变,在不同的文化视角、宗教信仰及材料色域上的拓宽,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时期、阶级的基本观念”[47]7。在当下,作为观看者如何解读岩彩画、如何创作岩彩画尤为重要。如胡明哲所说,要以“开放的心态”和“个性的立场”去“吸取东西方的精华,从宏观的角度拓展审美视野和表现能力”[17]。未來世界并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单边文化世界,是不同文化及文明互鉴、人类文明的共同体[48]1,以岩彩画为载体,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彼此尊重材料和观念的差异性,寻找沟通差异的方法[49],不以既定的模式与观念去禁锢人们的思想与心灵。新时期以来,以岩彩进行绘画创作的觉醒,既是中国色彩绘画在“中国画格局中地位的重新构筑”[50]93,亦是对汉晋隋唐以来绚烂辉煌的中国传统绘画古典样式的重新揭示。因而,在当下,亟须以岩彩画厘清中国绘画的色彩观。
[参考文献]
[1]尚辉.开放中的审美突破与文化穿越——中国美术改革发展30年[J].艺术百家,2009(1):8-16.
[2]朝鸿.岩彩的回归之路[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12):21-23.
[3]大村西涯.中国美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4]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M].郑威,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6]翁再红.从民族艺术走向世界艺术:论跨文化传播的“三重门”[J].广西社会科学.2016(7):180.
[7]刘晓路.世界美术中的中国与日本美术[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
[8]杨佴旻.二十世纪中日绘画革新比较与批判[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1.
[9]刘晓路.日本美术史话[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10]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11]东山魁夷.我的窗[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胡明哲.闫振铎先生访谈[J].中国艺术,2010(11):24-31.
[13]胡明哲.澄怀观道——反思中国岩彩绘画之历程[J].中国艺术,2010(11):144-151.
[14]王伯勋.存在与转换——访谈中央美术学院胡明哲教授[J].美术,2008(3):58-63.
[15]纳禾雅.岩彩与微尘——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教授胡明哲访谈[J].中国艺术,2009(2):73-91.
[16]胡明哲.以岩彩为契机——从熊文韵画展谈起[J].美术观察,1997(3):36-37.
[17]胡明哲.谈“岩彩”命名[J].美术,2002(11):60-61.
[18]高占祥.中国岩彩画的开拓者[J].中国民族美术,2016(9):42-47.
[19]刘新华.勿忘民族性[J].艺术沙龙,2013(5):158-175.
[20]潘世勋.“岩彩”作为画种的提法不妥[J].美术,2002(7):78.
[21]杨劲松.岩彩是个话题,也是个问题[J].中国艺术,2010(11):57-63.
[22]李熙耀.词义的引申和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J].教学与进修,1984(7):21-24.
[23]宗守云.新词语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J].现代语文,2006(3):10-12.
[24]王雅观.山海经颜色体系探究[D].温州:温州大学,2018.
[25]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含义探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6]朗格.艺术的问题[M].藤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7]姚最.续画品并序[M]//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2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29]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J].语言文字应用,1999(2):16-22.
[30]夏坚贞.斑斓之美——中国岩彩画艺术[J].西北美术,2003(3):45.
[31]王雄飞.中国岩彩画材料与表现[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
[32]阿纳蒂.艺术的起源[M].刘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3]豪厄尔斯.视觉文化[M].葛红兵,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4]蔡曙山.人类的心智与认知——当代认知科学重大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5]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3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37]艾略特.文化定义札记[M].伦敦:Faber and Faber,1948.
[38]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范景中,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39]王镛.印度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0]张小鹭.岩彩画的艺术环流特征及其当代发展的可能[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35-37.
[41]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J].文物,1984(2):14-22.
[42]侯黎明,梅繁,章后儀.敦煌岩彩与敦煌画派——来自西部的岩彩[J].美术研究,2015(10):113-116.
[43]李彩.浅析岩彩、重彩之异同[J].美术教育研究,2016(9):22.
[44]何鸿.唐卡绘画与岩彩画矿物色使用比较[J].荣宝斋,2013(12):60-77.
[45]蒋开发.日本岩彩风景画发展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68.
[46]伯格.观看的方式[M].伦敦:BBC and Penguin Books,1972.
[47]帕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M].纽约:Harper and Row,1972.
[4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9]景宇平.中西方文化概念与跨文化交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5):54.
[50]牛克诚.色彩的中国绘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3.02.005
[收稿日期] 2022-12-16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唐代敦煌壁画服饰中印染工艺的应用及特征研究(20YB123);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2020A-180)
[作者简介] 田卫戈(1962—),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理论研究。杜星星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