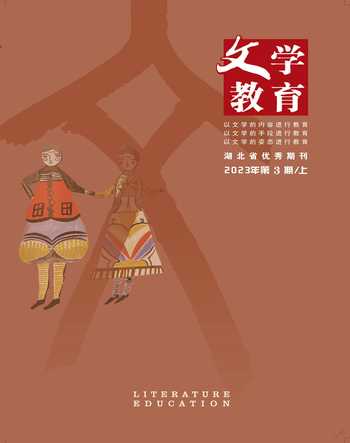白先勇《孽子》中的身体叙事
陈雨楠
内容摘要:《孽子》是白先勇至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白先勇对于人物身体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身体可以说是《孽子》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本文将从身体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文本中的身体表征与身体呈现,以此剖析小说中的同性恋群体怎样在身体上实现其主体性,释放自己内心的本能欲望与生命活力,并逐渐确立自我身份。
关键词:白先勇 《孽子》 同性恋 身体叙事
白先勇是当代中国台湾文坛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孽子》是白先勇至今为止唯一一篇长篇小说。小说出世之后受到了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的关注,称赞这部小说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因此国内学界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讨,但大多数论者都是从主题、人物形象、意象意义、社会历史内涵等维度对《孽子》展开研究,对于文本中的身体话语投入的关注不多。其实《孽子》中有不少有关身体刻画以及身体体验的文本内容,身体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元素,因为它承载了其他叙事元素所无法表达的意义。身体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彼得·布鲁克斯指出“叙述性写作的对象与主题——在想象的生活中,身体受到了第一位的、强烈的关注”[1],身体被看作是指意活动,独特的他者,“写作指向身体则意味着试图将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2]。本文将以“身体”作为切入点,试图为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内涵与特征提供另一种可能。
一.动物化的身体:对抗规训的生存形态
《孽子》中有许多动物性的、原始性的描绘,在第二部“我们的王国”中,公园被描绘成一个丛林,四周“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3],而“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地聆听着”[4]。对于孽子们,作者并没有以普通常规的方式去刻画他们,而是将他们的身体动物化,他们不仅有着动物的名字,人的身上也出现大量的动物特征与元素,他们的行为也与动物有着相似之处。人的动物性是一种原始的状态,在原始社会时人的动物本能并未受到什么约束,而在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人身上的动物性则被逐渐消除。孽子们身上所附带的动物化特征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描写,它所表现的是对于文明社会秩序的抵抗,是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并回归到自己的生命本能以及欲望之中。
在这些动物化的身体中,最为形象的就是老鼠,他长着“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5],不论是笑还是惨叫总是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他总喜欢偷东西,看见别人的东西就喜欢拿来玩玩。在盛公家开派对的时候,“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6],老鼠偷东西却从来不偷钱只偷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到“百宝箱”里当宝贝供着,通过占有他人的东西而使内心受到的巨大压迫得以释放从而获得一种放松感。与瘦弱的在夹缝中生存的老鼠相比,有着充满原始野性的铁牛与阿凤。铁牛与他的名字一样,有着强健有力的身体,他的“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坟起”“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7],就像那个艺术大师所说的一样,在他身上才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不像那群大学生只是一束塑料花。而阿凤则是一只野凤凰,他长着一张最为桀骜不驯的脸,“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8]他生下来就是为了逃的,谁也“关”不住他,只能任由他四处浪荡,也因此才有了他与龙子的传说。孽子们在动物化的身体之中实现了自我欲望的释放与满足,同时这种动物式的身体表达之下所隐藏的还是一种不被社会主流认可从而产生的一种异化,在排斥中去寻找来自边缘地带的自我认同。
在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身体是被规训的对象,“纪律的历史环境是,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9]《孽子》中虽然没有有意刻画这种规训机制的存在,但它却在小说中时隐时现,默默的展现自己的强制力量,它以自身的存在强调着社会中不可侵犯的基本准则。李青在小说的开头便因和管理员赵胜武发生淫亵行为而被勒令退学从而逃离家庭;傅老爷子的儿子阿卫在部队时被长官发现与下属发生行为而要受到军法审判;在警察局中被审问的“我们”以及大家都惧怕的火烧岛。学校、军队、警察局、监狱甚至家庭都难以容忍孽子们的“非法”行为,它们企图将“不正常”的孽子们治疗与教化成“正常人”,在这种压迫中他们逃离到被称为“我们的王国”的公园当中。正如孽子们自己也认同的那样“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10]在无规训的边缘地带,靠着动物的本能去生存必然会有一些非法活动。犯罪以及同性恋行为都是被主流话语当作一种怪物而孤立起来,但是这些行为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反对‘文明的武器”,它“唤醒了我们浑沌麻木的情感与半遮半掩的激情。没有犯罪,我们将长久地陷于混乱与软弱。”[11]但与遵守法律的人相比动物并没有这种意识,他们的行为来自于生命欲望,正如尼采所讲的那样,“唯有总是被不恰当地忽略与诅咒的、与动物共同分享的生物性身体才是人类最重要、最真实的本己力量。”[12]被动物化的孽子们所做出的非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合理化”了,同时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也在其中被“合理化”了。
二.衰老的身体:生命活力的喪失与渴求
在《孽子》中有两类对照鲜明的同性恋者,一类是充满着生命活力但生活在社会底层无依无靠的“青春鸟”们,如:李青、小玉、吴敏等;一类是不为金钱与地位所困扰但是精神空虚的老同志们,如:盛公、阳峰、郭公公等。后者时时刻刻追逐着这些青春鸟们,从他们身上汲取生命的活力,在他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中感怀自己昔日逝去的岁月。
“在白先勇的小说里,返归起源、寻求归属的意识,以及对生命有限性的自然焦虑,是极其强烈的两个相关方面。”[13]身体是时间流逝最为明显的标志,白先勇有意的刻画衰老的肉体与年轻充满活力的肉体,并将他们并置在同一时空下。盛公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举行一次派对,他总坐在自己的太师椅上,头上顶着一撮残剩的稀发,背因为风湿痛得弯成一把弓,“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既感兴味又无可奈何地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14]这些青春的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在客厅里蹦跳着,飞跃着。而盛公只能望着他们,在宴会结束之后颓然坐在太师椅上,淌下了两滴衰老的眼泪。相同的还有阳峰,曾经的他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非常英俊,是台语片的红小生。现在的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只能用一顶巴黎帽遮住自己的脑袋。在书中他是华国宝的追逐者,华国宝有着漂亮而又健硕的身体,似一只一只踌躇满志、羽毛灿烂的孔雀一般。在这种对照中刻画了暮年人精神萎靡的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力退化的生命现状,而青春的肉体则能唤起他们片刻的活力,衰老的人们需要通过年轻肉体的存在来安慰自己由于生命力不断消逝而出现的焦虑,所以他们总是寻找、追逐着这群 “青春鸟”。可是实际上这种并置所呈现出来的却是更加沉重的悲哀,因为这种关照与注视与其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安慰,还不如说是一种证明,证明自我的青春已永远的消失而再也无法重现。
这种对照不仅仅只出现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文本中它同样还体现在此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当中。《孽子》里几次出现那些已经衰老的人们过去的画像,相片里的盛公是一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青春艺苑里也挂着阳峰年轻时的照片,那时的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不仅仅是对于同性恋群体有这样的描写,同样在这个群体之外的人也表现出了今昔的对照。傅老爷子墙上挂了一张盛年时候在大陆着军装的半身照,那时他的身子却是笔挺的,很是英武,而现在整个背都弯了下去。父亲的案头上也有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脸上带有胜利的得色,不似现在这般一头钢丝般花白的短发和悲痛灰败的脸。在时间的腐蚀下他们年轻的脸上布满皱纹,强健的身躯失去活力。他们为时间的流逝及其有限性而感到焦虑与忧郁,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总是抵挡不住时间长河的奔腾,过去的辉煌与青春在一眨眼间便消失不见。在这种对照之下,时间显得格外的残忍。为了留住那片刻的青春,里面的人物借助外力尤其是艺术将青春之美定格,从而“想象着返回起源(青春)”[15],正如艺术大师所说的那样:“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16],他不断地挑选着身上具有原始生命力的人来做他的模特以完成《百子图》这个巨作。郭公公的《青春鸟集》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本相册里全是一些少年像,每张相片都有编号,下面还标注了日期与名字。这些是由被定格的身体而形成的图像,它们背后都承载了每个人在那时的故事,人们通过“看”这些图像而追忆某个人的当时,在“追忆”与“看”时也是对生命活力的渴望与回溯。
三.疗愈的身体:自我身份的迷失与确立
在《孽子》中白先勇多次描写到身体上的伤痛,它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是伤痕,有的是身体上的变形。这些伤痛不是仅仅代表着肉体上所受的伤害,它们背后还隐含着诸如人的心灵、社会的排挤以及生存的艰难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些伤痛可以看作是标记或者象征,就如同奥德修斯的伤疤,“身体的标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字符,一个象形文字,一个最终会在叙述中的恰当时机被阅读的符号”[17],作为符号的身体承载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作为同性恋的“孽子”们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他们只能飘荡在黑暗的角落,他们身上的伤痛象征着他们所经历的不幸与苦难,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驱逐与排斥使得他们承受着精神上与肉体上的双重重负。吴敏因为无缘无故的遭到了张先生的抛弃而选择了自杀,他的手上留下了两寸长的刀痕。吴敏的自杀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家”。吴敏是个爱干净的人,他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流浪,连个像样的洗澡间都没有,他头一次搬到张先生家里时就在洗澡间里洗了一个多钟头。“干净”对于吴敏来说意味着流浪生活的结束,而这个家终究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它并不真正属于吴敏,他还是带着他的疤痕回到了黑暗的王国里。老鼠因为相貌较差只能接一些带有虐待性质的性交易,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18],他还时常受到表哥乌鸦的毒打,总是旧伤未好又填新伤。龙子在杀了阿凤之后被赶到美国,短短的一个夏天瘦的和麻风病人一般,一双手臂瘦棱棱像钉耙似的。还有小金宝畸形的右足使得他脚背磨得都是老茧。在小说中“孽子”们对于自己内心的隐痛很少直接的去表达与宣泄,通常是以身体上的一些特征以及行为体现出来,心灵的感觉往往是捉摸不定的,而身体的知觉却是具体的,以身体作为媒介传达难以言喻的内心感受。这些伤痛不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它背后都暗含着令人心酸的故事,正是由于伤痛的存在故事才有被叙述出来的可能,只有通过这些伤痛背后的故事才能知道“孽子”们为何会变成这样的又是怎样变成这样的。
这些故事是残酷的,这是“孽子”过去的经历,而伤痛的愈合则象征着自我身份确立的可能。孽子们起初是凭着一种本能来到公园来寻求认同,他们内心还时时抱有对自我的怀疑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迷惘与疑惑,而在第四部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各自的蜕变,真正的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老鼠臂膀上的泡疮出现过三次,三次泡疮的出现都分别对应着三个不同的场景,第一次是老鼠因为偷人家东西被杨教头教训了一通,这时老鼠的臂膀刚被烫出泡疮;第二次是乌鸦输钱把老鼠当出气筒打了一顿,老鼠的泡疮已经冒出白白的脓头了;第三次是老鼠和乌鸦起了冲突最终离开了乌鸦家,泡疮只是作为“烧起过的烟泡”出现在他的臂膀上。最终泡疮的愈合象征着老鼠开始自己的生活的可能,就像他最后给李青写信时所说的那样他找到了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吴敏一直很羞于将自己手腕上的刀痕露出来给人看,它时刻提醒自己过去的难堪,傅老爷子在看到吴敏手腕上的刀痕时将自己的表褪了下来给吴敏带上,遮住了他的伤痕。这是一种别样的治愈方式,伤痕的遮盖意味着对过去的和解和心灵上的治愈,尤其是这个手表来自于一个父亲的赎罪与悲悯。在第四部《那些青春鸟的行旅》中他们重新开始了各自的生活,小金宝的右足也在王夔龙的帮助下得到了治疗,摆脱了身体的畸形对他的折磨。这些身体上的伤痛在最终得以愈合,这种身体的感知与心灵的感知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身体在知觉场域以自己的方式原发地激起被知觉者的景象,知觉也从所给予者那里获得已潜藏着的感受。”[19]如同这些身体上的伤痛在时间的流逝或者治疗之中逐渐愈合,心灵上的伤痛同样也得到了治愈,自身也在这個过程中得以重塑,孽子们在确立自我身份的基础上重新开始面对这个世界。
综上,“身体”在《孽子》中是不可忽略的叙事元素,作为社会边缘人群的同性恋难以以常规的方式生存,而他们的生存处境与心灵状态在最原始的身体当中得到了体现。因此,身体在小说中表现出双重特征,它不仅是被放逐、被迫害的身体,它更是积极反抗、主动追寻的身体。少年同性恋者寻求着自由与认同,老年同性恋者则追寻着青春的影子,他们内心深处都有着难以抑制的生命活力或者欲望渴求,而这些在他们的身体话语中有很深的体现。本文运用身体叙事学进行分析,为研究《孽子》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参考文献
[1][2][17](美)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28.
[3][4][5][6][7][8][10][14][16][18]白先勇.孽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7,13,87,62,88,66,7-8,86,19,13.
[9][11](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 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56,327.
[12][19]陈治国.论西方哲学中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84-91.
[13][15]朱立立.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77-81+104.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