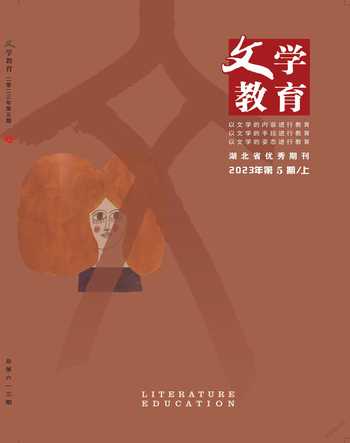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文本细读
杨华
内容摘要:《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其后续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基点。在这篇小说中,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打破了小说叙述的理性逻辑,通过对官能的极致调度实现了一种直觉式的写作。这种官能调度的手法背后隐藏着作品的文本逻辑,也暗示着作者创作的内在意图。或许莫言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实现的对生命、对希望的呼唤,最初就是从黑孩对红萝卜的追求开始的。
关键词: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 官能调度 生命意识
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自发表便广受好评,作者莫言也不曾吝啬表达对这篇成名作的喜爱。他对作品的主人公黑孩称赞有加:“黑孩子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护神。”[1]
可以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其后续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基点。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莫言第一次找到了独属于他的笔调,讲述了一个7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故事。在文本中,他打破了小说叙述的理性逻辑,转而以一种感性的、直觉的方式进行写作,具体体现为对官能的极致调度。他不仅让作品中的人物被官能所主导,甚至会让读者不得不最大程度调动感官去追随作家的文字,探寻文本的主旨意图。
一.文本的官能调度
在《透明的红萝卜》创作谈中,莫言说:“这篇作品第一次调动了我的亲身经历,毫无顾忌地表现了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写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2]为了将自己对自然、对人事的直觉感受融入到作品中,作家强化了作品中人物的感官体验,同时将情感注入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当中,营造出神秘与真实相交织的氛围。为了更加突出作者想表达的内容,文本中人物的官能也在作者的调度下相应地放大或削弱,构成了互相之间力量的转化。
1.听觉的变形
文本中听觉的变形可以说是本篇小说的一大特色。故事主人公黑孩全文没有说过一句话,几乎所有交流都是通过神态变化或肢体动作完成。我们从小石匠的话中能得知,他是从一个说话像“竹筒里晃豌豆”的孩子變成当下沉默寡言的“小哑巴”的。文本的小天地中,人们的语言极度贫乏、野蛮,在基础交流之外缺少深层沟通的欲望和能力,语言存在的意义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文本中的自然之声被相应地放大了。作为一个关闭了语言表达系统的孩子,黑孩具有超自然的听觉。他能听到“黄麻地里的音乐和秋虫鸣唱”,能听到“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震耳欲聋的声响”和“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自然之声的放大一方面是因为黑孩关闭了部分的语言表达官能,而增强了听力;一方面也是因为黑孩将自己的想象与声音结合了起来。换言之,他听到的声音都是被他的主观精神所放大的。比如在菊子给他送饭的时候,他听到菊子“头发落地时声音很响”。头发落地的声响是正常人的器官无法捕捉到的,但因为黑孩对菊子隐秘复杂的感情,这种声音就在他耳中被无限放大了。
2.视觉的强调
文本中存在着两个维度的色彩,一是现实环境中存在的景物、人物外在形象的色彩,一是超现实的、抽象化的色彩。这两个维度色彩之间的界限被作者有意模糊,导致文本中的色彩呈现处在一种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境界中。作者在写作时俨然以画家自居,以油画的方式对文本的人物、景物进行大面积的着色。作品中的人与物都被强烈的色彩所包裹,色彩被赋予了符号化的意味。
主人公黑孩就是这样一个被色彩包裹住的人物。他不需要有名姓,一个“黑”字就能准确地称呼他。黑孩瘦小的身体、清澈的眼睛、在风箱边烘烤出的煤炭似的皮肤仿佛都可以被黑色概括。同时,黑色也能表现出黑孩的沉默、阴郁,以及他本性中的灵气。除了黑孩之外,女性角色菊子也被浓烈的色彩所笼罩。菊子蒙着紫红色头巾,穿着有红线交叉成的方格的上衣,连手帕上也绣着鲜红的月季花。红色,代表炙热的情感,也是引人迷乱的情欲象征。文本中还有多处红色的点缀,如小石匠的红运动衫,小铁匠烧红的钢铁,黑孩的红萝卜,无一不附着了这近乎妖冶的色彩。
在这篇小说中,色彩可以代表人物的形象、个性,也可以抽象为一种情感、欲望,甚至可以指向某种能量。当反差强烈的色彩共同出现,读者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能量的交锋。小石匠与小铁匠因菊子大打出手,视觉上的呈现即为“一白一黑两个身体扭在一起”。争斗的结果是潇洒漂亮的小石匠敌不过粗鲁野蛮的小铁匠,黑色盖过白色,意味着黑色代表的原始兽性悄悄抬头。当菊子与小石匠在黄麻地里野合,菊子的紫红色头巾落到黄麻杆上,红格儿上衣也落到地上,衣料的红与黄麻的黄相融合,人也在自然的怀抱中释放欲望与情感。文本的最后,黑孩被扒去衣服钻入黄麻地,就像一尾黑色的游鱼回归黄色的大海。作家通过对画面中色感的强调,抽象地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
3.触觉的削弱
故事主人公黑孩在官能上的另一特征就是他触觉的极度钝化。这种钝化人物某种感官的情况与上文写到的听觉类似,意味着作家希望在关闭黑孩某种感受通道的同时打开他另一个小天地的大门。黑孩感受不到冷热的刺激,对疼痛的反应也十分迟缓。因而,读者在不自觉代入黑孩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就随之淡化了触觉上的感受,在阅读时下意识选择不在意外界环境给黑孩带来的触觉上的刺激,转而更加专注于他脑中种种奇异的想象,或是心中隐秘的情感。同时,黑孩对肉体伤害的无感,也意味着他不会因为感受到身体上的折磨而被伤害。
事实上,黑孩所处的环境充斥着野蛮和暴力。在小说里的年代,最被轻视和最被重视的都是人的身体。人的价值以其能等价的劳动力为单位进行计算,包括工分其实也是一个力量单位。此时,环境的逻辑已经退回到原始社会弱肉强食的模式当中,这也就导致了人性的野蛮,精神沟通的缺位等等问题,肉体力量成为了最重要、最基础的东西。或许正因如此,故事的每次冲突都会引向一次肉体力量的交锋。小铁匠对黑孩的殴打、小铁匠与老铁匠打铁时的暗中较量、小石匠与小铁匠的冲突,这些冲突充满了力量的较量。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小铁匠这一人物几乎就是环境逻辑中典型的强者——结实的肉体、优秀的打铁技术,这让他区别于普通的劳动力。围绕着小铁匠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两代铁匠之间的地位之争,一条是小石匠、小铁匠与菊子之间的三角恋。作为学徒的小铁匠迫切希望学到淬炼的手艺,真正能够替代老铁匠的地位。这种急迫的争夺欲促使小铁匠以野蛮的方式逼走了老铁匠,代价是在小臂上留下了一个疤。而老铁匠小臂的同样位置也有一个紫色的疤痕,暗示着师徒间力量的争夺、代际的更迭成为了规律。但在另一条故事线上,作为三角恋中的一角,小铁匠因为嫉妒小石匠与之大打出手。小铁匠虽然获得了肉搏的胜利,但在情感的较量中,只有力量作筹码的小铁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胜者,所以他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有力量的躯壳。
二.文本的欲望逻辑
由作者对人物感官的极富特色的运用,可以看出文本中普遍存在着官能力量的转化。换言之,作者在关闭人物部分官能的同时放大了其他官能的作用,拓宽了读者感受的疆域。作家文字中对官能的充分调动,也能直接地对读者产生冲击,从而将其带入到文本奇异的环境当中。在这样强调感官而弱化思想的环境中,肉体力量成为了最浅显的逻辑。我们或许可以猜想,作者将故事的时代背景、发生地点模糊化,就是为了呈现出人类最原始的生命状态,即原始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模式。但我们也发现,力量为尊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作为力量象征的小铁匠最终失去理智,沦落成了一个疯子。这也就说明,肉体力量并不是真正的主宰方,其背后必然有更根本性的存在。
重新回到文本开头,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故事的发展始终是在不同人物不同欲望的影响下进行的。队长的出场状态就是进食,老鼠一般的咀嚼动作传递出了强烈的饥饿感。而紧接着村民们眼巴巴望着队长腮帮子的目光告诉我们,故事就设定在一个连人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环境中,从而顺理成章地让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欲望成为了支配性力量。但小说的几个主要角色显然并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产生了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欲望。此处,我们可以把这种欲望的实现分成三条线来进行简单的区分:一是小铁匠、老铁匠对于地位的欲望;二是小石匠、菊子、小铁匠、黑孩对情感与性的欲望;三是黑孩对于自我实现的欲望。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梳理文本脉络,可以发现文本的两个高潮(红萝卜事件与打斗事件)正发生在这三种欲望交织并相互碰撞的时刻,其中前者可以说达成了欲望的满足,后者则伴随着欲望的破灭。
1.欲望的满足
某天晚上,众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在桥洞里烤地瓜、吃萝卜,这个场景其实承载了多重含义。具体来说,这个夜晚既是老铁匠的谢幕之夜,小石匠与菊子的定情之夜,同时也是小铁匠与小石匠的结仇之夜,黑孩的成人之夜。
铁匠师徒力量争夺的最后结果是小铁匠完成了对老铁匠权威力量的挑战,并且成功拥有了超越老铁匠的力量。老铁匠显然希望在这个夜晚最后一次释放出属于他的,或者说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力量,所以他倾注所有感情吟唱了一段戏文。这段吟唱同时成为了菊子与小石匠的催情剂,二人在歌声中敞开心扉,达成了情感上的沟通。因此,自第二日起菊子与小石匠在黄麻地里私会,来满足克制已久的情欲。二人情感的圆满刺激到了两个人:一是对性有极强欲望的小铁匠,他直接被激怒,產生了与小石匠争夺菊子的想法;二是对菊子有畸形情愫的黑孩,但与小铁匠不同,一直以来他对自己的欲望没有明确的认知,是小石匠与菊子的恋爱激发出了他的嫉妒和占有欲。也可以说,菊子与小石匠的恋爱成为了黑孩成人的催化剂。菊子清洗遗留下来的红萝卜上附着了黑孩对母性温情的需求、朦胧的情欲,所以他会看到一只禁果一般闪耀的“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的萝卜”。当然,这并不是黑孩成人的全部动因。天性中的灵气指引着黑孩对大地的馈赠有着神秘的感知,而老铁匠的存在同时教导了黑孩关于人世的体会,于是黑孩拥有了能在自然与人之间穿梭的感知能力。由此,他才能从一颗自然的作物中体会到人类心灵的震撼。可以说,这棵红萝卜不仅凝结着黑孩青涩的情欲,更闪烁着他理想信念的光芒。
2.欲望的失落
然而,几个人物之间欲望的互相影响最终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小铁匠失控地扔出了红萝卜。随着萝卜沉入河流,老铁匠随之离开。留下的四个人物中,黑孩与小铁匠、黑孩与小石匠、小石匠与小铁匠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当小石匠与小铁匠为了争夺菊子贴身肉搏时,黑孩冲出来帮助了小铁匠,实现了自己情欲不得满足的报复,这场闹剧最终以小石匠的重伤、菊子的失明、小铁匠的发疯和黑孩的怅然若失收场。打斗中占上风的小铁匠并没有获得实际上的胜利,因为肉体力量永远无法成为复杂世界里单一的主宰。而余下的各人也因为欲望的破坏与消解从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渐离开了故事的中心。最后留下的黑孩,心中终于只剩下那颗金色的、透明的红萝卜。
在黑孩最后一次去萝卜地偷盗时,作者特意让他换上了衣服,又很快借惩罚为由将衣服全部扒光。在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情节中,黑孩的眼睛清澈如水,他赤裸的身子最终化成了一尾游鱼回归到了自然的怀抱中。黑孩在钻入黄麻地的那一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生命力的个体,他直接通过自我与自然的结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由此,因众人欲望的失落而失去生机的黄沙漫天的世界终于回到了明晃晃的秋色与阳光之下,一种全新的力量由此诞生。
三.文本背后的生命力量
莫言曾说过“这篇小说里写得几乎全是‘我”[3]。在写作过程中,作家调动了自己对最熟悉的故乡的土地和人事的记忆,创造了一个极简的、原始的、真实的空间。人退化到最简单的状态,基本的生存法则是力量至上,大多数人都被个人的欲望所支配。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或者感人至深的情愫。人只能偶尔凝结起微弱的情感,或者直接选择面对自己纯粹的兽欲。作者剥落了复杂社会的外壳,向我们呈现出他所认知的时代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展示了人性的卑弱,以及人类生存模式的亘古不变。然而,荒凉且贫瘠的人类世界还是有斑斓色彩的,这是感知力与想象力的功劳。作者赋予了黑孩细致入微的感知,甚至近似于超自然的能量,并且通过黑孩最后回归自然的一幕让我们明确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相融合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的希望感与生命力。文本中真正有力量的都是人与自然的产物,譬如老铁匠的歌声、透明的红萝卜、用以野合的黄麻地。只有这些存在的时候,人才能感受到希望。而这种力量和希望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所缺少的,也是作家希望通过作品来呼唤的,对这些东西的信仰是作家写作整部作品的支撑。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找到自己创作方向的起点。莫言说黑孩子伴随他走遍天下,是他的保护神,或许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实现的对生命、对希望的呼唤,最初就是从黑孩对红萝卜的追求开始的。与莫言之后的一系列作品相比,《透明的红萝卜》在技法上似乎表现得还不够纯熟,但恰恰是这种青涩让莫言小说里包含的生命意识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因而,我们阅读《透明的红萝卜》也就是在尝试解开莫言创作的冰山一角。
参考文献
[1]谢尚发.莫言的“红萝卜故事”——《透明的红萝卜》文本内外[J].东吴学术,2017(03):131-143.
[2][3]莫言.莫言散文新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8-29.
[4]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63-69.
[5]赵歌东.“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J].齐鲁学刊,2005(4):97-100.
[6]殷相印.莫言小说色彩词的超常运用谈片[J].修辞学习,2000(01):7-9.
[7]张清华.细读《透明的红萝卜》:“童年的爱情”何以合法[J].小说评论,2015(1):96-102.
[8]程光炜.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J].当代文坛,2011(05):16-22.
(作者单位: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