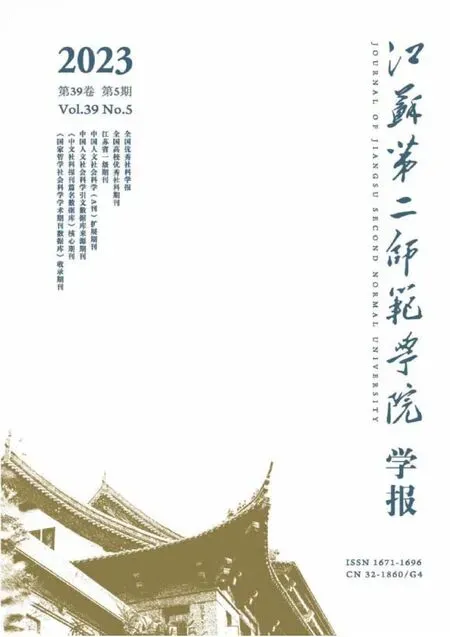林语堂的《水浒传》外部研究*
陈 智 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福建漳州 363105)
林语堂偏爱明清文学,尤其推崇明清小品和小说。国内外学术界对林语堂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其红学论著《平心论高鹗》(1966),有学者甚至认为,除了《红楼梦》之外,“林语堂对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可能主要停留在阅读、了解和使用层面”[1]。其实,林语堂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其他古典小说也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和论述,他对《水浒传》的研究虽然比较分散,但其研究深度仅次于《红楼梦》。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把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大体分为四类,即每一件艺术品必然涉及作品(文学作品)、艺术家(作家)、世界和欣赏者(读者)等四个要素。除了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加以研究之外,“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2]5;而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同样提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分野,他们除了研究作为自足体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把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之类不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统统归于‘外部研究’”[3]8,除了对林语堂在各种著述中谈论《水浒传》的文学类型、文体语言、艺术手法等问题的“内部研究”进行系统梳理[4]之外,为了更全面理解林语堂研究《水浒传》的深度,有必要以林语堂评论《水浒传》的文本史料为基础,进一步梳理林语堂对《水浒传》与作者、世界和读者等三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一“外部研究”问题的判断性文字论述,从而进一步完善林语堂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形象研究。
一、《水浒传》之作者
艺术家,即作者是文学活动的四大要素之一。韦勒克和沃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5]71如果作家未将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理解或感受行诸语言文字,文学作品的存在就无从谈起。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作者论”包括作者的身份定位、作者修养、创作目的和创作过程等几个方面。林语堂多次论述《水浒传》作者的身份定位和小说创作过程等问题。
首先,《水浒传》作者身份定位的模糊性与小说这种文体不为正统文学所接受的社会现实、小说家的心态以及中国小说兴盛较晚等主客观因素有关。早在1913年12月,林语堂就在《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爱好者一般喜欢诗歌、历史、哲学经典,更普遍喜欢短小精悍的论说文名篇(masterpieces in short skillful treatises),但却极少喜欢描写中国社会及介绍女性角色的小说”[6]。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读者既不尊重也不重视这种主要关注社会的小说”[6]。1935年9月,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中探讨中国学术时,对《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选集依据正统标准而收入其中的著作颇有微词,“虽然有更多著作受到赞誉,但仅在总目中进行简要介绍,这些著作并没有收入《四库全书》而永存于世。像《水浒传》或《红楼梦》等真正有创意的作品当然不被列入其中……”[7]223。林语堂认为,中国小说的兴盛比较晚,大量优秀小说值得保存,却未被视为正统文学,这与作者的心态有关,“中国小说家害怕让人知道他们竟然屈尊到写小说的地步”[7]269,因此这些小说家通常匿名而作。1917年胡适考证《红楼梦》而确定作者为曹雪芹,但《金瓶梅》在当时未知作者是谁,《水浒传》亦是如此,由于受正统文学传统的束缚,创作小说常常危及自身生命安全。“我们至今依然不知两位涉嫌作者,即施耐庵或罗贯中,究竟何者为《水浒传》的作者。”[7]269
林语堂还以一则民间传说详细介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成书过程的艰辛。《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故乡江阴仍有一种传说,该传说讲述施耐庵如何躲过一劫。据说,施耐庵具有先见之明。他拒绝在刚刚建立的明朝任职,当时他已写完这部小说,过着隐居生活。一天,皇帝和施耐庵的同窗刘伯温(当时已是皇帝的左膀右臂)来找他。刘伯温看到了施耐庵桌上的小说文稿。由于他认识到施耐庵天赋奇才,遂设计想置他于死地。当时,明朝初建,局势未稳,而施耐庵的小说宣扬非常危险的思想,包括盗匪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平民思想。因此,刘伯温随即以此为理由,请求皇帝宣召施耐庵入京受审。圣旨到达的时候,施耐庵知道自己小说的手稿被盗,认识到死期将至,于是他便从某一友人处借白银500两以贿赂船夫,让其尽量延缓舟程。“施耐庵得以在前往南京途中匆忙写完一部幻想神怪小说《封神榜》(该小说的作者实为未知),以此让皇帝深信自己精神不正常。施耐庵在假疯掩盖下得以保全自身性命。”[7]271林语堂不厌其烦复述有关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传说说明,当时作家创作小说往往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其次,林语堂还结合胡适、鲁迅等人的观点以及中国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详细概括小说中故事演变和作者身份的问题。1948年2月,林语堂用英文为赛珍珠再版《水浒传》英译本作序。他在这篇序言中并没有评价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质量,却以较多篇幅探讨该小说形成过程,尤其是作者的身份定位问题,他认为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2世纪初至16世纪,水浒好汉的故事经过民间说书人在口头上不断修改与完善,包括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很多编者在此期间不断改动故事、挪移事迹、变化人物名字和姓氏、变换重点人物的塑造,以富有的想象力和持续性的叙事手段,把许多水浒英雄的事迹或轶事有机串联起来,写作痕迹版本最终才以留存至今的形式逐步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林语堂依次列举郭勋、李贽、胡适和鲁迅等人的观点详细讨论该小说不同版本的作者身份问题,比如:“胡适认为,施耐庵乃16世纪一位默默无闻作家之假名,他修订了这部小说,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认同此说法。在1933至1934年,一个名为晁瑞廷的研究再次确定施耐庵的确存在,他证实施耐庵籍贯淮安,住于东台,并证实施耐庵乃罗贯中的老师,他在江阴某徐家做家庭私塾教师时完成了当前这部小说。”[8]13-18可见,林语堂在该英文序言中评论《水浒传》的重要论述焦点之一是该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备受争议的作者身份问题。
总之,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一文中所强调,“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9]林语堂对《水浒传》作者并未拘泥于某一特定的说法,而是对该小说身份定位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小说的复杂形成过程,即该小说创作主体、创作目的和创作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上的探讨。
二、《水浒传》之世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2]4。简言之,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条件,即“世界”“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感情、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2]4。就文学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西方传统文论的模仿说强调现实世界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林语堂在论述《水浒传》的世界这一问题上,重视现实世界对人的影响,多次强调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世界和反映作者心理状态的主客体相融合的统一体,即《水浒传》作者在创作时特殊微妙的心理过程。
1934年4月20日,林语堂在《论谈话》一文中认为,有闲的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有闲并无罪,善用其闲,人类文化乃可发达,谈话乃其一端……‘闲’有时是迫出来,非自求之”[10],除了周文王和司马迁在监牢里分别写出《周易》和《史记》之外,林语堂还举施耐庵及《水浒传》序言写作为例,“或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愤于文章,如施耐庵,蒲留仙,便有《水浒》,《聊斋》出现。施乃深得谈话个中滋味者。贯华堂古本序虽未必出施手,然其言朋友过谈之乐,实太好了……其文其情皆合著书心境,也是有闲所致”[10]。可见,林语堂强调,作者所处的社会风气、政治局势等社会现实对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35年9月,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谈及中国人的文学生活时指出,小说是在没有教化的环境中发展并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诞生,它完全是出于作者内在的创作冲动。所有优秀的故事和小说完全是出于作者对创作的兴趣,它与金钱并无关系。“再多的钱都无法让没有创作天赋的人讲好故事。虽然安逸的生活有可能让有创作天赋的人从事写作,但安逸的生活从不产生作品。”[7]272除了塞万提斯、薄伽丘、狄更斯等作家之外,“我们伟大的故事叙事者,比如笛福、菲尔丁、施耐庵和曹雪芹等,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有故事要讲且天生善于讲故事”[7]271。可见,林语堂强调作者的创作冲动与创作天赋对小说的发展尤为重要。换言之,作者与社会现实以及人生遭际等因素的互相感应,引发文学创作的冲动。
1937年11月,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论述日常生活享受之一的谈话时又一次强调“有闲”的重要性。“很明显,只有在有闲社会中才能产生谈话艺术;同样明显的是,只有谈话艺术的存在才能产生优美小品文……有时这种‘闲’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我追求的结果。然而,许多优秀文学作品是在被迫的空闲环境中产生的。”[11]217-218林语堂在此除了再次举周文王、司马迁为例之外,还举元朝画家、剧作家以及清初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为例,“其他在科举考试中落榜的伟大作家则把自己的精力转化为创作,施耐庵给我们留下《水浒传》,而蒲留仙给我们带来《聊斋》,当属此例”[11]218。林语堂同样以更长的篇幅翻译《水浒传》序言,并对这篇英译文做了相应点评,“我们认为《水浒传》的序言为施所作,这是最绝妙的朋友间谈话乐趣的一次描述……施耐庵的伟大作品就是在这种格调和情感之下产生的,朋友享受悠闲,才使该文的产生成为可能”[11]218-219。换言之,林语堂再次强调了悠闲的谈话气氛对艺术作品诞生的重要性。这和1934年《论谈话》一文中的观点基本一致。
1948年2月,林语堂在《水浒传》英译本的英文序言中认为,该小说的产生与宋代茶馆里说书人的底本《宣和遗事》存在巨大关联。“梁山泊盗匪的故事最早是由职业说书人口述的。如前所述,《宣和遗事》是根据众多职业说书人的口述而产生的……这些只不过是说书人的底本,语言大都草率,叙事简单,人物描写也薄弱。《宣和遗事》毫无疑问属于这一类型。”[8]16林语堂认为战乱时期王朝更迭的社会现实,即“世情”使说书人有话可说,施耐庵以此为基础,结合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特殊的人生遭际,使其自身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相互感应,《水浒传》由此生成。
1964年,林语堂在为其女婿黎明所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他说:“这些[文学]形式总是源自大众娱乐和音乐的土壤。当某种文学表达形式(比如唐诗)的最后细微差别消失殆尽,某种强大的大众艺术造就了新生活。宋词只不过来自歌女,而小说(或故事叙事艺术)则来自茶馆。诸如《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伟大小说只不过是对茶馆里早已为人所知的传奇故事的编写。中国文人素来‘抄袭古人’。当他们在技巧和词汇互相抄袭至极致之时,某种创新再一次从大众娱乐形式中焕发生机。”[12]vii换言之,外部社会因素是中国文学形式兴衰之周期性循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总之,林语堂论及《水浒传》产生的前提条件与他大力提倡性灵文学和闲谈笔调的小品文所需要的“有闲的社会”和“谈话的艺术”等因素别无二致,该小说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悠闲谈话。施耐庵经历科举落榜的人生遭际,他处于社会风气盛行谈话的现实世界,因而发愤著书《水浒传》。可见,林语堂在《水浒传》之世界这一问题上,注意到施耐庵与特殊的社会现实、人生遭际等之间形成的相互感应并引发他的艺术创作冲动。
三、《水浒传》之读者
艾布拉姆斯在艺术批评的四个坐标中同样强调欣赏者(读者)的重要性,“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2]4。他把以欣赏者为中心的批评称为“实用说”,这种实用主义批评其实是源自古代修辞学理论,即演说者为听众提供信息而感染其心灵,从而说服他们并获得其好感。他认为,实用主义观点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审美观点,此学说强调作家应该重视读者的阅读感受。林语堂同样多次论述《水浒传》与读者的关系。
1931年2月1日,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中反复以《水浒传》等小说说明,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书籍以及个人化的读书才是最佳的读书方法。林语堂认为,学生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他人无关,但现在却受到学校注册部、父母或妻室等人的制约。相反,读者自主决定阅读小说的读书方法才是真正的读书之道。“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13]林语堂认为,只有以主动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强制的方式去阅读某学科的书籍,才能真正学有所成,他对李清照兴味到时随手即读这一阅读方式的读书之法表示赞赏。林语堂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看不懂的书,看不懂的书无非就是原作者笔法表达晦涩难懂或是作者笔法与读者口味、学识等不相符合。换言之,如果读者选择兴味和程度相近的书,读者便可无师自通,如果遇到疑难,涉猎久后便可融会贯通,不存在阅读障碍的问题。他再次以读者看小说时遇到不懂字、句说明,所谓生字或难句等不会造成阅读障碍的问题,“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13]他同时认为,许多中国读者优秀的中文功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主阅读中国古典小说,频繁接触不懂的字句会提高中文阅读素养,这种“习惯成自然”的读书法也适用于读专业或学术性质比较强的书籍。
1934年2月15日,林语堂在《论读书》一文中指出,学校所读之书并非学生真正该读之书,他强调读者自由看书和读书,即自主阅读的重要性。学校读书的四大弊端之一就是:学校要求学生重点阅读的教科书不是真正的书籍。他认为,阅读《水浒传》等小说的阅读效果比阅读一本小说概论要好,而阅读《史记》的阅读效果比阅读历史教科书要好。他反对苦读,而是主张快乐读书,偷看《水浒传》等小说的人是在享受读书之乐,“国文好的学生,有些是由偷看《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六十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好学的人,于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14]。可见,林语堂强调《水浒传》等小说是读者自由消遣和快乐阅读的最佳书目之一。
1935年9月,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以小说的内容为标准进一步把中国小说细分为八种类型,而《水浒传》为冒险小说(侠义小说)的典范。《水浒传》的大众影响力远超神怪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淫秽小说、社会讽刺小说、幻想小说以及社会写实小说等各种类型的小说而位居榜首。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只能从读者阅读心理的角度去解释,小说中的侠义之士因为过度关注民间百姓之疾苦而为其打抱不平,并因官司牵连而被迫放逐异地,最后又被迫落草为寇。《水浒传》中官府眼中的绿林盗匪在普通百姓眼里却是绿林英雄,“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里,坚持替穷人及受压迫者打抱不平的人确实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硬汉……中国社会的这些安分百姓非常崇拜绿林好汉,犹如纤弱妇人崇拜面孔黝黑、满脸胡须和胸毛蓬蓬的彪形大汉。闲卧被褥中阅读《水浒传》,对李逵勇敢和英勇行为赞不绝口,还有比这更安逸、更兴奋的事?要知道,卧床阅读小说在中国乃是家常便饭”[7]275-276。可见,林语堂注意到阅读《水浒传》等侠义小说时读者的心理需求以及这类小说给读者提供心理补偿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小说阅读受众的广泛性。
1943年10月,林语堂在抗战期间第二次回国时再次对中国思想的混乱状态表示担忧。他在《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一文中认为,把《水浒传》等书列为有毒之书无助于本国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外国文化,且不必说,本国文化也难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但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就不能建立。”[15]因此,林语堂并不认同《水浒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有毒之说,也不同意小说里忠孝节义的思想有毒,而是强调《水浒传》对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的传承作用,而不刻意追究其历史或社会负面效应。林语堂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接受态度在当时还引发一定的社会热议。
1948年2月,林语堂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撰写英文序言中也论及《水浒传》内部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给读者带来愉悦感。首先是该小说的故事材料打动读者。他以翔实的文史资料进行阐述该小说赢得读者的同情在于,水浒英雄彼此之间高度团结、忠诚,在蒙元时期,百姓深受异族压迫和剥削,他们从绿林好汉的水浒故事中寻找慰藉便不难理解。换言之,林语堂对《水浒传》这部“怒书”的理解就是小说的创作者贴近读者的内心世界,作者与读者感同身受而互为交融,这是读者与小说作者在深层心理上,二者感应、共鸣、共振的最好写照。其次是该小说的人物塑造打动读者。林语堂认为,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和宋江等人物刻画在小说中最为深刻,尤其是小说第20章至41章武松的故事、攻打江州及宋江在江州之战后投奔梁山的叙事,以及第46章至49章攻打祝家庄、第62章至67章攻打大名府与曾头市的征战叙事。此外,“黑旋风”“小旋风”“豹子头”等各种人物绰号的使用为小说增色不少。这些细节评论足以说明作为《水浒传》书迷的林语堂对该小说的熟悉和喜爱程度,也代表了作为读者的林语堂对自由阅读作品的接受理念。
1966年3月14日,林语堂在《中央日报》“无所不谈”专栏发表《论趣》一文,他再次以《水浒传》等小说为例强调随性读书的重要性。他说,“读书而论钟点,计时治学,永远必不成器。今日国文好的人都是于书无所不窥,或违背校规,被中偷看《水浒》,偷看《三国》而来的,何尝计时治学?必也废寝忘餐,而后有成。要废寝忘餐,就单靠这趣字”[16]38。简言之,现代的机械教育导致读书论钟点,不易启发读者的灵机或启发心智。
1974年,林语堂在《论泥做的男人》一文中认为,《红楼梦》文字技巧的出色之处是作者对小说人物儿女私情的描绘。他以《水浒传》等为例进行幽默的比较评论:“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雌中又是丫头比姑娘出色。所以他不像《三国演义》,活现的写出关羽、张飞等一流人物;也不像《水浒》里,有武松一类的男人。我们不能据此而论,中国社会只有泥做的男人。我们看《汉书》,有范滂一流人物,也有范滂的母亲,都是有节气的人。那时还是封建社会,有义侠之风,睚眦必报……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也像日本的武士道,也像宋江忠义堂的义侠。”[16]46可见,林语堂对《水浒传》等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跨文化解读,正是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体现。
总之,林语堂反复以《水浒传》等小说为例说明读者与作者、作品的紧密关系,以及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林语堂多次强调《水浒传》是读者自由阅读和快乐阅读的重要文本,这既是《水浒传》本身巨大艺术魅力的体现,尤其是在故事材料和人物塑造方面对读者的巨大影响,更说明《水浒传》等侠义小说具有消遣娱乐和心理补偿等作用,对包括林语堂在内的读者一生读书甚至个人写作习惯的培养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结语
林语堂非常重视《水浒传》的外部研究,即关注小说的作者、世界和读者等问题。林语堂在众多论著和大量文章中以《水浒传》与作者、世界和读者的关系来评论《水浒传》。他关注《水浒传》的作者身份定位、创作目的及其复杂的创作过程,强调悠闲的谈话气氛对小说诞生的重要性。林语堂还探讨《水浒传》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即读者与作者、作品存在一种相互对话、相互召唤的关系,读者与时代也相互呼应,他从读者阅读《水浒传》的主观能动感受论述《水浒传》是培养读者自由、快乐阅读以及个人写作习惯的重要文本。总之,林语堂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论述《水浒传》的作者、世界和读者等问题,既是他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外部研究的重要例证,也是他向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