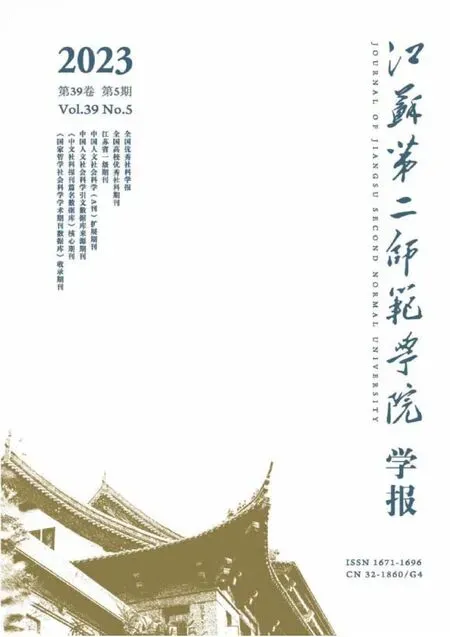试论《征兆和象征》中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叶 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文体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纵观其文学生涯,纳博科夫总在追求文学的艺术创新,并捍卫其文学创作的纯洁性和公正性。尽管并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流派,但他毕生用创作来践行使一部小说流传不衰的,不是它的社会影响,而是它的艺术价值。自然而然地,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先锋性”体现在其摒弃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被他贬为“可憎的庸才”,因为这些所谓的“大师”充其量是在逼真地模仿现实。但是,世上根本不存在逼真的模仿,任何作者充其量仅仅是在扭曲地模仿现实。他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超越了表面的模仿,而是一种揶揄式模仿,而“揶揄模仿的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 纳博科夫在1944年所写的《尼古拉果戈理》大声疾呼:“在艺术超凡绝俗的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者谴责强者之类的事情,它注意的是人类灵魂隐秘的深处,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声无息航船。”。[1]178
《征兆与象征》是纳博科夫在1948年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篇幅极其短小,只有四千多个单词,而且情节也颇为简单,主要叙述了一对老夫妻在儿子生日当天,精心准备了装有十种果冻的礼品篮子,兴致勃勃去精神病院给他庆祝生日。在路途上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到了疗养院,却被告知不能见到儿子,因为他刚刚自杀未遂,情绪仍然不稳定。万般失望之下,夫妻俩只好带着果冻,悻悻地离开疗养院。回家当晚因为牵挂着儿子,两人辗转反侧都失眠了,一番商量之后一致决定即使有再多的困难,第二天也要把儿子接回家来亲自照顾。心里石头一旦放下来,他们如释重负,感觉未来生活重新充满希望。老两口兴奋得睡意全无,开始沏茶畅想未来美好的生活。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一个女孩子温柔地问是查理家吗?老太太说打错了。过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还是问查理在吗,老太太只好再次解释打错了,此时老夫妻原先愉悦的心情多少被蒙上了一丝雾霾,当他们还在谈论未来团圆生活时,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这时故事戛然而止,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和现实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是,纳博科夫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之下,把大量的笔墨都聚焦在一家三口荒诞离奇而又窘困无望的生存境况——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他们沦为“难民”,万般无奈被迫逃离自己的祖国,流亡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流离失所的苟且偷生在他们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烙上了焦虑和痛苦的深深印记。本文将结合纳博科夫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理念来分析文本中涉及的象征主义手法、拉康的镜像理论以及黑色幽默艺术风格。
一、现代文明的荒原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建立在把社会秩序和“社会人”设想为相对稳定并且连贯一致的前提下的,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应该来源于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生活,因此是对现实世界高度浓缩的真实反映。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引发的动荡剧变,巨大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愈发难以调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结果就是旧世界的固有秩序彻底崩溃瓦解。随之而来的,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也被彻底颠覆,“理性”和“人道主义”失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普遍的幻灭情绪像厚厚的乌云一般,漂浮在人们的头顶上空,让人们窒息迷惘。生活在如此语境下,西方艺术家们彷徨挣扎在精神的“荒原”之中,痛苦地面对裂变的现实世界,只能抛弃长期以来对田园风光和风花雪月的吟诵和对理想生活的讴歌,转而深入到对现代人生存境况和内心世界的考量和思考。
首先, 由于人类所生活的客观世界遭到无情地解构, 小说很难再被认为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或者模仿,于是乎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取代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刻意用文本的虚构性来凸显对传统文本执着于真实性的反思和批判, 因为所谓的真实性, 究其本质来看不过是主观臆想中的海市蜃楼而已,“现实主义之所以是最虚假的小说形式恰恰是因为它显得真实, 从而掩盖它是幻觉的事实”。[2]178
纳博科夫不止一次强调这样的观点:“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里的加底板,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于是我们多少生活在鬼一样的事物里,被它们包围着。”[3]12很显然,纳博科夫执意与肤浅的现实主义决裂,不想被“艺术模仿现实”的传统所羁绊,他孜孜不倦地力图去厘清艺术的本源问题,因为“艺术模仿现实”不仅曲解了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经常使小说堕落为政治、宗教和道德服务的丑恶工具。文学作品崇高的使命是洞察人类的生存命运,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焦虑、彷徨和无助。
故事中的儿子看似精神错乱、无药可救,就是因为他想法和行为根本无法为常人所理解。在他心目中,所有人工制造出的器物和产品都是邪恶的,同时人世间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无疑是庸俗堕落的感官享受,总之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人类产品在他精神世界里如同一堆腐朽的垃圾。“在排除了一系列有可能伤害他或是吓坏他的东西之后(任何小巧的机械一类的东西都属禁忌),他的父母挑选了一种精致且无害的小玩意儿:一篮子装在十个小罐子里的十种不同的果冻。”[4]236其实,小说中这个并没有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类”,他义无反顾地在反抗传统的价值观,否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所以普通人乐于享受的产品和各种文化娱乐只会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伤害他。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作为“局外人”只能选择逃遁,退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拥有安全感,才能维系个人的尊严。
在医学上,男主人公病症很复杂,既有“妄想狂”,也有“联想狂”, 以至于他的神经系统错乱曾经是一家科学月刊上的一篇论证详尽的论文的主题。正常情况下,“妄想狂”病人都是幻想周围的人在密谋算计,陷害或迫害自己,但是他超越了这种情况,他属于“妄想内容夸大型”。这种人自命不凡,通常认为自己智力超群,洞察力敏锐,他“想象在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其隐含的所指都是针对他的个性和存在的。他把真实的人都排除在这一阴谋之外——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要聪明很多”[4]236。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想象中的敌人是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无论他走到哪里,大自然都在尾随跟踪他,“明朗天空上的云彩通过缓慢的示意方式互相传递着与他有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消息。他内心深处的思想都是在夜幕降临时通过以手语示意黑暗的树木,按照手势符号加以讨论的。鹅卵石或污点或太阳光斑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模式,它象征着他应该截取的信息。一切都是密码,而他是一切的中心。这些间谍中,有些是公正的观察者,比如玻璃的表面以及平静的池水;其他的,比如橱窗里面的衣服,都是有成见的证人,内心里是以私刑处死他人的人;还有其他的(流动的水,暴风雨)也是歇斯底里几近疯狂,对他抱有扭曲的看法,还荒唐地曲解他的行为”[4]236。在这里,纳博科夫匠心独运地运用了大量象征手法,即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表征一些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通过定格在具体的形象,同时借助对应、联想和暗示等文学手段,彰显强烈的艺术效果,从而实现对世界真理性的认知。
现代主义文学书写的是人的“异化”,既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人与自然不和谐。现代主义不会像浪漫主义那样去赞美美好的大自然,更不会去憧憬向往“天人合一”的乌托邦生活;相反,作为独立存在的大自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成为人的意识的附属物。现代人虽然面对大自然仍然保留少量积极而正面的情愫,但更多的是负面而否定的情绪和意识,所以从波特莱尔到王尔德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大自然很多时候就是丑恶的象征物,令人感到痛苦,只有艺术才具备永恒的美和善,因此艺术家可以从丑恶的真实存在中,书写出唯美的抽象理念,印证了波德莱尔的一句名言 “给我粪土,我把它变为黄金”。
二、镜子的反照
作为现代主义大师,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中交织使用了多种现代主义手法,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 “没有一部小说没有文字游戏和镜子的反照,这是他幽默的主要表现。另外,每部小说也都有下棋或蝴蝶的意象。他最喜欢的小说形式是滑稽模仿,也喜欢玩弄换音词、双关语等文字游戏”[5]。在《征兆和象征》中,作为小说重要符号和代码的镜子以及其拥有的镜像功能有着双重所指:其一是小说中出现的实物镜子,再者则是指小说中由叙事结构呈现出来的镜子/镜像式框架。
根据第一个模式来看,从精神病院回来后,老夫妻俩一“走进他们的两居室单元房,他立刻就走向镜子。用两个大拇指拉开他的嘴角,做出一副可怕的像面具一样的怪脸,他取出那副叫他难受不堪的新的假牙托,而后切断牙托从他口里带出的长长的分泌物”[4]236。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类认知过程必然绕不过“镜像阶段”:镜前的客观存在的人或物与镜中的影像,称之为“镜像”。客观存在和影像两者看似相同,实则有着天壤之别。“镜像”本质上不是真实的自我,只是一个在环境和当事人内心世界情感共同作用下,再经过主观想象最终构建出来的虚幻的自我,充其量只能说一部分是真实自我,其他则是臆念中的执念。如果自我想蜕变为有真实意识的自我主体,就要通过其和他人的交往和互动来实现其身份的建构。《征兆和象征》里的老父亲在沦落为难民前曾是当地成功而富有的商人,但世事难料,从明斯克,到莱比锡,再到柏林,最后定居在美国,经过多年不停地迁徙,家产丧失殆尽,现在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兄弟艾萨克的救济,后者是一个有着近四十年身份的真正美国人。虽然是亲兄弟,他们很少能见到他,并且一直尊称他为“王子”,兄弟间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财富和地位面前,被扯得荡然无存,主人公一家窘迫的生存境况跃然纸上。
建立在叙述模式基础之上的镜像结构则更为隐秘和抽象,通常作品中的主人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缺失自我,随即开始寻找自我,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自我的彻底迷失。几千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从最初最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蒸汽机时代,直至目前现代社会的信息化时代,而不久可期的未来,我们将迎来崭新的智能时代。人类历史长河中作为个体的人无一例外地具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显而易见的是人类日益高度发展的文明使得自然属性日渐衰微,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属性完全压制了自然属性,屹立在舞台的中央,后者只能退缩到后台的阴暗处。社会属性统治下,一个人没有可能对个人身份和存在价值进行评价,自我的认知必须通过他者的认定来反映,也就是说,如果失去了外界的参照,自我意识将沦为空虚。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老母亲“那浅棕灰色的头发只胡乱地收拾了一下,身上穿的是便宜的黑色衣衫。与同龄的其他妇人不同(比如索尔太太,他们的紧邻,她的脸上总是涂成粉红色和淡紫色,她的帽子就是一串小溪边的花朵),对着春日吹毛求疵的光亮,她总是露着一副未经修饰的苍白的面容”[4]236。与此同时,在去往地铁车站长长的一段路中,她和丈夫互相无言以对,每当看见丈夫那双握住伞柄的苍老的手时,她都感觉到眼眶噙满了凄凉的泪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老夫妻在社会中完全被抛弃和边缘化,实际上等同于被他者的否定,而正因为他者的否定,主人公才感觉到失去自我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彻头彻尾地沦为社会边缘人。
回到家,痛定思痛之余,自我身份的缺失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处境和出路,开启自我救赎的模式。长期以来,儿子被关在精神病院,原先一家三口的温情生活被残忍地击碎。“她想着那一阵一阵无尽的痛苦,她和她丈夫不知为何必须承受;想着那以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伤害着她的儿子的隐身巨人;想着那包容在这个世界里无数的温情;想着这种温情的命运或是被碾碎了,或是被浪费了,或是被转变成了疯狂……”[4]236当他者作为镜像帮助个体洞察到自己的独特身份时,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紧接着走上寻找自我的道路。于是两人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第二天就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回家,亲自照顾,这样就找回来失去多年的亲情和生命的意义。
可是,在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和生活一旦固化后就很难改变了,因为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不堪,无论如何反抗和挣扎,美好的愿景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毫无实现的可能性。正当两人放下了压在心里多年的沉重思想包袱,憧憬着一家三口团圆之后温馨的生活,电话铃响了,暗示着梦想破灭。无效的反抗完全粉碎了被边缘化的人们所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把他们推到无望的深渊之中,使之陷入茫茫的自我迷失的泥沼中。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 “文本就是在不停的编织中,被织就,被加工出——主题由于全身在这种织物里,而自我消融, 正如蜘蛛在吐丝结网的过程中获得解脱一样。”[6]64
三、绝望中的苦笑
作为一篇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征兆和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借用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手段,如讽刺、戏仿以及无厘头来颠覆所谓叙事的“真实性”, 其结果就赋予了作品黑色幽默的特征,它在借用传统小说种种创作手法的同时, 又把传统小说作为一种腐朽的裹脚布加以讥讽。
《大英百科全书》对“黑色幽默”的解释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用一句话来概括,黑色幽默显然是一种用喜剧搞笑的方式来彰显大写的人在社会存在中所遭遇到的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文学方法。其中“黑色”代表死亡和腐朽,意味着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的本质,而“幽默”则是作家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艺术元素,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滑稽、丑恶、畸形、阴暗等负面成分无限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诞不经,目的是使得这种冰冷无情的现实世界在读者内心深处留下永不泯灭的印记。
《征兆与象征》在故事一开始就将生活中诸多偶然性集中在同一时间,当那对年迈的父母在儿子生日那天去探望儿子时,“那个星期五一切都错乱了。地铁火车在两个站台之间丧失了它的生命电流,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人们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脏恪尽职守的跳动以及报纸的唰啦唰啦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接下去必须乘坐的公共汽车又让他们等了几个世纪似的;当它终于到来时,里面已挤满了叽叽喳喳的中学生。他们走在通往疗养院的褐色小路上时,竟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在疗养院,他们还得等待;地铁火车停电,公共汽车严重迟到……”[4]236这段描述中,纳博科夫采用了拟人修辞手法,赋予地铁火车以人的生命属性,其生命电流的丧失无疑在暗指现代人的“精神瘫痪”;接着又极具讽刺之能事来挖苦车厢里乘客们在面对地铁延误时的无动于衷,映射出他们对命运的屈服;最后还加上令人窒息地漫长等待公共汽车,其夸张的修辞无疑是为了显示出在无序和疯狂的社会里,主体的人是多么无助,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集中突发的所有偶然性凸显出理性社会的荒谬以及其对个体的束缚,而深陷其中的个体无力冲出牢笼拥抱自我,所有环境和个人之间的敌意被无情地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因而显得滑稽可笑。
纳博科夫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解构和颠覆故事内容,以各种方式暗示读者故事的虚构性,让读者感觉所了解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大文本,是语言虚构的文本,充分体现出元小说的特点”[7]54。在作家天才的文学世界中,故事情节被刻意扭曲,使得封闭的小说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对照下,显得荒诞不经,而表面上痴人说梦般的情节反映的却是作家对于理性与秩序的反叛,他用非理性的光辉折射出窘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
“上一次他们的儿子企图自杀,他的方法是,用医生的话说,一个创造发明的杰作;如果不是一个嫉妒的病友以为他是在学着要飞——而阻止了他,他就成功了。其实他真正想做的只是要在他的世界里撕开一个洞好逃出去。”[4]236老两口的儿子在世俗的看法里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他拒绝随波逐流和安于现状;相反他感觉外部世界仿佛是一个巨大无形的网把他牢牢的罩住,使他无法自由的呼吸。一方面,他想要“撕开一个洞好逃出去”的这个细节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解读,不能简单地理解“儿子”只是精神病再次发作了;相反,这是小说最能揭示主题的地方之一,是现代主义作家最擅长的一类比喻和象征。纳博科夫认为“小说的特色不仅体现在叙述方式和表达形式上,尤其体现在对 ‘细节’具体而微的筹划和运用之中。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囵吞下。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8]105。现代主义小说从形式上就反对传统小说的“拟真性”,丝毫不在意生活细节的真实,更注重的是真实的“心理世界”。纳博科夫推崇唯美主义风格,坚决反对文艺创作蕴含任何政治或道德的目的,在他看来,崇高的文学创作必须是运用语言工具来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现实,只有艺术创造才能反映比现实世界更多的真实,也只有艺术才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和迷惑性,所以他的作品致力于用语言构成各种隐喻,所有的隐喻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令读者困惑不解的迷宫,成功的文本阅读就等同于一次有效的猜谜经历。
其次 , 作者刻意混淆了现实世界与小说文本世界之间的界线, 换言之,现实世界被文本化, 而小说同样不再是封闭的文本, 它被拓展为现实世界文本的比喻和象征。细细品味小说的细节不能看出,老两口的儿子不仅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甚至连放弃生命,转而去另外一个世界来逃离苦难的计划,也被一个不明事理的病友阻止了,理性世界崩溃后个人的自我救赎变得徒劳无益。面对这惨淡而荒谬的人生,人们只能祭出玩世不恭的笑声,用狂放不羁的姿态从畸形现实生活中突围出来,以维护现代人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后尚存的一点点尊严,于是刹那间,黑色幽默元素跃然纸上。黑色幽默不同于一般幽默的地方在于,它的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之中包含了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忧郁和残酷,因此,在它的苦涩的笑声中包含着泪水,甚至愤怒。纳博科夫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现实世界的荒谬以及文明社会对生命主体的压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来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个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把这种对抗有意无意地加以放大、变形,既强化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所遭遇到的荒诞不经和滑稽可笑,同时更令人感到沉重和灰暗,仿佛所有的出口和通道都被封堵住了。往深处去看, 困扰小伙子精神的“联想狂”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疾病,其实在哲学层面上所指涉的是个人主体和外界客体相互融合的特殊形态,但纳博科夫却认为这种主客体的统一并不能带来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相反演变成束缚并且囚禁人的“牢笼”, 基于此, 个人从根源上失去了获得自由的可能。
结语
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曾经说,“彼岸世界(other world)”一直是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相对于“此岸世界”,彼岸世界毋庸置疑指的是一种抽象而概念化的心灵世界,从而促成他在文学语言与小说文体上的另辟蹊径,尤其是对情节的精美构思与大胆的艺术想象。《征兆与象征》毋庸置疑是一篇寓言故事,这个寓言被赋予了双重属性,既属于现代人的,也是流亡者所特有的。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里,纳博科夫都拒绝空洞的道德说教,相反,他擅长通过荒诞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叙事结构来书写现代人恶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堪。在叙事中,作家通过实物的镜子和其象征意义使得故事人物和情节发展虚虚实实,亦真亦假,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魔幻的效果,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人物的精神生活中,从而印证了他的一句名言“伟大的作家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法师”,使得这部作品成为读者心目中美轮美奂的艺术大餐。此外,纳博科夫还通过文本不可靠的叙述、拙劣的游戏以及戏仿等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去展现人物流亡的人生,用荒诞而夸张的元素去暗示人生诸多不公和无奈。黑色幽默仿佛是一把手电筒,让读者探入到纳博科夫的个性世界,也照亮文学人物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