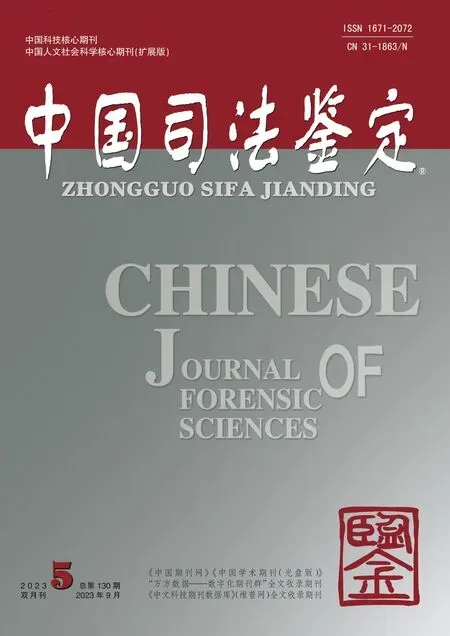从《洗冤集录》看宋慈尸体验定思想
段乐民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洗冤集录》是中国较早、较完整的法医学著作,作者宋慈(1186—1249 年),南宋人,是中国古代法医学的集大成者。 《洗冤集录》自淳祐七年(1247 年)“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1]1以来,就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刑狱案件中尸伤验定之圭臬。后世学者虽多有研究,但均未突破《洗冤集录》的内容范围和水平,至今仍被尊为法医学专业的经典之作。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洗冤集录》的研究多集中于宋慈法律思想、礼法合流思想、证据裁判观、验尸避秽方法,以及封建王朝司法制度等方面,亦有学者就《洗冤集录》的史料价值、宋慈与林几学术对比展开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然而,学界在尸体验定这一方面的成果甚少,更遑论宋慈所提尸体验定思想的向前溯源和向后发展。 基于此,本文结合出土文献、历代法医学著作和南宋理学名家刑法思想等资料,对宋慈所提的尸体验定思想进行概述,以期推进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
1 尸体验定思想在南宋以前的发展历程
“验定”意为检验审定,最早出现于南宋书画鉴定领域,“用内府书印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验定”[2]。 在法医学领域,对尸体的检验和死者死亡原因的确定被称为尸体验定。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便开始了尸体验定,这在中国古籍和出土文献中均有记载,为研究南宋以前的尸体验定思想提供了大量资料。
1.1 尸体验定
中国古代医书中很早就有对死亡征象的经典表述,如《黄帝内经·玉版论要篇》第十五中记载“脉短,气绝,死”[3]。 对于尸体的检验,古代司法官员很重视验定这一环节。 《礼记·月令》第六中记载,古代司法官员在孟秋之月应“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4],这是中国古代尸体验定的最早记载,而“瞻、察、视、审”作为四种诊断方法,则有效区分了外伤的不同严重程度,即“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5]。20 世纪70 年代,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的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亦有大量关于尸体验定的经典表述,弥补了中国古代尸体验定和量刑定罪的空白。 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擅杀子”中,“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和“今生子,子身全也,毋(无)怪物……可(何)论? 为杀子”[6]181的对比说明,经过理官验定,小儿生下便身有异物、肢体不全,杀之无罪,反之有罪。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乃是一例他杀死的经典案例,“死”为人奴妾“黥颜頯,畀主”[6]183的刑事责任提供量刑依据。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与人斗”中直接将“夬人唇”等同于皮肤肿伤的“疻痏”[6]185。 同时,秦律十分重视对活体、尸体的创伤验定。《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夺首” 记录了一次军事战斗中首级抢夺事件, 强调对活体创伤处进行验定,“伍甲缚诣男子丙,及斩首一,男子丁与偕”,期间丙“直以剑伐痍丁,夺此首”,将丙逮捕后“诊首,已诊丁,亦诊其痍状”[6]256-257。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里亦有一则尸体创伤的论述,“诊首□□发,其右角痏一所,袤五寸,深到骨,类剑迹;其头所不齐”[6]257-258。
此外,中国古代早期尸体验定也关注到了妇幼。 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出子”中对孕妇流产和胎儿形状的描述相当生动,其中有对孕妇斗殴致流产的描述“甲到室即病复(腹)痛,自宵子变出……皆言甲前旁有干血”, 以及流产胎儿的样貌“已前以布巾裹,如衃血状,大如手,不可智(知)子。即置盎水中榣(摇)之,衃血子也。 其头、身、臂、手指、股以下到足、足指类人,而不可智(知)目、耳、鼻、男女。 出水中有(又)衃血状”[6]274-275,如无丰富的验定知识,不可能对孕妇流产和死亡胎儿的法医学征象表述如此清晰。 这都是早期尸体验定经验在司法定罪和表伤检查中的运用。 上述一系列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尸表检验,一方面为量刑定罪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为确定死者死因奠定物证基础。
1.2 确定死因
尸体验定的最终目的在于确定死因,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刑事案件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宋慈所言,“切须子细验定,因何致死,唯此等检验最误人也”[1]14。 通过对尸表的创痕等征象的检验,确定死者根本死亡原因,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屡见不鲜。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癘(疠)”中,先秦时期的理官通过死者“三岁时病疕,麋(眉)突”和“艮本绝,鼻腔坏,肘膝□□□到□两足下奇(踦),溃一所”[6]263-264等征象,判定其死于癘,即麻风病。有关杀伤死、自缢、身首异处等死亡原因判定的相关爰书更是在云梦睡虎地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现。
汉唐以后,确定死者死亡原因不但要专条列罪,并有相应惩罚。 如《唐律·诈伪·诈病死伤不实》中明确规定,对于验定不实的司法人员,应“杖九十,徒一年”[7],这就为开展更精确的死亡原因分析和死亡原因确定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清朝。 与此同时,各界学者对死亡的系统研究更加深入,并尝试对死亡原因进行归纳分类。 比如:儒家学者主张“民有五死,圣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8];魏征在《群书治要》中列举“民有七伤,又有七死”说[9],劝诫唐太宗爱民;以王充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兵烧压溺、强弱寿夭[10]是人的主要死亡原因。 虽然各界学者论及不同死亡原因,但是都强调了暴力死是人类死亡原因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处理尸表创伤较为隐秘的案件时,这一时期的司法官员更多地借助于生物学、光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通过形成对比物证来断定疑难复杂案件。 如三国时期,吴国句章县令张举在断定一桩火灾案时,通过向火堆里投入生猪和死猪,对比猪口中是否有烟灰来断定火灾现场的尸体是否是谋杀后投入火中[11]1。 唐代润州刺史韩滉在处理一桩没有任何尸表创伤的人命案件时,发现死者“大蝇集其首”,乃“发髻验之”,最终确定死者乃是酒醉后被妇人和与其私通的邻人用钢钉钉入脑颅致死[12],这是利用苍蝇嗜血的生物属性来断案的典型案例。 在《折狱龟鉴·照伞见伤》中,我们也可得知,宋代的司法官员已经开始注重尸体的冲洗和防腐,面对“以糟胾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的尸体,审案官员通过“用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尸”[11]15,最终看到了和周遭不一样的伤痕,断定死者死于斗殴。 这类运用科学知识进行断案的记载不一而足,同时也说明我国古代的尸体验定思想和方法正在逐步趋于理性和科学。
综上所述,南宋之前的古代司法人员很早就注意到尸体验定,并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法医学知识,并在确定死亡原因方面成果颇丰,这为宋慈“四叨臬寄”[1]1,编著《洗冤集录》及形成他独有的尸体验定思想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2 理学视阈下的宋慈所提尸体验定思想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 年),理学经过长期斗争,最终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其集大成者朱熹被尊为“世间之巨儒”[13]292,朱熹的“慎狱”“恤刑”思想由此主导了南宋的司法制度。 宋慈师承西山先生真德秀,而真德秀又传承朱熹学说,因此宋慈的《洗冤集录》 和尸体验定思想很大程度上带有理学风格。 《洗冤集录》全书计五卷,共五十三目,录前有序,以记宋慈治狱心得与著书缘由,卷一包括验尸条令、检复总说和疑难杂说,卷二论述尸体初检、复检和洗罨尸体的具体步骤,卷三至卷五记载各种伤亡死因的验定方法,文后附避秽方和救死方。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指出,开展尸体验定,务必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验尸过程一定要科学,对待相似案发现场的尸体应该辩证分析,如发现活体应积极开展救治。宋慈所提的尸体验定思想具有理学视角下的独创性,贯穿了《洗冤集录》全文,成为古代法医学宝贵的经验财富。
2.1 依法开展尸体验定
有宋一代,社会各方面发生快速变化,要求统治者及时有效地调整和规范法律,因此自宋初就非常注重法律修订,发展至南宋已是“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14]。 这些法律中,有关法医验定的法令条目相当繁多,大多刊布于北宋神宗至南宋宁宗时期(1068—1224 年)。 南宋建立后,朝廷相继颁布相关法典,如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颁布《乾道敕令格式》,淳熙元年(1174 年)“五月壬寅,班郑兴裔所创《验定格目》”[15]234,以及淳熙十一年(1184 年)“癸未,重班《绍兴申明刑统》”[16]等,这些法典的条目涉及现场检验、免检事项、尸体初复检、回避制度、保辜制度等方面,内容详细而明确,这为宋慈开展尸体验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宋慈依法验尸的思想还来源于南宋理学“慎狱”“恤刑”的观点和长期担任基层司法人员的特殊经历。南宋时期(1127—1279 年),司法领域出现“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17]2712的轻刑现象,朱熹批评此类现象将导致“长奸惠恶”的不良后果[17]2789,疾呼“狱讼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恐有误也”[17]2711,强调审理狱事必须慎重,以严为本。当时基层官员大多徇私舞弊、不奉法律,断案“率然而行”, 结果必然是导致大量冤假错案产生,“死者虚被涝漉”[1]1,案件长期未能得到正确处理,对此,真德秀主张“苟非当坐刑名者,自不应收系”,号召基层官员“每每必须躬亲,庶免枉滥”[18]11。 宋慈从小接受朱熹理学教育,“慎狱”“恤刑”的观点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至淳祐七年(1247 年),宋慈相继担任赣州信丰县主簿、长汀县知县、福建路邵武军通判、南剑州通判、广东提点刑狱官、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湖南提点刑狱等职。 据清代沈家本记载,主簿是最基层的父母官之一,“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通判主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而提点刑狱官“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核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15]518-520。 以上三职均涉及司法和案件审判,宋慈长期沉浸其中,对基层办案的流弊了如指掌,形成了依法办案的职业思维。
在实际办案中,宋慈特别强调官员应亲自验定尸体,约束身边的行人、仵作等随行人员,并令基层人士画押作保。 宋慈如此行事,一方面是为了确保验尸过程的程式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办案官员的自我保护,“官吏获罪犹庶几,变动事情,枉致人命,事实重焉”[1]14。 在亲赴案发现场勘验尸体方面,宋慈多次指出,官员面对尸体不能“掩鼻而不屑”[1]1,一定要“躬亲诣尸首地头”[1]5,做到“诸尸应验”[1]1,否则“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处以“违制论”[1]1。对于仵作等随行人员, 宋慈采取严格约束的态度,“不得少离官员,恐有乞觅”[1]5,这是因为宋慈在常年基层办案中了解到仵作等人多是受教甚少、素质极差的“差厅子、虞候,或以亲随作公人、家人名目”[1]5,这些人“打路排保,打草探路,先驰看尸”,容易“骚扰乡众”[1]5。 加之“仵作之欺伪,胥吏之奸巧”[1]1蛊惑初涉刑案的年轻官员, 对现场尸体进行伤痕造伪,造成“发端之差,定验之误”[1]1。 此外,宋慈强调断案期间,要让“土着有家累田产、无过犯,节级教头、部押公人”[1]5等基层人士参与尸体验定,“以邻保为众证”[1]5,官员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术人、僧道,以防奸欺,及招词诉”[1]5。在案件审问结束后,“点数干系人及邻保,应是合于检状着字人齐足”[1]5。 看似繁琐的程序背后,是宋慈让地方人士对官员办案发挥权力监督作用,防止出现其他意外情况。
2.2 尸体检验重在科学
尸体检验是确定死者死亡原因的最重要环节,能否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科学性,关系至深。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突破理学“以心为主”的先验论,强调检验尸体的科学性,做到有效保护尸体、合理检验尸体的有机结合。
南宋时期(1127—1279 年),朱熹等理学家认为在格物的过程中,作为“万事之宗”[13]273的心的作用远大于环境等客观条件,“近复体察, 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13]264。 但宋慈在长期的基层办案中认识到,“格物”的基础是有效保护尸体这一“物”,这就必须做到人和环境、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非如此不能合理验尸。 宋慈指出,尸体四时变动不一,又兼以“人有肥瘦老少”和“南北气候不同”[1]22,因此验尸官员在接到请官验尸的牒后应尽快亲自赶赴案发现场护尸,防止尸体出现变化,在干检和清洗尸体结束后“衬簟尸首在物上,复以物盖。 候毕,周遭用灰印,记有若干枚,交与守尸弓手、耆正副、邻人看守”[1]15,期间“勒令看守,不得火化及散落”[1]16,确保尸体完整。 断案期间出现争论时,不能将尸体交给血属,“且掘一坑,就所簟物,舁尸安顿坑内,上以门扇盖,用土罨瘗作堆,周遭用灰印印记,防备后来官司再检覆。仍责看守状附案”[1]16。针对高度腐败但是尚可检验的尸体,“即先用水洗去浮蛆虫,子细依理检验”[1]60,除非“委实坏烂,不通措手”[1]16,方能判定其无凭验定。 在尸体高度白骨化或者完全白骨化的情况下,宋慈也指出,白骨应远离金属,在洗净后“用麻穿定形骸次第,以簟子盛定”[1]29,或者“先用纸数重包定,次用油单纸三四重裹了,用索子交眼扎,系作三四处。 封头印押讫。 用桶一只盛之,上以板盖,掘坑埋瘗,作堆标记,仍用灰印”[1]31,等待天气晴明时再检骨验伤。
尸体得到有效保护后,获取物证和尸表信息乃是必要之举。 朱熹认为,“毫厘之差,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故夫专于巧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13]273,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慈的证据裁判观,因此宋慈认为“人命告状切不可信”,对于现场物证的提取和尸体的科学检验“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1]45。 在提取现场物证方面,宋慈强调要做到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先打量尸首,身长若干,发长若干,年颜若干”[1]24,并“先剥脱在身衣服,或妇人首饰,自头上至鞋袜,逐一抄札,或者随身行李,亦命名件讫。 且以温水洗尸一遍,验”[1]23。 宋慈在常年的基层司法工作中,总结了杀伤、斗殴、缢勒、溺水等数种可能死亡原因[1]31,并依据自己创立的罨尸法、蒸骨法和煮骨法来获取尸表信息,确定最终死亡原因。其中,极为可贵的是宋慈能根据季节、时令、天气、尸体状况等实际条件的不同来变通处理,获取证据,如在春初、寒冬等气温较低的时节,尸体的外敷应用热醋、热糟,仲春、夏秋之季则醋、糟微热,以防烫伤尸体皮肉。 在验尸中如果已经出现尸僵,须得尸体软透,就要用烧红的高温深坑和平铺的湿炭火,用醋罨尸至软,后“以葱椒盐同白梅和糟研烂,拍作饼子,火内煨令热,先于尸上用纸搭了,次以糟饼罨之”[1]25,尸体痕迹就会浮现出来。
这些科学的验尸方法一方面是宋慈长期作为基层司法人员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体现了宋慈验尸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秉持从实际出发,一切依据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科学理性精神。
2.3 谨慎指出尸体伪证
中国古代司法人员很早在现场检验中就注意到了犯罪分子伪造证据这一恶劣行为,此类记载不绝于史,如宋代法学家郑克在《折狱龟鉴·证慝》中记载“甲强而乙弱,各有青赤伤痕”,北宋尚书李南公“自以指捏之”,即断定乙真而甲伪,原因在于李南公认识到因殴致伤,其痕坚硬,反之则软,并指出伪证来源,“盖南方有榉柳,以叶涂肌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棒伤,水洗不下”[11]2。这说明古代就有对活体伪证的判别。进入南宋时期,理学家论及人类生活之本质时,认为“人物在天地间,其生生不穷”的原因就在于“理”,“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13]259,但“死衔冤愤者”由于生前“或遭刑,或忽然而死”,导致“气犹聚而未散”“终是不甘心”[13]260,这从天理的角度要求官员审理狱事务要公正谨慎。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宋慈在《洗冤集录》中一分为二地指出了自杀死、他杀死等各种暴力死亡现场的正常尸证和伪造尸证的不同,这是宋慈“贵在审之无失”[1]42的辩证思维在验尸当中的体现。
《洗冤集录》中,宋慈对自杀死亡笔墨较多,其内容主要涉及缢死、溺死和毒死三方面,同时指出了真假尸体的不同征象。 缢死方面,宋慈首要看缢死高度和绳索松紧程度,因为自缢必须是在踏物基础上自系绳索,依靠重力作用下垂,尸首距离楣梁、枋桁等承载物一尺以上,且绳索紧直,方可致死。 如果出现“上面系绳头处,或高、或大,手不能攀,及不能上”[1]33“头紧抵上头”“所缢处只有一路无尘”“绳索宽慢”[1]34之状,必是移尸无疑。 其次,宋慈观察尸体法医学征象,正常自缢尸首的绳索痕迹呈紫色八字交于耳后发际,“眼合、唇开、手握、齿露”[1]35,且伴随舌抵口齿,胸前、谷门多涎、粪,如打杀假作自缢,则与上述征象相反,且“项上肉有指爪痕,身上别有致命伤损去处”[1]35。 溺死尸首有无造伪,主要观察尸首头髻松紧、肚腔响否、面色赤否、甲缝有泥否、口鼻中有水沫否,如果周身无痕、面色赤、十指甲黑黯色,以及口青肚胀,乃是被人倒提揾死。 在他杀死方面,宋慈着重强调凶手对尸体的毁坏以形成伪证。宋慈指出,死后受创的尸体“皮不卷向里”“无血行”[1]44,与生前遭创时“其痕肉阔,花文交出”[1]45“有血汁, 及所伤痕疮口皮肉血多花鲜色”[1]46形成鲜明对比,反之则无。 对于死后焚尸,宋慈认为,虽然其具备“手脚皆拳缩”和“头发焦黄”[1]47的正常征象,但是由于死后气脉已闭,故判断死后焚尸的主要依据是死者口中是否有烟灰。
2.4 积极拯救现场活体
两宋时期(960—1279 年),理学家推崇人在天地中的特殊地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260,但是真德秀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南宋刑狱中存在刑讯逼供和囚犯得不到医治而早死的情况[18]11。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慈提出在检查现场时,对于尚能救治的现场活体,一定要开展救治,“如少迟,无可救者”[1]51。 宋慈现场拯救活体的方剂来源于中医理论和民间偏方,大多载于《洗冤集录·救死方》,主要分为刺激法、针灸法、饮药法。
濒死期由于人的身体机能下降,需要开展呼吸道护理、体位护理以刺激身体呼吸、意识功能的恢复。 如服断肠草毒未久,宋慈建议对死者灌大粪汁,或者“急取抱卵不生鸡儿,细研,和麻油开口灌之,乃尽吐出恶物而苏”[1]51。 在自缢不久,心口尚温的条件下,两人通过运动尸身或“令二人以笔管吹其耳内”,宋慈认为“若依此救,无有不活者”[1]61。 对于魇死的人,宋慈采用“痛咬其足根,及足拇指畔,及唾其面”[1]62或“取病患头发二七茎,捻作绳,刺入鼻中”[1]62,如此可得救。 此外羊屎烧烟熏鼻中以救猝死、好酒灌鼻以救溺死等方法亦在书中有所体现。宋代针灸技术相当先进,通过针灸刺激腧穴以传导经络,调动气血的理念不仅常用于中医,而且也在宋慈的活体拯救方法当中。 如救溺水者,通过解衣、去脐垢、灸百壮穴,可以取得“治胀满”[19]的效果。 饮药救死多见于杀伤、胎动不安、猝死等相关现场的活体救治,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宋慈中医造诣的高深。
作为一名常年奔走在案发现场的司法人员,宋慈在经手无数案件后,形成了涉及尸体、活体检验救治、依法科学验尸等各个方面的独特尸体验定思想。 这些思想既是对古代法医学知识的总结,也是宋代至清代基层司法检验的理论渊薮和行动指南。此后,虽有元代王与编纂的《无冤录》、宋代赵逸斋编订的《平冤录》相继问世,并分别由清政府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乾隆七年(1742 年)编订、修订《律例馆校正洗冤录》[20],但是范围、内容、水平均未超越《洗冤集录》。 直至民国初期解剖学传入中国,林几教授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办法医学教室,创建中国现代法医学学科,中国法医学才实现了新的发展。 可以说,《洗冤集录》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法医学发展的基础,无出其右。
3 宋慈所提的尸体验定思想中的不科学之处
在南宋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宋慈所提的尸体验定大多具备科学性,但是我们也应从《洗冤集录》中看到,宋慈在尸体验定思想中亦有不少讹纰,主要表现为对法医学现象的宗教化解释、对日常观察的牵强附会,以及对死亡概念的模糊不清。
对法医学现象的宗教化解释最明显的当属“棺内产子”。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同样关注到了妇女,并有专章描述,但将“有孕妇人被杀,或因产子不下身死,尸经埋地窖,至检时,却有死孩儿”[1]19这一法医学现象却归咎于传统佛教思想中世界四大元素——地、水、火、风的作用,这与南宋理学吸收佛教思想密切相关。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中,朱熹借“人死地水先散而风火尚迟”则“能为祟”,来说明“今人多思虑役役,魂都与魄相离了”[13]258。 宋慈延续这一说法,将正常的尸体膨胀挤压归结为“盖尸埋顿地窖,因地水火风吹,死人尸首胀漏,骨节缝开,故逐出腹内胎孕孩子”[1]19。 宋慈勤于观察日常生活,这些经验同样被运用到尸体检验之中,出现了很多“想当然”的结果。 如宋慈认为,人骨有365 节,“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1]27,骨色分女黑男白,究其原因乃是“妇人生骨出血如河水,故骨黑”[1]27,辨别真自缢的一个标准是“开掘所缢脚下穴,三尺以来,究得火炭方是”[1]33,判断虎咬伤的方位雷同于“猫儿咬鼠”[1]57等,诸如此类的荒谬结论,不一而足。此外,宋代佛教盛行,“救生不救死”的观点在司法领域开始盛行,即注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21],以至于宋慈在《洗冤集录·救死方》中提出了“若缢从早至夜,虽冷亦可救”[1]60“水溺一宿者尚可救”[1]61等不科学观点,这主要源于南宋时期人们囿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了解死亡的三个主要阶段,对“死亡乃是个体心跳、呼吸的不可逆和停止,表现为全脑功能的永久性丧失”[22]的死亡概念不明,不明晰在致死一段时间后,尸僵、尸斑已高度发展,人是不可能救活的医学常识。
综上,宋慈在尸体验定中的错误思想主要来源于其所尊奉的理学,对日常经验的直接引用,以及当时医疗发展水平低下等因素。
4 结语
尸体验定关乎“死生出入之权舆”,对于基层官吏培养“洗冤泽物”[1]1的官德不可谓不重。 纵观《洗冤集录》中的尸体验定思想,不仅可以看到宋慈对验尸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应变能力的高指标,而且也突出了宋慈对验尸人员开展法医学检验,尤其是尸体验定中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的硬要求。 正如林几教授所言,尸体验定的本质是“据学理事实,公正平允,真实不虚”[23],宋慈的验尸过程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宋慈所提的尸体验定思想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和不科学之处,但是其毕竟在历史时期切切实实推动了数百年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