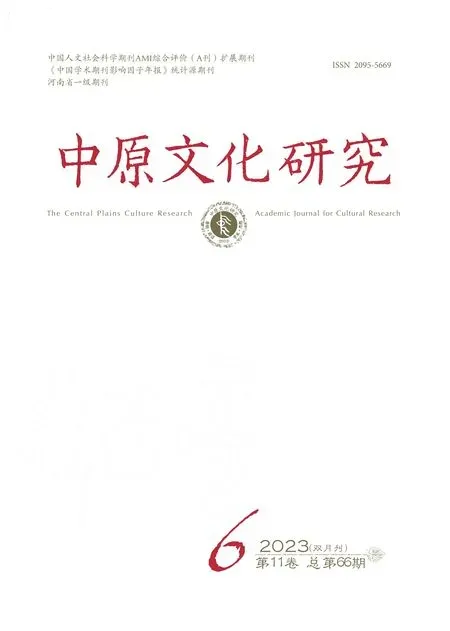试论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许兆昌
西周铜器册命铭文,除记述具体的职事授予和物品赏赐外,还有不少篇章会追述先王以及先臣的功业,追忆周初天下康宁的政治局面,由此构成西周时期在一种特殊的仪式场合下不断再现的历史叙事。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随着西周中期王朝廷礼制度的建立,在叙事风格、主题呈现及行文布局等方面都走向规范化,能够集中体现西周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主观建构。以下试从这三个角度对此主题做初步探讨,敬呈专家指正。
一、叙事风格:由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
西周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早期呈现出突出的写实主义风格,史事叙述具体,史料信息丰富。晚期则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记述历史的话语已经格式化,史料信息匮乏。目前所见西周册命铭文最早出现历史叙事内容的,是成王时器何尊(《铭图》①11819),其铭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易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该铭文字虽然不多,但除制器刻铭者记述了成王当时所行礼仪外,主体内容记录的是多种西周创建时期的重大史事,信息非常丰富。而铭文中这些重大史事的叙述者正是成王本人,此时距离文、武时代尚近,有的事迹可以推测或为成王所亲见亲闻。具体分析其中包括的重大史事信息有:第一,文王受命;第二,武王克商;第三,武王确定建都成周,作为王朝统治的中心;第四,作器者何之父考公氏为文王重臣,在西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若再味其文义,则何之父考公氏所做贡献应与文王受命这一具体史事有关。故其前文有“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后文又有“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之类的记述。而且全铭所载亦为器主何因助成王行祭天之礼而得赏赐。种种迹象表明,何父子二人所从事的,应正是与祭天受命等事务相关的早期宗教类工作。总之,通过何尊铭文中的历史叙事,确实能够发现西周王朝建国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资料,其史料价值十分突出。
同为西周早期铜器但较何尊略晚的大盂鼎(《铭图》02514),其铭文属西周长篇铭文,多达291 字。其主体内容记载的是康王对盂的册命和各种丰富的赏赐,因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无关,不备引,其中关涉叙述历史的内容也不少,其铭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酒无敢舔,有祡烝祀无敢。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女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女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命女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与何尊铭文一样,大盂鼎铭文中的历史记述也非常丰富。具体分析,可以归纳出的史事有:第一,文王受命;第二,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第三,周初群臣兢兢业业,共创王朝统治局面;第四,殷商晚期,外服之侯、甸,内服之百辟,酗酒成风,统治集团腐朽糜烂,等等。尤其是对殷末统治集团内部酗酒成风的记述,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上述两件早期铜器册命铭文对历史的记述,无论是相同部分还是相异部分,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写实特征。受限于铭文的篇幅及此类文献主要是为记述当时的册命内容和赏赐物品的特殊目的,其中所述史事,自然不可能完全展开,因而往往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但即使在这一条件下,铭文对所涉史事也还能做到描述具体,并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绝非仅是一般性的泛指泛称。如何尊铭文述武王选定洛邑建立成周,就直引了武王当时的“告天”之语,所谓“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从中国早期史学的发展看,“语”的记述具有使叙事完整的重大意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1]509,左丘明为防儒门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因而“具论其语”[1]510,遂成《左传》一书。《左传》在历史叙事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而何尊铭文在关涉历史叙事的不多文字中已经能够做到兼顾“事”与“语”,说明这种记述历史的成熟手法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出现,并不是春秋鲁史官左丘明的发明创造。又大盂鼎铭文述群臣功绩,描述也非常具体,一是“酒无敢舔”,即不敢耽于饮酒;二是“祡烝祀无敢”,对于字,学者尚有不同认识,根据上下文体会其大意,总之应是指在祭祀等宗教活动中有良好的表现。而对于殷商晚期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铭文也有具体的体现,即“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殷商晚期与西周初期群臣的史事叙述恰构成一个对比,前后两件史事拥有同一个叙事主题,即“饮酒”。也就是说,铭文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将殷、周统治集团的不同政治面貌鲜明地描述出来,同时又兼具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主观用意。即使由今日视之,这也是一种相当高水平的历史叙事技巧。叙事技巧的进步,自然对史料记述容量的扩大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早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沿着写实主义的路径发展,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意义。
西周中期,王朝廷礼制度逐渐形成。由于册命礼仪本身呈现出突出的程式化特征,册命铭文的记述也随之格式化,包括场景、仪式、册命话语等的记述都会使用大量的现成套辞。与此同时,在这种特殊场合下发生的历史叙事也很快形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这样的铭文材料很多,试列举如下:
西周中期有,訇簋(《铭图》05378):
王若曰:“訇,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命女适官司邑人……”
乖伯簋(《铭图》05385):
己未,王命仲致馈乖伯狐裘。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它邦,有芇于大命。”
西周晚期有,师訇簋(《铭图》05402):
王若曰:“师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亦则于女乃圣祖考克辅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绍厥辟,奠大命,盩和于政,肆皇帝亡斁,临保我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靖。”
王若曰:“师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唯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捍御王身,作爪牙。”
卌二年逨鼎甲(《铭图》02501):
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工散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尹氏授王赉书。王呼史淢册赉逨。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唯乃先圣祖考,夹绍先王,闻勤大命,奠周邦。”
卌三年逨鼎庚(《铭图》02509):
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周庙,即位。司马寿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史淢授王命书,王呼尹氏册命逨。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唯乃先圣祖考,夹绍先王,闻勤大命,奠周邦。”
毛公鼎(《铭图》02518):
不难发现,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三段式的叙事结构。这种三段式叙事结构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一是文、武受命,二是先臣用命,三是天下(四方)康宁。其中,前两句可以看作条件叙事,第三句则是结果叙事。具体地说,就是文、武受命与先臣用命这两组条件叙事共同促成了天下康宁这一结果叙事的出现。由于其因果具备,逻辑完整,已经很好地满足了册命仪式这一特殊政治场合之用,自不需其他史事再行加入其中。即使是迄今所见铭文篇幅最长的毛公鼎,记述的周王所发之语字数最多,丝毫不亚于早期的大盂鼎或何尊,但其实质性的史事内容却也并不超出这三句话的概括,完全可为这种三段式的叙事结构所涵盖。只不过该铭中历史叙事的描述性语句、词藻更为丰富而已。
此外,值得注意还有两件逨鼎,一述四十二年五月册命,一述四十三年六月册命,前后相隔一年有余,但所记述的出自周王的历史叙事居然完全一致,而且不只是内容一致,具体文字也完全相同。显然,这不会是实际发生的史事实录,而是后人拟定的结果。拟定者及拟定过程有多种可能性。一是周王在册命场合中所说的具体话语实有不同,但内容并无重大差异,因而记录者根据自己所熟知的行文格式予以笔录,并没有按照原话逐字逐句地记录。二是据两器所载册命场景,可知命书实际上是事先由史官写好,然后在册命场合由史官诵读的。其中四十二年命书当由尹氏书就,史淢当场诵读;而四十三年命书则是由史淢撰写,尹氏当场诵读。因此存在史官所作命书就是按照已经成形的行文格式予以撰写的可能。这一点与后世诏书中常见的“奉天承运”之类的套话相似。三是此段两次借周王之口出现的历史叙事,其实只是器主逨在铸器时据两次册命的记忆拟成的。它当然有当时周王或史官在册命场合的话语蓝本,但实际的记述和措辞都出自器主逨本人或由逨在铸器时聘请他人撰写。
以上三种可能性无论何种成立,都可以说明西周中晚期关于王朝初建时期的历史叙事已经形成了高度格式化的特征。与高度格式化的历史叙事相伴而生的,是真实历史进程中丰富的史事及具体历史细节的消失,所能提供的差异性的史料信息近乎为零。像何尊铭文那样所述及的武王定都洛邑之语,以及大盂鼎铭文对比记述的殷周两朝群臣在饮酒一事的差别,都不再出现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之中,而留下来的,就只是些“形式主义”的历史表述。与其说它是历史叙事,倒不如说是经由王朝官方认证过的统一了口径的“政治决议”。显然,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形式主义化的历史叙事,其目的只是为再现某种政治层面的命题判断,强化或灌输某种政治观念,其史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消解。不过,册命仪式自有其特定的政治语境,这一场域中历史叙事的风格由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其发展路径是符合其本来逻辑的,无可非议。
二、叙事主题:由散漫模糊走向精准聚焦
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三段式历史叙事是在继承早期叙事的主要内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册命仪式这种特定政治语境的制约或影响,中晚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内容的改造与建构,使其所欲表述的政治主题变得更加明确,能够聚焦册命仪式中的特殊政治诉求,并提供精准的政治服务。
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标准化格式虽然完成于中晚期,但主要叙事因素实际在西周早期册命铭文中就已存在,而且在当时也是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像文(武)王受命、先臣用命及君臣共创周初统治局面等,都在早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中作为主要内容重复出现过。这说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对册命铭文历史叙事所应表达的政治主题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甚至于一些铭文叙述历史的具体形式,也与中后期的格式化叙事具备一定的相关性。例如,大盂鼎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就已经很明显地呈现出后世格式化叙事文案的主要内容乃至于叙述的形式,如文、武受命,早期大盂鼎是“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晚期毛公鼎是“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如先臣用命,大盂鼎是“在于御事,酒无敢舔,有祡烝祀无敢”,毛公鼎是“唯先正辥厥辟,勋勤大命”。如四方康宁,大盂鼎是“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毛公鼎是“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以上三个方面,不仅内容与中后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基本一致,在行文形式及顺序上也非常接近。借用考古学中“类型学”的概念,这前后两类历史叙事显然具备着某种由早期直接发展到中晚期的直系“亲缘”关系。
但是,早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写实主义风格,决定了不同铭文的叙事内容和形式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达到中后期形式主义风格下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例如,另一件时代更早的何尊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就与大盂鼎铭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尽管何尊铭文不像大盂鼎铭文那样与后世格式化文案具有某种明显的“亲缘”关系,但具体分析何尊铭文的叙事内容,同样可以发现它也基本包含了后世格式化文案的基本要素。如“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句,就兼含了“文、武受命”和“先臣用命”两项内容。其后文又说“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只是又再度表述了“先臣用命”这一格式化叙事的重要内容。显然,中后期册命铭文中出现的“标准的”历史叙事,正是在吸收早期历史叙事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过,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除了文王受命、先臣用命及天下康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外,还会同时记述一些其他方面的史事,有的甚至是历史细节的描述,如武王亲自定下营建成周之国策,殷人酗酒、民不堪命以及周初群臣兢兢业业、勠力同心等。从后人研究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略显散漫而不工整的叙事当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史事信息,但册命礼仪这一重要政治场合下的历史叙事,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和诉求。从这个角度看,早期枝蔓丛生、散漫模糊的写实主义风格不免会削弱这一特定叙事主题的呈现力度。因此,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在由早期向中晚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要求其在主题呈现方面实现由散漫模糊、不够集中向精准聚焦、简明扼要转变。因为册命仪式毕竟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自不容周王做长篇大论甚至只是毫无目的地“八卦”些先王先臣的陈旧往事,发一点思古之幽情。廷礼仪式的规范化必然也会要求周王针对受命臣属的训嘱实现“规范化”,以使此种训嘱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展现其特殊的政治诉求。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规范化,就是在这一目的驱使下分别在君、臣两个方面展开的。它通过叙事内容的高度统一,使册命仪式中的历史叙事在主题呈现方面能够精准地满足这一特殊场合中的政治诉求。
从君的角度,“受命”成为先王叙事的唯一主题,且由文王受命转换为文、武共同受命。
首先是“受命”最终成为先王唯一的规范性史事,从上引多条材料可以看出,文王、武王是西周册命铭文中历史叙事的两位主角。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除文王、武王外,铭文叙事并不关涉其他诸王。这反映出文王、武王在西周王朝政治史叙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但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内容丰富多样,有文王受命、武王克商以及武王选定洛邑建立成周等。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仅剩下“受命”一件史事。武王克商及建都成周等都被排除在有关先王的规范性叙事之外。
其次是“受命”由早期的文王受命调整为中后期的文、武共同受命。早期册命铭文中,文王事迹是受命,武王事迹是克商,两者界线分明。如何尊铭文称“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大盂鼎铭文亦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等。不过,这种写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被中晚期册命铭文所继承。中期以后,像克商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册命仪式的叙事中被裁减掉,而王朝建立阶段的历史则被进一步压缩到仅剩“受命”一事。由于这个新兴王朝的实际建立者毕竟是武王而非文王,尤其历代周王还都是武王的嫡系子嗣,如果仅突出文王受命,则文王子嗣的范围显然要大得多,并不利于强调仅有现实中的周王才是天之所命。因此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就采用了一个变通折中的办法,即将文王受命调整为文、武共同受命,使武王有点委曲地隐身于“受命”这一重大史事之下。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无不以文、武受命并称。如中期的訇簋(《铭图》05378)云:“王若曰:‘訇,丕显文、武受命。’”又乖伯簋(《铭图》05385)云:“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晚期的册命铭文如两件逨鼎都记述:“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师克盖(《铭图》05682)也记述:“王若曰:‘师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师訇簋(《铭图》05402)同样记述:“王若曰:‘师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以上自中期以至于后期的铭文辞例,语辞近乎统一,似乎出自一人之手。稍有不同的是毛公鼎,该铭为迄今所见最长的西周铭文,其有关早期历史的叙述较之上述同期铭文更为丰富。因此相对而言,该铭除记述了文武受命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武同为受命之君这一点上,毛公鼎与中晚期其他册命铭文的历史表述并无差异。不过,毛公鼎在“膺受大命”句后,又增加所谓“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耿光”句共十三个字,似乎与同期其他册命铭文颇有不同。这里面或许有强调武王伐商及以武力经营天下这些史事的意味。但是细究起来,这一表述不仅不够具体,更主要的是它并没有写实性地将这些史事归诸武王名下,而仍是以“文武”并称,这就意味着将以武力经营天下这样的重大史事同等地列在文王和武王两人之下。总之是将文王和武王视为一体,无论是“受命”还是“克商”,已不分彼此。因此,尽管铭文在此节描述中多出了九个字,仅从文字数量看,多出两倍有余,但其语义并不出前述多例铭文中的“匍有四方”四字泛称之所囿,最多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另一种语辞更加丰富的表述而已。
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最终规范性地表述为“受命”一事,其目的自是为了确认王朝统治权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同时也为其册命臣属这一政治行为提供权威性,因为臣属通过周王册命所得到的地位和权力也可以说是经由周王而间接地来源于天授。不过,西周王朝的受命之君只是文王,武王并非受命之君,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为克商作准备,观兵于盟津时,就曾“为文王木主,载以车”,武王虽已继位,但仍“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1]120。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强调伐商为奉天命,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因为文王是得天命之君,因此奉文王以伐,通过语义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表示奉天命以伐。显然,若武王同样是受命之君,则自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西周时人对文、武史迹的不同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西周中期史墙盘铭文(《集成》②10175)述王朝前代先王事迹,于文王称“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这是明言文王受命。而于武王则称“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显然是在说其克商建立新王朝的事迹。总之,文王、武王功业的差别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般士众的常识。但是,在西周中后期册命铭文的套语中,虽习惯上于先王仍合称文武,但史实却简化为受天命这一事,武王通过军事征伐消灭商王朝一事竟被抹去。此种叙事变迁,其意义自然值得从多角度予以审视。
其一,这种叙述变迁凸显出在册命这种政治行为中,周王对于强调王权之神圣性及由神圣性所衍生的合法性的心理诉求更加突出。显然,这才是西周王朝最高统治者尤其是中晚期最高统治者所欲建构的政治观念体系的核心部分。
其二,对暴力克商这一史事有意无意地忽视,在西周王朝军事力量日益削弱的中晚期,也可以有效地抑制新崛起势力对于天下宗主权的觊觎。西周中晚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政治格局虽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但王朝的军事能力已无法与鼎盛的早期相比。昭王南征而不复,虽暂时压服楚人,但只可谓之惨胜。穆王周行天下,浪费了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虽征犬戎得胜,但从此“荒服者不至”[2],失去了对周边政治实体的控制。恭、懿、孝、夷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对王位发生激烈争夺,这必然会对王朝实力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夷王在诸侯的拥护下,才得以继位为王。虽然维护了恭王以下受到冲击的王位父子相传的体制,但是,自夷王以后,却不得不违背礼制,“下堂而见诸侯”[3],王权的削弱显而易见。而之后厉王的“专利”,则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以国人为主导力量的统治基础,致使国人不得不揭竿而起,居厉王于彘,王朝十余年无君。周、召共和,实际只是一个维持局面的看守政府。宣王虽号称中兴,但千亩一战中败于姜氏之戎,损失惨重,不得不料民于太原,试图通过加重盘剥来挽回王朝迅速衰落的颓势。
种种史实都表明,西周中晚期,王朝的军事实力显然已大不如从前。如果此时在册命铭文中还继续强调武王克商的超强军事实力,则无异于置现实中的周王统治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显然,中晚期册命套语的历史叙事部分对于文王受天命的强调及对武王克商之武力的忽视,正是此期的王朝统治者在观念领域试图为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所做的一种努力。
实际上,直到东周时期,强调天命仍是王朝统治集团维持政治地位的最后手段。据《左传》记载,鲁宣公三年,楚庄王观兵于周疆,向受周王之命前来犒劳的王孙满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的回答是“在德不在鼎”,并强调指出:“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可见,当东周王朝面临日益强大的其他军事力量的逼迫时,天命几乎成为其抑制这些新兴势力觊觎之心的唯一可用手段。然据对西周册命铭文中相关历史叙事的分析,可知这种借助观念领域的手段来强化或巩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的方式,早在西周中晚期就已悄然出现。
从臣的角度,“夹绍先王”成为先臣叙事的唯一主题。
早期册命铭文中关于先臣用命的叙事,一般都会有具体的实事记述。如何尊铭文述何之父考公氏,称其“有勋于天”,这是针对其“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之事绩的具体描述。大盂鼎铭文述周初群臣用命,特地强调他们“酒无敢舔”以及“有祡烝祀无敢”等表现,并与殷末群臣侯田百辟的“率肄于酒”相对比。这些具体的史事记述是早期写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必然结果。中晚期册命铭文中先臣用命叙事则不再有这种具体的史事记述,而是格式化为“克弼先王”(乖伯簋)、“辅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绍厥辟”(师訇簋)、“有勋于周邦,捍御王身,作爪牙”(师克盖)、“辥厥辟,勋勤大命”(毛公鼎)、“夹绍先王,闻勤大命”(逨鼎)等并无实际史事内容的表述。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早期铭文中的先臣用命,尽管也与先王有关,但其叙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像何之父考公氏“有勋于天”,群臣“酒无敢舔”等,其叙事都是以先臣本人为中心展开的,文王和武王在此种有关先臣的独立叙事中意义并不凸显。而中晚期铭文中的先臣用命,表面上看仍是以先臣为叙事主语,但叙事中心却已由先臣转换为先王。像“夹绍先王”“克弼先王”“辅右先王”“夹绍厥辟”等表述,都体现出先王、厥辟才是先臣用命叙事的真正中心。至于先臣们如何夹绍之,如何克弼之,如何辅佑之,这些具体的史事已不重要。说到底,是否“用命”才是关键,怎样“用命”则毋庸在此赘言。
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无论是统一为“受命”的文、武叙事,还是笼统的“夹绍先王”的先臣叙事,都显然更能为册命仪式中的特殊政治需求提供精准的叙事服务。册命仪式中,自册命者的角度,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至上无他的诉求。而在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说明,舍“天命”无其他。自受册命者的角度,强调其必须忠于权力、财富的授予者,也是最根本性的诉求。在君(册命者)臣(受册命者)关系中,臣子永远不能超越君主而成为政治关系的核心因素,他也不被容许拥有独立的政治身份,并进而获得历史叙事中的主体身份。显然,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统一为“受命”的文、武叙事,以及史实空心化、表述态度化、一言以蔽之的所谓“夹绍先王”的先臣叙事,正是这两种现实政治诉求投射到历史叙事领域而最终形成的“完美”文本,其用语简明扼要,其语用则精准到位。
三、叙事布局:由自然原生走向次序规范
空间是产生仪式的重要因素,也是“规范化”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叙事中的行文布局一直被当作时间因素来考虑,但如果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研究对象,叙事研究中的时间因素实际上可以转换为另一维度中的空间因素。或者说,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本身就具有空间排列的另一重属性。同样,具体的空间排列一旦进入到叙事领域,也必然会呈现出特定的先后关系,使之同时具有了叙事范畴中的时间属性。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行文布局,经由了一个由自然原生向次序规范转换的发展过程。这一“规范化”历程,就可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去观察。
从时间的角度看,早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写实主义风格,必然会将史事的实际发生顺序自然地转换为史事的叙述顺序,不会有太多为突出某种政治命题或政治观念而刻意为之的行文安排,因此其叙事布局会呈现出更多自然原生形态的特征,使得史事时序与叙事时序处于近乎重合的“零度”状态[5]14。例如,早期的何尊铭文在记述文王受命这一历史事件时,就没有将文王和器主何之父考公氏的政治地位代入叙事之中,即没有让两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君臣之别——影响事件的叙述。我们看到的是,其叙事是按照两位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责任,采用如实记述的方式来完成的:“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前文已述,据何尊全文,可以判断何及其父考都应是王朝负责祭天类早期宗教事务的官员。进一步看,何尊铭文所记史事,按顺序分别包括成王本人“爯武王豊,祼自天”,成王追记“文王受兹大命”、武王“廷告于天”,并称赞何之父考公氏“有勋于天”,之后又告诫器主何要“彻命,敬享”。何本人在铭文中又自称“宗小子”,因此,可以判断这应是一个世职祀天事务的家族,或即人所熟知的祝宗卜史类官员中的“宗”职。显然,成王对器主何称“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不是泛指,而应是对何之父考公氏确曾在文王受命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史事的如实追述。也就是说,公氏克弼文王——文王受兹大命是史事发生的自然顺序,同时也是此段历史叙事的叙述顺序。
这种“零度”状态的历史叙事对于册命仪式中特殊的政治诉求显然是有害的。像“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这样的叙事,将臣属之祖考辅弼文王的君臣关系置于文王受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中,自然具有暗示臣属之祖考在文王受命事件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语义,由此会使文王受命这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历史叙事失去排他性或垄断性。这显然不利于巩固和强化周王的现实统治权力。
从空间的角度看,早期写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往往会使历史事件的叙述缺乏统一的安排,从而导致叙事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某种“零乱”的特征,这是其自然原生形态特征的另一种表现。例如,在字数不多的何尊铭文中,何之父考公氏事迹就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成王诰语之首,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另一次出现在成王诰语之末,称“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这两次诰语前后语义重出,显然是对当时成王诰语的如实记录,并没有什么主观布局的意识。这与晚期的两件时隔一年有余的逨鼎铭文叙事布局相比,一者零乱,一者工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件早期铜器大盂鼎其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同样有写实主义风格留下来的缺乏布局意识的痕迹。该铭在记述周初群臣用命之表现时,运用插叙的手法将殷末群臣的表现拿来作对比。从描述群臣用命这一单个主题看,这当然是一种高明的叙事技巧。但如果将这一插叙内容放在该铭整篇历史叙事中来看,其叙事的突兀性又是明显的。它既破坏了西周建国阶段君臣叙事的完整性,使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被撕裂,同时对册命仪式中特定政治主题的表达也不能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
形式主义风格下的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其布局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从时间上看,“先王—先臣”这一叙事顺序上的主次关系成为统一的布局模式,为后来的叙事者所严格遵守。通过这一布局模式,“受命”一事很自然地成为先王所独享的叙事内容,先臣很难再介入(尽管他们可能像何之父考公氏那样实际上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曾发挥过具体的重要作用);先臣用命的史事也随之被确定或只能确定为“夹绍先王”,即只能以先王为中心,而先臣不再在整个叙事中拥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由此,先王与先臣两者在叙事时间上顺序清楚,界限分明,杜绝了越界的可能。从叙事布局的角度看,史事发生的实际顺序已不再是叙事顺序的决定因素。叙述者充分利用了他的“叙事时间自主的能力”[5]52,创造了一个不能(再)与史事时序相吻合的叙事时序。显然,这种次序严谨的规范化布局能够更好地满足册命仪式中的特定叙事需求。它也说明,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在形成特定政治话语方面的能力是写实主义的叙事所无法比拟的。
从空间上看,册命铭文历史叙事中的三段式结构,排除了一切有害的甚或只是无效的史事记述,最终完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凸显册命铭文特殊叙事主题的工整布局。先王受命、先臣用命以及天下康宁是构成一篇完整的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三大基本要素,但此叙事要素的完整性并不是西周中晚期才得以实现的。无论是西周早期还是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都能完整地挖掘出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以前文曾指出,西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晚期,对册命仪式中历史叙事的特定政治诉求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大盂鼎铭文自无需赘言,即使是布局相对混乱的何尊铭文,这三大要素也能够通过语义的分析而完整地呈现。像“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句,就包涵了先王受命与先臣用命两大叙事要素。“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句,是对先臣用命这一叙事要素的重复再现。而“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句,蕴藏的正是天下康宁这一叙事要素。只不过与其他册命铭文中的同项叙事句相比,何尊铭文采用的表述形式(直接引用武王告天之语)及其字面所呈现的意义都太过特殊而具体,因而很容易使人忽视其所欲表达的本意。前文已述,大盂鼎铭文在布局上已经非常接近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但它还存在着枝蔓过多的问题。其叙事要素虽然齐备,三段式结构的布局也已经显现,但整体上看尚未臻于工整。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则完全摆脱了史事细节问题的困扰,其三段式结构所形成的空间布局干净整洁,在册命仪式政治主题凸显方面做到了既完整又简洁。
四、历史叙事中的思想建构
除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会提供较为丰富的不同史事信息外,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大多为习用的套辞,内容重复,没有新意,史料价值不高,因而一直以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些不断被重复的故事和套辞,却正是叙事文本分析的重要话语对象。热奈特曾断言:“‘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5]73这一判断虽然是基于文学叙事的研究语境形成的,但对历史叙事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无论是文学性的虚构还是历史学的“如实”直书,任何文本的背后都不能不包含作者的主观写作意图及由此而推动的语料(或史料)选择与叙事表述。即使是个体的无意识或下意识写作,隐藏的也是集体性的无意识或下意识,具有反映一个时代主流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显然,册命铭文中不断重复的历史叙事,折射出来的正是西周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观念建构及价值建构的根本取向和深层逻辑。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准确地讲,这是指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具有当代属性。作为本体的历史已经隐身于时间隧道之中,人类并无打破这种时间性“隔离”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后人叙述出来的历史,天然具有服务叙述者现实需求的责任和义务。不过,这种现实服务,却不能等同于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着意强调的“编造”或者说“虚构”,它只是通过选择性的史事叙述来为某种特定的目的提供服务。理论上讲,没有人能够叙述全部的历史,因此,所有的叙述都是选择性叙述。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于叙述者现实目的和需求的选择性叙述,自有其学术层面的合理性。
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发生在王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合——册命礼仪之中,当然要服务于这一政治生活的特殊主题。册命是册命者对受册命者权力、地位以及财富的授予行为,因而自然构成册命铭文的主导叙事线索。同时,为了保证册命者能够在这样的政治行为中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它同时会有确定、约束受册命者的行为以及申明其与册命者之间关系的诉求,由此形成了几乎所有西周册命铭文必备的另一条隐性叙事线索。它既可以是册命者对受册命者施以直接的政治教诲和训令,也可以是通过叙述历史的方式来达到灌输某些重要的政治观念,以及维系某种现实的政治关系的目的。大盂鼎铭文中周王所云“余唯命女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毛公鼎铭文中周王所云“女毋敢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善效乃友正,毋敢于酒,女毋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易”(《铭图》02518)等,就都属前者,而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则属后者。
为了确定、约束受册命者的行为,并申明其与册命者之间的君臣等级关系,首先必须确立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现实政治诉求的总前提。传统时代,在政治学理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历史叙事是确立最高权力合法性的主要形式。至于其叙事内容的安排,自然还要求之于早期宗教中的神权。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通过记述国王与巫师两位一体的关系,对此有充分的讨论③。西周册命铭文中,文、武受命的先王叙事被置于章首,就是这一政治诉求的具体呈现。其次,针对受册命者的约束及其与册命者之间关系的强调,是此条隐性叙事线索的主体内容,也是其最终目的。现实从来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本身是历史的自然延续。现实世界的诸种原因,也都深藏于逝去的过往之中。因此,“夹绍先王”的先臣叙事紧接在先王受命叙事之后,被置于章次,正是欲借受册命者祖先的功业及其与册命者祖先即先王的固有君臣关系,来维系和强化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并激励受册命者承担政治责任。最后,历史理性的“工具性”本质,决定了历史经验、历史模式的现实重现,必须提供一个成功甚至完美的历史结局。由此,天下(四方)康宁的结果记述,自然成为完成这一历史叙事的终章必选。
不难看到,前文曾归纳过的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三段式结构,所构成的正是服务于册命仪式中特定政治目的的核心叙事。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风格、主题、布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发展,诸如史事的精简、历史细节的省略、事件主角的转换等,最终凸显了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最高统治者也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无意识的话语重复,不断地强化他们有关权力的合法性、君臣等级秩序等统治思想的建构。
注释
①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文中简称《铭图》。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7 年版。文中简称《集成》。③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79-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