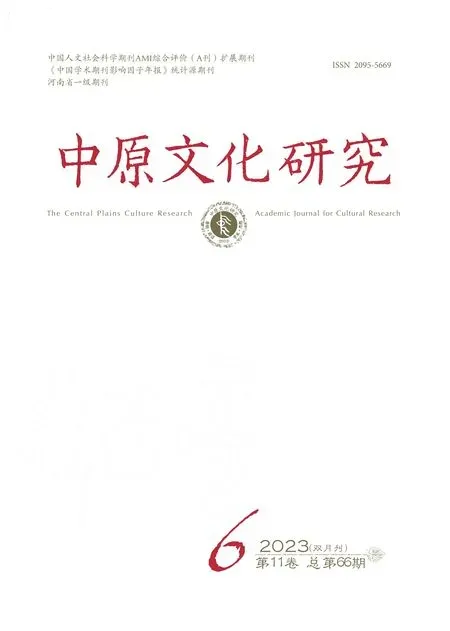论孔子与其后学的精神修炼*
匡 钊
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①的谱系当中,孔子后学普遍坚持一种“贵心”的态度。《性自命出》的作者明确主张在各种达成德性的修身技术中“心术”最为重要②,他们这种态度可谓是“承前启后”的。孔子绝少直接言及“心”,孟子的理论兴趣则主要集中在与“心术”有关的话题上。儒家哲学的传统常被称为“心性之学”,这种说法虽然不足以涵盖早期儒家思想状况的全部内容,但至少说明,与心及其修养有关的话题,肯定在“为己之学”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系列。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弟子以促使其获得应有的德性之时,曾明确提出由经典学习与礼乐实践两条进路来推进修身之道的教学方法。此外在不同场合,孔子还提及上述两个类型之外的多种修身技术,无一例外均与人的心灵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从修身活动的最终效果来说,对于一个有德性的品质高尚者而言,是否已经真正获得某种超乎世俗享受之上的精神快乐,也是识别其人格境界的最基本标志。这种标志便是宋儒所强调的“孔颜乐处”,无论颜回箪食壶浆不改其乐,还是孔子本人“乐以忘忧”,均与一定的内心状态有关,这便是仁者与智者“不忧不惧”的精神气质。孔子及其后学在对人自身加以反思时,不断转向“内在”,并在这个方向上逐步显现出一条直接关乎精神修炼的修身进路,而本文的目标便在于对其在孟、荀之前的发展加以系统性展示。
一、“爱人”与“自爱”
孔子对于德性的追求,以其反复强调的“仁”为代表,此“仁”如其在传世文献里的字形“相人偶”和郭店简书里的写法“身心之仁”所暗示的那样,同时包含着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自己两种关系的反思。前一层意思,在答樊迟之问时,曾得到孔子的明确解说,所谓“仁者”,即是“爱人”(《论语·颜渊》);后一层意思,则如《荀子·子道》中引颜渊之语,所谓“仁者自爱”,这正好为我们披露了“爱”同时还涵盖着如郭店简书中“仁”字的写法所揭示出的那种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自爱”与“爱人”结合起来,方能覆盖孔子所谓“仁”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仅将“爱”揭示为一种情绪或情感,无论这种情绪是关乎自己还是关乎他人,都是不充分的。如果说对于他人的温情还较好理解,那么对于自己的温情,则很容易就倒向某种自私、自恋或者顾影自怜。因此孔子口中的“爱”必定包含更为深刻的内容,而当其表现为情绪之时,这种内容的意义便在于“爱”乃是基本生存样式意义上的“关心”,大体相当于古希腊所谓“关心”(epimeleia),或者海德格尔所谓“操心”(sorgen)。孔子所谓“爱”,归根结底能被理解为一种情感或者情绪,是因为其首先可被视为某种海德格尔所谓的“现身情态”(befindeichkeit),后者乃是“‘此’之在活动于其中的生存论结构之一”[1]166。或许古今中西不同哲人用不同术语表述了对于同样一种生存状态的领会。
“关心自己”的话题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意义,乃是福柯从某种具有伦理学意味的视角出发思考古希腊哲学时的轴心:“福柯将伦理学设想为关心自己(the care of the self)与其自身间关系的道德的组成部分。”③从古希腊到福柯与海德格尔,我们几乎可以观察到一个贯穿全部西方哲学的围绕“关心”所展开的语义线索,而此线索同样曾经出现在孔子对于“仁”所包含的人与自己关系的维度中。“关心自己”意义上的“自爱”,在荀子看来,如其对“仁者自爱”的强调所显示的那样,显然与“使人爱己”和“爱人”相比具有更为高级的哲学意义,他似乎是将“仁”的最终的、最为深刻的价值定位于这种“自爱”之上。有意思的是,在先秦哲学中老子同样也提到过“自爱”的观念,并赋予其高度正面的意义:“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老子》第七十二章)这或许表明,尝试通过关心自己而对于自身存在状态有所领会乃是先秦最伟大哲人的通见。但这是否意味着关心自己相对于关心他人,或者说“自爱”相对于“爱人”具有某种优先性呢?从荀子的观点来看,围绕“关心”所展开的叙事似乎是从关心自己、从人与自己的关系维度中拓展到关心他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上面去的,但这真的能够反映儒家的真实立场吗?孔子本人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曾有过明确的态度,他告诉子贡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是将对他人的关心置于对自己的关心之前。
对于我们伦理生活中他人必不可少的地位,中西哲学从来都被认为是有清晰觉悟的,“很难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说明中推衍出向来我属性的中心地位或以一个人自己的生存为基调,因为完善的伦理美德,即普遍的正义,并不是仅为自己的,而且也是为了他人的”④。出于对上述他人地位的觉察,有研究者在论及儒家思想的时候也认为:“我相信古典儒家信仰的独特之处在于,精神的自身修养需要他人;这完全不是一种孤立的修炼。”⑤对于他人地位的看法似乎更多属于经验的范畴,而并不属于对我们存在状况的理论说明。人的存在归根结底被海德格尔揭示为一种“共在”——总已经有自己之外的他人先行地在世。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回溯到黑格尔,早在他对“意识”加以判断的时候便已经主张,只有在和另一个对象的对立关系中,意识以否定对方的方式才能识别自身:“自我意识在这里被表明为一种运动。”[2]132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2]137自己对于自己的识别,是以自己对于他人的识别为前提的:“自我意识最初是单纯的自为存在,通过排斥一切对方于自身之外而自己与自己相等同;它的本质和绝对的对象对它说来是自我。”[2]141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他人作为被自己排斥的“对方”,“在它看来是非本质的、带有否定的性格作为标志的对象。但是对方也是一个自我意识;这里出现了一个个人与一个个人相对立的局面”[2]141。后一种局面大约可被看作对于“共在”的一种早期描述:“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2]138黑格尔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自己和他人、“我”和“我们”之间的对称性,从这种对称性中再前进一步,一旦放弃对于“自我意识”之为精神实体的假设,这里他所主张的对称性,便被一种共在的优先性所取代了——“我们”的生存先于“我”的生存,虽然这绝非一个经验事实。从此在的存在之为一种共在而言,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必然是相互伴随的。从时间上讲,关心自己先于关心他人;但从逻辑上讲,上述先后顺序则是颠倒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出现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之前,“我”和世界、他人、事物打交道要先于“我”和自己打交道。孔子在将他人的地位置于自己之前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对上述人的根本生存状况的某种极为深刻的洞察,而此种洞察,大约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那种“无私”的哲学意义。至于荀子在上文中对于“自爱”的强调,则可能是因为观察到了上述两种“打交道”在经验和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基于这种对于“爱”或者“关心”的理解,抛开给予他人恩惠的现实行为层面,孔子进一步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而后者与人自身的人格塑造关系重大,并属于“心术”或者精神修炼范畴。
二、“省”与“忠”
在精神修炼的意义上以修身为目标关心自己的特定方式,《论语》中所言及的最为重要的一种便是“省”。孔子与其弟子所谈论的“内省”或“自省”,完全不同于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对于世界或人自身的“反思”,这种内心活动所要解决的并不是任何一种“是什么”的知识问题,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些品质,或者说达到一定伦理上的效果。关心自己意义上的“内省”或“自省”,具有专门的塑造人格的功夫论意义。
《论语》中言及“省”的地方,计有四处:
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二、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其中无论单独的“省”字,还是“内省”“自省”甚至“内自省”的用法,意思都是一样的,与现代汉语中“反思”或“反省”的意思一致。这种“反思”的指向,从上引材料四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司马牛所谓,乃是“君子”的意义,或者说君子所应有的人格境界或精神状态,孔子对之以“不忧不惧”,但司马牛未能立即看出孔子所言及的情绪或心态的深刻之处,或者对于这种心态的达成仍有疑问。对于他的不解追问,孔子再对以“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最终提点出“内省”二字,告诉自己的学生,人之所以能达到“不忧不惧”的心态,是因为经由一定的精神修炼活动而获得提升的缘故。“忧”与“惧”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日常情绪,其反面的状态,早已被孔子视为有德者的标志性心态,所谓“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仁”与“勇”当然都是“君子”的理想德性,以此来考虑孔子所言,或恰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晁氏之言:“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3]135总体而言,此段对话中司马牛问“君子”之所谓,孔子不但告诉他君子乃是有仁勇之德性者,更点出了从精神修炼的角度获得这些德性的方式。这种意义上的“内省”或“反思”的后果,冯友兰统而言之:“由这种反思而了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总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仁’。”[4]92这里的“仁”字可被视为诸德性之统称,而这些德性都是需要我们通过修身之努力去获得的——能够通达德性的反省活动因此正是精神修炼的方式之一。类似于此,史华兹也曾将“反省”与“仁”或者“个人的内在道德生活”联系起来,并指出“仁”所指称的这种内心生活中,“包含有自我反省与自我反思的能力”[5]。这无不说明,早先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内省”这种内心功夫对于达成道德生活,获得理想品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此立场反观上述其他几条材料,其意义所在也就很清楚了。材料二中孔子表达了对于“省”这种修身功夫的重视,这从他以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举例可见一斑。孔子说颜回绝非鲁钝之人,善于“省其私”而达到提升自己的效果。在孔子看来,颜回拥有超乎常人的反省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获取德性的方向上具有极为可观的效果。颜回是“好学”的代表,而他所好之学,不外乎以“成德”为目标的“为己之学”。材料三中孔子推崇“内自省”,则是更为具体地指示我们寻找自己与道德榜样之间的差距,正如“省”是精神修炼领域内的一部分内容一样,这种内心功夫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除了孔子所言及的角度之外,材料一中曾子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便向我们提供了“省”另外的三个具体入手角度:是否忠人之事、是否交友以信、是否研习经典。《论语·公冶长》曾记录了孔子本人言及“忠信”的方式,这揭示了孔子对于特定的内心体验之于修身的关注,与此处曾子将其列为“省”的精神修炼角度之一相互契合。曾子提及的是否研习经典的问题,虽被孔子明确列为独立的修身进路,但经典学习不可能离开心智活动的参与,将经由经典学习所获得的思维训练列为精神修炼之一种并非无的放矢,而这方面的内容将在后来得到荀子的特殊强调。实际上无论忠信,还是与经典学习有关的思维训练,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溢出了单纯的“省”的范畴,曾子举这些例子,用意也不是以“省”来对所有这些活动加以统摄。曾子提及的三个“省”的角度,与孔子所谓“见不贤而内自省”之间真正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从反面出发寻找不足的内心活动,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严格审视,这种审视可能涉及多个角度,但其之所以能作为精神修炼方式之一,则完全在于这种审视活动自身的意义。这种人对自己的严格审视,曾被认为是儒家的主流态度,如朱熹引谢氏之言:“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3]48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须等到当代才充分显示,但“省”作为修身方式的重大价值早已为学者所共知。
这种精神修炼意义上的“省”,是将自己置于检视、审查的中心,而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这种思路在古典世界的哲学实践中并非为孔子和儒家所独有。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检讨自己”,或者说对于自身加以严格的审视省察,在古希腊早有渊源,最初可回溯至毕达哥拉斯的教义,并在罗马斯多葛主义者,如塞涅卡等人中间十分流行⑥。当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出于更为明确的改变自己、净化自己或者拯救自己的目的再次将自身置于认识和行动的中心时,他们为了这些目标,“迫使自己自省被认为很重要”⑦。完全可以说,在中西哲人眼中,针对自己的审视省察均具有塑造主体的作用,而这种精神修炼无论对于早期儒家还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来说都并不陌生。
如果说“省”的问题主要是在关心自己的维度上展开,那么“忠信”或同样被认为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忠恕”,则明显与关心他人的维度有关。前引材料一中曾子提及的“忠信”,均是在与他人打交道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相比之下,“忠恕”的问题则更为复杂。《论语·里仁》记载孔子之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对此的解释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种说法,是将此话题明确认定为孔子所揭示出的成人之道的轴心,而“忠恕”之所以能够占据这样的地位,能够一贯夫子之道,首先或如朱熹“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3]72所暗示的那样,乃是由于这个观念结构是对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两个关系维度的同时呈现:“‘推己及人’,就是孔丘所说的‘忠恕之道’。”[4]83“忠”所表征的便是某种自己面对自己的态度,而“恕”则意味着将这种态度向他人扩展——虽然其仅关乎时间上的顺序而无涉于逻辑上的先后。
如果说“忠恕”的观念结构同时表明了儒家核心观念“仁”所包含的两个相互纠结的方面——自爱与爱人或者说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而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忠恕之间存在某种先后次序和推广关系,那么践行者首先是从专注于自己内心状态的“忠”开始的,而由这种自己对待自己的负责任的态度开始,以这种情绪体察他人,便是“恕”。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忠恕”之道可以被较为方便地理解为由内在品质生发出外在行为的过程,虽然并不排除“忠”的观念本身就包含行为层面的内容。仅从外在行为的角度,可将忠视作“对上者或与自己同等的人尽责”,而“恕表明对地位相等或地位更低的人的恩惠”[6]80。在儒家传统中,对于外在行为的考察,必定会归结为对于内在品质的把握,无论“德”的内在化还是孔子对于礼乐制度之内在精神性的追求,都遵循上述思路,而对“忠恕”行为的反思,也将同样最终指向内在于“心”的品质。如“忠恕”二字的字形本身所表明的那样,这两个观念都与人心密切相关——朱熹引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3]72,而这种相关性并不仅仅在于其关乎人内心的情绪活动,而更在于其已经被充分地人格品质化了。有论者指出,忠乃是“‘内在’(中)的自我完善”[6]82,这种基于心灵的“自我完善”无疑是某种理想的人格品质。相比之下,在“忠恕”之道的整个观念结构中,作为“忠”之推广的“恕”,则可以被仅仅用以暗示某种道德实践中的基于“自我完善”之上的普遍规则——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的这种对于“恕”的解说被研究者称为中国的道德金律,而后者被认为是比其他任何原则和规律更基本的东西:“它是社会的真正的基础,没有它,道德就根本不能发展。”[6]92这种评价与曾子的言说一样,均足以表明“忠恕”观念结构在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恕”作为某种规则的有效性基于“忠”,于是在此一贯之道中,对于后者的获得便是至关重要的。“忠”在通常的意义上被儒家视为某一特定的德性,本应出现在一系列修身活动的末尾处,同时,一般来说被孔子作为诸德性之代表的乃是“仁”,从这些角度来看,“忠”似乎难以被作为一贯夫子之道的轴心——而在我们看来,曾子之所以会对“忠”给予如此的高度评价,并不能仅仅从德性的角度来考虑,同时需要从获得这种德性的方式角度来对其加以考虑。
德性与获得德性的方式,一般来说可以被视为不同的内容,但这种区别在运用于“忠”之观念的时候,似乎需要进一步的分辨。对于孔子之所谓道的内容,抛开天道的内容之外,我们认为其真正的发明所在乃是最终向“成人之道”或者说“人道”收束,指的是以改变人自身为目标的一定的规范、方式与操作程序,而非某种形而上的实体,在这种意义上,能够贯通此道的,一定也应是同类型的修身方式。这促使我们认为,孔子及曾子眼中的“忠”,一定也具有修身技术的意义,而从其与人内心活动的关联来看,它必定是一种精神修炼。那么应如何考虑作为精神修炼方式的“忠”呢?我们已经发现,“忠”与“省”和“身心之仁”一样,都明显暗示出包含着关注自己内心的意思,而这种关注,恰能与前文所讨论过的“省”形成对照。精神修炼技术意义上的“省”,偏重于负面的、逆向的、批判性的对自身的检视,那么同样意义上的“忠”,则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对自身所表现出的某些优秀倾向的坚持。
当然如果更进一步深化上述话题,无论是“省”的否定还是“忠”之坚持,其所依赖的标准如何肯定会成为一个不得不加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孔子这里尚未产生,甚至其在孔孟之间的儒者当中,也并未真正成为关注的焦点。狭义上心性修养的标准与广义上的德性的标准问题,要到孟子与荀子的思考中才变得无可回避。对于我们追寻早期儒家心术的谱系的目标来说,孔子在转向内在的过程中,在精神修炼的进路上,已经开始从正反两方面同时提点出的“心术”的初期形态,而从这些心术的雏形开始,早期儒家将在随后的思考中发展出更为丰富的精神修炼技术。
三、“诚”与“独”
出现在传世文献《大学》《中庸》里的另外一些心性修养功夫,早已为历来的儒家学者和研究者所熟知。《大学》开篇讲修身次第之“格、致、诚、正”,并明言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随后围绕此关键点明前后关联的心术范围内的修养次第乃是“致知、诚意、正心”。暂不论“格物”,“致、诚、正”所言,均为精神修炼功夫无疑,且此次第从后文可推知,乃是以“诚”为中枢。如“致知”是与理智德性⑧有关的活动,其在《大学》中的作用,是为“诚意”做铺垫。至于“正心”的说法,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作为“诚意”的后果,或者说任何精神修炼功夫的目标;其二是某种独立的心灵修养技术,《大学》中对这层意思自反面言之:“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换言之,“正心”作为一种精神修炼技术,其入手处则应是摆脱或克服各种诸如“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这样的情绪,以使心灵回归中正平和的状态。这种意义上的“正心”,或与孔子早先所言“克己”有关,也与后来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同类,都是一种由负面入手的,重点在于“克服”“去除”的心灵修养方式,而与此处欲讨论的“诚”的、建设性的精神修炼技术完全不同。
对于何谓“诚”,《大学》中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将“诚”与“自欺”对立起来,而从《中庸》的有关论述来看,“诚”的观念在早期儒家中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理解这一点,或与以前孔子曾有“乡愿德之贼”(《论语·阳货》)的议论有关。后来万章曾问孟子,孔子批评“乡愿”是什么意思。孟子回答说: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上述言语的要点在于“自以为是”,这已经很接近“自欺”的意思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点明“乡愿”的特点乃是“似德非德”“似是而非”,从孟子的意见来看,尚不够深入。“似是而非”可能是立足于欺骗他人,而“自以为是”是更进一步地连自己都要欺骗了。骗别人是作伪,而骗自己则是作伪的最高境界,这样作伪的人,便是“乡愿”,便是不“诚”。“诚”与“伪”的对立,一来是理解“诚”之意义的基底,二来也引出了中西哲学的一个巨大差异。
如果说西方哲学有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是“真不真”的问题,任何性质的言说判断,最终都要接受检验而断定其是否为真理,而这个思考的方向,与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知识论以及逻辑的、分析的传统都密不可分。但在儒家哲学甚至全部中国哲学中间,上述“真不真”的问题却从未出现。比如《庄子·齐物论》关心的核心即“是非”,这主要是一种价值判断,与个人道德立场有关,而在儒家哲学中间,占据这样一个核心位置的便是“诚不诚”的问题。论者常说中国哲学具有一种实践的性格,而这也就意味着哲人们最关心人的人格品质问题,关注某人从道德境界上说究竟是否有德性,必然会引出如何才能适当地辨别出这种德性的问题,而这就是儒家言“诚”时所欲解决的。西方哲学中的“真”与“假”相对,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客观地从形式上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儒家哲学中的“诚”,接近“实”或“情”的意思,与“伪”相对,恰是一个缺乏客观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一个人诚或不诚,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作伪而被人察觉,还算不上最老辣的“乡愿”,只有自知其非而骗过所有旁观者的眼睛,才是老辣的“乡愿”。
诚与不诚,虽然对应着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德性,但其作为仅与个人主观内心态度有关的问题,从客观上无法判断。于是意欲追求德性的人,便必须主动督促自己努力做到诚——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表现出的道德行为具备真正的伦理价值,才能获得真正高尚的人格品质。因此早期儒家会对“诚”予以足够重视,而其自宋代以来就被指为儒家功夫论的核心,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我们看来,诚在儒家“为己之学”的问题域中也占据同样的地位:“道四术”中“心术为主”,而从诚与不诚实际上决定着任何德性品质可靠性的意义上,诚无疑也应是精神修炼范围内最为重要的话题。
在传世文献中,《中庸》对“诚”的重视程度可能最高,而其被误读的程度也最高。就其文本构成而言,梁涛曾在总结以往王柏、冯友兰、武内义雄、徐复观等人的说法后,参照郭店竹简《五行》篇的思想,分现有的《中庸》文本为《中庸》与《诚明》两篇。前者包括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所以行之者一也”为止;后者为第一章与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其中前者为记言体,除第十二章之外均有“子曰”为引导;后者为议论体,与《五行》体例接近。梁涛认为这两部分内容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一部分谈“中庸”不涉及心性,乃是从礼乐等外在规范入手;后一部分则通过“性”“独”和“诚”这样的观念,重在讨论内在的道德精神。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荀子·不苟》言“诚”,则与后一部分,也就是被称为《诚明》篇的文句多有类似,区别在于荀子的改造在于使此“诚”重新与外在的礼仪相关,从而淡化了“诚”的抽象意义与神秘的精神性⑨。上述见解,为我们揭示了《中庸》中所包含的不同思想倾向,从传世文本中分出的新《中庸》部分,实际上界定的是“为己之学”的理论背景,并最终以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为收束,而《诚明》部分,则是对功夫论意义上“诚之者,人之道”的专门论述。
从前文对于“人道”的分析与《大学》中对“诚”的用法可知,孔孟之间儒者所言“诚”,本来都是在修身方法的意义上讲的,但这一层朴素的意思,往往被《中庸》里一些较为隐晦的话搞得很复杂,如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诚者,天之道也”。谈《中庸》无法回避对于“中”的理解,直到宋儒对于此观念(包括“诚”)的看法,尚未神乎其神,但其在现代研究者眼中,却忽然具有了某种“本体论”地位。典型如杜维明所称:“道既有其中心焦点……它是从本体论上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中’意指每个人所固有的最精微的绝对不可化除的品质。”[7]19-20也就是说:“‘中’指的是一种本体论状态……‘中’这个字只能够恰当地运用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7]21且不论 上述看法 中出现的“本体论”这样的术语及其背后隐藏的哲学范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的思考,这种预先设定某一本体的看法,恐怕与孔子认为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努力方能追求自身之应是的主张相扞格。搁置以往孔子视“中庸”为君子的某种应有品质的看法不谈,《中庸》明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是以“情”言“中”,将“中”视为一种人生而实有的情感能力。在此意义上,上述说法与《性自命出》中对“情”与“中”的用法之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语义关联。《性自命出》里的“中”字,所指内容大体就是人心,而情感属于人心的能力早已是三代以来学者的共识。《性自命出》里的“情”,可被视为修身活动的真正起点,而此起点也同样出现在《中庸》里——这两篇文本都有由“情”与“中”出发经由“道”而抵达“德”“性”的主张。这仍然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修身的进路,而如将此进路与“即心言性”的理路相对照,可称之为“即情言性”。后者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具体,而无需设想牵扯一些神秘对象在内,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意思不外是将人心所具备的情感能力视为修身的基本起点,而相应的“未发”“已发”的说法,则是从一头一尾的角度锚定了修身过程之始终。
在这个修身过程中,“诚”在心术范围内被早期儒家认为占据枢纽地位,但在其上仍然覆盖着另外一些干扰性的说法,如“诚者,天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出现的“天之道”,与“赞天地之化育”之类的说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朴素一面,从《中庸》文本写定的时代广泛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因为此文本的编成既然如其他很多中国经典文献一样,并不属于一人一时之作,而其中被掺入一些与原来的理论旨趣相左的内容也就不难想象了。因为这些内容更接近汉儒的观点,《中庸》的全部文本以往都曾被研究者视为汉初的作品,但从其与郭店简书之间明显的相关性来看,其大部分仍应出于孔孟之间儒者的手笔,不过不排除其中某些内容来自更晚时代的增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孔子后学的整体思想中并不具有太大分量的内容,却在现代新儒家的解释体系中被放大成为某些具有本体地位的观念,并以此种“诚体”来解释人心的德性与人和世界的关系⑩,但这种假设对于解释先秦儒家思想绝非必要。
具体就此种精神修炼技术而言,除《大学》中言及之外,《中庸》第二十一章以下专门论“诚”,而《五行》⑪说部文字中也反复谈“诚”:“君子知而举之也者……诚举之也”;“事之者,诚事之也”。《性自命出》虽不见对于“诚”的正面解说,但对于其反面之“伪”有明确的批评:“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凡人伪为可恶也”。总体而言,《大学》主张“诚意”是“正心”的环节,也是“致知”的发展,并在《中庸》里得到从两个角度的论述:“《大学》的‘诚其意’……后来发展为《中庸》‘自诚明’和‘自明诚’。”[8]131《中庸》分别称上述两个角度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所谓“明”,应该就是“致知”的意思,而“自明诚,谓之教”因此也较为顺畅,将“致知”的“思”的功夫放在“诚”的功夫前面作为铺垫,而这个过程都属于“教”,即人格培养的环节。但“自诚明,谓之性”则稍微难以捉摸一些,这种说法,乃是看到了“诚”具有决定一切德性是否真实有效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只有先立住一个“诚”字,其他任何成就人性的努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徐复观曾就《大学》里所谓“正心”入手论“诚”:“心要从生理冲动中突破出来,不为生理冲动所淹没,乃能呈现于自己生命之中,这即是‘心在’,即是‘正心’;此时正心的工夫,可以与诚意无涉。心呈现出来以后,要使其贯彻于所发之意,这便如后所述,须要诚意的工夫。”[9]171其论点似有将不同性质的精神修炼功夫混合来谈论的嫌疑,但他将“诚”认作“先秦儒家修养工夫发展的顶点”[9]173大约不错,“道四术”中“心术为主”,而心术又以“诚”为其枢纽。郭沫若一度指“仁义礼智诚”为思孟“五行”⑫,大概也是因为看到了上述一层意思。“诚”的修养功夫的上述关键性地位,实际上早已为后来的孟子所揭示。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对此,朱熹“万物之理具于吾身”的说明有过度诠释的嫌疑,其实际的意思可能就与《中庸》里所谓“不诚无物”相同,都是要说明丧失了对“诚”的把握,一切事物对于人而言均毫无意义。孟子后面一句话则不外是向我们说明,此“诚”作为一种修身功夫,推而实行之,便是最为切近的追求德性与理想人格的方式。
无论《大学》还是《中庸》,都曾言及另一个与“诚”密切相关的观念“独”,如《大学》所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里也出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故君子慎其独也。”对于这两个“独”或“慎独”,以往的解释以为其所指乃是“谨慎独处”,直到发现新出土的简帛佚书《五行》中出现了同样“君子慎其独”的说法,才启发研究者逐渐开始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发现以往对于传世文献中“慎独”的理解,可能完全偏离了原有的意图⑬。就“慎”的意思来看,“不但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王念孙以及今人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也不可信。传世文献也好,出土简帛也好,‘慎独’之‘慎’皆宜以本义‘珍重’为解”[10]。那么所珍重之“独”指的是什么呢?虽然传世文献未提供足够的信息,但《五行》却对此“独”之所指有明确的解说。
《五行》经部文字云:“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这显然是将“能为一”与“独”联系了起来,对此说部文字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文解上句“能为一”云:“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说文解下句“慎其独”云:“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一也者,夫五夫为□心也。”并在稍后的地方对“独”做出了专门的说明:“独也者,舍体也。”更明确的说法就是:“舍其体而独其心也。”由此最终的解说可见,上述所引文字的意思非常清楚,“慎独”要我们珍重的东西,不外就是“心”。《五行》此处出现的“能为一”的说法,可能原本是一个来自黄老学的观念,在《黄帝四经》、《管子》“四篇”和新出土文献《凡物流形》中,均强调过作为一种修身技术的“能一”。《管子》“四篇”曾清楚交代,这种功夫最终便是“一于心”⑭。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行》中所谓“能为一”和基于此的对于“独”的看法,不排除是受到来自稷下黄老学影响后的主张。无论“能一”还是“独”,最终都指向一种专注于内心的精神修炼功夫,并最终使之保持完整的“全心”之状态。对于《五行》引文中出现的另外一些观念,比如“五”和“体”而言,如依陈来所言,以为此“五”为五官,则“体”之所指同样也是这五官,而“以五为一”的意思就是指心使五官的作用专一。总之,“一是指心的专一,独是指心的独自主宰,而一和独都是为了使精神从外转向内,专注于内心”[11]。至于“舍体”的说法,可以通过《五行》中大小体的观点来理解,“舍体独心”便是舍小体、独大体,是在以心统摄官能的基础上,进而摆脱其影响,完全进入内心专一的精神状态。进而言之,“慎独功夫强调专诚向内,排除感官的向外追求,这些与《孟子》书中的思想是一致的”[12]。但有论者认为:“《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慎独’思想的来源,不用说来自于彻底去除人的身体性、物质性,高扬其主体性的道家之‘独’思想。”[13]这种说法却夸大了“独”和“一”的观念与稷下道家的关系及其相关意义,实际上从孔子所开辟的在反思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转向内在的角度来看,我们无需认为其后学最终达到的对于专注内心的强调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早期儒家所谓“慎独”,与其强调心与心术的关键地位一脉相承。
在《五行》未出土以助我们澄清以往对于“慎独”的解释中存在的方向性错误之前,徐复观已经对先秦儒家所谓“慎独”的意义表现出了极高的洞察力,他将其与《中庸》所谓情感内在而“未发”的内心状态联系起来:“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未发’,指的是因上面所说的慎独功夫,得以使精神完全成为一片纯白之姿,而未被喜怒哀乐所污染而言,即是无一毫成见……无一毫欲望之私。”[9]78至于“所谓‘独’,实际有如《大学》上所谓诚意的‘意’,即是‘动机’;动机未现于外,此乃人所不知,而只有自己才知的,所以便称之为‘独’”[9]77。徐复观的解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于“独”的“独处”之类的错误理解,从功夫论的意义上发现先秦儒家所言“独”的最终目标,不外就是希望使人达到某种无私欲、无成见的精神状态——此状态可被视为专注内心、关心自己的结果或者所欲达成的目标,在此种状态下,人才能成长为具有道德价值的自己。如果将“慎独”作为执守内心的功夫,作为“保持和守护‘自我’道德本性的过程”,那么将传世文献与新出土文献对读,我们还可以获得更为精细的理解,早期儒家言及两种不同形态的“慎独”:“一是由《中庸》和《大学》所代表的,注重的是约束和控制等消极意义上的‘慎独’”;“一是由《五行》(还有《礼记·礼器》)所代表的,注重的是专注等积极意义的上‘慎独’”⑮。此“消极意义”的“慎独”,如《大学》里所言“正心”一样,都是从负面提醒我们注意精神修炼问题的复杂性。
《五行》经部另一处地方同样言及“慎其独”:“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相应的说部文字为:“差池者,言不在哀绖;不在哀绖也,然后能[至]哀。夫丧,正绖修领而哀杀矣。其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陈来解释这段话说:“意思是,参加丧礼或其他从事守丧活动,不把心思放在丧服的形式上,才能完全表达出哀痛的心情。若把心思放在讲究丧服的形式上,哀心就势必减弱了。”[11]此种思路可与《礼记·檀弓下》谈到“丧礼”之时的某些言论相比较,此文中的核心观点就是要将治丧时的注意力专注于内心的各种状态,比如“祷祠之心”“生者有哀素之心”“主人有齐敬之心”“与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等,相应地,《五行》中的思路同样是要人专注内心,放弃对于外在事物的过分关注,甚至放弃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五行》篇的‘说’从‘舍体’即从‘内在性’‘内心’或‘中心’看待和理解‘独’……实际上就是从人的‘内在’方面思考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据”[14]428-429。这种基础也就是“为德”的基础,而“为德,简单说来就是一种舍体的独心论”[15]。在较窄的意义上看,“作为人的‘内在性’的‘独’……是指‘人’的内在道德‘本性’‘本心’和‘德性’,再具体地说,就是‘诚’和‘仁’等伦理道德价值”[14]429;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独’可以说就是个人自身或自己,这也符合儒家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如‘修身’和‘正己’‘有诸己’等)以‘自我’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特征”[14]425。总而言之,可以说《五行》中与“独”有关的内容,都是从专注内心以追求德性的功夫论角度来立论的。
对于《五行》所谈的“独”与“中心”,有论者以为其指向人心的不同部分,并认为《五行》中的“心”具有“独心”“中心”与“外心”三重结构。“独心”乃“形上、超越之心”,“中心”为“五德形之于内”,“外心”为“四德行之于外”⑯。这种解释显然有过度诠释的嫌疑,实际上此文提倡所慎之“独”,即后文谈论的“中心”,就是要人专注内心,关键是对一种“心术”的揭示。至于“中心”在文中则是相对于“外心”而言,两者间的区别不在于心本身的概念结构,而在于内外之别,如《五行》经部谈及“以其中心与人交”,“中心辩然而正行之”,与“以其外心与人交”的区别,分别与仁义和礼的区别有关。这里似乎将仁义均视为内在,而将礼视为外在,如此实际上也就是仅从表现形态和行为举止方面来考虑礼,而未曾将其与某种“德之行”或者说内在的德性关联起来。这种文本内的龃龉,可能就是《五行》篇包含的一些“僻违而无类”的地方。
《大学》涉及的“独”与“诚”的莫大关联,虽然在孔孟之间的文献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但后来的荀子却对此有比较明确的理解。《荀子·不苟》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这段话首先如《中庸》一样,强调了“诚”在精神修炼类功夫里的核心地位,其次则强调了“诚”与“独”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自己面对自己时的真诚、不自欺的态度,任何专注内心的修炼都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真正开展的。另有论者结合“慎独”与“五行”,就孔孟之间儒者的思想得出了类似的看法:“慎独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统一于心,与心为一,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意思是相近的。”[8]130这提示我们,“独”与“诚”这两种精神修炼功夫,都是打通孔孟之间儒者思想的关键。无论对于传世文献中所见的思考还是展现在新出土文献中的思想而言,通过真诚地专注于内心,才能使“德之行五”统一于自己,以成就具有道德价值的理想人格。
结 语
就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全部内容而言,精神修炼、经典学习与礼乐操演三条大的修身进路,基本上是平行展开的,虽然孔子后学已经开始强调其中应以“心术为主”,但这只是一种对理论上的重要性的强调,而非对实践上的次第说明,也就是说,并没有在以上三条进路之间建立任何一种前后关系,比如断言必须首先进行精神修炼,之后才能开展经典学习或礼乐操演。具体到“心术”的范围之内,孔子时期,“省”与“忠恕”这类内心功夫的思考也相对独立,既未特别强调其中某种功夫的枢纽地位,也未尝试在其间建立某种较强的顺序关系。但在孔子后学中间,对于各种精神修炼技术的轻重地位及其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已经有了高度关注——如《大学》《中庸》与《五行》里呈现出的“诚”的枢纽性地位,“诚”“独”之间带有递进意味的关系。总体而言,在被称为心术的诸种修身功夫中,孔子后学基本一致主张“诚”占据着最为关键的理论地位,且他们至少部分地主张,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功夫相对于“独”具有某种优先性,如荀子所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这个理论焦点,虽然本身是“实践的”,但仍然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理智德性”,那么此“诚”作为一种获取德性的修身功夫,虽然传统上会被视为一个“道德的”问题,但其实际上应是与诸“理智德性”相关的功夫焦点。这无损于“诚”在所有精神修炼技术中的枢纽地位,“理智德性”作为“实践智慧”对于“道德德性”具有指引作用。在孟、荀之前,孔子及其后学在心术的范围内已经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功夫论思考,回溯这个聚焦于精神修炼活动的理论谱系,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儒家乃至全部历史上儒家的发展面貌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功夫的问题在宋明蔚为大观,但其源头深埋于先秦儒家的种种相关思考当中。
注释
①匡钊:《孔子对儒家“为己之学”的奠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②匡钊:《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江汉论坛》2012 年第7期。③按:此处所引文献系笔者自译,注释⑤⑥⑦亦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edited by Gary Gutt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8.④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实践之知还是存有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刘玮译,刊于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8 年版。⑤Henry Rosemont Jr.,IsThereaUniversalPathofSpiritualProgressinthe TextsofEarlyConfucianism?ConfucianSpirituality,Volume One,Edited by Tu Weiming and Mary Evelyn Tucker.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2003.p.192.⑥⑦均见Michel Foucault,The Care of the Self,Volume 3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English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Vintage Books,1998.pp.60-61.⑧早期儒家对“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划分,详细讨论参见匡钊:《早期儒家的德目划分》,《哲学研究》2014 年第7 期。⑨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86 页。⑩如杜维明在《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中的典型观点。⑪本文所引《五行》篇,均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 年版。下文不再出注。⑫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⑬对于这方面内容,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澄清相关问题,有代表性的论文可参考廖名春:《“慎独”本义新证》,《学术月刊》2004 年第8 期;王中江:《早期儒家的“慎独”新论》,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陈来:《“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中国哲学史》2008 年第1 期;以及梁涛、斯云龙编:《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漓江出版社2012 年版一书中的相关部分。⑭相关的讨论参见匡钊等:《〈管子〉“四篇”中的“心论”与“心术”》,《文史哲》2012 年第3 期。⑮参见王中江:《早期儒家的“慎独”新论》,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39页。⑯参见郭齐勇:《郭店楚简身心观发微》,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