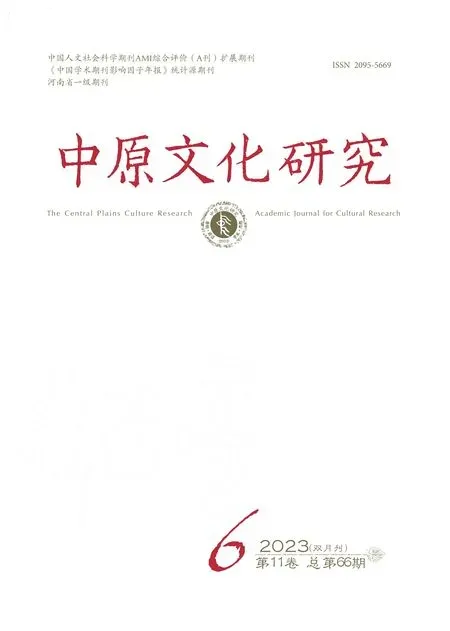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构成与特征*
纳秀艳
丝绸之路发展到元代,经由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三次西征,得到了空前扩展与延伸,许多外国商人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其中大都、上都及和林三地成为聚集外商的重要地方。与此同时,又有西域色目人拥入中原,许多人定居于此并自觉学习中原文化,从中汲取文学养分,陶冶审美情操,写下了富有鲜明丝绸之路印记的诗歌,成为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的一支劲旅,他们以独特的身份,积极参与元代文化事业,与汉族诗人、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共筑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坛。
一、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构成
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人群体与以往的任何朝代相比,诗人群体的构成更为错综复杂,他们在身份、地域、经历以及文化修养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汉族和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及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行旅诗人群体的两大主体。
(一)汉族和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
这一群体特指的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汉族诗人、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中原少数民族诗人共同构成的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亦可称之为中原诗人群体。之所以将二者合为一个群体,一方面基于契丹诗人耶律楚材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和文学造诣,一方面在于他与这些汉族诗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元代或因公出使西域,或因私行走于丝绸之路的汉族诗人较之于前之唐代和后之清代,屈指可数,主要有陈义高、丘处机、李志常、尹志平、郑景贤、王君玉等人。
陈义高曾以道士身份任忽必烈太子真金及其长子甘麻剌的文学侍从,《永乐大典》有记载:“高士陈义高,闽人。至元丁丑,与其师张大宗师居大都。初侍裕皇,继从晋王镇北边。成宗登极,王入朝,上赐义高卮酒,劳曰:‘卿从王累年,无劳乎?’对曰:‘得从亲王游,岂敢告劳。’”①这里的“裕皇”即太子真金。陈义高是元早期第一位行旅于丝绸之路的南人,是一位宗教人士。1290 年冬,忽必烈孙甘麻剌被封梁王,出镇云南。陈义高作为梁王侍从,一路随行。他们从大都出发,经过真定等地,然后向西。1291 年春,梁王一行经过陕、甘,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直抵交河城。在这次丝绸之路行旅中,他写下了《过交河作》《隆徳县徳胜寨》《扈跸作》等丝绸之路行旅诗②,其中《过交河作》最为著名:“黄昏饮马伴交河,吟着唐人出塞歌。后四百年来到此,夕阳衰草意如何。”诗人饮马交河畔,吟咏着盛唐边塞诗人的名篇,观经历沧桑巨变的西域,对夕阳衰草,发万千感慨。“后四百年来到此,夕阳衰草意如何”,诗句表层似乎了无深意,却在怀古叹今中蕴含着多少无奈。
丘处机是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弟子,于1219 年应召率李志常等18 名弟子,随成吉思汗近臣刘仲禄西行。1221 年抵西域成吉思汗行宫(今阿富汗界内兴都库什山北麓),觐见成吉思汗,欲以道教养生法来劝说成吉思汗停止杀戮行为,三年后回燕京。此行往返之间,丘处机写下了许多反映丝绸之路风情的诗歌,诗多被弟子李志常收集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另元人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录了其部分诗歌作品。丘处机行旅丝绸之路虽仅有三年时间,却使得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较高的成就。诚如顾嗣立在《元诗选》中所说:“长春子西游诗最多奇句,如《龙阳观度贞》云‘碧落云峰天景致,沧波海市雨生涯’。《望大雪山》云‘南衡玉峤连峰峻,北压金沙带野平’。《寒食日春游》云‘岛外更无绝情地,人间惟有广寒宫’。惜全首多涉道家语。”[1]显然,顾嗣立妙赏那些丝绸之路行旅中写下的奇句,但对其诗文多关涉道家语有所排斥。清代诗歌评论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三中指出:“邱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句。”[2]此“精警清切之句”指的就是丝绸之路行旅诗。可见,丝绸之路的行旅经验不仅开阔了诗人的眼界,也使其诗歌风格有了突变,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如此,因丝绸之路之行,丘处机结缘于诗人耶律楚材,二人之间相互唱和,成为丝绸之路诗歌创作之佳话。
提及丘处机,就不能不提他的弟子李志常,他随师父行走于丝绸之路,见证了丘处机西传道教的经历,记述师父不平凡的丝绸之路之行,领略西域迥异的风情,并记录师父一路写下的诗歌作品,其编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典雅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师徒一行的西域经历,不仅为后世研究丘处机丝绸之路行旅诗提供了一手资料,也是后世了解元代西域风物、文化的重要文献。李志常虽然无丝绸之路行旅诗传世,但《长春真人西游记》则是难得的美文。元人孙锡对其成就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门人李志常从行者也,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3]
丘处机的另一弟子尹志平也曾随其西行。有诗词集《葆光集》一部,收录诗词作品数百首,其中有丝绸之路行旅诗4 首,即《金山三首》以及《西域物熟节气比中原较早》③。诗人以新奇的眼光打量西域,诗歌描写异域风物,不仅是其诗词集中的珍品,也是元代汉族诗人中难得的丝绸之路行旅诗歌。特此选录四首诗如下,以窥其诗歌内容和风格:
金山
自宣德州至田相公营,约七八千里,乃金山之北也。
其一
西北行程近八千,却成南下过金山。金山更向西南望,才见阴山缥缈间。
其二
曾从神仙日下游,五千里外水分头。时人只解东溟注,不见长河西北流。
其三
西出阴山万里多,一重山外一重河。大河五次亲曾渡,余外山河未见他。
西域物熟节气比中原较早
止渴黄梅已得尝,充饥素椹又持将。
时当小满才初夏,椹熟梅黄麦亦黄。
尹志平的诗歌内容多以修“道”、悟“道”为主,而上述几首则反映他亲历丝绸之路的所见所感,“金山”“阴山”是丝绸之路上的奇峻山峦,在诗人的描述中却显得平常如见,语言平实,风格平淡,体现出其以平常心观异域风物的写诗立场,是其“修得平常心”诗学主张的实践。
郑景贤精通医、易、诗、书、琴,作为成吉思汗西征的从征医,是窝阔台身边的医官④,深得成吉思汗信任,与耶律楚材关系甚密。二人在西域生活的近十年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是知己,也是诗友,多有诗歌唱和。在《湛然居士文集》中,耶律楚材酬答景贤的诗歌多达75 首⑤。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说:“公集中投赠唱和最多者有一人,即郑景贤是也。集中呈景贤或和景贤之诗有七十五首,占全集诗的十分之一(全集凡诗文七百七十六首)。景贤初与公同在西域,洎于暮年,交谊尤笃。细读诸诗,其人盖以医事太宗,即《长春西游记》所谓三太子之医官郑公者也。”⑥从耶律楚材在唱和、投赠景贤的诗中可知,景贤是一位饱读诗书、才情非凡的诗人,如其在诗中言“龙冈便腹尽诗书,落笔云烟我不如”“佳句服君仰泰山”“辞雄韵险实难还”“文章自愧不如君,敢以玄言渎所闻”“诗笔饶君甘在后,琴棋笑我强争先”。在这些诗句中,流露出耶律楚材对景贤诗才的敬仰之情。耶律楚材是一位天才俊发、文采卓越的诗人。王邻《湛然居士集序》:“中书湛然性禀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数句,或挥扫百张,皆信手拈来,非积习而成之,盖出于胸中之颖悟,流于笔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语语,其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掞,又以薄云天,如宝鉴无尘,寒水绝翳,其照物也莹然。”[4]4王邻对耶律楚材文学才华予以极高的推崇与评价,而能够让耶律楚材钦佩的景贤,其诗才可以想象。遗憾的是,后人仅能在《湛然居士文集》中读到耶律楚材赠答给景贤的诗歌,而景贤的唱和诗则散佚,靡有孑遗。
王君玉也是耶律楚材相识于西域的诗人,二人多有唱和,耶律楚材诗云:“一从西域识君侯,倾盖交欢忘彼此。”(《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一)[4]25阅读《湛然居士文集》,耶律楚材在西域时,酬答王君玉的诗歌有34 首,诗题标明为唱和之作,即《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和王君玉韵》。从诗歌标题即可知,这34 首酬答诗皆是对王君玉诗的唱和,也就是说,耶律楚材诗或用王君玉诗原韵和诗。从这些唱和诗可见二人关系之融洽。然而,遗憾的是,王君玉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均不见文献记载。关于王君玉其人,刘晓等认为:
王君玉,君玉应为其表字,名与籍贯均不详。原隐居山林,后投靠蒙古政权,并随成吉思汗西征。此人与郑师真一样,亦为耶律楚材在西域结交的知己之一……他不仅为“六韬三略无不通”的军事将领,而且擅长诗歌、书法、古琴,并喜欢参禅,在赠答诗中,耶律楚材曾对他的多才多艺赞叹不已。蒙古西征之役结束后,王君玉回到山西,在平阳行省长官胡天禄手下任职,后大概终老于此。[5]
耶律楚材非常珍惜与君玉的这段缘分,在遥远的西域,孤独的诗人有幸相遇志趣相投的君玉,备感欣慰,有相见恨晚之感。《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其三云:
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
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
字老本来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
出伦诗笔服君妙,笑我区区亦强为。[4]99
诗交代了王君玉与耶律楚材在河中府的邂逅。那么,王君玉是早于耶律楚材到西域的汉地诗人,而非“并随成吉思汗西征”之人。丝绸之路的开辟由来已久,中西往来交通较少中断,至元代,在撒马尔罕有中国诗人居住,亦是常见之事。
诚然,郑景贤和王君玉的诗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难以知晓诗人的才情,但是,从耶律楚材“异域风光特秀丽,幽人佳句自清奇”(《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其一)[4]98、“翻腾旧案因君玉,唱和新诗有景贤”(《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其十二)[4]120的感叹中可知二人皆为才华卓越的俊才,赢得诗人的赞叹与钦佩。尤为重要的是,在1220 年至1222 年间,在寻思干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境内),曾经举行过多次高级别的诗人雅集,耶律楚材与丘处机、郑景贤、王君玉等诗人之间的唱和,成为丝绸之路行旅诗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以诗歌为媒介,开展了中西交通史上高雅的文学交流,借以抒发知己之情,以此彰显中国诗歌艺术的魅力,传播中国文化艺术精神。
契丹诗人耶律楚材是一位天资颇高、极富才情的文人,并且与丘处机等汉族诗人邂逅于西域,交游于丝绸之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留下了诸多互为唱和的锦绣妙语。他扈从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创作了160 多首诗歌,堪为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坛之杰,在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评价道:“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6]340将他视作元代诗坛的开创者。
的确,耶律楚材是元代诗文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也是蒙古政权下第一位诗人”[7]。不仅如此,他也是元代历史上第一位扈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诗人,是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人中远游西域的代表,他和扈从忽必烈征云南的刘秉忠,堪为远征诗人中的佼佼者。他沿丝绸之路行走,行程数万里,他自称“忙里偷闲谁若此,西行万里亦良图”(《赠蒲察元帅七首》其六)。他在河中府曾停驻近7 年,游赏山水风光,体察民风民情,写下了大量歌咏西域的诗歌。他暂居河中府,与丘处机、王君玉等诗人唱和,表达对此地的热爱。他暂住蒲华城,即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与当地驻守官员蒲察七斤多有交往,对当地风情赞不绝口,多以诗赠答蒲察七斤。
作为一位契丹人,耶律楚材的丝绸之路行旅诗为人们展示了西域风情,尤其是遥远的河中府的自然气候与人文景观。这些诗歌在元代诗歌史,乃至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其迥异的风姿、丰富的内容,堪为独具风格之作,对元代游历诗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域诗人群体
色目诗人是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的主体部分。色目人并非某一民族的族别称谓,而是对西域诸多民族的统称。据明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所录“色目三十一种”,可知元色目人组成的大概民族数量,但学界多认为陶氏将蒙古人以及部分汉人亦收入其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4)之《色目氏族表》中,经屠氏考证,认为陶氏收录有误,有将一个民族分成两个民族,甚至分为三四个民族,亦有将几个民族合成一个民族的情况⑦。清人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列出色目人二十三种。屠寄认为钱大昕以陶氏统计数字为基础,其所犯错误相同,故而亦有出入。有学者认为近人屠寄所统计数字较为准确[8]13。元代西域人的成分十分复杂,有来自西方诸国的各色人,如欧洲人、中亚人等,加上元代对各个民族的译名又不尽统一,且随着时代变迁,各民族间不断融合,很难精准地予以区别。诚然,对元代色目人精确的种族统计,学界尚存在争议,但若以明代陶宗仪所收录的三十一种为准,可略知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中,用汉语写诗的色目诗人族别之众多,为前所未有之奇观。元代西域诗人群体构成较复杂,群体较庞大,且大多数诗人离开西域故地有数代之久,亦无亲身的经历。但他们对西域故地充满着眷恋,视之为精神家园,在其诗歌创作中,西域故园情结挥之不去。或神游,或遥想,多赋予诗歌淡淡的丝绸之路情怀,成为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坛上的一支奇葩。
关于元代西域诗人群体构成族群情形的概括,最早者为清代学者王士禛,他在《池北偶谈》中指出:“元名臣文士,如移剌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真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剌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9]王士禛以欣赏的口吻列举出这些在元代诗坛占据重要地位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他们是元诗的半壁江山,赋予元诗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基调。他们在功名、节义、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远超那些自古以来以文名取胜的齐、鲁、吴、越之地的世家贵胄子弟。当然,王士禛是站在清代学术的前沿阵地,一览元代诗坛的西域诗人群体构成情况而予以评述。他对于每一个诗人的族别,或籍贯有大概的交代,但是,因西域地域广阔,族群众多,王士禛关于籍贯、族别之说,过于模糊和廓落。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关于辛文房和萨都剌,一为西域人,其所属区域过于广泛;一为色目人,其所属族群过于宽泛。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专设“文学篇”,从“西域之中国诗人”“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西域之中国文家”“西域之中国曲家”等五方面论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族别及其文学创作。其中,第一类诗人有15 人,仅知其身处西域者有8 人,即泰不华、聂古柏、昂吉、完泽、马彦翚、辛文房、阿里、伯颜;知其部族者有2 人,即迺贤(葛逻禄人,亦称葛罗禄、卡尔鲁克等,是一个说突厥语的游牧部族,为铁勒人诸部之一)和郝天挺(朵鲁别族,又译朵儿边、朵鲁班,属于尼伦蒙古部族);知其民族为畏吾者有2 人,即三宝柱和薛昂夫;知其为西夏遗民(包括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者有3人,即张雄飞、余阙、斡玉伦徒。第二类诗人有5人,知其部族为雍古(阴山以北的部落)马氏者有3 人,即马润、马祖常、马世德;不知族别者有2 人,即雅琥和别都鲁沙。第三类诗人有9 人,均为信奉回回教的西域诗人。第四类诗人有8人,除马祖常、余阙二人外,知其部族为雍古者有1 人,即赵世延;知其为唐兀人者有1 人,即孟昉;知其国家或城市者有2 人,即赡思(大食国)和察罕(板勒纥城,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知其民族为回回者有1 人,即亦祖丁;知其身处西域者有1 人,即贯云石。第五类曲家有16 人,除贯云石外,知其身处西域者有8 人,即马九皋、琐非复初、不忽木、兰楚芳、沐仲易、虎伯恭、虎伯俭、虎伯让;知其民族者有3 人,即丁野夫和赛景初为回回人,全子仁为畏吾人;知其信仰基督教者有4 人,即月景辉、金元素、金文石、金武石。此外,有许多西域书法家、画家亦擅诗歌,粗略统计起来有20 余人,分涉不同民族。
当代著名学者杨镰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可谓典范之作,他以20 年的探索为奠基,查阅大量资料,爬梳多种古籍文献,钩沉史籍,甄别材料,考镜源流,几乎覆盖了元代西域汉语诗人,总括大貌,择其要而论之,在宏大视野的综论与见微知著的考辨相结合的研究中,既展示了元代西域诗人的风貌,也论辩著名诗人的生平事迹与诗歌成就。杨镰共统计出元代确属西域人,且用汉语写作诗歌,并流传至今者有100余人,色目人20 种左右,其族别或宗教派别主要有:乃蛮、畏吾、克烈、回回、康里、拂林、也里可温、答失蛮、葛逻禄、唐兀、撒里、雍古、西夏、于阗、龟兹、大食、阿儿浑、钦察、塔塔儿等[8]13。在100 余位诗人中,有很多人的族属不能确定。不过,20 余种族属并非在同一标准中,其中一大部分是民族,一部分是地域或国家,一部分是所信奉的宗教,如也里可温即是基督教。然而,无论是族别,抑或地区和宗教派别,这些都是来自西域的诗人,如伯颜、廉希宪、不忽木、高克恭、马祖常、贯云石、薛昂夫、迺贤、丁鹤年、辛文房、余阙等,一大批灿如繁星的诗人,他们的汉语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元代诗歌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仅是丝绸之路行旅诗中的奇迹,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诗坛曾有过这等奇异盛况?哪个朝代的文坛曾将大食、拂林、乃蛮、康里、钦察……作家都包括在其中?就这一点而言,西域诗人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8]14
基于前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再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对西域丝绸之路行旅诗人作如下概括:一是仅知民族者14 人,其中康里人5人,即不忽木、回回、巎巎、不花、泰熙奴;回回7人,即高克恭、萨都剌、阿里木八剌、伯笃鲁丁、买闾、吉雅谟丁、丁鹤年;畏吾1 人,即薛昂夫;葛逻禄(东突厥)人1 人,即迺贤。二是仅知国别者8 人,其中北庭人2 人,即大都闾、不花帖木儿;高昌人2 人,即五十四、道童;于阗人1 人,即李公敏;龟兹人1 人,即盛熙明;大食人2 人,即瞻思、哲马。三是仅知宗教信仰为也里可温(基督教)者2 人,即雅琥、赵世延。四是仅知所处地域为河西者6 人,即孟昉、观音奴(志能)、观音奴(鲁山)、甘立、斡玉伦徒、昂吉。五是仅知氏族者3 人,其中伯牙吾台氏1 人,即泰不华;塔塔儿氏1 人,即察伋;乃蛮答禄氏1 人,即答禄与权。六是知国别与民族者12 人,其中高昌畏吾人4 人,即贯云石、鲁山、伯颜不花、脱脱木儿;北庭畏吾人7 人,即廉希宪、廉恒、廉惇、廉惠山海牙、边鲁、三宝柱、别罗沙;于阗畏吾人1 人,即丁文苑。七是知民族及姓氏为蒙古克烈氏者2 人,即拔实、兰楚芳。八是知所处地域及民族为河西唐兀人3 人,即余阙、张翔、王翰。九是国别、民族及氏族为高昌畏吾偰氏人5 人,即偰玉立、偰哲笃、偰逊、偰斯、偰长寿。十是知民族及宗教信仰为信奉也里可温的雍古族人1 人,即马祖常。十一是知国别及宗教信仰者为信奉也里可温的拂林(大秦)人1 人,即金哈剌。十二是无所考证者9 人,即伯颜、烈哲、月鲁、月忽难、爱理沙、沙班、野先、定位、辛文房。
总之,西域行旅诗创作群体中的诗人,民族构成十分复杂,总体以畏吾、回回为主,约占31%。有国别可考的诗人共计16 人,分别来自于高昌、于阗、大食和龟兹四国,其中高昌诗人又以11 人之数居其冠。除了高克恭、贯云石、马祖常、余阙、丁鹤年及迺贤这6 位诗人,有著述流传于当世,其他诗人的诗文集大多散佚,仅存零星残篇于后世文人的辑录选集中。
二、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特征
由上述可知,汉族及中原少数民族行旅诗创作,留存较少,但可从中归结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以耶律楚材为中心,丘处机、王君玉等人为代表,他们彼此互相唱和、赠答,通过吟咏西域奇景,追忆在丝绸之路行旅中的独特际遇,以表达对彼此的思念与对过往岁月的不舍之情。总体而言,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的创作,西域诗人的佳作奇篇保存流传得更为完善,他们虽在民族、国别上更为复杂多样,但其思想倾向与审美志趣却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一诗人群体共同呈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一)民族标识 色目为征
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大多来自亚洲北部、中亚地区,甚至有欧洲部分地区。他们族源繁多,因其容貌异于中原汉人,故总冠以“色目人”之称,明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曾列出“色目人三十一种”。西域诗人群体,其实为色目诗人群体。
这些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因有较高的汉文化程度,都有汉语诗歌作品,其中不乏名家,如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等人,均有诗文集传世。而大部分人传世诗歌并不多,多则数十首,少则数首。这些人在中原主要作为官员,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政治原因,大多都起有汉族姓名,或以族属简称为姓,或以先祖任职中的一个字为姓,或以信奉的宗教为名。
(二)执笏庙堂 积功兴业
大多数丝绸之路行旅诗人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或任朝中要职,或任地方官员,在元代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40余位诗人皆有职务,有近20 人身兼数职,或一生担任多职。从朝廷命官,到地方要员,官职大小不等,但分布十分广泛,尤其突出的是其中多人任江浙、福建、江西等江南富庶之地的要职。有如此众多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任要职,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官员的极度重视,与元朝的基本国策相符合,从侧面也反映出政治权利不平等。元朝是多民族统一的朝代,在治国理念上倡导大元气象,在文化精神上以大为宗,在思想境界、政治理念上崇尚壮大宏伟,是为了实现海内归一的统治目的,旨在建立统一的政权。但是,在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在政治领域内,各民族之间所谓的“平等”终究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点与其追求的“大元”文化精神并不相悖。元朝统治者公开地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分为四个等级,将社会民众和民族等级化和区别对待,这是不争的事实。蒙古人为第一等人,色目人(西域各少数民族)为第二等人,汉人(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为第三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人。四等人中,汉族的地位最低。元代的汉人与汉民族并非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南人”实际上大多是江南的汉族。“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力和义务都极不平等。……元朝也因此显示出比辽、金等王朝更为浓烈的民族色彩。”[10]四等人中,南人的政治地位最为低下,凡要职与他们无缘。
对此现象,《元史·王都中传》中有记:“当世南人以政事知名闻天下,而位登省宪者,惟都中而已。”[11]4232而事实上,王都中虽仕至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但与行省之职相去甚远,用则参,不用则闲,可谓虚职而已。故而,有元一代,江南汉人能担任实职者寥寥无几。如赵孟仕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吴澄任翰林学士,正二品。他们的官职品级不可谓不高,然究其实质,皆为文学之职,其身份与品级则难以匹配,遑论其权力。抑或,他们是盛世政坛上的装饰或点缀而已,统治者以此昭示天下民众,大元之所谓气象而已。元末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指出: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12]49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的大学者,其去元不远,亦有在元生活的经历,他的言论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朝担任重要官职,享有优越的政治待遇和政治地位,既可从侧面反映出元统治者的用人主张与政治方略的关系,亦能解释西域诸多少数民族不辞千里,远赴中原的内因所在。这既体现出元朝最根本的政治生态与治国策略,也可窥见元代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不平等现象。
(三)璧奎取仕 得之科举
除去个别生平事迹不详者,大多数丝绸之路行旅诗人都能进士及第。元朝近百年间,以科举取士者并不多,曾两度停科,其中前55 年(1260—1314 年)停止科举。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举行首次科考,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最后一次取士,科举举行共51 年。另有6 年(1336—1342 年)中断,元代科举制度实际推行45 年。按元朝科举制度,三年举行一科,45 年共开科16 次。据《元史·选举一》之《科目》条记载,元代科举16 科,共计取士1139 名[11]2015-2027。而元代庞大的官僚群体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记载,元代各类官员总数为26690 人,相对元代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言,科举入仕者可谓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却有众多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子弟多有进士及第,这一现象非偶然,实乃统治者科举取士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而致。
虽然,元朝科举所取人士极少,但官员队伍却很庞大,这与元朝独特的擢录制度有关,即吏员出职制。所谓吏员出职制,即是一种直接从吏中提拔而入官制度。该制度保证了元统治者将擢拔官员的大权握于手中,大量的官员由此道而产生,实在是一大创举。元朝大儒姚燧在《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中说:“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13]元末明初叶子奇对此有着十分精辟之论,他说:“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岂时运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12]82元代科举制不过是粉饰太平之工具而已,吏员出职制才是真正的取士之道。清末学人曾廉考察元代文人行迹后认为,“元时人士皆竞于文学而不竞于禄仕”,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元代士人崇尚文学而轻视功名利禄的表现,是一种淡泊坦然的心态。而事实上,如果联系元代的职官制度,汉族士人热衷于文学创作,亦是多有无奈。
政治权利是吸引西域人前往中原的磁铁,在以京城为中心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他们留在中原,寻找进入高层社会的机会,同时,耳濡目染中原文化的魅力,加之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学习汉文化从元朝建国之初辄成为一股热潮,始终不减弱,并一发不可收。元代华化之甚,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反映,色目人对汉文化的推崇学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们崇尚汉文化,拜师大儒,交友儒生。元人许有任在《咬思永字说》中讲述了一个色目人家庭对汉学的态度和学习情况:色目人咬生,培养学识,积累学养,非儒生不交往,可见在他们的心中,儒生是最有文化的人,而儒学能够消除他们养成的不良习气。此非特例,在元代西域少数民族自觉接受华化是一种风尚,一种潮流。马祖常家族信奉也里可温(基督教),入中原后以“马”为姓氏,“子孙更业儒术,卒致光显焉”[14]。交友选儒生,成为儒者,是他们的理想。马祖常在其诗歌中,表达了其家世华化的历程以及能成为儒者的骄傲,《饮酒》其五云:
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
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诗书百年泽,濡翼岂梁鹈。
春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夷礼即夷之,毫发各有稽。
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敷文佐时运,烂烂应璧奎。[6]675
这首诗中,诗人追忆先祖在西域的生活和事业,然后讲述家族百年来受到诗书的润泽,并且,纯然以儒者的立场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华化现象和根源,最后四句以自豪的口吻吟咏,祖上虽然是夷人,但一旦入中原,则华化之甚。诗人巧妙化用了《春秋》所规定“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法则,强调先祖华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接受汉文化的陶冶化育,是追求进步的选择,而他自己更以“敷文佐时运,烂烂应璧奎”而骄傲,“璧奎”是壁宿与奎宿的并称,谓壁奎是主文章之星。从上述众多进士及第的西域诗人中可以想见当时华化风气之甚。在汉文化的普及中,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日益隆兴,并成为一股潮流,遍及各地。
(四)雅好文学 兴于世家
在上述总结的西域诗人中,康里不忽木家族,一家两代中三人为诗人;北庭畏吾廉希宪家族,一家人两代中四人为诗人;高昌畏吾偰氏一家三代为诗人。有元国祚相对较短,在不足百年内,却诞生了如此多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世家,这在中国历史上确为罕见。康里本游牧民族,不忽木家族入华最早,他拜元初大儒许衡为师,刻苦研读汉文文献,日诵诗书。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将两个儿子送到国子监读书,一家父子三人,皆有诗留世,虽仅存一二,但亦能自成风格,诚如陈垣评价不忽木《过赞皇五马山泉》诗时说:“虽一鳞一爪,然流丽可喜。”能诗者有父子,有叔侄,如廉氏家族;高昌畏吾偰氏,三代为诗人,堪为奇迹。
另外以二代、三代为主的诗人群体,亲历丝绸之路者并不多见。虽然能赋诗言志,但是因其离开西域久远,其诗歌内容基本不再有丝绸之路情怀或西域印记。因而,尽管从他们的身份和民族属性而言,隶属于西域诗人群体,然因主客观原因,很难在他们的诗歌中发现有关丝绸之路或西域家园的蛛丝马迹,他们在文学上并没有表现出丝绸之路经历或西域家园记忆,故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较少。除了马祖常、贯云石等极少数诗人的诗歌中有些许丝绸之路印记外,其他诗人的诗歌与一般汉族诗人的诗歌无甚差别。因此,在西域诗人群体中,选取马祖常、贯云石为代表,其他人的诗歌不再论及。尽管就丝绸之路行旅诗的创作而言,成绩寥寥,但他们以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参与到元诗的创作中,共筑诗坛。其中不乏杰出诗人,堪与汉族诗人并驾齐驱,为繁荣诗坛做出了卓越贡献。清顾嗣立《元诗选》称:
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迺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6]1185-1186
顾嗣立立足于全元诗坛俯瞰西北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成就。的确,元代诗坛因西域诗人群体的加入,改变了中国诗歌创作以汉族诗人为主体的诗坛格局,不仅丰富了诗歌题材和主题,也促使诗歌风格及审美的多元化。虽然,他们中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难觅丝绸之路痕迹,但是,毕竟他们代表着西域之风,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着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特质。
结 语
基于元代独特的文化气象和社会现实,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较之于其他时代呈现出内容丰富、审美纷呈、风格多样、情感奔放的特点,展示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总特征。丝绸之路行旅诗作为元代文坛上的一股溪流,尤其体现出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发自内心的钦佩,在自觉追求华化的过程中,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中原文化,并创作大量诗歌,抒发情志,表达对一统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不过,丝绸之路行旅诗人与其他文人有所不同,他们或亲历丝绸之路,感受异域文化,对家国的情感体验最深刻;或背井离乡,由西域到中原,在文化的融合中、在对中原的认同中,不断回眸记忆中遥远的故乡,他们的家国情怀独特且复杂。
注释
①解缙《永乐大典》第12043 卷,引《龙虎山志》“赐以卮酒”条。参见解缙编,郑福田点校:《永乐大典》,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22 页。②参见陈宜甫:《秋岩诗集》(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683-691 页。③此4 首诗见薛兆瑞、郭明志:《全金诗》(第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81 页。④《长春真人西游录》中李志常有记,丘处机师徒抵达河中府,“三太子之医官郑公途中详见,以诗赠云……”。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80 页。⑤赵福寿《龙冈居士郑景贤探析》一文中认为耶律楚材酬答景贤的诗有82 首;刘晓、匡亚明《耶律楚材评传》中认为酬答诗有73 首。因耶律楚材的酬答诗题材丰富,诗歌判断偶有出入,属于正常。此处笔者以王国维先生统计的75 首为准。⑥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参见《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统计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共有诗768 首,众体备兼。⑦参见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1984 年版,第1022页。参见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