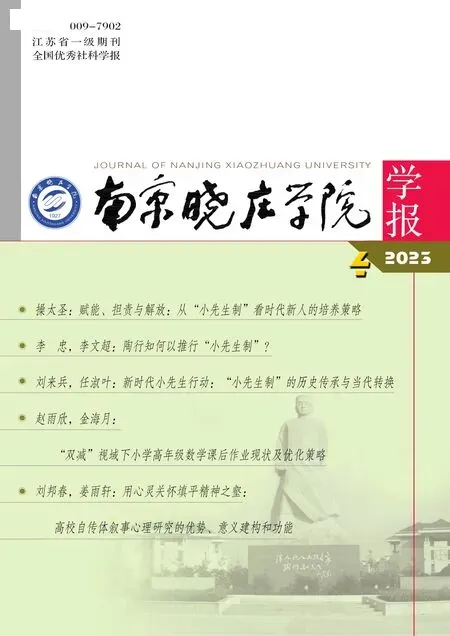由静穆到明丽
——陈之佛工笔花鸟画画风之转变论析
孙彩琪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明清以来,文人画家往往以画作抒发胸中意趣,水墨写意成为花鸟画的主流,传统工笔处于颓败之势。民国时期,传统工笔花鸟画已经到了不知何去何从的窘迫地步,几乎濒临灭绝的边缘。这一问题引起了时人的重视和思考。作为一名富有时代精神和时代责任感的画家,陈之佛深知工笔花鸟画的价值,对工笔花鸟画日渐式微这一现象痛心疾首,毅然决然接过复兴工笔花鸟画的重任。他取各家之长,融汇古今,形成了清新隽逸的艺术风格,终于在工笔花鸟画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开创了工笔花鸟画的新迹象。
陈之佛的花鸟画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早期的陈之佛以古人为师,格调高雅,超凡脱俗,追求画面的唯美意境;建国之后,陈之佛花鸟画呈现出富丽明亮的风格,营造出活泼生趣的意境。这一说法最早由罗叔子《画幅中的两种时代、两种感情》提出(1)罗叔子:《画幅上的两个时代、两种感情》,《南京日报》1960年7月21日。,陈传席、顾平编著的《中国名画家全集:陈之佛》对此表示认同(2)陈之佛绘,陈传席,顾平编著:《中国名画家全集:陈之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此后的研究者多将陈之佛的画作和画风分为这两个时期。而贾小鸽的《陈之佛工笔画研究》将陈之佛工笔花鸟画以时间为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即: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忘我之境。(3)贾小鸽:《陈之佛工笔画研究》,南京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笔者认为,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分水岭,前期为探索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陈之佛的绘画风格富有个人特色,是其在继承传统工笔花鸟不断创新与调整的过程;他在工笔花鸟画题材、技法等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因而绘画种类多样,画幅流露的情感也多有不同,但总体上以追求古人意境,超脱出世的情调为主;绘画题材大多以寒梅、残荷、翠竹等为主,带有文人洁身自好的指向性;同时,也有不少描绘花鸟生趣、传达诗意、用以寄托心灵的作品,代表了其对工笔花鸟画革新的多样化探索。后期为追求思想性及融合新时代阶段:对自然生活描绘的一类作品在建国之后发展成熟,在结合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开放、进取的新时代气息融入他的画作中,成为其后期艺术创作的主流。而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仍需要探究:从早期的探索阶段到后期的追求思想性阶段,其转化的原因是什么?画面在绘画语言和传达思想的方面进行了怎样的转变?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创作及画风
(一) 由工艺美术转向工笔花鸟的探索阶段
与同时代的于非闇从写意山水花鸟转到工笔画不同,陈之佛是由工艺美术转到工笔花鸟的。学生时代的陈之佛受同学影响对绘画与文学颇有兴趣,抱着“振兴实业”的愿景考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机织专业。毕业后,陈之佛留校任教,并在此期间编写出一本图案讲义。后于1918年赴日本深造,学习工艺美术,攻读美术史论,并进行花鸟画创作和研究,从而练就了深厚的写生功底,奠定了在图案构成和色彩运用方面的基础。在日学习期间,岛田佳矣教授启发陈之佛注重中国传统图案,成为其决心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引子。回国之后,当时的中国民族工业由于受到外国厂商的打击而很不景气,陈之佛在染织工艺方面无法施展自身的才艺,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后,陈之佛投身于艺术教育,在上海艺术专业学院任图案系教授,并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他在教图案学的同时,兼教美术技法理论和美术史,并挤出时间钻研工笔花鸟画。(4)“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了大讲“国学”整理“国故”的潮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国画”代替了“中国画”,这使从事中国画的人都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参见葛玉君:《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论争解析》,《美术》2007年第12期。陈之佛在工艺图案美术方向卓有成就,出版了《图案构成法》《中国陶瓷器图案概观》等技法工具书。
陈之佛在早年的学习中奠定了扎实的绘画和理论基础,他“早年曾热衷于埃及金字塔陵墓壁画和波斯密画的研究,其后对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和陶瓷纹饰纹样也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因而他的花鸟画带有明显的装饰性。”(5)陈之佛绘;陈传席,顾平编著:《中国名画家全集:陈之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工笔花鸟画的技法、构图、创作等方面,都与图案设计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使得陈之佛的绘画风格带有强烈的装饰性,造成了其别具一格的绘画风格。
20世纪30年代初,陈之佛开始工笔花鸟画创作。在1935年的画展中,陈之佛以“雪翁”之称展出画作,其独特的画风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从此,陈之佛醉心于工笔花鸟画,融汇古今,致力于花鸟画创作。1942年3月1日,陈之佛在重庆首次举办个人画展,这些画作是陈之佛对工笔花鸟画的探索和革新之成果,受到了人们的肯定。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国画展览等活动,参加国画相关研讨会,不断进行美术绘画创作,投身于工笔花鸟画革新事业。
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长期勤恳钻研。从1935年画作展出开始,直至1962年逝世,这期间创作了五百多幅工笔花鸟画(笔者统计了其女婿李有光,女儿陈修范所著《陈之佛研究》一书,有具体名字的工笔花鸟画作共228件),为后人留下许多精美的作品。
陈之佛早期的作品风格多样,不拘定法,体现了他对花鸟画革新的尝试。这一时期是他绘画探索时期,也奠定了其绘画艺术的总特征:“继承了我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优良传统,融会了西方绘画尤其是日本绘画及姊妹艺术之长,既富有强烈的传统色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6)陈之佛绘;陈传席,顾平编著:《中国名画家全集:陈之佛》,第93页。其艺术鲜明的个人特色在于:装饰性、积水法、清雅的色彩等三个方面。
传统工笔花鸟画本就具有装饰性意味,学习工艺美术出身的陈之佛更加强了这一特点。他师法传统、观临古画,学习《芥子园画谱》所用的花鸟范式,并提出“观、摹、读、写”,在写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工艺美术式的简化以融合画面,重视构图、设色;在学习宋元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同时,陈之佛取意广求,吸收陈洪绶、恽寿平等人的染色方法,并受到日本“宗达-光琳”画派的影响,创造了特有“积水法”塑造景物。他在作品赋色方面别出新意,使用色纸作画、加粉赋色、减少墨色等方法来统一画面色调,体现清淡典雅的效果。
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诗意境界、文人意趣和日本画派追求“物哀”“空寂”的审美意味影响了陈之佛画面的主体风貌,造成了陈之佛画面对唯美意境的追求,作品的格调趋向于淡泊、寂静而雅致。同时,特殊社会历史境遇造成了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在重庆展出花鸟画获得成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请他做国立艺专校长的打算,并许诺了支持陈之佛开展工作一些条件。陈之佛本不愿意从政,却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拒绝这一请求,只好勉强答应上任。然而,在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之后,当时的教育部门无法兑现之前提出的承诺,致使陈之佛无法开展相关工作。同时,陈之佛在艺术教育上的改革主张为国民政府所不允。当时,陈之佛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这使得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极为不满。陈之佛在任职艺专校长两年期间,身体不适,负债累累,身心皆遭受巨大痛苦。于是,他毅然辞去艺专校长职务。这才使他得以回到安宁的生活,继续从事花鸟画创作和研究。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陈之佛对国内形势感到担忧,内心处于彷徨之中。于是,他将这一心境用绘画表达出来。陈之佛曾经谈到:“艺术是情感的表现,与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它于个人于社会当必有更深更广的意义。”(7)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 436页。艺术能体现出艺术家精神及人格,而陈之佛确实做到了用画面表现个人的情感和体现其高洁的品格。这一时期,陈之佛的画面文静幽深,体现出古代文人那种超脱世俗的理想和洁身自好的意趣。比如,他喜画白色雪景和塑造白色物象来体现洁身自好,营造素雅恬静的氛围;取梅花、孤月、竹林等意象营造孤寂、空冥的氛围,体现出禅思;还会塑造各类鸟儿、山茶花来表现对生活的热爱,沉浸自然生趣之中,远离俗世。这阶段的代表作品有《梅花宿鸟》《寒汀孤雁》《茶梅寒雀》等。
(二) 工笔花鸟画创作的成熟时期
在经历早期的探索和创新过程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陈之佛的画风开始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工笔花鸟画基调,这是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之佛被聘任为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继续从事艺术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加各类艺术活动,为新中国艺术事业鞠躬尽瘁。这一时期,生活平稳,社会和谐,使得陈之佛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时代给陈之佛的绘画注入了新气象。对革命事业的诚挚,对生活前景的期望与祝福,在陈之佛的画作中显现出来。他也由此一改沉郁、清冷的基调,创作了多幅充满活力,歌颂新生活的作品,画面洋溢着对生活的赞美,风格也由清丽秀美转向了热闹明快。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探索期。特殊的时代对应特殊的作法,艺术为人民服务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此时的江苏画坛,傅抱石为核心人物,他以独具一格的个人色彩和张扬奔放的艺术风格,把毛泽东诗词作为题材原型,创作了一大批山水画,“成为当时正在谋求出路的中国画家所效应的榜样”(8)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而传统工笔花鸟画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行革新。人物、山水画用写实手法表现生活,与为政治服务的写意画不同,花鸟画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其在时代洪流面前的变革较为艰难。针对这一状况,陈之佛在“百花齐放”这一文艺方针指导下,提出“花鸟画对于培养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有很大功能……必须在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9)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文集》,第441页。这段话肯定了花鸟画陶冶情操的功能,并要求花鸟画家追求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这一时期他的代表性作品有《和平之春》《松龄鹤寿》等。
二、 陈之佛前后两个时期的画作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为分水岭,陈之佛两个时期的绘画所传达出的意境有着两种不同的基调。当然,其画风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陈之佛建国之后的花鸟画是由前期的探索和实践发展而来的,所处社会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画家思想境界不同,陈之佛花鸟画所表现出的意境也由静穆转向明丽,绘画技巧也在画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中逐渐成熟而更有魅力。陈之佛前后两个时期的绘画带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下面,结合具体画作分析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之佛绘画的变化与革新。
(一) 绘画语言的转变
中国传统花鸟画重视对二维画面空间的经营,画面形式美、装饰性意味浓厚。花鸟画与工艺美术的相通,使得陈之佛在形式美方面更为重视,他曾说:“花鸟画很讲究形式美,一幅优秀的花鸟画往往是形式美的处理最得法,也是最符合人们欣赏要求的东西;而表达花鸟画上的形式美,主要又在构图和设色两方面。”由于不同时期所要表达的思想不同,陈之佛在绘画语言方面也有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构图技巧的成熟。在早期的绘画探索阶段,他在花鸟画的构图方面做了不少新颖的尝试,将传统绘画理论的构图法与西方构图塑造的技巧相结合,加入巧思,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图样。在陈之佛的花鸟画革新过程中,他的构图偏向于以传统折枝画法为主,辅以多样化的尝试。他强调注意画面宾主、疏密、虚实关系,在绘制作品前常花费大量功夫构思白描稿。常采用长卷轴的竖幅作画,在画面中多使用折枝画法的一波三折式构图,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将禽鸟位于画面“势”的走向顶点,引导观画者的视线顺着植物长势看到画面的“点睛之笔”,使得画面充满生趣。1945年所作的《梅雀山茶》、1947年的《海棠绣眼》、1949年的《啼鸟寒枝》便是这一构图样式的典型。
同时,陈之佛在构图上敢于打破传统程式的许多禁忌。传统绘画中往往很少两条相近的平行线条,但在陈之佛1946年的画作《荷花蜻蜓》中,荷梗垂直平行于画面中间,这种难以把握的直线被荷花间隔其中,形成前后关系,并由蜻蜓,枯叶,另一株荷花枝干穿插其间,使得平行的线条不会过于生硬。在1953年的画作《露冷风静》中,竹的长势也趋于平行,陈之佛巧妙地把周围的物象介入竹子中间,打破了僵硬的程式。山茶花斜向左生长,分散指向上方的动势,梅花小鸟点缀其中,增添灵动之意,点明画面的主从关系。最下面的湖石色调偏重,起到稳住画面的作用。
由于陈之佛重视构图的精妙,大量的创作和尝试使得其在后期绘制大幅且具有多种意象的画作时,画面依旧和谐有序,达到乱中见整、平中求奇、熟中求生、个中见全。这种构图技法的成熟和章法布局的熟练,体现在其后期的绘画中。1953年的《和平之春》是陈之佛后期画作的代表,画中十二只鸽子姿态各异,分组散布,湖石厚重,梅花、山茶、桃花竞相开放,热闹非凡。整幅画面布局饱满却不杂乱,张弛有度,底部用花青及石绿色的湖石稳住画面,碧桃花与桃树穿插得当,疏密相间,体现出一种繁而不乱、和谐有序的韵味。
陈之佛重视对色彩的运用,其绘画风格的素净及后期的明丽与对色彩的合理运用有着很大的关系。陈之佛工笔花鸟画作品的设色,以传统色彩表现模式为基础,兼具工艺美术及西方色彩等元素。(10)赵自然:《陈之佛艺术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2页。他常采用双钩填彩的这一传统花鸟设色方法,但并不似古代花鸟画那样塑造得写实、细腻,而是偏向于平面化的填色,使画面更具装饰效果。“陈之佛擅长运用有色的熟宣纸作画,纸的色彩多为浅灰、米黄、次青、淡赭等淡雅的色调。利用纸的本色统一画面色彩,同时又起到托粉的作用。”(11)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研究》,第96页。通过加粉降低颜色的明度,减少画面中墨色的运用,使画面整体达到明度与纯度的统一。他将工艺美术原理中色彩搭配的原理适配到画面中去,在画作中注意同类色的使用和搭配,由此奠定画面的基调,并通过控制画面各部分的颜色,达到画面色彩的对比和谐。色块的明度、纯度统一和相近色的使用使得陈之佛的画面给人以柔和舒适之感,这种设色的方法给予观赏者“明洁清趣,纤尘不染”的情趣,达到了“艳而不俗,淡而不薄”的画面效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3年之后,陈之佛在设色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画面中运用的颜色更加丰富、明亮,画面中常出现颜色鲜艳的鸟,往往使人眼前一亮。画面中色彩对比更加明显了,朱砂色的色块与花青调染的绿色交相辉映,这种鲜艳的对比使人产生刺激,带有喜悦、活泼之感。在吸收了晚清任伯年常用的靛青色与黄褐色对比明显的颜色运用方法后,陈之佛亦将这种方法应用到画面中,起到稳重画面和突出装饰性的效果,靛青色的湖石与黄褐底色对比明显但不突兀,类似于其他绿色色块与这一颜色相呼应的效果。实际上建国前陈之佛便尝试过这一画法。后期则更加娴熟地使用这一色彩搭配,结合画面呈现艳而不俗的效果。这种绘画手法和绘画风格,在1957年陈之佛所作的《海棠寿带》中体现尤为明显。
(二) 意象取用及画面意境的转变
画家自身的境遇会影响到其对生活的态度,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创作过程中,绘制工笔花鸟画多着眼于使其适应时代,以振兴传统工笔花鸟画。他在技法革新的同时,所要传达的风神旨在“意古”,更偏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清代方薰有云:“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深则深、意远则远,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12)方薰:《山静居画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陈之佛重视立意,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意趣相符,画面常有着文人画的精神气质,传达出洁身自好,高风亮节的品性。他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捕捉生活妙趣,用现代的技法绘制传统的题材,追求诗情画意之美。这类作品常是绘制麻雀、山茶、芭蕉、梅等传统花鸟画题材,主要是技法的突破和与宋人相似的生活情趣的追求。如《梅雀山茶》《蕉荫双鹅》《雀捕螳螂》等作品,常描绘自然生灵花鸟的灵动,生动感跃然纸上。第二种类型是绘制带有象征意味的景物,用来体现画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与品性,常绘有雪景、白鸽、老梅、孤雁,等等,这一类物象往往体现一种孤寒、静穆的意味,表达画家淡泊名利,清高脱俗的品格。《寒月双栖》《秋江双雁》《寒月孤雁》等,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第三种类型则是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典型便是绘于1946年的《鹪鹩一枝》。该画作是陈之佛在辞去国立艺专后抒发愤懑之情所作,画中孤鸟独立枝头,别无外物,树叶微黄体现秋风萧瑟之感,与前面述及的《鹪鹩赋》一文相一致,寓意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
事实上,这三种类型都是陈之佛民族意识、文人倾向之心绪的生动写照。他力图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创新,但处于家国危机的特殊年代。身为革新画家的陈之佛广益博取,将心思放在对绘画技法的研究,致力于使工笔花鸟焕发生机的事业中。花鸟画家对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而陈之佛的作品常有对自然生灵的描绘,生趣盎然而妙意横生,承继了传统工笔花鸟崇尚意境情调的意趣。但他又受时政所影响,清高自勉的文人品性使得他不趋炎附势,借用明丽淡雅的色彩及古人所钟爱的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来抒发其宁静而致远的人生志趣,塑造出许多饱含感伤而孤寂意境的绘画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所赋予的活力及新气象在陈之佛的画面中充分体现出来。他曾说:“孤芳自赏再也不是作画的目的,仅仅追求艺术性,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绝不是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道路。”(13)李有光,陈修范编:《陈之佛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而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中国画,兼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欣赏的作用。旧时代孤高、清冷的文人气象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雅俗共赏的绘画被人们所需要。陈之佛在充满勃勃生机的这一大背景下,心境发生了改变,画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焕发出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
在新中国建国之后,陈之佛的绘画作品可归为一个大的时期,从其这一时期的画作可以看出,1949年到1953年成为其风格转变的阶段。陈之佛这一阶段的绘画作品,所画的题材多为白鹰、梅花、月季、斗雀等,前期冷清孤寂的意象已基本不见,描绘日常生活所见的画作越来越多,如《碧桃腊嘴》《豆荚花》《丝瓜花》等。而所描绘的意象也多带有积极向上,富于进取之心的意味。1949年所作《白鹰》,画面不带有其他背景,一只翎羽分明的白鹰歇息在梅花树上,枝干的长势趋向于鹰的位置,使其成为整幅图的焦点,宾主分明,白鹰目光灼灼、气宇轩昂,整幅画面富有气势,有着昂扬向上的风貌。
第二阶段始于1953年,这一阶段画面转变的分水岭便是陈之佛1953年所作的《和平之春》图,这是一幅显示陈之佛民族性、思想性的重要代表作。相较于陈之佛以往相同题材的画作《和平之春》,刻画的景物变得更多,画幅中六种物象组合,纷纷扰扰,显得更加气派,热闹非凡。象征和平的鸽子姿态各异,徜徉在热闹繁荣的祖国大地上,传达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追求。这种旋律和基调在1953年之后成为陈之佛工笔花鸟画主要传达的内容。这时的陈之佛已突破了传统审美意趣,不落古人窠臼,将时代气息融入其花鸟画作中,创作了一幅幅既有传统文脉延续,又能彰显新时代情感的优秀作品。从此之后,陈之佛的花鸟画便常用大量盛开的花来表达繁茂之景,画面构图偏向饱满,色彩运用更加丰富。
在传统工笔花鸟受到冲击和质疑的情况下,陈之佛用他的作品证实了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花鸟画的积极变革,原本体现孤寂、清冷的题材在他笔下面貌一新,变成了既富有诗意又生意盎然的审美创构。陈之佛1947年的画作《雪雁》与1960年《雪凫》同为雪景,分别用了两只野雁和野鸭做画面主体,却传达出两种不同思绪。《雪雁》描绘白雪纷飞,芦苇残败,两只野雁歇息在岸边,一动一静。雁在古代常有感时伤怀之意,雪景寓意高洁。画上题诗:“昔人有云,清如水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独立高步。直品当做此想,读此语真欲令人搁笔。”这一画作鲜明地体现出陈之佛早期文人画的意境。《雪凫》一图同是以雪景,芦苇作背景,但却不再是萧条之景,一对野鸭停靠岸边舒展身姿,带有积雪的芦苇却迎风傲然直立,瑞雪之中一派活泼、生机之意。画上题诗:“迎腊寒气加,满天风散花。预报丰年兆,粮棉盈万家。”
通过对陈之佛绘画作品的分析,可以认为陈之佛在建国后,通过改变艺术意象的创构,在构图、设色方面做出调整,有意改变了作品的审美意境,使得其花鸟画更加适合时代背景的要求,追求思想性,以达到用花鸟画陶冶情操,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不同时代之所以有不同风格不同感知的形式的艺术,是由于不同时代的心理要求,这种心理要求又是跟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14)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9-170页。陈之佛早期的工笔花鸟画,始于对传统工笔画革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画面传达的是淡泊、雅洁的传统意境;在建国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对于工笔花鸟画要求的改变,陈之佛经过积极探索,使得他的花鸟画呈现出时代的新风貌。陈之佛对于工笔花鸟画的探索和创新,与社会环境的更迭相吻合,体现出其自觉践行“审美随时代”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