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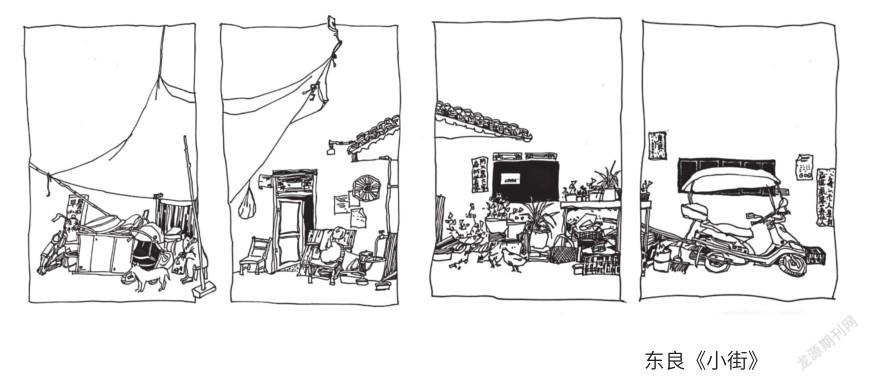
石片在池面轻盈地踱了七步,然后一头扎进水里没了踪迹。池岸上的枫茄花枝叶舒展,我从土堆上鱼跃而起,一个箭步来到他的跟前,收腹挺胸,威风凛凛,像个凯旋的将军。他伸出两根手指捏住我的脸颊,一双汪汪的眼睛时而怔怔地望着水面,时而笑吟吟地盯着我的脸庞。我瞥见他一整只骨感纤美的手,透着初生婴儿皮肤般的白皙。我挥舞着满是泥垢的双臂,对他说:“良哥,你的手,真漂亮呀。”“等你再长大些,自然也会变得好看。”他回答我。
良哥的名字叫姜寻,是他母亲给起的名字,但他恳请我管他叫“良哥”。他说他看到过一则故事,有个叫马良的少年,拥有一支让他羡慕的画笔,可以画出一切他渴望的东西,他也想成为村子里的少年马良。
村子名唤作“鱼泉”,因为毗邻大河,以前是个渔村,村里居民世代以渔为业,后来说是为了解决村县和省城的用电问题,在上游不远处拦了大坝,自此,包括鱼泉村在内的大片河道禁止私自下河捕鱼。村民丢了世代为生的活计,纷纷另谋出路,一些人挎着背包出了鱼泉村,再也不曾回来,但大多数人没能迈出出村的步子,有的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筑湖养鱼,做了渔民;有的开始春播秋收,成了农民。可无论养鱼人还是农民,似乎都与大河断开了关系,昔日亲昵的河水变成了村民眼中恒久不变的风景。
后来不久,村子又迎来了一批迁徙的客人。听我父亲说,她们十多个人,凑成一小撮全是女人的队伍,出现在一个明媚的三月,迎着夕阳朝着村子赶来。村里人得知消息,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聚在村口,出神地望着浸在远方霞光中的身影和轮廓。她们的步态沉重而不失端庄,高雅不掺雍容,仿佛天外仙女降落人间,一尘不染。那天傍晚,她们被迎进村长的家里,经过一夜长谈,便扎根在了鱼泉村。
村里人仅仅从村长口里听到关于她们的只言片语,除此之外,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家在哪里,又为何要来到鱼泉村。但不管事出何因,在那段时间,她们的到来让原本人口凋敝的村庄焕发了生机。只是后来短短十数年的光景,村子里的其他人生活如旧,她们却毫无由来地一个接着一个病倒了,直到我的母亲去世,昔日迁徙的魂魄尽数回归了故里。
良哥的母亲亦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想这或许就是我和他亲昵的缘由。良哥大我四岁,高出了我一个头,有着令我艳羡的体格和绝技。可惜良哥在小学毕业后的那年退了学,我当时心里感到一阵惋惜,连着几天梦到了落魄的他,但我终究没有问过他辍学的原因,揭人伤疤的事让我为难。良哥的父亲是个渔民,我管他叫姜大伯,脾气很大,完全不似良哥的个性,一个似水,一个似火,偏偏成了一对还算和睦的父子。每次他给鱼池里的鱼儿喂完草料,领着良哥从村子口的黄泥道回来的时候,我是既欢喜又害怕,只得慌乱地躲进我家的阁楼,从半掩的窗户远远地观望,看着他们摇晃着愈加高大的身影从村口走来,无声无息地擦过我家西面的灶房,然后渐渐缩成两粒小点,消失在村巷的拐角。
一阵说话的工夫,良哥又一头扎进了山池,水面传出一记扑腾声后便安静了下来,我也不安分地踅进不远处的小树林,麻溜地捡拾起干枯脆断的枝丫儿。等我抱着满满一堆的干柴回来,他手上已经拎着一尾鲜活的大鱼。下水捕鱼,这便是良哥的绝技之一,也是我做梦都想学会的本领,可惜良哥父亲是个养鱼人,他被允许甚至要求学会水下的功夫,而我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下课放学前的第一个叮咛就是不许私自下水嬉戏。我想着良哥在水中畅游的欢乐,应当和鱼儿一般自由,不,应当是比大鱼还要自由,因为良哥比鱼儿还要迅捷,他潜游在水中就如同鹰隼翱翔在天空。我把我心里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了良哥,他又挂起笑脸对我说:“我在水里游,你在书里游,没有什么区别呀,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我还是不觉地揭了良哥的伤疤,往里撒了盐,我不由地闭了嘴,不再说话,像只犯错的猫。他似乎看出我讪讪的窘态,给了我一个熟悉的眼神,提起鱼走开了。
我架好木堆,抽出兜里揉起褶皱的火柴盒,捻出一根可爱的小红帽,划出的黄亮光点引燃了一片赤红,火焰在微风中舞动,在看不见太阳的阴翳的天空下有些灼眼。良哥踱着步拎起处理好的鱼肉折回,这是属于我俩的默契。他把穿着鱼肉的竹棍递给我,朝我说:“你烤得好吃,我喜欢。”我来回烤着鱼,他不时地撒抹盐巴。良哥兜里总是揣着一小包盐,他曾炫耀地朝我说着它的能耐,牙齿、伤口、饭菜都可以撒它,它比鱼儿还要宝贝。
我递给良哥一份烤得半面乌黑半面金黄的鱼,他乐呵地朝我竖起大拇指,我已分不清这是实话还是习惯,但我享受着他的这份赞美,心中涌起绵长的暖意。我悄悄地瞧着良哥,他的腮帮鼓动,眼角闪着焰光,怔怔地望向远方,那是村口的方向,阴云盘在苍穹,高悬的木质牌坊下杂草斑驳,离乡和入乡的黄泥道在那里绵延,穿过晃眼的人工湖泊,蹿出缤纷的果树林,一股脑地扎进了山林丘壑,自此遁迹没了踪影。黄泥道通向何处?丘陵后面是什么?这些问题曾经让我和良哥那么地痴迷,撺掇起无数的遐想与晚梦。我常常把新鲜的梦说与良哥听,有时甚至忘记想说的梦,他从来不恼也不追问,他告诉我,如果忘了做的梦就告诉他一种颜色,一种代表梦的颜色,他就能找到我遗失的梦境。他用两根手指夹起树枝绘出梦的轮廓,用树叶和花草润出色彩,黄土地上现出一个杂糅斑斓的梦图,有我的也有他的,是我和良哥共有的。我欢快地跳跃高呼,想告诉所有动物和植物一个秘密,良哥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家,一个比马良还要出色的画家,唯独少了一支神奇的画笔。
黄泥道的归宿是丘陵,丘陵背面是大河,河道上汩汩东逝的水流喧腾,这是我和良哥第一次寻梦的收获。那一次,天依然阴沉着脸,良哥带着我翻过村子侧坡的土墙,沿着田埂一路小跑,绕了大半个弧线插进黄泥道,悄无声息地出了村子的地界。溜至山丘脚下,我颓然地驻足于戛然而止的黄泥道上,却瞥见良哥闪着清光的眼睛,如初春新笋般乖怜,惹得山泉湖雨尽数藏进了他的眼里。他轻柔而坚定地朝我说:“小凡,你先好生歇息,歇息好了我们翻过去瞧瞧后面的世界。”半晌的工夫,丘陵中浮现出两只状若稚鸡的身影,蹦跳啼叫间跃入了葱茏的峰顶。我和良哥跳上山丘顶处的岩石,四周苦艾草香袅绕,鲜绿的苔藓匐在脚底,七月的岚风夹携着浓厚的水汽袭来,隔着黏稠的空气,我和良哥第一次望见了家乡的大河。两叶小岛横卧于河心,苍茫的水面映出阴云的灰白,绵长的河道一端衔在远山,一端冲出沃野,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这一幕来得猛烈而隽永,我仿佛听见了心间猛烈的颤音,全身肌肉无法抑制地颤动。待到疾风间歇,耳畔传来良哥急促的呼吸声,我侧过头,看见他的胸膛剧烈急促地起伏,脖颈之上的整张面庞通红一片,唯独两颗明亮的眸子直挺挺地盯著河水。我读出了良哥心中的炙热,拉起他的手朝下疾行。离河岸愈近,良哥的步子愈加欢快,待到踏上河岸,方觉原隰郁茂,草木葳蕤,我们沿着河岸奔跑,河心的两叶小岛在视野中不断倒退,在粼光闪闪的河面,在波光漾漾的眼里,游过大鱼背鳍划破水幕般的倩影。
河水东逝,我们一路向西,越过拦河的白堤,不觉间拥入了群山的怀抱,逐河而上,河岸山势陡增,四周倾泻的水流重重地砸下,礁石上密密麻麻的坑洼肉眼可见。我们的耳边充斥着轰隆隆的脆音,昌茂的树冠下浓厚的水雾弥散腾袅,四周稀疏残存的几缕光柱渐渐地淡了下来,眼中全是灰蒙蒙的一片。不知行了多远,轰隆的巨响声消颓,渐闻水声潺潺,密林中山涧溪流暗生,支又分支,甚是繁杂。脚下的草地水流漫溯,我们脱掉浸满水的棉袜,揣进口袋,然后趿拉着布鞋蹚水玩耍。继续前行,灰蒙蒙的水雾愈加深沉,周遭模糊的微光完全消匿。我已经分辨不清前方的路,只得停下踱行的步子。黑暗中,良哥拉起我的手摸黑前行,不知过了多久,良哥身上突然泛起淡淡的柔光,我抬起头惊奇地望向前方,无数萤虫在密林中飞舞,参天的树冠垂下藤蔓,鲜红的树根渗出幽绿,光滑的滩石开出花瓣。清净的河面下藻荇招摇,一尊尊晶莹透亮的鱼儿不时在眼中闪现,有的游弋在水草之中,有的爬上垂悬的藤蔓,有的生出翅膀冲出水面。良哥眼中泛起清光,褪下衣衫跃入了水中,空中淡香的葱兰花瓣开始纷飞,成群的鱼儿朝他聚拢,斑斓的气泡缓缓浮出水面,他们时而潜在水中畅游,时而匐在河底呢喃。我拾起良哥的衣衫轻轻地跟在身后。
直至脚力疲颓,良哥领着我无声无息地摸回了村里,谁也不曾发现我们的这次冒险,我和良哥之间又多了一个秘密。此后的日子,我和良哥就像两只馋嘴的猫,时常惦记起装进心里的大河。我们用眼睛描摹,在梦境中添枝加叶,然后把它们绘成一幅幅沙画。
良哥收回远眺的目光,手里的烤鱼只剩得一副骨架,我们捧起沙土盖住火堆,跳脱的余焰渐渐蔫灭。他又说起了住在他心房的姑娘,我们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林中回荡。
几周后的一个黄昏,我伏在客厅的木桌上写着作业,父亲正仰靠在一旁的竹椅上养神。我不经意间瞥见一个身影靠在我家客厅的窗户外晃动,窗户上糊着的剪纸窗花遮住了他鼻翼以下的半张脸,露出的两只眼球来回朝着一侧的眼角跳动。我立马就领悟了良哥的暗示,轻轻放下手中飞舞的铅笔,缓缓合上泛黄的小学课本,悄悄地溜出了我家的大门。我们爬上后山的坡顶,看着太阳沉入西边丘陵,天边浮现起连片暈着金黄的霞云。良哥没有说话,但我从他涣散的眼神中能感受出他刻意压制的慌张,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良哥如此怪异的神态,我脑海中极力推测良哥变故的缘由,却始终理不出头绪。良久,我疑惑地问道:“良哥,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以和我说说吗?”他听着我的话,涣散的眼睛多了一丝生气,片刻的沉默后,紧闭的嘴唇微启,柔声地对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很真的梦,但早晨醒来后我却忘记了昨夜我做了梦,我像以前一样跑去湖里给鱼儿抛下草料,在回村的黄泥道上突然想起了我昨晚做过一个梦,我极力地回想,却怎么也回忆不出梦的内容。”“那你知道梦的颜色吗?你或许可以试着把它画出来。”我问。他摇了摇头,眉头微蹙,说:“我现在也说不清梦的颜色,自然没有办法画出昨晚的梦境,我能记得的东西只有一个,那是一种声音,一种以前从未听见过的声音,陌生中又夹杂着几分熟悉的感觉,像是婴儿的啼哭,又好似某种遗失的语言,低沉而深远,但我却如何也无法理解,它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回荡在我的梦里。”良哥画过无数的梦,具象抽象,可爱恐怖,深沉洒脱,这些我都见到过,并曾一度为之雀跃欢喜。他似乎有着进入虚幻和现实世界大门的钥匙,寥寥几笔便可以勾勒出两个世界的轮廓。但此刻,那扇连通梦境的大门顷刻间轰然崩塌,良哥被决然地拒之门外,我似乎明白了良哥的慌张,不禁心生几分疼怜。我伸出一只手搭在良哥的手背,希望传递给他几分振奋的力量,籍此寻回关于出逃的梦的记忆。可惜直到霞光消逝,夜色初显,我们踏上下山的归程,良哥依旧浸在淡黑的光里,异常沉默,我望着他的背影,只觉得阵阵冷黑如潮水向我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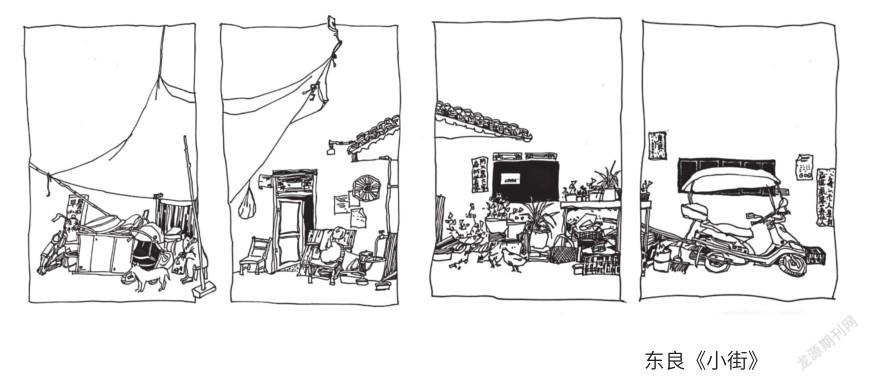
此后的很多天,我始终未曾见到良哥,只偷偷地瞧见每天往返鱼池和家里的姜大伯。蜿蜒的黄泥道、木质的牌坊、斑驳的杂草、灰白的灶墙,唯独少了良哥的身影,一切显得熟悉而乏味。我开始在期待和焦虑中徘徊,几周的时间又悄然地逝去,依旧没有等到良哥到来,却无意间听到了街坊关于他的家常。她们带着惊恐的语气说良哥正生病卧床,已经大半个月了,得的还是同样的肺病。我的心猛地一缩,久远的记忆和确凿的未来在滚烫的空气中弥漫,口肺间霎时涌起了强烈的灼痛感。我冲上我家的阁楼,把自己藏进逼仄的房间,掩上糊着薄纸的木窗,颓然地坐到地上,看着地面久未清扫的尘埃纷扬,羼入一束束被窗柩裁剪的光里。我挪过身子,睁开眼睛直视已显羸弱的光芒,却依旧照得眼睛干涩生疼,我眼角一阵湿润,一如五年前盛夏的那个午后。那一年,我还是初谙世事的年纪,入学的新奇和胆怯交织于我的生活,课堂的拘束和课后的作业令我烦躁。那一天,正午的太阳又大又红,毒辣的阳光如骤雨泼洒,正在课堂上打盹的我被父亲匆匆地领出了校门。回家的路上,父亲的步子迈得又急又大,我几乎是被父亲扯着跑回家里。我松开父亲的手冲上阁楼,隔着墙壁,我和她急促而深沉的呼吸声紧紧地交叠在一起,牵引着我向她走去。我熟悉地踅进母亲的卧室,蹲在床前握住她的手,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纸框住了我的上半张脸,照得我的眼睛生疼。我不停地问着问题,渴望着她能给我一声回应,但她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只剩一双清亮的眸子睁着。我循着她的视线,望见了对面墙壁上悬着的老物件——数寸大小的粗木相框泛着黄光,里层夹存着一张看似久远的黑白相片。画中灰黑的沙洲悬于乳白的苍穹之下,被无垠的水面揉成一粒砂石,又在灰白的女人像中延伸出真实的伟岸。水天之间,无垠的水面泛着涟漪,无数的气泡浮出水面,在空中升腾膨胀,汇成了铅白的云朵绵延。沙洲汀岸,一树海棠矗立,海棠树梢,沙鸥翔集,海棠花下,锦鳞嬉水。我再次被这幅相片中熟悉的画面所迷住,但并非由于扑面而来的岁月沧桑,而是那种恍若前刻的亲昵和哀婉,即使多年的时光消逝,这种感觉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我曾许多次问过母亲关于她在村子之外的故事,她总是重复着她们跋山涉水来村子的旅程,除此之外,我只能对着这张比我年龄还大的相片编织可能的想象。可是那刻,死亡的恐惧将它们从我的脑中一帧一帧地抽离,我的脑海中没有了关于它的幻构的画面。其实我并不清晰死亡的含义,只能借助诸如“悲伤”“沉眠”等字眼来修饰它的存在,或者把它置于生的对面,借此揣测它不为我知的一隅。肺病带走了母亲的生命,也带走了当年与她同行千里入村的同伴的生命。它用一个又一个消匿的面孔和记忆向我诉说着生命的哀婉与短暂,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类似腐烂的味道,我嗅着气味前行,最后发现这味道的源头竟是鲜活的生命,原来生命的外表不是鲜花绿草,也不是杨柳白絮,只是枯槁般一味地腐朽,直至生命的尽头。
转过两个拐角,村巷里忽然灌满了疾风,良哥家虚掩的大门被刮得扑哧作响,我壮着胆子踏进了良哥家。越过空荡的天井,我碰见了略显倦容的姜大伯,他正坐在内屋门楣下的矮板凳上大口地抽着水烟,他的眼睛透着丝缕彷徨,刀削的面庞添了几分柔和。白茫茫的烟气在他口中不停地吞吐,风中弥漫着水流翻涌和气泡迸裂的声响。我刚开口叫了一声大伯,他便把头扭向了连着扶梯的阁楼,示意我良哥的位置。我爬上阁楼,从半掩的门缝钻进了良哥的卧室。空荡荡的房间陈设简单,一台赭红色镶花衣柜、三五只红漆木椅和一盏实木雕凿的圆桌齐整地立在墙角。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洒进房间,久久定格在木质妆台的一块半人高的方镜面上。良哥正躺卧在垫着棉絮的棕榈床铺上,健硕的身子仿佛被绳索牢牢束缚,无法动弹丝毫。我凑到良哥的身侧,他发红的脸颊透出苍白,倦怠的眸子泛着清光。我看着良哥尽显疲颓却无比宁静的脸,仿佛前些日子的彷徨已经消失殆尽,我的脑海在片刻中涌起无数想说的话,却终究咽了下去,不忍地扭过头望着床尾的妆台。我斜眯着眼睛盯着那块半人高的方镜,它直直地反射着金黄的光线,照得整个房间亮堂堂的。我看不清镜子中任何的映像,它像个歇业的店铺,闭上了门,不再见任何顾客。我不由闭上眼睛,紧闭的眼中仍能辨识出周身模糊的微光,但渐渐地我只觉四周一片冷黑,唯独镜子和良哥发出明亮的光辉,如同寒夜中的火炬,温暖而明亮。我任由自己堕入无限荒诞的想象,借此淡漠掉翻涌的情绪。疾风刮跑了整个下午的时光,窗外竹林的呜咽声完全掩盖了良哥单薄的声线,我听不见任何语言。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趁着月色赶来,沉重的步子踏碎了满屋的星辉,他拉起我的手将我领出了良哥家。回家的路上,一轮圆月高高地悬在天际,父亲紧握着我的手沉默不语,我低着头踏在斑驳的树影上,耳边拂过一阵温柔而熟悉的嗓音,然后被风儿带出了村庄。
仲夏夜,入梦。我推开窗子,窗外细雨绵绵,氤氲的水雾罩住了田野屋舍,遥远的风拂来淡淡的鱼腥,偌大的村庄一片阒然,人影匿迹。我听见,一声大鱼的低吟划破大河深稠的寂寥,越过丘陵,沿着泥泞的黄泥道曲折向前,拂经果树林,掠出人造湖群,然后穿过木质牌坊钻入村巷,九十度左拐再右拐直奔良哥家,从紧闭的大门下面潜入,绕过无人的天井,紧贴台阶攀上阁楼,穿过浮着姜大伯鼾声的松木长廊,最后出现在卧室,良哥正躺在床上辗转呓语。大河,良哥从浅梦中惊醒,喊了起来。他寻着声音溯源而上,走出卧室,经过松木长廊——姜大伯的鼾声间歇——接着跃下阁梯穿过一个个房门,径直走到村巷,九十度右拐再左拐没入黄泥道。我跃下阁楼,踏上湿滑的黄泥路,循着良哥的足迹而去,身后静谧的村庄渐渐隐匿于白茫茫的水雾之中。不一会儿,雨势渐密渐急,已是滂沱的大雨砸下,四处奔涌的雨水冲散了良哥的印记,我已寻不见他的踪影。我停住艰难前行的步子,待在原地彷徨许久,四周豆大的雨点开始交连成线,然后汇成连片的雨幕将我包围,我开始感觉呼吸有些困难,用手捂着嘴鼻大口地喘着粗气。突然,我望见一尾蓝色的团影划过,它所过之处成片的水幕如垂帘般被拨向两侧,四处逸散的空气重新朝我聚拢,我追随着它继续前行,脚下的步子愈加轻盈,双脚似乎出离了地面,但每一步都传来强劲的脚力。我走得很快,如鱼一般迅捷,可我总是赶不上前方那团蓝色的糊影,无论加速还是减速,我和它之间的距離始终不曾改变,就好像太阳追逐月亮,可望不可抵达。我只得瞪大眼睛远远地望着它,却依旧看不清它的样子,它始终包裹在水簇之中牵引着我。不知行了多远,天空的雨幕渐渐消颓,连绵的雨线又重新断开成豆大的雨点坠落,那罩在水中的糊影也不见了踪迹。我环顾四周,良哥熟悉的身影又重新映入我的眼帘。他愣愣地伫立在河岸,我大声地呼喊,迈开步子朝他跑去。来到他的身后,我躬起身子大口喘着气,身侧是泛滥的大河水,密集短促的水纹荡漾,仿佛无数的睡眼惺忪。良哥转过身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没有说话,我抬起目光,硕大的雨点溅落在良哥的额头,划过异常突出的眉骨,尽数涌进了深凹的眼眶,刹那间被圆鼓鼓的眼白翻起,在空中一阵绕卷后跌落到拉长内陷的脸颊,旋即汇聚于尖锐的下颚底后破口下坠。我惊诧失语,定睛细看,他两颚的牙齿上下翻卷蔓延,化为无尽错落的鳞片,一呼一吸间晕散着周遭的白光。我仿佛被眼前良哥的模样摄取了魂魄,呆呆地伫立在原地,无法言语。许久,砰朗——啪嚓,我听见一阵清脆响亮的碰撞声,犹如镜片碎裂然后坠落地面的声音,紧接着良哥跃入了清冷的河面,无数的气泡开始从河面升腾飘飞,视野中浮现出一顶耀蓝的背鳍,无息地划破平展的河面。良哥消失了,我的世界只剩下不停歇的风声与雨声,以及河面上一条串起浮泡的水线。
窗外下起了雨,嘈杂的人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翻身下床,提起伏在小桌上的画笔,开始描绘一个经年的画卷。
作者简介
李一鸣,1999年生,厦门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范姝
——存在主义视域下《黄泥街》的叙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