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外一篇)
胡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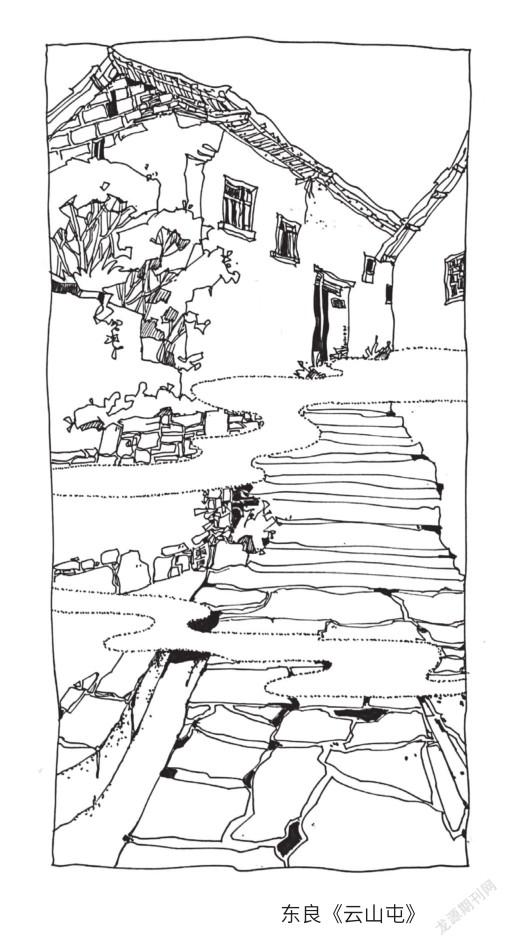
一
今年春夏之交我返回母校,拜访高中的老师。我带了两本自己的诗集,教地理的班主任接到手里后对我连连称赞,他不知道我经常在他课上偷偷写诗。语文老师接到后摆摆手说“你知道的,我不懂诗”。他也没有装模作样拆开翻一翻,就随手插到书架里面了。他满脸皱纹,离退休也没几年了。个子中等,瘦,驼着背。他瞅着我,吸了一下鼻子,问些在不在作协、发过哪些期刊、认识哪些文坛名流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当然不能给他什么惊喜,反而让他担忧我文学前途渺茫,转问我工作稳不稳定了,在大城市起居怎么样。我们这才聊得高兴起来。
在办公室聊到日暮,他看了眼工作表没什么事情,邀请我去他家喝点酒。我也没什么事情,欣然随他去了。他住在附中的老家属区里,里面的房子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上爬满了藤类植物,爬得高的仍是鲜绿,被彩霞红红地映着,和人齐高的则几乎都是些灰朽的死藤,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像现代艺术。我的语文老师名字叫李炎,和我算是老乡——他是永州人,我是茶陵人。这个老乡认得十分勉强,因为永州挨着广西,茶陵挨着江西,地貌和方言非常不同,而且他比我年长四分之一个世纪。李老师在我出生那年本科毕业,留在附中教语文。我读高中时,以老乡身份套近乎,找李老师讨教诗歌问题。李老师自称不懂现代诗,还发了通莫名其妙的感慨:“现在还有诗人吗?”这种感慨我在高中时就厌烦至极。但我没有因言废人,讨厌李老师。李老师的课很有意思,他会讲很多来自故乡和童年的怪力乱神的故事。本地同学对那些外省故事并不喜欢,甚至有些听了夜里做噩梦,私底下抱怨这个老师。李老师的那些民俗故事让我感到亲切的野性,和我父亲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起讲故事的技艺,我父亲就比李老师差了太远——他总是想要提炼出来一些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般的道理——然后扯到我近些日子做得不妥当的事上,教育我一番。不过,如果我是李老师的儿子,李老师可能也会这样对我。李老师没有结婚生小孩,所以无从证明这个猜测。但他在所有同事都结婚生小孩的环境里,是如何自处的呢?当我胡思乱想时,已跟着李老师走进感应灯坏掉了的黑漆漆的楼道。他的肩膀在黑暗中危耸,踏出使者般庄严的足音。
他拉开绿色的铁门,在尚未全黑的客厅开灯,顿时明亮地照见房屋的整洁,而且有点空旷。桌上有英文小说,还有些和工作相关的文件。李老师说:“不用换鞋。”他踏着运动鞋直往里走,感慨一句:“你也一直是文学青年啊。”我说:“当年语文课熏陶得好。”这话当然是场面话。但李老师忍不住笑了,笑得很开心。到书房我们坐下来,我环顾周围的两面书架, 里面都是些很老的书和杂志了。这些书架里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像穿越了一样。但李老师不是古板的,他已经拿起手机点了湘西菜的外卖,还贴心地给我点了啤酒。他知道年轻人喝不惯白酒,但他家里只有白酒。总之,李老师太不像一个高中老师了。那家湘西菜来得很慢,他自己先忍不住开始喝书桌上的牛栏山,杯子都不用。他喝了几口,变得更加放松,站起身拉开书柜,从里面缓慢地抽出两本杂志,分别是1994年6月刊的《宝石文学》和1995年秋季刊的《悬挂小说》。《宝石文学》现在还是大刊,《悬挂小说》我没听说过。他哗哗翻动,指给我看,那个“炎帝”就是他。我看到这个笔名心里发笑,但细细读下去,小说本身却是细腻微妙的。李老师说,《宝石文学》上这篇不得已被删改了很多,不好;《悬挂小说》上面这篇好。我粗略读完,感到还是《宝石文学》的好一些,更温和。我向李老师表达了这个看法,他笑道:“你们这代年轻人太保守了。”
我问李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小说?”李老师摇摇头,说:“没有了。”我补充说:“不是说发表的,没发表的还有没有?”李老师说:“没有了,我就写过两篇小说。”我表示不相信。李老师说:“后来我写不出来了。”我坚持不相信而且大呼小叫:“那你在课上讲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啊!”李老师说:“那不是我自己的,我写出来也不是。”即使才情如李老師,也不影响他和他那代人一样顽固。我不依不饶:“那总是写过吧,写了一半但是不写了。”李老师总算承认有这种情况,但也是二十年前了。他说:“近二十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但我一直在语文课上给学生讲故事。那些历史悠久的,我的父辈和兄弟编造的故事,比我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有意思。写小说还是太知识分子气了。读的人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你们这种极少数的文学青年。你看,谁还读小说啊,谁还读发在期刊上的小说啊,想到当年我在期刊上发小说那沾沾自喜的样子,和草包一样……”
李老师没喝多,他说得很诚恳。但我实在没法认同这个,我自己也在写小说,而且一篇没有发表过。李老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过两篇,随即好好上班,不再创作,现在说想在期刊上发表是草包,实在很不厚道。这时候湘西菜外卖到了,我们转移到客厅吃饭,他打开外卖盒就骂不正宗,骂骂咧咧地和我吃了一顿。吃得有点热了,他打开客厅的电风扇。电风扇在那里嗡嗡嗡地摇头,我大口大口地喝冰啤酒。说实话我吃不出来那个湘西菜正不正宗,茶陵菜不是这个做法。我对李老师说:“你知道我老家那边做菜有多野吗?炒鸡里面都是有鸡毛的。”李老师大概觉得我吹嘘这个很幼稚,他没有接招。但沉默一会儿后,他很突然地开始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而且特意强调:“我要给你讲一个亲身经历,我自己的事……”
二
我故乡的村庄藏身在山里,但离县城不远。村庄贫穷,我的家庭算优裕的。父亲懂一些文化,给公家算账;母亲是纺织工,在县里工作。因为母亲的影响,我很小就会刺绣,家里人也不认为男孩刺绣是可笑的。但这种兴趣爱好所养成的性格确实不合主流,导致我不是一个能和同龄人打成一片的孩子。我乐意跟着他们玩耍,但不能是同去偷花生,也不能是去河里戏水、摸鱼。这些事我做不来。我只是和他们一起去村小学旧址玩,那里有一架秋千,绑在一棵据说有几百年树龄的大树上。那秋千有多少岁月也不得知,我的父亲小时候就在那里荡秋千,也在那里念小学。我们这一代孩子没有在村小学那里上过课,但都知道那里有秋千,绑在村子最古老的大树上。村小学、大树、秋千都设在一处高坡的平整处,这平整处像一座空中的孤岛,一面通向山径的大道,三面的边缘之下是十米深的断崖。秋千当然也朝向断崖,但你坐在上面不会感到危险,你的手会把那坚固的铁链握紧,而且手指可以完全嵌进铁链的环扣。一开始你的手感到冰凉,但没荡多久那铁链在你手中就温热起来。金属的秋千绳看起来笨重,但这高坡的风太大了,只要你用力推动一下那秋千,不用再推,它就可以无限地回荡在风中。在我五岁那年,小学堂搬到了断崖下面的另一片平整处,但那个平整处的三面边缘,还是断崖,风还是那么大,新修了间小图书室,没有大树和秋千。我们如果想去荡那个秋千,就要往高处走,大概二十分钟的路程。那架秋千一直是村里孩子的乐园之一,另外两个乐园是田野与河流。对于我,秋千所在的高坡是唯一的乐园,它还多了一处完整的建筑废墟,里面有许多宝藏、玩意,虽然都是成年人认为没必要带走的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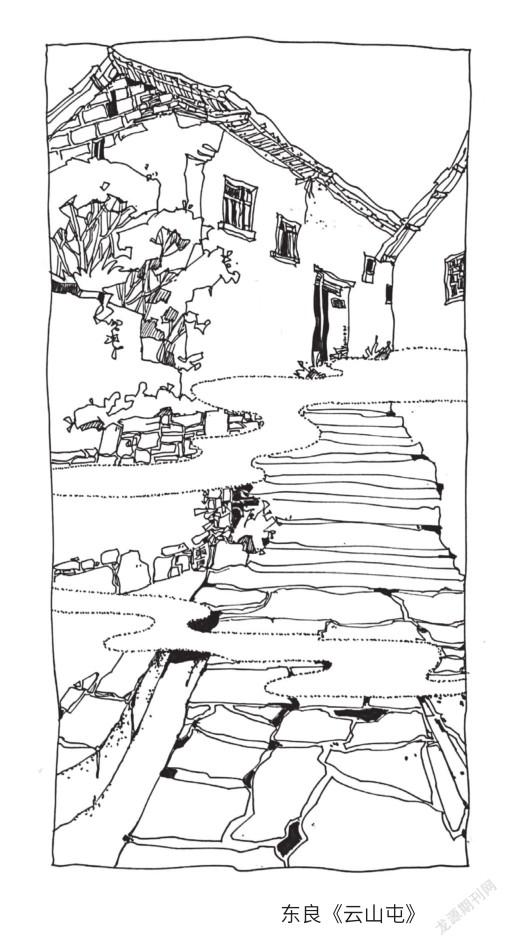
因为那秋千几乎可以在高风中永动,所以一般没有人会独自去玩那架秋千,因为需要同伴去帮忙制住铁链,减缓它的加速度,荡秋千的人才能稳妥地下来。当然也有比较勇猛的,当秋千回荡至高坡的低点,支起身子跳下来。最初这么做的男孩是王天虎,在他上三年级那年,赢得满坡喝彩。后来大伙发现这并不难,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们终于都学会了,女孩中也有两三个胆大的可以做到。除了我始终没有胆量,都是呼唤邓晓林帮我扶住铁链。邓晓林不在时,我就索性不玩秋千。
我在秋千場上如此依赖邓晓林,但邓晓林不是我特别的好友。实际上我和他一点也不熟悉。邓晓林和我们所有人都不亲近。他年龄比我们大两岁,身为班长,成绩向来是年级第一,沉默寡言。但他的沉默寡言和我不同,他是一个正气缠身的人,他的沉默寡言被认为是一种严肃,是一种领袖式的不苟言笑。所有同学有难处,他都会沉默寡言地帮忙解决。我荡秋千无法自理的问题,他也当然会帮忙解决。由于是他这样的人帮忙,我每次也都郑重地道谢,从来没有产生过和他拉近距离的感觉。但或许正是因为常常依赖的是邓晓林,其他玩伴从来没有笑话过我十二岁了还不能自己从秋千上跳下来。
那架秋千屹立多年,铁链依然像新修的小学堂般崭新,而且从未有人因为它发生意外,跳下来摔伤的都没有,可谓安全的奇迹。要知道村子里每年都有在河流里淹死一到两个孩子,田野里也出现过毒蛇咬伤不治身亡的个例。可是在上我六年级的春季,秋千乐园的安全奇迹也终结了。那天阳光和煦,我因为帮家里做事,上午没去学校。下午本来该去学校,但我也打定主意不去了。父母午后出门,我假装同路出门去上课,却又折回家去。我折回去干吗?去完成那面刺绣。可家里我四岁的弟弟太吵闹,他被关在父母的卧室,出于无聊不断地制造噪音。我不可能和他沟通,因为如果他知道我在家,一定缠着我玩,我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告我逃课的状。我离开了家,到有秋千的高坡上刺绣了。我坐在从那个废墟里搬出来的一个小板凳上,一针一线地勾勒起来。我在绣两只张开小翅膀的麻雀。绣了一个多小时,邓晓林来了。
邓晓林为什么会来,是来抓我回去上课的吗?我提心吊胆,比起同龄人、同学,他在我眼里更像是大人、老师。他和我对视一眼,非常短暂,又把目光移开。他坐到那架秋千上去。我脑子转过弯来,邓晓林也是逃课——他逃课来这里荡秋千?事情非常诡异,我把手中的刺绣放在膝盖上,看他荡秋千。我诧异得说不出话,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太缺乏说话的锻炼,声带退化了。我站起身,想去给邓晓林推一把,邓晓林已经用自己的双腿把秋千驱动起来了。秋千回荡在风中。我憋了半天总算发出了询问的声音:“班长,你为什么不去上课?”这话问得很可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可笑了,严肃的邓晓林没有回应我,也可能因为他耳边只有呼呼风声。我坐回板凳,看他高而瘦的身躯像端坐在课桌前那样端坐在那截阔大牢固的木板上,他已经十四岁了。我那时候还很矮,别人看我像只有十岁甚至九岁,我不到一米二。我没法一直盯着那架回荡的秋千,耀眼的日光会打断我。我低下头刺绣,时不时抬头看看邓晓林。但后来绣到翅膀的纹路我全神贯注起来,很长时间没有抬眼。我不知道那两次抬眼间隔了多久,但邓晓林不在秋千上了,秋千当然也悬在离土地一尺高的半空,被风吹出微弱的摇晃。邓晓林什么时候回去了?我依据太阳的位置感受时间,估计正是接近于放学的时间,我也应该回家去了。但我回得稍迟一点,我坐在那里把刺绣完成了,一幅漂亮的麻雀迎春图。但我怎么没有听见邓晓林从秋千上跳下来时,鞋底与土地响亮的摩擦声呢,可能是绣得太入迷了。邓晓林为什么逃课,这个困惑也没有在我心里停留多久,这天我沉浸在刺绣的欢喜中。晚上,村里的两个干部来到我家,问我们知不知道邓晓林的下落,说这孩子失踪了,下午就没有到学校去,一直没有找到他。其中一个干部指着我说:“李炎,你下午也没有去学校,你和邓晓林一起的吗?”我见逃课的事情已经败露,也没有遮掩的办法,只好老实回答:“是的,我下午逃课去高坡上刺绣了,我刺绣时邓晓林过来,他去荡秋千,他荡完秋千应该就走了,我反正没看到他,刺完绣我自己回来的。”干部记了一下我的说法,随后继续去挨家挨户问了。而邓晓林的父母以及族人,包括他们的一些朋友,四处找邓晓林,都找到了隔壁村子的田野与河流了。
第二天,他们走进了山里,在秋千架断崖下面的树丛里找到了邓晓林的尸体。邓晓林无疑是摔死的,而且没有立刻摔死,他显然在坚硬的土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因为他的身躯不是蜷缩的,而是展开的,一只手朝向树丛外面的路径,在爬。
最后一个目击邓晓林的人是我。这个信息不胫而走,一日之内传遍了整个村庄。我的父母和族人当然不相信我会行不轨之事,因为我是那么乖巧,但邓家那边则对我满腹狐疑。于是在这天晚上,干部、老师和警察就一起找上门来,审讯我是否加害于邓晓林。我急得大哭,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怎么无辜,毫不知情,而且说了很多现在想来与案情无关的事,比如邓晓林成绩很好,品学兼优;又比如自己下秋千架不能自理,邓晓林如何帮助我下秋千。我的反应其实是很反常的,为了洗清嫌疑,我和平时那种怯懦、退缩、羞于说话的形象判若两人。老师第一次听见我说那么多话——即使并不利索。我的嫌疑并没有因为证词洗清,但我还是照常要去学校上学。老师首先就认为我有嫌疑,因为邓晓林总是年级第一,而且品学兼优。我成绩在三到五名浮动,能否升上乡镇的初中是未知数,因为这所小学能升上初中的每届大约四人。邓晓林被除掉,我就很有机会。那位老师没有在班里表达过这个观点,我也从未想到过这个观点,但后来到我家里向我审讯的民警却抛出了这个观点,我一下子明白自己是如何被老师看待的。
这是多么悲哀的往事,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被民警审讯了半个月之久,而且没有因此洗清嫌疑。这半个月民警不是每晚都来,但每晚我都提心吊胆,仿佛自己随时会被抓到监狱里去,然后遗臭万年。民警的审讯也并不严厉,实际上,他比起村民们温和得多,他不太相信我是凶手,因为我长得实在太小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害怕这位叔叔,即使他后来基本没有来问我这件案子的事,而是和我打听邓晓林在同学间的表现,以及今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我即使积极配合办案,也想不出太多关于邓晓林的信息,我关于他的记忆,几乎全在那高坡的秋千上了。在一个晚上,民警和我说有需要时会再来询问我,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家里。这突然的消失更带给我巨大的折磨,因为他并没有开一个全村人都要参加的大会,和他们宣告,李炎是无罪的,邓晓林是自己不小心从秋千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一直盼着这样的宣告,但没有发生。当然我也没有去坐牢。这件事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暂定为事故死亡。
很多年后我才接触到“疑罪从无”这个词,但这个“无”指的是“无须坐牢”,而不是“无须被怀疑”。邓晓林的死给邓家蒙上巨大的阴影,给我也蒙上巨大的阴影。虽然我们两家一家住村西,一家住村东,本来就无甚交集,但这个事件以后,疏离演变成冲突,酿成许多丑事。而伴随半年后我考上初中,而邓家有史以来最会读书的孩子却英年早逝,这矛盾达到了极点。我的大堂哥被邓晓伟打折了一条胳膊,一个星期没法上工。随即的报复活动在村庄持续下去。我的父亲也辞去公职,跑到县里工作,为的就是避开祸端。我的弟弟升入小学,没少被人欺负、恐吓,他是这件疑案中活着的最大的受害者。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我在乡镇中学的班上,我很快就成了人人白眼的阴险之徒。在我們那里,你如果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把前途无量的苗子陷害了,你就是该遭雷劈的。但好在那时候人人都想好好学习、出人头地,所以也没人来专门整我。那是我不幸中的万幸。为了离开可怕的故乡,我拼命读书,想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那里就没有知道我往事的同学。后来也如我所愿,我摆脱了邓晓林的死,摆脱了故乡……
这件事想来,是非常悲哀的。那架秋千那么牢固,从来没出过事,为什么是最优秀的孩子邓晓林死去?在我升上初中不久,那架秋千被拆掉了,那坐小学堂的废墟也被彻底清空,那片高坡的平整地于是只剩下一棵巨大的树,显得它非常孤寂高旷,因为再没有小孩去那里玩了——当然不是因为有人死,而是因为没有好玩的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回乡办父亲的葬礼,还故地重游,去拍了那棵没有秋千的古树。在相片里,那就像是无风之地,那棵粗壮的树和它的树枝都不被吹动,相片里没拍到我随风颠倒的长发。总之,我的族人受了邓晓林太大的苦,但他们从来都相信我是无辜的,也没有因为此事因我而起责备我,只是支持着我一路考试,离开这倒霉的故乡……
三
李老师讲这件亲身经历的往事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兴致只持续了一半多。我首先听完不太相信是一件真事,怀疑它只是一篇口述的小说,或者说有原型,但不是发生在李老师身上的。我不相信李老师身上发生了这么沉重的事,他的讲法也不太沉重,尤其是讲到他被村民锁定为嫌疑人后的生活,讲得很潦草。而且逻辑完全是很老土的,那一代人的,靠用功读书改变命运,离开封闭愚昧的乡村,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
但我不想戳穿李老师,我希望李老师能把这篇小说写出来。于是我感叹它是多么有趣的故事,如果写成小说就好了。李老师说:“这写成小说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出名了,被我老家的人读到了怎么办,被邓家的人读到了怎么办……”我立刻讽刺他:“你想得可真多,你不是说期刊没人看吗?还担心这些。”
李老师脸一红,解释说:“不一样的。”他又低下头,沉思起来。
我恍惚感觉李老师实际上有可能是不是真的曾把一个同学从那架秋千上推下去过?
这感觉只是一刹那,却让我害怕起来。
我于是问:“你现在还刺绣吗?”
李老师说:“早就放弃这爱好了,但我针线活很好,闲来毛衣都是自己打。”说着就像变戏法一样指给我杂物堆里的一团褐色毛线球,好像是他一指就变出来的。
我放轻松了许多,拿起啤酒喝了一大口。今晚应该是愉快的。不要想邓晓林了。
我开始想起秋千和绑秋千的铁链,想起一棵很高大的树。我想起来叶琮,他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同学,人长得瘦瘦小小,像猴儿一样的。我想起小学的操场后面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有两棵大树。两棵大树间绑着铁链,铁链下是木板。左边的那段木板是叶琮的秋千。那一天,我们班在操场自由活动。独自荡秋千的叶琮从高台飞出,摔在操场边缘的砂石上,脑袋上的洞汩汩地涌出血。中断的丢手绢游戏,混乱的操场。我们互相跟随簇拥在抱起叶琮的老师身边,着急地叫喊:“快打110、120、119!”第二天,班主任告诫我们:“不要去高台荡秋千。”我和其他几个男生放学就去高台,坐上叶琮的秋千,看到眼皮下的血迹。我们都握紧铁链,也只敢轻轻荡起。一天就丧失对秋千之力的把握,很快就觉得没有意思。很快学校就把两架秋千拆了。没人知道叶琮的下落,他没有回到班里上课。他头上缠满绷带,缝了很多针,和我说关于秋千的灾难。那是梦里的片段。叶琮的长相也熔化到绷带里了,逐渐我只记得那摊血的形状。有时会在一片黑暗里绽放,耳边又响起喧嚣的童声:110,120,119……这声音像吹动铁链秋千的大风在我耳边响,呼呼的。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听故事时喝了点白酒。我快要睡过去了,身体在木板上摇摇欲坠,我听见李老师对我的呼唤,他一只手伸过来拉我……
网红
我回到籍贯上的县城,说是故乡,我在此地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年。但由于父母经常说起,我仿佛也见识过它在我出生前二十多年的变迁。但二十一世纪以后它怎么样了,我父母也不知道。这次我回来还是参加葬礼。除了死亡,我和故乡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同的是,葬礼结束我没有离开,而是选择逗留在县城,四处乱转。
我住在姑姑家,姑父有时很外行地问我关于文学的问题,他是本地高中的化学老师,很喜欢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也去他和我父亲的母校看过,他们曾是同班同学,也当过几年的同事。他告诉我,你六岁以前每年夏天在这所高中的教工宿舍里过。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是对这座县城飞驰的摩的和走在街上的流子感到新奇,每次都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看很久。姑父说,你可以拿这些写小说。我说,这么写不行。姑父说,你城里长大的,太斯文了,也写不出他们。
我的姑父快要退休了,他是本市一九九〇年的理综状元,全省第三,但英语只考了五分,只是读了本市的一个教育学院,而后来为了得到学校分配的那套高级教师洋楼,他放弃了考研。他去教课了。早上他和我一路走到学校,我开始自己逛。这时已经是初秋,我想起自己十三年前参加爷爷的葬礼也是秋季,和父亲同龄的姑父现在头发花白。我年龄不小,却还没有正经工作。我路过几家粉店,在一片树林的转弯看见小学,那小学的对面有一间挺漂亮的书店,漂亮得不像是县城书店。
走进那书店,居然铺了木地板,但书没有什么稀奇,还是以教辅书为主,以及语文新课标的老名著、时髦的畅销书和网络文学。我看见坐在店面深处的青年,他坐在通往二楼的台阶顶端。我开口就问:“怎么在县城开这么漂亮的书店?”他从手机屏幕里抬起眼睛回应我:“县城也可以开网红店啊,这家店在长沙很网红的。”我其实没听过这间书店的名号,但也注意到这家店制作咖啡和卖文创,心里觉得可笑。我连生意怎么样都不忍心问他。这个青年长得很像我的一个堂哥,也是一副不精明却顽固的样子。
正当我转身想走时,他却主动和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里,这里最近可是出了个网红文曲星呢。”他站起身,步下台阶,我站在原地等他。外面从阴天转为暴晴,水泥地金灿灿的,小学里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他拿手机给我看一条有一百多万人点赞的短视频,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书店地板上翻大部头,还有他写在练习本上的诗。小男孩长相憨厚,衣着简朴,写的诗也很简单,就是小学语文课教的写作逻辑,掺杂一些从书里看到的文学词汇。不过这种东西火起来也并不奇怪。他见我神情冷漠,相当诧异:“怎么,你不觉得写得好吗?这写得真是好极了,真是让我们大人羞愧啊!”他的夸张劲儿也挺本地的,我只好敷衍道:“写得是不错。”店主说:“是吧,你看门外,这小孩就是那所小学的。很多小学生来我这里,但读的都是这堆,图画书,高年级的看这堆,玄幻言情。就他不一样,看这排文学书,看得有味。他除了文学,还爱看字典,喜欢查里面的生僻字,遮住字的释义,让我猜字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里,我也啧啧称奇:“他看起来只有四年级啊!”店主说,他这学期五年级了,看起来比别的孩子小一点,头大,细胳膊细腿。店主说这孩子的父亲,就是附近的小杰牛肉粉的老板,晚年得子,今年放暑假看见孩子在本子上写诗啊,文章啊,拿他的手机不是玩游戏而是读小说,异于常人。老汉认为孩子是文曲星,以后要成大人物,就拜托他帮忙给他们开了个网络账号,来记录孙玉杰的生活。店主欣然接受了这件事,就当给书店打广告,他在几个大型平台创建了“小小孙玉杰”的账号,陆续发孙玉杰在书店读书的视频和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孙玉杰每天都写,他就每天都发,整个暑假都没什么人看。大约就在半个月前,他发的一条孙玉杰的诗爆红了,后面发的两首也爆红了。孙玉杰最近十来天没有写新诗,写的都是散文和小说,虽然点赞也有二十万左右,但和诗歌的影响力没法比。店主和我说,可能还是诗写得更直接,更好。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字不够好看,写成密密麻麻的一片,就不想看了。店主恍然大悟,确实,我自己拿本子读,觉得小说也好看,但用屏幕可能就不行了。店主确实是孙玉杰的铁杆粉丝。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刷“小小孙玉杰”,评论区很多人夸赞他的诗,表达对他新作的热烈期待,心中难免产生嫉妒。我也从他这个年龄开始就在写作,写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作品从未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即使深知作品质量和影响力不存在正相关,酸腐的心情还是泛了上来。
我于是问店主:“那他突然爆红,肯定有很多利益,会有采访和作协邀请,甚至能出书吧。”店主说:“那倒没有很多利益,文学能赚什么钱啊。采访也不见有,有又怎么样,我高中同学有人写历史书的,当时也有人来学校采访,他后面不也只是在县城当历史老师。作协邀请倒是有的,出书也会有。这些算什么利益啊。”店主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他对这些东西的轻蔑是发自内心的。我说:“你不写东西,所以那么无所谓。”店主说:“所以你写东西吗?如果你写得没有这个孩子好,也不必自卑的。文学这个东西太靠天赋。”这个店主的面目在我眼中顿时可憎了起来,但我知道这就是我老乡的语气,我也经常这样挖苦人。我沉默不语,像孙玉杰一样坐在木地板上,但我没有看这间书店的书。我看不起这些书,我看短视频里面孙玉杰写的东西,觉得真不怎么样,非常像初学者写的,但人们特别喜欢,他们的喜欢包含着对热爱文学的小孩的喜欢。想象中的文学和小孩,是再美好不过的存在,何况结合在一起,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接受和欣赏。
我就坐在地板上刷了一上午,老板出门去吃了个粉回来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怀着复杂的心情把孙玉杰的全部作品阅读完了,我有几次想在评论区和吹捧他的人对质,普及一些文学常识,后来还是颤抖着右手没有把大段的文字发送出去。因为我是拿自己的笔名上网的,在一个网红文学儿童风头正劲的时候说些批评的话,等于把自己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这个孩子还是我的老乡,是我故乡从未出现过的文学名人。孙玉杰,我又一次在脑中重复这个名字,他已经来到这间名为“时间之城”的网红书店,背着米老鼠书包,看见我坐在地上。他戴着眼镜,脑袋大,身体瘦小,一副斯文的样子,但一点也不怕大人。倒是我紧张起来,站起身拍拍屁股,好像木地板没有拖干净一样。我像是没控制住发声器官,叫出他的名字,孙玉杰。他有些诧异,看来这半个月他并没有发生在本地遭遇被陌生人叫出名字的偶像体验。他用一口乡音回应我:“你咋够晓得我够缅杂?”我早已失去了家乡话这一母语,只能继续用普通话说:“我看了你写的东西,想和你聊聊写作。”
孙玉杰出乎意料地高兴起来,一屁股坐下,拍了拍木地板,说:“来。”他娴熟地放下书包,从书包里掏本子。我问:“你不用回家吃饭吗?”孙玉杰说:“中午我们吃食堂,我吃过了。”我接过他的本子,其实里面的所有的作品我都读过了,我开始一篇一篇给他讲,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够好,哪里是很糟糕的,哪里是珍贵的……当孙玉杰坐在我面前,我开始忍不住夸赞他聪明和天赋异禀,是啊,才五年级,已经写得这么像模像样,这么恰到好处的聪明,未来多么值得期待。孙玉杰听得也兴奋起来,也时常给我反馈,或者直接表达他听不懂。我心想,如果我小时候遇到现在的我,能不能有孙玉杰这么好的修养呢,会不会虚心接受成年人的教诲呢?我不会,我只会妄自尊大,所以幸亏我小时候没有红,我的天赋也不能够出名……孙玉杰深感学到了许多,而店主在旁边听我和孙玉杰的对话,也对我刮目相看,并且偷偷拍摄了我们对话的视频。我注意到的瞬间,他立刻回应我:“我会剪辑的,会把你剪得很儒雅。”
我问孙玉杰:“你是不是要加入作协,作协还要给你出书?”孙玉杰回答说:“对啊,作协很厉害啊,叔叔你是不是也是作协的,我感觉你很懂,比我们语文老师懂多了。”我说:“我不是。作协的也不一定比你们语文老师懂写作。”店主打圆场说:“作协还是很厉害的,但很厉害的不一定都在作协。”我不再多嘴,心想就不必对小孩说些怪话了。我心里产生奇怪的珍惜感,于是凑近了一点,问他:“你想不想看看叔叔的诗和小说?”孙玉杰看了一眼手表,回答我说:“好啊,但我要去上课了,你可以等我吗?我下午放学过来看你写的。”
他背上书包,在冲出书店门之前还转脸和我强调:“等我下午放学!我很想看啊!”
孙玉杰走了,我心里顿时空落落的,而且不安起来,像眼前蒙上一层林翳。我真的要给一个五年级的孩子看我的诗和小说吗,而且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孩子?店长并不知道我的疑虑,他对我的态度和气起来,他认为我是一个懂文学理论的人。他说,小孩子写东西主要还是靠灵气,老师你刚才那些话是能点拨他的。我问:“你要在网上发我和他的对话吗?”他说:“对啊,当然要发,要不要在标题里写你的名字,给你增加流量。”这话说得很诱人,但我这时心神不宁,如果我告诉了他我的笔名,那么孙玉杰也会知道我的笔名,那么他一定会上网查我的作品,我真的要让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接触我的诗和小说吗?我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猛然拒绝了店主:“不要署我的名字,就说我是来这里看书的一个语文老师好了。”店主说:“果然,你说话的那个语气,就是语文老师。”
我感受到沉重的失败,不希望孙玉杰和店主阅读我的作品。一刹那我甚至不希望任何人再阅读我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的失败?趁着店主上二楼午睡的间档,我違背了和孙玉杰的约定,从这间书店落荒而逃。我路过了小杰米粉店,看见他秃顶干练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矮小结实,他站在熬制汤底的大锅前扫地。孙玉杰每天就在米粉店的二楼写作,几百万人见识了他此刻具有的才能。可谁像我一样挂念他的命运,而且还将持续不断地挂念下去?
责任编辑 张范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