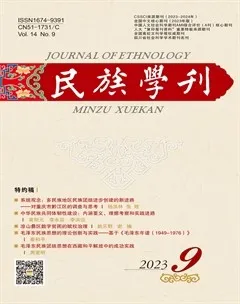少数民族非遗影像的传播特征及策略调适
唐英 黄娟 李正丽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3.09.016
[摘要]
全球化的传播场景,使民族文化的传播生态复杂化。此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成为一个重要与敏感交织的题域。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工具,影像能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为非遗的传承和弘扬提供新的机遇。本研究以藏族的唐卡绘画为例,探讨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特征及策略。阐述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受众群体的多元性和层次性,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统一性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分析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内容的适当性欠缺导致内容失真和过度商业化、忽略受众结构的多样性导致传播策略精准、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不足导致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规范性弱、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影响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质量和效果等方面的一些短板。提出了从源头上防范传播内容的失真、拓展和扩大受众面、强化政策和法规的支撑、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调适性的传播策略。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唐卡绘画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9-0145-08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项目“数字时代公共教育传播”(36)、2023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四川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特征及策略调适研究”(MZMS2023015)、2023年度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项目:“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整理、传承与互动传播的影响研究”(JD2023-Y001)、“川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十年影像创作与传播研究”(JD2023-D001)、“新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研究”(JD2023-Y011)、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渝双城经济圈视域下四川电影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2YJC760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英,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传播学;通讯作者:黄娟,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管理学;李正丽,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此,“非遗”作为一个文化范畴进入人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视域——那些传统的、民间的、地方的文化实践渐次成为多视角的理论观照对象,影像传播也是其中的视角之一。
近年来,学界不断延展对非遗内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价值功能的逻辑探寻。一方面,非遗承载着区域性群体独特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民间性、口述性、野史性、活态性的特点,对存续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方李莉就认为,正是“后非遗”时代的“生产性保护”,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1]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非遗承载着族群交流交往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对增强族群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创造力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2]尤其是,在国家“以文促旅,以旅兴文”的倡导下,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互促互动正在成为突出的社会事实。
从内涵和外延上看,作为嵌在日常生活世界及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独特的意义世界及审美的“活”的显现,[3]少数民族非遗主要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传统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与自然界和宇宙观有关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社会文化空间。[4]在本文看来,“少数民族非遗”主要是指被中国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之重要构成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及相应的知识、技能、呈现形式乃至有关的工具、实物和场所。从传播的角度说,知识和情感是其内蕴的主要信息,听觉和视觉是其主要的符号形式,而这也正是少数民族非遗在交流交往上与影像传播具有内在性亲和的关键。
作为一种主要通过视觉和听觉符号来传递信息或情感的媒介方式,影像传播的理论框架散布于符号学、叙述理论、感觉学等领域。在符号学维度,Saul认为影像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特定的意义和语境。[5]这对于少数民族非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影像往往携带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在叙述理论维度,Brovik认为影像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个叙事过程。[6]这也就意味着,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文本通过合适的组织和解释,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引人入胜和深刻的故事。在感觉学维度,(Pratt)强调影像传播与观众之间的感官互动,指出视觉、听觉等多重感官经验能增强信息的吸收和记忆。[7]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下,影像传播对少数民族非遗的呈现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文本形式上都有更多的可能。[8]以互动性、参与性为优势特征的社交媒体、自媒体、短视频,为非遗的影像文本创造了全新的传播环境。
在文化认同理论看来,“认同”的传递、建构和表达主要通过符号和象征得以实现或完成。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也就是通过展示本群体的文化事项,让自己与其他民族感受到相应意义并以此达成必要的理解和认同。作为一个过程,这既可展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也可培塑观众理解多元文化社会的丰富性,从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Barbara Pikur和Ramon Danils认为,广泛而多元的社会参与有助于建立社会认同和增强社会凝聚力[9]。以影像传播呈现的非遗,可激发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兴趣。特别是传播技术日趋智能化的当前,VR、虚拟数字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性、沉浸性,让用户有机会更深入了解非遗的历史背景、技艺传承和地域特色,增进对非遗的认知和兴趣,从而更好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如2021年中日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唐卡画师之乡》,就有力地丰富了不同群体对唐卡绘画的认知。
圍绕非遗的影像传播,有的学者阐释了非遗传承面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等深层次问题,探讨如何通过具备文献保存、文化传承功效的影像手段来传播非遗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非遗题材的纪录片来阐释并借以实现“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10];并强调电影也成为“‘非遗传播和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11];还有的学者认为非遗短视频因为用直观、动态的影像呈现其相关知识信息及其中蕴含的较为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从而能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12]
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少数民族非遗项目面临衰落甚至失传的危机。作为保护与传承非遗的重要手段,影像传播超越地域和时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当前研究者大多将重心置于影像传播“非遗”的理论层面,对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特征、问题和策略缺乏必要的关注。鉴此,本文以藏族“唐卡绘画”为个案,以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传承为靶向,讨论其影像传播的特征及策略。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特征分析
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受众群体呈现出多元性和层次性,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统一性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与弥补性。这些特性不仅是非遗影像传播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能够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同的关键因素。
(一)影像传播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
从传播角度看,地域性是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核心特点。地域性不仅代表了非遗文化的地理特性,也是其独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的具体表达。藏族的唐卡绘画,内容上以藏传佛教的传说、故事及场景为主,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传播地域也主要集中在涉藏地区。从其影像传播的媒体呈现上看,比较典型的如康巴电视台,一直立足于非遗文化传播唐卡绘画;尤其是结合“唐卡绘画”展览吸引各类爱好者。换言之,也正是影像传播促进了文化交流。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所在自然空间不仅是“非遗”的“乐土”,而且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与身份标签。[13]
与地域性相关联,少数民族非遗的历史性不仅表现文化元素的选择上,更在于整个意义体系内涵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从历史维度看,唐卡绘画反映了佛教在涉藏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以及作为佛教传播之重要动力的宫廷文化的繁荣;同时,其创作技艺的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确保了其技艺谱系和精神内涵在时间之轴上的延续。这种内容、技艺与传承的高度一体,使其成为藏族聚居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
受地域性和历史性影响,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还具有意义共享性——非遗“附载”的意义如何让更多人认同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唐卡绘画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藏传佛教及其信仰实践的一部分。唐卡的绘制过程及其文本体系,都蕴涵了藏传佛教丰富的精神内涵,其影像传播的过程,也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对其内涵的感受中来的过程。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并为非遗的影像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二)影像传播受众群体的多元性和层次性
受众群体的多元性,是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中的突出特征。数字化引领的媒介生态下,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所覆盖的受众不仅包括国内的各民族,还涵盖了广大的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多元性的背后,还内含着明显的层次性。作为非遗“主人”的本民族群体是第一层。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非遗不仅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认同的途径。唐卡绘画的传承者们,在将该技艺的系统性地传授给下一代的同时,也通过这一技艺的实践来表达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这也就启示我们,少数民族的影像传播在内容选择、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必须充分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及认同表达。
国内其他民族群体是第二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非遗的影像传播也需要最大限度地向其他民族开放。近年来,唐卡绘画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吸引了各民族的爱好者以各种方式加入到对该技术的保护和传承中来,这不仅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更好地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当然,其相应的经验和教训也启示我们,非遗的影像文本,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觉照顾民族意义上跨文化的可传播性。
国际受众是第三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少数民族非遗更有可能受到国际关注。因此,如何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使之具有国际传播价值,成为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唐卡绘画是藏族文化国际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形式、内容和渠道都适当的国际传播,吸引国际爱好者的关注,增加国际受众的文化认知,进而促进了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意义上可谓意义非凡。
在多元性与层次性的交叠中,每个受众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和审美趣味。对于非遗的原属民族,影像传播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确认,而对于其他民族和海外受众,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新知和学习。这也意味着,为了提高传播效果,需要对不同层次的受众实施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如对本民族群体,可采用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传播方式,展现非遗的历史和传统;对其他民族和海外受众,则需要采用更加普及和通俗的方式,强调非遗的“普世价值”和当代意义。在传播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的当下,VR、AR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让受众更直观地体验非遗的文化内涵,还有助于保存和数字化非遗。如可通过建立一体化的传播平台,集合各种媒体和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非遗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从而增加其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三)影像传播突显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统一性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从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角度看,统一性值得特别强调。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不仅是一种文化传递,还涉及到身份认同的建构和表达。作为文化载体,影像传播能够在受众中塑造、传达和强化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一方面,影像传播是一种富有符号性和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在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中,符号和象征都在传达文化的深层意义。唐卡是藏族文化的瑰宝,它通过绘画艺术传达了信仰、历史故事甚至生活方式。唐卡传承人通过绘画将特定的宗教内容、传统生活场景等呈现给接受者。影像传播的图案、色彩、音乐,都承载着文化的象征,接受者通过解读这些符号和象征,更好地理解和体认内在的意义和意蕴。
影像传播还涉及故事的叙述和构建。通过影像呈现的故事,观众能够沉浸在非遗的历史、传承和传统中,在理解和感受非遗文化价值的同时,与之建立相应的情感联系。所以,影像传播有助于建构和强化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通过影像传播,巩固内部凝聚力,同时也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也就意味着,跨文化传播视角有助于阐释非遗文化在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一方面,不同民族之間的语言和符号差异可能导致误解,某些词汇、符号及表达方式在一个民族中具有的意义,可能被另一个民族误解或引发不同的联想。因此,在影像传播中,需要考虑如何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观念,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和启发。唐卡绘画的色彩渲染、符号组合、空间构思,可以让所有接受者窥见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消弭文化偏见和误解,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推崇。因此,在非遗的影像传播中,需要考虑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沟通和解释,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数字化引领的媒介生态下,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作为“现象”,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在内容的适当性、受众的结构性、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资金和技术的短缺都有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和传播都有或这或那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非遗文化价值的流失和退化。
(一)内容的适当性欠缺导致内容失真和过度商业化
内容适当性是指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深度。它要求传播的内容既要忠实于原文化,又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和理解能力。少数民族非遗,通常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在影像传播中,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或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往往会对这些复杂的文化元素进行简单化或者片面化的描述。这种做法无疑会削弱非遗的内在价值,导致深度与表面的矛盾,使其失去原有的文化深度和多样性。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一些传播主体可能会过分强调非遗的娱乐性和“奇异性”,而弱化甚至忽视其文化和教育意义。这样不仅可能导致非遗本身变成一种可供消费和交易的“商品”,还可能引发文化异化,从而破坏非遗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唐卡绘画中,文化的异化现象之一就在于为了“迎合”市场需求,部分唐卡绘画的创作者可能会采取现代化、商业化的手法,使得作品失去了其作为非遗的技艺性以及附着于技艺的独特意蕴;之二则在于为了更好地实现商品化,唐卡绘画可能简化一些图案或标志,进而忽略或淡化其作为非遗载体承载的文化意涵。
此外,在对外部文化的借鉴上,部分非遗影像创作可能过度借鉴外部文化元素,导致原有的文化特色被淡化甚至是淹没。在某些“现代版”的唐卡绘画中,西方绘画技法的光影处理、透视原则被生硬植入,与传统不符的材料和工艺被不合适地使用,这不仅导致唐卡绘画失去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非遗项目对外部文化的依赖。
(二)忽略受众结构的多样性导致传播策略不精准
受众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年龄、地域等方面的不均衡。有文献显示,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受众主要是老龄群体。这种状况不改变,显然不利于非遗的传承、传播和普及。地域上,受众主要集中在对该项目具有较强认同感的民族聚居区。这意味着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迄今仍难触及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跨域群体。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多元性表现在受众群体及其需求的多层面、多维度。这不仅体现在内容多样性上,还包括传播渠道、形式、目的等多个方面。如藏族唐卡绘画的受众群体,涵盖了涉藏地区各族群众及内地各层面的爱好者。不同群体对唐卡绘画的兴趣和需求各不相同,信徒可能更关注佛教故事、信仰场景等宗教性内容,艺术爱好者可能更关注绘画技巧和艺术价值,学者则可能关注文本背后的意义体系。对接传播形式,也就可能是宗教仪式、艺术品展览、专题讲座等;对接到传播渠道,则可能包括寺庙、展览会、学术论坛、互联网平台等多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受众结构多元多样的背后,往往与非遗影像所选择的传播内容及相应的模式密切相关。而在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中,如未充分考虑受众结构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必然影响传播效果。
(三)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不足导致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规范性弱
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政策和法规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它们既是对非遗影像传播的指导和规范,也是通过此指导和规范促进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发展。然而,当前的政策和法规难以应对影像传播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进而影响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政策和法規对非遗影像传播的支撑性问题,不仅仅是执行力度的问题,更与非遗原生地的传播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等因素相关。一方面,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非遗的报道和推广往往缺乏必要的持续性、丰富性和多元性。这在媒介接触率上,必然影响非遗影像传播的社会可见性。即便是在有“可见性”的传播中,也存在因商业化、跨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内容的被曲解,出现传播的政策盲区。数字化时代,唐卡绘画的影像传播就不仅仅涉及传统影视媒体,更应该涉及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智能化媒体。但现有政策几乎未涉及这些新的传播形态,进而其传播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规范性指导和合法性保障。更为关键的是,这其实还存在着跨地域的传播风险——跨国或跨地域的传播规范缺位,唐卡绘画的影像传播可能导致文化误读甚至风险性争端。
另一方面,现行的文化政策和法规在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方面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首先是在非遗影像传播的实际过程中,部分政策和法规可能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对于非遗影像传播中出现的侵权、抄袭等问题,缺乏专门的法规进行约束和处理,使得部分非遗项目的资源被流失或损失。如在唐卡绘画的影像传播中,如何保障画师的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其次是标准化困境,为确保唐卡绘画的“非遗性”,政策如何在体现标准性和规范性的同时,兼顾对画师创新的鼓励。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是一个涉及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问题。然而,目前国内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很难满足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国际需求。
(四)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影响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质量和效果
资金和技术短缺,不仅制约了非遗影像本身的质量,还对其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构成了越来越严峻的冲击。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从内容创作、制作、编辑到传播,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但由于非遗内容通常不具备即时的商业价值,在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都不足的窘境下,很多具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的非遗难以得到有效的推广。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趋势下,高质量的影像传播需要先进的拍摄、编辑和传播技术支持。唐卡绘画,材料和绘制过程都与数字化的新技术有相当的张力。尽管数字化的新技术为唐卡绘画带来了便捷的复制和传播手段,但过度的数字化可能导致唐卡的制作流程与意义在被简化或忽略。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双重限制,非遗的影像传播在技术层面整体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也在客观上放大了非遗影像传播地域和文化的双重不平衡。资金充足和技术先进的地区或机构更容易制作出高质量的非遗影像,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和社会关注;资金和技术不足的地区则面临着非遗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如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先进的传播技术,唐卡绘画在影像传播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这不仅影响了其在现代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效果,而且还可能导致其在未来的传承中面临更多困难。
三、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策略调适
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既关乎不同民族之间以文化为桥梁和纽带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和拓展,也关乎不同民族之间在历史传统、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上差异和源发于此的风险。所以,立足现有的媒介生态及其发展趋势,综合性调适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策略,具有多维度的战略意义。
(一)从源头上防范传播内容的失真
在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内容适当性上,需以规范的审核和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内容的失真。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应在公开传播前,由专门的审核团队进行内容的准确性和文化敏感性评估。如唐卡绘画的影像传播,其影像文本在进入传播渠道之前,就需要有专业的机构或人员来审核传播内容,确保其符合传统标准,避免失真和误导——制作工艺、文本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应当经过专业人士的审核,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这也即意味着,该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专业机构的审核,还需要民间非遗传承人、民族文化代表等多方的参与,以确保内容的丰富性。审核过程中,还应当关注内容的文化敏感性,建立规范的商业推广模式,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社会效益为首要,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对此,可考虑通过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对拍摄团队进行专业培训,以提高其对非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只有确保非遗影像在文本意义上能真实、准确地传达该项目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在商业化推广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才能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非遗影像的顺利传播。
(二)拓展和扩大受众面
在受众的结构性上,需多角度、多层面拓展受众面。这首先需要拓展传播渠道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当前,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但平台的受众覆盖与非遗传承和普及所需的目标受众之间交集并不大。因此,需要开发和利用更多类型的传播平台,如社区活动、展览、文化节等,以便将非遗传播到不同年龄、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而且,因为不同的受众群体对非遗的接受度和认知水平都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根据受众特点来设计多元化的传播内容。如针对年轻人,可以通过增加娱乐性和互动性的元素来吸引他们,如抖音、快手、微博等;对于学者和文化爱好者,则可以提供更深入、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如南方周末电子报等。其次是需要加强与其他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联动,以提高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非遗的影像传播,不应仅仅被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或群体,而应该与其他文化因素,如历史、地理、民俗等,形成互补和交融。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丰富非遗的内涵,还可以提高其在全社会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并以此拓展民族之间以文化为桥梁和纽带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还需加强对外宣传以突破地域局限。目前,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主要在国内,国际场面相对有限。所以,解决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中受众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和多层面进行综合性的策略部署。
(三)强化政策和法规的支撑
在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上,首先应积极探索并逐步完善以保护和传承为首要目的,综合考虑商业开发和社会效应的非遗的传播规范体系。如针对唐卡绘画,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保护措施、传承义务和违规处罚等方面的内容。也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非遗传统的数字化保存,如拍摄高清影像、建立虚拟博物馆等。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鼓励唐卡绘画参与国际性的非遗活动和展览。
更为重要的是,再完善的规制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执行,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配套的监管机制,包括定期检查、责任追究以及处罚制度也就同等重要。已有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不能只靠政府监管。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和民间组织的参与也很重要。一方面,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来监督政策和法规的执行情况。这些机构可以定期发布监督报告,及时发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也可以定期进行社会评估和调查,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政策的修订和完善。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是那些与非遗相关的社群和传承人。可在政府主导下设立咨询委员会,让相关利益方提供意见和建议,确保非遗得到全面、准确的传播。这也就要求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充分考虑民族特色,以保证政策和法规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为非遗影像高效、规范地传播提供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支撐。
(四)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首先,需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如设立专门的非遗影像传播基金,用于非遗的记录和制作及培训、设备购置、推广活动等多个方面;也可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赞助和捐赠,支持非遗影像传播。同时,还需广泛借鉴先进的非遗影像传播模式,如引进先进的影像制作设备和软件并培训相应的人才,以提高非遗影像的制作质量和传播效果。
其次,需强化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共同开展非遗影像传播规律总结和推广。在实践上,可尝试建立研究中心——政府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非遗影像传播研究中心,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非遗影像传播的问题,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开展项目合作——通过合作,既解决技术问题,也利用其研究成果和人才优势,提升非遗影像传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最后,需鼓励社会各界参与以逐步优化非遗影像的传播环境。信息传播渠道的单一性、媒体平台的局限性以及由传播方式的不精准导致的传媒环境的不健康,是影响非遗影像传播的重要因素。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传播技术,为非遗影像传播的全面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达性。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非遗影像传播的效率,还可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不过,实现这些,就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传媒平台体系。因此,需要全面加强与社交媒体、流媒体、线下活动等多种传播渠道的合作,尽快形成一个多元化、立体化的传媒平台体系。当然,传播环境的改善需多方面、多角度综合施策。只有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具包容性的传播环境,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才能更有质量、更有效率,也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丰沛、更广阔的动力支撑。
四、结论
本文以藏族的唐卡绘画为例,从传播、受众、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差异等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主要特征,阐述了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受众群体呈现出多元性和层次性,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统一性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与互补性,这些特性不仅是非遗影像传播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能够获得广泛关注和传播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在内容的适当性、受众的结构性、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资金和技术投入存在的相关问题。
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是一个富有特色和复杂性的领域,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跨文化传播、受众需求等因素。为了提升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有效性,既需从源头上防范内容的失真,拓展和扩大受众面,强化政策和法规的支撑,也需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和传播策略的优化,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的非遗文化,实现文化的多元共享与共荣。
参考文献:
[1]方李莉.“后非遗”时代与生态中国之路的思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
[2]崔莹.论影像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意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06):38-42.
[3]普丽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综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05):64-69.
[4]安学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Saul.Semiotic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M]. New York: Routledge,2005.
[6]Brovick.Narrative Theory and Image-based Storytelling[J]. Journal of Visual Studies, 2010(12).
[7]Pratt. The Sensory Dimension of Image Communication[J]. Sensory Studies ,2012(4).
[8]龚诗尧.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研究[J].今传媒,2019,27(08):21-24.
[9]Barbara Pikur, Ramon Danils: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they distinct concepts? [J].Sage Journals,2013(8).
[10]陳敏南.“非遗”题材纪录影片的叙事策略[J].当代电影,2012(05):149-152.
[11]刘修敏.“非遗”题材电影传播力与教育力研究[J].当代电影,2012(05):155-157.
[12]蒋建华,张涵.非遗短视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传播[J].民族学刊,2023,14(08):13-20+157.
[13]周飞伶,雷伟.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少数民族非遗影像的诗性建构——基于《阿诗玛》纪录片摄制的考察[J].百色学院学报,2022,35(01):27-33.
收稿日期:2023-04-25 责任编辑:王 珏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ir Strategy Adaptation:
Taking Thangka Paint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as an Example
Tang Ying, Huang Juan, Li Zhengli
(Sichuan Film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Chengdu, 611331, Sichuan,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4, NO.9, 145-152, 2023(CN51-1731/C, in Chinese)
DOI:10.3969/j.issn. 1674-9391. 2023.09.016
Abstract:
In a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e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of ethnic cultures has demonstrated to be increasingly complex.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potentially sensitive issue.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images, as a kind of powerful communication tool, can overcome cultural and language barriers, and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ICH. Taking the Thangka paint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CH; it aims to showcase the regions, history, and shareability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ICH, its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of the audience, its un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identity, and its differ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also analyses the weaknesses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ICH with respect to content appropriateness, audience structure, policy and leg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adap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CH has suffered from many problems: First, a lack of content appropriateness, i.e. fake content as well as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second, ignoranc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audience has been impeding a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 policies; third, insufficient policy and legal support has been causing a lack of normative guidance in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CH; fourth,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shortfalls have been impact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ICH.
Taking the previou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in terms of policy adaptation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CH, efforts should first be made to ensure true communication content from the source. To guarantee content appropriateness, communication content should be subject to a standard-based review and evaluation. Before they are publicly disseminated, images of heritage assets ought to be reviewed by professional teams for content accuracy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Then, one should expand the aud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leverage various kinds of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such as community activities, exhibitions, and cultural festivals, to communicate ICH to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and from various reg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ird, it would be ideal if policy and legal support be strengthened. Efforts should indeed be mad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norm system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ICH that aims at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while also consider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and social effects. Moreover,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cluding regular examin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punishment rul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Past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CH cannot only rely o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Participation by all walks of life, especially the media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is also deemed significant. Fourth, it is highly desirable that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be increased: Special image communication fun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recording and production of ICH, training, equipment procurement, and promotion. Tax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may be offered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donate funds in support of image dissemination of ICH. Moreover, one should eagerly learn from tried-and-true methods of successful ICH image communication elsewhere. For example, one could introduce sophisticated image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software and train professionals to improve the image production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ICH; image communication; Thangka pai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