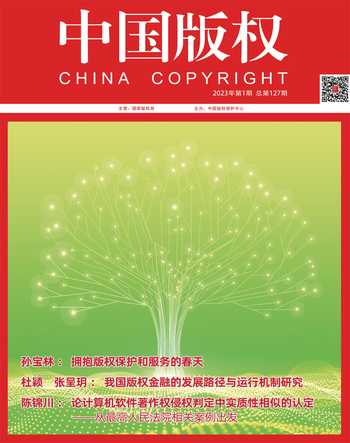元代出版业的发展及其版权保护考证
李明山 霍勇刚
元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时不到百年。但它国土广袤,疆土辽阔,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开启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程。元代继承了宋代书籍出版文化的发达基础,在近百年的短暂历史进程中对书籍出版和版权保护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明清文化出版和版权保护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一、元代出版业的发达与版权纠纷的增多
中国出版业发展到元代,印刷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是活字印刷术的运用和改进,另一方面是套胶印刷技术用于书籍刻印。王祯(1271-1368年)创造了木活字排印术。元代出现用朱、墨两色套印书籍(宋套印交子),是彩印的开始。一般认为,胶版与印刷术进步有关,或谓胶版是随着印刷术进步产生的。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上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使得大量书籍得到刻印发行,并传播到日本、安南(今越南)等亚洲国家。元代出版的图书,主要分官刻书、书院刻书、书坊刻书、私刻书等。元代的官刻得到了各级官府的重视,有大量的官银开支,刻印发行书籍很多。就大量的官刻书而言,可以分以下四种情况来了解:一是政治教化类书籍的刻印发行。元代统治者对政治教化类书籍的刻印发行非常重视,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学《孝经》上呈给武宗,武宗看后下诏,指令中书省刻板摹印,发至诸王以下阅读。元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看过《贞观政要》,对阿林铁木儿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于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元史·仁宗纪》)。《续文献通考·典籍》记载:“先是帝为太子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日:‘治天下此第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以赐臣下。至是翰林学士承旨和塔拉都里默色、刘庚寺译《大学衍义》以进。帝复令翰林学士阿林铁木儿译以国语。延祜五年(1318年)八月,复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二是《宋史》《辽史》《金史》等编修发行。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曾下诏令人编修宋、辽、金三史。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再次下诏命令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带人编修宋、辽、金三史,脱脱等力排众议,解决了编修宋、辽、金三史中悬而未决的体例问题。《宋史》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修,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修成,历时两年又七个月;《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设局编修,于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修成,历时11个月;《金史》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始修,于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成书,历时一年又八个月。三是刻印发行农书。元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农桑》)。期间刻印发行了大量的农书,如《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救荒活民类要》《山居四要》《田家五行拾遗》《打枣谱》《栽桑图说》《续竹谱》《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农家谚》以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等。四是官府及时、准确、统一编制发行历书。元朝官府在重视农书出版发行的同时,认为历书与安排农事活动关系极大,为了不误农时,要求有关方面必须搞好历书的刻印出版。元朝统治者对历书的编写要求十分严格,历书编成之后,还要及时刻印。为了加快历书刻印发行速度,常常由几个地方同时刻印,分散发行。
元代的书籍刻印发行业是比较繁荣的,有很多人从事这一行业,书籍发行面范围广,且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论及元代书坊刻书时就指出:“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夥,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这表明了元代书坊刻书的大概情况。上述表明,元代的整个书籍刻印发行业比之宋代有更好的发展,从业者有较好的收益。也正是书籍刻印发行利润丰厚,一些不法书商便以“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等侵权盗版形式刻印和销售书籍,谋求更多的利润,致使版权方面的纠纷也不断地增多。这类现象,从元代的书籍出版标记使用、书籍辨伪、刻书盗版管理、禁书事例等可见一斑。元代出版业的从业人员中,也不乏牟利之徒,这也对元代的版权保护提出了挑战。
二、元代书籍出版标记的广泛使用
在书籍刻印发行中,为了防止盗版侵权,一些出版者和作者不得不采取有关防范措施。为了更好地防止书籍被偷刻翻印,元代出版者在自己的书籍上都附印了形式多样的出版标记。如那些经过向上级衙门呈请核准的官刻书籍,都把当时所颁行的公文刊刻于该书前。刊刻于书前的官府批准文字称之为“牒”,牒文的内容十分简明,主要是讲刻印书籍的呈请、出版因由,注明批准刻印的单位。这种牒文,在宋代已经使用。例如宋元祐刻本《仲景全书四种》,收录有元祐三年(1088年)国子监牒文,称该镌刻书籍“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仲景全书四种》)。元代承袭了这种公文格式,不过在功能和形式上已发生不少变化。陆心源的《醑宋楼藏书志》有记载:“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诸路刊史。《两汉》则太平路,《三国志》则池路,《隋书》则端州路,《北史》则信州路,《唐书》则平江路”,书首也各附牒文。还有每卷末有宁国路教授题名的宁国路儒学刊印的《后汉书》;前有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明瑞序,序后有建康路监造各官题名的建康路刊印的《新唐书》;元翻宋本,有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云云五行的瑞州路等合资刊印的《隋书》85卷;苏天爵编撰的《国朝文类》,书前印有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修撰王文煜、应奉黄青老、编修吕思诚、王沂等给奎章阁的呈文——“伏都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历官翰林僚属,前后搜辑殆二十年,今已成书,为七十卷。……其文各以类分,号日《国朝文类》。……若于江南学校钱粮内刊版印行,岂惟四方之士广其见闻,实使一代之文焕然可述矣。”(苏天爵编撰《国朝文类》)在历书刊印发行方面,元朝政府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太史院刊印的历书都标有“印信”。这种“印信”,就是历书专印制度的合法标志,如同一种书籍专印出版的“准印证”,或是犹如现代图书的所谓正版防伪标识。这种标识,对元代书籍的盗版翻刻与窜改作伪起到了防禁作用。
在书籍中刻上版权告示,也是一种典型的版权保护措施。这一做法在宋代已有,其防范书籍被侵权盗版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有代表性的牌记如元代人出版的《古今韵会举要》所附版权声明:“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嘹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这样的版权声明,除了对那些可能会刻印盗版书籍的不法商人提出警告外,还明确告诉收集该书籍的读者,为了收集正版书籍,需要看清有此声明且无窜改与节略的《古今韵会举要》才是其所需的书籍。《古今韵会举要》是陈实作为出版人受作者黄在轩之托发表的,书上所附版权声明在版权保护问题上有以下几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是原作者诚实向读者声明,他将“千百年间未睹之秘籍”,呈献给当代读书之人,是十分认真的。而且是通过“三复雠校,并无讹误”,对读者是负责任的。他是出版者、传播者,同时代表作者,能够如此认真负责地创作、出版书籍,用现代版权观念来看,是很好地尊重和维护了作者和读者的权益。陈实在这里将“私著之文”与“见成文籍”分别加以阐述,他之所以发表版权声明,就是为了防止“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黄在轩的《古今韵会举要》这一“私著之文”。《古今韵会举要》与书肆中所刊的“见成文籍”不同,是经过作者投入极大智力劳动而完成的作品。假如一旦被“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就会出现“纤毫争差”的现象损害读者的阅读权益。因此,陈实才在当地禀官陈告,请求颁行禁约,防禁盗版侵权事件的发生。这种请求地方官府衙门颁布出版翻刻禁约的情况,在此前宋代已经出现不少。这表明,元代的著作者、出版者沿用了前朝用官方告示保护作者、出版者和读者权益的办法。在陈实看来,“私著之文”和“见成文籍”是不同的。根据《中国古籍编撰史》作者曹之的理解,“见成文籍”是指古籍,其作者已经作古,对古籍的使用可以宽一些;而“私著之文”的作者仍健在,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随意去侵害健在作者的作品完整性权利,不能随意去“改换名目,节略翻刻”。上述做法和现代版权保护意识,已有某些接近和相同的地方。
书籍所附有的各种出版标记,有很好的版权保护作用。第一,书籍所附出版标记具有“防伪标识”的功能,证明该书是经过有关机构审定的书籍,无此标记的是非正规书籍。例如官刻书籍所附“牒文”、太史院出版的历书上所标的“印信”等,有明显的书籍审定批准证明作用。第二,出版标记可提醒读者社会上有“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伪劣书籍销售,买书籍要买有“出版标记”的书籍,以免上当受骗。《古今韵会举要》所附的出版标记,就有这方面特别突出的作用。第三,有出版标记书籍的相关责任者(官府、书院或个人)都会经常留意查看所刻印的书籍有没有假冒翻刻,这就会使不法书商减少或放弃盗版翻刻有出版标记书籍的行为,从而起到保护版权的作用。第四,元代出版的书籍能够附上各种出版标记,特别如同《古今韵会举要》所附版权声明、官刻书籍所附“牒文”这样的出版标记,说明元代的著作者和出版者就有了较强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较为积极有效的版权保护行为,通过施行某些有效方式去保护原版书籍,使其不易被翻刻。元代人的这些版权保护意识和版权保护行为,不但对刻有标记书籍的版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对元朝所有刻印发行书籍的版权保护都有积极影响,对后世的出版物版权保护也有启示作用。
三、元代学者的多方面辨伪贡献
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均创作于先秦时期。但是在秦火(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真正的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流传下来的不多,汉代以后通过历代的古籍征缴和整理,又再现了不少所谓先秦经典,其实有一些是伪造的。出于各种原因,辨伪古籍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元代学者继承了唐宋学人的辨伪传统,在经典古籍的辨伪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元朝历史虽短,但也有诸多学者在古籍辨伪方面做出了成就。不过,有辨伪学家认为,元代学者的辨伪成就似乎微不足道。梁启超认为:“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闰位,比较好的任何学术都很少贡献,在辨伪方面也是如此。”其实,元代的辨伪学成就,已为当代学者所重视,杜泽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所撰的《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9月版)中认为,元代学者在辨伪学方面有诸多贡献,值得予以重视。通过对元代学者辨伪的总体浏览可以肯定,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
(一)吴澄等对《古文尚书》的辨伪贡献
在《古文尚书》辨伪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肯定文字叙述:“《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械作《书裨传》始稍稍掊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频《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此书”指的就是元代吴澄的《书纂言》。吴澄(1249-1333年),元代著名理学家,江西抚州人。他的主要辨伪著作是《书纂言》一书,其卷首先列出今文28篇目,再列有东晋晚出古文篇目,在篇题同今文的目录下注明“同今文”字样,用按语说明“孔壁真古文《书》不传,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验证,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张霸伪书辽绝矣……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吴澄在《尚书纂言》书中认为当时所传的《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的书籍,因而尽去古文,只释今文28篇,并在目录后识语中明确指出:“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无一字如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这个论断表明了其“尽去古文,只释今文28篇”的原因与依据。清代学者阎若璩也说:“自吴械始有异议,朱子也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由此可见,元代的赵孟頫、吴澄是继宋代吴械、朱熹之后进一步辨别《古文尚书》之伪的人。尤其是吴澄,能够在《校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序》中明确指出25篇是拾遗佚连缀而成,对后辈梅篱、阎若璩等的书籍辨伪启发很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进一步认为:经吴澄的进一步研究,晚出的《古文尚书》“其伪益彰”。当然,对于《古文尚书》的辨伪,元代的郝经、王充耘都是有所作为和贡献的。元代王充耘(生卒年份不详)的主要辨伪著作是《读书管见》,亡名子序写道;“《书》有《管见》,曷为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订《蔡传》而志其所见也。先生当前代科目鼎盛时,用《书经》登二甲进士第,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弃官养母,著书授徒,益潜心是经,自微辞奥旨、名物训诂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从,而不苟为臆说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诣微密,岂徒专门名家党同伐异者之为哉?此其能为蔡氏之忠臣不啻苏黄门古史之有功于子长也”。上述表明,王充耘在书中详细引用了历史资料来考订《蔡传》而成就“造诣微密”之作,并在书中通过摘录《尚书》中一词或一语进行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自宋末迄元,言《书》者率宗蔡氏,充耘所说,皆与蔡氏多异同,观其辨传授心法一条,可知其戛然自别矣。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日《虞书》;谓‘象以典刑为仍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逆河以海潮逆人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虽然“《洪范》错简之说,《伊训》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纠正,而所附周不改月惟鲁史改月一条,尤为强辞”。可见,王充耘的辨伪功力与辨伪贡献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此外,还有丘迪的《尚书疑辨》(卷数不详)、韩性的《尚书疑辨》1卷、赵杞的《尚书疑辨》(卷数不详)等都是很好的古籍辨伪著作,可惜这些书都见不到了,没有办法再探究书中的内容。伪《古文尚书》长期以来被奉为重要经典,历经宋元明清数朝辨伪学者的努力,才将它的伪造辨明并定为铁案。元代学者能够抓住中国版权史上的这一重大主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宋濂《诸子辨》的辨伪贡献
元代学者辨伪的另一个亮点,是宋濂的《诸子辨》。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原籍浙江金华潜溪。宋濂的《诸子辨》是一部辨群书之伪的重要书籍。《诸子辨》始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宋濂主要是有感于诸子书“有依仿而托之者”,因而便“辞而辨之”(《诸子辨·序》)。先是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在句无山期间,“因旧所记忆者”完成了《诸子辨》第一卷。在此卷中,他先对上至周秦、下至唐宋的40多部诸子书籍逐一进行了考辨,共辨别怀疑为伪书的有27部。以《诸子辨》对《管子》的辨伪为例,不仅认为《管子》不是管仲的自撰书籍,还对它的内容提出质疑:“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二其言至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撰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预载之也。”这是通过考证书籍的史事,来确定作者为伪的方法。一本书籍的作者,不可能将他身后的历史事件预先写在书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后世作者将后来完成的书,假托前人为作者。这种辨伪方法,为后世辨伪学者所沿用,也是当代辨别伪撰作品的主要方法之一。宋濂在颠沛流离中完成的《诸子辨》,史料难以寻找查阅,在辨别伪书时难免有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但他用一本书籍辨别诸子书之伪,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他打破了前人辨伪的零星记载状态,对后世辨伪专著的出现具有启发意义。当代学者杜泽逊就认为,《诸子辨》对明朝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乃至近世学者张心潋辑的《伪书通考》,都有先导作用。
(三)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的辨伪贡献
元代学者辨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贡献,那就是陈应润的《周易爻变义蕴》,首先向《易先天图》发难。陈应润(生卒年份不详),天台人,元代延祜年间起为郡曹掾,至正年间调桐江宾幕。其主要《易》学著作,是《周易爻变义蕴》。陈应润对陈抟之学存有异议,认为陈抟之学“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交之蕴也……汉魏以来,诸儒注释奚啻数百余家,往往皆于本卦取义,而用九用六之说不明。好奇过高傅会舛凿玄妙者,则涉乎庄老,衍虚无者,则流乎异端。《太玄》拟《易》也,而《易》为之破碎,《潜虚》拟《玄》也,而《玄》为之散灭。甚则假老子之学,以创无极太极之论,变炉火之术,以撰先天后天之图。自是以来,谈太极者,以虚无为高,讲大衍者,以乘除为法,强指阴阳老少为四象,而四象之说不明,妄引复銗逆顺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蕴愈晦矣。由是谈玄之士,承讹踵谬,画图累百,变卦累千,充栋汗牛,初无一毫有补于《易》”。从这些言论来看,陈应润是不赞同周敦颐、邵雍之原图的。《易先天图》在宋代,诸如邵雍、朱熹等大学者就深信不疑并加以尊重。但陈应润认为,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并非《易》之本旨。对于陈应润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重视:“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图案,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它最早记录于《尚书》之中,又在《易传》中记述,更散见于诸子百家文献。宋代陈抟(827-989年)创绘太极图、先天方圆图,著《易龙图序》,成为太极文化的创始人。其学生邵雍继承陈抟的易学研究,又有发展;朱熹进一步将陈抟的河图、洛书之学纳入他的《周易本义》之后,使这一道家文化很快融人到儒家学说之中,成为正宗官学。是陈应润将这一仅次于《古文尚书》的中国辨伪学史的重大伪案首先提了出来,他在中国辨伪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四)祥迈《辩伪录》的辨伪
元代的辨伪还有一例,即祥迈撰写的《辩伪录》一书,又称《至元辩伪录》,一共有5卷,收集在《大正藏》第52册中。祥迈(生卒年份不详),元代僧人。祥迈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接到皇帝的旨令后撰写这本书的,用以驳斥道教的一些虚伪说法。其起因是由于南宋理宗宝祜三年(1255年),全真道教的道长丘处机、李志常等强占寺院480多所,大肆毁坏佛像、宝塔,把其改建为道观,并在社会上传播《老子化胡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从而引起佛道二教的激烈争论。元世祖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下旨命令佛道二家进行道家经典的真伪辩论,然后把道德经以外的其他道书通通烧毁,此后令祥迈撰写一本辨伪书。《辩伪录》的前半部分总共十四篇,是些对道家、道教各种虚伪说法的驳斥;后半部分记述了元朝定国号(1271年)前后佛道争斗的各种原委,后面还附有相关的文献。祥迈的辨伪,不属于人们常指的古籍辨伪,但形成了辨伪书籍。他的《辩伪录》对人们辨别真伪道家经典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对人们辨别真伪儒家经典和当代书籍也有(方法上的)借鉴作用。
元代学者在辨伪方面的贡献,包括对整本古籍的通篇辨伪、在读书中对古籍词语的辨伪、针对当时一些“虚伪说法”的辨伪等多个方面。各个方面的直接辨伪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抑制着伪劣书籍的刻印与流行。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伪劣书籍的减少必然促动原著、好书的多刻与发行。另外,书籍辨伪搞得多了,必然会在社会上形成浓郁的辨伪之风,也会促使那些想暗中“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书商不得不收敛或减少伪劣书籍刻印。这样,书籍辨伪便起到了保护原著并维护著作者、传播者、读者受众权益的作用。
四、元代书籍校雠的辨伪作用
元代的另一种辨伪活动是对需刻书籍的校雠,当时的刻书都比较注重校雠。藏书家刘世常在其所藏《白虎通》上有一跋文,其中提到:“或谓是书中间多有鱼鲁之嫌。如首篇援《尚书》言迎子刘一事,即《尚书·顾命》考之,迎本作逆,其当时传写之误耶?借日初得旧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之,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学》以《尚书·尧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诗·熏民》秉彝作秉夷。谁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诵读岂无宗工巨儒者出?蔑有一人敢为改正。由是观之,《白虎通》亦犹是也。间有不安,尽从其旧。盖纂之者班固,汉时人去古未远,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尽知,后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轻议班固之述作。倘能知《礼记·缁衣》以《君牙》为‘君雅,《说命》为‘兑命之意,则能释鲁鱼之疑矣。昔人有云:‘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谈议汉儒,观书者试思之。”(卢文弨校刻《白虎通》)卢文弨在校刻《白虎通》时,特意附上这篇跋文而附题肯定说:“案古书不宜轻改,此论极是。”(卢文弨校刻《白虎通》)可见,元朝刘世常对待古书,其校雠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既承认或指出了《白虎通》中的文字误失,同时又主张用心去体会,不要轻易去修改。这一校雠见解是很有道理的,并不同执。还有吴师道(1283-1344年),字正传,兰溪人,著有《战国策校注》十卷。原《战国策》有宋姚宏、鲍彪为之补阙正误,吴师道选取姚、鲍的注解来参校,并引用其他书籍来考证。他在自己作的序言中认为:“事莫大于存古,学莫甚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又其所引之书,止于《淮南》《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吴师道著《战国策校注》)吴师道主张传疑存旧,虽然是对鲍彪而发的感言,却也可以说是个明通之论。他还提出了字多假借、音亦相通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既能上承汉儒,又为后人提供一种很好的辨伪校雠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师道的做法推荐道:“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日、正日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授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第,为彪所改窜者,别存于首。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益棼,节目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逐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之下,附著《别录》第几。林亿等新校《素问》,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几,即其例也。”吴师道将鲍彪窜改他人文字的部分,开列出来,记录在案,而不直接改动,使“变乱之迹”泯灭不见。这里所提及的体例,谨严详密,既不擅改鲍注的面貌,又能兼存刘、曾古本的次第,确实能够成为校勘古书的范例,在元代的校雠方面他应当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吴师道的做法,不仅维护了书籍作者的作品完整性权利,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读者的权利。刻印书籍中所采取的校雠做法,是一种很好的书籍辨伪方式。刻印一本书时,如能认真去校雠,就不会出现伪劣书籍。特别是由学者去校雠的书籍,所刻印出来一般是高质量的精品书籍。作为学者,见多识广,知识渊博,通过对需印刻书籍文字的校雠、辨伪,假冒窜改之迹无处藏身。通过书籍校雠,那些“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问题书籍也就无法刻印发行了。带有不良目的,用“改换名目、节略翻刻”他人书籍的做法,并不需要校雠。
五、政府的出版政策对版权保护的影响
元代的官刻书都要先呈请中书省批准,并由中书省详细审查后颁布牒文,然后才能刻印发行。《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中记载:“元时书籍皆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官刻书籍在出版时,必须由下上呈经过审查批准,这是一种严格的书籍刻印发行审批制度。关于元代官刻书籍皆须由下呈请批准出版这一制度,近代出版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也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又经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辗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元朝于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扬州设立江南行御史台,后迁往杭州,再迁到建康(今南京),下辖江南十道监司。各道监司称肃政廉访司,监治五六个或十几个路。各路儒学或州、县官署刊行书籍,需先向本路总管府申请,由路总管府转呈本道肃政廉访司而层层向上报批。例如:至正五年(1345年),抚州路儒学拟刊行虞集《道园类稿》50卷,先向抚州路总管府申报,经批准由路转呈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由该司主官肃政廉访使审核批准,再依次行文,交抚州路学去组织刻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平江路(苏州)儒学拟刊行《战国策》10卷,则先向平江路守镇分司申报由分司官佥事核准,再上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设于杭州)审查批准,然后逐级行文下达到平江路学去组织刻印。元代的官刻书由于是使用官府银钱等原因,审查批准手续就比较严格。这一官府批准手续等于给了出版者书籍刻印发行权。专有出版权在中世纪西方国家中有的用印刷许可证来表示。封建时代的出版专有权保护,也是版权保护的时代特征。在版权保护的(西方)皇家特权时代,政府用颁布专有许可证的方法来保护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它主要保护的是图书出版者的权益,而真正的作者权益还难以得到保护,这显示了版权保护的时代特征。
元代的部分私人著作是用官银去刻印的,私人提出刻书申请后先由地方绅士看过,然后报经当地主管官员审核批准,再上呈到上级管理部门,经其批准后才可以刻印,费用从各路钱粮或学田钱粮内开支。这种官银资助的办法,一方面保证了书籍刻印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减轻了私人著作出版的经济负担。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办法是元代官府钳制私人著作出版的做法,会限制一大批有价值著作的刻印发行。但因为元代的书籍出版政策总的来讲是较为宽松的,私人著作申请官银刻印,实际的核准过程大多是走个形式而已。应当看到,元代发放官银赞助部分私人著作的刻印,这是元代书籍出版业的一大特色,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
元代的书院刻书,质量都比较高。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一书中认为:“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刊行,三也。”明朝陆深在《金台纪闻》中也指出:“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人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则纠数处为之,以互易成帙,故校雠刻画,颇有精者,非以图鬻也。”这都表明,书院刻书追求精益求精。元代书籍刻印发行制度规定,书院山长的委任,必须先由行省札付部省,批准后才能移咨施行。具体委任时,按察司还必须对山长的工作进行必要的考核,然后上报都省,再由都省批准施行。由此可见,元代的书院刻书无论在人才选拔任用还是编校刻印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出版管理体制,保证了书籍的出版质量。那些“山长”“通儒”“学者”们精深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编校作风,以及“良工”们同样勤恳的工作实践,无疑都是书院刻书具有高质量的保证。这样的出版方式宋代也有,元代的书院出版方式是在宋代书院出版方式上有所发扬,从而很好地保证了书院所刻书籍都有较好的质量。
元代的书籍出版,主要是官刻,“元时书籍皆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说明元代的官刻实行“由下上陈”的管理制度,许多相关文献都有此记述。刻印私人著作,也可以申请官银资助。但私人著作若想获得官银资助出版,首先得向本路呈请,经过有关机构审核批准后,从各路钱粮或学田钱粮经费中支付开支。这样的书籍刻印,也是实行“由下上陈”的管理制度。元代的书院刻书,主持书刻事务的是山长,从“江南书院委任山长,必须先由行省札付部省,准拟,方才移咨施行”,以及私人向上申请刻书的部分费用可由学田钱粮内开支等情况来看,还是实行“由下上陈”的管理制度。总体来说,元代书籍刻印发行,实行的是“由下上陈”的书刻管理制度。“由下上陈”的书刻发行管理制度,符合封建时代版权保护特点。一方面,通过呈请一审查一批准的管理程序,在有“呈请与审批”的书刻范同内能确保翻刻的古籍不会是不法书商即时造假处理的产品。经过不法书商造假伪托的书籍,是不会被批准刻印的。另一方面.通过呈请一审查一批准的管理程序,在有“呈请与审批”的书刻范围内能确保元代较有名气的书籍不被“改换名目、节略翻刻”地刻印发行。经过“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书籍,是不可能被批准刻印的。如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官府不可能批准不法书商去改换名目翻刻或节略翻刻。与此同时,社会上大部分书籍的出版,都是“呈请与审批”的书刻,那留给“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等偷刻的空间就很有限,这对不良偷刻自然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