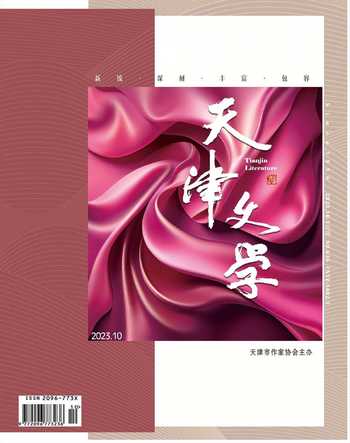萤河夜话
一个仲夏夜,我在随风摇曳的无边的芦苇地里走着,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由千万只萤火虫汇聚成的萤火河,真真切切地就在我的眼前。那时,不谙世事的我随教书的母亲一起,来到黄岩一个陌生的小村落“午尚洋”。学校坐落在田野上,低矮的屋檐,泥土的墙壁,光秃秃地裸露着它的冷漠与苍凉。透过古朴的窗棂,只见每个教室都空无一人,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桌凳……
学校开学后,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小伙伴,课余与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经常尽兴而归。在乡野的许多游戏里,最令我神往的莫过于夏夜追逐萤火虫。这些萤火虫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始终困惑着童年时的我。有好些夜晚,我和小伙伴们都迷醉于屋前、花旁、田畴、水沟……去追逐那一只只忽闪忽闪的流萤。这些萤火虫白天伏在墙隅或草丛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到了夜晚,它们就会飞起来,通体带着绿色的光。我们就用一只小玻璃瓶去装,每捉到一只就把它装进瓶里。不过,捉的时候还须小心翼翼,若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会机敏地飞走。慢慢捉的多了,那装有萤火虫的瓶子就犹如一盏小灯笼,可以照见前面黑暗的路途。我们每次去捉,都有收获,总会捉到满满的一瓶子萤火虫。尔后,把它们带回家,放在枕边细细欣赏,然后随它们入梦。
在乡下的夜晚,我喜欢听母亲讲故事,“囊萤夜读”便是其中一个。晋代吏部尚书车胤从小家境贫寒,晚上点不起油灯,就捉来一些萤火虫放在透明的袋子里,借萤光读书。传说有一天风大雨急,捉不到萤火虫了,无法读书,车胤则长叹:“老天不让我达到完成学习的目的啊!”一会儿,飞来一只特大的萤火虫神奇地落在窗户上,照着车胤读书。车胤“萤窗苦学”,最终成为著名学者。萤火虫成就了车胤一生的学业,为他的前途送去了一片光明。这动听的故事,以后一直伴随我的生活,并不断鞭策着我。
稍大后,已经不会再追着萤火虫跑了,也不再去捉萤火虫了,反而喜欢安静地看它们慢慢地飞舞,欣赏它们美妙的舞蹈。我认为自由的萤火虫比静止的更为美丽。每回看着它们舞蹈,我觉得自己也会入梦,那一闪一烁,仿佛带有不可磨灭的梦幻色彩。我的心中,也就只有芦苇荡里的那一片萤火河……听居住村里的老人们讲:每年都有着这样一个魅惑人的夏夜,成千上万的萤火虫不断飞来,在这片芦苇荡汇成一条光明浩荡的萤火河。可惜的是,我一直都没有看见过一大群的萤火虫,大多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只或数只萤火虫,在草丛,在田野间,在所有可以存在的地方,孤单地飞舞。于是一有空闲,我就苦苦地守候着村里这片芦苇荡,等待萤火河从夜色里显现。我对自己说,假如萤火河真的出现,我才会相信很多东西不是梦。
在无数次等待之后,奇迹果然出现。小小的萤火虫,穿过漆黑的夜色,一只一只地向芦苇荡飞来,十只百只,千只万只……很快形成了萤火河和那神秘的光带。
那是一幅多么瑰丽的画面,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光带在清风明月下不停地颤动,时而出现在平静的水面,时而在野花和晃动的影子间闪烁……光带逐渐像明亮的河水般离我愈来愈近,先是漫过了河岸,漫过了芦苇,漫过了林梢,最后向我迎面扑来。我很快被萤火包裹了起来,通体透明,耳畔传来的全是沙沙的振翅声。我真真实实地看到了萤火河,并和萤火虫融合在一起了。我是萤火虫,萤火虫是我。我欣喜万分,目睹奇迹的来临,奇迹确实变成了现实。我终于相信很多东西不是梦。
多年后的今天,遥远儿时的萤火河,它的光芒一直照亮我的生命。
水中的天堂
在这个距离海最近的地方,一次次头枕涛声入梦,人影、鱼影和月影,便构成家园最温馨的色调。
在台州湾生活多年,我每天都在呼吸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只要一有空,我就去海边听涛声,在沙滩上叠沙,在飘然的风里叠沙,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城。
寂寞的人,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观海,犹如一匹马,好似一只鹰,即使孤独到老到死,也要在水一方追逐云彩,留住花草清香。还喜欢徘徊在故乡的谷仓前,任凭远来的风和薄暮,掀起衣角的牵念。
家住东海边,天天忙着采风和赶稿。除了读书、看报、写诗外,有时发现自己,别的什么都不会。闲下来的日子,才有好心情去檐前听雨声,傻傻地看水中的鱼和水草,在“云中”自由穿行。它们也与我们一样,都在追求生命的本色,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些年,河水、江水和海水,多多少少发生了一点变化,可鱼们不甘失败,仍然在台州湾急流勇进。除了鱼们,还有身边许多熟悉的人和事,刚不久还是好好的,说消失就消失了,谁同意他们这样做的?我环顾四周,人们在流泪,没有人同意他们这样做。他们累了,就不想走了。随风而逝的,还有别的大大小小的记忆。漫步于东海岸时,我就会告诉自己,我不能因为我改变不了的事,就停滞不前。
我的台州湾很小,小如一朵岩衣,依在地球的怀抱。它是古代断裂河谷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敞式的河口湾,呈喇叭形向外延伸。水是它的生命,它与水生死相依,鱼儿是孩子,整日在它身边追逐和嬉戏。听着水声长大的人,在东海边住得久了,就把自己当作岩衣,把岩衣当作自己。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一朵岩衣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着许多美丽的奇迹。
还记得年少时的我们,在雨后初晴的岩坡上,一起去看海。指尖滑落下雨滴,小心翼翼地,怕它惊动了青石苔上跃动着的生命。有时跟随乡人去“讨小海”,看到岩壁上不断长出一只只可爱的小耳朵。那是一簇簇岩衣,长在南方海边湿漉漉的地方,那么卑贱,而又沉默地绿着。它们似乎在聆听大海的歌谣,向往远处的风景。只要你足够心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看上去,这些岩衣的外面颜色,与石崖崖壁没多少区别,但里边却藏着蓝色柔软的东西。最大的一朵,恐怕比巴掌还要大。
采岩衣回家后,母亲就把它们泡入水中,用手反复搓洗,像平日洗家人的脏衣服。再放入锅里煮,很快就端上了桌。那时在碗里上下浮动的,不仅仅是岩衣,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故乡的海是波澜壮阔的,而海的故乡又在哪里呢?一次次,我站在东海岸上,极目远眺,海铺天盖地见不到边际,那么一大片黄色的海水,就是像天一样大的幕布。涨潮时节,海水咆哮着、翻滚着,铺天盖地砸向海岸,大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势。
岸上有好多人家,他们熟识这儿的水域,如同熟识自己的掌纹。他们的建筑独具特色,石屋、石街、石巷和石阶,随地势升降而修筑,错落有致……青石老屋,墨色翘檐,粗大的木梁悬挂着打鱼的家当,有些很有年头,是我们的老渔夫祖父传下来的。它们在暮雨晨风里轻晃,好像能看懂人的心事。
我的台州湾很小,小如一枚贝壳,一次次被海潮送上岸,又一次次被浪花卷走。这儿好多人爱去海边,去寻找那枚自以为最美的贝壳。其实在每一枚贝壳内,都藏着一种心情、一段文字或一个故事。作为一枚完整的生命,壳带着核随波逐流,漂洋过海。在一次次与风浪的搏击里,他们始终紧紧拥抱,相依相伴,不离不弃。或许有那么一天,一个巨浪把他们分开,壳与核从此天各一方。那个核离开壳后,便成为鱼类的美味佳肴。而壳始终在守护那份约定,在大海的怀抱里,苦苦寻找着另一半。从棱角分明和光彩照人,一直到现在壁薄体轻和满脸沧桑,或许这就是现实中很多人所要经历的爱情吧!
在台州湾畔捡贝壳,我还发现在阳光、砂粒和海浪的淘洗下,贝壳内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消失。唯留有几滴海水在里面,那是大海送给贝壳最后的礼物,也是大海流下的伤心的泪。儿时的喜欢只是单纯的追求,多年后的今天,才明白深藏其中的禅意。
我的台州湾很小,小如一只寄居蟹,在这个时空里,它只是偶然地与宇宙天地擦身而过。我们背着一只只沉重的壳,生活在这儿,以为那是真实的。可是蓦然回首,发现只不过是一些梦的影子罢了!这时,它让我想起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玫瑰奇迹》:“我们是寄居于时间大海洋边的寄居蟹,踽踽终日,不断寻找着更大、更合适的壳。直到有一天,我们无力再走了,把壳还给世界。一开始就没有壳,到最后也归于空无,这是生命的实景,我与我的肉身只是淡淡地擦身而过。”
但是,比起东海边寄居蟹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和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把我所能做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地一丝不苟呢?
对于台州湾,其实我不比一只盘旋其上的飞鸟看得全面,也不会比鱼虾蟹螺更熟悉它的性情。人与海相处很多年,竟没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有朝一日坐下来好好谈谈吧。想必海肯定有许多话要对人说,尤其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海肯定比人要看得清楚。
最美的时光
在寂寥的冬日,书房是我心灵的一片栖息地。我在这儿寻觅一种梦想,一种精神的归宿,还有一种灵魂深处涌动的向往。
乡村和城市,就像我画笔下的不同风景。它们都小心地被我珍藏在时光里,所有的存在和消失、幸福和灾难、喜悦和忧伤,一切都散落于滚滚红尘间。
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乡村,再从城市到城市。就像一直走下去,没有始点,也找不到终点的那些永远回不去的路。
在我眼里,萦绕于心的乡村,是宁静、闲适和单调的,是一种慢,像月光下的一首朦胧诗;而城市是喧闹、动荡和丰富的,是一种快,像一首通俗歌曲,更像激流澎湃的摇滚乐。哪一种生活都不可或缺,哪一种生活都充满了母性的关怀,在呼唤那些浪迹天涯游子的回归。
我早就记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日子,穿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了。每回看到河流和浮萍,还有与我一起漂浮而过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地方,回顾风雨兼程路,那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由此而形成的想法是:我们既属于乡村,也属于城市;同样的,我们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始终在路上,像极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周而复始,疲于奔命。而我居然深爱着这种貌似悲怆、实则欢快的命运,甘为漂萍,拒绝扎根,不想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长久。
“羽村”就像一片轻盈的羽毛,飘落于江南大地,它是我快乐的老家。这儿留有我的成长记录,还有童年难忘的记忆。一生勤劳俭朴的父母,在工作学习之余,颇爱在田间地头种庄稼看墒情谈农事,享受简单而知足的生活。
在这个似乎被遗忘的村庄,春天到了,鸟儿们就纷纷衔着泥巴和枝草,辛勤地搭建自己的舒适小窝,以安家栖身。或因了每天的朝夕相处,这些鸟并不怕人。特别是燕子,不是站在枝梢上呢喃,就是在窗棂前与你对话。闲来无事,我喜欢聆听它们的天籁,或注视天边不断掠过的黑色鸟影。
在南方村庄,燕子是吉祥的象征,它在谁家筑巢,就会带来幸福与安详。因此在村庄不同的屋檐下,大伙儿都不会轻易地去计较燕子在家里垒窝。况且,时时看着它们穿着燕尾服轻灵的身影,聆听呢喃之声,享受简单的美,也是一种幸福。
父母也学起“春来燕衔泥”,衔回了春光,筑起了温暖。每次在田野上疯跑后回家,我都会注视着他们,搬来砖木,然后用石灰砌起白色的墙垣,很快新房上栋梁。每一道工序都那么仔细,那么专注地做着,不经意间,两只“燕子”终于完成筑巢任务……
我少时很顽皮,但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我喜欢去河边芳草地上,折几根草茎,制作成项链和戒指戴着;或行走在父亲的庄稼地里,抓几把番薯藤或野花,编织成头环,做一回大地的新娘;有时没零食可吃,那便嚼菜根……这些很可能是对“百事可做”理想的一种追求,上升到今天的理论,大概就叫“个人有意识”吧!
有时我就叼着一根胡萝卜,坐在堂前的门槛上看闲书。胡萝卜、青萝卜和白萝卜先后入口,嚼着,它们各有不同风味。每每进入忘情的地步,只有母亲多次督促吃饭的声音,才把我从书本的沉迷中拉回。
现在想起小时候嚼菜根,那种淡而有味的生活,也颇值得人去留恋。似乎许多菜根都能嚼得,而且还蛮有味道。记得父母常说:“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大哲理往往是家常语,直到多年后方才悟出。父母留下的这句话,是深蕴禅机的。它并不是动员人们专去吃菜根,而是教人不怕吃苦,就像明代洪应明著《菜根谭》这书,而非谈菜根一样。
之后追随父亲的踪影,母亲工作也调动了,我们举家迁徙到城市。在这儿后发现,城市里的人,都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他们仅需站在一个点上,做一样的动作,获得一样的货币,便可饱暖终生。他们吃粮,不是到田里去播种然后收获,而是到粮店或商场去买;他们吃菜,也不是到院子里去采摘,而是到菜市场去买;他们劳动,是在经过社会化综合与分工的流水线上的某一点,重复某一动作,直至终生……
城里又有了一个家和新生活,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这儿认成自己的家。认定这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或许到老也无法把这个地方真正认成家。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始终是无法看到的。
有人说,这世间所有不经意的想起,便是匆匆那年,时间里的人、事、物、语。但那些时光总会流逝,记忆也总会淡去,最终一切都将被我留在时光深处。乡村仍然在不断包围城市,同时被城市渗透和蔓延,它们就犹如我画笔下的两种不同的风景。而我却一厢情愿地希望,乡村永远和城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保留住属于自己的清新和宁静,就像捍卫我的另一种生活。
陈伟华,笔名宛桦,《台州日报》记者,曾出版散文诗集《蔷薇飘飘》。多篇散文和散文诗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和发表。曾获中国散文诗大奖赛“女娲奖”;“201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走近民间艺术家”浙江省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