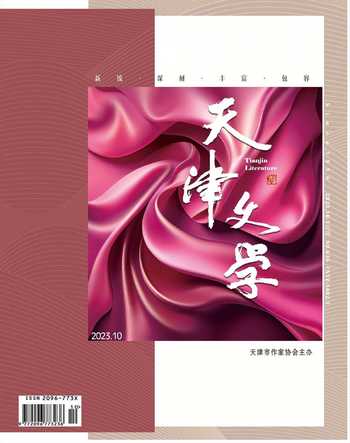大地目睹了一切(创作谈)
汤成难
我们村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从村庄的任何一面走出去,都能看到远处一条由麦田(或稻田)与天空构成的虚淡的地平线。当然,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我看到的,如今那些曾是地平线的地方早已被厂房代替。
我對童年的记忆大多与农忙有关,从白墙上把镰刀取下来、坐在井边磨刀开始,到割麦、脱粒、扬场、翻晒、堆草垛等等,我熟悉每一道工序,哪些活计需要男人去做,哪些是女人完成,哪些由孩子分担,分工似乎早已约定俗成。
很少有谁家独自完成农忙的,都是你帮我几天,我帮你几天,共同完成抢收。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在地里干活的大人送食物,我们这儿称“二顿儿”。挎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烧饼、油条或粽子,另加一锅稀饭和几只空碗。把食物放到田埂上,大人们陆陆续续收起镰刀走过来了,我喜欢坐在他们之中,也拿起一块烧饼或油条,舀一碗稀饭,嘴在碗边咻出“哧溜溜”的声响。
吃完不会立即下田,而是在田埂上说说笑笑歇会儿。我喜欢听大人们闲聊,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像皮球一样在他们之间弹跳着,回旋着,平日里原本端着饭碗在树下或某个墙脚闲聊的场景移植到了田间。只是玩笑的尺度更大了,笑声更放肆了,这与劳动强度成正比吧。
我绝没有美化劳动的意思,深知“夏收掉层皮”的辛苦。完成了割麦,整个农忙才下来大半。夜里是不回去的,睡在打谷场上,四周麦把儿堆积如山,鼻子里是泥土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我陪爷爷在麦垛上过夜,临睡前听大人们不紧不慢地聊天,不知不觉困倦起来。天没亮,有人醒了,但没爬起身来——身子骨还散着呢,继续躺在麦堆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再过些年,有了麦客,他们从北方过来,南方庄稼比北方成熟得早,麦客们便从南往北一路割回去,割到家,自家的庄稼也成熟了。麦客们操着我们不太听得懂的方言,我们那儿一律称北方人叫“侉子”,这词在乡邻的口中不具有贬义,几乎可看作一种昵称。侉子们在谁家割麦就住在谁家,说是住,不过是在堂屋里打个地铺而已。
一亩田大约三五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也不过十几元,因为都是种地的农民,这场“生意”显得十分质朴和单纯,麦客与主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抢收,如一家人。如果不是请麦客帮忙割麦,这种与陌生人共同生活的经历我们是不会有的,北方的麦客拓宽了我们孩子的世界,好像那个只在书本上看过的城市突然亲近或熟悉了。
再后来,有了收割机,一切都交给机器,不再看到一群人坐在田埂上说笑的画面了,麦客不见了,打谷场消失了,石碾子不知所踪。
前年,我把自己在城里的房子卖了,搬到了乡下。院墙外面的荒地里就有一只石碾子,问邻居,原来这儿以前正是打谷场。
我的窗外是一片麦田,从头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夏天,麦子由青转黄,再变成金黄。我目睹了时间的脚步。割麦的季节到了,窗外麦田里人们的闲聊与笑声像豆荚里的豆子一样炸裂。我无法专注于手中的书,于是合上书,向他们走去。那块地有点儿丘陵的意思,面积小,收割机也进不来,只能人工收割。我加入他们,拿起镰刀一起干活。歇下来的空档,也坐在田埂上,吃着他们带来的食物,突然有些恍惚。
有一天,我在一页旧报上看到了“麦客”二字,突然一惊,这个词仿佛与这个词所代表的那群人正在消失。我仍然要说明,我不是为劳动或乡村唱起赞歌,而是想写下时代变迁中人的情感变化,以及农耕文化被工业文明代替后那些消亡的部分。
小说是虚构的,或许,这篇创作谈也是我虚构的,唯有“麦客”这个词,以及这个词代指的那群人才是真实。
大地由青转黄,再由黄转青,麦子见证了一切。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