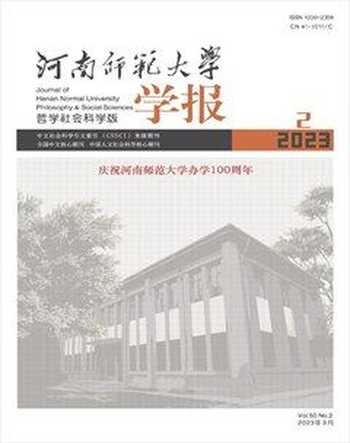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文体的创生
摘 要:在20世纪90年代,文体新变是中长篇小说比较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时期的小说叙事在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奇”“诗歌”“戏曲”等文体资源,呈现出“文备众体”的特征。与此相适应,这些小说在叙事上由“叙述”转向“说话”,并于“闲聊”“絮语”之中,表现出鲜明的杂糅化特征。这些小说在文体和语体上探索实践对其叙事结构产生影响,不仅使其获得了“完整时间长度”,也使其拥有了“共时态”的叙事空间,展现出了时空体组合的特征。
关键词:小说;叙事文体;叙事语体;叙事结构
作者简介:李御娇(1982-),女,湖北巴东人,文学博士,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8XZW029)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2-0100-07
收稿日期:2022-08-19
“文体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发表方式的聚合物”[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贺麦晓认为正是不同文体之间的竞争,才推动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文学体制与机制的巨变。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大量创制,20世纪90年代中长篇小说的繁荣创作成为了独特的风景,文体新变成为这些中长篇小说较显著的特征,文体问题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美学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家们用现代之“灯”烛照昏暗、幽深的乡土和“藏污纳垢”的民间,他们化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传统文体资源,用现代意识创化各类野史杂传和传奇故事,杂糅和并置多种语体,使之呈现出了复杂的时空结构。
一、混合式叙事文体
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叙事在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化用传统文学中的传奇、戏剧、戏曲、话本、诗歌、赋、寓言等文体资源,呈现出“文备众体”的特征。
(一)“文备众体”
“我尝试了以老式的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盖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苏童:《红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07页。]苏童从先锋的形式实验中抽身而退,在传统故事中找到了叙事基点。但当他返归传统时,所得到的不仅是“老式的故事”和题材,更是传统的“旧衣裳”——一种新的文体与语体。从传统小说叙事中获取文体资源,并非始于苏童,也不是苏童一人的追求,它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情结”之一。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格非、东西、张炜、余华、李锐和刘恒等作家都具有强烈的文体变革意识。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条阐释民俗文化事项,延展出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文学性故事”,“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词典体小说,而这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陈思和:《新时期文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1页。]。王安忆也是文体的自觉实践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就不断创新文体观念,这使她能始终站在小说叙事变革的最前沿,《长恨歌》可以算得上是她在文体方面的重大创获。絮语体和闲聊体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所呈现出的胡同、闺阁、鸽群、片场等沪上特有风情,活现了王琦瑶和蒋丽莉等人的传奇人生。贾平凹深得传统文学神韵,并对说话、评书、闲聊等文体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小说大多在原生态和生活流叙事中追求写实、张扬“意象”,是一种独特叙事诗学的呈现。从《废都》到《秦腔》,贾平凹延续和创化传统文体资源,把古典小说的“说话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叙事层次。《废都》算得上是“说话体”的典型文本,及至《秦腔》,“说话”则成为“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得到了细密、绵实的呈现。贾平凹在“闲聊体”叙事之路上越走越远,“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显然,文体观念的改变导致了贾平凹小说在叙事上的整体变革。“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也体现在一些中篇小说当中。格非《傻瓜的诗篇》把诗歌、叙事融合在一起,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将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技巧与叙事文体结合,均是“文备众体”的典型范例。张承志曾说,“新的形式就是再生的原初形式”[萧夏林:《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心灵史〉》,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无论是“回归”还是“返祖”,这些小说在叙事上的“文备众体”特征,不仅从形制意义上完成了对传统文体资源的创化,也从结构和语体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文体叙事诗学的修复。
(二)“传奇”体
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传奇”倾向的小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家们对叙事的传奇性追求则更加突出。《米》堪称是“五龙传奇”,小说中一无所有的底层农人走入城市,以隐忍、迎合和屈辱为代价获得了财富与权力,然而在完成种种复仇后,他却在归乡的途中死去。这是一种野史杂传式的传奇叙事,它回归本土语境,以传奇的笔法写本土故事的方法,也可称为一种俗化的“传奇”。如此来看,格非的《敌人》可称为“赵少忠传奇”,莫言《檀香刑》可称为“赵小甲传奇”,王安忆《长恨歌》可称为“王琦瑶传奇”,等等。
所谓“传奇”,简单而言,即是关于“奇人”与“奇事”的叙述。因为具有“奇”的特性,小说往往呈现出荒诞和怪诞的色彩。历史上的传奇分为前传奇、传奇和后传奇,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魏晋、唐和宋元明清时期。传奇和后传奇融合而成的“混合式”传奇文体,是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的主导性文体之一。作家们化用明清“后传奇”文体,并突出了“后传奇”的文体特性。苏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兼有“雅化”和“俗化”的基调,这与他主要创化的“后传奇”文体相关,这些小说一方面尽量追求通俗化和世俗化的效果,比较明显地借鉴了宋话本和拟话本的叙事特点,另一方面又避免不了高雅化和精英化的叙事情节,最终呈现出一种雅俗互渗、雅俗共赏的文体特征。贾平凹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化用了“后传奇”文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故事性的追求就一直是其小说叙事的主要特色,但繁密的故事并没有冲淡其小说叙事所具备的史传性,且散文化和诗化的叙事选择,又使他的小说叙事呈现出少有的诗学趣味。《高老庄》《秦腔》《古炉》等小说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除此之外,新写实小说也呈现出了这方面的叙事特征。有研究者称,“‘新写实小说实际上是以‘反传奇的面目实现了对‘传奇的创造性转化”[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5页。]。由于存在主义文化视野的获得,新写实小说沉浸于对“生活流”的呈现,这些小说在和缓、平淡的叙事中为普通人立传,尽管这些小说旨在突出日常伦理和平民意蕴,主人公身上也几乎没有了传奇色彩,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主人公仍然是以传主的身份被看待的,所以,围绕他们所展开的故事情节仍免不了一定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是“反传奇”的传奇性。作为深得先锋神韵的“新生代”,新女性作家不僅熟悉现代叙事技法,而且拥有与男性作家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她们既讲父权的败落,也说自我的经验。凭借“后传奇”式的叙事,她们写出了男权的卑劣无能,“弑父”与“恋父”的狂欢,隐性的意识空间,以及隐秘的生活经验。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期的“后传奇”叙事,大都以野史杂传为宗,不再追求哲理和抒情的意味。陈染《私人生活》《无处告别》,林白《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羽蛇》都是这样的典型文本。“新生代”作家毕飞宇、东西和麦家所创作的小说也有类似的特征。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上深得明清“后传奇”的古韵,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王老炳的传奇,至于麦家《解密》,容金珍的人生事迹则堪称是一段传奇。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王老炳一家人的残疾既是作为个体的残疾人的辛酸故事,也是在现代性冲击下,个体在传统农业社会解体过程中命运遭际的一种象征性叙事。在《解密》中,容金珍的成长之路由于他罹患肾病而发生了变化,更因为他所罹患的精神分裂症而失去了人生前途,将这些偶然要素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无疑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效果。
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小说几乎一边倒地化用“传奇”文学传统,但在处理“传”与“奇”的关系上,作家们的思考并不一致。“传”大于“奇”的小说多接通古典小说中的“多中心”结构,常常专注于“俗中见雅”风格的创造之中;“传”“奇”兼备的小说,更具生命悲剧的意味;“奇”大于“传”的小说往往能“雅中见俗”,也更显出一种罗曼司色彩[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1页。]。总之,这时期作家有意于叙事中的传奇要素,他们追求的是“传”奇而不是传“奇”,所谓“传”大于奇,或者“传”“奇”并重。这些小说既强调传统的“史传”精神,又注重人物的心理写实,并在粗细相间、虚实互现之中,把民族传统叙事资源与现代叙事技法精妙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在叙事过程中“传”与“奇”的融合与统一。
二、杂糅化叙事语体
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叙事语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杂语”倾向,方言、口语、俚语、母语、书面语、标准语、外来语,以及戏剧语言、说话语言、闲聊语言等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的语言复调和狂欢效果。“统一的民族语内部”,分解成各种语言、行话和职业话语,这些“社会性杂语”和“独特的多声现象”,使得作家们能自如地驾驭题材、描绘实物,以及表现“文意”。巴赫金认为,小说就是按照一定的艺术法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页。]。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叙事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2页。],它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敞开,这使得叙述者和小说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说话”权利。
(一)從“叙述”到“说话”
在小说《檀香刑》中,赵小甲是一个身强体壮、力大无穷的人,但是,他的力气除了用在杀猪卖肉之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他的妻子孙眉娘视其为窝囊废,竟然和县太爷钱丁暗度陈仓、两情相悦。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赵小甲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通过一根虎须,即能洞见钱丁、孙眉娘和孙丙等人的“兽性”本质。赵小甲后来作为助手配合赵甲对孙丙施行“檀香刑”,与作为监斩官的县太爷钱丁共会于刑场,此时,父亲、岳父和情敌的同时在场,瞬间将亲情、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冲突推向高潮,小说的戏剧性因素由此被推向极致,刑场也同时演变成为剧场。赵小甲的“娃娃腔”和“娃娃调”式的“说话”对小说的戏剧性效果无疑具有强化的功能。譬如,在第三章,叙述者就为读者展示了赵小甲的“娃娃腔”:
俺姓赵,名小甲,清早起来笑哈哈。(这傻瓜!)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白虎到俺家。白虎身穿小红袄,腚上翘着一根大尾巴。(哈哈哈)大尾巴大尾巴大尾巴。白虎与俺对面坐,张嘴龇出大白牙。大白牙大白牙大白牙。(哈哈哈)白虎你要吃俺吗?白虎说:肥猪肥羊吃不完,吃你个傻瓜干什么。既然你不把俺来吃,到俺家来干什么。白虎说:赵小甲,你听着,听说你想虎须想得要发疯,今天俺,送上门来让你拔。(哈哈哈,真是一个大傻瓜!)[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这段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说话”,颇合韵文的声律,是赵小甲特殊思维的语言表达。这是一段简单、断裂和碎片化的记忆,也是一段缺乏逻辑的思维和夸大内涵的语词之间的组合。这一语体特征在第十七章“小甲放歌”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红衣大炮呼隆隆,晴天里响雷刮大风——咪呜咪呜咪呜——跟着爹爹来执刑……有爹真好——有爹真好咪呜咪呜——爹爹说杀人要比杀猪好,乐得俺一蹦三尺高——呜哩嗷嗷呜哩嗷……油条里有股血味道,好比一只小死耗——咪呜咪呜咪呜——牛肉也有血味道,也是一只小死耗——呜哩嗷嗷呜哩嗷——檀木楔子早煮好,在肥猪身上练过了,爹爹把着俺手教,爹的手艺高。就等着孙丙到,往他的腚上钉木楔,钉木楔呀钉木楔钉木楔——咪呜咪呜咪呜……又是那通灵虎须显了灵,俺眼前的景物全变了。一个人种也没有了,校场上全是些猪狗马牛、狼虫虎豹,还有一个大鳖乘坐着八人轿。他就是袁世凯那个老杂毛。别看他的官儿大,比起俺爹差远了——咪呜咪呜咪呜——喵——[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
根据这段引文可知,赵小甲傻子般的呓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说话”,它道出了赵小甲随父亲赵甲来到行刑现场观看檀香刑的整个过程。这种“说话”带着儿童般的好奇,使惨烈的生命悲剧转化为一场狂欢的喜剧。一个高密东北乡猫腔戏的传承人被施以“檀香刑”的悲剧场面,由此不再具有震撼和启蒙的效应,留下来的只有类似于赵小甲“娃娃调”式的喜剧化了的氛围。《檀香刑》中的“小甲傻话”和“小甲放歌”都突出地体现了语体的变化,一个傻子所经历、所见证的现实,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被其独白式的“说话”和高密东北乡特有的方言土语——猫腔敞开。猫腔特有的韵文属性不仅增加了语言的形式感,也突出了语体的独特性。尤其当它以第一人称“我”来表现的时候,这种“说话”就更具有了非凡的艺术品质。莫言在小说中融合使用日常生活化的语言、地方语、韵文和猫腔,确立起这一时期小说叙事语体的杂糅化范式。
贾平凹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把“说话”作为小说的语体去追求。贾平凹曾说,“小说是一种说话”,是一种“新的说法”。那么,所谓的“新”如何在小说中加以体现呢?贾平凹认为,小说要达到“新的说法”,至少要突破三种“说话”成规:一是民间说书人式的“说话”。这种“说话”惯用“插科打诨”“制造悬念”的叙事技法,以获得“哗众取宠”“渲染气氛”和“煽情”的效果,这是古代章回小说常用的语体。二是政治报告式的“说话”。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者从不同的视角剖析问题,“拿腔捏调”“慢慢地抿茶”,有意控制情绪节奏,说到动情处“慷慨陈词”,用肢体语言强化“说话”效果,迫使听者也随之“心有灵犀”“心照不宣”,譬如,“革命英雄传奇”等小说就运用了这种说话体制。三是“洋化”式的“说话”。顾名思义,“洋化”的说话是借鉴西方小说的说话体制,注重对叙述者说话技巧、人称、视角、空间、时间、节奏等形式要素的处理,此时,“说什么”被“怎么说”替代,说话策略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说话”方式不仅构筑了复杂的叙事“圈套”“迷宫”,而且迷惑了听者,造成说者和听者的隔阂[贾平凹:《白夜》,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贾平凹对以上三种“说话”方式都是极力排斥的。他喜欢没有技巧的“说话”,那种“围炉夜话”的方式,常常能把故事娓娓道来,它们“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这样的小事,“话”的是那些平平淡淡、鸡零狗碎的生活细节。当然,“说话”语体并不仅限于莫言和贾平凹的小说,余华、阿来、韩少功和王安忆等人的小说中也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说话”语体。《活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福贵向读者将他自己的生存挣扎、苦难记忆和生死离别等人生细节娓娓道来。一个垂垂老者在回忆自己由富而败的一生时,却能举重若轻地放下心中的千斤重担,以平和、平静的心态讲述出来,正得益于这种语体的使用。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经常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依靠对这些人类元命题不停地追问,阿来创作出了属于这部小说独特的“说话”形式。韩少功《马桥词典》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语体,它的突出标志就是对方言的大量使用,这是马桥人“说话”方式的逼真体现。正是通过这篇小说的语体展示,中国的一个荒凉偏僻山村所使用的语言,得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呈现。
小说叙事语体从“叙述”到“说话”功能的变化是当代小说语言范式的一种根本转换。这种转换有着复杂的原因,譬如,作家身份、文学功能、消费文化语境,等等。但是,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主要还是由于小说主导人物的变化引起的。小说主导人物从英雄式人物向平民化、丑角化人物的转换,必然会带来小说叙事视角、人称、立场、结构、文体和语体的一系列变化。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都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说话”必然是生活化、碎片化的“说话”,是有关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的“说话”。从人称视角来看,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的人称视角几乎都由第三人称叙事转向了第一人称叙事,这无疑给“说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正如申丹所说:“使用‘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者更‘天经地义地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原因正在于他就是主人公。”[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二)闲聊与絮语
《废都》中的老太太是一个“怪人”,50多岁时就没了丈夫,她从60岁起开始糊涂,但是到了80多岁的时候却能窥见阴阳。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老人,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说话”者。说到“热”,她滔滔不绝,完全没有了庄之蝶说话的余地:“这热什么呢!我年轻的时候天才叫热的,六月六就炸了红日头,家家挂了丝绸被褥晒……你爷爷却夹了伞从村巷里走,一句话不说的,村里人赶紧收拾衣服,紧收拾慢收拾,雨就哗哗啦啦下来了!现今天不热了,你觉得热是心热,你蘸口唾沫涂在奶头上就不热的。”[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8页。]庄之蝶插不上话,她又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之蝶呀,刚才你爹回来了,就坐在你坐的那地方,给我说他泼烦,说他的新来的邻居不是好邻居,小两口整天价吵,孩子也顽皮,常过来偷吃他的馍馍。你给你爹点一炷香吧。”[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8页。]老太太的“说话”,远不止于上述的“喋喋不休”。作为一个拥有了话语权利的“说话”者,她所说的话完全是拉拉杂杂的“话语”碎片,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修饰,它就是平实的生活流、细节流。这样的“说话”语体实际上是一种闲聊体,它是贾平凹自《废都》开始极力实践的语体。在《白夜·后记》中,贾平凹曾这样说,“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贾平凹:《白夜》,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37-338页。]。一如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平常心、平常视角,以及平常的听众,这是拉家常般的娓娓道来。贾平凹认为这是故事本身的技巧,它与那种依靠“拿腔捏调”而获得的说话效果完全不同。
王安忆《长恨歌》也有着闲聊的语体特征。蒋丽莉罹患癌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与她的人生经历以及她争强好胜的性格相关,也与她最终在失去了对王琦瑶的所有心理优势后、孤注一掷地以求补偿有关。在肝癌晚期,蒋丽莉唯有无限喟叹“我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王琦瑶的安慰和自况也适时而来,“你倒霉,我就更倒霉了。多少不如意都是压抑着,此时翻肠倒肚地涌上来,涌上来也是白搭,任凭怎么都挽回不了的”[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王琦瑶与严师母、毛毛娘舅、萨沙和康明逊等人之间的围炉夜话、打牌品茶,都是在鸡毛蒜皮般的闲聊中进行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主导人物从英雄向凡人甚至残疾人的变换,为“说话”体进入小说叙事提供了可能。第一人称视角的普遍采用,使得主导人物拥有了自由的“说话”权利。此外,方言、土语、白話,以及地方腔和戏曲等语体普遍受到作家们的重视,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杂语”化的美学特征。
三、时空体叙事结构
作家们在文体和语体上的探索实践对小说的叙事结构产生了影响。譬如,“传奇”文体会要求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与其匹配,这就对叙事时间的时长、时序等产生影响;小说中的人物一旦有了自由“说话”的权利,他的叙事空间就不得不有所延展。巴赫金认为,“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展现在空间里”,空间则“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小说的这种时间和空间交互、嵌入和汇流的关系,就是巴赫金所言的“时空体”。在这个“时空体”中,时间与空间不再被分割开来,形式与内容交叉融合,它是现实、历史、价值的投射与辐射,是“不同寻常的时空规模”,同时也是历史的动力、冲力和巧力所延伸、裂变和创化的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巴赫金从历史诗学的视野探讨了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把长篇小说视为一个混合式的“时空体”,从而把小说叙事研究上升到了诗学与美学的层面,并以此构建了历史诗学。从“时空体”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不仅获得了“完整时间长度”,也拥有了不同寻常的“共时态”的叙事空间。
(一)具有“完整长度”的时间叙事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端白从人间的帝王转变为遁世的隐士,他曾经拥有一切,但此时却一无所有。从“入世”层面来看,这是端白的权力和名利的下降,从“遁世”层面来看,他却由此获得了精神和灵魂的上升。“完整时间长度”所蕴含的时间意识使个体生命意识得到了空前突出,但这样的生命又注定是一种无可把握、具有悲剧性质的宿命。与端白的人生命运相似,余华《活着》中的福贵也走过了一条从腰缠万贯到一无所有的人生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样因“身体的下降”而获得了“灵魂的上升”。活在“过去”的福贵,由于吃喝嫖赌、好逸恶劳而耗尽家财,然而,当参透了人生只为“活着而活着”的时候,他便开始有勇气、有底气地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设置中,生与死、疾病与健康、病态与健全不断地进行着比照与对话,“完整长度”的时间观念影响了叙事的情感、节奏和格调,《活着》由此成为人生苦难历程的一个象征,呈现出比较深刻的悲剧美学意味。
格非《敌人》叙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赵家的全部财产被一场大火烧掉,“谁是纵火者”一直是赵家几代人无法弄清楚的终极问题。赵少忠成为家长后,“敌人”仍然没有下落,但对“敌人的恐惧和想象”彻底压垮了赵少忠,他在无意识中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孙子,家族的延续也由此被“中断”了。这样一个历时几代人的“完整长度”的时间修辞,凸显了传统社会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这个结构中的“轮回”和“常在”使小说具有了突出的悲剧色彩。余华说,“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时间过去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学》,1989年第5期。]。在余华看来,小说中的时间并非从过去走向将来,而是“过去”和“将来”互为表象、相依相存和相互映照,“过去”通过“现在”得到了延续,“现在”则依托“过去”得到了存在。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也使用了“完整长度”的时间修辞。一个从青年到壮年、中年再到老年的底层市民,为了家人的生存,前后十二次卖血,随着许三观卖血节奏的加快,小说的悲剧意味也逐渐变得浓郁,血站最终因为许三观年迈不要他的血了。作家以这样的叙事表达了对底层农民生存苦难的悲悯之情。
王安忆《长恨歌》中“完整长度”的时间叙事是通过两个主导人物来体现的。王琦瑶,一个有着美丽容颜、魔鬼身材的胡同女孩戏剧般地“遇上”了爱情,却又阴差阳错地“失去”它,最终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蜗居胡同深处,与邻里好友靠着“围炉夜话”来消磨时光。这是一个沉湎于日常生活、善良而温情的女人,并没有获得命运之神的垂青。她以“上海芯”的平常心逃过了重重劫难,却在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文化大潮中被“一只大手”夺去了生命,这是人生悲剧的另一种书写。同时,“完整长度”的时间修辞也带来了另外一个主导人物——蒋丽莉的人生悲剧。一个平凡的女孩,在寻找对闺蜜王琦瑶的“精神胜利”失败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企图重得心理补偿,但是在“革命的第二天”,她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找到优越感,反而在不间断的“革命”中耗尽了生命。她们都是社会的“局外人”,并且都在历史的变化曲折中喟叹人生,展现出了“长恨”的姿态。
(二)“共时态”的空间叙事结构
“不同时间的东西被堆放在同一空间或平面中”,是“某种歪斜的、扭曲的、拼贴的、过分的以及失真的状态”[陈晓明:《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实际上,结构是一种空间,也是文体的核心,依托不同的结构,文体才有不同的形态。这不仅契合了小说空间叙事的主题,也是对文体研究的一种映照。“树状”与“块茎”是古代“讲史”的两大结构模式[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8页。]。德勒兹把小说思维分为“树状”和“块茎”两种思维,认为前者是“国家思维”,后者是“游牧式思维”[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28-133页。],并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消解,具有消解中心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中,单体式“树状”结构和组合式“块茎”结构得以修复,越来越多的小说家采用上述结构模式进行叙事,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复调特征。
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叙述不乏单体式“树状”结构。苏童的《米》围绕五龙这个主导人物形象展开叙事,他从“枫杨树故乡”来,又回到“枫杨树故乡”去,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他的人生就像浮梦一般。格非《敌人》也是单体式叙事结构,小说叙述主要围绕赵少忠的“无意识”展开,无法找到“敌人”却又时时感受到“敌人”的存在,这种巨大的“恐惧”最终压垮了赵少忠,这种“对恐惧的恐惧”正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象。叶兆言《十字铺》、余华《活着》《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和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小说也都是单体式叙事结构。
但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更多地体现为组合式“块茎”结构。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檀香刑》和王安忆《长恨歌》等小说都属于这一类型。《废都》多中心、多形态的叙事,赋予了小说人物特定的行动和思想,它们之間交互错杂,为小说建构了一种网状叙事结构。莫言《酒国》中的三条叙事线索交汇于侏儒症叙事,余一尺也就是“一尺余”,从躯体上是婴儿的同类。他先验般地“停止了生长”,却有着奇迹般的“智慧”和“精明”——为食客送上残忍的宴席,这是人类全部兽性与恶性的折光和映像。《檀香刑》是莫言另外的一部杰出小说,这种杰出集中地体现在小说对组合式空间叙事结构的采用上。“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安排是与赵小甲这一形象的存在相关的。他以自白、独白和地方戏——猫腔叙事,使小说呈现出了荒诞的色彩,他所见证的“檀香刑”和“围观”文化,正如他借用一根虎须所窥见的人的兽性本质一样,都是“文明”的恶性。其中几个主导人物以第一人称“我”叙事,构成了相对独立又互为犄角的叙事单元,使得小说具有了复调的空间叙事结构。此外,李锐《无风之树》中第一人称的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交相呈现,也形成了组合式“块茎”叙事结构。韩少功《马桥词典》和张炜《九月寓言》等小说的叙事结构也都是组合式的。
90年代小说叙事化用传统文体资源,把章回体、哲思体、寓言体、戏剧体、闲聊体和叙事体等文体融为一体,又在一定程度上把叙事剧本化、蒙太奇化和奇观化,体现出文体的狂欢、复调意味。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李锐、韩少功、史铁生和张炜等作家的小说叙事都使用了组合结构。组合式结构是一种叙事空间,它能形成一种复调式的空间化叙事。由多条线索、多重叙事构造的叙事文本,因“共时性”的空间并置、聚合与排列,而具有了戏剧、喜剧和狂欢的性质。“文辞以体制为先。”[朱乔森:《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页。]文体是人们用语言符号对话、交流时呈现出来的“具体的言语形式”和“功能变体”。与日常语言的“文体”不同,小说的“文体”是一种“审美功能变体”,它是从真实与虚构结合的层面上,探讨叙事带来的观念之变和文学审美取向与形态之变。从根本意义上来看,文体又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文本结构形式”“符号的编码方式”[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它也是文本艺术品质、美学蕴涵,以及作家生活感受、生命经验、美学精神的折射。莫言说,文体似“铁笼”,作家如“呆鸟”,“呆鸟”力图突破笼子,撞大了笼子,扩大了空间。即使有一天把笼子撞破了,也“依然无法飞入蓝天”,不过是飞进了一个“更大的笼子”而已。“新文体的形成,非朝夕之功,一旦形成,总要稳定很长的时期,总要有它的规范——笼子”[莫言:《会唱歌的墙》,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莫言形象地把作家突破文体比喻为鸟撞“笼子”,作家总是依赖一定的文体创作,服从文体规范,但时间长了,总有“九头鸟”式的作家寻求某种突破,去寻找、创造具有更大美学空间和艺术品质的文体。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敞开。随着作家个体化、民间立场、边缘身份的确立,由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语境推动的食色欲望和本能冲动,以及生命意识和生存体验,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书写。它们的出现推动了宏大、中心、王者视野和“元话语”的解体。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小说叙事的变化问题是一个文体问题。断裂式、阶段化和区段化的时间修辞,被“完整长度”“人文主义”和“永恒循环论模式”的时间观念取代,个体和民间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延展。小说叙事以空前的速度和频率,转化了传统小说中的时间修辞资源,使得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完整时间长度的叙事”在获得“自由自在”涵义的同时,确立起了生命本体论的时间意识和修辞观念。它们和“共时态”的空间叙事所构成的复调叙事,与“文备众体”“传奇”所形成的混合式文体,以及由“闲聊”“絮语”“独白”“说话”所构成的杂糅化语体,一起构建出了具有感伤主义特征的生命本体论的悲剧美学。
On the Cre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Chinese Novels in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Li Yujiao
(Hubei Minzu University,Enshi 445000,China)
Abstract:In the 1990s, the creative change of literary styl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latively distinct features of medium-length and full-length novels.In the course of drawing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the novel narratives in that period transformed creatively the stylistic resources, such as legends, poetry and opera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us yielding the mixed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style isomorph (MSI)”, a regenerated literal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e.Rigidly in concor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SI and legend, the narrative style of novel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hybrid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alk and slang from “narration” to “talking”.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so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novels. In general, the narrative of the 1990s novels not only obtained a “complete length of time”, but also had an unusual “synchronic” narrative space,demonst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time combination.
Key words:novels;blended narrative style;hybrid narrative style;narrative structure
[責任编校 海 林]